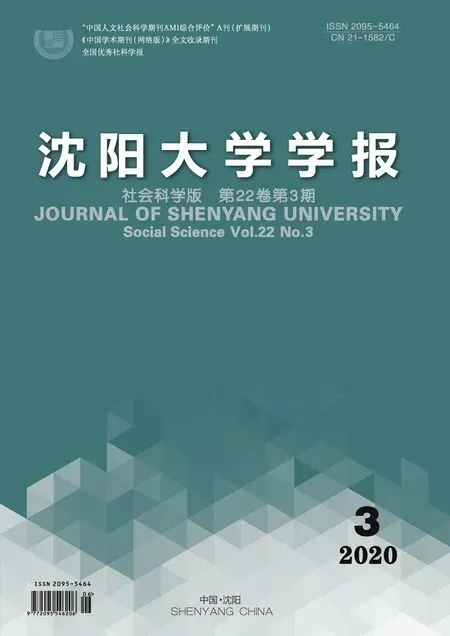勘界、越界、心理化:埃德加·爱伦·坡小说中的空间营造
岳 俊 辉
(合肥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近年来,学界从多重视角组构了埃德加·爱伦·坡作品中的空间图景。学者们或从文化视角建构包含都市景观、大众媒体和异位想象等“三重空间”[1],或结合叙事学、地形学理论分析其地形学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等[2],或从心理学视角评估其哥特式建筑空间对恐惧心理,以及身份的建构作用,或据刑侦学界定罪案现场,解析杜宾系列小说中的犯罪空间特征。最新成果是菲利普斯(Philip E. Phillips)主编的论文集《坡与空间》(Poe and Place),结集的15篇论文从地理学、虚拟性和想象性三方面探讨了坡作品中的空间叙事。以上研究探析了坡作品空间的内涵、成因、特征等论域,丰富了其叙事维度,深化了其空间话语。
但是,上述研究多致力于空间本体的呈现,未触及界限这一空间的核心问题域。界限是空间成型的基础性工程。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建构更离不开界限勘定,因为后者直接规范着空间的质性和场域。坡文本中惯常描绘的密闭空间展示了作者用文字“勘定”界限的不懈努力。而对于坡的界限意识有何特征,如何运作,学界鲜有论及。众所周知,坡注重分析人物心理,但人物必处一定空间,而心理与空间的交互机制已入空间心理学研究域,也可成为理解坡文本及其效果的新法门。此外,空间历来与权力关系紧密。空间是权力运作的重要载体,是权力运行的场域,是体现权力的效应和工具[3]。作为微观权力要素的集聚之地,空间配置其场域内的资源,参与文本效果的塑形。坡小说重视界限勘定,暗含权力运行的逻辑机制,关联文本效果的实现途径。权力视角有助于分析空间权力的形成与交互机制,完善文本研究的空间维度,为深入认知爱伦·坡的叙事艺术带来新机遇。
鉴于此,本文从坡作品中的空间书写入手,考量勘界的叙事意义,透析其为“图”加“框”的界限逻辑,阐明空间及其权力的营造策略,进而解析作品中的越界事件,指出越界隐匿的“区隔-融合”双向矛盾运动在建构空间及其权力的同时,也注解了“统一效果”美学。最后分析空间与居者心理的协同机制,指出心理化是其空间营造与效果内化的重要技术手段,拓展了坡文本的空间内涵,以期从权力视角呈现坡小说的空间营造技艺。
一、 勘界:基础营造
坡文本中的空间多与世隔绝、封闭窒息,有阴森的城堡、阁楼、钟楼,也有狭窄的房间、地下室、墓穴、棺椁等。此类空间需界限来建构场域环境。作者作为文本的总设计师,勘定界限,为人物虚构适宜的空间环境是其必备技术,而像坡这样推崇“统一效果”的作家更不例外。坡的“勘界”技术体现于其营造法式中。
1.针对内部装饰和空间变换两个方面
详细描写空间内部针对内部装饰和空间变换两个方面。罗伯托·卡格里罗(Roberto Cagliero)认为坡的空间可分为装饰性、哥特式和隐喻性3类[4],他详析了后两者,而忽视了装饰性空间对效果的建构作用。而在坡看来,内部装饰惟“繁复”才能“美”[5],对空间效果建构意义重大,因此其作品中的内部描写随处可见。《丽姬娅》中大段的空间描写渲染了叙述者的婚房既华贵又透出阴森恐怖,没有任何新婚的温馨祥和[2]477。《厄舍古屋的倒塌》(以下简称《厄》)中叙述者详细列举了看到的“物件”[6],通过“物”叙事营造了古宅的颓败与腐朽。《幽会》《莫雷娜》《陷坑与钟摆》《椭圆形画像》《一桶蒙蒂利亚白葡萄酒》(以下简称《酒》)《贝蕾妮丝》《死荫》《威廉·威尔逊》等作品中的窗帘地毯、家具摆设、形状布局等都有详细的空间描写,如房间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印证了主人的神经质症状,那个房间的所有细节赋予室内一切一种恐怖不安的生动[7]。可见内部装饰是坡细描之所在,唯美之表征,能调动空间韵味和氛围,影响居者。
坡在文本中不断勘定界限,推进空间变换,通过“气氛-空间”的一体建构,营造了“气氛充注的空间”[8]。在《酒》中,蒙特雷索和福尔图纳托沿着长长的盘旋式阶梯行至地窖,又穿过由尸骨和大小酒桶堆成的一道道墙,经过一连串低矮的拱道,向下,往前,再向下,最后进了一个幽深的墓穴,另一个更小的墓穴,然后到达一个更小的凹洞,这个凶杀的罪案现场。可见,空间不断缩小,位置层层下坠,阴森的死亡效果也随之不断强化而最终弥漫整个地窖。作者不断收紧的空间,层层充注死亡氛围,反向建构、逐步强化为读者营造的窒息感。《厄》中“我”先沿着一条短短的堤道来到哥特式的大厅拱门,穿过昏暗而曲折的回廊,来到罗德里克的房间,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种凛然、钝重、驱赶不散的阴郁[7]12。然后是安放玛德琳的地窖,这里已经多年未打开过,气味令人窒息。地窖正处“我”所居房间的正下方,可见,小说借空间描写导入破败、死亡气氛,通过位置变换逐步强化。以内部描写勘定边界,使空间成型、效果产生。
2.设置参照空间,协助构建核心空间
《红死魔的面具》中所有的欢乐和平安都在墙内,墙外则是“红死病”的天下[7]53。院墙内外的对照显而易见。红死病最终降临正是故事的高潮,也是墙内恐怖氛围顶峰之时。墙内是核心空间,而墙外空间参照并营造了墙内因被围困而致的压抑氛围,讽刺了人们对红死病的低估。《酒》提及两位主人公在狂欢节高潮期的一天傍晚、夜幕降临的府邸之外相遇。狂欢节的府邸之外是坡设置的参照空间。狂欢意味着暂时搁置规则,无需对行为负责,而傍晚所预示的黑暗便于掩盖罪行,因此惩罚他人之后自己可以不受惩罚[7]25。参照空间进而引发对核心空间地窖内杀人事件的伦理质疑,增加读者对生命危险处境的担忧,强化了恐怖氛围。《威廉·威尔逊》中一周只能见两次墙外的世界,而每次大门打开就会发现许多奥秘,许多值得认真观察也更值得严肃思索的事务[7]139。校外空间还包括如罗马、莫斯科、马德里等威尔逊所到之处,也是其被跟踪之处。可见,这些空间无非是校内空间的外延,服务于故事的神秘氛围。总之,这些由非中心物件构建的参照空间,协助生成了空间图像性,使坡能够为读者提供通过个人化、主观的方式描绘一种情景的心理意象所必须的东西[9]。
描写内部旨在给定场域,设置参照空间实为规划空间,两者都离不开勘定界限,界限也由此成为坡空间话语的核心。坡曾指出,空间界限的封闭对于单个事件之效果极其必要:其作用如画框之于图画[10]。其意义体现在,框界暂时区分了内、外,因此“图”寓言了内界与外界的关联,建构了内外互指且共生的关系。界限规划了空间范围,同时也生成了内、外对立,或一种权力掌控的策略。勘界首先是设定规范,以强制性、否定性的范围界定实现空间权力的生成。同时以建构性、扩张性边界逐渐扩张其作用领域的界限,凭借自身,有效地构成了规范适用的经验场[11],培育权力外溢的合理渠道,为越界提供可能。
勘界是空间建构的基本技术、生成权力的一种策略。空间权力一方面有赖于界限的勘定,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场域。在其中,居者无处逃遁,被赋予一种绝对化权力。福柯曾指出,禁闭已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12]。禁闭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空间权力化的例子,是权力运行的结果。[3]73密闭空间隔绝内部,界内因受专权之力而成为权力客体,变成权力化的空间。另一方面,权力又需逾越界限,展示其“力”本质。可见,勘定界限实际上是作者施行效果魔法,使文本具有“万有引力”,通过空间权力的凝固和挥发,营造其预设的“气氛”。
爱伦·坡细描内部,设置参照空间,通过勘定边界规划场域,实现了空间与效果的一体化建构。其勘界行为设计了内、外相依的形态,促进了空间权力生成。同时也正是源于对界限的依赖,其空间营造必涉及界限的设立或移除等基础性建构技术。权力也需借助界限叙事来显现。越界事件意义重大,因此成为理解坡空间叙事的密匙。
二、 越界:权力强化
卡伦·格伦伯格(Karen Gumberg)在分析《红死魔的面具》时指出,修道院不能表达人类经验的最基本和确定的结构之一:空间的内外二重性[13], 将其看成是修道院必须灭亡的原因。但需注意二重性,生于内、外相互依存的逻辑关系,随时转换。按照坡的画框理论,框介于画与非画的结合部,随时承接并转换着两者的关系。框的跨界性为阐释图画提供了多重可能,为空间越界创造了机会。基于界限的空间型构同时生成了越界可能,越界也成为空间权力运行的标志性事件。界限排斥差异使无差异集聚,而成为特定类型的空间。而差异存活于边界,由界限所标志,在于对既有疆界的不断跨越[14]。越界也由此成为探索坡空间及其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基点。
坡的很多作品都描绘了“界限时刻”。《红死魔的面具》中舞会的场所是城堡内的蓝、紫、绿、橘、白、紫罗兰6个颜色的房间,而黑色的房间无人敢入,凡进入该房间的人无不吓得魂飞魄散。作者已经在暗示黑色房间的排他性及对生命的不友好。空间界限已被清晰建构。但普洛斯佩罗倒毙后,人们一哄而上冲进了黑色的房间,界限被打破,结果他们一个接一个倒在血泊里。作为世俗权力象征的王子逃遁于代表宗教神权的修道院,本身就表征了世俗空间对宗教空间的逾越。红死魔穿行于两个空间,打破了修道院内、外界限,消弭了宗教权力庇护下的世俗权力。此外,红死魔是死亡的象征,王子及大臣则是普世生命,而红死魔的杀戮体现了死亡对生命权力的终极僭越。
《钟楼里的魔鬼》中自治城严格按照钟面格式建造,居民生活严格按时间安排,可见时间型构了小城空间,成为控制空间的权力象征。小丑是破坏小城“时空体”及其隐形权力的 “他者”,严重威胁了城内的秩序“中心”:他闯入钟楼,乱拨大钟,暴打守钟人,扰乱市民的生活。其他作品也不同程度的涉及越界,包括《威廉·威尔逊》中精神对肉体的越界戕害,《凹凸山的传说》和《与一具木乃伊的对话》中古代与现代、现实与历史的跨界穿梭,《莫诺斯与尤拉的对话》《催眠启示录》《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的死亡与再生的跨界幻想,以及《黑猫》《泄密的心》和《威廉·威尔逊》中对善、恶心理的跨界拟态。
一方面,越界行为暂时移除界限,实现了空间内外的互通及演化,放大了其权力范围。《红死魔的面具》中,红死魔混迹于修道院没被察觉,直到午夜才显露真容。被认为固若金汤的修道院早已遭渗透,被熔死的大门形同虚设,其所表征的界限被悄无声息地移除。这种外部力量代表了内部空间的最内部,弥散于内部空间。但这种“移除”展示了死亡对生命的压迫及人类难以逃避的恐惧。血液是其(红死魔)保证,而生命本身就是红死魔,是人类难逃的宿命。生命与红死病是一体两面,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钟楼里的魔鬼》中,小丑进入自治城,寓意移除了空间界限。外来者大闹钟楼并痛打守钟人,越界破坏了自治城的时间秩序,展示了秩序缺失后的混乱,秩序则借助短暂的越界操演显示了权力的“威严”。罗杰·弗克拉兹(Roger Forclaz)认为人物的这种自我分裂实际上是对空间感的另类处理,由此也生成了一个黑暗的中介性世界。模糊了的界限及被拉黑的“中介性世界”为坡小说中即将上演的恐怖布置好了场景。越界勾连了各相关方,扩展了空间场域,使基于界限的分裂关系演化为融合性的共生关系,为拓展权力场域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越界强化了空间边界, 操演了空间权力。封死修道院“大门”是勘界的典型表征,而院内房间分割更说明了界限的区隔功能。正是越界才使其他房间的色彩得以显现,黑色房间的恐怖才得以强化。红死魔降临表征了死亡对生命的威胁,强化了死亡空间的无限边界。若非小丑越界,秩序对居民的控制程度则无法界定。自治城的边界在小丑的越界擅闯中强化,其所表征的时空权力中心被小丑的异者身份所跨越,使居民意识到秩序的重要性。可见,界限只有在被侵犯时,空间区隔才得以清晰勾画,权力也因此得以强化。
越界其实演示了一种双向矛盾运动,在消解边界、破坏原有空间的同时,生成了一种临界于界限的新的间隙空间。间隙空间作为处于异位的镜子发挥功能,为主体性的边界提供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地带[15]。这一空间成为主体投射自身的新的场域所在,越界由此也生成了自我发现和指认的崭新视角,为空间心理化提供了理论支持。
坡小说中的越界事件在移除、强化界限的过程中呈现了权力的运作和关系的演化。可以说,越界是坡借以推进故事的主要抓手,通过移除和强化这一双向矛盾运动进行空间的实体化和虚拟化营造,拓展了空间内涵,彰显了其权力运作。
三、 心理化:效果内渗
除了越界,空间心理化是坡空间书写的另一重要方面。坡小说除布置封闭环境、营造统一效果外,还探讨了空间与个体的同构关系,藉由心理化,规划了空间对居者和读者心理产生作用的策略,开辟了空间内在化的建构路径。
众所周知,坡被认为是将哥特小说向内在化方面发展最突出的作家[16]。“内在化”就是指对人物心理的关注。坡实现了心理描写与外界环境的匹配,构建了一个内、外协同的共同体。坡笔下的房间不单单是无序的排列,每一空间建筑都精心挑选以匹配居住者的性格,从而使其能够接驳人物心理,助力读者窥见其精神状态,揭示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恐惧和不安。
空间与居者心理的联动效应在坡小说中处处可见。厄舍府阴郁、顿重,这与宅院、宅院主人公认的特性完全相符。厄舍府所受的影响是一种由灰墙和塔楼的外观及映出灰墙和塔楼的那湖死水最终给他的精神状态造成的影响[7]。汤普森(Thompson)更认为厄舍府最终沉入湖中就是在与自我以外的稳定现实结构链接的努力失败后,理性部分沉入内心的虚无的一种体现。小说表现了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精神世界间的知觉或者互动[17]39。《红死魔的面具》中,黑色房间让人心生恐惧,房间内的大钟更是让人心惊胆寒。钟声是大钟、甚至房间隐形权力的象征,居者对钟声的恐惧与对黑色房间的恐惧如出一辙。居者的心理与房间及其钟表时间定时共振、完美融合。《酒》从入口、楼梯、地窖、大墓穴、小墓穴,直到仅能容身的凹洞,让福图那多沿着盘旋的阶梯往下走,直至欺骗和死亡,而非走向灵魂的升华[18]。空间渐缩,死亡渐明,空间与内心的关联渐趋明显。《幽会》中灵魂在香火中扭曲,房间的装饰、家具的风格、布局及窗户玻璃和窗帘等的杂糅预置了主人公的心智混乱及服毒自杀的结局。
空间影响居者心理,居者也通过心理建构空间,两者同源同构,跨界联动,促空间心理化。文本建构的空间是主人公内心、情感变化的一种回声,空间与居者同一,成为后者是心理具象。同一是同源同构的变换机制,而不是面积完全对等的几何重叠。空间提供心理规划的基础,心理赋予空间以动态形构和效果,可以说心理化提供了物理空间的拓扑结构,进而扩展了文本效果。而读者的任务就是去探寻并建构自己个性化的拓扑空间,文本的多维空间也由此被建构出来。
空间控制居者心理,影响读者对文本的接受。一方面,居者心理被掌控,空间演化成个体心理的具象,与之协同形成心理化空间。此过程在逻辑上打通了心理情境与物质现实的通道,为两者的互动铺垫基石。个体心理模拟空间,形成相应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空间,也驱动居者认同空间及其权力。空间规训个体心理,成为一个被教养技术所支配的社会[19]。权力施于居者,通过心理作用使其抽象化,剔除具体或固定主体,而泛化受力客体,使居者及读者都服从于其影响。坡作品的人物与空间匹配的心理情境就是空间权力作用于居者的结果和直接体现。
另一方面,空间心理化实现了对读者心理的控制。读者在阅读中会认同与自己类似的居者,并通过居者的视角来观看周围,而且坡常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也无疑强化了这一角色认同。居者是空间作用的结果,而对居者有先天认同的读者心理必然也带有其权力作用痕迹。心理化空间通过控制居者影射心理,进而影响读者。作家主导的文学叙述层面与读者主导的阐释层面间的“圆桶配对法”完美体现了坡读者的资格要求,而坡作为短篇小说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则恰恰在于其强烈的读者换位意识[20]。有人认为坡的室内恐怖小说有意识地削弱无所畏惧、独断专行的自我,展示了一种非美学或道德的、野蛮的、奇特的、非人性的审美具体化的倾向[21],这不无道理。坡凸显了人物的空间存在及其读者代理人的角色定位,制造灵魂的恐怖,反映了心理学上所说的人性的矛盾和分裂[22]。
在坡文本中,空间心理化推进了读者与居者、文本等深层融合,放大文本之于读者的效果,促进囚徒叙事(captivity narrative)或诱拐文学(abduction literature)[23]的生成。空间与居者的心理协同交互,体现了权力对个体的规训。空间通过心理渗透控制个体行为,进而促进效果内渗。总之,在坡文本中,居者是空间的产物,而空间又是其心理的反映,两者同一正体现了坡徘徊于人类心理模糊界限、对读者实现精神控制的尝试。
四、 结 语
埃德加·爱伦·坡的文本严格勘界,细描内部,建构参照空间,一体化建构空间及其权力。越界事件在消弭、强化界限的隐形操作中凸显了空间权力的运作,拓展了文学表现的广度和深度[24]。空间心理化实现了空间与居者心理、读者心理的同一,促文本效果内渗。坡展现出高超的空间建造技艺,不愧是高明的文本“建筑师”,其营造法式建构了独具界限特色的空间话语,可深化理解其作品中的空间,全面把握其创作实践及美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