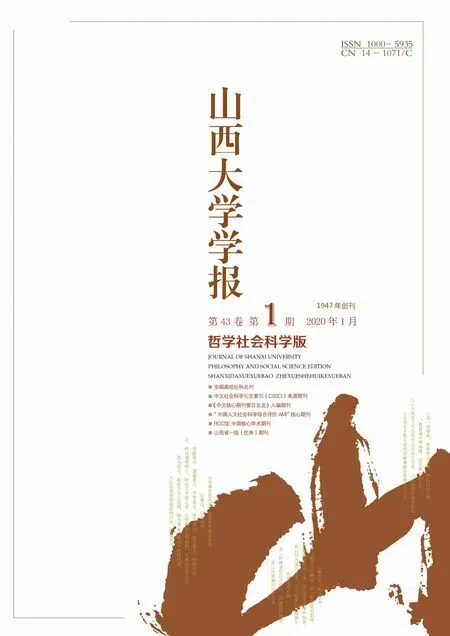新时期初期的“外国文学”形象
——对《外国文艺》创刊号的研究
李建立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同“新时期文学”本身的复杂构成过程一样,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形象也不是一次性地形成的,而是随着语境的不断变化被逐步建构起来的。同时,这一过程也不是简单地以日积月累的方式发生的,而是经常出现“突变”情形。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笔者在翻阅“内部发行”时期的《外国文艺》(1978—1980)(1)《外国文艺》创刊于1978年7月,1980年第3期前为内部发行时期,共出刊12期,之后改为公开发行。时,“震惊”地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展开之前,居然川端康成、索尔·贝娄、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萨特、帕斯捷尔纳克、福克纳、索尔仁尼琴等等在“新时期文学”不同文类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已经赫然在目。要知道,到了1982年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还相当激烈,到底要不要向“现代派”学习仍属悬而未决的问题;另外一个事实是,这里列举的大部分作家迟至1985年后才在中国作家和批评家中产生实质性影响。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译介“过早”地出现?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会牵涉到外国文学译介为“新时期文学”提供的多种可能性这一话题。本文要关注的对象正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特别是对这些译介的先知先觉色彩的疑问:当时的译介行为所秉持的标尺是什么?是一种文学观念上的冒失之举带来的意外收获,还是某种外在力量导致的结构性后果?在知识形态上留下了哪些话语争夺的痕迹?其中潜藏的意识形态内涵是什么?在社会语境出现大变动之际,是怎样的机制保障了这些译介的进行?创刊于1978年的外国文学译介期刊《外国文艺》曾在“新时期”产生过重要影响,本文尝试以其创刊号为例,对“外国文学”形象在新时期初期重新被建构的情形进行分析。
一 译介对象:作为新尺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外国文学”(2)套用划分近代以来的历史时段的惯例,“外国文学”可以粗疏地分为外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古代”文学两个阶段。后者不是《外国文艺》译介的主要对象,所以这里所谓的《外国文艺》中的“外国文学”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的外国“现当代”文学。不用“外国现代文学”是因为这个概念易和“现代主义文学”弄混;不用“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是此概念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内涵;而不用“当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则是在学科建制上少有这样的划分。不过,本文在引证史料和行文中,这几个概念仍会出现,但其含义相类于此处的“外国文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同质的或单一的概念。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之交,全球显在的意识形态斗争仍然相当激烈,加之当时中国正处于较为特殊的历史时刻,刊物选择译介哪些国家的文学作品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某种潜在政治立场的暴露。按照当时的分类标准,可供选择的译介对象除了外国古典文学外,还包括如下非常常见但互有交叉的三类:第一、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第二、亚非拉文学;第三、西方“现当代文学”。按照20世纪50—70年代的“传统”,前两种被认为是“优秀”和“进步”的,最后一种则是需要批判的危险品,在政治上最不“正确”。当时的译介活动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处理世界政治格局划分带来的文学等级关系。(3)参见:杨水远.同一性思维与中国20世纪50—70年代文论的一元化[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99-105。
在这方面,《外国文艺》有一个成功的榜样,即此前1977年复刊的《世界文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世界文学》主要以“介绍和评论当代和现代的外国文学为主”,在编辑方针上,它把“全世界最革命和最有生命力的文学,是世界文学发展方向”的“无产阶级文学”和亚非拉文学作为首要的译介对象,具体的选择标尺是在坚持政治标准第一和首先重视革命题材的前提下做到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1]很显然,这是一条相当稳妥的编译路线,也使得《世界文学》在复刊后很快就获准公开发行(1978年10月)。实际上,在《外国文艺》的创刊号(1978年7月)上,也有专家为刊物指出了这条“明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的。对于亚非拉和其他地区全国人民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我们必须多多介绍”[2]。
但不管是内部发行时期,还是公开发行之后,《外国文艺》从来没有提出过如《世界文学》那样明确的编辑方针。创刊号是交代编辑方针或译介标尺的最好时机,编辑们却有违常识,始终没有提供显明的讯息。创刊号上唯一一篇带有“宣言”性质的“编后记”写得含含糊糊,提到的译介动机和《世界文学》差不了多少:为了“认识和了解外国的社会现状以及文艺的发展演变趋向”,并按照当时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批判其中“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以利于“我们在斗争中锻炼人民,提高识别力”。[3]言尽于此,似乎没能提供更多的东西,但需要解读的恰恰是看似空白的地方——《外国文艺》没有说而《世界文学》说了的那些内容。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世界文学》提出了要借鉴、学习和了解无产阶级的部分,《外国文艺》只字未提。也就是说,它要译介的,很可能是处于当时“外国文学”等级底层的西方“现当代文学”;同时,它也不打算通过突出“无产阶级文学”的方法来“打压”它的译介对象,而是要将后者置于主要地位。
选择西方“现当代文学”作为主要译介对象,实际上将刊物置于了一个特殊的境地——这意味着《外国文艺》失去了一个容易把握的、可依凭的译介标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了。话虽如此,《外国文艺》仍然需要在译介中有相对统一的标尺,否则刊物的面目将显得过于模糊,进而影响到刊物作用的发挥和读者群的稳定。那么,在回避了前面提到的“外国文学”分类的尺度之后,它要依凭怎样的标尺呢?
在《外国文艺》创刊号上,这个标尺未被明示。于是,当时的读者同时也是后来的文学研究者就对创刊号产生了这样的认识:“看得出这期目录是经过编辑精心设计的,从空间上的东方到西方,从时间上的20年代到60年代,从形式上的剧本、诗歌到长篇小说,从内容上的现代到后现代,可以说是相当丰富和全面”[4]。按照这种说法,似乎尽可能地囊括不同的空间、大跨度的时段以及作家、作品、文体、内容上的多样,是《外国文艺》创刊号选择译介对象的标尺。实则不然。
如果换个角度去阅读这期目录(参见文后所附“《外国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目录”),会发现所谓“精心设计”的“丰富和全面”背后,隐藏的却是高度的“单一”:该期共翻译了四名作家的作品,其中三名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蒙塔莱和拒绝受奖的萨特,共179页,占作品部分总页数的73.7%;不唯如此,该期使用了27页的篇幅介绍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和获奖者”。二者共占整个刊物总页数的64.3%,也就是说,“诺贝尔文学奖”占据了整个创刊号一半还要多的篇幅。在此后的《外国文艺》中,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主的多种外国文学奖项成为《外国文艺》及时追踪和译介的对象,仅仅在内部发行的12期刊物中,就编译了川端康成、蒙塔莱、萨特、阿莱桑德雷、索尔·贝娄、帕斯捷尔纳克、加西亚·马尔克斯、海明威、福克纳、辛格、索尔仁尼琴、莫拉维亚等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作品。(4)读者也注意到了《外国文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刘心武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感慨《外国文艺》“在那个年代里”能很及时地介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创作“是难能可贵的”,他举例说在《外国文艺》创刊后的第3期在1978年11月出刊,但“更为及时地报道了仅仅在1978年十月才揭晓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新消息”。见:刘心武.滴水可知海味[M]∥作家谈译文.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61。除此之外,还译介了没能获得诺贝尔奖的博尔赫斯,并专门编发了外国评论家为之鸣不平的文章《从诺贝尔奖金谈到博尔赫斯》(5)在《外国文艺》1979年第1期上,选译了四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并配发了美国评论家理·依德尔的长篇文章《从诺贝尔奖金谈到博尔赫斯》。。
在这次介绍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料中,编写者在诺贝尔的遗嘱之后加上了一句话,指出所谓的“理想倾向”是“有着政治倾向”的。且不去分辨这是一句善意的提醒还是规避风险的策略之语,单单看看这种“政治倾向”的后果就足以令人深思。当《外国文艺》的选目遍布诺贝尔文学奖和欧美评论家的眼光时,它所译介的“外国现当代文学”具有了隐晦却重大的意识形态内涵。(6)需要说明的是,《外国文艺》上之所以当时能发表一些带有“先知先觉”色彩的翻译作品,很可能和“文革”中“内部发行”的包括《摘译》在内的译介刊物有关。由于这方面的资料匮乏,目前只能存而不论。一位读者曾非常深情地谈起了自己对这个《外国文艺》的“外国文学”的接受:“我感激这份杂志是因为它在那个亟待精神营养的时代里及时地在我面前展开了一个新的艺术世界,或者更准确一些说,是把我溶化到这个世界里去,以致使我发现了自己的心灵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新世界:一种属于现代社会环境里的精神状态”[5]。也就是说,这个艺术世界的“新”使其被认定为这才是“现代”的,是“现代社会环境里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在和这样的“现代”的比照中,这位读者很明确地将自己刚刚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现实定位为处于“蒙昧状态”[5]的前现代。“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不再是两种文学类型的标签,而因为某种价值观念的掺入使得前者在和“现代”社会径直对接中赢得了优先权,后者在这个新的“空间”划分中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与此同时,一种相异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将原有其他的方式排挤了出去,原来的阐释系统和抚慰机制也被取代:“原来像是打量一个陌生人那样的眼光会变得温柔,因为你最终发现了这个陌生人就是你自己。不是那个陌生人不存在,而是你没有发现;就像是现代主义思潮以并不孤独的方式传达出‘人是孤独的’信息,但人之孤独是早于现代主义思潮就孤独地存在了。——这是我从《外国文艺》的创刊号里获得的一个感受”[5]。
二 叙述语言:屡试不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外国文艺》创刊的1978年,文艺政策尚在调整之中。来自于当时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表态仅仅是对文化(文学)的总的态度,虽然透露出了较为宽松的引进指示,但仍然是以不同冷战阵营之间相当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为基础的。到了具体的译介实践,还需当事人谨慎操作。译者要在“原作者所处的论域(如属于某一特定文化的一整套概念、思想意识、人物和事物)与译者和他的读者所处的另一个论域之间取得平衡”[6],必须找到一套合适的叙述语言。那么,如何找到一种更为稳妥的方法,在不碰触主流意识形态阈限的情况下“讲述”这种“外国文学”呢?尤其是曾被反复批判的“西方现当代文学”?(7)徐迟曾在他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中撰文谈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在列举了意象派、艾略特、海明威、斯坦因和里尔克后,他这样写道:“此外,还有一些现代派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是我所喜欢的,不在这儿一一的说了。我现在写这几页也许还是担着一定的风险呢。好在我胆子还比较大”。见:徐迟.外国文学之于我[J].外国文学研究,1979(1):88-90。
如果说在作品的选目上,《外国文艺》通过将“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提升到“外国文学”的主流位置,从编目上改变了原有“三个世界”分类标准对外国文学的既定分割的话,它还需要在时间维度上获得叙述的合法性。在共时性的空间里,译介一个怎样的“外国文学”牵涉到的是对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判断;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这涉及的是一个继承怎样的文化传统的问题。也就是说,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不变的“传统”,而是选择哪一部分“知识”并将之历史化之后建构出一个 “传统”,从而这一“传统”之外的“知识”将成为被遮蔽或被打压的“他者”。
同样道理,在“世界”或“世界文学”的背景之下,只有对“外国文学”有了一个较为明晰的判断,“本国文学”才更容易获得踏实的位置感。以茅盾为例,他在1920年主持《小说月报》时曾这样描述“西洋文学”的发展史:“西洋古典主义的文学到卢骚方才打破,浪漫主义到易卜生告终,自然主义从左拉起,表象主义从梅德林克开起头来,一直到现在的新浪漫派”,概而言之,“西洋的小说已经由浪漫主义(Romanticism)进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表象主义(Symbolism)、新浪漫主义(New Romanticism)”。[7]作为一种以进化论为方向的文学观的产物,茅盾对“外国文学”史“发展”图景的描述,和他对当时中国文学的判断是密不可分的。而到了现在被很多人认为相对“封闭”的20世纪50年代,当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判定同样来自于和“外国文学”相比照。同样是茅盾,政治上追求“进步”的他在1958年出版的《夜读偶记》里修正了自己1920年的看法。他认为,当时他提出的“文学思潮发展程序”,“表面上好像说明了文艺思潮怎样地后浪推前浪、步步发展,实质上却是一个美丽的尸衣掩盖了还魂的僵尸而已”,他的理由是“现代派”的思想根源其实是“主观唯心主义”,“在创作方法上是反现实主义的”。[8]不过,他最后遵从的依然是“进化”逻辑,只不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新浪漫主义”取而代之。在新的发展脉络中,由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必然取代和天然优越,与之配套的社会主义文学也因合乎“历史规律”,具有了其他阶段的文学所无法替代的价值。这显然来自于苏联的影响,典型的莫如日丹诺夫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衰颓与腐朽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文学的衰颓与腐朽,这就是现在资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学状况的特点和特色。资产阶级文学曾经反映资产阶级制度战胜封建主义,并能创造出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伟大作品,但这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9]。
可是,无论是“无产阶级文学”,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都无法成为《外国文艺》译介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叙述用语,因为前两者所限定的文化等级中并没有多少空间留给其他类型的文学。(8)当时高校中使用最多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仍然不讲“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见: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欧洲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朱维之,赵澄.外国文学简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而当时社会上引进“外国文学”的热切要求——一大批译介刊物的复刊、创刊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隐含着的,却是对自身不足的判断,即对原有的以“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包括其附属的翻译文学)先进性的怀疑。很显然,在此时想要重新叙述“外国文学”,需要回到某个足以达成共识的界面上来。当时能够在文学领域提供这种共识性的界面的,只有马列经典中备受褒扬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在当时时代是最“安全”不过的办法了。
于是,马列经典作家对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评价,在新时期初期被当成了屡试不爽的“语法”。《外国文艺》每篇翻译作品的“前言”里,一概带上了浓重的批判现实主义语调。为翻译作品附加一个政治性的“前言”早已有之。20世纪60年代,出版部门就在出版中外过去的名著时,加强“前言”的撰写工作,达到“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10]的目的。只不过,这里的前言不仅有“引导、规范读者理解阐释趋向”的作用,还将译介者和编辑的立场鲜明地呈现出来。当时大概有这样一些具体的方法:强调被译介作家的无产阶级出身;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出身——马恩赞赏的那些作家大多也是中小资产阶级,作家的经历中有“进步”行为也会被格外标示出来,但要同时描述其作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外国文艺》创刊号中,中产阶级出身的诗人蒙塔莱曾“拒绝加入法西斯党”而被“开除公职”、参加“抵抗运动”,他以“对大自然景色和风物的描绘,咏叹‘生活的邪恶’和它带来的‘不可捉摸的痛苦’”等为主要特点的诗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意大利中小资产阶级对法西斯反动统治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厌恶、失望的情绪, ……他逃遁于自我的情感世界,抒发抽象的、超阶级的‘生活之恶’,把它当作一切痛苦的根源,实际上掩盖了现实的阶级社会的矛盾和实质。这是‘隐逸派’诗歌必然具有的消极性。”还有一种更为常见的方式,是在译介作品中发现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特别是对资产阶级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如“黑色幽默派”对“美国社会以至周围世界中的丑恶、畸形、残忍、阴暗的人物和事件”的“讽刺嘲笑”等(9)类似的分析请参见:柳鸣九.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J].外国文学研究,1979(1):11-28。这种“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分析方式对当时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史的写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如果将《外国文艺》创刊号里出现的这个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外国文学”形象完全当真,似乎还可以由此上溯一个中国需要“批判现实主义”的“历史”(比如从“五四”开始),但这很可能是出于言说当下的需要将“一切历史”都阐释成“当代史”,刻意寻找“起源”的结果。其策略和茅盾在不同时期对“外国文学”发展线索的不同描述如出一辙。实际上,当时对这个批判现实主义统驭下的“外国文学”的不满已经开始涌现。1978年下半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研究室的一次学术讨论中,陈焜提出“狄更斯死了”,即“现实主义的魅力当然是不朽的,它在十九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现代派的某些手法在表现现代人复杂的意识、经验和感受方面是不是也有独到的创造和发展呢?”[11]稍后,作家戴厚英在小说《人啊,人!》的“后记”中说:“单从艺术上说,现代派艺术的兴起,也有它的必然性,它既是现代派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否定,也是现实主义艺术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在戴厚英看来,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外国文学”只不过是“现代派”作家的“祖宗和古董”。[12]尽管支撑陈焜、戴厚英的依然是某种线形发展的逻辑,但可以由此看出他们对“外国文学”的评价持有一种不同的标尺——既不同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统驭下的“外国文学”,也和以批判现实主义为评判尺度的“外国文学”大相径庭。
如果将这里《外国文艺》和陈焜、戴厚英等对“外国文学”形象的不同描述,和上文提到的《世界文学》里的“外国文学”形象放在一起看的话,会发现它们是同一时空中出现的对“外国文学”的多种叙述。在这里,“外国文学”形象的建构虽然仅仅是一个“开头”,但它却为“新时期”准备好了多种可能。从这个“丰富”的开头里,并不能推导出某种“历史的必然性”。所谓的具有“规律性”和“确定性”的历史,往往是后来者出于某种需要提交的宿命论断。
三 传播方式:“内部发行”中的新话语秩序
虽然《外国文艺》中的“外国文学”被打扮成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模样,但仍是一种需要被批判的文学,要想“抛头露面”,必须有一些相应的保障机制来规避风险。其中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外国文艺》刚创刊时的“内部发行”。作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内部发行”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扮演过多种角色。“内部发行”的“内部”显然不能与表述“人民内部矛盾”时的“内部”等同,而是对大的受信任群体的再区分,是政治身份的配给品。比如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上有名的“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的“内部”就是相当级别的党政干部。复刊后的《世界文学》“内部发行”的对象是 “国内文艺工作者和工农兵文艺积极分子”[1]。与之相对应,《世界文学》复刊号刊发的笔谈里不仅有刘白羽、曹靖华、林林、冯牧等“文艺工作者”,而且还有狄蟠和长青这样不知名的普通工人、农民。在刊物的编排上,前一个群体大多只有署名,没有单位,而后者则有明确的身份标识——如狄蟠来自“北京汽车制造厂”,他文章的题目为“我们工人的希望”;长青属于“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他在《世界文学》上撰文呼吁“农村知识青年需要外国文学”。[1]
《外国文艺》与之有着重要差别。在创刊号的“编后记”里,译介的目的是为了“供有关部门和专业文艺工作者了解和研究”,“它是一个以宣传、文教等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外国文艺教学和研究人员、专业文艺单位和专业文艺工作者为对象的内部期刊。”[3]也就是说,《外国文艺》的读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监管部门的领导,另一类是从事“教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前者被认为有着较高的意识形态管理能力,后者被认为拥有丰富的知识而具备了较强的免疫力。果不其然,在创刊号上,《外国文艺》发表的一组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做好现代外国文艺的介绍和研究工作”的笔谈,作者全为“专业”人员:巴金、沈柔坚、草婴、谭抒真、周煦良、任溶溶和李俍民。把读者圈定在如上这样一个稳妥和安全的范围,也就意味着刊物具有了一种“内参”性质,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现一些和当时的主流文艺理解有冲突的不宜公开的内容。
读者们是怎样对待《外国文艺》里的这个有“内部发行”保障的“外国文学”形象的呢?如前所述,他们要寻找的是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新的文学评价标准提供的“世界的普遍经验”,并借助它“来理解他们自己的处境以及如何感受这种处境”。也就是说,这个“外国文学”正以“非政治的姿态或者惊人的政治无知性显示着”一种新的“话语的秩序”,而“这秩序本身就是政治的痕迹”。[13]套用一位历史当事人的措辞,这个新的“艺术世界的意义超过了某个思潮流派的局限”,但当“它涵盖了现代人在当代处境中的某些精神特征”时[5],也使得其他的“现代人在当代处境中的某些精神特征”给排挤掉了。可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在破除原有意识形态强制力的同时,可能也在催生新的意识形态神话。虽然新的排斥机制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也会激活文学写作的潜能,但后来的批评家和作家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之努力的“人类的普遍经验”或“世界的普遍经验”其实并不那么“普遍”。这不仅表现在此种文化本来就和冷战条件下的排他性思维有着复杂的关联,而且在引进的时候也潜隐着某种逆反心理。他们去寻找“外国文学”中的“人类普遍经验”时,在逆反心理的作用之下,会使其很容易忘记作品原有的语境。
就这样,在一种特殊的“内部发行”机制保障下,混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派、后现代主义(后来追认的(10)参见:王宁.论“后理论”的三种形态[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5-14。)等等色彩的相当“暧昧”的“外国文学”形象,在《外国文艺》创刊号上诞生了。依附在这个形象上的多种意识形态话语都以一种看似历史化的努力安排了各自非历史化的“排他”计划。这一出现于新时期初期的充满历史印记的“外国文学”形象留给人们的思考是:如何在具体语境中构筑更具包容性的经典序列,用一种更具反思性的眼光把传统“发明”出来,而不是被所反对的立场所限定或被逆向思维方式所规定,然后简单地站在赞成和对抗的队列中进入下一轮历史循环;单就文学译介来说,必须考虑“异域文本所由产生的文化”,如何“面向本土文化中的不同群体”。[14]关注“新时期文学”对外来文化资源的建构,是为了“力求显示文学经典之形成本身的得当方式和应该包含的文化档案类型”[15]199,至于这些不同的知识在话语角力中如何此消彼长,以及它们本身的构成状况如何影响了读者的接受等等更多的话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附:
《外国文艺》一九七八年第一期目录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深入揭批“四人帮”,做好现代外国文艺的介
绍和研究工作(笔谈)
巴 金 沈柔坚 草 婴
谭抒真 周煦良 任溶溶 李俍民(3)
川端康成短篇小说两篇
伊豆的歌女
侍 桁 译(17)
水月
刘振瀛 译(41)
幸福 外三首(诗歌)
[意大利]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作
吕同六 译(52)
肮脏的手(七幕剧)
[法国]让-保罗·萨特 作
林 青 译(58)
第二十二条军规(长篇小说选译)
[美国]约瑟夫·赫勒 作
南 复 译 主 万 校(195)
美国绘画七十年
[英国]多尔·艾什顿 作
何振志 译(259)
1977年欧洲文坛一瞥
[美国]约翰·斯特罗克 作
主 万 译(270)
外国文艺新作介绍
格·格林的新作《人的因素》出版
戈哈(277)
1977年出版的三部美国政治小说
施咸荣(279)
诺贝尔文学奖金和获奖者(外国文艺资料)
(282)
外国文艺动态
简·奥斯丁一个喜剧剧本手稿幸免湮没
(309)
美国作家亚瑟·赫利访问苏联并发表谈话
(310)
西德作家格拉斯及其新作《鲽鱼》
(276)
苏联公布1977年度文艺和建筑学方面国 家奖金获得者名单
(311)
贝多芬《对话笔记》前六集出版
(312)
美国举行“激光音乐会”
(313)
几部外国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
(314)
苏美合拍影片《青鸟》
(315)
莫扎特的《魔笛》拍成电影
(315)
西德上映反动纪录片《希特勒的生涯》
(2)变条件不变结论的“变题”。主要是指在以一题为基准,对此题的条件进行变换,而所求的结论不变。通过这一系列的题目的练习,使学生形成完整的与这道题所涉及到的相关知识结构。
(315)
英国举办透纳画展
(315)
毕加索在西班牙
(258)
罗丹作品被窃
(317)
古图卓的新画
(317)
巴黎拍卖雷诺阿和德加的画作
(317)
编后记
(318)
[美国]杰克逊·波洛克(封二)
走下楼梯的裸体者
[美国]马赛尔·迪尚(封三)
印第安纳的历史
[美国]托马斯·本顿(封四)
封面设计
任 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