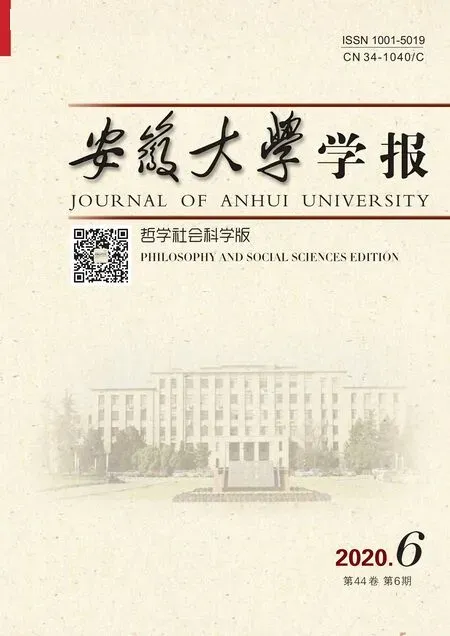论梅曾亮对袁枚诗学的接受、批评及其意义
蒋明恩
嘉庆八年(1803),梅曾亮求学于钟山书院,是时姚鼐正讲学于此。梅氏对姚鼐所倡导的古文义法甚为推崇,因而尝言“是时文派多,独契桐城师”(1)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彭国忠、胡晓明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63页。。后梅曾亮拜师姚鼐,入桐城派,系统学习桐城文法,然“虽祧在桐城,声貌初不相袭”(2)蒋国榜:《题辞》,梅曾亮《柏枧山房全集》文集,《续俢四库全书》第15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97~598页。。梅曾亮并不拘囿于桐城,而是继续保留自身家法及先前所学,常将其他诗派或诗人的优秀诗学思想纳入桐城文学体系之内,因而时人评之“义法本桐城,稍参以异己者之长”(3)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435页。。其中,梅曾亮对袁枚诗学的接受和吸纳最为显著,也最具有代表性。虽表面看来袁、梅二人无直接交往,但却存在间接联系。梅曾亮诸多师友及长辈皆与袁枚过从甚密,尤其是梅父冲,更是袁枚最喜爱的弟子之一。正因梅曾亮早年多接触袁枚诗学,故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其熏陶,进而又在深谙其利弊的基础上,对其加以借鉴、继承乃至改造。由此可见,厘清梅曾亮与袁枚诗学之关系至关重要。目前学界对梅曾亮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古文,对其诗学的独特地位尚未予以足够重视,而在袁、梅诗学关系问题上,更未见有人关注。鉴于此,本文拟以相关文献的疏通阐释为基础,试图对二人诗学关系展开深入探讨。
一、梅曾亮与袁枚诗学之渊源
自乾隆十三年(1748)起,袁枚寓居江宁随园,以金陵为中心,接着以“性灵”为旗号,开始了长达近五十年的文学活动。在此期间,海内文人翕然归附,性灵诗风有流衍全国之势,而金陵风气尤著,且影响久难下矣。长于金陵的梅曾亮,对袁枚性灵诗学便多有接触、深受熏习,并形成诸多认知。如《侯起叔先生家传》一文中梅氏便云:
是时,钱塘袁简斋方寓江宁,及阳湖赵瓯北、铅山蒋心馀,皆以诗震襮天下,而袁为魁。自王公大人,下至商贾妇孺,读其诗者,人人自以得其意。宾客游士投诗卷为弟子者,名纸之积如山。(4)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170页。
可见,梅曾亮对乾嘉时代兴起的性灵派有着清晰了解,并对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三大家在乾嘉之际产生的轰动性影响,有着相当准确且客观的认识。
又于《缘园诗序》一篇中云:
昔袁子才先生居随园时,以诗名盛于时,搜奇挹胜,吐纳烟景,园所蓄蕴,一洩于诗。一时士大夫逸乐富厚无事,皆自喜为诗,过从先生无虚日……曾亮不及从游于袁先生。(5)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102页。
梅曾亮于文中盛称袁枚诗才高绝、趣味高雅、有名士之气,引领一时士大夫雅集游乐之风,并且梅氏还为自己因生年晚,未能从游于袁枚而深感抱憾。
当然,梅曾亮对袁枚也存在一些误解。如在《万裴园诗序》一文中,梅曾亮分析袁枚诗法取径时说道:“简斋之诗自以为岀于乐天。”(6)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136页。其实袁枚从未如此说过,并且袁枚因不满时人称他诗学白居易,而赋诗申辩道:“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7)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王英志编纂校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8页。考究梅曾亮之所以如此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当时人皆认为袁枚诗宗杨诚斋而上溯白乐天,包括袁枚好友蒋士铨。且袁枚在阅读《白氏长庆集》后,也认为自己的诗作的确与乐天有相似之处。这虽为误解,但也充分表明梅曾亮对袁枚诗学投入了一定关注。
袁枚诗学对梅曾亮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无异议。那么梅曾亮是通过哪些途径接受袁枚诗学呢?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从梅曾亮诗文、书信等材料考见,他是阅读过袁枚诗文作品的。除此之外,他应当还通过师友间交流以及家庭诗学教育两方面间接了解、接受袁枚诗学思想。
首先,通过师友间交流间接了解袁枚诗学思想。梅曾亮年少时多有接触性灵派人物,其中便有乾隆后三家之一的王昙。王昙是袁枚弟子,性灵派后期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一生多坎坷,然性格却率性自然,时人评之“恃才放纵……自是桑悦、徐渭一流人物”(8)钱仲联编:《清诗纪事》,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725页。。王昙为诗重“奇”,对龚自珍诸人影响颇深。梅曾亮二十一岁游历浙江时,曾拜访过王昙,并作有《赠王仲瞿丈》一诗:“早岁声名宝剑篇,论兵谈槊过年年。三车作伴行千里,一饭留宾破万钱。南国微词聊寄傲,东山远志已堪怜。只今憔悴西湖上,绕屋清溪二顷田”(9)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446页。。诗歌围绕王昙一生经历展开,将其性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足见梅曾亮对王昙的尊重和敬仰之情。此外,梅曾亮与袁枚弟子严骏生也有交集。严骏生虽为词家,但词作直抒性灵,将袁枚性灵诗学思想贯彻到了词学中。梅曾亮与严骏生的交往,集中体现在两篇词序上,两篇都是为严氏《餐花吟馆词钞》作序。在《严小秋词序》(为侯云松代)中,梅氏云:“凡性灵所不居,皆风雅之外道。”(10)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438页。可见,梅曾亮很重视性灵,且认为性灵是诗词作品不可缺少的核心要素。再有,桐城派重要作家陈用光也曾学诗于袁枚,他在《赠陈春麓别驾》一诗云:“我昔游江南,亦曾拜诗佛(梦楼先生谓随园先生为诗佛)。”(11)陈用光:《赠陈春麓别驾》,《太乙舟诗集》卷一,清咸丰四年孝友堂刻本。陈用光后又师从姚鼐学古文,与梅曾亮有同门友谊,且陈氏年长梅曾亮近二十岁,又与梅父友情甚笃,曾一手提拔梅曾亮。梅曾亮在《祭陈石士先生文》一文中说:“公字先君,曰吾昔友。随园赋诗,二客一叟。……自此视我,与犹子同。”(12)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368页。该文展现了陈氏与梅父同于袁门学诗的场景,也表现出梅氏对陈用光的敬仰、感激之情。不仅如此,梅曾亮还以陈用光为典范,对他多有学习,二人常一起讨论诗文之法,梅氏称赞陈用光诗文重情尚真而不拘泥于师法,能自成风格。
其次,通过家庭诗学教育接收袁枚诗学思想。梅家诗文鼎盛,文脉体系完善而严密,家族文学得到了很好传承,家族内部还有本族人自编的《梅氏诗略》相传。梅曾亮早年的文学悟性正是来源于家族文学传统的熏习。梅家自文穆公梅縠成被乾隆皇帝赐籍江宁后,便定居金陵,造建宗祠,多与当地文士名流相交。其中,梅氏家族与袁枚过从甚密、多有交流。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春,袁氏兄弟招高涧南、严东友、龙愚溪……梅隅庵、二如昆季等耦巢宴牡丹,其中“梅隅庵、二如昆季”即为梅曾亮两伯公。梅隅庵即梅,被钦赐为举人;二如即梅,虽只一贡生,然为人至孝,亦工于诗文,时人评其诗文“有高格清气,异于世之为文者”(13)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2页。。可惜梅未得长寿,著作亦甚少,仅《新晴阁诗草》《大事论》等,文名未起。梅与袁枚私交甚深。乾隆四十二年(1777)秋,梅卒,袁枚作《挽梅式庵》一诗哭悼之:“读史研经四十春,终嫌竹素少传真。九原此去无他乐,看见古来无限人。”(14)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16页。后又题亡友梅式庵画册,悲伤之情难掩,其诗云:“识面长安日,题襟白下时。卅年如昨耳,一别竟何之。绝好佳公子,居然老画师。相知惭未尽,头白泣袁丝。”(15)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周本淳标校,第621页。梅曾亮祖父梅镠与袁枚也多有交情。梅镠因不慕名利,不喜俗学,而绝意科举,然其颇有文学造诣,有古文一卷存世,梅曾亮自幼便得其亲炙。他曾在《书示张生端甫》一诗中回忆祖父授书的场景:“我年未及十,我祖授书时。襟裾戒牛马,解授城南诗。覆醢悲子路,读记泪绠縻。谓我有文性,祖亦为唏嘘。”(16)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562页。可见影响深刻。可惜梅镠也过世早,嘉庆二年(1797),袁枚闻其与王葑亭同日卒,感伤不已,作《王葑亭太仆、梅石居居士同日讣来俱年未六十感而有赋》一诗哭悼之。从以上材料可见,梅氏家族与袁枚交往甚密,常有酬唱互答。也正因这层关系,梅曾亮父亲梅冲曾受业于袁枚学习诗文。
关于梅冲何时受业于袁枚,已难考证,但当早于乾隆五十年(1785)。袁枚所编《续同人集》中收录有梅冲《随园夫子七十寿序》一文,从该文中“初陟龙门,便唤瑶池同宴;时亲马帐,遂许丝竹传经”(17)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十九册),第283页。等句可知,袁枚七十岁时,梅冲刚入袁门不久。梅冲入袁门之后诗歌创作便以“性灵”为旨归。袁枚《诗话补遗》卷五收录梅冲《芜湖遇顺风》一诗云:
江行已三日,不迟亦不快。知我将他行,乃示神通大。一声天乐鸣波中,高浪挟我凌长空。不知两岸孰鞭叱,一齐倒走如飞龙。洲渚玲珑树疏密,层层遮抱如相恤。好峰十里早揖迎,转瞬已嗟交臂失。中流抚掌同笑歌,天公今日赐太多。我谢天公赐不领,误我好景当如何?(18)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十册),第765页。
该诗整篇气势宏大,感情奔泻,又不拘格套,属性灵一路,因此袁枚赞赏不已,称其诗力大有精进。另外,梅冲还有诗句如“心逐野僧依寺定,梦如芳草入春多”“书声出寺清于梵,松影来窗信似潮”(19)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十册),第765页。等,袁枚称之俱佳。这些诗句能得袁枚交口称赞,在于这些诗句构思巧妙、新颖独特,而又情感浓郁、充满灵性,完全符合性灵诗的标准。
梅冲不仅从诗歌创作上践行袁枚性灵诗学理论,他还是性灵派重要成员之一,为袁枚诗学宣传的得力健将。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云:“弟子梅冲为作《诗佛歌》云‘心余太史不世情,独以诗佛称先生。……先生即佛佛即诗,佛与先生两不知。我是如来大弟子,夜半传衣得微旨。放胆为作《诗佛歌》,愿学佛者从隗始。’”(20)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十册),第694页。梅冲在诗中自许为袁枚“大弟子”,并且有志于为袁枚性灵派张目,招揽门徒。在《随园夫子七十寿序》中,梅冲云:“至于冲之于夫子也,附青云之骥尾,一介何知。”(21)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十九册),第283页。袁枚曾作《重赴泮宫诗》,一时和者百人,其中梅冲诗云:“锦袍笑赴青衿会,似把灵光照泮宫。”(22)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第459页。可见梅冲对袁枚甚为推崇和景仰。
梅冲宗法袁枚性灵诗学,对其子梅曾亮影响很大,这充分体现在他对儿子曾亮的早期教育上(23)关于梅冲对梅曾亮的影响研究,目前有陈欣所作《梅冲生平著作考——兼论对其子梅曾亮的影响》一文,该文对此问题讨论仍不全面,几乎未涉及梅冲对其子梅曾亮的诗学教育。。梅冲虽为了生计长期奔波在外很少及家,但对子女的教育却从不放松。嘉庆九年(1804),梅冲馆江西巡抚署,专门将长子曾亮带在身边亲自课读。他曾将程恩泽所作《咏史》诗与其子曾亮诗作进行比较,以此勉励儿子在功课上不可懈怠,“汝见程公子诗乎?渠长汝一岁耳”(24)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146页。。嘉庆十年(1805),梅冲试礼部至京,子曾亮随往,其间梅曾亮与诸学友以作诗为戏,好为奇语。正是在父亲梅冲的影响下,梅曾亮刻苦钻研诗法,诗艺大进。另外,梅冲骈文功底深厚,其骈俪之作文辞优美、对仗精工、用典贴切、气势浩大,多有吸纳袁枚骈文艺术风格,因此深受袁枚赏识。其中袁枚所编《续同人集》便收录梅冲《随园赋》《随园夫子七十寿序》《寄简斋先生书》《谢馈苏糯和烛启》等四篇骈文作品。梅冲善骈文,对其子梅曾亮影响甚深,之所以梅曾亮年少时好作骈俪之文且终生未辍,与其父熏陶不无关系。不仅如此,梅冲的一些治学思想和学诗经验也影响了梅曾亮。如在“汉宋问题”上,梅冲认为,“学而别之曰汉曰宋,固非圣门之所为学矣……善学者,固有所以自处哉”(25)梅冲:《汉学宋学》,《然后知斋答问》卷一,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仔细分析这一见解,与袁枚治学态度相类。在汉宋之争中,袁枚也是跳脱出来,不拘汉宋,他说道:“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说近玄虚;汉偏于形而下者,故笺注之说多附会。”(26)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六册),第346页。只是相对于袁枚,梅冲并非一味排斥汉宋,而是能做到兼取汉宋之善。梅冲这一治学倾向直接影响了梅曾亮,因而梅曾亮治学不拘汉宋,唯求能自处,与其父一脉相承。再如,在学诗路径上,梅冲始效父亲梅镠,以韩、杜、苏三家为宗。袁枚在《与梅衷源》尺牍中劝诫道:“杜少陵曰:‘转益多师是我师。’皆极言师法之不可不宽也……我辈宜兼收而并蓄之,到落笔时,相题行事,方不囿于一偏;迨至真积力久,神明变通之后,其中又有我在焉。自成一家,令人莫测其所由来,则于斯道尽之矣。”(27)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十五册),第111页。袁枚指导梅冲作诗取径要宽,不可拘囿一家一派,而这一学诗路数后来对梅曾亮也颇有影响。与桐城诸子专攻一家不同,梅曾亮的诗法取径颇为复杂,常从桐城派学诗体系中旁逸斜出。其不效姚鼐学诗只从明七子入,而是博采众涉,以杂取为法。因此,他自己也表示“我初学此无检束,虞初九百恣荒唐。”(28)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534页。
由以上分析可知,在梅曾亮与袁枚之间,梅氏师友、亲族及父亲梅冲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梅曾亮正是通过这些媒介,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袁枚性灵诗学,并得以完整理解和掌握袁枚性灵诗学的内在机制。
二、袁、梅二人诗学之契合
正因为梅曾亮对袁枚诗学多有接受,所以袁、梅二人在诗学理念和诗歌实践上契合之处颇多。纵观梅曾亮诗歌,与桐城诸家殊异,其作品多感怀身世、彰显性情,沾有性灵气息,即便应酬唱和、细碎琐屑之诗,亦不尚客气俗套,必有为而发,且常有自然流露、言真意切之作。另外,梅曾亮诗论多重情尚真、凸显个性,且不避凡俗,而这些论诗主张正是性灵诗学的核心内容。
首先,诗重情尚真。袁枚性灵诗学与桐城诗学之间最大的分歧在于对“性情”的诠释和把握。在性情论上,桐城派多奉韩愈及程朱的儒家性情哲学观为圭臬,因而虽强调诗歌发乎情,但更重视止乎礼,主张约情归性,使情感符合中道原则而不致发生偏离。尤其是自方苞倡导“义法说”以后,桐城派由重性情转而趋向于重技法,故而桐城文章“性其情”的特征更加明显。如姚鼐便斥不合法度,只“自适己意,以得其性情所安”(29)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第291~292页。的文章为“畸文”。与桐城派不同,袁枚的性情论则立足于“情”,主张“情其性”。也正因如此,袁枚认为“言诗者,必本乎性情也”(30)袁枚:《随园诗话》(上册),顾学颉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90页。,并将诗歌聚焦于饮食男女,多放纵个人情感而不加约束,这也便引得以“雅正”自居的桐城文人对其猛烈批判:“荡灭典则,风行流传,使风雅之道,几于断绝。”(31)方东树:《昭昧詹言》,汪绍楹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第17页。与贬袁众声不同,梅曾亮作为桐城派文人,却少谈及性理,且在性情论上与袁枚多有契合。梅氏曾在《柏枧山房诗集自序》中云:“顾以少好吟弄,长多坎坷,凡为悲欢,萃此楮墨。”(32)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444页。可知他是将诗歌作为自我情感的寄托。在他看来,“诗者,不得舒其意之所作也”(33)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96页。,情感即为诗之核心,情至而诗来。因此他在《浦君锡诗序》中毫不讳言地说道:“然就其工者论之,其情纵,其理疏,其志伉,其音悲。其情纵,故孤往而深寄。其理疏,故怪迂而多奇。其志伉而音悲也,故多诋诃怒骂,不得如古圣贤之一于优柔和平。”(34)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90页。可见梅曾亮在诗歌理、志、声律的基础上,更加注重诗歌的抒情功能,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然跳脱出桐城诗学“温柔敦厚”哀乐皆中节的法度。
除重情外,袁、梅二人皆尚真,且都认为真与性情乃相辅相成的关系。袁枚性灵说之中枢即“真情感”“真性情”,因此他表示“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35)袁枚:《随园诗话》(上册),第234页。。梅曾亮论诗也重真性情。他认为诗歌的主要目的在于吟咏性情,而所咏之情应当以“真”的状态呈现出来,因此他说道:“吾是以知物之可好于天下者,莫如真也。”(36)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116页。于《黄香铁诗序》中,梅氏还以“真”为中心,系统讨论了境、心、才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将“适乎境”“称乎情”“止乎真”作为评价诗文之准则,其实梅曾亮是“展显才情以显现性情,其所持乃真性情至上论”(37)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前言第9页。。
梅曾亮“重情尚真”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尤为明显。细观梅曾亮的诗歌作品,既有以细腻笔法描绘自然之景,又有以深沉笔法展现身世之叹;既有亲朋聚会、诗酒唱和的愉悦之情,又有子丧妻亡生活艰辛的无奈之感。他的诗歌多有感而发,因而情感浓厚,字字可感可触,这正是他诗歌创作重情尚真的有力体现。如《哭幼弟曾诰》一诗中:
我言未及发,我妻哭在房。我妹掩面啼,我母痛搥床。心知子已卒,呢呢不忍详。回头抱我弟,解颜慰高堂。痛定始自思,缪误近不祥。复念丈夫身,忌讳那置肠!岂知隔岁秋,我弟竟为殇。……天地不汝宽,我涕空淋浪。昨日啼母侧,今日归高岗。高岗无人居,汝啼谁汝伤?呜乎弟兄恩,不得共死亡。(38)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459页。
这首诗平白浅切,皆为平凡语,但悲伤、压抑、苦痛之情流露于字句间,极具感染力,读者能够通过阅读,真切体会到诗人当时万般无奈的痛苦之情。该诗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跟诗人所述之情事真实,所抒之情性真切是分不开的。再如《琢句》一首:“琢句销愁亦自痴,那堪愁与笔相随。凄然阁笔胡为者?事有伤心不忍诗。”(39)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635页。这首诗为梅曾亮避地期间创作,字句里浸透了诗人内心无法排遣的无奈、苦闷情绪。可见梅氏是以诗歌为抒写心灵、寄托情感的最佳载体,真实地呈现了自己当时的生存状态。
梅曾亮还有许多诗作题含“偶成”“偶书”“杂咏”“遣兴”“有感”“拨闷”“叹”等字样,而这类诗无实题,乃属无题诗。何以梅曾亮喜作这类无题诗?袁枚曾说道:“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天籁易工,人籁难工。”(40)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八册),第247页。此类无题或为一时情感之所至,或为一时天机之所现。如《可叹》《偶书》《戏书》《冬夜偶成》《遣闷》《漫兴》《杂咏》《拨闷》《出都偶成》等皆为此类,梅氏这类诗多感情复杂、真切、贴近真实,读者读罢亦常能感同身受。此外,梅曾亮还不喜作叠韵、和韵诗,他曾说道:“诗不贵叠韵、和韵。”(41)杨希闵:《诗榷》卷二,江西省图书馆稿本。其诗集中极少有和韵、叠韵之作,仅为应酬和东坡诗韵数首。何以诗不贵叠、和韵?袁枚便有此类阐释:“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42)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八册),第4页。可见正是袁、梅二人皆重情尚真,因而能得诸多共识。
其次,追求创作个性。袁枚性灵说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个性化追求,因而强调真实,主张诗中应有“我”在。与袁枚相类,梅曾亮也非常注重彰显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袁、梅二人皆认为诗人创作风格及个性的形成,与学古分不开,且学古便是为了脱化自立,达到“著我”的目的。袁枚指出:“人闲居时,不可一刻无古人;落笔时,不可一刻有古人。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43)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第380页。可见他将“学古”与“著我”相联系,要求学习者汲取古人之精神与学识,从而创新自立,达到戛戛独造的境界。梅曾亮也表示“吾非贵古也,贵古之能得其真”(44)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95页。。他把“真”归结为作家独属于自身的艺术个性。之所以要向古人求“真”,是因为今人之作多生乎学,而古人之作多生乎情,因此古人之作更合乎“真”,更“肖乎我”(45)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7页。。关于学古即为“著我”的问题,袁、梅二人在欧阳修身上达成共识。袁枚曾评价欧阳修:“公学韩诗,而所作诗颇似韩,此宋诗中所以不能独成一家也。”(46)袁枚:《随园诗话》(上册),第177页。正因为欧阳修诗气味常被称为“昌黎体”,因而梅曾亮以公允心态于《古文词略》中不录王士禛《古诗选》所选的四十首欧阳修诗歌。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梅曾亮与袁枚相类,即诗学思想之中极力凸显自我艺术个性。现结合梅曾亮相关诗作加以说明。如《急雨歌》一首:
急风吹雨如追逃,斗室喷沫生波涛。黑云无缝天周遭,电光着壁飞霜刀。秘怪恍惚求其曹,哀鸣燕雀藏屋敖。朽株败叶争怒号,吾身嗒焉渺秋毫。俄顷雨断云不牢,岀门一笑波滔滔。野人赤足青天高。(53)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500页。
品读这首诗,情景交融,趣味十足,画面感极强。“急风吹雨如追逃,斗室喷沫生波涛。黑云无缝天周遭,电光著壁飞霜刀”四句,运用白描笔法将“雨之急”的画面刻画得淋漓尽致;“俄顷雨断云不牢,岀门一笑波滔滔。野人赤足青天高”三句写得快意洒脱,风味独具。再有诗中“燕雀”“败叶”“野人”等意象的选取,灵动自然、个性十足。
又如《程春海侍郎人日雪后招饮龙树寺中》一诗中四句:
荡摇天影倒平地,江水橫铺波不裂。悄然坐我浮玉山,夜听谈天答铃舌。(54)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545页。
此四句想象奇特,又有汪洋恣肆之貌,令人咋舌,可见梅氏独具手眼立意出奇之功。
安魂殿是临时存置尸体的地方,也是尸体接受洗礼、祛除生前罪孽的地方,任何一具需要施行割礼的尸体,都要提前放入殿中。在这里,神明会对死者生前所犯的罪恶进行审判,并为灵魂烙上印记,那是通往天空的通行证,天空的使者能够据此辨别灵魂的善恶。大善者的灵魂将被白鹫食净,全部升上天空,而对于大恶者,白鹫会拒绝吞食,等待他的,将是被天葬师以烈火焚烧,灵魂碎灭。
再如《鹰游登岸图为师禹门作》:
海州有山曰鹰游,其东巨海之所浮……稽首再拜风回舟,经历闲切达中头,说天朝德无时休。(55)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571页。
该诗虽有学韩愈之迹,但从立意、章法布局、汪洋之气来看,丝毫不输韩愈诗,甚至更胜韩诗一筹。可见出梅曾亮诗歌虽“自得于古人,而寻声相逐者或未之识也”(56)吴敏树:《吴敏树集》,张在兴校点,长沙:岳麓书社, 2012年,第486页。,已然有自成一家、独具特色的一面。可以说,从梅曾亮诗歌风格、题材、情感、诗意,以及诗法技巧来看,梅氏一直在极力追求自身特色和创作个性,因而才会发出“自成一家今未尝”(57)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535页。的感慨。
第三,雅俗汇通。袁枚以性灵为中心,诗歌多取材于生活中平凡琐屑之事,在创作手法上多用白描,语言通俗平易多口语化,又言“情所最先,莫如男女”(58)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七册),第595页。,多创作艳情诗,因而时人皆批之“鄙俗”。其实,袁枚诗歌在追求通俗的同时,也有雅正的要求,只是在诗歌创作实践中,袁枚发现此二者很难兼顾,“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也”(59)袁枚:《袁枚全集新编》(第八册),第255页。。袁枚企图重建一套以真我个性为目标的新的诗学体系,以之与传统诗学文化相决裂,可在实践中他又发现,自己很难从固有的诗学体系中跳脱出来,因此其诗歌作品呈现出雅俗互斥的局面,甚至与其性灵诗学也常有离合。与袁枚同,梅曾亮诗歌也追求雅俗贯通,而梅曾亮比袁枚高明之处在于其能雅俗兼顾得当。作为桐城弟子,梅曾亮虽继承了桐城派“正雅去邪”的诗文主张,然又与桐城文人一味“黜俗崇雅”有所不同。梅氏论诗以“真”为贵,又强调“因时”,且主张“工诗者皆瘦辞漫言以适己”(60)杨新平:《梅曾亮集补遗一篇》《江海学刊》2011年第2期。,因此他并不反对诗歌的通俗化。如梅曾亮对桐城派嗤之以鼻的元、白诸人不仅加以肯定,还多所学习,他评价白居易诗有“心旷神释”的一面,便是一证明。不仅如此,梅曾亮还在诗文创作实践中追求通俗性,他有许多诗作选材平凡琐屑,运用口语化表达,通俗易懂且不拘格式,生活气息很浓。
梅曾亮写了很多贴近日常生活题材的咏物诗,这些咏物诗见于《柏枧山房诗集》第十卷,卷后题为消寒诗,诗作多围绕尘俗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展开。如《咏牙刷》《腊八粥》《元宵》《烟火盒子》《煤车》《冰车》《酒车》等即为此类。这类随笔而作之诗,描写生活中最不起眼的琐碎事物,这在桐城文人中几无人会去吟咏,也便更体现出梅曾亮诗歌异于桐城而呈现通俗化的一面。梅氏这一类诗不仅题材通俗,还语言浅白且具有形象感。如《酒车》一诗:“酒车不用牛,乃用肩与手。邪许者何人?一滴不入口。”(61)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629页。该诗虽用语浅白,写日常之物,但立意不俗。诗歌以写实手法,来表现底层劳动人民的生存困境,因此虽写酒车,实写劳动者无奈的生活苦境。梅曾亮诸如此类诗歌,虽吟咏生活日常之事物,语言通俗易懂,但立意很高,多具有讽刺意味和警示作用。
为增强诗歌通俗性,梅曾亮还常借助于虚词、代词等来增强语言口语化,如《过滕县作时县令赵毓驹贵州人》一诗有句云:“旅食问主人:县官竟何如?主人叉手言:乃是大好官。自从上任来,廉洁不受钱。时时审官事,吿期不拖延。”(62)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490页。这一类诗歌平白浅近、生动自然,与乐天通俗、写实的诗风颇相类似。梅氏还将散文化的句式运用于诗歌,他曾说:“以文为诗古有之,拟经拟子斯尤奇。”(63)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608页。梅曾亮“以文为诗”的方式多是以散文的章法、句式入诗,因而其诗多用白描手法,达到叙事绘声绘影的艺术效果。如其《嘲蝉》一诗,在谋篇布局上完全采用古文写法,将议论与抒情相结合,起承转合间,行云流水、荡气回肠。再有,梅氏曾说:“商旅里巷之谚,一曙得之,童至耄而习之。”(64)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116页。因而他常将歌谣体、民谚等引入诗歌,以增强诗歌的通俗化效果。如《栾城谣为故邑令朱承澧作》一组诗:
官鸡一只,民钱五百,官鸭一双,民钱二千。呜呼县官今六年,至死未收鸡鸭钱。
官有事借民马,借马数百家。百姓无不愿者,官养如我自养肥。民借还迟迟,官借早来归。
……(65)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493~494页。
以上诸诗从形式上来看,句式参差不齐,语言高度口语化,韵脚也极具跳跃性,显现出简单明了、平易自然、生动灵活的特点。再如《送穷》一诗句云:“送穷神,东海东,群仙皆住金银宫。黄金可成玉可种,虽有穷技难为工。”(66)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628页。这显然是吸收了地方民谣、谚语等。
从以上分析比较可见,袁枚性灵诗学对梅曾亮之影响甚深。梅曾亮在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建构的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借鉴了袁枚的诗学思想,因而其诗学及诗作才会呈现出与性灵诗学诸多相同的特征。
三、梅曾亮对袁枚诗学的批评及意义
作为桐城派中期代表性作家,梅曾亮有着“奉姚姬传为师,其意以为方望溪传刘海峰,刘海峰传姚姬传,姚姬传传于我”(67)舒位等:《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程千帆、杨扬整理,杨扬编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62页。的理想追求,因而他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并讲求因时通变,致力于创新、突破。正因如此,他游走于桐城派别内外,一方面钻研桐城之学,另一方面又兼包其他流派优秀思想,企图从外部角度对桐城派之弊进行矫正或补充。其中,在对袁枚性灵诗学的吸纳中,梅曾亮思虑最深,他以桐城派的眼光,对袁枚诗学进行了选择性改造,而这深刻反映在他对袁枚诗学的批评上。
首先,关于学古问题。袁、梅二人皆主张通过学古达到“著我”,但袁枚以“性灵”为“学古”的基本立场和角度,主张只需学古人之精神。他引用周栎园之言“学古人者,只可与之梦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昼显形”(68)袁枚:《随园诗话》(上册),第191页。,指出学古者不可去追摹古人诗歌的外在形式和技法。“人悦西施,不悦西施之影”(69)袁枚:《随园诗话》(上册),第164页。,只有与古人神合,才能达到“著我”的要求,才能呈现“字字古有,言言古无”(70)袁枚:《续诗品注评》,王英志注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78页。的最佳境界。与袁枚不同,梅曾亮将“形式”也纳入“学古”的范畴,并且强调“学古”不仅只在诗文立意上合于古人,还可以追摹古人之格调,学习古人之章法。在梅曾亮看来,“神、理、气、味”与“格、律、声、色”为诗文之精、粗,皆为重要元素,学古者不可不关注。因此梅曾亮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多学宋人用典、多学杜甫诗歌之起承转合、多学韩愈以文为诗等。梅氏正是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追摹古人,而又“不规规于古人”(71)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160页。,因而得以自成一家。
其次,虽然袁枚与梅曾亮皆尚真,但是二人对“真”的认识,仍有差异。袁枚所谓的“真”为性灵论的基本要求,强调的是自我情感之“真”、性情之“真”。与袁枚不同,梅曾亮是以“真”来统摄他全部的文学思想,因而他从内容、实现途径、意义价值、反馈等几个方面对“真”作了理论性和概念性总结。在梅氏看来,“真”不只限于“情性”之真,“真”还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如“景境真”“情事真”“时代真”等。他围绕“适乎境”“称乎情”来讨论诗歌之“真”,主张“物与我相遭”,情与境相合,而这显然已跳脱出袁枚只注重“真我”的局限,而将“真”扩大到了物与境。可以说“梅曾亮能从‘物我相遭’的角度提出诗歌个性化的问题,比起性灵诗学的一味宣泄私情,显得更为切实而中肯。”(72)周兴陆:《桐城亦有诗派》,《中国文学研究》2012年第4期。此外,梅曾亮还积极发挥诗歌的经世价值,不仅将“真”同诗人的艺术个性联系在一起,还强调通过“真”“积极表现时代特征反映时代变化”(73)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7页。。 可知,相对袁枚,梅曾亮“真”的观念更加丰富具体,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复次,讨论才与情的关系问题。袁枚性灵诗学始终围绕“才与情”两点展开,并将“性灵说建立在才性论基础之上”(74)张健:《清代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26页。。在袁枚看来,“诗才”即指“诗性”,也是写诗的天赋,因此他表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75)袁枚:《随园诗话》(上册),第488页。,“天性无诗之人有作如无,天性有诗之人不作如作”(76)蒋寅:《袁枚性灵诗学的解构倾向》 《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梅曾亮认可袁枚的才性论,因此他说道:“故诗之道,以性近者皆能工之。”(77)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43页。然与袁枚不同,梅曾亮在袁枚才性论的基础上,又强调“才学”。可见梅曾亮所说的“才”包括“才性”与“才学”两个方面。关于“情”的问题,梅曾亮与袁枚都强调“真情感”“真性情”,主张诗歌“适己”,但梅曾亮多以才驭情,重情而不纵欲,因此不类袁枚流于淫放。另外,梅曾亮所说的“情”不只限于个人的自然性情,还包括用世的社会性情,这是他超脱袁枚性情论的地方。也正因如此,梅曾亮在袁枚“才与情”基础上,又加入“境”,而这里的“境”即是指外在事与物。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性灵诗学逐渐式微的背景下,梅曾亮依然悖逆师说对袁枚诗学进行批评和吸纳,正是出于为我所用、自辟新境的目的。梅氏很清楚“性灵说”与“义法说”之间有鸿沟之隔,如何消解其中的矛盾,整合两者,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通过仔细考量,他发现两种体系各有利弊,选择了相互参补的方法,即以桐城义法规范性灵之淫放,又以性灵之灵动松绑义法之禁锢。无疑梅曾亮的策略是正确的,性灵之气的确给桐城派灌输了新的活力,帮助桐城派整改了论述空洞、辞章枯槁的弊病。那么梅曾亮是如何将诗论顺利引入文论的呢?梅氏首先在桐城派“诗之与文,固是一理”(78)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第290页。的基础上,通过实践彻底打通了诗文的界限。他不仅喜以文为诗,还常以诗为文,并且在编选《古文词略》时增设诗歌一类。当诗文之壁垒被打破,梅曾亮便顺理成章地援引诗性入古文,因而其古文既重情韵,又词兼雅俗。如此也便将桐城派所标举的“雅洁”转向了更适应时代的“称心”准则。虽然梅曾亮这种游走于桐城派别内外、杂取各家的做法引得批评——“子之文病杂,一篇之中数体互现,舞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79)梅曾亮:《柏枧山房诗文集》,第109页。,但是在桐城派日渐凋敝的情况下,梅曾亮扛起桐城大旗,“以辞兼雅俗、自然真率为要”(80)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年,第66页。,确实帮助桐城派完成了一次新的成功的转型,也建立起了桐城诗古文新范式(81)萧晓阳先生认为梅曾亮古文以骈入散,别具一格,自成一体,建立起了桐城古文新范式(见 萧晓阳《近代桐城文派研究》第二章)。笔者认为梅曾亮诗歌创作与其古文同步,亦不拘囿于桐城,能自成一家,因而谓梅曾亮诗古文皆能成桐城新范式。。
四、余 论
嘉庆二十年(1815),姚鼐过逝,桐城古文的传承与发展事业,自然落到了桐城诸弟子身上。面对“方、姚惜以往,斯道堕尘境”(82)朱琦:《怡志堂诗初编》卷五,清刻咸丰本。的局面,桐城派弟子们肩上的责任重大,他们企图重振门派。其中,梅曾亮用力最深。梅氏虽师法桐城,却并不为桐城所拘,他常杂取各家之长,力求变化,“欲自辟一境地”(83)杨希闵:《诗榷》卷一,江西省图书馆稿本。。梅氏承续师道之法,异于方东树、姚莹诸人,他心力瘁于如何在桐城之学中推陈出新。于是,桐城派所津津乐道的“义法”“古雅”准则被打破,而代之以更契合于时代的“因时”“真”等新的理论体系。因此,姚莹《惜抱先生与管异之书跋》中说道:“伯言之道既大行,告归江宁,先生之风于是乎在。”(84)姚莹:《姚莹集》《桐城名家文集》(第六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13页。他认为梅曾亮诗文之法已然跳脱姚氏之学说,成其一家之道。可以说,梅曾亮从外部环境来审视桐城派,且不断将新的、合理的因素纳入桐城文学发展范畴内,给桐城文学体系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其中,梅曾亮打破了性灵诗学与桐城文学积不相能的局面,使桐城文学体系朝着更全面的方向发展,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开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