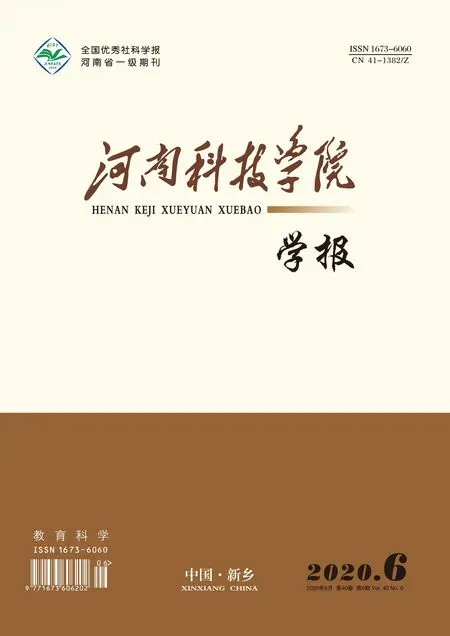美国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变迁
——以大学章程的发展史为视角
范佳洋
(浙大城市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已步入“双一流”建设的新阶段,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国家层面的“放管服”改革延伸至高等教育领域,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又一次成为改革的关键词。然而,201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放管服”的改革尚未完全落地,地方政府“放不下”与高校“接不住”的现象并存[1]。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进程中,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是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大学章程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载体,理应发挥规范作用。《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高等学校的举办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明确学校的办学方向与发展原则,落实举办者权利义务,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因此,通过大学章程明确界定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被认为是大学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因此,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也一直是国际教育学界的热议话题。美国大学历史悠久,大学章程的形式与功能也日趋多元。当下,美国的“大学章程”实则是一个复合体:“charter”和“statutes”属于大学设立的基础性规范,是大学抵抗政府不当干预的规范依据,主要保障大学的法人资格和自治权;“bylaws”“ordinance”“legislation”等属于大学的自治规章,用以规范大学内部的组织设置和权力运作机制。不同类型的大学章程分工合作,共同形塑大学的治理体系[2]278-293。美国大学章程的发展史带来以下启示:若要通过大学章程厘清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就应当区分不同形态的大学章程所承载的不同功能。唯此,才能使大学章程发挥推进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作用。
一、起源:作为特许状的大学章程
欧洲中世纪主要采用地方分权制,并无独大的中央集权组织[3]31。当时的西欧社会正处“弱政治”时期,拥有最高政治权力的封建王权几乎无法行使控制、整合社会的功能。在相对松散的环境下,城市逐渐出现了经济自治的框架。自由、敢于冒险的商人开始修建永久性的商业据点,企盼自由的农奴和手工业者纷纷涌入商人初建的城市。随后,以各个城市为基础的市民社会逐渐形成。经济的发展与行业利益的保护总是相辅相成的,最初的行会(guild)正是为了保护行业利益而设。之后,行会逐渐发展成了对外争取权力的组织。在设立宗旨的引领之下,行会表现出了行业垄断性、高度自治性、职业同质性等组织特征[4]。公元1099年出现的同业公会(Craft Guilds),就是手工艺者们对抗领主的侵略压迫而组成的组织。这一组织不仅可以维护共同利益,也具有传承技艺的专业职能,它不只是利益团体,更是教育机构。为了促进行会技艺的进步,同业公会进而设立了行会学校,既提供技艺方面的教育,也提供一般文化的熏陶,以正规的教学取代个别学徒制。
从11世纪末到13世纪,西欧各地陆续上演了“城市公社革命”,以对抗领主实现城市自治。自治城市发展为一股可以与教会、国家相抗衡的力量,由此为大学的兴起提供了温床。一方面,城市拥有便利的交通,学生前往城市学习的客观阻力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可以向学生提供足够多的房间,作为住处抑或授课场所。另外,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消费水平,在城市购置物品或谋求兼职,完善自己的生活。12世纪初,受优秀的师资及浩瀚知识的吸引,大量学生从欧洲各地云集于博洛尼亚学习法律知识。虽然大学的成立离不开城市的环境,但两者免不了产生经济纠葛。为了保护自身免受当地市民的侵犯,学生们效仿经济领域的行会,亦形成了组织,合力对抗哄抬房租及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暴利行为[5]7-8。这些与行会类似的学者型社团,就是大学的原型。“世界上最古老的四所大学,即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都是在没有获得权威许可的情况下自发出现的。”[6]以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为例:12世纪末,外国学生自发组织起了“同乡会”(natione),这一由异邦学生组成的社团就是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的开端;13世纪初,巴黎的教师们为自己和学生的利益创建了一个社团,随后成为了巴黎大学的雏形。
1158年,腓特烈一世为保护博洛尼亚大学的异邦学生免受侵害而颁布的《安全居住法》(Authentica Habita),被誉为“中世纪建校的基础性章程”[7]105,该法规定:“经过主教、大寺院主持、公爵、伯爵、法官和我们神圣宫殿中其他贵族对这一问题缜密考虑之后,出自我们的虔诚,对为学习而来的学生特别是神学和宗教法的教授给以特权。就是说他们(包括本人和他们的使者)可以平安地到学习的地方并安全地住在那里……保护他们免受任何伤害……这一法律普遍且永远有效。”[8]169-170《安全居住法》主要包括四方面的内容:其一,特定人员享有类似于神职人员的豁免权和自由;其二,出于学习目的,特定人员享有自由迁徙的特权;其三,特定人员豁免于报复性行为;其四,学生由教师或主教法庭进行审判,而不能由地方法庭进行审判[9]78。由此,《安全居住法》为学者们享有的自由与豁免提供了制度依据。
从《安全居住法》的颁布过程可以看出,在中世纪,大学章程与统治者是息息相关的。实际上,中世纪的大学章程几乎都是以谕诏、特许状或官方文件的形式出现的。1224年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颁发谕诏,决定组建那不勒斯大学(Naples),并正式将那不勒斯大学纳入皇权的庇护;1233年图卢兹大学(Toulouse)获得的谕诏也明确体现了教皇对大学的庇护;1243年萨拉曼卡大学(Salamanca)的创始人费迪南三世(Ferdinand III)在授予大学的官方文件中,作出了保护师生及其随从的承诺。之后,蒙彼利埃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亦分别于1289年、1290年、1292年获得了授予其特权的官方文件。
中世纪大学章程的内容主要是确认大学在经济和法律方面享有的特权。在经济方面,大学成员通常能够豁免于缴纳费用、税收和关税的义务,还能够豁免于参与义务性劳动。至于法律方面,大学成员享有特殊的待遇,即他们不能在普通法庭受审,与之有关的法律事务全部交由教师依据教会法处理。此外,大学章程还让中世纪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破除了君权神授和世袭君主制的权力理念。
当然,中世纪的大学章程也确认了大学在学术方面的特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授予大学通行执教资格(licentia unique docendi)。执教资格最早是由罗马教廷控制的,在12世纪之前,教会几乎垄断了西欧的教育。然而,随着大学的成熟,教师们逐渐开始要求拥有更多的权限。在大学的抗争之下,1213年,教宗英诺森三世将考核和评判教师的权限从地方教会之手转移至巴黎大学。英诺森三世规定巴黎圣母院的总务长只负有颁发执教资格的职权,而大学享有对新教师的教育、甄选和考核权限。到了1233年,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在图卢兹大学的特许状中明确规定,“凡自该图卢兹大学任学科内通过考试并获得许可之学人,即享有于各地(ubique)执教(regendi)之自由权利(liberam potestatem)而无须再行任何考试”[10]。从此之后,授予大学通行执教资格亦成了特许状的基本内容,大学因此拥有了学术特权。
虽然中世纪的大学经教权或皇权的认可并授予章程后,就享有一定的特权,如颁发盖有印章的证书、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并自己制定章程要求成员服从[7]17,但这些特权并不能让其成为一个独立于权威机构的实体,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虽然章程赋予了大学一定的特权,但只有当大学与外部权力发生争执或大学内部产生纠葛之时,教皇才会支持大学的特权;其二,章程并不能反映大学的意志,教皇只是单方面地对教学、教师薪水以及学生管理等事项作出规定[11]124;其三,章程所赋予的权利是脆弱的,权威机构拥有任意变更或忽略章程的权力。此外,由于中世纪大学章程的制定主体是权威机构,其旨在推进“正确的”信仰或是促使大学更好地为政权服务,因此大学章程主要处理的是权威机构与大学的外部关系,至于大学内部的学院、同乡会、学舍等大学分支机构,虽然他们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这些内容几乎没有在章程中涉及。
总体而言,虽然特许状令中世纪的大学散发出了一些独立气息,它将源自行会的学者社团转变为了类似于“法人”的独立组织,但是,大学的独立教学环境是无法得到法律保障的,其得来依靠权威的批准,其失去也只听凭权威的一句话。
二、大学章程作为政府介入大学的界限
根据英国普通法传统有关“法人”的规定,成立大学的先行条件是获得政治权威的认可。在1612年的“萨顿医院案”中,科克大法官明确指出法人的第一要素是获得合法权威的认可,换言之,法人必须是依据或经由普通法、议会、皇家特许状或惯例创立的[12]210。如果没有权威的许可——无论是明示、推定或是默示——就不得创立法人。由于英国大学的法人身份受制于权威的认可,因此,大学章程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以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章程为例,它们均授予王室在监察和管辖大学法人方面的特权。由此,王室通常以法令的形式,对大学行使排他性的监察权。并且,王室有权修订甚至取消作为特许状的大学章程。例如,在1570年,伊丽莎白女王向剑桥大学颁布了章程——The Elizabethan Statutes,该章程重申,由于英国大学是依据王室颁发的特许状设立的,因此国家亦有权将特许状撤回。1636年,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兼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William Laud)以自己的名义向牛津大学颁布了章程,该章程将大学的管理机构交由王室委任的学院领导人来负责,进而为王室介入大学事务的运作提供了媒介。
追随英国法的传统,美国殖民学院的章程在本质上也是政治权威对学院合法身份的确认,是学院行使法人权利的制度依据。殖民时期的大学章程并不包含自治的内涵。囿于英国法的内容限制,法人必须在权威的监督下履行公共和慈善使命。因此,殖民统治者和立法者并不认为学院是独立于权威控制的私人机构,相反,他们认为学院是类似于政府的分支机构。因而有学者认为,当时的法人“只是一个准政府机构,其设立宗旨即为了促进公共或国家福利,而无关私人利益”[13]9。鉴于章程是由权威机构授予的,因而权威机构也有权终止授权。
由于长期远离英国殖民地,美国的法人制度作出了自己的改变。具体而言,殖民者认识到,若将各类组织法人化,则可让不同人基于共同利益而集合在一起。法人章程可以对成员起到具体的、有效的约束,从而,每名成员对法人负有相同的义务,他们因法人章程而互相约束。因此,殖民时期的美国学院并非政府的组成部分,而是独立的实体。总体而言,殖民时期的美国学院具有两大特色:其一,教育与政府分离,但政府对教育负有责任,且学院必须在自治与公共问责之间保持平衡;其二,由私人组成的董事会是学院的权力机关[14]55。
此外,章程也逐渐摆脱了政治权威的色彩,这主要体现在章程的获取方式以及章程的内容上。一方面,英国的权威机构不再是颁布学院章程的唯一主体,例如耶鲁大学的设立就是由康涅狄格州议会确认的——州法院批准了设立“大学学院”(collegiate collage)的法案,并授权10名牧师作为法人的托管人、合伙人或者承担人,他们有权管理大学的内部事务,也有权获得和持有财产。另一方面,章程的内容也分散了大学的管理权力。通过法人章程,美国学院将管理权授予了一个独立于政治力量的私人团体,由该团体来履行对学院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的职能。
自美国大学章程独立于英国权威之后,如何处理政府与大学之距离问题,则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亟需解决的问题。从殖民地晚期到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殖民地政府及大学所在地的州政府,皆与大学出现了不少矛盾。虽然矛盾的缘由各不相同,但解决方式不过三种:其一,通过政治途径(主要解决方式);其二,通过法律程序;其三,打拖延战[15]。通常而言,法律程序被认为是最为公正的处理方式。不过,在处理府学关系时,法院虽承认大学是一个独立机构,但同时亦认可立法机关拥有修改特许状的自由,因此,大学自治并未获得充分保障。例如,1812年,立法机关在未经哈佛大学的同意下擅自修改了特许状,而哈佛大学督学委员会(Board of Overseers)对此表示默许,他们投票决定不走法律程序来处理这一问题[16]301。
181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案”,则令大学章程具有了独立于政府的法律效力。在本案中,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认为大学法人与州政府之间的特许状实为一项契约,争议双方应当依据契约的规定解决问题。因此新罕布什尔州修正达特茅斯学院的特许状的行为是违宪的。“达特茅斯学院案”虽然没有彻底消除美国长达两个世纪的殖民时期的影响,但该案令美国的法人概念在职能和宗旨方面都有了比英国更为宽泛的内涵。美国法院支持法人对内部事务享有自治权,并认为所有获得证书的法人都拥有特权而无须获得政府的庇护。因而有学者评价:“直到1819年马歇尔和斯托里两名大法官确认特许状实为受联邦宪法保护的契约,大学法人才有了反对立法干预的正当理由。”[17]
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是美国殖民地时期建立的最后一所学院,是牧师以利亚撒·惠洛克(Eleazar Wheelock)于1768年在慈善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1769年12月,新罕布什尔殖民地总督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名义向学院董事会颁发了特许状,允许达特茅斯学院在新罕布什尔的土地上建校。特许状明文规定了授予学院的权力及其行使方式,规定了董事会的人数及其权力与职责,并宣布以利亚撒·惠洛克为创始人,授予其依据遗嘱确立继承人的权力。1779年以利亚撒·惠洛克去世后,其子约翰·惠洛克(John Wheelock)继位为该校校长。
“达特茅斯学院案”的争议源于继承人约翰·惠洛克校长和达特茅斯董事会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而后激化为了一种政治冲突。达特茅斯学院的董事会是受当权的公理会和联邦党人所支持的,而学院的改制是由新教徒和民主共和党所发起的。1815年,董事会以小惠洛克无法胜任为由,撤去了他的校长职位。1816年,民主共和党在竞选中获胜后,新罕布什尔州即颁布了《修正特许状并扩大、 提升达特茅斯学院法人地位法案》(An Act to Amend the Charter and Enlarge and Improve the Corporation of Dartmouth College),根据该法案,小惠洛克重获管理地位。同时,该法案将“达特茅斯学院”更名为“达特茅斯大学”,增加了董事会的人数,增设了由州任命的监督机关,并对其管理模式做出了彻底的改变。学院董事会坚决反对该法案的实施,并于1817年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新罕布什尔州法院审理了该案,并认为争议的焦点在于州议会通过法律变更学院特许状的内容,此举是否违反了州宪法。在经历了初审和上诉审之后,新罕布什尔州最高上诉法院作出了支持州议会的判决,认为如果某法人所享有的特权皆以公共目的为本源,那么它就是公法人,它对公众是有现实益处的,因此州议会有权对其特许状作出修改。
学院董事会不服判决,随后将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马歇尔大法官并不认同教育是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的观点。鉴于达特茅斯学院最初是由私人捐赠的财产为基础成立的,因而马歇尔大法官援引英美的宪政传统“私有财产是自由和分权的体现”,对抗政府权力的不当干涉。所以最高法院得出了不同于州法院的意见,认为案件的争议点是州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否违反了联邦宪法。首席大法官马歇尔认为,创设达特茅斯学院的特许状具有契约性质,因此法院须要做的是明确这类契约是否受宪法保护。换言之,法院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依据美国宪法,新罕布什尔州是否有权变更或终止依法授予的且得到接受者履行的特许状。对此,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特许状属于受联邦宪法保护的契约,并且认为州议会颁布的法案损害了这一契约。马歇尔法官指出,英国王室曾与达特茅斯学院就捐赠财产的用途和管理模式达成了一定的协议,这些协议于1769年达特茅斯学院获得的特许状中得到了明示或默许,因而该特许状显然是一份契约,原始捐赠者、受托人和王室是原始契约的当事人。最高法院认为,特许状属于宪法意义上的契约,而新罕布什尔州对特许状作出的修正,改变了原来的契约制度,损害了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
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确认法人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权是有重大意义的。此前,受英国法人传统的影响,“法人的公共属性是通过特许状而被赋予的。无论自由结社的传统多么的有生命力,法官也只会以机械地重复特许权理论作为回应……这是因为法官巧妙地将自身的主观想法隐匿于法律之中,并由此让权威认知‘植入’(bootlegged)法律……在英国国内,除了慈善事业外,他人无权依据一般法律而创设法人”[18]。“达特茅斯学院案”表明,虽然大学的宗旨是服务公众,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个在法律上与政府分离的、获得特许权的机构。至此,大学章程也被正式确认为政府干预大学的制度边界。
三、大学章程接受法律的监督
1844年,《合股公司法》终结了特许状的使命,受公司法律制度及信托法律制度的影响,特许状不再被视为是王权与合法性的象征,而成为与公司法人章程抑或信托制度相类似的制度(如私立高校的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主要用以规范大学的内部组织机构与运行方式[6]。随着特许状的式微,大学内部的规则体系逐渐发达,由此,美国大学复合型章程体系逐步成型。波士顿大学的章程体系就是一个典型,其中charter、statutes/acts和by-laws共同构成了以“charter—statutes/acts—by-laws”为三阶层的、内容逐步趋细的复合型大学章程。具体而言:charter是马萨诸塞州于1867年向波士顿大学颁布的,旨在使波士顿大学的受托人法人化;statutes/acts则是州议会向波士顿大学颁布的各项法案,旨在确认波士顿大学的独立法律地位及相关权利;by-laws则是波士顿大学董事会制定的,主要规定了受托人、官员、各委员会等重要权力机构的构成、选拔方式及议事规则,还规定了学术事项的基本运行框架[19]。
虽然大学章程确认了大学的独立法律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可以豁免于政府的监督。实际上,美国各州的公立大学,根据法律地位的不同,须接受不同程度的法律监督。具体而言,州政府可以依据州宪法或其他州法来设立公立大学。依据州宪法设立的公立大学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公立信托”(public trust)、“自治大学”(autonomous university)、“宪法大学”(constitutional university)或“宪法法人团体”(constitutional body corporate)四种;依据其他州法设立的公立大学的法律形式主要包括“州立机构”(state agency)、“公法人”(public corporation)或政府的“分支机构”(political subdivision)三种[20]1253-1257。总体而言,依据州宪法设立的大学比依据其他州法设立的大学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比如,依据州宪法成立的大学一般不受制于州行政法管辖,而依据其他州法设立的大学,则不得豁免于相关法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依据州宪法设立的大学能够完全豁免于州政府的管辖。例如,以公立信托的法律形式设立的大学,其受托人必须依据州法和信托文件,履行特殊的信托义务,并依据公众的教育利益妥善管理、经营信托财产。
相较于公立大学,州政府对私立大学的管理权则相对较小。在“达特茅斯学院案”之后,美国私立大学的独立法人地位得到了确认。然而,“达特茅斯学院案”并没有剥夺州政府监管其所创办的私法人的权力,只是限制了立法机关在解释特许状时的权限。至于司法机关应当如何适用“达特茅斯学院案”确立的原则,即如何适用契约原则解释特许状,最高法院于1906年在“布莱尔诉芝加哥市”(Blair v.Chicago)一案中作出了说明,要求所有对抗政府的权利都必须得到明确的界定,而不得采用推论或假设的方式,如果特许状对某项权力保持沉默,那么该项权力就不存在。在“达特茅斯学院案”之后的案件中,司法机关亦遵循了严格解释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法院越来越重视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政府甚至拥有“谨慎监管”的义务,以确保受托人履行管理的义务。府学关系的变迁对特许状主要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通常而言,立法机关会在特许状中明确限定董事会的活动范围,这样一来,就超出范围的事务而言,州政府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其二,政府可以在特许状中规定保留条款,保留修正、更改和撤销特许状的权力,并在不减损合同义务的情形下行使保留的权力[14]150。当然,政府的保留权力并非无所限制,州政府在依据保留权力对信托管理作出更改时,必须以不得侵犯大学的特色化规定或大学的主要目标为限。
简言之,虽然“by-laws”“ordinances”及其他由大学自主制定的规则,属于大学行使自治权的表现,但是,相关制度的调控对象不得超出其自治权限范围。一旦调控对象进入法律规制的范畴,那么大学章程亦不得排除法律的管辖。
四、结语
美国的大学章程起初表现为依附于政治权威的特许状,特许状在给予大学相应保障的同时,却无法将政府的随意干预阻挡于大学之外。随着时代的推移,特许状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大学章程更多地表现为设立机构与大学之间的“契约”,这一契约划定了政府干预大学的边界,政府不得随意变更章程内容。与此同时,大学章程的内涵也日益丰富,大学自行制定的规章制度亦成为大学章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内部的有序化运作中发挥着显著的规范功能。当然,大学的独立法律地位并不意味着其可豁免于政府的一切干预,大学章程仍须接受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外部法”的调整。这种依规则行事的法治进路,确保了政府对大学事务的介入必须有法律依据,也要求大学章程的内容不得逃逸于法律框架的限定。在这种彼此制衡的制度之中,大学的独立精神得以维持,大学的依法运作得以保障,这也是大学章程的根本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