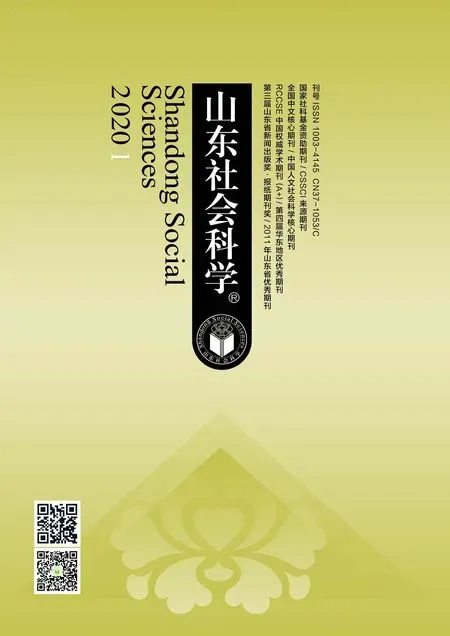不法与伦理的和解
——以黑格尔法哲学为中心
魏 博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随着弗莱希特海姆(Ossip K. Flechtheim)有关黑格尔刑法理论的著作于1975年得以再版,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再一次引起了学界的讨论热情,形成了“刑法学理论中的黑格尔复兴”(1)Vgl. Ulrich Klug, Abschied von Kant und Hegel“, in Skeptische Rechtsphilosophie und humanes Strafrecht Band 2: Materielle und formelle Strafrechtsprobleme,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1981, S.149-155. cf. Wolfgang Schild, “The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Hegel’s Concept of Punishment”, in Robert B. Pippin and Otfried Höffe ed., Hegel on Ethic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50.。在这股法哲学的复兴潮流中又以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问题最为引人关注。一些法学家如帕夫利克就曾依据黑格尔的法哲学宣称,“一种前后一致的、与主体有关的归责模式将会把法律所向往的秩序的实现,慎重、适度地委托给单个的、对法表示服从的主体”。如果公民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拒绝这种协作努力的“共业”(gemeinsame Projekte),那么他就是现实化了的公民的不法,而“刑罚是对公民不法的回应”(2)[德]米夏埃尔·帕夫利克 :《人格体、主体、公民 :刑罚的合法性研究》,谭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72页。。另一些学者如希普和霍耐特则依据黑格尔耶拿早期手稿中的不法理论,试图以“承认”为关键概念,建立一种个体与共同体和谐相处的理论。(3)Vgl. Ludwig Siep, Der Kampf um Anerkennung. Zu Hegels Auseinandersetzung mit Hobbes in den Jenaer Schriften“, in hrsg. von Friedhelm Nicolin und Otto Pöggeler, Hegel-Studien Band 9, S.170-171. 参见[德]霍耐特 :《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3-29页。相对而言,黑格尔晚期的法哲学缺乏“承认”这样的概念,那么是否在法哲学中就无法达成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呢?
在黑格尔看来,以特殊性而非普遍性为第一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个人处于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他曾在耶拿早期的自然法论文中将现代社会个体的战争状态概括为“自然的不法”,并试图在《伦理的体系》中以“为名誉而斗争”的方式来实现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而这一方案由于其古典主义特征而造成了“伦理的悲剧”(4)参见韩立新 :《〈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249-250页。。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从未放弃在共同体中保存个体的自由或者说在个体中保持共同体的伦理性的努力,最终,黑格尔的这一尝试在其法哲学中得到了实现 :不同于其他自然法哲学家,黑格尔既未完全依赖主观德性,又未完全依赖客观强制,而是将两者统一于“无限形式的主观性”的基础之上从而使主体与实体达成和谐状态。(5)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7, Suhrkamp, 1986, S.293.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4页。因此,本文将围绕黑格尔的法哲学,分三步来论证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过程 :(1)自由意志特殊化为“主观性的自我规定”(6)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Werke 7, Suhrkamp, 1986, S.199.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9页。。在没有外在强制法制约的情况下,特殊意志与普遍意志的冲突会陷入“犯罪—复仇”的恶无限中,特殊性不断地进行相互否定的结果是主体在内心中希求普遍的正义而形成了主观的道德法。(2)真实的良心使得主体摒除了恶意而在内心重新确认了普遍的法。当主体依据真实的良心行动时,就恢复了对法的信任与忠诚。(3)为了在现实中维系主体对法的信任与忠诚,需要有司法制度的保障。司法使得市民社会中的不法因素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而最终被扬弃。其作用在于使罪犯在内心中伏法,以实现个体与法、个体与个体以及个体与共同体的三重和解。
一、不法状态 :承认的丧失与复仇的特殊性
黑格尔在两个意义上谈论“自由意志”(der freie Wille) :一个是作为法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的“精神的东西”(7)Hegel, GPR. S.46.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页。,强调自由意志作为实体具有自在的、客观的、普遍的一面;另一个是“作为自我意识的那种形式的意志”(8)Hegel, GPR. S.58.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页。,强调自由意志作为主体具有自为的、主观的、特殊的一面。不法就在于人格以特殊意志为法,而违反了以普遍意志为标准的自在的法。(9)Hegel, GPR. S.172.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1页。不法状态是人格作为法人所处的状态,这其中既没有道德主体所具有的道德律令,也没有伦理状态下的各种现实制度,因而自在的法只是人格的权源和应然的状态。根据特殊意志与自在的法的关系,不法状态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无犯意的不法、诈欺和犯罪。“不法意味着对承认关系的妨碍”,随着其程度的加深,对法的承认和人格之间的承认就逐渐丧失了,法人对自在的法的信任与忠诚也就无从谈起。(10)Kurt Seelmann, ”Hegel und die Strafrechtsphilosophie der Aufklärung“, in Anerkennungsverlust und Selbstsubsumtion, Verlag Karl Alber Freiburg/München, 1995, S.41.
在“无犯意的不法”即“权利冲突”中,特殊意志承认存在着自在的法,但是这种自在的法还只是作为权利根据潜在地存在着。对于它的理解和根据它进行现实的主张,却是由特殊的东西主导的。特殊意志根据自己的利益,认为自在的法是支持自己的,并在这种主张下否定了他人的权利。(11)Hegel, GPR. S.174-176.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3-94页。正如莫尔所说 :“如果一个人处于无犯意的不法之中,那么尽管他本质上是承认法的,但其实他是把某种客观上是不法的东西在主观上当作了法。”(12)Georg Mohr, ”Unrecht und Strafe“, in hrsg. von Ludwig Siep,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7, S.98.而在诈欺中,自在的法是不被承认的,它仅仅是作为特殊意志的手段而存在,因而仅仅只是假象。在契约中取得物的所有权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物的内在普遍性”或价值,一个是“该物原系他人所有”。(13)Hegel, GPR. S.177.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4-95页。诈欺就是在假装尊重后一个条件的时候,同时将第一个条件用欺骗的方式替换成主观和任性的意志的要求。这种替换行为本质上是将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建立在他人的相信或者认同之上,但没有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诈欺者仅仅只将契约中的意见的一致性当作是“这一次单一的行为”,而暗地里隐藏了法权意义上普遍的一致性。(14)Vgl. Georg Mohr, ”Unrecht und Strafe“, in hrsg. von Ludwig Siep,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7, S.99.在从权利冲突到诈欺的过程中,法人完全丧失了对自在的法的承认而沦为以主观任意为法。第三种不法状态是“犯罪”,即“自由人所实施的作为暴力行为的第一种强制,侵犯了具体意义上的自由的定在,侵犯了作为法的法”(15)Hegel, GPR. S.181.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8页。。自由意志只有达到定在才可能被侵犯,因而存在着对所有权和人格的肉体两种侵犯形式。对财产和肉体的侵犯,就是侵犯了固定在这两者中的自在的法。从人格的角度说,实施犯罪的一方本身也是自由意志的定在,那么以犯罪这种不法为法就是一种“否定的无限判断”,也就是说,犯罪的概念成为虚无。这样的自由意志没有规定性,仅仅破坏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自由意志特殊化的极端就是成为虚无和空洞的东西——不仅仅不承认自在的法,而且也不承认一切。(16)Vgl. Georg Mohr, ”Unrecht und Strafe“, in hrsg. von Ludwig Siep, G. W. F. Hegel,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97, S.100.
从第一种到第三种不法,自由意志不断地特殊化,那个最初的自由意志分裂成自在的自由意志和自为的特殊意志。思维把这个差别以最普遍的方式加以固定,就是绝对对立的正义和犯罪,但实际上这种固定的存在却以向对方直接过渡为其灵魂。正义通过扬弃犯罪得到彰显,而法也是通过扬弃不法而实现自身。或者说,犯罪由于其虚无性,它的本质不在自身的概念之中,而是作为否定的法,其规定性在法的概念之中。由于这种“概念的必然性”最终作为理念实现出来,所以不法必须被扬弃。在“抽象法”章,对不法的扬弃是对犯罪的直接的强制或反作用,其主要形式是“抵抗暴力”和“复仇”。而自在的法所要求的“惩罚的正义”还只是一个应然的要求,因为抽象法仅仅是一个法权状态,它还不涉及法律、法庭和具体的惩罚,所以惩罚的正义还不具有现实的效力,它只能假借个体或特殊意志之手来表现自己的存在。(17)cf. Dean Moyar, “Consequentialism and Deontology in Philosophy of Right”, in ed. by Thom Brooks,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Wiley-Blackwell, 2012, p.27.如此,对于自在的普遍的法的概念而言,“抵抗暴力”和“复仇”都是外在的以特殊性的方式表征普遍性。
“抵抗暴力”是受害者的直接防御,虽然在概念和思维中是对正在发生的不法进行直接的、非反思性的抵御,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双方力量的差异,能否成功地抵御不法行为则带有巨大的偶然性,也有可能防卫过度而造成新的不法。“复仇”是对不法的事后强制,是对“强制的强制”。虽然其正义性的依据是一种观念的必然性,或者说自在的法的外在的客观强制,因而是一种报应论的理由。但是它进行“报复”的动机则是受害人的主观意志,这种报复行为只能纠正不法带来的损害,即“肯定的外在的实存”,而并不能恢复法的概念本身,因而是一种威慑论的理由。报复行为同样由于没有客观标准而陷入“不法—过度报复—新的不法”的恶无限中去。(18)cf. Dudley Knowles, Hegel and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 p.165.
黑格尔说 :“对作为法的法所加的侵害虽然是肯定的外在的实存,但是这种实存在本身中是虚无的。”(19)Hegel, GPR. S.185.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0页。在外部可以扬弃犯罪带来的损害,但是在犯罪概念自身内部无法被扬弃。因而即使法在外在的一切地方获得恢复,犯罪带来的损失在一切地方被克服,仍然还有罪犯的内心这一处是法的空白,在这里统治着的仍然是不法。如果不区分犯罪的概念和犯罪带来的“祸害”,就会陷入到威慑或预防主义的片面性中。仅仅从效果上来克服犯罪,会带来复仇的正义,但是同时也是主观性的正义,是主观性的无限报复,以一种犯罪去强制另一种犯罪,犯罪的效果虽然不断地被克服,但是又不断地被产生,因而犯罪概念本身反而持存。
黑格尔将上述不法状态中承认的丧失与复仇的特殊性所带来的矫枉过正称之为自由意志“返回于自身”的过程 :“普遍意志在自内映射中是对纯然自为存在的特殊意志的关系的否定。”(20)Diethelm Klesczewski, Die Rolle der Strafe in Hegels The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991, S.77.这种普遍意志的自我否定带有双重性 :(1)普遍意志通过复仇的正义揭示出特殊意志本身不是普遍物;(2)通过否定特殊意志,普遍意志也摧毁了自身存在与发挥效准(Gelten)的地基。换句话说,在“抽象法”章,客观的自在的法是一种应然,反而主观的复仇的法是一种实然。人格本身是一种排他性的存在者,在自身内并不存在着对彼此信任和忠诚这一类情感,因而对于自在的法并没有任何主观上的情绪要求必然遵守。(21)cf. Alan Brudner, “Hegel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Justice”, in ed. by Thom Brooks,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Wiley-Blackwell, 2012, p.187.
同时也不存在着任何普遍的组织和体系从外部制约人格的任性,自在的法也就因此没有任何制度的保障。所有权作为一种人格关心的只是保护“我的所有权”、“我的人格”和“我的生命”,在抵抗暴力和复仇的过程中他们不会关注和保护别人的所有权、人格和生命。然而保护一般的所有权、人格和生命是自在的法的概念要求,要使得这个要求在一切个体的人格中成为实然的东西,必须形成主体内部的绝对命令。
因此,依据普遍意志的天意而声张复仇的特殊意志实际上就不再是作为天意的法的直接存在,而是一个在自身之内映射的意志。这个自内映射的意志一方面在自身内部将自己设定为与普遍意志相对立的东西;另一方面,它知道只有当自己的意志被其他个别的意志所普遍承认的时候,它的个别意志才有普遍性。(22)Vgl. Diethelm Klesczewski, Die Rolle der Strafe in Hegels The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991, S.77.这反映了道德概念的要求 :“虽然是特殊的主观意志,可是它希求着普遍物本身。”(23)[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8页。譬如,要求“不可杀人”——受害者依据自在的法要求“不可杀人”,这是对他人的要求,当罪犯杀害了受害人,则罪犯面对复仇时也会依据自在的法要求对方“不可杀人”——复仇使得施害者变成受害者,同时使得“你不可以杀人”变成“我不可以杀人”,如此“不可杀人”成为主体的道德“戒律”。通过道德戒律,特殊意志就在内心中获得了一种主观的普遍性,它要求道德主体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赋予这种主观普遍性以客观的形式。(24)Vgl. Diethelm Klesczewski, Die Rolle der Strafe in Hegels The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991, S.78.
二、重建对法的信任与忠诚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样,随着不法程度的加深,对不法的纠正只能诉诸于特殊性,从而引起人格的无限报复。又由于并没有其他的外在制约,对不法的扬弃转而在内心中要求道德法则。黑格尔认为,“为了满足对他人的邪恶、对他人加于自己或别人、全世界或一般人的不法所抱的感情,因而消灭这种包藏邪恶本性的坏人,以期对杜绝邪恶至少有所贡献”,这些行为都出于善良意图,都是善行。(25)Hegel, GPR. S.27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0-151页。也就是说,出于对他人的恶的厌恶,进而对一切不法的厌恶都是一种善良的意图,这种意图期望通过消除恶来消除不法。而在黑格尔看来,“意志作为主观的或道德的意志表现于外时,就是行为”(26)Hegel, GPR. S.211.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6页。。根据善良的意图去行事,就能在外部消灭不法,同时内心也与普遍的法保持一致的状态。因而,扬弃不法的关键在于消除主体的恶意,反过来说,在于在道德中重建真实的良心,重建主体对法的信任与忠诚。
在抽象法通过主体的主观意图上升为主观普遍的道德意志的法的过程中,埋下了恶与良心的根源。黑格尔说 :“在反思的领域中,伴随着主观普遍性的对立,这种主观普遍性时而是恶,时而是良心。”(27)Hegel, GPR. S.213.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7页。主体根据自身的特殊性为自己的行为和目的进行评价 :当行为的具体内容加入到道德法的形式之中的时候,主体要依据利害关系判断自己的行动“应当”或是“不应当”。恶与良心的分野就在于主体对自己的行为的判断是否与自在的法一致,它不同于康德的道德法,康德的道德法并不涉及任何功利和效果的判断,而仅仅停留在对动机的判断中,黑格尔则要求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判断,因而效果和动机都要进行考虑。恶的根源就在于主体将意志的特殊性当作行动的普遍原则。其自在的形式就是主体将意志的自然性当作自由,将自身的任性提高到普遍物之上,并将它作为行动的原则而为非作歹。诸如情欲、冲动、倾向等意志的自然性本身并非一定就是恶的自为存在,但是如果将它们提高到普遍的规定性的高度,将它们作为行动的原则,这就是恶。(28)cf. Timothy Brownlee, “Hegel’s Moral Concept of Evil”, in Dialogue Vol. 52 (2013), p.86.
除了表现为自然意志的恶,形式的良心则是恶的更为隐蔽的形式。在黑格尔看来,形式的良心与自在的恶在抽象的自我规定中有共同的基础。一般说来,良心(Gewissen)也是一种主观性,但并不是任性的主观性,而是在自身内部认识到和确信客观的自在的法,并自觉地遵守这个法。黑格尔说 :“这一主观性当它达到了在自身中被反思着的普遍性时,就是它内部的绝对自我确信(Gewissheit),是特殊性的设定者,规定者和决定者,也就是他的良心。”(29)Hegel, GPR. S.254.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39页。但是,如果良心仅仅坚持形式的主观性,那么它就处于“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30)[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3页。。因为尽管形式的良心在自身内部也追求普遍性,但是这种主观的普遍性仅仅是形式的和抽象的东西。或者说,它只是给出了一个一般的行动原则而缺乏具体的内容。而在实际行动中,真正依据的不过是主体自己确信的主观的东西。譬如,“不可杀人”作为道德戒律是针对一般的普遍情况,但是具体的情况会使这个一般的规律出现二律背反 :在保家卫国的战争中杀敌恰恰也是应该遵循的道德戒律。更为恶劣的情况是,作恶者反而依据这个空无的形式而宣称自身恶行的相对的正确性。如此,形式的良心就沦为了伪善。
为了消除恶意与重建真实的良心,需要给主观的普遍性注入客观的内容。这个客观的内容来自于伦理实体。在黑格尔看来,伦理实体是“活的善”,它通过主体的行动而成为现实的东西,而与此同时,主体的行动也在“伦理性的存在中”有其目的。(31)[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64页。换句话说,伦理实体的标准才是主体行动的客观原则。那么,主体在主观上按照伦理的要求而行动就是对伦理实体的信任。布朗利说 :“黑格尔强调伦理本身预设了其成员对它的信任,如果没有这种信任,某套制度就无法使自由的生活成为可能。这种信任有两种形式,即制度性的和主体间的。”(32)Timothy Brownlee, “Hegel’s Moral Concept of Evil”, in Dialogue Vol. 52 (2013), p.94.而“道德”章的顶点就在于消除了主体内心的不法与恶意,确立了真实的良心的地位。这为主体对自在的法与伦理的信任和忠诚提供了可能性。而要在现实中维系这种信任,还需要客观条件 :在这个客观条件中,主体“必须能够在参与伦理制度的过程中体验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保留和包容’,并且感觉到制度不是对自己的外在强制,而仅仅是表达自己对它的信任”(33)Timothy Brownlee, “Hegel’s Moral Concept of Evil”, in Dialogue Vol. 52 (2013), p.94.。
当主体遵循真实的良心而行动时,在外部他就是符合法的自由的存在者,在内部他就对自己的特殊性和任性设定了法则,因而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借由真实的良心,主体就将恶的可能性控制在萌芽中。遵循真实的良心而行动,法就在主体身上达到了主客观的统一,外在的自在的法与内在的自为的法就在良心中结合为自在自为的法,因而也就是自由。但当主体的行为偏离了真实的良心时,则必须由伦理实体对主体进行纠正,并使得主体重新认识到客观的普遍性的权威。这一点只有在司法制度中才能做到。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
在市民社会中,特殊的自由意志和普遍的自由意志的分裂与对立以特殊性原则和普遍性原则的形式保留了下来。所谓特殊性原则是指“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而普遍性原则强调的是市民社会作为需要的整体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因为“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34)Hegel, GPR. S.339.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页。关于这一点的分析可以参看韩立新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研究》,《〈巴黎手稿〉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28页。。普遍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的矛盾就具体化为社会财富的普遍增加和分配不均,而正如不法的根据在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市民社会的这种内在矛盾导致了贫困,而这是市民社会的不法的根源。
贫困表面上导致了穷奢极欲、道德败坏和贫病交迫等社会现象,但是更大的问题其实在于,市民社会的自由表现为通过财富和需要使人格达到自己的定在而实现自身,而贫困恰恰使得人格无法获得定在,从而导致自由无法实现。贫困会导致市民社会的形式普遍性的破裂,因为它导致了一个被排斥在这个自由体系之外的群体。“在社会状态中,匮乏立即采取了不法的形式,这种不法是强加于这个或那个阶级的。”(35)Hegel, GPR. S.390.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5页。这种阶级就是“贱民”——从黑格尔的描述来看,贱民的概念包含两点 :其一是贫困而不能自食其力,另一个是丧失了从自食其力中获得的“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其中第二点是贱民的本质,它表现为对财富、社会和政府等普遍物的“内心抵抗”。这种内心的抵抗是一种“卑贱意识”,它“认定国家权力和财富这两种本质性都与自己不同一”(36)Hegel, PG. S.372. [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8页。。一方面,它只在财富当中意识到了自身的“个别性和享受的变灭性”(Verganglichkeit),因而在贫困中固守自己贫瘠的精神本质,放弃了从劳动实践的教化中认识普遍物的可能性(37)Vgl. Diethelm Klesczewski, Die Rolle der Strafe in Hegels The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991, S.210.,另一方面,它视社会、政府和国家等普遍物都是对自己自由的束缚和压迫。所以贱民要么退回到自暴自弃的斯多葛主义者,将普遍物放置在自身之外而置之不理,只在乎自己清高的特殊性;要么堕落为暴民,敌视社会和国家,伺机进行犯罪和叛乱。
市民社会的司法体系会顾及到“从这种状况和他们(贱民)所受不法待遇的情感中产生出来的其他罪恶”(38)Hegel, GPR. S.388.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43页。,但是仅仅依靠司法并不能完全限制贱民数量的增加和消除贱民对市民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矛盾的存在在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贱民完全陷入自身个别性当中的纯粹特殊性,他们没有组织,也不会联合,他们对于社会的敌视完全是出于自私的情感,而对于处于相同情况的其他同类,他们相互之间的态度是冷漠的,所以,他们对社会整体进行的犯罪表现为自己的一己之力的不法。在抽象法中,这些犯罪行为针对的是个体的财产和人格,而在市民社会中它们伤害的是受害人以及他背后的“整个市民社会的观念和意识”(39)Hegel, GPR. S.372.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8页。。
司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普遍的财富不受不法的伤害,而更一般地说在于保护所有权不受伤害。在抽象法中,所有权是由特殊的人格以抵抗暴力和复仇的方式进行自我保卫,在形式上表现为特殊性保护特殊性;而在市民社会中,是由整个司法体系保障所有的所有权,在形式上表现为普遍性保护普遍性。因此,总的说来,司法的目的在于以保障特殊的自由的方式来保障普遍的自由。而犯罪不论是在抽象法部分还是在市民社会中都是个别的和特殊的,因而司法对不法的扬弃就是普遍性对特殊性的扬弃。
司法的普遍性在于它是“作为法律(Das Gesetz)的法”,这个普遍性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它是被自在的法设定(gesetzt)到语言中的“普遍有效的东西”,普遍性的第一层含义就是立法的普遍性;其二普遍性要求对法进行言说和公布,普遍性的第二层含义是法律的公开性。(40)Hegel, GPR. S.361.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18页。第一层普遍性在层次上比第二层普遍性更高,也更具普遍性,它属于国家的立法权的普遍性,即宪法(Verfassung)的普遍性。“立法权所涉及的是法律本身(因为法律需要进一步规定),以及那些按其内容来说完全具有普遍性的国内事务”(41)Hegel, GPR. S.465.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5页。,因而较之一般的司法,宪法涉及的是公民对于作为最高普遍物的国家的一般权利和义务 :“个人从国家那里可以得到什么”和“个人应该给国家些什么”(42)Hegel, GPR. S.466.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6页。。这种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确定根据上是由国家主权或作为单一性的主体的国家来决定的,但是这只是进行最终决断的国家主权的自我规定(Selbstbestimmung),因而是完全形式的方面。被决断的内容在于等级要素及其代表、选民及其议员所进行的讨论和决议,同时也包括公共舆论的意见,这些内容或者具有真理性,或者流于特殊性和任性,因而只是立法的补充和被规定的内容。黑格尔说 :“各等级对普遍福利和公众自由的保障,并不在于他们有独到的见解……部分地在于代表们的见解补充了高级官员的见解。”(43)Hegel, GPR. S.470.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19页。这种最高的普遍性与普遍的特殊性的结合与统一是实现了的自在自为的法。在宪法(Verfassung)中,作为自在的法的民族精神、伦理实体的风俗习惯就被书写(verfassen)出来,这种被书写出来的宪法就是具体司法的普遍性根据。
此外,司法本身也应该具有公开性,即司法的内容和规定应该传达到每一个个别意志的意识当中。从外部方式看,这意味着司法首先必须取得外在的形式,即成文法或者关于不成文法的书面的知识;其次得对更为具体的特殊问题作出一般的解释和规定。从内部方式看,法律的语言必须是有理性的人都能明白的语言,同时市民自身要有共同的公共生活,并在其中培养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和意识,否则“他们诚然有权摆动两条腿,亲身跑去出庭”,但是他们无法使用这些知识,法对于他们来说仍然只是“外在的命运”(44)Hegel, GPR. S.381.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6页。。
但是仅仅有法律的条文和体系,法律本身还没有取得自己的“无限形式”,要成为活的、真实的法律,就得有法官和法院。他们是普遍的特殊性,一方面是个体,一方面是法律的主体,要通过自己的理智将自在的法的精神贯穿到法律之中,将伦理实体的真实意志贯穿到审判当中。尽管法律是面向特殊性的普遍性,但是它所处理的事务是完全偶然和繁杂的,案情的杂多表象不可能自动对应到某个法条,而总是必须由具体的个别的有理性的人来进行辨别和归纳,而惩罚的尺度总是在一个范围内确定的,这就得由法官和法院根据经验做出判断。如果缺乏这些活的理性,法律就会沦为空洞的条文——要么过于死板导致严酷的惩罚,要么过于宽松而使得冤屈没有得到昭雪。
法官和法院毕竟是法律的主观理性,而不能凭借个人的任性去处理法律事务,否则就沦为一种不法,使得法律成为专断的东西而完全堕落。他们应盖抛开个人对特殊利益的主观情感,但是“在历史上,法官和法院的产生可能采取过家长制关系,也可能采取过权力或任意选择的形式”(45)Hegel, GPR. S.373.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9页。。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中,法官和法院超过了自身的权力范围,僭越到了立法的环节当中,他们虽然没有改变法律的形式,但是实际上却篡改了法律的内容。要限制这种情况,不仅仅要依靠法官们的个人的德性,还要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也就是说,要有一系列的程序来保证法律各个环节的客观性,诸如侦查程序、诉讼行为、专职法官对事件进行归类、证据的呈现、陪审法院、判决前的审议以及公开审判等等。
以上是司法体系的普遍性的来源和构成。当罪犯和嫌疑人来到法庭上的时候,当他身处于这个普遍性的结构和体系之中,他这个特殊性面对的不仅仅是受害人,更为根本的是代替受害人的“受害的普遍物”。他要在法庭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作出陈述,将自己的任性直接地、完全地暴露在普遍性面前。从而由于特殊性的力量的弱小,他完全地拜服于普遍性的权威之下,发现自己的任性并非真理的一方。另一方面,法院从外部实施强制,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惩罚,从事实的必然性上纠正不法带来的损害,或是责令他直接进行补偿,有时往往为了预防的作用而加大补偿的力度,或是在等价值的情况下用其他的办法补偿。对他的不法进行纠正的正是作为普遍物的法律,因而司法对不法的扬弃是“法律同自身的调和,由于犯罪的扬弃,法律本身回复了原状,从而有效地获得实现”(46)Hegel, GPR. S.374.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30页。。综上所述,在司法部分特殊性有一个走向普遍性的过程——从罪犯的任性,到法官的普遍的特殊性,再到司法系统的形式普遍性,最后到达宪法的真实普遍性。
一般说来,法律以强制的方法纠正不法就已经是对普遍性的恢复,但是黑格尔的强制法是依据伦理精神现实化的宪法而设定的,而不是依据共同意志或契约论制造出来的。所以,黑格尔的强制法还要求主体的内在环节也要恢复普遍性,这一点表现在罪犯不仅出于法的权威而伏法,而且出于内心对法的确认而认罪,换句话说,罪犯要重新认同自身与伦理精神的一致性。(47)Vgl. Diethelm Klesczewski, Die Rolle der Strafe in Hegels The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Berlin: Duncker und Humblot, 1991, S.280-281.那么认罪何以可能?黑格尔认为 :“行动只有作为意志的过错才能归责于我,这是认识的法。”(48)Hegel, GPR. S.217.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19页。认罪的第一步是归责的可能性,只有罪犯的不法行为和其意志的错误一致时,他才能被归责。意志的过错不仅仅在于罪犯在动机上是恶的,而意志的主观疏忽也是可以被归责的——主动作为的恶和不作为的恶。第二步是罪犯对自己行为的主观认识,“犯人在行为的瞬间必然明确地想象到其行为是不法的”,知道自己是要受到处罚的。(49)Hegel, GPR. S.247.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版年,第135页。这一点是为了判别犯人是否具有足够的理性,如果他本身的理性是不完整的,则在概念中他的存在既不是合法的,更不能是不法的。他应当受到限制,但是这是针对他可能进一步带来损害,而不是因为他故意犯法。
客观上的意志的错误和主观上认识到不法并不必然导致罪犯认罪,而只是为他内心的内疚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情绪上的倾向就是认罪的意向(Gesinnung)。当他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时,他就是一个脆弱的灵魂,自知在道德上理亏,因而总在逃避与法的正面对视。他只是为了逃避惩罚,所以不愿伏法认罪,而隐瞒自己的真实情绪和行为。促成认罪的意向成为真实的行为也需要一系列步骤。首先是保障罪犯的主观意识的权利,使他有为自己进行辩护的能力,以解除他对于法的恐惧,而不必过分担心受到多余的惩罚。其次在于保障法的程序与仪式的威严,使得罪犯拜服在法的权威之下,同时唤醒他内在的对法的崇高感与尊敬。再次在于要有一个陪审制度以防止罪犯“赖皮”,陪审法院使得社会的表象有一个具体的实存 :“陪审团的成员与罪犯都是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分享了同一个伦理实体,陪审团代表了罪犯的灵魂……并满足了‘主观性和自我意识的权利’,他们的宣罪对于罪犯而言并非外在之物。”(50)Mark Tunick, “Hegel’s Immanent Criticism of the Practice of Legal Punishment”, in Hegel's Political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122.作为普遍的法的中介,陪审团替罪犯的良心说 :“我犯了罪。”(51)Hegel, Philosophie des Rechts nach der Vorlesungsnachschrift K. G. v. Griesheims 1824/1825, in hrsg. von Karl-Heinz Ilting, Vorlesungen über Rechtsphilosophie 1818-1831 Bd. 4,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73, S.579.作为最后一个环节,犯人的自白或者陪审团的宣罪起着三重和解的作用 :罪犯自身的法与普遍的法的和解;罪犯与受害者的灵魂的和解;特殊意志与社会的表象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