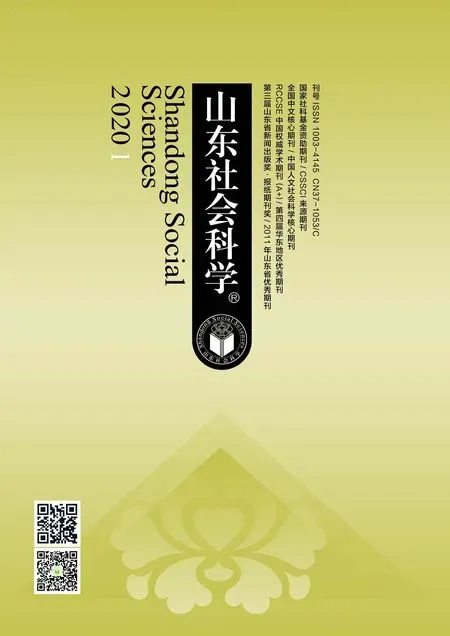古代诗经学的意义维度与阐释策略
——兼谈《诗经》的文学阐释何以可能
郑 伟
(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经学是通经致用的学问,古代学者“下学而上达”,由知识而通义理,须从经典之中阐释出为我所用的价值来。因而透过现象看本质,虽说经学史上有着无数的知识性差异,但鲜有逸出经学义理的存在方式这一主题。对此,哪怕是最具“科学精神”的乾嘉学者,也仍然抱有“训诂明而义理明”的期待,否则也就不成其为经学了。抱定经学的广大宗旨,我们就不能片面地满足于知识整理的成就,而应当更内在地谈论经学的义理到底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种追问体现了经学价值论研究的必然之义,还有待于我们做出更好的回答。尤其是对诗经学而言,这种追问是颇具代表性的。由于《诗经》很特殊,它具有声诗、文字诗和文学诗的多重性质,因而形成了多元化的自身阐释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规定了经义建构的多维理路。或者以《诗》属乐,从音乐角度来治《诗》;或者以诗说《诗》,用文学的观念来解《诗》;主流则是坚持“主义”之维,通过文辞义训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义理诗经学。这样三种维度参与到古代诗经学的建构之中,主导着经学意义的生产。对此,如果缺乏一种彻底之思,我们将很难从逻辑上把握诗经学史的内部结构,以及某些关键人物所具有的确立学术范式的重要意义。在今天,现代语境早已重构了《诗经》的性质,人们也乐于谈论《诗经》的文学阐释史,有时不免“定向”地寻摸出无关教化的现代意义来——仿佛古代真的存在着那样的一群“放任自流”的经学家。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无论他们采取何种维度,都旨在明道致用,都联系着该如何保障经学义理这一用心。换言之,教化理路的问题乃是诗经学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说彻底的“主声”和“主文”之维将要威胁到“思无邪”的正旨,那么,多维交织的诗经学史就常常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冲突,或者通过特殊的阐释策略来化解这种矛盾,从而构成了诗经文学阐释史的主线。
一、郑玄与义理诗经学的确立
《诗经》本来是“以声为用”的周礼乐章,后来逐渐成为一种可供阐释的文本。这种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到汉代郑玄等儒者将周礼乐诗彻底地改造成一部文字经典,其建立的“重义而不重声”的阐释体系才得以宣告完成。其影响不待多言,正如宋人郑樵所说 :“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若不能歌之,但能诵其文而说其义可乎?不幸腐儒之说起,齐鲁韩毛四家,各为序训,而以义说相高。汉朝又立之学官,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1)[宋]郑樵 :《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83页。先秦以来,随着礼崩乐坏,《诗经》的文字义便凸显出来成为秩序重建的资源;而汉代的君权专制则开启了局限在君臣关系之狭小空间的“诗云”时代。在这里,郑樵没能理解汉儒“以义理相授”的必然性,但他将宋学纳入汉儒“义说”的思想谱系,从而勾勒出“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2)[宋]郑樵 :《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83页。另外,郑樵在《通志》的《原学》和《乐府总序》之中,以义理之学贯通三代以后尤其是汉以后的学术史,而《通志》本身也是针对“宋人以义理相高”的弊端而发的。如此说来,郑樵认为汉、宋义理之学是一脉相承的,而他反对宋学的空疏就追溯到它的汉学源头那里去。这种认识对我们重新理解汉、宋之学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的脉络来。这种观点颇具启发性。
汉代四家诗,只有郑玄笺注的《毛诗》流传下来。在他之前,儒家的《诗》学理论和解释形态尚不完备,时代最近的《毛诗序》也还残留着乐文化的痕迹。(3)比如《毛诗序》说诗歌具有“动天地,感鬼神”的力量,能够导致清明政治的出现等等,严格地说只有置于乐教语境下才是可以理解的。对此,《孔疏》曾专门提示说 :这种功能是通过《诗》的乐用来实现的,“此《序》言诗能移俗,《孝经》言乐能移风俗者,诗是乐之心,乐为诗之声,故诗乐同其功”。等到郑玄笺注《毛诗》的时候,就设置了双重的“义说”依据 :既总论群经,以为“皆天神言语,所以教告王者也”(4)[汉]郑玄 :《六艺论》,载[清]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88页。;又从诗人作诗、孔子录诗的角度来维护经典的文辞义理。由此,则《诗经》乃是天神垂教的言语,王者或顺或逆以行事,诗人或美或刺以属文,后经孔子删诗取义而得。这样,周礼乐诗就成为纯粹的文字书写,即一种言教文本。这是郑玄诗经学的一个逻辑基点。
郑玄自然是清楚周礼乐诗的,但他似乎有意识地与之保持了距离。首先,关于《诗》的作由。所著《诗谱序》和《六艺论》反复申张“弦歌讽喻”“颂美讥过”的诗道,《周礼注》更将“六义”解释成关于政治善恶的六种言说方式。但这个诗道本身即有“可疑”之处,因为它如此的纯粹,几乎将先秦以来的诗用传统(比如儒家的修身诗学)排除殆尽,更没有给乐教留有余地。在毛诗学派看来,诗歌的价值端在于美刺教化的功能。《毛诗序》有“(国史)吟咏情性,以讽其上”的观点,郑玄《毛诗笺》进而在史实层面上落实“颂美讥过”的诗道,孔颖达《毛诗正义》更直截了当地宣称 :“凡是臣民,皆得风刺,不必要其国史所为”(5)[唐]孔颖达 :《毛诗正义》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毛诗序》“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的观点,也是经过郑玄诗学的承接,后来在孔颖达那里就凝结为一颗“乐歌民诗,诗述民志”(6)[唐]孔颖达 :《毛诗正义》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的诗心。说得都很明白,《诗经》是缘政而作的历史叙事,而诗人负有美刺其君、防邪止僻的言谏职责。总之,在郑玄那里,《诗》之神圣性联系着儒家的道义精神及其身份意识,意指一种通过文学来介入政治的实践精神,一种为天下代言的话语立场。这即是毛诗学的精髓之所在。
其次,关于《诗》的运用。郑注《毛诗序》“主文谲谏”和“国史作诗”之说,云 :“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曚歌之。其无作主,国史主之,令可歌”。(7)[唐]孔颖达 :《毛诗正义》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5页。这里重复了《六艺论》中“诗者,弦歌讽喻之声也”的观点,实则将声歌之道混入诗的“义用”层面,只将“弦歌”看作有利于讽喻的形式。如其说,《诗》的作用就不是表现为“以声为用”的仪式职能,而是取决于《诗经》的文本价值与诗谏制度的支撑等等。郑玄对《诗》的演唱性质是了解的,比如对弟子“何诗近于比赋兴?”的提问,就说 :“比赋兴,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8)[唐]孔颖达 :《毛诗正义》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在他看来,孔子录诗的意义非比寻常,自此《诗经》成为一部美刺教戒的文字经典,所以郑玄对《诗》的声用采取了一种漠视的态度。
再次,关于《诗》的编录与诗史问题。《毛诗谱》云 :
文、武之德,光熙前绪……其时《诗》,风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鸣》《文王》之属。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礼作乐而有颂声兴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风、雅而来,故皆录之,谓之《诗》之正经。后王稍更陵迟……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以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则受颂声,弘福如彼;若违而勿用,则被劫杀,大祸如此。(9)[唐]孔颖达 :《毛诗正义·诗谱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正变论包含了郑玄对诗人之意和圣人之旨的理解,兼及《诗经》的部类和时运升降的诗史。在他看来,诗歌的价值端在于谏政与垂教的功能。所以郑玄“蔑云”上古歌诗,只将虞舜时代的“用诗规劝”作为诗道的滥觞。同样的道理,按照“礼之初起,盖与诗同时”(10)[汉]郑玄 :《六艺论》,载[清]严可均辑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90页。的设定,“诗亡”的结局也就难以避免了。这种着眼于诗与礼的共生关系而来的诗史观念,大有深意。一方面,从“录诗”的角度来看,正变说暗合孔子笔削《春秋》的用意,即通过风雅正变的划分来行使文化批判的权力,寄托拨乱反正的用心。这样的诗史观念,已经不限于诗谏的实际运用,更表达了儒家垂教万世的文化意识。而在另一方面,郑玄将上古之歌与陈灵以后的诗歌排除在外,只把诗史框定在制度化的诗谏时代,这说明其所关注的并非诗歌的自然史,而是儒家的诗谏话语还能否起到实际的效果。换言之,郑玄是把诗歌当作介入政治的一种话语方式来看待的。
经过郑玄“有谱有笺”的传述,诗经学的表述有了重大的变化。诗人作诗是“颂美讥过”的劝谕,国史用作“弦歌讽喻”的谲谏,孔子编成垂教万世的明法,也都是从文字义的层面来体认诗歌的教戒意义。最终反映在《诗经》的文本阐释之上,郑玄之后的毛诗学形成了体例完备的阐释系统 :既在章句层面上训诂考据、解读物象,通过“标兴”的方式折入“譬喻政教”的诗人之意;又在历史的层面上以史传经,通过“正变”阐释来提炼《诗经》的史鉴价值;最后上升到文化批判的层面上,揭示“孔子删诗”的无限深意。在这个阐释系统中,比兴阐释是价值的初步赋予,正变阐释是经学意义的根本保障(对于那些不便“标兴”或漏标之诗,经义是在历史框架中自动地生成的),文化批判则更进一步赋予经义以垂教万世的普遍价值。这种复合型的阐释机制,滤掉了《诗经》的声歌性质和诗性活力,将整部《诗经》阐释成为关于历史的叙事与道德寓言,亦成为张扬王道教化的意识形态渊薮。总之,在郑玄那里,周礼乐教混同于《诗经》的言教功能而消失殆尽,而义理诗经学随着《毛诗正义》官学地位的确立,遂成为诗经学史上的主流,影响极为深远。
二、郑樵以后声、义二维诗经学的内部结构
虽然诗经学史上以乐论诗的不少,但真正贯彻“主声”之维来建构新《诗》学的实不多见,或如郑樵所说这是一段“义理之说既胜,则声歌之学日微”的历史。郑樵是南宋初人,彼时的科举用书采取的是王安石主持编撰的《诗经新义》。王氏“音声者,以文为主”(11)[宋]王安石 :《诗义钩沉》,邱汉生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页。和“诗字从言从寺,谓法度之言”(12)[宋]王安石 :《字说》,载《宋元学案》卷九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50页。的诗经学观念,及其“诗礼足以相解”的方法,体现的正是典型的“义说”思路,也即文辞义训的义理维度。闵道安曾经撰文指出,郑樵主声诗学的潜在论敌就是王安石。(13)参见闵道安 :《诗经学上的转折点 :论宋学关于诗乐问题》,载[美]田浩编 :《宋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那么更进一步说,郑樵的卓见是将王安石的新经义追溯到汉学源头那里去,通过重构孔子删诗之旨,从而抽离了汉、宋义理诗经学的立论基础。
郑樵著《通志·乐府总序》说 :“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自后夔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八音、六律为之羽翼耳。仲尼编诗,为燕享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也。”(14)[宋]郑樵 :《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83页。从乐教传统来审视孔子编诗,也就只在“正乐”,非关文辞义理之取舍。以此为基点,郑樵猛烈抨击了汉儒的“删诗取义”之说,以及此后乐道沦亡的历史。他甚至重新定义了诗六义,诸如“风雅颂皆声”、“风雅无正变”、二雅“特随其音而写之律耳”、“诗之本在声,而声之本在兴”、逸诗为六笙诗“不必辞也,但有其谱耳”(15)顾颉刚辑 :《郑樵诗辨妄附录四种》,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249、249、245、230页。等等,这些观念不啻是对汉儒义理诗经学的一次体系性的拆解。
郑樵诗经学最突出的地方,一是他的 “淫诗”之说。郑樵把“说义”排除在孔子删旨以外,进而扫除了历代层累起来的诗教伦理内涵,也就发现了《诗经》中大量“淫奔者之辞”的存在。人所周知,关于“淫诗”问题,历史上通常是转换为“刺淫”和“述淫”之诗,才能走出解释的困境。但对郑樵来说,其之所以能够正面地确立“淫诗”说,是因为他是从“乐”上来把握诗的教化的。其云 :“孔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亦谓《关雎》之声和平,闻之者能令人感发,而不失其度;若诵其文,习其理,能有哀乐之事乎?”(16)[宋]郑樵 :《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87-888页。乐教的精神即是“正声育人”,由理想人格的养育勾连起艺术的政教价值,非是道德义理之外烁也。所以郑樵才认为,若把《关雎》当作文字诗来看待,是起不到这样的效果的。虽然他没有具体地谈及“淫诗”的教化问题,但“孔子正乐”的视野蕴含有这样的潜词,即这些诗歌于义属“淫”,于声属“正”,归于乐教的文化统绪。
二是以“声歌之音”贯通古今,重建诗史。所著《通志·乐府总序》“以诗系于声,以声系于乐”,以汉魏乐府接续风雅传统,反对将诗史框定在三代之内。这种观点显然是针对郑玄而发的,因为后者用讽谏之义来剪裁诗歌史,导致了“诗亡”。对此,郑樵很不以为然,他说 :“史家不明仲尼之意,弃乐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又说 :“古之诗曰歌行,后之诗曰古近二体。歌行主声,二体主文,诗为声也,不为文也。”(17)[宋]郑樵 :《通志二十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887页。在他看来,由于史家不明孔子正乐之义,“弃乐府不收”,导致诗歌史误入了文字诗的歧途。郑樵重建声歌之道,是把乐府歌诗当成“宛同风雅”的后继者来看待的。所著《通志·乐略》以“乐府正声”继《风》《雅》,以“祀享正声”继《颂》,对汉魏以来的乐府曲调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应该说,郑樵此论确有它的合理之处,它走出了郑玄诗史论的拘囿,发掘出音乐文学史的潜流。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郑樵的主声诗经学在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四库总目提要》称 :“郑樵作《诗辨妄》,决裂古训,横生臆解,实汩乱经义之渠魁。南渡诸儒,多为所惑。”(1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九《蠹斋铅刀编提要》。这里的“南渡诸儒”,包括朱熹、吕祖谦、王质、李樗和陈知柔等人。其中,李樗和陈知柔乃是郑樵的同乡。陈知柔曾劝导朱熹“《诗》本为乐为作,故今学者必以声求之”(19)《朱熹集》卷三十七,郭齐、尹波点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3页。的道理。李樗也反对王安石“音声者,以文为主”的观点,认为“此不知诗之理者也”;并教导后学说“诗之用于乐者如此”,“学者不可言语文字求”。(20)[宋]李樗、黄櫄 :《毛诗李黄集解》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13页。其所引证的观点,就是郑樵的声歌之说。
但必须指出,虽然宋人也从声歌的角度解诗,骨子里却是根深蒂固的义理观念。这样二维建立起来的诗经学,常常陷入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之中。比如吕祖谦对诗乐关系的理解,其云 :
《诗》,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间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桑中》《溱洧》诸篇,作于周道之衰,其声虽已降于烦促,而犹止于中声,荀卿独能知之;其辞虽近于讽一劝百,然犹止于礼义,《大序》独能知之。仲尼录之于经,所以谨世变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郑果尝庞杂,自卫反鲁,正乐之时,所当正者,无大于此矣。(21)[宋]吕祖谦 :《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90页。
这里讲到《诗》有两种性质,包括“荀卿独能知之”的“中声”,以及“《大序》独能知之”的辞诗和“止于礼义”的文字义。由此上溯到孔子删诗那里,自然认为那是根据“声音”和“文义”的双重标准来进行的,因而也就没有“淫诗”的着落了。所著《吕氏家塾读诗记》卷首《纲领》和《诗乐》两章,前者只就文辞体认义理,反对“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后者专在乐上把握诗用,以为“《诗》皆雅乐”。二者的教理有别,但当吕祖谦做出“(淫)诗皆贤者所作,直陈其事,所以示讥刺”(22)参见朱鉴《诗传遗说》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16页。等判断的时候,实际上重新融入了义说的思路,才得以化解“主声”说的威胁。
“淫诗”问题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公案,除了“刺淫”的理解以外,郑樵和朱熹都认为是“淫奔者自述之词”。虽然朱熹自称是受了郑樵的影响(23)参见《朱子语类》卷二十三 :“诗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劝,恶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恶事至多。此等诗,郑渔仲十得七八,如《将仲子》诗只是淫奔。”,但他们的理路是很不相同的。朱熹认为“淫诗”乃是删诗取义的有意留存,“乃是要使读诗之人思无邪耳”(24)[宋]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39页。。现在看起来,吕、朱对“淫诗”的理解,前者的学理依据固然高明,却难以承受“据文求义”的语境压力;后者回应了《诗经》的自身诉求,但不免有“厚诬圣人”的嫌疑。两说都不如郑樵诗经学来得自洽,实则骨子里的义理观念之使然也。对此,他们也是有所自觉的。比如吕祖谦曾告诫朱熹不要误信郑樵 :“若如郑渔仲之说,是孔子反使雅、郑淆乱;然则正乐之时,师挚之徒便合入河入海矣,可一笑也”(25)[宋]吕祖谦 :《诗说辨疑》,载束景南 :《朱熹佚文辑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页。。朱熹也拒绝了陈知柔“必以声求之诗”的劝告 :“愚窃以为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也。然则志者诗之本,而乐者其末也”。(26)《朱熹集》卷三十七,郭齐、尹波点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3、1673-1674页。在后来,王柏对朱熹的态度大加赞赏,所谓“善夫朱子之答陈氏” :王柏也反对“主声而不主义如此”的郑樵,认为其说将要颠覆“玩味其词意而涵泳其情性”的诗教根本。(27)[宋]王柏 :《诗疑》卷二,朴社1935年8月印行,第39、61页。吕祖谦和朱熹都擅长以声论诗,但他们清晰地意识到 :彻底的声歌维度将要威胁“思无邪”的正旨。所以就暗自地用“删诗取义”置换了孔子正乐的主题。所不同者,吕氏“刺淫”之说回到了汉儒那里,而朱熹则通向了“废序”之路。但朱熹的“废序”并不彻底。对此,何定生先生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 :
朱子对于诗经的乐歌解释,除六笙诗之外,其余完全和仪礼的郑注相一致,但郑注对于仪礼的礼乐观念始终是脱离不了诗谱的,所以注释的对象虽然是仪礼的乐章,骨子里依然是有一个有诗无乐的义理观念。这样一来,不但一部仪礼的乐歌关系被曲解了,即周礼礼记所由的乐歌关系也无不在同一原则下被曲解,这是郑氏的诗教思想体系。朱子既依照仪礼来解释诗经的乐歌关系,自不能不入郑氏的毂中而不自觉,这是朱子虽反诗序而也终于挣不了序说的一个基本原因。(28)参见林庆彰编 :《诗经研究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412页。
这篇文章还提到,汉人不知变诗入于乐,而宋人不知变诗入于“无算乐”,都忽视了周礼语境下“重声而不重义”的诗用性质。一旦离开了原始的礼乐关系,郑玄确立了“颂美讥过”的诗道,朱熹抉发了“思无邪”的人生教义,前者注重美刺其君的规谏作用,后者着眼于风动教化的人生功能,也都只能更加务实地采取以文设教的办法了。在古代诗经学史上,郑玄义理诗学和郑樵声歌诗学是最彻底的,故而它们之间构成了体系性的对抗;朱熹则兼取声、义之二维,所以有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存在,表现为以“废序”的姿态落入了序说的窠臼。
南宋以来,以乐论诗的风气渐开,相关的著作之中常常能够见到“诗乐”的专章。学者集中讨论《诗经》的入乐问题,由程大昌的“国风徒诗”之说而渐进于全部入乐的观点;又大抵反对郑樵、朱熹的“淫诗”之说,而和吕祖谦一样把孔子正乐看作兼取义理的行为。明代顾起元《说略》认为 :夫子正乐之后,风雅颂“非特意义相属,亦其音律相比”(29)[清]顾起元 :《说略》卷十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6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68页。。清人黄中松也说 :“凡诗,各有其音节,各有义理,犹不失为中声,故夫子录之也。”(30)[清]黄中松《诗疑辨正》,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15页。晚清魏源所著《诗古微》反复强调“声与义之不相离也”,认为孔子“以其声中,其德盛,其义阂深而无不存”(31)参见《魏源全集·诗古微》之“正始上”“诗乐篇二”,岳麓书社2011年版。。由此及于“淫诗”的问题,明代杨慎以“过”释“淫”,对清儒的启发很大。他说 :“《论语》‘郑声淫’,淫者,声之过也。水溢于平曰淫水,雨过于节曰淫雨,声滥于乐曰淫声,一也。‘郑声淫’者,郑国作乐之声过于淫,非谓郑诗即淫也。”(32)[明]杨慎 :《升庵经说》卷十三,丛书集成初编本。后来,清儒毛奇龄、陈启源、戴震、马瑞辰等人皆主此说,以为郑声非郑诗。在他们看来,经过孔子“放郑声”之后,现存《郑诗》乃是“声义俱正”的。
三、从文学角度证入经义的两种“读法”
反思《诗经》的文学阐释史,有一类是我们能够从前人的经说中寻摸出诗意来,还有一类是前人基于“文学之诗”的认识,来自觉地阐释《诗经》的文学意味。二者之前是有区别的,现代学者普遍地设定《诗经》是一部文学书,但这种认识显然很少成为古代诗经学的逻辑起点。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不然就容易“郢书燕说”,乃至遮蔽古代经学的本质。实际上对古人来讲,所谓“文学阐释”与其说初衷是为了还原文学,毋宁说是一种以文设教的“读法”而已。这意味着研究《诗经》的文学阐释史,那种外在的鉴赏式批评难称其职,而应当更内在地谈论“文学阐释何以可能”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在“诗意”与“经义”之间建立张力关系,在保障经典教化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释放《诗经》的文学活力,这种思路也就构成了《诗经》文学阐释史的主线。对此,欧、苏和朱熹分别提供了两种读诗之法,影响都很深远。
(一)朱熹 : 复性之教与“诗可以兴”
朱熹主张“以诗说《诗》”,因为在他看来,那些“感物道情”的诗歌为学者提供了窥探性情之道的最佳范本。《诗经集传序》云 :
或有问之于余曰 :诗何为而作也?余应之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曰 :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 :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33)[宋]朱熹 :《诗经集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8页。
人“性”本来是“静”的,“杂”感于物就呈现为“欲动情胜”的状态,形于“思”而发为“言”,自然就是“邪正”“是非”不齐的。在朱熹看来,《诗经》最为生动地呈现了“性”体层层发用的整个流程,更重要的是,它仿佛使人窥看到无善无恶的“性”本体,究竟如何一步步地发露为善恶混的世俗行为。所以《诗集传序》和《朱子语类》里谈到圣人立教的原理,说是把《诗经》当成了“必思所以自反”的格致场所。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正是读者玩味诗心而“切己省察”所得出的自我教化。这是典型的理学逻辑 :二程即反对佛家的“枯槁”和“恣肆”,而将“道”附于“物”之流行。(34)《二程遗书》卷四称 :“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臾离也。……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此佛之教所以为隘也。”(《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3页。)朱熹反思孟学的空疏,也说过 :“论性而不论气,则收拾不尽,孟子是也”;“盖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气质而论之,则莫知其有昏明开塞、刚柔强弱,故有所不备”(35)[宋]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五十二,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389、1387页。。这里所谓的“气”,涉及人情欲望以及各种利害关系的考虑。朱熹等理学家甘当“乡先生”,志在“行道民间”,他们将“天理”落实到“气”上磨炼作工夫,也是将复性之教植根于最真实的世俗的人性层面。这样就改变了孟子“尽心以知天”的心性上证之路,无疑是对孟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一旦将诗教落实在“气”的世俗层面,则《诗经》的美刺和贞淫都是本然自在,而又不能篇篇如此的,它们甚至充当了某种功能。所谓“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惊惧惩创之资邪”(36)《朱熹集》卷七十,郭齐、尹波点校,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0-3651页。云云,就是说“读诗”充满了人性的较量,而“彼之自状其丑者”更能显示人性尚未自觉的窘迫来,因而足以作为吾人之镜鉴。按照“道不远人”的理学逻辑,所谓“善”乃是人的自我成就,“恶”则是人的“自暴自弃”。只有理解了理学家对“人”的信心与期待,我们才能真正地解开朱熹“淫诗”说的秘密。如此一来,朱熹尽可以把《诗经》从经学母体中抽离出来,“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的文章”(37)[宋]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八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083页。,也就提供了“文学阐释”的可能。
朱熹把“感物道情”还给了“诗人之意”,《诗》的教化也就只能寄望于读者的自我领悟了。读者涵泳诗文,明了诗心的几微变化;又切己审察,以自警醒,从而回归“思无邪”的正途。朱熹诗经学的关键,即是这种“切己审察”的工夫。他讲到读《诗》的“体验是自心里暗自讲量一次”(38)[宋]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879页。,诸如“存心不在纸上写底,且体认自家心是何物”(39)[宋]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04页。,“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40)[宋]黎靖德编 :《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81页。,“深味其言而审于念虑之间”(41)[宋]朱熹 :《诗经集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49页。,“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义理,须反来从自家身上推究”(42)[宋]朱熹 :《诗经集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99页。等表述所在多是。由此看来,理学家所谓的“以诗说诗”和“涵泳讽诵”绝不是轻松的享受,而是剔骨抉皮一般的自我拷问,乃是真正“豪杰”的行为。以朱子学影响之深远,后人尤其是理学家们昌明“文学之诗”的性质,又要维护“思无邪”的正旨,尤其是在处理“淫诗”的时候,多采取朱熹的观点。而像王柏那样以为“淫诗”乃是汉儒的窜入,而尽皆删除之,其实是很不得朱子旨趣的。
(二)欧、苏 :“自述”之言与“诗可以观”
朱熹之“诗”与“经”不妨两看,在欧阳修这里却是凝合不二的关系。《诗本义》说 :“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43)[宋]欧阳修 :《诗本义》卷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0-291页。也就是说,古诗人触事感物,兴发为诗,自是美刺的意思,而不必强为说解。比如闻雎鸠之和鸣,“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见草虫异类相感,“有似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呼,诱以淫奔者,故指以为戒而守礼以自防”;听黄鸟之声,“因时感事,乐女功之将作”(44)[宋]欧阳修 :《诗本义》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83、190、184页,等等。揣摩其中的诗人形象,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古诗人皆触境而兴,抒情自遣而已,也就不同于汉儒笔下那个执着于讽喻上政,进而索物比附的有德之人。第二,这里的“美刺”是以“兴”的情感状态呈现的,它在触类旁通的过程中得到了排遣。就此而言,“诗人之意”也就具有了纯粹的表现性质,只关乎诗人之己身。比如《诗本义·四月》 :“盖知其无如之何,但自伤叹而已”;《小明》 :“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自相劳苦之辞”;《正月》 :“大夫自伤独立于昬朝之辞也”。(45)[宋]欧阳修 :《诗本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卷八第241、242页,卷七第231页。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欧阳修把诗歌当作“自述”的言语,其所彰显的乃是诗人的自我生命意识。
然则,经学之诗的性质安放在何处?欧阳修说 :“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46)[宋]欧阳修 :《诗本义》卷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4页。可见,他反对的并非“美刺”说本身,而只在于将“美刺”一律地附会到诗人的自觉意识层面。在欧阳修看来,诗歌皆一时心境的流露,并没有“言志讽喻”的动机,但“王化”就隐含在诗人联类感物的生命咏叹之中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诗歌是一种社会象征性文本,诗人的生命情感传递着历史的信息。如同“野老”“郊童”的歌唱,这些信息是昧于诗人意识之外的,所以,阐释的任务就是将其还原为“在场”。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部《诗本义》热衷于讨论时世的原因。后来,苏辙在《诗集传》中也说 :“(诗)发于思虑之不能自已,而无与乎王泽之存亡也”(47)[宋]苏辙 :《诗集传》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88页。,但正、变之诗所蕴含的性情,却是由时势盛衰与王泽教化所决定的。实际上是把“经义”与“诗意”相对区分开来,而沟通的办法就是通过语境阐释来赋予诗人意识之外的教化内涵。这样,欧阳修体认古诗人触物起兴的生命冲动,及其无意而然的政教价值,同样是真正的文学阐释了。
在汉唐经学家那里,《诗经》的文本意义是客观自足的,其中的“诗人之意”和“圣人之志”也是同一的。这样,“经义”就附着在对“诗人之意”的阐释之上,但阐释者并不发现经义,而只是将其更加确定地呈现出来。欧、苏则不然,既然诗歌只是“自述”的言语,那么读者就应当比作者了解得更多。这样把“经义”寄托于读者的再创造,也就改变了汉儒的那种过分倚重诗人而来的“缘字求义”的解经思路。苏轼《诗论》有云 :
《诗》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妇羁臣贱隶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夫天下之人,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兴亡治乱之迹,而下及于饮食、床笫、昆虫、草木之类,盖其中无所不具,而尚何以绳墨法度区区而求诸其间哉!……夫兴之为言,犹曰“其意云尔,意有所触乎”。当时已去而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阳”,此非有所取乎雷也,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此其所以为兴也。(48)《苏轼文集》卷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页。
苏轼接着就两次以“嗟夫”起语,一再强调观诗者“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与比同”。因为在他看来,如《关雎》之比“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而《殷其雷》之兴乃是触乎当时的无意而然。这样来理解诗人的“自述、自伤”和“君臣父子、兴亡治乱”之间的关系,就不是自觉取义的比附,而是一种偶尔契合又无法指实的关系。所以苏轼强烈反对汉儒的“绳墨法度”和“言解”,提倡一种“意推”的方法。也就是提倡以人情解诗,感受“自述其情”的诗人之意,并体会出“六经之道,惟其近于人情”的道理来。
在明清诗经学史上,也能够清晰地见出这种读诗法。明人万时华评点《关雎》说 :“诗人自言其忧思喜乐之情然,本无与于文王,而文王之化自见。”(49)[明]万时华 :《诗经偶笺》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徐光启评点《小星》说 :“此诗只说勤劳而安于命,而夫人之不妒,众妾之感恩因此可见。昔人称《易》在画中,诗在言外,言外之旨此类可见。”(50)[明]徐光启 :《毛诗六帖讲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6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所谓的“言外之旨”,也就是由读者“观风俗之盛衰”而创构的经学意义,与“诗人之意”的关系不大。又如清代方玉润笺注《芣苢》之诗,再现了田家女拾菜欢笑的情景,结题却是“化行俗美”朱子义。他还认为《二南》多是乡野之词,“不必定咏文王,亦无非文王之化;不必定指召伯,罔非召伯之功”(51)[清]方玉润 :《诗经原始》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7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在崔述看来,《关雎》“乃君子自寻良配”的诗歌,《江有汜》等诗也都“自喻身世而已”,而“皆可以见先圣之化入人之深”。(52)[清]崔述 :《读风偶识》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6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252页。这些说法明显的都是继承欧、苏而来的。众所周知,姚际恒把大部分“淫诗”阐释成“刺淫”之作,但对《野有死麕》难以自圆其说。他认为,“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昏姻之诗……亦情欲之感所不讳也欤!”(53)[清]姚际恒 :《诗经通论》,续修四库全书第6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五第76页、卷二第40页。就从这篇“属淫”的诗歌中,体会出圣人观风设教的深意来。由此观之,根据这种读诗之法,《诗经》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诗人“自述”的私言,又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社会化表述。因而文学论者无须篇篇落实诗歌的美刺作旨,他们把无为而自发的生命诉求还给“诗人之意”,同时也通过语境阐释来窥探诗歌的政教价值。这样,文学魅力和经学义理互不妨碍,前者表现为诗人个体生命的舒展,后者实际上反映的是读者的自我理解与期待。
总之,古人以文学的观念来解读《诗经》,仍然在探讨“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不同于汉儒把经义安放在诗人的自觉意识层面,文学论者更加强调阅读过程中的意义生成。朱熹等理学家“涵泳讽诵”而“切己审察”,主张以《诗》的性情几微之变来格正己身,以此求得内圣境界的完满。欧阳修等人则认为,作者无为而自发,读者联系语境“观”出它的社会价值来。随着宋代以来世俗社会的兴起,《诗》人的身份也下移到民间,“国风民歌”“感物道情”“触境而兴”逐渐成为学者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之下,既然“美刺两端”难以周全其说,则文学论者唯有“据文求义”地继续从事义理诗经学的建构。汉儒将文学性排除在解释活动之外,后人则以文学的观念来沟通《诗经》之教,在坚持义理底线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去感受诗歌的真美。虽取径不同,但内在的尺度并无实质的区别。毋宁说,文学论者通过反驳汉儒的方式,更好地继承了汉儒的义理之学。
四、余论
以上我们分析了古代诗经学的意义生产机制,论证了多维理路之间相互竞争和交织所产生的某些普遍性问题,以及相关的解决办法。这种分析自然是冒着“本质主义”的风险的,但它有利于我们对诗经学史这样复杂的对象做出宏观和明澈的把握。总的说来,在宋代以来多维交织的诗经学史上,自然是“主义”一脉始终占据了主流。因为显然的,无论是作为士人立政造事的凭借,还是作为刺上化下或自修其身的文化资源,《诗经》从来都是普遍地作为文字经典而发挥作用的。在后来的古史辨派学人那里,他们要拆穿古代诗经学的“虚伪”面目,同时也清晰地指出 :古代的以乐论诗者常常误入《诗序》义说的窠臼,而最具文学眼光的诗论家也不免“迂儒之声口”(54)这是古史辨学者的共同认识,并由反对《毛诗序》入手切入对古代义理诗学的拆解。参见《古史辨》第三册之俞平伯《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何定生《关于诗经通论》、郑振铎《读毛诗序》等文章,以及上引何定生《宋儒对于诗经的解释态度》。。也说明了这一点。要之,“主义”之维始终规范着“主声”和“主文”之维的实现方式及程度,由此也体现了古代诗经学的某些本质特征。
这一点,通过比照先秦儒学,就能够清晰地见出古代经学的文化品格来。我们看先秦儒家的《诗》论,常常引《诗》以自申其说,或者把《诗经》当成修身的资源来看待,绝无汉儒那般强烈的诗谏意识。实际上,儒家先师主要是针对本阶层自身进行言说的,他们以道义精神和君子人格相劝勉,既是出于凝聚儒家身份认同、挺立儒家主体意识的需要,同时也埋藏着很深的“以德居位”的政治诉求。因此先秦儒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儒者的自我教化。但是汉代以后,随着君权大一统体制的确立,儒家士人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得已才把秩序重建寄望在“得君行道”乃至世俗社会日用而不知的奉行之上。历代儒者莫不以教化君权为己任,有时也甘当“乡先生”化民易俗。如此说来,古代经学不同于先秦儒学,它是一种他律性的话语,是面向统治者和全体大众展开教化的。同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儒家士人已不复先秦的那种真理独占者的身份,而是以学术研究和经典重释的方式来申张理想,通过依经立义的话语建构来影响世道人心,这就构成了义理诗经学之形成的文化根源。汉儒以《诗》规谏,阐述《诗经》的史鉴价值;宋明理学家论《诗》以致理,抉发更加普遍的人生意义;清代朴学家精于训诂考据,仍抱有由训诂而通义理的期待——实则遵循了同样的义理维度。理解了古代经学的文化品格,也就不难弄清郑樵诗经学在后世晦而不彰的原因,以及古代以诗说《诗》者的界限问题。同样的道理,彻底的声歌之维与文学之诗的性质有待于现代语境下的张扬,也是宜其如此的。在古史辨派也包括今天的学者看来,古人都不能摆脱诗教思想的束缚,找不出纯粹的文学解读来。这种判断也是有待商榷的。
第一,根据欧、苏和朱熹等人的读诗之法,经学内涵是由读者的解释权所掌握的,体现的是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样就把“诗意”还给了诗人,更意味着“诗意”正式地进入了阐释者的视野之中。特别是在欧阳修等人那里,明显地透露出这样的意思,即文学性涉及“表现”,而不在言说的内容。这种观念已经非常“现代”了。所以我们不必见到“美刺”便疑若不文;同样的,也不能在诗经学史上随意地去寻摸出诗意来。文学的概念向来是模糊的,所以需要我们联系诗经学的意义结构来衡量《诗经》的文学阐释史。
第二,即便文学的预设具有绝大的合理性,也不必然要求把《诗经》当作一部文学书来看待。《诗经》与诗经学是两码事,前者在史实层面上具有确定性,而后者是在历史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地生成的。时代需求塑造了诗经学的风貌,也决定了它在参与后世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所持有的价值立场。这一点,便是古史辨派也不能例外的。他们用现代精神来烛照《诗经》的本性,其所还原出来的那个“赤裸裸的文学真相”,不也是有些“迂”吗?在很大程度上,诗经学史就是《诗经》的重读史,是这个文本在新语境下被重构和激活出新意义的历史,因而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自我理解的心灵史。这即是诗经学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