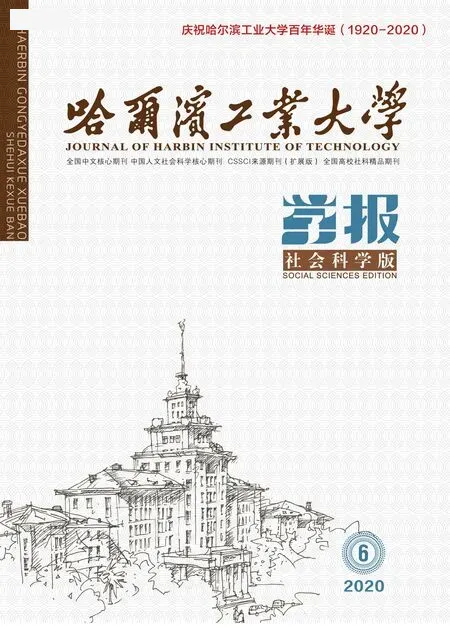中西方戏剧中科学家形象差异与原因
武 静,孔令然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100089)
“科学家”的形象在中西方戏剧舞台的刻画截然有异。 在《法西斯细菌》《岁寒图》《地质师》《马兰花开》《钱学森》及讴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抗疫英雄事迹的《巍巍南山》等中国戏剧中,民族大义、国家建设是主旋律,科学家的形象经历了从埋头科学、不问世事的“逃避者”到积极献身革命和祖国建设事业的“民族英雄”的转变。 西方戏剧中,从《浮士德博士》《大鉴赏家》到《伽利略传》《物理学家》等戏剧中,从最初沉迷于科学研究、不合群的“怪人”,转变为布莱希特口中背叛科学的“罪人”,科学家形象复杂且耐人寻味。 对科学家的形象及所揭示的历史场景作以分析,有助于理解中西方戏剧舞台上科学家形象差异的深层原因。
一、中国戏剧中的科学家形象:从“逃避者”到“民族英雄”
(一) 将科学作为避风港的“逃避者”形象
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戏剧”是夏衍于1942 年创作的《法西斯细菌》。 该剧的主人公俞实夫是一名从事微生物学研究的细菌学家,时间跨度从1931 年至1942 年,场景设置从日本、香港、上海到桂林。 夏衍描摹了抗战大事件对主人公开展科学研究的影响,通过对俞实夫心理嬗变过程的刻画,展现了一位最初将科学作为避风港的“逃避者” 到抗战关键时刻决定投身革命、服务国家的科学家形象。
夏衍在谈到创作该剧的初衷时曾说,“我想写一个以‘科学与政治’关系为主题的剧本”,其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界有许多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家”,他们埋头于科学研究,采取“逃避者”的姿态对当时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避之不闻[1]。 正如陈坚所言:“从二十世纪以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历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超脱政治、埋头于专门知识领域这样一种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文化现象。”[2]112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素来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这既是知识分子超然的一面,也是知识分子对严酷社会现实的逃避。 剧中的俞实夫就是这样一个“逃避者”,他对科学的超然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试图通过埋头科学研究来逃避纷繁复杂的政治。 他对政治和时事抵触逃避,甚至定下不允许家人订阅报纸的规矩,并将“不看报”作为行动原则,试图以此来逃避政治。当他攻克黑热病原体的研究被《东京朝日》刊发出来时,邻居和好友纷纷前来祝贺,他依旧不为所动,并叮嘱妻子:“今后要是有什么新闻记者来,统统给我回了,说我不在。”[3]7对于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日本的报纸也将他称为“新中国医学界的光芒”,他却坚持认为“科学没有国界,我们从事的是全人类的事业”[3]28。 事实上,从一开始他的研究就受到政治的影响,他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与自己的民族身份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超然与逃避并不能让他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独善其身”。 他的好友赵安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点:“咱们中国人在日本念书,谁都想平平静静地做一点真实的学问。 可是,你能逃得出中日两国间的政治问题? 这几天万宝山的问题没有解决,又闹出了什么中村事件,要是事件扩大起来,谁能担保两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3]9
俞实夫所谓的“科学没有国界”的说法事实上也是一种对政治的逃避,也许这种说法在和平年代是成立的,但在当时国际政治局势异常严峻的情形下显然站不住脚。 夏衍曾说:“史坦因美茨在他的祖国波兰是遭受过惨淡经历的,现世界所能产生的最伟大的哲学者,物理学者爱因斯坦,不是因为犹太人的关系被希特勒驱逐,连一个安静的研究机会都不可得么?”[2]113因此,俞实夫想要将科学与政治完全割裂开来,通过埋头科研来逃避政治是不切实际的,就像赵安涛所说:“你不管政治,政治却要来管你”[3]56。 面对赵安涛的劝说,俞实夫依旧对政治和时事采取回避态度。
在赵安涛看来,政治经济是“每个人都得知道的近代人的常识”,所以俞实夫一味地逃避时事政治而埋头科研的做法是“学究、书呆子”的做法。 不过,现实的情况最终让俞实夫反思自己一贯坚持的“科学至上主义”和“科学不分国界”的思想。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他再也不能平静地埋头于科学研究,不得不离开日本,辗转香港、上海多地寻找一个“不会打仗的地方静静地做研究”,这一想法被现实一一粉碎[3]35。 这使他认识到自己的科学研究根本无法与政治局势相分离,最终他向赵安涛坦言:“我的科学至上主义都已经支离破碎,不存在了……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可能;就是要关上门,做一些对人类有贡献的研究,也会时时受到阻碍和破坏。”[3]79
在本剧的末尾,经历了一系列由于战争带来的变故之后,俞实夫的思想发生了质变,他认识到了科学家想要回避政治而在科学中“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从一个埋头科研不谙时事的“逃避者”,转变为一个主动投身抗战的科学战士。 他决定放下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前往抗战大后方桂林,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支持抗战。“一件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讲的大一点,为了国家,为了伤兵难民,要去;讲得小一点,为了阿裕的遗志,我也要去。”[3]82夏衍本人将俞实夫定义为一位“悲剧英雄”,因此戏剧并没有一开始就将他刻画成一个英雄人物,而是着重表现了他的心理活动起伏,展现了一个“逃避者”成长为一个献身革命的英雄形象的嬗变。 尽管在戏尾俞实夫转变了思想,但是纵观整部戏剧,夏衍着重刻画了俞实夫内心的挣扎与犹豫,在现实的政治境遇驱动下所激发的民族大义,使科学家形象具有更强烈的悲剧色彩。
(二)迎难而上的“民族英雄”形象
《法西斯细菌》中的俞实夫最终选择投身革命,展现了被时事所迫的“逃避者”形象;有研究者认为该剧是“对于知识分子‘带着眼泪’的批判”,指向科学家“为科学而科学”、脱离和逃避现实的行为[4]18。 不过,《法西斯细菌》中俞实夫这类“逃避者”的科学家形象在抗战期间的戏剧作品中并不多见;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剧作家们意在激发和鼓励知识分子投身革命。 正如曹禺于1938 年7 月在“战时戏剧讲座”中提出的“一切剧本全是有宣传性的”,要为抗战服务;关于知识分子的戏剧更多侧重展现“爱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所蕴藏着的精神力量,对于民族振兴事业具有特殊意义”[5]618。 在这些歌颂知识分子的戏剧中,陈白尘1944 年创作的《岁寒图》是赞扬科学家形象的力作。
《岁寒图》的主角黎竹荪是医学院的肺结核专家,迥异于《法西斯细菌》中的俞实夫面对复杂政治时局的犹豫和逃避,黎竹荪以刚毅高尚的品格坚守科学家的初心,制订《防痨计划》与国民党当局艰难斡旋,期望能够拯救每年新增的数以百万计的肺结核病人。 黎竹荪的研究出发点与俞实夫的科研初衷有一定区别,前者致力于解决当时肆虐中国的肺结核感染,后者则出于对死于“斑疹伤寒”的音乐天才莫扎特的惋惜,而决定攻克这种疾病。 相比之下,黎竹荪忧国忧民,全心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生命健康威胁,而俞实夫略显荒唐的浪漫主义情怀,更专注自己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俞实夫是在一系列的变故和打击之后,被迫选择对抗“法西斯细菌”,那么黎竹荪的初心便是坚定地对抗社会与政治的“病菌”。 “黎竹荪是一个‘无声的人物’,但同时更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因为他展现了在艰难的现实境况中“知识分子坚毅与高洁的品格”[4]18。 不仅如此,黎竹荪之伟大造就了科学家心怀天下、与残酷的现实作斗争的勇士形象。
《岁寒图》中的“英雄”科学家形象成为新中国戏剧中科学家形象的模板。 剧作家杨利民创作于1996 年的《地质师》,讲述了1961 年至1994 年间一批石油地质科学家献身祖国石油事业的事迹。 他称创作该剧“是因为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苦难中的崇高及生命的真正价值”[6]。 本剧的主角是以洛明为代表的一批石油地质科学家,他们中有人放弃爱情,有人放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一生。他们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为了解决林林总总的科研难题,有人终身残疾甚至失去生命,同时遭受“文革”的严酷迫害与社会的不公。 最终攻克陆相沉积油田理论、注水采油、分层开发、石油外输困难、原油含水等科学难题,致力于祖国的石油事业,摆脱了曾经“贫油国”的帽子,技术上跻身国际先进水平。 剧中“骆驼”的形象贯穿始终,成为新中国建设道路上科学家为国家献身的象征符号。 主人公洛明说:“我是骆驼。 你知道骆驼吗?它除了耐饥渴、耐干旱,有韧劲儿,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那就是当它死后,它的体内还有一个水囊,拿出来还能救人……我要去远方,去天边外,一直朝下走去,走进土地,走进底层。”[7]
《地质师》中的科学家形象代表了无数为祖国建设默默奉献的“英雄”形象。 2010 年后,科学家形象频频登上戏剧舞台,以“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邓稼先、钱学森的事迹为原型的《马兰花开》和《钱学森》,以数学家陈景润为主角的《哥德巴赫猜想》,讴歌以钟南山为代表的抗疫医护英雄事迹的戏剧《巍巍南山》,形成了一批以高校及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为主创,由中国科学技术学会和国家教育部等多部门共同推出的“共和国的脊梁——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歌颂知名科学家、校友、时代英雄事迹的科学戏剧作品,旨在培育科学文化和弘扬科学家精神。 这些戏剧中的科学家及其事迹广为人知,与以往戏剧中虚构的科学家形象不同,他们的真实事迹更能够触动人心。这些科学家是为国家献身的民族英雄,也成为当之无愧的民族精神的代表。
二、西方戏剧舞台上的科学家形象:从“怪人”到“罪人”
(一)沉迷于无用学问的“怪人”形象
西方戏剧舞台上的科学家形象从沉迷于无用学问的“怪人”转变为逾越界限、亵渎神灵的“罪人”形象。 克里斯托弗·马洛1592 年创作的《浮士德博士》是西方“科学戏剧”的鼻祖,剧中的浮士德博士也成为最深入人心的科学家形象。 在本剧中,科学天才浮士德博士不再满足于中世纪推崇的正统学问——神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盖伦的医学,企图超越已有知识的边界,探索未知领域。 于是他用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交易,背叛上帝最终堕入地狱。 作为最早的科学家形象,浮士德博士既是沉迷于非正统学问的“怪人”,也是逾越禁忌、亵渎神灵的“罪人”,两种形象兼而有之,成为西方文学和戏剧中科学家形象的原型。
在马洛之后,本·琼森(Ben Jonson)的《炼金士》(The Alchemist,1610)与托马斯·夏德威尔(Thomas Shadwell)的《大鉴赏家》(The Virtuoso,1676)中的“科学家”,继承了浮士德博士的“怪人”形象,被剧作家刻画成沉迷于令人费解、又脱离实际的无用学问的“诡计多端的假内行”和偏执古怪又不问世事的“怪人”形象[8]。 在本·琼森的《炼金士》中,狡黠的炼金士“夏特”(Subtle)和他的同伙“菲斯”(Face)以“炼金术”这种无用的“伪科学”为幌子,装腔作势地卖弄各种科学术语,打着科学的旗号招摇撞骗,最终弄巧成拙。 本剧中的炼金士怪人形象是他们贪婪内心的戏剧呈现,而在《大鉴赏家》(The Virtuoso, 1676)中,托马斯·夏德威尔创作的滑稽可笑的科学家尼古拉·金坷垃爵士(sir Nicholas Gimcrack)也是“怪人”科学家的典型。 在剧中,金坷垃爵士热衷于各种新奇怪诞、脱离实际的科学实验,如在旱地里摹仿青蛙游泳,将羊血输入人体等。 他花费大量的金钱用于搜集昂贵的标本和科学实验仪器,如“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计、风动引擎,闻所未闻的奇怪试管等等类似的东西”[9]111。 不仅如此,夏德威尔笔下的科学家还是不问世事、醉心于研究与人类社会格格不入的怪人;当被问起他为何不关心社会的民风民俗和社会政治时,金坷垃爵士回答道:“研究人民和风俗对我来说是大材小用,不值得费神。 我研究昆虫。”[9]139托马斯·夏德威尔擅长创作讽刺喜剧,不管是从金坷垃爵士滑稽可笑的名字,还是他本身的怪异举动,将科学家标榜为“大鉴赏家”的讽喻可见一斑。 经学者考证,剧中的金坷垃爵士实际影射了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即《显微学》(Micrographia)的作者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0]。 这反映了剧作家和社会大众对当时新兴科学知识的态度,折射出人们对科学知识的怀疑和不解,认为它只是某些狭小圈子里的令人费解、又脱离实际的无用学问,而这些科学家也被刻画成了沉迷于无用学问的“怪人”形象。
同样,在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中,主角斯托克曼既是一名医生,也是研究病菌的科学家,与《炼金士》和《大鉴赏家》中的怪人形象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怪异更多地体现在他的“不合群”,即他的思想与大众思想和意见相左。 斯托克曼医生发现作为镇上经济支柱的温泉中含有化脓菌和大量纤毛虫,需要关闭温泉进行消杀,否则会导致泡温泉的游客死亡。 对于他的这一发现和提议,镇上的人们并没有感激,相反,他们拒绝关停盈利的温泉,斥责医生的发现危害大众生计。 剧中斯托克曼医生的学识被认为是一种威胁,他的知识使他与镇上的人们格格不入,成为不合群的怪人。对此,谢泼德·巴尔曾指出:“医生在易卜生的戏剧中总是被批判的对象,斯托克曼医生也不例外。与易卜生其他戏剧中的医生一样,斯托克曼医生是软弱无能的。 尽管他能够诊断出社会的病症,但是却无法医治它。”[11]萧伯纳在《医生的两难抉择》中,呈现了一名与斯托克曼医生类似的科学家形象,与《人民公敌》不同的是,本剧更加强调科学知识在解决现实问题时的困境和徒劳,如何在一个本来就不道德的情况下做出符合伦理的选择,将科学知识在解决某些现实问题上的无解与苍白表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这些剧中的科学家形象与马洛、琼森和夏德威尔剧中的科学家形象有了一些差异,但本质上他们的知识终究不能对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他们本人也成为不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怪人”形象。
(二)逾越禁忌的“罪人”形象
上述剧作中科学家尚且是无害和无能的“怪人”形象,在布莱希特的《伽利略传》(Life of Gali⁃leo, 1938/1947)之后,转变为拥有巨大毁灭潜力并背负科学“原罪”的“罪人”形象。 这一改变也源自大众对知识认知和态度的改变,导致这一改变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1945 年8 月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 原子弹爆炸使世人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了科学的危险性,人们将科学家看作科学毁灭力量的始作俑者。 在1938 年最初版本的《伽利略传》中,布莱希特将伽利略塑造成一名“捍卫科学与知识、为进步而战,并不遗余力地为新时代播撒科学真理的英雄形象”[12]7。 可以说,彼时的布莱希特对科学家和科学知识怀有敬意,并乐观地认为新的科学发现会带来社会进步,而科学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是高尚和值得敬佩的举动。 然而他的这些信念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1945 年的原子弹爆炸之后彻底幻灭:“一夜之间,近代物理学奠基人的生平事迹对我来说有了另一番意味。 原子弹摧天毁地的可怕后果,使我[布莱希特]对伽利略与权威之间的冲突要做新的、更深刻的思考。”[12]8于是,在1947 年版本的《伽利略传》中,伽利略不再是为真理和进步而战的英雄形象,而成为“背叛科学的叛徒”,成为科学史上的罪犯。 用布莱希特的话说:“伽利略所犯下的罪行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原罪’。”[12]10几乎一夜之间,科学家不再是马洛笔下勇于求知的浮士德博士,也不是普罗米修斯般为人类盗取火种的英雄,更不是琼森和夏德威尔笔下狡黠贪婪的假内行和滑稽无用的书呆子,而是变成了引诱人类堕落的毒蛇、背叛上帝的犹大和杀死兄弟的该隐,与毁灭和背叛相联系。
布莱希特两个不同版本的《伽利略传》算是科学戏剧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和风向标,当某些科学知识被认为是“禁忌”和罪孽之后,戏剧舞台上的科学家形象就变成了逾越禁忌的“罪人”形象。在查尔斯·摩根(Charles Morgan)的《取火镜》(The Burning Glass, 1953)、迪伦马特的《物理学家》(The Physicists, 1962)和海纳·吉普哈特(Heinar Kipphardt)的《罗伯特·奥本海默》(In the Matter of J. Robert Oppenheimer,1964)中,当剧中科学家发现他们的知识和发明有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时,都选择了隐瞒自己的发现,像是要隐藏和撤销他们所犯下的“罪孽”。 《物理学家》中的科学家莫比乌斯不惜将自己关在疯人院,他坦言:“我们的知识已经变成可怕的负担,我们的研究极具危险性,我们的发现是致命的凶器……必须撤销我们的知识,我已经撤回了它。”[13]而《取火镜》中的科学家在意识到自己发明的可怕破坏力后,不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控这一威力巨大的发现而选择自杀,吉普哈特剧中的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则在见证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威力后,拒绝继续参与军方研制氢弹的项目,并因此被控“通共”和“叛国”而受到审判。 在这些剧中,科学知识都不是造福人类的智慧,而是人类尚不能掌控的破坏性力量,它与“罪孽”相联系,科学家也成为打开罪孽之门的“罪人”,因此他们选择了隐藏和逃避自己的知识。 对于这一点,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在《铜蝴蝶》(The Brass Butter⁃fly, 1958)中借凯撒之口表明了相同的看法:“蒸汽船或者其他任何强大的发明在人类的手中,就如同将一把匕首交给一个孩童。 匕首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蒸汽船也没有什么不对,人类的智慧也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人的本性。”[14]在这些剧中,科学知识潜在的巨大破坏力带有“禁忌”色彩,人类有幸窥见上帝的智慧,但并没有足够的理智和智慧来掌控它,因此知识便成为一种负累,成为一种逾越禁忌的罪责。 对于这一点,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在《赫拉克勒斯》(Herakles, 1964)中通过主角霍德利教授表明了这一点:
霍德利:我们需要成为神,才能真正懂得我们所知道的。
霍德利夫人:难道我们不是吗? 我以为我们已经是神了。
霍德利:神可以承受他所知道的。 而我们不能。[15]13
正是因为知识的禁忌色彩,人类没有能力承受和掌控自己所知道的知识,因此才造就了上述剧中科学家的“罪人”形象和他们的悲剧结局。正如恩内斯特·桑迪恩(Ernest Sandeen 所述:“麦克利什将[赫拉克勒斯]神话看作是人类心理的投射,它对准的不是神,而是人类自己,当人类奋力夺取天神一般的力量时,身后则拖着长长的荣格式阴影……当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将人类自身的普遍缺陷放大到令人恐怖的程度,因此普罗米修斯与赫拉克勒斯的神话有着可怕的先见之明,也传达着一种对人类经历的悲剧同一性的感同身受。”[16]
在这些剧中,剧作家都传达了对知识的相同看法,即某些前沿的知识是神灵才能拥有的,是人类无法承受的智慧,就像霍德利教授所说的“我们需要成为神,才能懂得我们所知道的”[15]14,而当人类想要成为神灵时,便是“罪孽”的开始,也是人类悲剧性经历的开始。 这种悲剧性是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无法被祛除的“普遍缺陷”,因此在赫拉克勒斯的神话中古人早早就预言了这一切。人类对禁忌知识的追求便成了亵渎神灵的僭越。“科学家想要成为上帝”这一主题在后来的许多戏剧作品如《变身怪医》(Jekyll & Hyde,1990)、谢拉格·斯蒂芬森(Shelagh Stephenson)的《气泵实验》(An Experiment with an Air Pump, 1998)、卡尔·德杰拉西(Carl Djerassi)的《完美误解》(An Immaculate Misconception,2000)等中反复出现,而无一例外这些剧中的科学家都成为违背自然和背叛人性的“罪人”形象,并最终为他们的求知行为付出了良知甚至生命的代价。
三、中西方戏剧中科学家形象差异的原因
(一)中西方科学戏剧栖居的不同政治历史境遇
中西方戏剧在对“科学家”这一形象的呈现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原因之一在于中西方戏剧的发展所处的不同历史背景及政治诉求。 中国虽然有着悠久的戏曲传统,但是“话剧”这种戏剧形式是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才传入中国的,而作为其中更为小众的“科学戏剧”,到20 世纪中期才零星地出现。 不管是中国的话剧,还是更为小众的“科学戏剧”都诞生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在创作上会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的影响。 《法西斯细菌》与《岁寒图》的科学家是投身抗战和民族解放事业的英雄;新中国建设时期,《地质师》《马兰花开》《钱学森》等剧中科学家形象肩负民族振兴,成为建设祖国攻坚克难的英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巍巍南山》剧中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医护英雄,秉承护佑生命的医者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成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缩影,彰显爱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蕴藏的精神力量。
自1592 年《浮士德博士》一剧开始,西方的“科学戏剧”创作传统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西方科学戏剧与文明社会的科学发展进程交织,从僭越神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盖伦的医学发端,伴随着经典科学与现代科学的推陈出新,西方科学戏剧携手天文学、数学、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勾勒出始于中世纪、兴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盛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现代主义的绵长画卷。 此中既有科学知识对宗教神学冲击过程中遭遇的抵触,也有在科学的演变过程中人类的怀疑与不解,更不乏对科学知识滥用的批判。 与美术、音乐、文学相比,戏剧的社会性愈加明显,作为一种叙事性的艺术,戏剧反映充满矛盾冲突的情节与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处于协商互动之中,反映的意识形态深浅错落。
(二)中西方文化对待科学知识的不同态度
近代中国在现代科学领域略迟于西方,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西方现代科学,代表西方先进科学的“赛先生”成为打破旧学和开启民智的一面精神旗帜。 彼时的知识分子将西方现代科学看作是启蒙大众和救国图强的先进知识,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的“科学家”形象几乎都是探索科学前沿知识,用知识造福国家和人民的英雄形象。 基于此,不管是改编国外的科学戏剧,还是中国原创的科学戏剧,对于科学知识与科学家都进行了积极正面的呈现。 例如,在1979 年改编的第一部国外科学戏剧《伽利略传》中,导演黄佐临便“将原剧中关于科学的认识和对科学的评判做了省略、替代或者淡化”[17]41,“原剧的主题是反对科学发展……[布莱希特]为科学,为科学家感到惭愧忏悔的心理。 先在美国,后来到德国演出,调子都是灰溜溜的。 而我们演出的时代,科学家是最宝贵的人物。 所以我们对戏剧中科学家形象的处理是富丽堂皇的。”[17]49与此回应,在国内原创的科学戏剧中,科学家也是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宝贵知识和智慧的英雄形象。 《法西斯细菌》《岁寒图》《地质师》《马兰花开》《钱学森》《巍巍南山》等剧中科学家形象都是肩负民族和国家使命的英雄人物,他们不仅是国家建设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缩影,也反映了中国观众对科学家和科学知识的崇敬。
反观西方戏剧舞台上的科学家形象,则带有更多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也与西方科学知识的发展及西方对科学知识的接受态度密不可分。 西方“科学戏剧”是伴随着科学的诞生而出现的,对科学保持怀疑甚至批判的态度,导致剧作家在刻画科学家角色时带有很强的批判和反思色彩。 因此在西方科学戏剧的传统中,《浮士德博士》一剧传达出的是对科学知识潜在危险性的担忧,对科学家不信任的态度。 西方对待知识的矛盾态度也源自“知识”在西方文化中的禁忌色彩,从神话中为人类盗取火种而触犯神怒的普罗米修斯、因飞得太高而被太阳融掉翅膀葬身大海的伊卡洛斯,到偷吃智慧树上禁果的亚当夏娃,以及文学作品中与魔鬼做交易的浮士德博士和想充当造物主的弗兰根斯坦,等等,都在强调知识带有某种“禁忌”色彩。 对“知识”的警惕与质疑也通过宗教和文化传统沉淀下来,浸润于公众的集体无意识中,这些故事都在提醒世人:求知超过神灵允许的界限便会招致灾难。 作为知识发现者和代言人的科学家在西方戏剧舞台上,更多地被刻画为触碰禁忌的“罪人”形象。
(三)中西方戏剧创作传统的差异
中国的科学戏剧产生于民族危难之时,勃兴于民族振兴、国家建设的各个发展阶段,接受了苏联戏剧尤其是左翼的政治宣传剧的影响。 在左翼戏剧创作思想的指引下,剧作家创作现实主义戏剧,“把戏剧作为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生的工具”,因此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紧密相连[5]166。这也是为什么在《法西斯细菌》和《岁寒图》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与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Leo⁃nid Andreyev)的《向星星》(To the Stars, 1906)和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太阳之子》(Children of the Sun, 1905)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即主张科学研究与科学家不能脱离政治,而应该服务于社会和国家。 而到了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左翼戏剧的传统和理念得以承继,在《地质师》和《马兰花开》等剧中仍然保留了政治宣传和教育色彩,其中的科学家主角也都是为国为民的英雄形象。
相比之下,西方的“科学戏剧”伴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而诞生,更多的是对现代科学的质疑、反思和批判。 鉴于此,西方戏剧舞台上的科学家形象承载了剧作家对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的反思与质询。 从最初滑稽傲慢的喜剧角色,到后来掌握可怕知识、令人恐惧的“罪人”形象,矛盾性贯穿始终。 西方科学戏剧的创作自1990 年以来进入第三次创作高峰,被称为西方戏剧界的“千禧现象”。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如汤姆·斯托帕德的《阿卡迪亚》和迈克尔·弗莱恩的《哥本哈根》等一系列当代经典科学戏剧,涵盖了当代科学的各个领域,“科学家”形象刻画得更加多元,依旧继承了《浮士德博士》以来对科学的反思和批判的传统。
概而言之,尽管中西方戏剧对“科学家”的刻画存在一些相似性,如木讷、不善辞令的书呆子形象,但是两种文化展现的科学家形象嬗变的差异更加明显。 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中西方科学戏剧所处的政治历史境遇不同,戏剧创作反映了鲜明的历史样貌和政治诉求;中西方文化对待科学知识的不同态度,在戏剧中代表知识的科学家便具有差异的符号意指;中西方戏剧创作传统的溯源,使受左翼文艺理论影响的中国科学戏剧与以保守见微知著的西方科学戏剧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