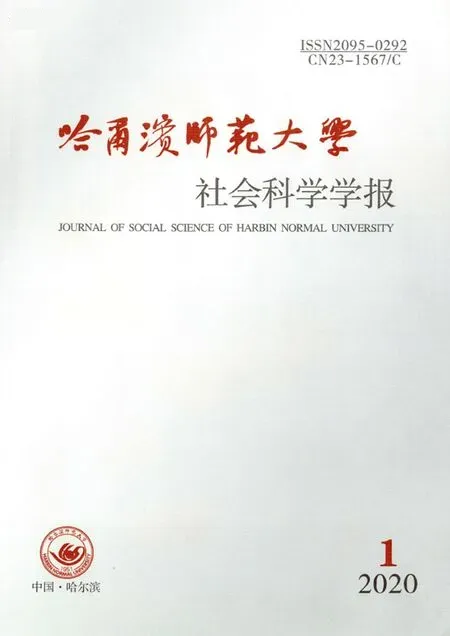“香草美人”的传统抑或传情寄意的密语?
——从木斋先生的《曹植甄后传:汉魏古诗写作史》谈起
丁 涵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治汉魏六朝文学者大概都不会对木斋先生(以下简称木斋)(1)木斋,原名王洪,担任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美国休斯敦大学客座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世界汉学会会长、中国陶渊明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及其专著——《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感到陌生。本文在进入主题之前,有必要先对这部书的研究步骤做以下概述:(一)追根溯源五言诗的生成机制、成熟标志、文体特征和流行前提;(二)质疑乐府的民间与贵族二分法,缩小五言诗的作者阶层范围,细化五言诗的产生条件;(三)在前述背景下,从语汇语句角度对古诗十九首进行年代断限,否定“西汉说”“东汉说”,修正“曹王说”等成见,并结合曹植(192—232年)、甄后(183—221年)的事踪加以考量,将其中的九首(其一至其六、其九、其十三、其十五)之作者径指为曹植;(四)与此同时,曹植、甄后之恋也在这九首作者归属的确立过程中水落石出[1]。这四层意见,在学界引起反响的激烈程度依次递升,借用作者的原话说,“在海内外的学界掀起轩然大波”[2](P14)。经年之后,木斋经过沉潜、反思和提炼,近期新推出一部大著——《曹植甄后传:汉魏古诗写作史》(以下简称《曹植甄后传》),相对前著可谓更进一竿。新著不仅从之前认定为曹植所作的九首古诗着眼,将具体诗篇的系名系年进一步精确化(如对《青青河畔草》的作者修改、对《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的写作时间的判断);而且把目光也投注到曹、甄二人各种文学体裁的字里行间(如《七哀》《洛神赋》《灵芝篇》《妾薄命》《芙蓉赋》《九咏赋》《感婚赋》《愍志赋》《蝉赋》《东征赋》《节游赋》《塘上行》等);甚至还将其视域拓展到原不具名的作品(如《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或本署他名的作品(如《怨歌行》《室思诗》等)、或目前被认为是曹植的但或许更应是甄氏的作品(如《闺情》等)。木斋期待达成的目标,显然旨在让长期被张冠李戴的作品在曹植、甄后名下得到重新安置;此外,又让无名氏作品背后的确切作者浮出水面、重见天日;最终让曹植、甄后之间曲折隐秘的恋情迷局豁然可通。此书大体上能够兼采“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甚至“多重证据法”,力图透过“以诗证诗”“以史证诗”最终“以诗证史”,不时地体现出“直觉兼考证”与“内证与外证”绾合的特色(2)这一特色在木斋的前著中已有所显现。参见傅璇琮:《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序》,载木斋:《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窃以为,其学术价值即便抛开考论的功夫不计,至少它对过去文学史书写和文学批评约定俗成的范式的挑战和启示已足以发人深省。
受其影响最大者,可能要推“香草美人”模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适用范围的问题。肇自先秦,中国早期文学中便出现芰荷、芙蓉、薜荔、蕙、茞、兰、梅、菊等“香草”意象和佳人、蛾眉、倾国、倾城、秀色、织女、王啬、嫦娥等“美女”意象同置并举、交相辉映的例子。如在《诗经》中,《国风·邶风·简兮》云:“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宋代朱熹(1130—1200年)《诗集传》曰:“西方美人,托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离骚》亦以美人目其君也”[3](P24)。《国风·郑风·野有蔓草》中的“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3](P55-56),还有《国风·陈风·泽陂》中的“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3](P84),等等,均以佳木或芳蕤借代美人,建立了二者彼此的对应联系。不过这种联系还只是简单临时性的,当时完整定型的“香草美人”象征体系尚未健全[4](P116)。其真正生发和大量运用始自《楚辞》。《离骚》便是典型,东汉王逸(生卒年不详)谓:“《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5](P2)《离骚》赋予“香草”志洁行芳的人格化意蕴、给予“美人”贤臣明君的象征性隐喻。这种模式在《楚辞》其余的《抽思》《思美人》《九歌湘夫人》《九歌少司命》诸篇中也屡试不爽。自兹以还,“香草美人”模式被后世文人绵延不绝地宪章祖述,其相应的“自喻或喻明君或贤臣”之理解[6](P34-35),似乎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悖的批评范式。当今人再次面对但凡牵涉到“香草美人”的古代诗文,是否会自我追问:这一根植于比兴寄托的批评范式真的可以普适地诠解一切文学作品吗?这些作品究竟是遭到了前人的片面曲解、还是过度阐释?“香草美人”的意象是否有作者主观感情的融注和真实体验的羼入,因而存在实有所指的可能性?
《曹植甄后传》一书,紧扣“香草”类中的灵芝、芙蓉、蘼芜和“美女”类中的邻人之女、神女、出妇、弃妇、织女、采桑女、罗敷、秦氏等意象,在曹植、甄后的文本和人生时空内遗留的蛛丝马迹中探寻它们被谱写的真实意图。针对“香草”类,木斋指出:“灵芝、芙蓉就是甄后的象征,曹植文集中写作的一个中心语汇就是芙蓉、灵芝,在他的《洛神赋》《芙蓉赋》《九咏赋》等凡是涉及曹植个人自传性质的佳篇名作中,不难处处看到灵芝和芙蓉的倩影”[2](P16),而“‘灵芝’‘芙蓉’‘菱华’等都是同一物的不同说法……这样来看《七启》中的‘采菱华,擢水蘋’,正是《九咏》赋中的‘探菱华而结辞’”[2](P77),是故芙蓉和灵芝是曹植、甄后鱼雁传书的中心语汇和感情升华的媒介递质。针对“美女”类,木斋指出:(《感婚赋》)“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此两句可以和前文《愍志赋》所说的“时无良媒,礼不成焉”对照来看。如果是偶然一次使用,我们可能会理解为一个比喻,现在两次使用,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一定是实有其事,曹植拜托了一位朋友为之说项,但最后得来的消息却是失败了。此事,曹植后来在《洛神赋》中再次提及:“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2](P43)
木斋又说道:“甄后终于接受了曹植漫长岁月的苦苦追求”,《洛神赋》“正是甄后第一次接受曹植恋情的艺术化写照。”[2](P80)他还补充道:
《愍志赋》:“欲轻飞而从之,迫礼防之我拘”,《洛神赋》:“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恃。”曹植在这一句式中,将自己的痛苦、矛盾、纠结、彷徨,倾诉了出来,同时,将自己悲剧性一生的《愍志赋》和《洛神赋》中的关键词用语,在这一诔词中贯通起来。[2](P302)
是故邻人之女、妖娆女子的恨无良媒和河洛之神的限于礼防,是曹植笔下对单向无望的爱情、无从传达的愿望的情节设计。在木斋看来,这些关键篇目就是曹植、甄后缠绵悱恻的爱情见证和扑朔迷离的悬案缩影。
实际上,古往今来对上述作品背后的创作动机是否另有隐情而置疑、揣度者不乏其人。例如《感婚》一赋,既然距曹植时代不远的张华(232—300年)的同题作是对身边事有感而发(3)晋人张华《感婚赋序》曰:“今方岁在己巳,将次四仲,婚姻者竞赴良时,粲丽之观,相继于路。虽葩英肯顾,嫁娶之会,不乏于目,乃作《感婚赋》。”龚克昌认为,张华写就此赋史“见到了民间的婚礼而启发了灵感”。见龚克昌等评注:《全三国赋评注》,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版,第379-380页。,为何曹植在自己的赋中就不能自剖心迹呢?曹植《感婚赋》云:
阳气动兮淑清,百卉郁兮含英。春风起兮萧条,蛰虫出兮悲鸣。顾有怀兮妖娆,用搔首兮屏营。登清台以荡志,伏高轩而游情。悲良媒之不顾,惧欢媾之不成。慨仰首而太息,风飘飘以动缨。[7](P31)
赵幼文就在校注此赋时案曰:“赋句佚落过甚,就其残存部分探索,似为曹植青年时期,有所恋慕而志不遂,发为篇章,以抒写内心苦闷情绪之作。”[7](P32)再如其《愍志赋》云:
或人有好邻人之女者,时无良媒,礼不成焉。彼女遂行适人。有言之于予者,予心感焉,乃作赋曰:
窃托音于往昔,迄来春之不从。思同游而无路,情壅隔而靡通。哀莫哀于永绝,悲莫悲于生离。岂良时之难俟,痛余质之日亏。登高楼以临下,望所欢之攸居。去君子之清宇,归小人之蓬庐。欲轻飞而从之,迫礼防之我拘。[7](P32)
日本学者泽田总清认为,与《感婚赋》一样,曹植此赋“也是表白悲痛的心情的,或者也是失恋的作品罢”[8](P152)。张乘健认为特别是最后一句“正是曹植心中不能明言的隐衷”[9](P32-43)。至于《洛神赋》中的“模特”是否为甄后[10](P515-542),就愈加耐人寻味了。陈庆元分析洛神的形象,认为“她又是人世间最美丽的女子的化身(也许还有甄后的影子)”[11](P233)。唐人李善(630—689年)注《文选〈洛神赋〉》引《记》则更直白地说:“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12](P895)又在该赋末尾“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句后加注曰:“盛年,谓少壮之时不能得当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12](P900)嗣后曹、甄互生情愫的故事在晚唐诗人如李商隐(约813—858年)《无题》等诗、唐传奇如裴铏(约860年前后在世)《传奇》、明清戏曲小说如汪道昆(1525—1593年)《洛水悲》、蒲松龄(1640—1715年)《聊斋志异·甄后》、黄燮清(1805—1864年)《凌波影》等作品中得到进一步的丰满和发展[13](P380-382)。
只是在批评史的长河中,这一类观点大多被指斥为谬言妄说。明清以降,张溥(1602—1641年)、何焯(1661—1722年)、朱绪曾(1805—1860年)等人的挞伐声音更是不绝于耳。代表性的有如明代张溥的《三曹集》引时人张燮(1574—1640年)语云:“燮按,植在黄初,猜嫌方剧,安敢于帝前思甄泣下,帝又何至以甄枕赐植?此国章家典所无也。若事因感甄而名托洛神,间有之耳,岂待明帝始改?皆傅会者之过矣。”[14](P249)清人丁晏(1794—1875年)在《曹集铨评》中曰:“感甄妄说,本于李善。注引《记》曰云云,盖当时记事媒蘖之词。”[15](P11-12)时至今日,占据主流的批评范式,恐怕仍然是遵循“香草美人”的传统来审读。在此视野中,曹植的这些作品无非借着男女缱绻、夫妇离合的套路来主要达到下述目的:
其一,寄寓君臣遇合。丁晏认为,《感婚》《出妇》二赋是:“借男女之辞,讬君臣之谊。一则云欢媾不成,一则云无愆见弃,可以悲其志矣。”[15](P11)蒋寅认为,《杂诗》(特别是其四)以及曹植以怨妇独守空闺为主题的作品“每用男女关系隐喻君臣”,本质上是“继承《楚辞》香草美人的象喻传统”[16](P142-143)。
其二,暗示己志不伸。蒋寅又认为“曹植一再用类似的隐喻来表达这种时不我待的焦虑”,《感婚赋》:“同样是取盛年不偶的隐喻,但更具体到婚媾,由此又派生出《愍志赋》的志愿落空、所处非地的自身遭际的隐喻。”[16](P142-143)池万兴也认为曹植以美女、弃女寄兴的赋作如《愍志赋》《感婚赋》《静思赋》《出妇赋》,“大都有寄寓。其《愍志赋》序文说或人有好邻之女者,时无良媒,礼不成焉,彼女遂行适人。有言之于予者,予心感焉,乃作赋《静思赋》中所歌咏的美女,显然与其诗《美女篇》相同,都寄寓了作者自身壮志未酬的情怀”[17](P247)。
其三,表露慕贤求才。《洛神赋》作为曹植赋中知名度“最著”[18](P1060)者,自然也是备受瞩目,其旨归更是被今人胪列达五种之多(4)分别有“感甄说”“君臣大义说”“悲观失望说”“苦闷说”“理想化身说”。见陈庆元:《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第231-232页。。除了抒发一腔爱君恋阙的衷情和怀才不遇的感慨经久不衰以外,慕贤求才之说也颇得人心。詹锳注意到王逸注《离骚》“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结言兮,吾令蹇修以为理”几句曰:“宓妃神女以喻隐士,言我令云师丰隆乘云周行求隐士清洁若宓妃者,欲与并心力也……言己既见宓妃,则解我佩带之玉以结言语,使古贤蹇修而为媒理也”,后来的五臣注亦曰:“虙妃以喻贤臣”,当詹锳再参读刘向(前77—前6年)《九叹》中《愍命》一章时,发现所用宓妃用意与《离骚》无异,所以他认为《洛神赋》中求女之情和宓妃寓意“乃喻思慕贤者”[19](P12-13)。
实则这种沿袭“香草美人”模式的批评范式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就比如说“原型批评”的运用,即主张从神话、宗教、民俗中挖掘相关文学母题和原型的形成、积淀、嬗变的元素和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涌现大量爱情主题和女性题材的文学作品并非偶然,郭建勋指出,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曹植《洛神赋》、应玚《正情赋》、阮籍《清思赋》、陶渊明《闲情赋》等作品,作为汉魏晋南北朝阶段“神女—美女”母题文学中的一大分支,“剔除了高唐神女原型中‘情欲’的因子,却保留了原型美丽和崇高的特性”,这一系列作品,借鉴陶渊明在其《闲情赋》中的总结,即“‘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的基本模式和‘将以抑流荡之邪心’的基本思路”[20](P360-361)。从中可以看到曹植在描写恋爱及女性方面的程式和渊源。
而木斋的《曹植甄后传》对“香草美人”传统的颠覆力无疑是目前为止最为彻底的,不过他的假设并非出于一己标新立异的臆想,他的结论也不是来自全然无凭的推理,而是自有其通过苦心孤诣地搜集、辨析得来的证据和观点的支撑。兹试将他书中的精华归纳并转述如下:
第一,木斋发现《北堂书钞》划归为曹植所作的诗句“弹筝奋逸响,新声好入神”与同书同页所载之曹植《箜篌引》中的“秦筝何慷慨,齐瑟且和柔”诗句异曲同工,由此纠正此前学者将前诗论为曹植的“逸文”之说,并坐实曹植就是古诗十九首之一《今日良宴会》的作者。
第二,木斋通过比较图像与文字,深感现存宋临本顾恺之(348—409年)《洛神赋图》中所绘洛神的发髻形制与晋人陆翙(生卒年不详)撰《邺中记》、元代文言志怪小说集《琅嬛记》描摹的别无二致,而图中洛神的体态神情则与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兰芝的形体刻画殊途同归。
第三,木斋发觉元代无名氏编纂的《河南志》附录的汉魏之际的《洛阳宫城图》中出现了芙蓉殿与灵芝池,由此体悟到曹植诗作《灵芝篇》实乃曲笔对甄后吐露心意、追忆二人之间刻骨铭心的恋情的语码。图中还有“阿阁”“芙蓉殿”等建筑物也赫然在列,印证了汉魏之际使用过的宫廷语汇。
第四,木斋通过田野考察,获悉甄后所葬之村即“灵芝村”,在邺城原址之南城郊外。比对《隋书》“志”第十五所记载,又可知邺城在北周时期曾被改名为“灵芝县”。而曹植文集中的中心语汇就是芙蓉和灵芝,这种“巧合”增添了对曹植、甄后之恋联想的说服力。
第五,木斋对接近曹植时代的作者作品的旁引曲证,加固了曹植、甄后的关联。例如,他认为陆机(261—303年)的《拟古诗》中的“阿阁”“兰室”等关键词揭示了曹植、甄后新婚燕尔诗之地,诗尾又将曹植最后被鸩死的情景进行了复现。木斋书中还论及了阮籍(210—263年)《咏怀》诗其二、其十九等此类或与曹植、甄后恋情相关的作品。
笔者在感佩木斋勇气可嘉、用心良苦之余,还要再“吹毛求疵”,不揣冒昧略举这部书中有几处我个人不甚明白的小问题,以待求教作者并与之商榷。譬如,书中说道:“曹丕另有一篇《出妇赋》:……这是否为曹丕自己人生经历的真实记录?……是否就是对甄氏出妇的记载呢?……是说送甄氏去了临淄侯曹植的居所呢?”[2](P102)这一连串疑问不但与其前著《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中谈及曹丕(187—226年)、曹植同题诗《代刘勋妻王氏杂诗》与《出妇赋》“诗赋同写一事”的既有看法相悖[21](P29),也与本书中言之凿凿的“曹丕的《出妇赋》和《代刘勋妻王氏杂诗》,诗赋同写一事”[2](P132)的结论略相扞格。其实曹丕等人诗赋的本事源自邺下文人酬唱共作,前人已有明辨[22](P1-411)。
又如书中说道:“牛郎织女”的爱情传说是“甄氏的创造”,而“牛郎织女的原型,正是曹植、甄后之间的恋情在此前传说文化基础之上创造出来的,曹植、甄后在后来漫长离别的痛苦岁月里,创造了这个故事”[2](P77)。虽然在《诗经》中,《小雅·大东》一诗提及的牵牛、织女、天汉与“牛女传说”无涉,但据赵逵夫考证,另有分别形成于秦早期活动区域和汉水流域周人活动地区的《秦风·蒹葭》《周南·江汉》两诗所表现的情节、意境已非常贴近同后代的牛女传说,二者仅仅是未点出“牵牛”“织女”字眼而已。西汉末年所成的象数学专著《易林》中《夹河为婚》《天女推床》二首中的数句韵语也敷衍了牛女传说。东汉末年蔡邕(133—192年)的《青衣赋》《协初婚赋》中都可见“牵牛织女”传说在周、秦人群体记忆中印象之深。汉代昆明池边一对牵牛织女石像,在东汉班固(32—92年)《西都赋》、张衡(78—139年)《西京赋》中有载,也侧证了牵牛织女故事早于曹植生活年代便已广为传播[23]。
另外,书中说道,《捣素赋》和《自伤赋》(《全汉文》中题作《自悼赋》)是反映“班婕妤的人生经历”的两篇赋作[2](P131)。《捣素赋》的作者真伪结论洵为定谳,从李善至当代学者,多辨其为后世托言班婕妤(前48—2年)所作,因而被视作班婕妤的自传性作品再而充当论据似有不妥[24](P260-278)。
当然,以上献疑和浅见断然不能否定也不会影响木斋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最大努力地系统梳理和考辨曹植、甄后的际遇、处境、纠葛始末的贡献。可以预见的是,伴随此书的付梓,相关领域内会是怎样一番雷霆乍震、石破天惊的景况。木斋将这些散落的诗文和零碎的史料重新安放到可能出现的时、空交叉点上,试图寻绎曹植、甄后的情感纽带与其中的地名、方位、时间、节气、人物关系上存有严丝合缝的契合性[2](P340),尽管读者们未必会人人认同,但这未尝不是使这一问题的研究避免陷入停滞的嘉惠学林和激励后学之举,更何况“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本来就是探讨各种可能性”[1]。笔者真诚期待学界对木斋新作和后续的不同声音能继续秉持认真和开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