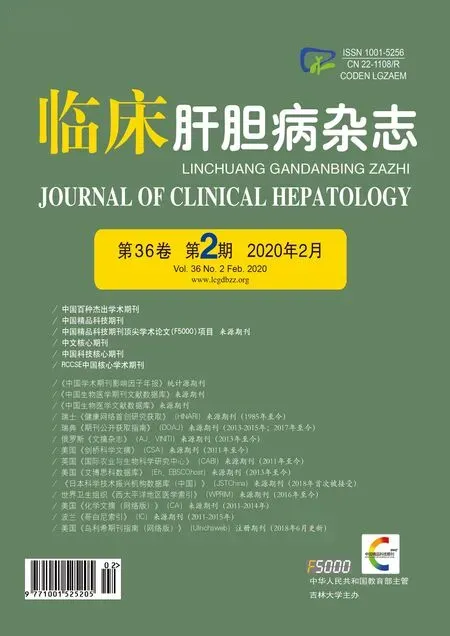循环游离DNA在肝癌和肝相关性寄生虫病中的应用进展
后亚军, 张灵强, 樊海宁
1 青海大学 研究生院, 西宁 810000; 2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肝胆胰外科, 西宁 810000;3 青海省包虫病重点研究实验室, 西宁 810000
Mandeld等[1]在1948年首次报道循环游离DNA(circulating free DNA,cf-DNA),是指在非细胞成分中发现DNA片段。这一发现的意义几十年来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77年,Leon[2]发现癌症患者的血液中cf-DNA浓度增加。10年后,Stroun等[3]发现cf-DNA来源于癌细胞,这一结果得到了Sorenson等[4]的验证,该研究通过等位基因特异性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在血浆cf-DNA检测出突变的KRAS癌基因序列。经过多半个世纪的研究,为cf-DNA的临床应用打开了大门。
1 cf-DNA的来源
目前研究[5]发现,cf-DNA通过细胞凋亡和坏死被释放到血液循环中,或通过活性细胞分泌以及寄生虫感染导致免疫反应引起的炎症衍生DNA片段进入血液循环中。此外,cf-DNA在其他体液中也有发现(包括唾液、脑脊液及尿液等体液中)[6-9]。最初认为血液中较高水平的cf-DNA可能是肿瘤生长的指标[2],但正常人循环中也存在较低水平cf-DNA(平均10~15 ng/ml),在组织应激条件下可升高,包括运动、炎症、组织损伤等[10]。
2 cf-DNA的分离和检测
由于疾病源性cf-DNA水平低,半衰期短,需要对cf-DNA进行专门的分离和检测。目前主要的分离方法有:相分离法、基于硅膜的旋转柱技术和基于磁珠的分级筛选法[11-12]。Campos等[13]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微流控固相萃取装置用于cf-DNA的分离,该方法具有操作简便、成本低等优势。目前检测cf-DNA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方法是靶向DNA测序技术,如数字PCR(dPCR)、液滴PCR(ddPCR)、巢式PCR(nested PCR)、实时PCR(real-time PCR),深度测序以及靶向纠错测序等[14-16];另一种检测方法是非靶向第二代测序技术,如全基因测序、全外显子组测序等[17]。
3 cf-DNA在肝癌中的应用
精准医疗在肿瘤学应用的关键目标是提高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水平[18]。在癌症患者中,从肿瘤细胞中释放出来的cf-DNA通常被称为循环肿瘤DNA(circulating free tumor DNA,ct-DNA),ct-DNA在整个cf-DNA中的占比差异很大,从小于0.1%到大于90%不等[19]。由于肿瘤异质性的存在穿刺组织活检很难反映癌症基因组全貌[20],有证据[21]表明ct-DNA提供了较全肿瘤基因组信息,因为它呈现了从多个肿瘤区域释放入循环中的DNA或者来自不同肿瘤病灶的肿瘤相关循环DNA。总之,ct-DNA的这些特征使其在精准肿瘤医学应用中成为有前景的分析物。
肝癌已成为中国人群过早死亡的第五大原因[22]。大多数肝癌患者就诊时已进展到中晚期,预后极差[23]。因此,开发精准分子检查工具至关重要。Xu等[24]通过比较肝癌组织和正常血液白细胞,确定了肝癌特异性甲基化标记板,并发现肝癌相关基因和与之匹配的血浆ct-DNA的甲基化特征呈高度相关,且与肿瘤负担、治疗反应和分期密切相关。该研究表明ct-DNA甲基化标志物在肝癌的诊断、监测和预后中的实用性。近期Cai等[25]通过对cf-DNA中5-羟甲基胞嘧啶(5-hydroxymethylcytosines,5hmC)的全基因组定位,发现并验证5hmC-Seal技术是一种高灵敏的表观遗传学工具,可用于早期肝癌的诊断。cf-DNA在肝癌中的应用,因其非侵入、可靠的生物标志物等特性,可以补充并最终取代侵袭性肝穿刺活检,用于肝癌的诊断、分期、疗效评价以及预后分析。同时,在疾病的早期发现肝癌,并行根治性切除,这对于提高患者的生存率至关重要。
4 cf-DNA在肝相关性寄生虫病中的应用
cf-DNA作为生物学标志物应用于肝相关性寄生虫疾病的检测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虽然cf-DNA检测在寄生虫学领域的应用没有像在肿瘤学领域发展迅速,但该方法可能对未来肝相关性寄生虫病的诊断和控制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用于诊断寄生虫病的方法中,宿主体液中检测寄生虫cf-DNA具有良好前景。迄今为止,cf-DNA已应用于疟疾[26]、阿米巴肝脓肿[27]、血吸虫[28]以及肝棘球蚴[29]等累及肝寄生虫疾病的检测中。
4.1 疟疾 疟原虫是导致疟疾的病原体。尽管血液涂片的显微镜检查仍然是疟疾诊断的“金标准”,但使用PCR进行分子检测因其灵敏度和快速诊断性在疟原虫诊断中越来越受欢迎。在早期研究中,Gal等[26]首次报道疟疾患者的血浆中存在疟原虫源性cf-DNA,共采集了10例疟疾患者的血样,其中6例疟疾患者血液涂片镜检均为阳性,血浆PCR检测均为阳性。2例疟疾患者显微镜检查呈阴性,血浆PCR检测呈阳性。2例疟疾治愈的患者,显微镜检查和血浆PCR检测均为阴性,血浆中疟原虫源性cf-DNA的定量测定可能是诊断疟疾和评价疟疾预后的潜在指标。研究[30]表明,利用PCR技术可在唾液和尿液中检测到疟原虫源性cf-DNA。Ghayour等[31]采用巢式PCR技术,对恶性疟原虫和间日疟原虫的唾液、尿液和血液样本进行线粒体细胞色素B基因定位,结果显示,巢床PCR对疟原虫混合种感染的诊断比血涂片显微镜检更为敏感。唾液和尿液样品的巢床PCR扩增结果显示,唾液样品更准确。因此,在需要重复取样的疟疾诊断中,唾液可以作为血液的替代品。
4.2 阿米巴肝脓肿 阿米巴肝脓肿是由于溶组织内阿米巴突破黏膜屏障,经门静脉循环进入肝脏引起的肝脓肿[32]。未及时诊治的阿米巴肝脓肿是导致阿米巴患者死亡的主要因素。由于阿米巴肝脓肿与化脓性肝脓肿在血清学及影像学检查较难鉴别,易导致病情延误。Parija等[27]首次报道由于阿米巴肝脓肿患者的肾脏滤过屏障对溶组织内阿米巴DNA具有渗透性,通过PCR技术对疑似患者尿液检测有助于阿米巴肝脓肿的诊断,也可为经甲硝唑治疗后阿米巴肝脓肿患者预后评估提供帮助。Haque等[33]研究表明,在阿米巴肝脓肿患者的血液、唾液及尿液中应用实时PCR技术检测到了溶组织内阿米巴相关cf-DNA,但唾液和尿液检出率优于血液。cf-DNA检测技术为阿米巴肝脓肿的诊断以及疗效评价提供了新的方法。
4.3 血吸虫病 cf-DNA作为诊断工具已用于血吸虫患者的血浆、血清和其他体液(如唾液、尿液)的检测[28,34]。检测cf-DNA的临床样本获取方便,克服了使用Kato-Katz方法收集粪便样本和进行显微镜检查的实际困难和低精确度。因此,cf-DNA检测经常被用于血吸虫病筛选的敏感项目[35]。最近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与显微镜检查相比,人粪便样品定量PCR检测可提高诊断准确性。这种cf-DNA可能来源于成虫或虫卵。然而,尚不清楚成虫DNA如何从循环中进入肠道[36]。 实际上,与Kato-Katz检测相比,血吸虫相关cf-DNA检测有更高的准确性[37]。 此外,研究[38]表明,宿主血清检测血吸虫cf-DNA,在动物模型感染的早期阶段就可以进行阳性诊断。 使用cf-DNA检测能发现早期感染,有利于早期治疗,这将为血吸虫患者的治疗提供机会,而不会发展成慢性疾病。
4.4 肝棘球蚴病 肝棘球蚴病包括由细粒棘球蚴绦虫感染引起的肝囊型包虫病和多房棘球蚴绦虫感染引起肝泡型包虫病。目前,该病的诊断方法主要有影像学及血清学检查,影像学检查的挑战在于对微小病灶(<2 cm)诊断存在困难,血清学检测的局限是感染人群中有一部分患者无包虫病阳性血清学标志物,cf-DNA用于棘球蚴病诊断有望提供新的途径[29]。Chaya等[39]首次应用PCR技术检测囊液、血清和尿液中细粒棘球蚴特异性核酸用于囊型包虫病的诊断,研究结果表明,PCR对棘球蚴囊液中细粒棘球蚴特异性DNA的检测是高度敏感的,在囊型包虫病囊泡破裂的患者血清中检测同样具有高度敏感性(可能与囊泡破裂特异性DNA进入血液循环有关)。Baraquin等[40]报道,首次确定在泡型包虫病患者、泡型包虫病动物模型中存在cf-DNA。丰富了泡型包虫病的分子学诊断方法,但由于该研究患者中检测到的cf-DNA浓度极低,可能与样本量、样本提取以及样本的性质(该研究从血清中提取cf-DNA,肿瘤研究中多在血浆中提取)有关,此外关于特定的寄生序列是否优先被释放有待进一步研究。
5 总结
cf-DNA检测技术在肝癌领域和肝相关性寄生虫感染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是,有效临床应用cf-DNA检测技术需要准确理解这种技术的优点和局限性,同时也要标准化该技术的检测方法,以便正确解释结果,以指导临床决策。此外,cf-DNA检测技术应用于肝相关性寄生虫疾病诊断相对不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特别是在改进DNA提取方法的同时降低检测成本,以及提高诊断准确性和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