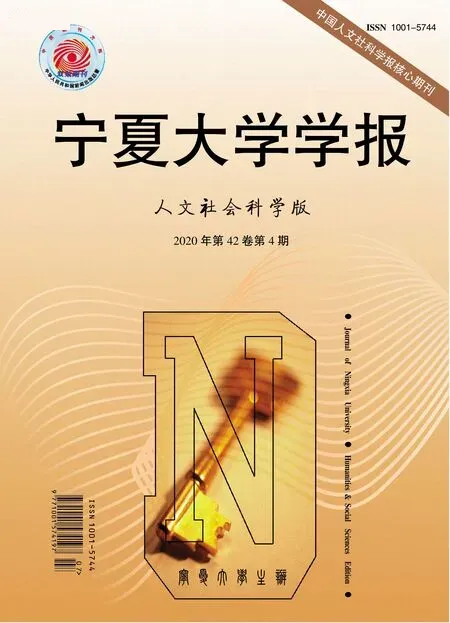唐宋易代之际帝王身份困境的书写与词体发展
宋 华
(北方民族大学 文传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晚唐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帝王面临藩镇权臣威胁和权力的失落,五代之后,更是小国林立,政权翻覆。帝王在战乱之际失却了九五之尊的地位,陷入自我身份认知与现实处境相矛盾的困顿之中,他们的心灵困惑和内心挣扎,借由词这一言情的文学体裁留下了痕迹,并对词体的发展起到作用。简要而言,在词的发展过程中,帝王通常有两个途径对词的发展起作用:一是通过词的创作直接具有引导之功。二是通过政治导向间接起作用。
一 帝王词的创作与词体言情疆界的拓展
词体由于字数更多,相较于诗歌而言,形式上更为灵活多变,能够容纳更丰富的思想内容,适合抒发较为复杂的情感。王国维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所谓“言长”正是指词能够将感情表达得更为细致深长,将不足为外人道的曲折幽隐之情通过语言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达到情感宣泄的目的。“情”的范畴,既可以包括那些在诗歌中不便言说的艳情,也可以包括一些与身份不相符合的﹑不能随意吐露的隐幽之情。在唐宋易代之际,君主生活际遇的改变和心灵体验的丰富也在词的创作中得到呈现。
首先,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君主大权旁落,生存困境带来的生命忧虑在帝王词中得到展现,这在客观上拓展了词的言情疆域。唐昭宗的创作是这方面的代表。朱彝尊《词综》载唐昭宗所作《菩萨蛮·题华州城楼》:“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开篇遥望秦宫殿,感情基调和盘托出,非艳情之思,也非寻常伤春悲秋之调,遥望秦宫,隔山隔水,缥缈不可及,“茫茫只见双飞燕”,是在一片空茫之中,万物沉寂,唯有燕子高飞,似乎隐含插翅欲飞之意,据词后注引尉迟偓《中朝故事》言,乾宁三年军阀李茂贞破长安,唐昭宗出奔,被华州军阀韩建收留,住在陕西华州,史料载“帝郁郁不乐,每登城西齐云楼远望”,古人每有离愁,往往登楼远望,昭宗在华州齐云楼登楼,心中深锁的愁已经不是普通离愁,身为皇帝,一朝寄人篱下甚至于仰人鼻息,远望旧日宫殿邈远,此处也仅是暂时栖身,由身份落差带来的悲凉定然较之常人更甚,此词亦颇有凄惶无助之感。生逢乱世,人人艰难,但与乱世中士大夫为生存而如履薄冰的状态不同,末世君主往往成为众矢之的,或被争夺利用,或成为被追杀的对象,他们连变节自保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在权力的角逐中成为牺牲品。在这种时候,责任所带来的压力促使帝王呼唤权力的回归,唐昭宗言“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大权旁落,李氏的大内早已不再是权力的归处,这种呼唤正是帝王威信丧失的表现。
安史之乱以后,藩镇拥兵自重,唐王朝国祚式微,昭宗登位之初“有恢复前烈之志”,且“体貌明粹,有英气”,并“尊礼大臣,梦想贤豪”,但面对藩镇割据﹑大权已失的事实,他也无法力挽狂澜,在藩镇的混战中疲于奔命,最终死在朱温手中。《礼记·乐记》中说“亡国之音哀以思”,唐昭宗在词里说“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其哀婉凄伤之状,正是一个王朝不复兴盛﹑渐行渐远的缩影。与唐昭宗创作歌词大概同时的晚唐词人,如牛峤,其词尚在写艳情,诸如“舞裙香暖金泥凤,画梁语燕惊残梦”(《菩萨蛮》),沉浸于声色描摹之中,即便其写柳枝名句“解冻风来末上青,解垂罗袖拜卿卿”亦需要与“无端袅娜临官路。舞送行人过一生”的赠妓之意相连,主人公的私人感情隐于词句之下,大有逢场作戏的意味,禁不起更深的推敲。生年稍早,名声更大的温庭筠,曾写“虚阁上,倚栏望,还似去年惆怅。春欲暮,思无穷,旧欢如梦中”,词中不沾染艳情,而有极强的今昔对比之感,婉柔而低回,呈现出一定的言外之意,以至于清末张惠言在其《词选》中称: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节节逆叙。此章从梦晓后,领起“懒起”二字,含后文情事,“照花”四句,《离骚》初服之意的附会之说。相比之下,唐昭宗也有一首写今昔对比的词《菩萨蛮》:
飘摇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思梦时时睡,不语常如醉。早晚是归期。穹苍知不知[1]。
寄人篱下的飘摇命运促使词人生出伤今悼昔之感,他怀恋皇室昔时的繁华,“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归又不能归,于是“思梦时时睡,不语常如醉”,由于现实中渺不可及,于是别寻寄托于梦境。命运的不可捉摸使帝王失去立身存世的根本,陷入身份的尴尬与人生的迷茫,只能在浑浑噩噩中度日,“早晚是归期,穹苍知不知”,绝望之情已达极致,与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一样,只能通过问天的形式来表达心中的困惑。然而帝王思归,与普通士人终究不同,作为处于国家至尊地位的人,权力就是归处,一旦失去权力,归处也就无从谈起,与上一首词相类似,这首词所描绘的也是帝王失却权力的迷惘之情,由于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遂呼唤英雄的拯救,英雄迟迟不来,以至于绝望而问天。《全唐诗》中载:“帝攻书好文,承广明冠乱之后,唐祚日衰,遗诗只字,皆其播迁所制也”[2],言唐昭宗好读书喜作文,所谓“遗诗只字”指向诗歌,但其本意乃言昭宗文学作品是其颠沛流离之时所作,词亦在其列,与诗歌的应酬兴味相比,词反而更能展现出帝王如履薄冰之际的生命状态。《唐诗记事》中记载:“帝在洛日忧不测,与皇后内人唯沈饮自宽,尝歌云:纥干山头冻杀雀,何不飞去生处乐。此古语,帝述之者。”[3]帝王名不副实且怀生死之忧,但身份的尊贵又不容许他在诗歌中表达太多的细索伤感,饮宴之际,在酒精的作用下,难免将深锁之愁向内人宫女吐露出来。这种生命落差下对幽隐之情的独特体验,非但超出艳情的范畴,直指乱世中的世态人心,同时也由于其可以通过文献佐证,将此种感伤之意落实为必有之情,从而在词体的发展中具有拓展词的言情疆界的意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指的正是帝王的身世之感对词体的改造,实则在李煜之前,唐昭宗李晔的《菩萨蛮》已有此意。
其次,易代之际,君主的亡国之词,成为拓展词的情感疆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安史之乱后,山河破碎,小国林立,权力被不同的武装势力掌握,政权翻覆,小国的君主被俘成为阶下囚,面临身份的困境和心灵的焦虑,这其中李煜的创作具有典型性。
李煜词虽以风花雪月的传统题材为主,却不乏有突破艳情而表达士人之思的作品,诸如“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等均不涉艳情而有深意,被王国维称为“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其亡国后所做《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成为拓展词之情感领域的典型作品: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4]。
这首词记述李煜被俘的状况,上片描写国土的广袤和境内的富庶繁华,“几曾识干戈”既是表达百姓不谙战事,同时暗示出自己缺乏军事才能。下片抒发亡国之感,与唐昭宗词中那种朦胧怅惘的忧思不同,李煜作为亡国之君,表达出他特有的人生落差和极致失落,其词中“最是仓皇辞庙日”是这首词的关键,也是最能表达其情感落差之处。回望历史,他可能很遗憾自己是一个不懂军事的帝王,也可能在国破的那一刻,幡然醒悟出为君之道,富庶繁华需要依赖强大军事力量的保障,然而一切为时晚矣,一句“最是仓皇辞庙日”,道出几缕悲情也道出了几缕悔恨,然而接下来集中笔墨给亡国之际的特写镜头,“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作为亡国之君,在被俘虏的那一刻,他似乎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仓皇之际,最令他难忘的是听教坊离歌,是与宫女垂泪作别,祖宗江山责任之类并不在思考的范围内,让他最悲哀的是华贵生活的逝去,是对“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的凄楚现实带来的对往昔逍遥的留恋,难怪苏轼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罪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5]。苏轼生活在宋仁宗﹑神宗时期,王朝国祚稳定,秉持儒家士大夫以道自任的情怀,极具责任感的苏轼自然对李煜的感叹有所不满,但李煜作为君主在亡国之际,他所承受的感情落差实则是十分独特的,反映出帝王这一特殊阶层在国破家亡时的特殊心态,清代尤侗《西堂杂俎》中言:
安禄山之乱,明皇将迁幸,当是时,渔阳鼙鼓,惊破霓裳,天子下殿走矣。犹恋恋于梨园一曲,何异“挥泪对宫娥”乎?后主尝寄旧宫人书云:“此中日夕只以眼泪洗面”而旧宫人入掖庭者,手写佛经为李郎资冥福,此种情况,自是可怜。乃太宗以“小楼昨夜又东风”,置之死地,不犹炀帝以“空梁落燕泥”杀薛道衡乎?[6]
从尤侗的记载来看,在“挥泪对宫娥”的问题上,乱家失国后留恋教坊歌姬的君主不只李煜,唐玄宗也是如此,尤侗认为李煜因此受到额外的责怪是不妥的。歌姬是达官显贵享乐的产物,歌舞升平是每一个封建帝王所渴望的社会图景,留恋教坊也是对过往治下繁华的留恋。这是一种情感层面的表达,而不是言志层面的叙说,是为君之道和作文之道两个层面的问题。梁晋竹在《两般秋雨盦随笔》中称:“讥之者曰仓皇辞庙,不挥泪回宗社而挥泪于宫娥,其失业也宜矣,不知以为君之道责后主,则当责之于垂泪之日,不当责之于亡国之时。若以填词之法绳后主,则此泪对宫娥挥为有情,对宗社挥为乏味也。此与宋蓉塘讥白香山诗谓‘忆妓多于忆民’,同一腐论”[7]。梁氏所论点明了问题的关键,王国维称后主“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也在《人间词话》中称李煜是有赤子之心的词人,均是指向其文学创作才华,尤其其词中所展现的亡国之君在亡国之际的独特情感体验。
言情是词的本质特征之一,苏轼等人以为君之道责备李煜,恰恰是词人的至情体验,帝王对亡国之情的书写,其心灵落差感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情感体验,这正是易代所带来的契机,词在帝王词人的手中,情的内涵得到丰富,言情疆域得到扩展,促进了词的言情特质的发展,创造出具有极高审美水准的词作。
二 帝王与贵胄词人群体对词体功能的拓展
在唐五代纷乱的社会背景中,群豪崛起,政权翻覆成为常态,人人都有可能占据顶级权力,各个小王朝的帝王在这个过程中失却了天子身份的独特性。一些在末世乱局中继承皇位的君主,虽然政治才能有限,但由于占据显要位置,拥有一定范围的社会财富,便将个人意志最大化,而权力的朝不保夕,又使他们分外在意拥享权力的人生体验,遗憾的是,由于缺乏魄力,这种体验往往不是以权力的扩张为表现,而是以探寻个体生命的欢愉为主要内容,他们往往纵情声色,大臣也投其所好,词这一佐酒伴宴的文体得到显贵阶层的欢迎,这些人通过政治地位而结成创作团体,如西蜀和南唐君臣,他们的创作强化了词的娱乐功能,也促进了词在创作上繁荣。
五代时前蜀后主王衍是帝王纵情声色的典型代表,据《北梦琐言》记载“衍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脂夹粉,名曰醉妆”[8],宫廷生活充满荒淫味道,他曾自作《醉妆词》记述其享乐生活:“这边走,那边走,莫厌金杯酒。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沉堕情欲的生活可见一斑。又有记载王衍“宴于怡神亭,自执板,歌《后庭花》﹑《思越人曲》”。身为君主,沉迷声色,以至于充当伶人角色,从为君之道的角度看,自然是有违伦常。但身为国主而创作歌词,将艳情之思述之于文学的行为必然带动整个时代对文学娱乐功能的认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词体娱乐性的发展。
南唐二主善作词,《老旧续闻》中称“金陵妓王感化善词翰,元宗手写山花子二阕赐之云:‘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韵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又云:‘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李璟的词写得情思细婉,是婉约词中的上乘之作,这些作品又与妓女相关,写相思流连之情,委实臻于极致,《词苑》中载:‘南唐书云:王感化善讴歌,声韵悠扬,清振林木。系乐部为歌板色。元宗尝作《浣溪沙》二阕,手写赐感化。后主即位,感化以词札上之,后主感动,赏赐感化甚优’。”[9]王感化为妓女,元宗身为君主写词赠妓,本是与帝王身份不符的行为;后来李煜对王感化的赏赐,不仅是出于对父亲的怀念,同时亦可目之为对元宗填词赠妓行为的赞赏,由南唐二主的行为可见晚唐五代时期君王享乐风气之炽。南唐大臣每每能文,徐铉﹑冯延巳﹑陶榖皆是其中佼佼者。
南唐宰相冯延巳存词百余首,是南唐贵胄词人中的典型,据《南唐书》载:“其《鹤冲天》词云:‘晓月坠,宿云披,银烛锦屏帏。建章钟动玉绳低,宫漏出花迟。’又归国谣词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明朝便是关山隔。’见称于世。元宗乐府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10]从这些史料来看,南唐君臣将词的创作作为谈资,虽无意于改造词体,但以君主和大臣身份,他们对小词的津津乐道,是对文学娱乐功能的强化,他们的作品所展现出的审美倾向也必然会引导词的发展。君王的这些作为无疑大大地刺激了词的创作,提升了词体地位。
帝王沉迷歌舞声色享乐,并不总是能够笼络到投其所好的大臣,也有个别劝谏者的身影见诸史料,《古今词话》中载:“中宗一日乘醉命春天水调,乐工惟歌‘南朝天子爱风流’及‘本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再四不易,因罢鼓吹。”[11]时常有这样勇敢的伶人乐工见诸史料,大抵是为突出君王兼听则明的一面,所以这些伶人可能真的侥幸逃脱被治罪的命运,也可能是史料有意回避了这些劝谏伶人的结局。《幸蜀记》中有关王衍的记载则展现了另一幅场景:“衍尝宴怡神亭,召嘉王宗寿赴宴。宗寿因持杯谏衍:‘宜以社稷为念,少节宴饮。’其方言慷慨激烈,至于流涕。衍有愧色。佞臣潘在迎﹑顾在□﹑韩昭等奏曰:‘嘉王从来酒悲,不足责。’乃相与谐谑戏笑。衍命宫人李玉箫歌衍所撰宫词侑宗寿酒,宗寿惧祸,乃尽饮之。在迎曰:‘嘉王闻玉箫歌即饮,请以玉箫赐之。’衍曰:‘王必不纳。’宗寿字永年,建之族子。”[12]在皇帝饮宴娱乐的场合,伶人也好,士子也罢,甚至是皇帝近亲,忽然发出好好治理国家少一些宴饮的不同声音,无论如何都是不合时宜的,容易引起反感,如臣子王宗寿一样进谏后战战兢兢,如君主王衍一般暗藏在笑脸下的隐晦不悦,似乎更符合历史的实情。这些劝谏之所以流传下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词的印象,是与娱乐享受相联系的是“小道”“艳科”,不值得提倡的,这也从一个侧面促进了其娱乐功能的强化。
值得注意的是,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的记述是士大夫的劝谏,其中“潘佑以词讽谏”条载:“南唐张泌﹑潘佑﹑徐铉﹑汤悦,俱有才名,后主于宫中作红罗亭,四面栽红梅,欲以艳曲记之。佑应令云:‘楼上春寒三四面。桃李不须夸烂漫。已失了东风一半。’时已失淮南,故佑以词讽谏云。”李煜是典型生在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君主,沉迷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无力自拔,在朝臣的保护和蒙蔽中伤春悲秋,直到家破国亡才如梦方醒。此处潘佑以词进行讽谏,一方面是对君主投其所好,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劝谏,可以看出词在娱乐功能之外已经开始具有某种政治意义。
入宋以后,宋太祖对词的态度呈现出矛盾性,客观上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北宋由后周转化而来,士大夫擅词者本就不多,宋太祖对南唐后主李煜的评价较低,词更加失去其土壤。但由于唱词活动广为流传,作为一种娱乐项目,在一些场合却具有了特殊的政治作用。如《后山诗话》中载:“吴越后王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妓弹琵琶,王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楼云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从这段记述来看,太祖也是将吴越王的唱词当作其心声的反映,从而在政治谈判中利用了这一点,以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
后蜀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因文采得到太祖的赏识,蔡绦《铁围山丛谈》中载:“蜀传至昶则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宫词者是也。国朝降下西蜀,夫人随昶归中国,至十日召入宫中,而昶遂死昌陵。后亦惑之,尝造毒,屡为患不能遂,太宗数谏未能去。一日从上猎苑中,花蕊夫人在侧,太宗方调弓矢引满拟走兽,忽回射夫人,一箭而死”[13]。蔡绦对花蕊夫人的来历和在宋朝的经历及最后归宿记述甚详,太祖欲宠花蕊而杀孟昶,听起来是一段风流故事,但如果回到真实的历史情境之中,情况可能又有不同。这虽然不一定能鼓励词的创作,但至少可以一窥词在宫廷娱乐中必不可少的地位,甚至可能起到决生死的作用,透露出一丝其终将在和平年代走向壮大和繁荣的讯息。
总之,安史之乱后,帝王手中权力失落,唐末士人之间的党争与宦官专权是帝王无力驾驭权力的突出表现,在混乱中登基的唐五代君主或将权力委托给个别大臣,或交由宦官,在争权夺利中,整个时代陷入家国不宁人心不安的动荡局面之中。五代君主并不像统一王朝的帝王那样拥有执政的自信,手握权力又没有安全感,加之缺乏远见卓识,身为君主却不能行使君权,或者所掌控的权力稍纵即逝,他们陷入群体性的焦虑。焦虑的君主,或者通过作词表达自己的焦虑,或者通过纵情娱乐来纾解内心的焦虑,词体也就在这动荡和焦虑中觅到了一丝发展的契机,最终壮大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家族中最能表达作家内心深微幽隐之情的文学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