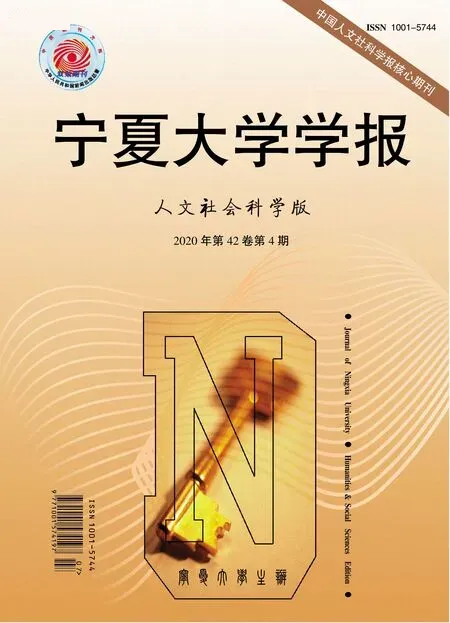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叙事”
王 潇
(辽宁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如今,以双雪涛﹑班宇﹑郑执为代表的铁西青年作家群,用自然流畅的笔法﹑朴实粗犷的语言﹑虚拟现实的手法记录了东北经济转型时期的改革大潮。正是老工业基地厚重的文学“黑土地”,赋予了他们创作中的时代感。双雪涛﹑班宇﹑郑执3 位80后作家不约而同地出现,把“铁西”变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1]。凭借《人民日报》集“严肃性”与“通俗性”为一体的特性,“铁西三剑客”的提法,既体现了来自“权威”的意志,又体现了来自“民间”的呼声。
当下对于“铁西三剑客”颇为密集的评论话语与活动,始于2015 年2 月双雪涛在《收获》上发表的《平原上的摩西》,黄平甚至将之称为“新东北作家群”出场的“标志”。2018 年班宇发表《冬泳》《逍遥游》产生轰动效应,同年匿名作家计划评选活动当中,郑执超越阎连科等文坛大家获得首奖引发广泛关注。2019 年10 月《人民日报》从新的文学审美角度阐明“铁西三剑客”的写作意义。同年11 月“文学辽军‘铁西三剑客’探讨会”﹑第十届辽宁文学奖特别奖共同授予“铁西三剑客”,均从正面角度评价了其存在现状及其意义。当然,以2019 年12 月《文艺报》发表黄平与张定浩的对话为典例,两人评价“铁西三剑客”迥然不同的维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评论界的“多声部”状貌。2020年以来,对“铁西三剑客”的评论文章显著增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期便以“新现象研究”的专栏探讨“铁西三剑客”,这均从侧面显示出丛治辰称“铁西三剑客”为2020 年初一个“文学事件”的根据所在。
当下对于该“文学事件”的解读,主要存在“内容层面”(即“写什么”)解读﹑“技术层面”(即“怎么写”)解读﹑“意义层面”(即“写得怎么样”)解读。然而这类弥漫文坛的解读,大多以既定的作家作品为中心,辐射文本自身及其同现实意义之间的“有无—高低”。其实,在“正负”批评导向的表述之下,有意无意地遮蔽了“铁西三剑客”在多个场合传达出对“东北”“城市文学”等字眼的逃离,以及近期新作当中透露出的“去东北化”。可见,“评论导向”同“作家心声”之间颇具迷惑性的背离,在一定程度上尚有待发掘。
厘清“评论导向”同“作家心声”之间的背离,首先,文本创作同作品接受之间,本就不具有必然一致的特性,更何况仅在文本创作阶段,其构思同创作之间也并非绝然一致。其次,“铁西三剑客”由“日常生活叙事”向“宏大叙事”合潮的“表象”之下,其“成长经验”“型构现场”“意义阐释”背后的“异托邦”型构效应无处不在。
至于“铁西三剑客”东北城市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异托邦”理论,由米歇尔·福柯在1966 年出版的《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中首次提出,其本质特征区别于“乌托邦”式的“非真实”存在,“异托邦”则强调主体通过凭借自身的“想象力”及其“经验”,对世界上的真实存在进行人为解构与建构。由此可见,“异托邦”型构的基本范式可理解为:以主体为型构中心,将作为“原材料”的“真实空间”,通过“主体化”的解构与结构机制,建构出“主体化”后的“镜像空间”。
也就是说,当下关于“铁西三剑客”东北城市文学书写这一文学现象,这“评论导向”同“作家心声”之间颇具悖论性的背离,并非“正—误”之分,而是由隐秘在“表象”之下的“多重现实”之间复杂关系使然。准确还原“铁西三剑客”的“异托邦”型构现场,亦即还原“多重现实”之间如何营构这一“文学事件”,其意义不言而喻。
一 “异托邦”视域下“铁西三剑客”之成长经验
“铁西三剑客”按照代际划分与地域划分,是一批成长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东北80 后作家。那么,其一“成长于20 世纪90 年代”与“东北”的限定性时空要素,建构起“铁西三剑客”以“感性”为主导的“少年成长体验”之有限视域,同特定时代﹑群体的立体化“真实空间”之间共同延展的特性。其二,年逾而立的“铁西三剑客”在当下进行文本型构时,则是以特定时空“域外”的亲历者身份,凭借其潜隐在“感性情感体验”之下的成年人“理性”追怀而完成。
显然,在不同历史时空下的“铁西三剑客”,其通过调动自身情感体验记忆与想象力,进入特定真实空间的“路径”是存在差别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存在异质性的“路径”,却也均在当下由“真实空间”上升为“镜像空间”的具体文本型构过程中实现合流。而问题在于,“铁西三剑客”相对统一的“异托邦”型构意志同评论界(文学接受界)之间存在背离。换句话说,存在评论界巧借“铁西三剑客”之“异托邦”型构,来消解“现有社会‘乌托邦’存在”之可能。故而,回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东北”的历史现场,厘清“真实空间”同“镜像空间”之间的复杂型构关系极为必要。
就“真实空间”而言,其一,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来看,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新中国历史上长期以“老工业基地”而振兴的“东北地区”,却因为大规模的工业衰退而走下神坛。刘中树在《关于开展东北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考》一文中,正式提出“东北现象”和“新东北现象”的概念。其中,“东北现象”通过详尽的数据表明,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东北出现了“工业生产衰退﹑企业大量停产半停产﹑大批工人下岗﹑技术人才流失﹑资源枯竭﹑矿区城市塌陷”[2]等所谓“东北现象”。而“新东北现象”则特别指代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曾经是全国粮仓的东北三省,近些年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出现了传统优势农产量积压﹑农民增收缓慢﹑农业经济效益下滑等较为尖锐的问题”[3]。在“东北现象”和“新东北现象”之下,“城市失业工人群体和收入菲薄的农民群体,并且累计了大量的社会问题”[4]。世纪之交,作为东北地区支柱性产业的“工业”与“农业”尽显颓势,大量的“工人下岗潮”“农民破产潮”将占据东北地区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群体,挤出往日安稳的物质生活轨道。在这样的转型背景之下,不仅涉及广泛的“社会现象”,更触及深刻的“社会心理现象”。
其二,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东北地区严峻的“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带来触及社会各方位转型危机的同时,“中国东北地区一方面城市化水平在全国比较高……无论是非农业人口比重还是城镇人口比重,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水平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速度在放慢”[5]。也就是说,这类看似存在悖论的社会“真实空间”,一方面,得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厚重“家底”,即使东北面临发展速度放缓﹑社会市场转型阵痛期等严峻局面,但地区整体现代化水平并不是“社会刻板印象”下所谓的“绝境”。另一方面,这类表征层面悖论化的“真实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文学层面上“失语”的窘境。此外,“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家战略与社会潮流,同样需要正视“社会前语境”。这也就决定了“铁西三剑客”城市文学书写之于“东北”社会“真实空间”的意义所在。
其三,从文学转型的时代“真实空间”来看,“铁西三剑客”作为一批“80 后作家”,其文学经验成长的“真实空间”主要在于新世纪之交。而20 世纪90年代以来,占据重要地位的传统“宏大叙事”,已成为“天鹅绝唱”般的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反宏大叙事”作为一股重要文学思潮则弥漫文坛。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笼罩下成长的一代,“铁西三剑客”成长时期所面对的文学主导面貌,是以“解构一切”为表征的文学思脉。可见,在此前提之下所呈现出的“后现代”城市文学创作,将既有的城市文学传统中“宏大叙事”的一面,很大程度上转为琐屑﹑庸常的城市生存体验书写,以感性化的“零度体验”解构常规意义上的意义阐释。而“解构”之后“结构”的缺席,使得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弥漫文坛的“后现代”话语,迅速走入“转喻”的危机。
在“异托邦”型构中,主体将“想象力”与“经验”熔铸至“真实空间”之中,便构建起“镜像空间”。值得注意的是,“镜像空间”是基于“真实空间”而建构起自身的存在基础,但是在社会层面的“泛化”过程中,也会有蜕变为“乌托邦”的可能性。或者,在“镜像空间”的型构过程中,出于“想象力”与“经验”的误解,使得原本“真实空间”消解,进而成为“乌托邦”叙事。其实,在上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真实空间”之中,均存在同“镜像世界”相对立的“乌托邦”存在,这也就导致当下消解“乌托邦”与建构“异托邦”之间的矛盾。
其一,就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弥漫文坛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言,确实构建起当下在“镜像空间”同“乌托邦”身份之间的“含混”定位。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兴起,一方面,尽管存在着“西学东渐”的影响,但是的确同20 世纪90 年代之后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从这一点来看,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速发展的反映,是特定转型时代的“真实空间”的反映。另一方面,就现代化发展程度而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于“现代主义”思潮之后,是对高度发达工业文明下的批判与反思。而20世纪90 年代的中国很明显没有达到这样的社会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后现代主义”思潮存在的社会“真实空间”又是“乌托邦”性质的。
对于“后现代”的暧昧性质,就“铁西三剑客”而言,其文本表征层面呈现出由“日常生活叙事”向“宏大叙事”合流的鲜明特质,本身就是对“后现代”叙事的消解。值得玩味的是,2018 年班宇在张悦然主编的《鲤·时间胶囊》发表的一篇文章,可以视作其个人,或“铁西三剑客”集体向“后现代”文学书写的“宣言书”。“同年某地下室,东北作家群体遭逢博尔赫斯,并将其击倒在地。原因不明”[6]。作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博尔赫斯被打倒,表明其显然是站在“后现代”思潮对立面的。而就既定地域文学而言,其“解构一切”的意义,只能使得在一定程度上本就“缺席”的东北特定文学更加支离破碎。
其二,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不同于“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下深刻的“社会心理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在全国范围内,以赵本山为表征的“乡土喜剧”风格甚至获得同“东北地域文化”的对等性。“赵本山的作品……凭借二人转拉场戏……成为21 世纪初的中国大众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东北人形象,同时反向构造了东北人自身理解现实人生的‘民间’符号秩序”[7]。这类弥漫性的“自动化”风格,一方面,使得“喜剧化”刻板印象之下,占据东北主要矛盾的“工人下岗潮”“农民破产潮”下的“异托邦”型构被遮蔽。另一方面,就赵本山为表征的“乡土喜剧”风格自身而言,其艺术本身仍是基于“东北”社会“真实空间”的“异托邦”型构。但是,在获得同“东北地域文化”对等性的“泛化”过程中,由于对于东北社会主要矛盾的遮蔽,则最终走向“乌托邦”一极。
总之,在“铁西三剑客”同转型时代“东北”的共生共存过程中,既奠定了其日后文本型构的宝贵“成长经验”,又因为社会层面的“缺席”与“乌托邦”式存在,使得“铁西三剑客”的“异托邦”型构在获得广泛关注度的同时,也产生了阐释与接受层面截然不同的走向。
二 “异托邦”视域下“铁西三剑客”之型构现场
“铁西三剑客”基于当下的历史时空,在依据“成长体验”进行文本型构之时,便既有“少年成长体验”视域内对“真实空间”进行追索与复现,又有基于当下成年人“体验”下“想象力”与“经验”的熔铸。而在由“真实空间”体验与“想象力”而拥入“既定回忆现场”的情感投射过程中,其文本现场呈现出由“日常生活叙事”而上升为“宏大叙事”的鲜明文本特质。
“铁西三剑客”作为一个“文学群落”的称谓,既显示了其文本型构层面“群落”的特质,又潜隐地暴露出社会层面对某一地域集体创作风景的期待心理。故而,深入“铁西三剑客”的“异托邦”文本型构现场,亟须厘清其在现实场域中形成的“异质性主体”(作家群体的创作活动﹑评论界的批判导向)对型构现场的“合力”作用。
那么,先行探究“铁西三剑客”作为一个“文学群落”,是如何遮蔽作为作家“个体”层面的创作特质?继而在文本型构现场中,形成由“日常生活叙事”而上升为“宏大叙事”的鲜明“共性”呢?
首先,作为“作家”身份而存在的“铁西三剑客”,其群落内部的“异质性”特征不容忽视。双雪涛的作品往往倾向于语言的冷峻,在凝练的叙事中型构出“理想主义”下的“倔强者”形象,譬如《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安德烈”,取材于其初中同学“小霍”的原型,爱好研究电磁铁并且达到近乎“理想主义”式的痴迷程度;班宇的作品倾向于意象的绚丽,其人物型构谱系中,勾勒出被遮蔽的“工人下岗潮”中“沉默的大多数”,譬如《冬泳》中群像式的“黑社会小弟”“足疗店老板”“出租车司机”等;郑执的小说叙事悬谜曲折,潜隐地传达出“下岗潮”工人后代,在孤单中冷峻成长的“心理”历程。
显然,“铁西三剑客”群落内部的“异质性”特征,深植于作家独特的“成长体验”视域。作家从各自的“成长体验”出发,从“日常生活叙事”的维度,分别营构出契合其自身“情感记忆”与“情感意志”的“记忆版图”。转而,从“群落”的角度考量,作家各自独特的情感叙事,又恰恰连接起关于“东北”既定时空的“宏大叙事”。也就是说,作为群落意义的“铁西三剑客”,恰好将其“域内”亲历者维度下“日常生活叙事”的真实性,通过“集体景观”的作用,转而获得“宏大叙事”的整体性力量。
其次,作家群体从“日常生活叙事”的“自发性”维度出发,可见其并无意于构筑“宏大叙事”的文学城堡。但是,就形成文本表达的“铁西三剑客”东北城市“异托邦”型构而言,其已在意义延展的过程中形成了“集体景观”的独特效应,并且契合了社会层面的某种期待心理。那么,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这类意义延展的过程中形成“集体景观”究竟是如何具体型构的呢?
其一,这类“集体景观”的形成,依赖于作家群落内部的“情感记忆版图”。也就是说,“铁西三剑客”以其个体化的情感版图,连缀起麦吉尔所谓“无所不包的叙述,具有主题性﹑目的性﹑连贯性和统一性”的“宏大叙事”蓝图。
从“铁西三剑客”文本型构中的“地理”元素来看,其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呈现出由“实体地理元素”向“地理要素结构”与“地理要素功能”迁移的趋向。具体来看,“铁西三剑客”作家群体以其独特的“成长经验”,拥入客观的“实体地理要素”。譬如,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中,将混杂在记忆深处的底层情感真相,熔铸到铁西区中山广场毛主席像之中;班宇则在《冬泳》中,将成长记忆深处的“血性”与“情义”,吸收到铁西区“工人村”“水渠”等“实体地理要素”之内;郑执则在《生吞》中,将个人之于“城市伤疤”的遐思与情感,呈现于“烂尾楼”“大坑”等地理实体之中。很显然,从其小说的篇幅与容量来看,“铁西三剑客”无意于,也无力于建构叙事层面“无所不包”的东北及其群体记忆。而这类“实体地理要素”的呈现,亦是作家“个人化情感话语”的衍化,是作家各自“情感记忆”的“日常叙事”,是对其既往生命体验的梳理与当下,或未来生命记忆的立证。
其实,正是在所谓“文学地理学”的维度之下,“铁西三剑客”将各自“情感记忆”的“日常叙事”,集体融会成有关“东北”的“宏大叙事”。譬如,黄平将“铁西三剑客”延伸为“新东北作家群”,其“共性”的地理范畴从“铁西区”延伸至“东北”,进而将“双雪涛﹑班宇﹑郑执—铁西区—沈阳—东北”的链条进一步延伸,接上了“阶级”[8],也正是在这样的型构过程中,“实体地理要素”获得由内容与意义层面,向“地理要素结构”与“地理要素功能”层面延伸的无限动力。
其二,这类“集体景观”的形成,依赖于作家群落内部的“情感体验心理”。诚然,“铁西三剑客”群体的“成长经验”基于“20 世纪90 年代”“东北”的“真实空间”,通过“少年成长体验”的有限视域进行持续“异托邦”型构。而这类“少年成长体验”视角的潜在影响在于,一方面使“铁西三剑客”在数年后得以占据“域内”特有的“成长体验”资源,获得文学型构与接受层面的先天优势。另一方面,这类“成长体验”资源在具体文本创作之后,从社会学意义上,将看似统一的“20 世纪90 年代”与“东北”的“真实空间”分裂化,继而,呈现出社会各界以“遮蔽或反遮蔽”为表征,无限化地向着“真实空间”靠拢。
具体来看,“铁西三剑客”一方面以“少年成长视域”下“域内”亲历者的形象定位,完成自身文学身份的建构。另一方面,就“社会阐释”层面的某种需要或意义而言,“子一代”的“域内”亲历者身份,恰达到了某种得天独厚的作用。也就是从所谓“社会心理学”的视域出发,其“子一代”视域出发型构的“日常叙事”经验,同叙写对象的某种“被遮蔽”的历史之间,呈现出“双向度”的建构关系。譬如,郑执曾在《面与乐园》的演讲中谈到,其“匿名作家首奖”作品《仙症》,将“魔幻”与“现实”的叙写笔触,对准“东北”及其土地上的“个人”与“群体”,其主人公“王战团”亦取材于作家的一位亲人。再比如其作品《生吞》,在秦理﹑王頔﹑冯雪娇等人物悲剧性成长谱系之下,从侧面切入“父一代”东北及其时代命运的“隐喻”式变迁之中。诚如郑执在“一席”演讲所言,在东北重金属后摇迷幻音乐氛围背后,“啤酒屋”式的“穷鬼乐园”内外,寄寓着大规模下岗潮之后大量“离婚破碎家庭”的“情感需求”,以及“啤酒屋”内外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有在“啤酒屋”外为生活所保留最后“尊严”的人,也有在“啤酒屋”内通过“综合豆”“扎啤”而寻求麻痹的人[9]。正是郑执等“铁西三剑客”作家,凭借其对“东北”及其命运变迁所达到的“内化生命领悟”之深度,才将“内省”层面的“集体景观”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
其三,这类“集体景观”的形成,依赖于作家群落内部的“情感生成基因”。“东北素以荒寒﹑冷硬著称,北方寒冷的气候﹑广袤的山地……以及北方人豪爽的性格……顽强的毅力,在这种场域下形成的文学自然有特定的印记和符号”,因此,东北地区“荒寒”的地理状貌﹑“血性”的群体特征﹑特殊的文学样态之间似乎呈现出“同构”的关系。从这个角度观照,其中既涉及“文学地理学”的间性关系,又涉及鲁枢元所谓的“精神生态学”的间性关系。
而值得深思的是,这类地理﹑群体﹑文学“同构”关系,同作家群落内部的“情感生成基因”之间如何生成?作家群落内部“情感生成基因”同“集体景观”之间又如何生成?
首先,东北地区“荒寒”的地理状貌﹑“血性”的群体特征,共同熔铸于“铁西三剑客”的独特文学样态之中。更近一步考量,在“铁西三剑客”具体的文本型构之下,又通过大量血性化的“动词”(打斗﹑械斗)﹑冷峻化的“名词”(刨锛﹑断臂)﹑阴冷化的形容词(血红雪白)等将“场景”“情节”等叙事要素构建起来,最终形成体现作家独特“成长经验”的话语表达。而这类色彩化的情感话语表达,亦潜隐于伦理情义之中。比如,班宇《冬泳》之中,“尽管‘我’和隋菲存在情感纠葛,但‘我’仍将隋菲的前夫打得满脸是血,血红雪白地倒在冬夜雪地。”在冷峭的血性叙事之中,却潜隐着“我”对于隋菲之情义,以及不顾体型差异悬殊,而敢于“动手”教训“隋菲前夫”之胆魄。
其次,在厘清地理﹑群体﹑文学“同构”关系之后,亟须明确其与作家群落内部的“情感生成基因”之间如何生成。如前所述,在“双向度”的型构现场之中,大量血性﹑冷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场景”“情节”的营构,均归属于大量“东北日常生活叙事”之用语。也就是说,具有高度语言学﹑民俗学价值。譬如,班宇《肃杀》之中“刨锛”这个概念,其所指意义丰富。既可指代“一种常用于暴力械斗的工具”,又可指代“上世纪90 年代中期,长春﹑吉林等大城市流行一种‘刨锛’的犯罪行为”。而这类“作为文学语言的东北话”,则充当了作家群落内部“情感生成基因”的载体之一。其实,就“日常生活情感叙事”层面而言,作为“东北”域内的成长经历者,有关“东北”的一切语言及其图景早已成为“铁西三剑客”的内化生命体验与话语表达,并无太大“预设”的意味。正如双雪涛所言“因为我就是一个东北人,在东北生活了30 年……所以天生就决定了我写东西大部分都与东北有关,这是一个无法选择的命运。我是一个被选择,被推倒一个素材充满东北意味的写作者的角色中来”[10]。
再次,刘广远在2014 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及,“而新时期以来,东北荒寒文化的迷遁和退隐,也是不可回避的事实”[11]。而2015 年以来“铁西三剑客”的文学热潮,或许在某种意义层面,是作为刘广远心目中“东北作家群”式“高峰的群体写作姿态”的回归。黄平发表于2020 年1 月的《“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也从侧面印证了上述设想的文学趋势。
但是无论如何,“铁西三剑客”将一切有关东北的“情感生成基因”,内化为个人“情感记忆”的“日常叙事”,并且形诸文本。而在彼此作品“意义延伸”与“文本互文”的过程中,最终形成“宏大叙事”式的“集体景观”。
三 “异托邦”视域下“铁西三剑客”之型构反思
深入“铁西三剑客”文本型构现场,其中形成的“异质性主体”(作家群体的创作活动﹑评论界的批判导向),对型构现场的“合力”作用不容忽视。上一章已经阐明,“铁西三剑客”基于当下历史时空,将内化的“东北成长经验”糅进“日常叙事”的笔触之中,其关于东北既定的“真实空间”型构之中,加入大量当下的“想象力”与“经验”。进而,在作品“意义延伸”与“文本互文”的“异托邦”型构过程中,实现了“宏大叙事”式的“集体景观”。但是,反观“评论界的批评导向”对“铁西三剑客”的评论话语本身,其“自我批判”的程度显然有所遮蔽。
以“评论界”对“铁西三剑客”城市文学的“批评导向”为具体研究视域,很显然,无论是刘广远在2014 年以新时期“东北荒寒文化”的衰退,而呼唤“东北作家群”式的“高峰式群体写作”,亦或黄平﹑李陀﹑王德威对“新东北作家群”的意义延展与价值肯定,还是张定浩对“铁西三剑客”的东北城市文学“祛魅”化表达,都整体显现当下“评论界”(社会),对具备表征性的东北地域文学群落之期待意图。
那么,首先应当厘清的是,在“评论界的批评导向”视域之下,“铁西三剑客”究竟是以何特质获得“新东北作家群”的意义延伸与价值延展呢?
其一,从刘广远提出的新时期以来“荒寒文化”的“迷遁和退隐”着手,其心目中的“理想国”,是以“东北作家群”为代表的“荒寒文化”下“高峰群体写作姿态”。而东北作家群独特的“审美力学”,带血的旷野﹑彪悍的民风和铁的人物,交融成一块和这块土地相默契的阳刚之美[12],最终将“东北作家群”的文学书写获得了与东北广袤的黑土﹑铁蹄下的不屈人民﹑茂草﹑高粱,搅成一团的“综合性荒寒审美力学”。也就是说,“东北作家群”的“荒寒文化”表征,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链条“生死存亡”之际所型构的。诚如鲁迅评价萧红《生死场》,“力透纸背”地描写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
较之危难之际“东北作家群”的“血性”呐喊,世纪之交以来,“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之下沉重的“物质生存”问题,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刘岩所谓的“自动化”喜剧色彩所遮蔽。恰如有的学者指出,当下的东北社会,在中华文明共同体内正处于集体荣誉感最低﹑生存境遇最窘迫的阶段。也就是说,以内化生命体验拥入既定被社会所遮蔽的东北“真实空间”,这是当下东北区域文学所“缺席”的基本要素。而“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下“物质生存层面”所面临的“荒寒文化”氛围,便在社会学层面“预设”出“新东北作家群”之“血性”呐喊模式。
其二,诚如第一章所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反宏大叙事”思潮之下,“解构一切”旗帜之下的“后现代主义”城市文学书写,其“物质”条件袭扰下的“人”陷入“转喻”的泥淖当中。譬如,邱华栋《平面人》中的“田畅”与“何铃”在物化北京的异化之下被迫逃离,然而逃离途中“乘坐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乘坐飞机﹑火车﹑轮船,这些交通工具都是从城市到城市,除非你从半途中下”[13]。张欣在《爱又如何》中,形形色色地勾勒出“爱宛”的物质生活,“金巴利开胃酒﹑苏格兰威士忌﹑沙律和牛扒,开着雪铁龙,用的护肤品是名牌兰金,家里茶几上的大理石面,凉润水滑”。后现代城市文学在解构城市本质的琐屑与流式的叙述策略中,以“城市物化现实中人的生存困境”为文本话语的聚焦点,其意义图景遂日渐趋同,无所不包的宏大叙事分散为物质城市的主体“异化”书写,利奥塔口中的启蒙解放叙事与思辨叙事,被作为“前话语霸权”而则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
故而,由“铁西三剑客”所开启的叙事模式,超越了“后现代”城市文学书写的窠臼。具体而言,其以“域内亲历者”身份,将内化“成长体验”转化为“日常叙事”层面之“真实”,继而,在延展层面跃升为“宏大叙事”之“深度”。物,避免了类似于“后现代”笔下人物“转喻”的危机。比如,在班宇《工人村》中,“前夫”余正国身上的宝贵精神,矗立着小人物“向下超越”的精神“丰碑”。“我说,家里出事儿了,我爸病了,可能是血栓,挺重的,正往医院去呢。大头说,谁啊,你爸不是早没了吗?我说,不是亲爸,张婷婷他爸。大头说,你有病啊,你不离婚了吗,还啥事儿都管呢。我说,买卖不成仁义在。大头说,鸡毛仁义。我说,总有亲情在啊”[14]。在这段稍显粗陋的言语之中,身为“出租车司机”的余正国,尽管在时代的夹缝中寻求物质生存,但是同妻子“张婷婷”离婚后,仍恭恭敬敬照顾岳父岳母。生活与情感的重压之下,“余正国”们并没有走向后现代城市描写下“人存在意义究竟如何”的泥淖之中,而是坚持以自身的原则与温度砥砺着不屈的魂灵。
“铁西三剑客”笔下的东北城市文学书写,既契合了“东北现象”“新东北现象”下“物质生存层面”的文学书写需要,又型构出“评论界的批评导向”下超越“后现代”城市文学书写的全新品质。进而,就“评论界的批评导向”而言,既具备“新东北作家群”型构的命题趋向,又寻到“新东北作家群”型构的现实基点。以“铁西三剑客”之“日常情感叙事”为起点的东北城市“异托邦”书写,在文本型构前后均置身于社会层面的多重现实空间之中,以至于衍生出魅惑化的阐释视域。
从贺桂梅在《“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 年代的发生》一文中所提出的“自我批判”出发,可发现当下对于“铁西三剑客”东北城市文学“异托邦”型构之考察,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对文本型构的“技术层面”“意义层面”之考量,而对其多重话语之间的“自我批判”则明显不足。
其一,从多重话语现场本身来看,在“铁西三剑客”凭借内化“成长体验”,以“日常叙事”之视域,型构“宏大叙事”层面文本“异托邦”现场之时,“评论界的批评导向”也在凭借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达到对“既定真实空间”异质性的“异托邦”型构。在这样的交叉现场之下,无论是以黄平为代表的建构“新东北作家群”的努力,还是以张定浩为代表的对“铁西三剑客”从“技术”与“意义”层面是否撑得起“东北”之重担的疑问,还是“铁西三剑客”自身对“东北城市文学”字眼的逃离,都从侧面显示出张定浩在《“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文末所提及的“更有价值的批评,是分析这些小说中的这些效果是如何产生的”之重要性。也就是说,从发生学的角度着眼,只有深入分析“异质性主体”(作家群体的创作活动﹑评论界的批判导向)之间的多重话语现场,才能真正厘清“作家群体的创作活动”之下,其文本型构本身所具备的“新东北作家群”的趋向,以及在“评论界的批判导向”之下的话语“预设”与“过度阐释”之嫌疑。
其二,在看似明晰的“型构状貌”归类之下,其实也仅仅是“占据主导”的话语侧面而已。在“铁西三剑客”文本型构过程中,鲜明地呈现出由“日常生活叙事”向“宏大叙事”建构的趋向。但是,这并不能取消其他形式的存在,正如双雪涛所讲,“对我来说,东北一方面是我内在的部分;另一方面现在它也是我的一个他者,我是努力地保持距离看待它。”[16]也就是说,在鲜明的文本型构趋向之下,并不能掩盖作家“多趋向”的创作空间。就“宏大叙事”而言,“铁西三剑客”未必没有“预设”层面建构的雄心,或许碍于“日常叙事”经验的局囿与“宏大叙事”机缘的缺陷,致使其在多重话语型构的空间之内,旗帜明晰地显现出一种特定的代表面貌而已。这也就将多重话语空间“异托邦”型构的“有—无”,转移到“异托邦”型构的“显—隐”层面上来。
厘清“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叙事”维度之下,“铁西三剑客”东北城市文学书写类似于“异托邦”型构的复杂本质,便更能理解当下为何“评论导向”同“作家心声”之间,存在颇具迷惑性的背离。而正视有关“铁西三剑客”的多重话语空间之存在,便更能以“自我批判”的深度,还原颇具迷惑性的“异托邦”型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