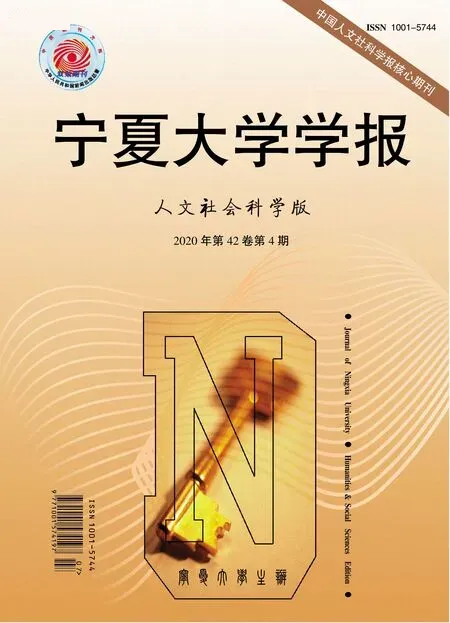论“马嵬兵谏”
——“安史之乱”背景下禁军将士的救国之举
白述礼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 安史之乱 马嵬兵谏
唐朝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一月九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统率三镇军队及境内同罗﹑奚﹑契丹﹑室韦共15 万人,号称二十万,“以诛国忠为名”[1]于范阳(今河北涿州)起兵反唐,发动了一场唐朝历史由盛转衰长达八年(755-763 年)的灾难性战争。叛乱总指挥是安禄山和史思明,史称“安史之乱”。叛军南下,势如破竹,河北﹑河东﹑河南许多城池,相继沦陷。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二月十二日,叛军攻占洛阳,安禄山称帝。
安史之乱爆发半年多后,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初九日,叛军攻陷京师东大门潼关,逼近长安。唐玄宗拒高适“募死士抗贼”主张﹑采纳奸相杨国忠弃城逃跑的“幸蜀之策”[2]。六月十二日,玄宗就悄悄地为逃跑紧锣密鼓做准备: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置顿使;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将军边令诚掌管宫闱钥匙;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禁军,给他们多发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这些,外人一概皆不知。
六月十三日清晨,唐玄宗放弃作为大唐皇帝领导军民征讨叛军的职责,率皇太子﹑贵妃姊妹﹑皇子﹑嫔妃﹑公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高力士﹑宫人等,在禁军将士护卫下,出长安延秋门西行,开始弃城逃跑之旅。妃子公主皇孙凡在外者,皆丢弃不顾,一路上十分狼狈。当天中午,到达咸阳望贤宫小歇。在咸阳望贤宫,到晌午都没有吃上午饭,唐玄宗皇帝本人都饥饿难忍,竟然狼狈到要饭吃,“如何得饭?”好心的百姓献食。咸阳老父郭从瑾,善意的教训唐玄宗,后期不理朝政,昏庸招乱。玄宗承认,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后悔来不及了。六月十三日半夜,来到金城(今陕西兴平县)。咸阳﹑金城的官员﹑驿卒,全部跑光,无人接待,玄宗一行人不能及时得到饭食,吃不饱﹑睡不好。金城驿站无灯,黑灯瞎火,靠智藏寺僧人进粟。人困马乏,一行人顾不得分贵贱,“枕藉而寝”。王思礼自潼关赶来,玄宗方知哥舒翰战败被擒,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赴镇收散卒,东讨叛贼。随玄宗西逃的禁军将士,家属在长安,不知死活,思家亲人,饥饿疲困,狼狈不堪,怨声载道。
就这样,在“安史之乱”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在长安以西一百多里的马嵬驿,突然爆发了护卫唐玄宗一行出逃“幸蜀”的陈玄礼等禁军将士,为救国而除叛乱“祸根”“尽诛杨氏”的特大历史事件。《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唐史文献,记载了马嵬事件的经过:
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十四日,即“丙申”日,午后,唐玄宗一行逃跑幸蜀西行,到达金城的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禁军“将士饥疲,皆愤怒”,禁军统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惧乱”,劝谏唐玄宗,奏曰:“逆胡指阙,以诛国忠为名,然中外群情,不无嫌怨。今国步艰阻,乘舆震荡,陛下宜徇群情,为社稷大计,国忠之徒,可置之于法。”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没有公开表态。禁军将士追杀杨国忠,“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祸国殃民的“祸根”杨国忠,被禁军将士诛杀,“屠割支体,以枪揭其首于驿门外”。唐玄宗“慰劳军士,令收队,军士不应。”将士们的愤怒仍未平息,唐玄宗让高力士问怎么回事?将士们高喊“贼本尚在”!陈玄礼再次进谏:“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爱正法。”指玄宗宠妃“贼本”杨贵妃。玄宗犹豫不决,韦见素之子御史大夫京兆司录韦谔,叩头流血劝谏:“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愿陛下速决!”玄宗仍不忍心杀杨贵妃。最后,“千古贤宦第一人”玄宗最忠实的老宦官高力士进言:“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高力士“将士安,则陛下安”这句话,最能打动唐玄宗,促使他“审思”之后,为保命,决心割爱舍弃杨贵妃,在禁军逼迫下,玄宗“命力士引贵妃佛堂,缢杀之。”陈玄礼等禁军将士,除掉二杨两个安乱“祸根”,同时,杀杨国忠子户部侍郎杨暄﹑杨国忠亲信御史大夫魏方进等人,众怒才得以平息。“尽诛杨氏”之后,陈玄礼等卸甲请罪,玄宗“慰劳之”,于是,禁军“始整部伍为行计”。杨国忠妻裴柔﹑幼子杨晞﹑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逃至陈仓县,被“县令薛景仙帅吏追捕,诛之。”
这就是唐朝历史上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十四日午后,发生在马嵬驿的震惊朝野的历史性大事件。马嵬驿,唐人又称之为马嵬﹑马嵬坡﹑马嵬山﹑马嵬亭,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以西23 里,位于渭北,南望渭水,坡前有西安至宝鸡公路穿过。马嵬驿小驿村镇,是全国最出名的古驿站之一,自古有通向西部的官道。景龙四年(710 年),唐中宗御驾陪金城公主出长安经金城县,“送至马嵬,群臣赋诗以饯”。马嵬历代设有驿站,是古丝绸之路第一个驿站,故名“马嵬驿”,今为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马嵬事件后,玄宗分兵,唐玄宗,继续躲避平叛责任,远逃成都。玄宗分兵太子,宣旨传位,太子李亨,北上朔方,遵玄宗“马嵬之命”,即位于灵武,史称唐肃宗。(唐肃宗即位的灵武,指灵武郡,即古灵州。古灵州城的城址,在今宁夏吴忠市。唐代灵州,辖今宁夏吴忠﹑灵武地区为核心的宁夏平原全部及陕甘蒙部分地区。)[3]“肃宗受禅灵武”“顺天应人”,扛起平叛大旗,收复两京,谋大唐兴复。唐肃宗在位七年,是艰苦平叛的七年。诗圣杜甫诗赞肃宗为兴复唐朝的“中兴主”。
关于马嵬事件,唐代同时代著名的诗圣杜甫等人,当时,即提出正面评价马嵬事件的历史作用﹑对陈玄礼等禁军将士给予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的观点。稍后,又有一些文人则流行另类说法,说马嵬事件是绝代佳人杨贵妃与风流天子唐玄宗所谓李杨爱情的悲剧。近代不少学者认同李杨悲剧﹑绝代佳人杨贵妃死于非命等说法。当代学者一般称为“马嵬事变”“马嵬之变”,不够确切;而广泛流行的另类说法,说马嵬事件是“哗变”“兵变”“政变”,有说陈玄礼发动政变,也有说高力士指挥陈玄礼发动政变,还有说是唐玄宗授意除二杨的自导自演,而较为流行的说法则是太子李亨是事件“主谋”“太子李亨策划政变”,其实,皆为学者的推测,均无确切依据。
我认为,唐朝中期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十四日的马嵬事件,作为唐朝安史之乱背景下的重大历史事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为首的禁军将士们,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为救国救民,“临之以兵”,以武力威逼唐玄宗“惧而从之”,铲除了安史之乱的“祸根”二杨,激发了全国军民平定安史之乱的决心和信心。马嵬事件的性质是禁军的兵谏,因此,马嵬事件宜称为“马嵬兵谏”。安史之乱特定历史背景下突然发生的“马嵬兵谏”,是扭转唐朝局势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重大历史事件,是扭转唐朝安史之乱战局的转折点。“马嵬兵谏”是安史之乱特定历史背景下使大唐“中兴”“国犹活”的救国正义之举。陈玄礼等禁军拯救大唐免遭灭亡的“马嵬兵谏”,让唐朝历史延续一百多年的历史作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陈玄礼将军本人及所统禁军将士的救国之举,应该予以褒扬﹑称赞,让他们名垂史册。
“马嵬事件”是“兵谏”,不是“哗变”,不是“兵变”,更不是“政变”。唐史有关马嵬事件的史料中,人们找不到足以证明有人发动政变的证据,特别是,找不到足以证明太子李亨策划“政变”的证据。
二 何谓哗变 军队叛变
先说“哗变”。有的说马嵬事件是禁军的“哗变”。《大河报》提出:“唐天宝十五年六月,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为避祸乱逃往四川,逃亡途中在马嵬驿做短暂停留,不料却发生了禁军哗变”[4]。《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一书指出:“潼关失守,玄宗被迫逃离长安,到成都避难。御驾途径马嵬,杨国忠被哗变的兵士所杀,玄宗被迫令贵妃自缢”[5]。
什么是“哗变”呢?《辞海》“哗”字词条下有“哗变”词条:“哗变指军队突然叛变。如:敌军大部队哗变”[6]。
查马嵬事件的史料,陈玄礼将军统帅的禁军是唐玄宗的护卫军,禁军突然叛变了唐玄宗吗?没有叛变!陈玄礼为首的禁军誓死效忠唐玄宗,事后,唐玄宗也并未怪罪陈玄礼等禁军,陈玄礼率禁军,继续护送唐玄宗安全到达成都。太子李亨叛变了唐玄宗吗?更没有叛变!“太子仁孝”“百姓遮路乞留皇太子”,太子还不答应,还说“至尊远冒险阻,吾岂忍朝夕离左右”,要孝敬父皇随去成都。因此,马嵬事件,不宜称为“哗变”。
三 何谓兵变 武力夺权
再说“兵变”,有学者说马嵬事件是“兵变”。《唐肃宗皇帝列传》一书指出:“马嵬驿兵变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的行动”[7]。《唐肃宗评传》一书指出:“六月十四日,逃亡队伍到达马嵬驿”,“禁军将士因饥疲劳顿,已有不逊怨言”。“队伍的骚动给暗中操纵与策划兵变的太子李亨提供了绝好时机”[8]。
什么是“兵变”呢?《新五代史·王宴球传》记载有“明宗兵变”(“邺都兵变”):
明宗兵变,自邺而南,人招晏球,晏球从至洛阳,拜归德军节度使[9]。
《新五代史·王宴球传》记载提到的“明宗兵变”,是五代后唐同光四年(926 年)四月,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李嗣源,出讨邺都(今属河北省)赵在礼兵变,赵在礼迎李嗣源入邺都,合兵回师取大梁(今河南开封)。唐庄宗李存瑁在兵变中被杀,李嗣源入洛阳称帝,为后唐第二位皇帝唐明宗,史称“邺都兵变”。可见“兵变”是军队领导人以武力的夺权行动。
马嵬事件,随玄宗幸蜀的“六军不发”,诛杀二杨。而“明宗兵变”,是李嗣源兵变,夺权﹑称帝。禁军首领陈玄礼将军发动“马嵬兵谏”,武力夺权了没有?没有夺权!陈玄礼本人就是禁军统帅龙武大将军,有指挥禁军的大权,不必要夺权,他忠于玄宗,也更没有称帝。因此,马嵬事件自然也不宜称为“兵变”。
四 何谓政变 夺取政权
再看“政变”。人们不难发现,不少人说马嵬事件是“政变”。《历史罪》一书指出:“旧史记载是为尊者讳,这并非历史真相”。马嵬事件的“真实的情况是,这次政变蓄谋已久”[10]。《唐肃宗评传》一书也指出:“太子预谋策划政变”[11]。
什么是“政变”呢?《辞海》“政变”词条指出:“政变通常指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通过秘密策划,迅速采取军士或政治行动,夺取国家政权。如获成功即导致突然的权力转移﹑政府更迭,以致政体的改变。往往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其情况和性质各不相同,有的是拓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有的是进步势力为革新政治作斗争,有的是反动势力复辟,有的是帝国主义通过代理人,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其侵略政策”[12]。
考唐朝历史,开国不久,就发生了政变“玄武门之变”,这是一场由并非太子的唐高祖第二子秦王李世民策划的真正的政变。李世民通过与秦王府亲信秘密策划,率领亲信长孙无忌﹑尉迟恭等亲信将领二十多人,各自带领数千人亲兵,在玄武门设伏,杀死亲哥哥当朝太子﹑唐朝储君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元吉,发动政变成功后,秦王李世民夺得政权,唐高祖退位,为太上皇。李世民先为太子,后即位为大唐第二代皇帝,即唐太宗,这才是“政变”。
同唐太宗类似,原本也不是太子的李隆基,唐高宗第三子,是亲王,先封楚王,后封临淄王,他也发动“唐隆政变”,亲率万骑果毅(禁军)将领葛福顺﹑陈玄礼等禁军杀死韦后集团等多人。政变后,李隆基也先为太子,再夺取政权,登上大唐皇帝宝座,成为历史上的唐玄宗。
有关马嵬事件,史书记载,陈玄礼等禁军,诛杀杨国忠,逼唐玄宗接受禁军劝谏,赐死杨贵妃。事件结果,陈玄礼等禁军夺取政权登基当皇帝了没有?没有,大唐皇帝还是唐玄宗,陈玄礼率禁军继续誓死效忠皇帝。太子李亨发动政变﹑夺权没有?没有,太子李亨没有策划政变,没有夺权,而且还准备跟随唐玄宗幸蜀,孝敬父皇左右。因百姓请留太子,玄宗分兵宣旨传位,命太子留下,北上主持平叛。因此,我认为,马嵬事件,更不宜称为“政变”。
五 武力劝谏 谓之兵谏
马嵬事件,既不是“哗变”,也不是“兵变”,更不是“政变”,应该是“兵谏”。“马嵬兵谏”类似于古代春秋时期的“鬻拳兵谏”,五代十国时期南吴的“颢温兵谏”和近代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兵谏”。
那么,什么是“兵谏”呢?《辞海》载有“兵谏”词条,“《左传·庄公十九年》载:‘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后称用武力胁迫君主接受劝谏为‘兵谏’。范宁《春秋谷梁传序》:《左氏》以鬻拳兵谏为爱君”[13]。
《辞海》“兵谏”条指出“用武力胁迫君主接受劝谏为‘兵谏’”。东晋范宁撰《春秋谷梁传序》记载说明,春秋时期史官左丘明著《左传》记载楚官鬻拳,出于“爱君”,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春秋时期的“强谏楚子”“用武力胁迫君主接受劝谏”“兵谏”——“鬻拳兵谏”。《资治通鉴》记载了五代十国一次“兵谏”——“颢温兵谏”:
后梁太祖开平元年(丁卯﹑907 年),春正月,丙戌,渥(杨渥)晨视事,颢(张颢)﹑温(徐温)帅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尔果欲杀我邪?’对曰:‘非敢然也,欲诛王左右乱政者耳!’因数渥亲信十人之罪,曳下,以铁檛击杀之。谓之‘兵谏’。[14]
南吴烈宗杨渥“性猜忌,不能御下”,“渥居丧,昼夜瀚银作乐”,左右牙指挥使张颢﹑徐温率牙兵诛杀杨渥的“亲信”,司马光提出,张颢徐温以兵诛国君身边的“乱政者”,“谓之‘兵谏’”。
综上可知,‘兵谏’就是“临之以兵,惧而从之”,以武力“强谏”,逼迫昏庸的当权者,接受劝谏。“马嵬兵谏”就是陈玄礼等禁军将士以武力威逼唐玄宗接受“强谏”,“为社稷大计”,诛“乱政者”造成安史之乱的“祸根”二杨,以便动员军民,抗击叛军,是禁军将士为重振河山的一次成功的兵谏。“马嵬兵谏”以陈玄礼等禁军将士既挽救了大唐免于灭亡,也保护了唐玄宗的人身安全。
“西安事变”也是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武装发动,抓蒋介石,逼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义的“西安兵谏”。军旅作家杨闻宇著有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近看西安兵谏》一书,书名就是“西安兵谏”,可供读者参阅[15]。
六 正确评论 马嵬兵谏
“马嵬兵谏”,唐史文献有详细如实的记载,事件本身经过其实很简单,事件发生的时间也不长,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十四日中午过后,算一算时间,顶多几个时辰的事件。古今许多文人学士,专家﹑学者发表论著﹑诗文﹑论文以及各种文章,正确评价“马嵬兵谏”,是“安史之乱”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禁军将士的救国之举,肯定“马嵬兵谏”的历史作用。
1.杜甫诗赞 马嵬兵谏
唐朝同时代诗人首先站出来诗赞“马嵬兵谏”,对“马嵬兵谏”的历史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和评价者,是亲历安史之乱的著名诗圣杜甫。爱国诗人杜甫(712-770 年),河南府巩县(今河南省巩义市)人。“安史之乱”灾难的亲历者杜甫,对安史之乱,深恶痛绝,他本人曾与百姓一起,躲避战乱,辗转多地“逃难”,流离颠沛,“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曾经“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杜甫的诗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真实地反映唐朝历史,是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被尊称为“诗圣”,其诗被称为“史诗”,并与诗仙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对马嵬兵谏给予肯定的正面评价。《新唐书·杜甫传》记载: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今陕西富县)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757 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右拾遗。[16]
天宝十五载(756 年)七月十二日,马嵬分兵后近一个月后,“肃宗受禅灵武”(唐陈鸿撰《长恨歌传》),太子李亨灵武受禅即位。“会禄山乱,天子(玄宗)入蜀,甫避走三川。肃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行在”指唐肃宗即位的灵武,是灵武郡的简称,即古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境内。杜甫听说唐玄宗传位,太子李亨即位,“窃闻天子己传位”(杜甫《哀王孙》),立即从避难的鄜州(今陕西富县)住地羌村,只身奔赴灵武,急切地盼望觐见并当面表态拥戴唐肃宗。不幸,途中被叛军所俘,关在长安。“马嵬兵谏”之后仅半年多,“至德二载(757 年)甫自金光门出,间道归风翔”,杜甫再次“自贼中”,从叛军占领的长安金光门“脱身”,“窜归”唐肃宗下一个行在凤翔(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17],终于“麻鞋见天子”,见到大唐新皇帝。唐肃宗很高兴,授杜甫左拾遗。
至德二年(757 年)四月,杜甫在凤翔,朝拜新即位的唐肃宗后,作《述怀一首(此已下自贼中窜归凤翔作)》诗,自述“脱身得西走”,“自贼中窜归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称赞天子让“朝廷愍生还”,大唐天子唐肃宗让朝廷从祸乱中生还。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
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
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
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18]
左拾遗是供奉皇帝﹑谏净时政得失﹑推荐贤良的谏官。八月,杜甫自行在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出发,北征赴鄜州(今陕西富县),探家后,杜甫在长篇叙事诗《北征》中,歌颂唐肃宗是唐朝的“中兴主”,赞颂陈玄礼是唐朝的“忠烈”,充分肯定禁军将士发动“马嵬兵谏”,诛杀“奸臣”杨国忠及其“同恶”杨贵妃等,挽救了唐朝得以“国犹活”。像古人诛杀褒姒和妲己,灵武即位的唐肃宗像周宣王﹑汉光武帝,使周朝﹑汉朝得以“再兴”,唐肃宗就是“中兴主”。《北征》诗写道:
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
……
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
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
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19]
“桓桓陈将军”,指威武的左龙武大将军唐玄宗的禁军统帅陈玄礼,杜甫肯定“马嵬兵谏”的历史作用,赞扬威武的陈玄礼大将军等禁军将士们,是保护国家的“忠烈”之士。如果不是马嵬驿陈玄礼为首的禁军兵士发动兵谏,唐朝已经灭亡,百姓已经被叛军统治。正是因为陈将军率领禁军军将士们发动马嵬兵谏,诛杀“安史之乱”祸首二杨,清除安禄山反叛借口,“中兴主”唐肃宗领导全国军民奋起平叛,让大唐江山“国犹活”,百姓得益。杜甫对马嵬兵谏正面肯定的评价,高度赞扬“马嵬兵谏”后,玄宗分兵,太子李亨,北上朔方,灵武即位,即唐肃宗,主持朝政,扛起平叛重任,是扭转唐朝国运的“中兴主”,应该是对唐肃宗执政权威性的评价。诗中用“君”和“臣”,是因为《旧唐书·杜甫传》记载:“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20]。唐肃宗当年为皇太子,因此,杜甫认为唐肃宗李亨与杜甫本人,早就是君臣关系。
2.高适平乱 诗赞马嵬
诗圣杜甫与著名诗人高适,是同时代感情颇深的亲密好友,两位著名唐朝诗人,都是马嵬事件发生的同时代人,都有诗赞“马嵬兵谏”,同时代人论同时代事件,他们对马嵬事件的评价应该最为可信。
高适(704—765 年),沧州渤海县(今河北省景县)人。46 岁才任命为最低级的封丘县尉的小官。后赴凉州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任掌书记。高适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安史之乱起,拜左拾遗,转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后,护送玄宗幸蜀。升任谏议大夫。至德元载(756 年)十一月,永王李璘谋反,十二月,肃宗任命高适为淮南节度使,讨永王李璘。后参与讨安史叛军,曾救睢阳之围。为平定动乱作出重大贡献,深受朝廷重视,曾任任剑南节度使。广德二年(764 年),由刑部侍郎升任散骑常侍,人称“高常侍”。以功封“渤海县侯”,高适成为唐朝历史上唯一以军功封侯的诗人。“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21]。唐代宗永泰元年(765 年),六十二岁。正月,高适卒,赠礼部尚书。
高适与杜甫交往友情珍贵,杜甫住成都期间,出任蜀中刺史﹑剑南节度使的高适帮助杜甫在涴花溪修建草堂——杜甫草堂。当杜甫生活遇到困难,高适又慷慨解囊,给予资助。杜甫答谢高适诗“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高适给好朋友故人杜甫送诗《人日寄杜二拾遗》,这是高适最动人的诗篇:“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十年后,高适已病故,杜甫重读该诗,仍然“泪洒行间,读终篇末。”(杜甫《追筹高蜀州人日寄并序》)
高适从安史之乱开始,就站在反击安史叛军抗战的最前线。潼关失守,大唐朝廷朝官百余人,唯有低级文官监察御史诗人高适一人,挺身而出,力主“募死士抗贼”。《新唐书·高适传》记载:
翰败,帝问群臣策安出,适请竭禁藏募死士抗贼,未为。不省。[22]
《册府元龟》记载:
国忠于朝堂命朝官报潼关之败,访以救援安危之策。刑部尚书张均﹑御史大夫张倚已下百余人,唯唯无敢言者,唯监察御史高适请即日招募城中敢死之士及朝官个率家童子弟,出军防遏。国忠曰“兵已入关,事不及矣。”[23]
安史叛军进逼潼关,哥舒翰战败,潼关沦陷,唐玄宗征询对应之策,朝官“百余人,唯唯无敢言者”,唯独高适一人提出“募死士抗贼”。遗憾的是,唐玄宗﹑宰相杨国忠,没有接受高适的“死士抗贼”主张。肃宗上元元年(760 年),高适出任蜀中刺史住彭州,赋有470 字的五言长诗《酬裴员外以诗代书》,特别赞颂“马嵬兵谏”:
乙未将星变,贼臣候天灾。
胡骑犯龙山,乘舆经马嵬。
千官无倚著,万姓徒悲哀。
诛吕鬼神动,安刘天地开。[24]
诗中“乙未将星变,贼臣候天灾”的“乙未”,指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三日,玄宗避安乱自长安出逃的日期。“诛吕鬼神动”,说的是公元前180 年,西汉临朝称制的吕雉,刚刚薨世,刘襄﹑刘章﹑周勃,入宫发动政变,斩杀吕产﹑吕禄,结束了吕雉统治,拥立汉文帝称帝,汉朝开始“文景之治”时代。“安刘天地开”,说的是,汉初唐高祖时“商山四皓”辅助太子刘盈(即汉惠帝)安定刘氏江山的故事。高适用刘襄﹑刘章﹑周勃以及“商山四皓”,比喻陈玄礼将军等都是功臣。用“诛吕”诛杀吕氏集团,比喻陈玄礼诛灭奸相杨国忠等杨氏集团。高适的诗,赞颂陈玄礼率领禁军发动的“马嵬兵谏”,是“动神功”“开天地”的救国之举。
3.专家肯定 马嵬兵谏
著名老一辈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著《中国通史简编》一书,充分肯定“马嵬兵谏”的历史作用,指出:“唐玄宗逃出西京,到马嵬驿(在陕西兴平县西),随行兵士杀杨国忠,又迫唐玄宗杀杨贵妃。两条祸根拔去了,算是平息众怒,这个骄侈已极,酿成祸乱的唐玄宗才得到兵士的护送,走到成都去安身”。范老提出,禁军兵士在马嵬驿除去二杨是“拔去了”“两条祸根”,明确肯定“马嵬兵谏”是禁军将士“临之以兵”劝谏“骄侈已极”的唐玄宗,为国为民除害的救国正义之举。另一位著名百岁唐史专家﹑吉林大学历史系乌廷玉教授(1919 年生)著《唐玄宗皇帝传》《隋唐史话》,同样肯定陈玄礼等禁军“马嵬兵谏”的历史作用,乌老指出,“六月十四日,大唐皇帝銮驾到达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随从护驾的禁军将士”“饥疲已极,激起了强烈不满情绪”,“大将军陈玄礼带头发难,迅速得到禁军的支持,一场反对奸相杨国忠的斗争从此开始”。“随行将士杀了奸相杨国忠,又胁迫唐玄宗杀了杨贵妃。众怒平息,然后,护送唐玄宗到达成都”[25]。
2020 年春夏,防疫宅家,我与专家网论唐史。讨论中,著名唐史专家学者们,认同“马嵬事件”称为“马嵬兵谏”的观点,肯定“马嵬兵谏”的历史作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吴宗国教授:“你说的是对的,马嵬事件的性质,可以说就是一次‘兵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教授:“是这样的!马嵬事件应该就是‘马嵬兵谏’。您的认识很准确。”
中国唐史学会会长﹑陕师大杜文玉教授:“关于马嵬事件是‘兵谏’的说法,您说的有道理。我赞成您的观点,‘马嵬兵谏’是符合历史实际情况的。唐肃宗灵武即位,利国利民,对平定安史之乱也是有利的。因为唐玄宗已经跑到成都去了,等于他放弃了平定叛乱的领导权。唐肃宗灵武即位,可以统一来领导全国平叛力量,对于平定安史之乱﹑维护国家统一是有好处的。有人说太子李亨是马嵬事件最大得益者,因而就说太子李亨发动政变,缺乏确凿的史料证据,只能算是人们的推测。”
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您这个把马嵬事件定性‘兵谏’的思路,非常有趣,挺好!可以多方面进行思考﹑研讨,我表示认同。不能说李亨发动政变,政变是要夺权的﹑夺皇权的,李亨在马嵬夺权了吗?没有。李亨就是太子,是储君,就是要继承皇位的,太子李亨没有必要夺权。”
中国军事科学院大校邱剑敏研究员:马嵬驿的“这个历史事件我没有做特别的研究,但是就个人所看过的史料来说,我同意您‘兵谏’的观点,‘政变’‘兵变’说,都不太妥当。马嵬事件应该看作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救国之举。”“您提出‘兵谏’的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说明这个观点揭示了事变的本质,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任士英教授:“白教授您好:谢谢您的信任。您的大作(《论“马嵬兵谏”》)刚刚收到了,此前您来电来信,对我很多鼓励。谢谢您。宁夏大学历史系的刘志虎老师,是我研究生时候的同班同学。我不是北大的学生,北大吴宗国先生却是我的老师,您与他同门,也就是我的老师。您寿迈年高,笔耕不辍,令人钦佩。”“感谢您提供了很多资讯,包括宁夏灵武本地的一些情况。大作中提到很多学界朋友,我都是熟悉的。您对马嵬之变称为‘兵谏’,并当做‘安史之乱’背景下的救国之举,有自己的认识与评价,很有意义。”任士英教授肯定禁军的积极作用,指出马嵬事件后,太子主持平叛,“给叛军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增添了当地百姓守土杀敌的信心。”
《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蒙曼教授:“白老师,我同意您(“兵谏”)的说法。马嵬之变确实是在安史之乱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拯救了唐朝,重建了信心,也竖起了抵抗的旗帜。”
陕西教育学院穆渭生教授:“白老师:对,应该用‘马嵬兵谏’更准确。”
《陕西博物馆论丛》副主编张维慎研究馆员:“我认同:把马嵬事变件称为‘马嵬兵谏’”。
北方民族大学张多勇教授:“我赞成把马嵬事变件称为‘马嵬兵谏’,这个观点是比较可靠的。说太子政变,太不厚道。”
上海师范大学张安富教授:“白先生,我昨晚拜读了您的大作,感觉‘马嵬兵谏’这个提法很新颖,也很贴切。用“马嵬事变”有歧义,‘马嵬兵谏’比较客观,符合历史事件的性质。您的观点,后学受益了。”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马新教授:“白先生,您一说,我就明白了。我认同您把马嵬事件定为‘马嵬兵谏’的观点。”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刘玉峰教授:“关于马巍事变,学界多认为是兵变或政变,其主谋又有太子李亨﹑宦官高力士﹑禁军将领陈玄礼之说,然多推测,难以坐实。白述礼先生不同意以上观点,认为是武力进谏的‘兵谏’。从事变后禁军继续护卫玄宗逃难入蜀,以及白先生征引的杜甫和高适的诗作等,可证“兵谏”性质的认识是更为客观平实的。”
全军军事志首席专家﹑宁夏军区原副参谋长孙生玉:“应当对马嵬事件给予公正评价,确实是一次‘兵谏’。安史之乱阻断了大唐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命脉,“马嵬兵谏”延缓了大唐的命运,是大唐中兴的一个关节点。”
宁夏吴忠市地方志办主任胡建东研究馆员:“我支持您把马嵬事件称为‘马嵬兵谏’的观点。‘兵谏’直接指出了当时的史实,更易理解,定性﹑定位更准。”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院长杜建录教授:“白老师,马嵬驿这件事,以往学者并没有仔细琢磨,应该不是兵变﹑政变!‘陈桥兵变’,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黄袍加身’成为宋朝开国皇帝,那才是兵变。您说清楚了兵变﹑政变和兵谏的区别,马嵬事件定位‘兵谏’是切合实际的!”
洛阳师范学院毛阳光教授:马嵬事件“陈玄礼当然是功莫大焉。总体上,这个事件的意义是积极的。”
西北大学刘文瑞教授著《唐玄宗评传》一书中,肯定马嵬事件的历史作用:“诗人杜甫从国家安危的大局出发”,对陈玄礼等禁军“诛灭杨氏家族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赞扬。”对马嵬事件“历史作用肯定,还是恰当的,如果没有”马嵬事件“诛杀杨国忠,唐朝能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确实是个问题”[26]。
徐崧巍教授著《唐肃宗皇帝传》一书,称赞“晚唐诗人郑畋的一首《马嵬坡》极为深刻地评价了”马嵬事件的“作用及意义: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27]
蒙曼教授著《蒙曼说唐-长恨歌》一书,特别肯定马嵬事件的历史作用,明确否定马嵬事件是“政变”。她称赞陈玄礼将军,“陈玄礼可不想谋反”,正是为了避免发生“政变”“军士哗变”,陈玄礼将军在“太子的支持”下,诛杀安史之乱的“祸根”杨国忠,劝谏那个“不是情圣”的唐玄宗,赐死“贼本”杨贵妃。“既疏导禁军的不满情绪,又为国除害,不是两全其美吗?”[28]
穆渭生教授著《郭子仪评传》一书则肯定地指出:马嵬事件发生时,“皇太子(李亨)虽预闻其事,但并非主谋。因为他当时根本无权指挥禁军。”山东大学齐涛教授﹑马新教授著《刘宴杨炎评传》肯定马嵬兵谏的作用,指出,太子李亨,受到士民拥戴,北上朔方,抗击叛军:“玄宗一行行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时,杨国忠被愤怒的士兵所杀,杨贵妃页被缢杀,玄宗继续南行及蜀,太子李亨则被士民拥戴,前往西北,准备依托朔方,召集将士,抗击安史叛军。”[29]
上海社会科学院陈磊研究员《论马嵬事变》一文,不赞成太子李亨策划马嵬事变之说,提出了太子李亨“是否有能力策划这次事变”的问题?她从五方面加以究论证:第一,“李亨在天宝年间应该没有一定的政治势力。”第二,“李享是否对禁军有了控制权”,她认为禁军“到马嵬事变之时仍然为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所控制。”第三,“马鬼事发友生当时“太子并不在其地。”第四,“从事变针对的目标看,杀杨国忠和杨氏家族目的是相当明确的。”第五,“事变发生的仓促”,要“预谋并计划一次兵变”,太子“不是一朝一夕办得到的。”否定太子策划事变。河北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时为在读研究生的吕晓青﹑艾虹撰《马嵬驿事变原因新论》论文,把马嵬事件定性为“兵谏”:“马嵬驿事件本身并不存在幕后主谋,仅是一场突发性偶然事件。是陈玄礼为疏导众怒﹑转移矛盾以保护玄宗而临时发起的兵谏。”[31]
4.宁夏专家 评论马嵬
著名宁夏地方史志专家吴忠礼研究员,作为宁夏历史学者第一个在其2011 年出版的《朔方集》一书中,把“马嵬事件”定性为“兵谏”。“禁卫军在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发动兵谏,怒杀误国的奸相杨国忠后,又坚决请求诛杀误国祸首的杨贵妃”[32]。
孙生玉主编《宁夏军事史话》一书,肯定马嵬事件的历史作用:“玄宗父子仓皇出逃。途经马嵬驿,‘六军不发无奈何’,唐玄宗只好下诏杀死杨国忠,含泪赐死爱妃杨玉环”[33]。
宁夏灵武市市志办主任马学海主编《灵武史话》一书,肯定马嵬事件:“六月十四日,逃亡队伍到达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北23 里)”,“随行士兵杀了宰相杨国忠,又逼迫唐玄宗缢杀了杨贵妃。”[34]
宁夏文史馆馆员﹑著名宁夏历史专家宁夏灵武人杨森翔先生撰《李亨灵武登基始末》一文,肯定马嵬事件:“到了马嵬驿,六军不进。玄宗追问其故,禁卫军首领陈玄礼等军官要求围杀杨国忠,屠灭掉他的全家。因为他们认为,今天的这个局面都是杨国忠造成的。玄宗无奈,只得应允。为了防备后患,禁卫军又要求唐玄宗处死杨贵妃。玄宗也只好忍痛割爱,赐她自杀。”[35]
宁夏史志专家﹑吴忠市地方志办主任胡建东研究馆员主编《吴忠史话》一书,同样把马嵬事件定性为“兵谏”。“军士们把造成战乱的罪责归罪咎于杨贵妃和杨国忠,便在阵前发动兵谏,要求诛杀误国害民的杨国忠兄妹。唐玄宗李隆基身处危境,无可奈何,只好在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缢杀了杨贵妃,然后逃往四川避难”[36]。
我赞同诗圣杜甫和著名边塞诗人高适等唐朝诗人﹑学者对“马嵬兵谏”历史作用的肯定,对陈玄礼等禁军“马嵬兵谏”挽救大唐是历史功臣的高度赞扬。赞同范文澜等几十位专家﹑学者,对禁军发动“马嵬兵谏”历史作用的肯定﹑赞成把马嵬事件称为“马嵬兵谏”的观点。
“马嵬兵谏”类似张学良﹑杨虎城的“西安兵谏”。两次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将士们以武力对当权者的昏庸,予以强谏,逼迫当权者迷途知返﹑挽救国家的爱国表现。说明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历来具有优良的爱国主义历史传统。
“西安事变”捉蒋介石的地方,1946 年曾建一座《正义亭》,取西安事变是一次救国正义之举的意思,后改为《捉蒋亭》。1986 年12 月,“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改为《兵谏亭》,明确西安事变性质是“兵谏”,不少专家﹑学者提出“西安事变”应该称为“西安兵谏”。如张志荣教授撰《“西安事变”宜称“西安兵谏”》一文,特别提出,把“西安事变”称为“西安兵谏”[37]。
由此,我想建议陕西省兴平县,为纪念发生在马嵬驿的唐朝禁军救国重大历史事件“马嵬兵谏”,可否考虑,参考西安华清池的《兵谏亭》,在兴平县马嵬驿地方也建一座《兵谏亭》。同时,我还建议,可否考虑,修建一座诗圣杜甫称之为“忠烈”“桓桓陈建军”的《陈玄礼将军塑像》,马嵬驿《兵谏亭》和《陈玄礼将军塑像》,也可作为汲取“马嵬兵谏”历史经验教训的历史文化旅游景点。
七 马嵬兵谏 众说纷纭
“马嵬兵谏”,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影视界﹑新闻媒体以及网络网文作者,都特别关注。人们会发现不少专著﹑论文,大量的网文,出现了大量各种各样用“猜测”“可能”“或许”撰写的著作和文章,千方百计地去“发现”马嵬“兵变”“政变”的“真相”,似乎还真“发现”了“真相”,发现了“策划”马嵬驿政变的“主谋”。有说太子李亨是政变的“后台”“主谋”;有说马嵬“兵变真正的后台是高力士”;有说主谋是陈玄礼;还有说,因安禄山为杨贵妃“有乱天下意”而反叛,“唐玄宗主动赐死杨贵妃以阻止安禄山追击,这就是历史上马嵬坡事件的真相。”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天宝十五载(756 年)的“马嵬兵谏”,六月十四日午后发生,前后不过几个时辰,事情并不复杂。但是,不少学者反复“寻找”密谋策划的“真相”,说马嵬事件是一场“预谋策划”的“蓄谋已久”的“政变”,说“太子李亨突然发动政变”,是“政变”的“策划者”。
《历史罪》一书寻找“真相”:“旧史记载是为尊者讳,这并非历史真相”。马嵬事件“真实的情况是,这次政变蓄谋已久。其实早在长安的时候,政变行动已经悄然开始,太子李亨与亲信密谋以后,派李辅国去拉拢陈玄礼,伺机对付杨国忠。李辅国还是中介”[38]。书中并未举出证据。《唐肃宗评传》一书中,指出“禁军将士因饥疲劳顿,已有不逊怨言”。“真实情况是:太子李亨同亲信密定之后,派李辅国去拉拢陈玄礼,这一行动,或许在长安城内就已开始”。“太子亨发动政变”“太子策划政变”。《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一书,则写道“太子李亨是这场兵变的幕后策划者。”[39]
《唐肃宗皇帝传》一书,写道:“马嵬驿兵变决不是六军将士一时头脑发热,感情冲动所致,实际上它是在有人精心策划与指挥下,六军将士们在这场兵变中充当了某些人去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亲自设计与导演马嵬驿兵变的幕后人物就是其后不久于灵武自立太子李亨”。“马嵬驿兵变的真正幕后指挥者是善于伪装的太子李亨。”所不同者,《唐肃宗皇帝传》作者,没有说“马嵬兵谏”是“政变”,说的是“马嵬驿兵变”[40]。
《唐玄宗评传》一书,提出陈玄礼发动马嵬事件,并不认同“太子李亨发动政变”。“行至马嵬驿,在愤怒的军士们停顿不前﹑滞留驿站﹑有可能出现哗变的情况下,陈玄礼当机立断,召集诸将,……就这样,兵变开始发动了。”“兵变一发动,杨氏就遭了殃”[41]。不过,也是把马嵬事件叫作“兵变”,“杨氏”是“遭了殃”。
与《唐肃宗评传》《唐肃宗皇帝传》的作者既相同又不同,《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一书,认为马嵬事件是“兵变”“马嵬驿事件绝非禁军军士因饥疲而自发的兵变,而只能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的行动。”作者认为:“在排除军士自发行动和肃宗为后台之说后,指出兵变真正的后台只能是玄宗身边最宠信的大宦官高力士。”作者“排除”了“肃宗为后台之说”[42]。
八 政变之说 只是推测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既然是科学,就必须言之有据,秉笔直书,论史务实。言之无据,立论不稳。凡史论,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不能仅凭“猜测”“推测”“可能”“或许”的主观意识下结论。言之有据,立论才稳。
上述的“政变”说﹑“太子预谋策划政变”说,其证据是什么呢?是言之有据吗?今提出商榷。
第一,有书上说“掌握着精锐飞龙军的太子李亨发动政变”。
《唐肃宗评传》一书作者写道:“唐玄宗避乱出逃,离开了京师,这给掌握着精锐飞龙军的太亨发动政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嵬之变发微》一文中写道,
“据《通鉴》:政变后‘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乃使(广平王)做驰白上,上绳警待太子,久不至,使人侦之,还白上,上曰:天也。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疑马从太子’。由此推测,在玄宗一行之中,太子一系成员皆在后军之中,且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展马都已在太子的控制中。《旧唐书》卷10《肃宗纪》载‘留后军朕马从上’似‘留’比‘分’更能反映真实的情况。”而“《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一书写道:“皇太子能够控制这支武装对于成功地发动兵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43]
看来,太子“控制”“掌握”后军二千人“发动政变”说法,是从《通鉴》“由此推测”出来的,并未提出依据。“推测”不能作为史论的可靠证据。相反,此“推测”还有出入:上述作者引用的史料《通鉴》记载,正是马嵬事件“后”,唐玄宗“乃分后军及飞龙厩马从太子”。《旧唐书》记载也是“马嵬之变后”“留后军厩马从上”。既然承认马嵬事件之后,玄宗乃分二千人给太子,那么,如果事变前太子已经掌握了后军二千人“发动政变”,事后,禁军三千人,太子“控制”二千人,还余一千人,唐玄宗就不可能能从一千人中再“分”出“后军二千人给太子了;既然是马嵬事件后才分兵给太子二千人,证明马嵬事件前,太子并没有掌握后军二千人,就没有因为“掌握着精锐飞龙军”而发动政变。
晚唐诗人张祜的《马嵬坡》诗句,“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也正是反映马嵬事变后玄宗才分兵的史实:玄宗分兵后,玄宗南去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一千三百人,南稀;太子北去灵武,玄宗分给二千人,北多。正好证明马嵬兵谏发生时,太子并不掌握禁军。
第二,有书上说“太子李亨”“派李辅国去拉拢陈玄礼”“发动政变”。
《唐肃宗评传》提出,司马光“颇重君臣大义”“按春秋笔法修史”,从而“掩盖了历史真相”“真实的情况是:太子李亨同亲信密定之后,派李辅国去拉拢陈玄礼,这一行动或许在长安城内就已开始”[44]。其依据是,《旧唐书·杨贵妃传》“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旧唐书·韦见素传》:“龙武将军陈玄礼惧其乱,乃与飞龙马家李护国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谋于皇太子,请诛国忠,以慰士心”。《资治通鉴》所记“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欲诛之,因东宫宦者李辅国以告太子,太子未决”[45]。唐史所记“陈玄礼密启太子”“陈玄礼惧其乱”通过李辅国“谋于皇太子”,只能证明陈玄礼怕乱禀报了太子,不能证明“太子拉拢陈玄礼”。《资治通鉴》所记“太子未决”,只能证明太子预先是知道陈玄礼要除杨氏一族的,太子内心里肯定是支持陈玄礼除掉杨氏的,但史书“未决”的古汉语意思是:尚未决定,是犹豫不决,并未表态。因此,太子拉拢陈玄礼发动政变说,只能是学者的推测,没有依据。我认为,还是上述穆渭生教授的看法符合史实:马嵬事件时,“皇太子(李亨)虽预闻其事,但并非主谋。因为他当时根本无权指挥禁军。”
九 玄宗分兵 宣旨传位
“马嵬兵谏”后的第二天,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十五日,《资治通鉴》记载,“上将发马嵬”“及行,父老皆遮道请留”,但是,唐玄宗“不肯留”,百姓又请留太子,百姓说“至尊”“殿下”都走了,“中原百姓谁为之主?”要不然就让“殿下”留下领导百姓平叛,唐玄宗说,这是“天也!”唐玄宗对百姓“中原百姓谁为之主?”问题的答复,是传位太子作中原百姓之主。为此,唐史文献记载,唐玄宗在马嵬与太子李亨分道扬镳之前,安排了”传位”三件大事,即“马嵬之命:玄宗分兵;使送内人;宣旨传位。[46]
1.玄宗分兵 南稀北多
首先是唐玄宗下令马嵬分兵。玄宗分兵,是“马嵬兵谏”的直接结果,非常重要。《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百姓遮道乞留皇太子,愿力破贼,收复京城”,玄宗不肯留,“留后军厩马从上”。《旧唐书·肃宗本纪》记载,“时从上(肃宗)惟广平﹑建宁二王及四军将士,才二千人”[47]。《资治通鉴》具体记载,唐玄宗“乃分后军二千人及飞龙厩马从太子”[48]。因此,到马嵬分兵时,玄宗才下令从其随扈禁军三千人中分出二千人,给太子。让太子以二千禁军,作为太子代父皇完成大唐皇帝领导平叛﹑收复二京﹑兴复社稷任务的武装基础。
请注意,史书记载证明,是在“马嵬兵谏”之后,玄宗才下令,马嵬分兵,唐玄宗才分给太子二千人,“留后军厩马从上”的“留”,也是玄宗留给太子禁军的“后军厩马”跟随太子,说明是玄宗分禁军和战马给太子。因此,关于太子“马嵬兵谏”前,事先早就已经掌握二千人禁军在马嵬“发动政变”的说法,只能是学者的推测。
有的书上不认为是唐玄宗分兵,说是“太子分兵”“为了个人的最大利益,李亨只有分兵,另谋发展”[49]。为证明太子分兵,书上还举出太子李亨的两个儿子“在出逃队伍中乃是‘典亲兵护送’”,“说明太子李亨确实控制着这支精锐的禁军队伍。”[50]并举出《旧唐书·后妃传》“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51],证明是“太子分兵”。其实,“太子不敢西行”无法证明太子有权“分兵”﹑分禁军。而太子李亨儿子所“典亲兵”,乃是护卫太子的亲兵,不是护卫皇帝的禁军。唐朝太子﹑亲王以及节度使等,都有亲兵。护卫太子的亲兵与护卫皇帝的禁军,不是一回事。禁军是皇帝的护卫,自然是皇帝掌握,太子不可以随便掌握,更无权把禁军“分兵”。
2.使送内人 服御等物
唐玄宗在马嵬临行第二件事,是下令送内人随太子北上。《旧唐书·肃宗本纪》:“乃令高力士与寿王瑁送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留后军厩马从上”[52]。《新唐书·肃宗本纪》:“十五载,玄宗避贼,行至马嵬,父老遮道请留太子讨贼,玄宗许之,遣寿王瑁及内侍高力士谕太子,太子乃还”[53]。《资治通鉴》记载比较简单就一句话:“又使送东宫内人与太子”[54]。史书记载说明,直到马嵬兵谏之后,唐玄宗马嵬分兵,唐玄宗才分二千人禁军给太子,同时,才命东宫内人,包括张良娣等嫔妃﹑宫女以及她们的服饰行装,派寿王李瑁(杨贵妃前夫)和宦官高力士,送还到太子李亨的身边。也就是说,从长安出发太子妃张良娣等是随唐玄宗在一起走的,不让她们在太子身边。说明玄宗一路对太子也是严密管控。既然马嵬事变前,太子妃张良娣等内人,随唐玄宗一起走,那么,太子李亨,在马嵬驿,也不大可能不顾太子妃等,轻举妄动,冒险去发动所谓的政变。马嵬分兵,送内人等给太子,让太子才得以无后顾之忧,放心地去完成平叛使命。
3.玄宗传位 “马嵬之命”
玄宗“传位”的“马嵬之命”,是“马嵬兵谏”最重要的积极的成果。马嵬分兵,唐玄宗再次宣布“传位”太子:一是,“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曹善辅佐之”。二是,“且宣旨欲传位,太子不受”。
司马光《资治通鉴》称之为“马嵬之命”,这正是太子李亨北上朔方,到达灵武,“万人劝进,让不获已,乃即皇帝位于灵武”皇位合法继承的法统依据。
关于“马嵬之命”玄宗宣旨传位的史实,唐史文献多有记载,千百年来,学界有不少学者也多认同唐书记载的史实,“马嵬兵谏”发生的同时代人,诗圣杜甫“窃闻天子已传位”诗句证明,杜甫在陕西鄜州偏僻的乡村羌村避乱,都已经听说,玄宗传位太子已经即位,证明唐朝当时,玄宗传位﹑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应该已在城乡广为传播了。
在《唐肃宗皇帝传》一书中,徐松巍教授明确肯定唐玄宗有“马嵬之命”,指出:“李亨以太子身份即位称帝也是名正言顺,因为玄宗马嵬驿时就有言在先”[55]。徐松巍教授的玄宗的“有言在先”,指的就是唐玄宗在马嵬驿时,事先,已经有宣布太子“可奉宗庙”,有“宣旨欲传位”,就是已经有“马嵬之命”。
然而,有的不少学者却对玄宗事先有传位提出质疑或异议。《大唐英雄传》一书提出,唐肃宗即位是“抢班夺权”[56],明显错误!什么是“抢班夺权”?李世民﹑李隆基不是太子,不可能由他们接班掌权,他们都是通过发动政变,抢着接班掌权,那才叫“抢班夺权”!李亨是太子﹑是“储君”,是大唐皇位合法继承人,事先,玄宗又有传位旨意,有“马嵬之命”,李亨太子没有必要抢班夺权,没有发动政变,而是受命即位,合理合法。唐史文献找不到太子李亨即位是“抢班夺权”资料,唐朝当代人没有说李亨即位是“抢班夺权”的:唐人郭湜据高力士口述撰笔记《高力士外传》记玄宗本人肯定太子李亨灵武即位是:“我儿嗣位,顺天应人”。唐人陈鸿撰《长恨歌传》明确记载,太子李亨灵武即位是“肃宗受禅灵武”。“受禅”,就是接受玄宗事先宣布禅位旨意而即位,绝非是什么“抢班夺权”;《唐肃宗评传》一书提出,“唐肃宗即位灵武,其实没有得到唐玄宗的任何旨意”。“唐玄宗根本没有传位之心”。“唐玄宗命太子监国一事,这与传位根本就是两码事”。司马光《资治通鉴》“把唐肃宗登基说成了雅符唐玄宗初衷的事情”,“正是他用《春秋》笔法的局限”[57]。更是学者推测,没有依据。
《唐玄宗“传位”史实辨析》一文,关于玄宗传位,列举数则唐史文献,表示质疑文献的真实,包括《旧唐书·韦见素传》一则﹑《旧唐书·杨贵妃传》一则﹑《资治通鉴》两则。[58]
但是,笔者发现,唐史文献中,关于玄宗事先有“传位”“禅位”之意史实的记载,远不止这数则,而是有二十数则之多。人们可以看到,包括唐人﹑五代人﹑宋人撰著的史书,十数部文献二十余则史料反复记载有玄宗传位。唐肃宗灵武即位前,事先,唐玄宗本人分别在天宝十三载(754 年)秋,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二月,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十五日在马嵬驿,八月十八日,在成都等,曾多次亲自谈及宣布传位太子,证明唐玄宗确有传位之意,文献反复记载:“欲传位太子”“有传位之意”“亦有处分”“内禅”“禅位”“帝且禅太子”“可奉宗庙”“嗣位”“传国”“付以神器”“传国之诰”“宣旨欲传位”“受命之书”“马嵬之命”“受禅”“嗣统”“禅让”等,唐史文献详列如下:
第一,《资治通鉴》:“去秋(天宝十三年754 年秋)已欲传位太子”;天宝十四载(755 年)十二月,玄宗欲亲征,让太子监国,然后,传位,“朕将高枕无为”[59]。
第二,《旧唐书·韦见素传》:“往十三年(天宝十三年754 年),已有传位之意”;“昨(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十五日)发马嵬,亦有处分”,“亦有处分”指也已经有传位太子的“马嵬之命”[60]。
第三,《旧唐书·后妃传》:天宝十四载(754 年)十二月,“贵妃衔土陈请,帝遂不行内禅”[61]。
第四,《新唐书·后妃传》:天宝十四载(754 年)二月,“帝欲以皇太子抚军,因禅位,诸杨大惧,哭于廷。国忠入白妃,妃衔块请死,帝意沮,乃止”[62]。
第五,《新唐书·杨国忠传》:天宝十四载(754年)十二月,“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帝欲自将而东,使皇太子监国,谓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国忠揣帝且禅太子,归谓女弟等曰:‘太子监国,吾属诛矣。’因聚泣,入诉于贵妃,妃以死邀帝,随寝”[63]。
第六,《资治通鉴》:天宝十五载(756 年)六月十五日,“太子仁孝,可奉宗庙”。古代只有皇帝的身份,才有资格奉宗庙,因此,“可奉宗庙”,意思就是太子可以即位称帝;“且宣旨欲传位,太子不 受”[64]。
第七,《资治通鉴》:天宝十五载(75 年)七月十二日,“裴冕﹑杜鸿渐等上太子笺,请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太子不许”[65]。
第八,《旧唐书·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756年)七月十二日,“自逆贼恁凌,两京失手,圣皇传位陛下,再安区宇”;“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予恐不德,罔敢祗承”,“圣皇传位陛下,已有成命”[66]。
第九,《旧唐书·裴冕传》:“主上厌勤大位,南幸蜀川,宗社神器,须有所归”[67]。
第十,《新唐书·裴冕传》天宝十五载(756 年)七月十二日“主上厌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须有所归”[68]。
第十一,唐杜甫作《哀王孙》:撰于天宝十五载(756 年)八月,“窃闻天子已传位”[69]。
第十二,唐元载撰《杜鸿渐神道碑》:撰于大历四年(769 年),“付以神器之重”“受传国之诰”[70]。
第十三,唐郭湜著《高力士传》:撰于大历中(677-678 年),“万人劝进,让不获已”;“我儿嗣位,顺天应人”;“西蜀﹑朔方,皆为警跸之地”[71],“警跸”是帝王所在之地。
第十四,唐杨炎撰《灵武受命宫颂》:约撰于永泰元年(765 年),“我圣皇天帝探命历之数,启龙图作受命之书,付与我皇帝”[72]。“受命之书”即指传位的马嵬之命。
第十五,唐陈鸿《长恨歌传》:撰于元和元年(806 年)冬十二月:“既而玄宗狩成都,肃宗受禅灵武”。“受禅”,指太子接受玄宗禅位旨意,即皇帝位。
第十六,《明皇令肃宗即位诏》:“昔尧厌倦勤,尚以禅舜,况我元子……付之神器,不亦宜然!”“禅让之礼,圣贤高躅”“朕之传位,有异虞典,……。”[74]
第十七,唐贾至为唐玄宗撰《肃宗皇帝即位册文》:“命尔元子某,当位嗣统”“洎予六叶,恭位四纪,厌于勤倦,缅慕汾阳,当保静怡神”。[75]
综上所述,包括唐朝﹑后晋﹑宋初多位史家撰著的唐史文献多处记载的史实,特别是唐朝玄肃代时期同时代的杜甫﹑郭湜﹑元载﹑杨炎﹑贾至等人,当时人记当时事,尤为可信。因此,应该肯定,在唐肃宗灵武即位之前,事先,唐玄宗确有“传位”之意,“马嵬兵谏”的第二天,唐玄宗马嵬分兵,确有“马嵬之命”,并非“根本没有传位之心”。读上述数十则文献记载玄宗传位史实,我想强调五点:
其一是,读到《新唐书·杨国忠传》“国忠揣帝且禅太子”这则史料,我想提醒读者,有书上说“唐玄宗命太子监国,这与传位根本就是两码事”,那么,究竟唐玄宗命太子监国与传位是一码事,还是两码事?唐玄宗左右的最可靠的人﹑身边宰相﹑当事人杨“国忠揣帝且禅太子”,杨国忠告诉人们,他揣测,玄宗命太子监国,肯定就是要禅位给太子,监国与传位就是一码事!因此,杨氏一族才“聚泣”,杨贵妃“以死邀帝”,直到唐玄宗妥协作罢,唐玄宗没有亲征,太子没有监国﹑传位。玄宗身边的宰相杨国忠,已向后人证明唐玄宗让太子监国就是要传位太子,应该可信。人们就不必要再怀疑唐玄宗的确有给太子传位的“马嵬之命”了。
其二是,发现《唐玄宗“传位”史实辨析》一文质疑玄宗传位,该文评论引述《旧唐书》韦见素传﹑杨贵妃传和《资治通鉴》等记载了数则玄宗传位史实时说:“乍看起来,玄宗早有传位之心,事属确凿无疑。但若细究,我们注意到,在较为严肃的记载如《实录》纂修的《旧唐书》玄宗纪﹑苏州纪中,就没有上述记载”[76]。但是,我们正是看到同样根据《实录》纂修的《旧唐书》肃宗本纪,有玄宗传位“圣皇传位陛下”“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军兴之初,已有成命”记载。《旧唐书》的韦见素传﹑杨贵妃传﹑杨国忠传﹑裴冕传等,都有玄宗传位记载,证明玄宗确有传位旨意。
其三是,杜甫诗句提出“窃闻投资已传位”。《唐肃宗评传》说,杜甫的“‘窃闻’,曲折地言明唐朝人已在隐晦这一‘传位’过程了”[77]。其实,杜甫诗句中使用的“窃闻”,唐人诗中,多有使用,意为听说﹑私下里听说,“窃闻”的这个“窃”,《辞海》解释是,“常用作表示个人意见的谦词,如窃闻;窃思”“犹言私”[78]。如姚合诗的题目就有“窃闻”:《杨给事师皋哭亡爱姬英英窃闻诗人多赋因而继和》诗。杜甫的诗句中的”窃闻”,就是杜甫听说,无法证明唐人“隐晦”唐玄宗这一传位的过程。
其四是,唐肃宗灵武受禅嗣位,正如唐玄宗本人所说是:“我儿嗣位,顺天应人”。大唐太子,是唐朝皇位合法继承人,是“储君”。在国家处于战乱危亡的特殊时刻,太子李亨依据唐玄宗“马嵬之命”以及多次传位旨意,作为大唐储君受禅嗣位,虽然当时玄宗不在场不知情,应该确实是尊玄宗“马嵬之命”即位,名正言顺。只是经历几十年磨难的太子李亨,为人谨慎,马嵬传位时,太子不受,在灵武,玄宗不场的情况下,经过大臣亲信军队百姓“万人劝进”,延后日期,接受了玄宗传位的“马嵬之命”即位,当日即派使者赴成都报告父皇。同时,唐肃宗遵照玄宗传位旨意和百姓瞩望即位,领导平叛,收复二京,兴复大唐,太子李亨尊玄宗“马嵬之命”即位,属于唐代安史之乱特定时期一种新的别样的“皇帝禅位”之“新局”。正如陈寅恪老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评价,唐肃宗“受禅灵武”是“别开唐代内禅之又一新局”[79]。
其五是,著名唐史专家已故赵文润教授在其主编《隋唐历史人物》丛书序中,评价丛书之一任士英教授著《唐肃宗评传》一书,指出:“在唐代21 位皇帝中,对肃宗的研究历来不为学者重视,甚至被斥为‘昏君’”任士英教授“在潜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史料的搜集﹑考辨,令人信服的证明,肃宗李亨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功绩显著,而且还继承了开元通宝盛世的成果。他表面看来谨小慎微,实则大智若愚,是一位颇有主见的皇帝”[80]。赵文润教授的评论发人深省,今天我们应该对唐肃宗灵武受命即位,给予必要的肯定,特别是对唐肃宗继承开元通宝盛世的成果,主持平叛中的功绩,予以客观合理的肯定和评价。任著《唐肃宗评传》中,虽曾质疑肃宗即位有玄宗传位旨意,但是,书中仍然充分肯定并评价唐肃宗灵武即位,领导平叛,复兴大唐的历史作用。任士英教授,在《唐肃宗评传》一书中强调指出,唐肃宗“灵武即位的消息传到叛军占领区后,给当地的抵抗运动带来了巨大的促动”。“从政治上扭转了唐玄宗出逃后全国平叛的被动局面”。“唐肃宗在四海近乎分崩离析的严峻时刻,在灵武举起平叛的大旗,给全国臣民的复兴带来了希望”[81]。
十 “马嵬兵谏” 救国之举
综上所述,距今1264 年前的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十四日,安史之乱特定背景下陈玄礼将军率禁军的“马嵬兵谏”,是大唐国运由盛转衰转折点的重大历史事件。自古至今,唐朝诗圣杜甫和高适等同时代中晚唐以至历代诗人﹑学者,当代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等众多专家﹑学者,对“马嵬兵谏”历史作用给予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对陈玄礼将军为首的禁军将士挽救大唐给予高度赞扬。总结“马嵬事件”全过程,探讨“马嵬兵谏”的性质﹑历史作用和重大意义,有助于深入研究唐朝中晚期历史,以史为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弘扬爱国救国精神,激励新时代国人,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马嵬兵谏”是陈玄礼等禁军将士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救国之举。“马嵬兵谏”的特定历史背景,就是“安史之乱”。国家出现危机的情况下,随扈唐玄宗一行的禁军将士挺身而出,为挽救国家免于灭亡,“临之以兵”,诛杀杨氏,“拔去了”“两条祸根”,清除了安禄山造反的借口,鼓舞了唐朝军民奋起抗击叛军,扭转战局,“马嵬兵谏”成为大唐朝廷主政者由逃跑到抗敌的转折点。
几个时辰的时间,禁军将士尽管“愤怒”并未发生叛乱或夺权,而是一场禁军将士的“兵谏”,兵谏最大成果是马嵬百姓最紧迫﹑最关心的问题:“使中原百姓谁为之主?”领导平叛,兴复唐朝,有了明确答案,这就是当时人说的唐玄宗的“马嵬之命”,马嵬分兵,唐玄宗宣旨欲传位给太子,命太子李亨北上朔方,嘱咐随护太子禁军将士辅佐太子“奉宗庙”即皇帝位,由太子李亨受命做大唐新主,领导平叛,收复二京,兴复唐朝。正如诗圣杜甫评价的陈玄礼率领禁军发动的“马嵬事件”使“国犹活”。也正如邱剑敏研究员提出的,“马嵬事件应该看作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救国之举”。因此,我提出,把“马嵬事件”定性为“马嵬兵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