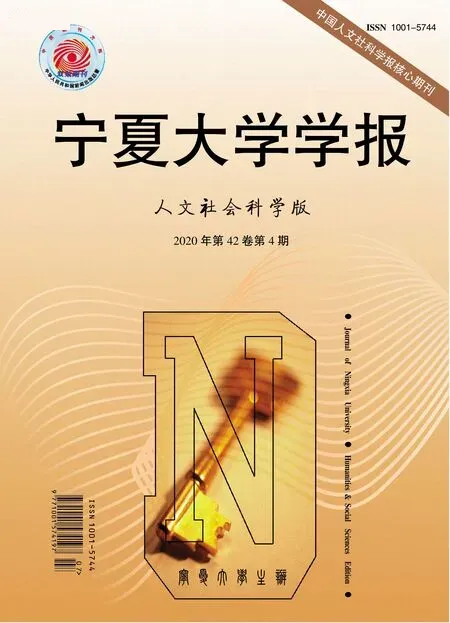出土《论语》简牍:东北亚地区行走的文化符号
裴永亮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儒家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语》作为儒家学派最为重要的典籍之一,书中记载了孔子及其部分学生的言行。“论”为编辑的意思,“语”为言语,“论语”即为“言语的编纂”。全书共分二十篇,每篇分若干章,共492 章。每章记一事或一话,全面反映了孔子的政治主张,教育思想﹑伦理观念和品德修养等各方面的观点。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论语》的行文言简意赅,记事﹑记言富有形象性,又富有哲理和感情色彩,其语言形成一种平易雅正﹑隽永含蓄的风格。《论语》的影响不仅在中国,还远及朝﹑韩﹑日等东北亚国家。近年来,东北亚地区先后出土了记载当地文化传播情况的汉字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简牍资料,而其中的《论语》简牍,更为研究儒学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一 传世《论语》文本的发展
《论语》在先秦时期即已成书,至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成为儒学教育的重要教材。东汉时,《论语》和《孝经》《诗》《书》《礼》《乐》《春秋》并列为儒家七经。三国魏何晏集汉儒各家学说着成的《论语集解》是现存最早的《论语》的注本,此中何晏首创集解体经注,被认为是“对《论语》解释的精粹集”[1]。《论语集解》釆用了孔安国﹑包咸﹑周民﹑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诸家之学说。但在注释时标明注者姓名,对于较易解的内容,只列一家,而难以尽意时,则兼采多家之说。南宋起,《论语》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及《孟子》合称“四书”。注释还有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论语正义》﹑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等[2]。
早在汉代就开始对儒家经典进行整理与研究,汉武帝末年,山东曲阜的鲁恭王要扩建宫殿,将孔子宅院拆毁。在孔子宅第的墙壁夹层中,发现了一批古代简牍书籍。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几十篇。孔子后人孔安国为文学,对这批简牍进行整理与研究。如《汉书·景十三王传》载:“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磐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3]。又《汉书·艺文志》:“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札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 也”[4]。
秦火和战乱使《论语》一度失传,汉初所传《论语》出现了若干传本,即《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古论》《齐论》和《鲁论》都是今本《论语》的前身。《鲁论语》为鲁人所传,亦称“鲁论”,属于《论语》的今文本。《齐论语》亦作“齐论”,亦属于《论语》的今文本。皇侃《论语义疏序》引刘向《别录》称“齐人所学谓之《齐论》”[5]。《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二篇,下注曰:“多《问王》《知道》”[6]。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以为《问王》疑即《问玉》,因篆文形似而误[7]。近人陈汉章《经学通论》认为《礼记聘义》《荀子·法行》各有“问玉”﹑“论玉”的文字可为佐证。此外,“其二于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8]。清代刘宝楠疑此所谓“章句”指训释之词。汉时传《齐论》的有庸谭﹑王吉﹑宋畸﹑贡禹﹑五鹿充宗等人。西汉未张禹即是合《齐论》于《鲁论》,删其烦惑,除去《问王》《知道》二篇,而成《张侯论》。为现行《论语》的来源之一。清朝马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齐论语》辑佚一卷。《齐论语》为齐人所学,《古论语》其书用古文字写成。
二 东北亚地区出土的简牍《论语》文献
以汉字为载体的书写文化和以汉字为表达手段的儒家思想,自公元前2 世纪以来便逐步成为中﹑韩﹑日三国共同的文化要素,也成为东北亚简牍文化的象征。近年来,由于东北亚各国均加强了考古发掘工作,各国先后出土了相当数量的记载东北亚地区文化传播情况的汉字资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简牍资料,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各国均出土了《论语》简牍,为研究儒学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中﹑朝﹑韩﹑日四国同属于东北亚文化圈,历代统治者长期崇尚儒家文化和推行儒学教育,对四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四地出土的儒家简牍,作为一个典型标志,具体而微地反映出四地间古代文化的交流状况,现将东北亚地区出土《论语》叙述如下:
(1)江西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论语》。
2015 年,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出土竹简约5000 支,从初步清理和保护情况看,竹简的内容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孝经》《医书》《六博棋谱》等文献,其中《论语》简500 余枚,三道编绳,每简容24 字,每章另起。而《论语·知道》或属于《论语》的《齐论》版本,目前可释读的文字约占今本《论语》的三分之一[9]。
西汉时期,《论语》分为《鲁论》《齐论》《古论》三个版本。皇侃《论语义疏序》引刘向《别录》称“齐人所学,谓之《齐论》,《汉书·艺文志》著录二十二篇”[10]。《齐论》相比其他版本,多了《问王》《知道》两篇。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竹简正面写有“智道”二字,背面书写“孔子智道”等24 字。篇题“智道”即取自首句开头“孔子”之后的两个字,符合《论语》各篇的命名规则。据此,此句当为《知道》篇的首章[11]。
(2)甘肃敦煌悬泉地区出土的《论语·子张篇》部分。
20 世纪90 年代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20000多枚汉简,其中除反映中西交通﹑丝绸之路﹑西北边疆等内容外,一些儒家经典也被保存下来,其中亦包括《论语》相关简牍[12]。根据简文所载:
乎张也,难与并而为仁矣。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子,孟庄子之孝,其也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V1812②:119)[13]
据今本《论语》所载,“《孟子》云:‘亲丧。固所自尽也。意同’。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悬泉汉简《论语》简与今传世略有不同,简文称“子”,今本称“夫子”,今本中“吾闻诸夫子”,汉简中均为“吾闻诸子”,可能是《论语》的版本不同或者是在传抄时有所缩略[14],另外也可以说是文献的地方性所导致[15]。
(3)中国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
1973 年在河北省定州市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出土的《论语》竹简,共620 余枚,简全长16.2 厘米﹑宽0.7 厘米,残简居多,释文共7576 字。定州《论语》竹简出土在中山国怀王墓中,为宣帝时上层社会流传的版本。时间下限最晚为汉宣帝五凤三年,所以它是公元前55 年以前的本子,而当时已有《鲁论》《齐论》《古论》的三个版本[16]。
(4)清华简有关《论语》简牍。
2008 年7 月15 日清华简到达清华大学,其年代是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主要是楚国文字,共有2388 枚。清华简最长的46 厘米,最短的10 厘米左右。简文书写出于不同书手,风格不尽一致。
清华简是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批战国简,由于是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写本,为研究先秦时期儒家文献提供了契机。对传世文献的理解,历来争议较大,清华简的出现为理解这些有争议的内容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17]。
(5)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论语》。
肩水金关位于甘肃河西走廊黑河东岸,在汉代是扼守弱水,防止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扰汉地的大门。1973 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在金塔县北部肩水金关遗址出土汉简1.1 万枚,从2011 年至2016 年,由中西书局出版的《肩水金关汉简(全五册)》将简文全部出版,作为两汉时期西北边陲出土的简牍,其中亦有儒家相关文献:
孔子知道之昜也,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73EJT22:6[18]
据学者考证: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论语》简牍是今本《论语》中《雍也第六》《泰伯第八》《卫灵公第十五》《阳货第十七》诸篇中的部分内容。肩水金关所出纪年简以宣帝时期为最多,宣帝时社会上主要流行《齐论》,肩水金关汉简中的《论语》或可是《齐论语》中的一部分。肩水金关中出土的论语文献说明当时儒家思想在西北边陲的传播情况,亦可见宣帝时各地文化交流的状况[19]。
(6)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诗论》。
1994 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得两批战国楚简,总简数约1700 枚,内容多为战国古籍,其中多为古佚书,与今传者内容有诸多差异,对研究先秦思想﹑哲学等提供资料[20]。《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五册中有《君子为礼》一篇,共16 支简,前半部分内容主要是孔子与其弟子颜回的问答,文中孔子向弟子颜回传授礼﹑仁﹑义等儒家伦理的记载,孔子认为依仁而行,能使社会政治秩序安定和谐,这一思想与《论语·颜渊》中“颜渊问仁”所反映的思想一致,子曰:“克已复礼为仁”。后面部分内容涉及贵族大夫“容礼”的规范,并记载有关孔子与子产﹑禹﹑舜四者“孰贤”的论说[21],是研究早期儒家相关思想不可多得的补充材料。
(7)朝鲜平壤地区出土的《论语》简牍。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 年),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推行郡县制度,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汉文化由此走向了朝鲜半岛。20 世纪时,朝鲜考古发掘大量乐浪郡时期墓葬,出土部分简牍。包括20 世纪90 年代以前出土的木制简牍10枚,90 年代后朝鲜平壤贞柏洞364 号墓出土的简牍约120 枚。
朝鲜地区出土的简牍材料近年才对外公布,竹简是编联成册,书写着传世本《论语》中《先进》和《颜渊》两篇的内容。从目前公布的资料看,能辨别出具体内容的完整简有39 枚,残简5 枚,共44 枚,其中《先进》33 枚589 字﹑《颜渊》11 枚167 字,两种合计756 字,公开的资料仅占全部竹简的1/3 左右[22]。据史料可知,汉武帝时儒家思想成为官方学说,后逐步向各边传播,至宣帝时儒家经典及思想传播到乐浪郡等边地郡县,而平壤地区出土的《论语》简牍恰好证明了这一点。西汉时期半岛地区四郡的设置奠定看了中国东北及东北亚地区地区各邦国﹑部族与中原文明交流的基础,朝鲜地区出土的《论语》简牍为认识东北亚古代社会文化与思想的传播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据李成市﹑尹龙九﹑金庆浩等先生的研究,平壤《论语》简的内容很可能反映了西汉元﹑成时期所谓《论语》三论融合为传世本《论语》祖本时的情况[23]。
(8)韩国出土的竹简《论语》。
韩国共出土700 余枚古代木简,有字简400 余枚。其中《论语》木简有2 枚,即1999 年金海市凤凰洞发掘1 枚和2005 年仁川市桂阳区所在的桂阳山城发掘五角柱形木简1 枚。金海市凤凰洞发掘《论语·公冶长》篇为四面木简,是韩国出土的最早的典籍木简,桂阳山城发掘五角柱形木简内容也是《论语·公冶长》篇[24]。
(9)日本出土简牍《论语》。
据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全国木简出土遗迹报告书数据库”和“木简数据库”最新数据统计,截至2016 年6 月底日本出土木简的遗址数有1364 处,出土木简389380 枚。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各地区陆续出土木简总计近40 万枚[25]。
日本木简从公元6 世纪到近代都有出土,主要集中于7-8 世纪,其中以8 世纪奈良时代木简居多,日本的《论语》,发掘出土的日本木简中,还写着《尔雅》《王勃集》《千字文》《春秋》《尚书》《本草集注》《乐毅论》等内容,但《论语》和《千字文》木简占压倒性的多数。日本出土简牍中包括《论语》《尔雅》《文选》《王勃集》《千字文》书籍,《论语》简主要包括《学而》《为政》《八佾》《公冶长》《尧曰》等篇名。日本的论语简不是以册书形式呈现的书籍,只是作为习字的,抄写了书籍的一部分,是单独的 简[26]。
三 《论语》简与东北亚地区行走的文化符号
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7]。即以出土文物(地下之新材料)所记载的新材料和古籍所记载材料相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以获得对古史的新解。
20 世纪90 年代出自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悬泉汉简,除了对中西交通﹑丝绸之路﹑西北边疆内容的记录外,还有一些儒家经典保存了下来。西汉武帝将匈奴逐出河西走廊后开始修墙筑塞﹑屯兵驻守,并将其统治思想传播到西北边地[28]。与此相照应,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推行郡县制度,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汉文化由此走向了朝鲜半岛,之后形成了东北亚地区的汉文化圈。
儒家思想在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开始向社会各领域渗透,并逐步向新开拓地区传递,这与当时王朝实现对新开拓地区宣扬大一统政治理念息息相关。汉王朝开拓疆域过程中一方面采取政治﹑经济等方式,另一方面亦在思想文化上加强统治[29]。
韩国出土的《论语》书写在觚上,中国出土的《论语》简到目前尚未发现有写在觚上的,但西北地区有用觚书写的木牍,另外日本出土了书写有《千字文》的觚。由此可以推断,朝鲜半岛的文字文化受到了中国汉代书写方式的影响,后来又将其传播到日本[30]。
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往来由来已久,商周之际箕子率族人通过东北地区到达朝鲜半岛,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史载:“箕子率中国五千人入朝鲜,其诗书礼乐医巫阴阳卜筮之流百工技艺,皆从而往焉。既至朝鲜,言语不通,译而知之,教以诗书。使其知中国礼乐之制,父子君臣之道,五常之礼,教以八条。崇信义,笃儒术,酿成中国之风教,以勿尚兵斗,以德服强暴。邻国皆慕其义而相亲之,衣冠制度悉同乎中国。故曰:诗书礼乐之邦,仁义之国也,而箕子始之,岂不信哉!”[31]箕子到达朝鲜半岛将中国文化﹑物质等带往朝鲜半岛等地,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互动加强,尤其是中国与朝韩等国的交流更多集中以“文化”为媒介的精神层面,从而实现了“教其民以礼义”“诗书达于礼教”。
结合韩国以及日本和朝鲜出土的《论语》简分析可见,汉文化在对外传承的过程中发生了衍变,当其传播到朝鲜半岛时即与当地的文化相交融,形成了朝鲜半岛的特色[32]。虽然中国木简与朝鲜半岛以及日本木简在形态﹑功能等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它们之间具有比较明显的承继关系,共同构成了东北亚地区同源的简牍文化(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角谷常子教授语)[33]。虽然东北亚三国出土简牍有地域和时代差别,但在整个东北亚文化的背景下可见儒家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论语》木简成为了东北亚地区行走的文化使者,实现了该区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对推动当地文化多元一体发挥了重要作用[34]。
东北亚地区大量简牍材料的出土,说明简牍作为书写文字材料,在东北亚地区曾长期使用。就目前所出土的简牍材料来看,中国使用简牍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之后随着纸的普及使用,出现了简牍和纸张共存的局面,之后简牍逐渐不再作为书写材质,后世依然零星有简牍使用,如邢义田《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代木牍试释》中载,20 世纪初斯坦因曾发掘一批明代简牍,现藏英国国家图书馆[35]。在朝鲜半岛﹑日本等地,简牍与纸张长期共存的时期较长,简牍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得以强化。东北亚地区国家出土的《论语》简证明,儒家文化通过东北亚走廊传递到了朝鲜和日本等地,实现了汉文化与朝日等国家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