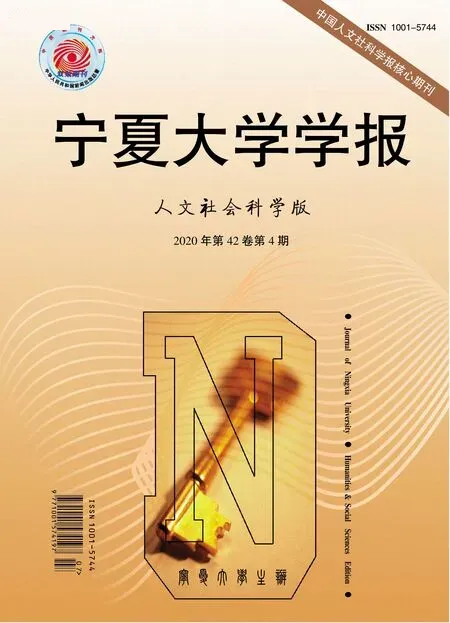人类·自然·对话
——《大草原之旅》的生态意识解读
霍舒缓,王 刚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常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常州 213159)
美国文学产生于一种特殊的人文和自然背景之下,从一开始就与自然有着天然的联系。17 世纪,当第一批旧大陆移民漂洋过海来到美洲新大陆时,他们被眼前的原始风光所震慑,“原始森林绵延无边,肥沃的土地沉睡了千年,这里是飞禽走兽幸福的天堂,更是人间的伊甸园”[1]。这片土地一派荒野景象,广袤的大地上水草丰美,各种野禽无忧无虑四处游荡,成为一片应许之地。从早期美国殖民时期的作品开始,我们就发现美国文学是“一种与地理环境紧密结合的文学。在他的著作中,我们第一次感受到自我与大自然的融合﹑个性与环境的交融”[2]。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作为美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作家更倾心于描述大自然的宏伟和崇高,该时期作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和表现成为美国自然文学的一个里程碑,爱默生(Emerson)﹑惠特曼(Whiteman)和梭罗(Thoreau)已经成为歌唱自然的“绿色圣人”。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1783-1859 年)作为美国浪漫主义初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也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美国作家,“欧文的‘美国’作品中有一种真正的兴味,并且在方兴未艾的西部文学中占据了一席重要位置”[3]。虽然他当时所处的美国工业文明已经发展起来,但是远西部还几乎很少有白人涉足,是一片蛮荒旷野之地。1832 年欧文应邀参加远西部的远征探险,于1835 年公开出版以美国为基础的《大草原之旅》(A Tour on the Prairies),背景是“美国景色中‘美国味’最浓的地方——美国西部”[4]。《大草原之旅》以作者的亲身探险为主要线索,跋山涉水,游历了尚处于荒野之中的美国远西部,对动植物群和自然风貌都加以书写,并不时地抒发内心情感,融自己的内心情感于对大自然的热爱之中。
生态批评是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盛行于美国的一种关注文学外部研究的文学批评方法,产生背景是全球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人类的生存受到威胁。1962 年美国当代女生态学家瑞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 年)的著作《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问世,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掀起了一场生态运动并促使建立了第一个地球日。卡森将人的伦理关怀广泛运用到整个自然界,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对后来“大地伦理”“荒野伦理”“动物伦理”等生态主义思想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1972 年生态批评家约瑟夫·米可(Joseph Meeker)在他具有开创性的理论著作《生存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中指出文学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所有生物主题。总之,生态批评旨在通过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文学的形式启迪人类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作为一个物种的人只是他们所栖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并使这一事实在所有思维活动中留下印记”[5],主要“目的是从文学领域开始来促使人们认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6]。
此后美国生态文学批评持强劲之势迅速发展,文学批评家对生态的关注有增无减,1989 年美国西部文学会议召开,切瑞尔·葛罗特菲尔地(Cheryll Glotfelty)要求将生态批评运用到“自然书写研究”之中,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西部文学在生态批评文学史上重要的作用。欧文作为美国建国之初的作家,他“普及了这样的观念,即中部大平原的绝大部分是名副其实的荒原,但他那些雄伟壮丽的描写有时又无意中流露出他对这片空旷土地和土地上野生动物的着迷”[7]。他的作品作为早期西部文学,尤其是《大草原之旅》,其中的生态意识已经初露端倪。《大草原之旅》分别记录了作者的“大草原之旅”,在已故拜伦伯爵“新地庄园”的乡间旅行和“阿伯茨福德”之旅。其中的第一部分“大草原之旅”主要记录了作者随一小队人马去西部边疆地区做了一次冒险旅行,表现出对在荒野和草原上无拘无束生活的羡慕。本文主要以该书的第一部分“大草原之旅”为主要研究分析对象,通过文本解读来探讨其中蕴含的生态意识。
一 大地部落:荒野描写与生态意识
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亨瑞·纳什·史密斯(Henry Nash Smith)认为,“能对美利坚帝国的特征下定义的不是过去的一系列影响,不是某个文化传统,也不是它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8]。由于17 世纪的新大陆移民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这片荒野上生存下去,如何开发和认识这片土地,以及在与旧大陆完全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下如何认识自己。所有这些与荒野自然有关的人类活动必然会反映到美国早期的文学书写中去。欧文在这部有关西部的《大草原之旅》中,赋予荒野以美国式的憧憬和骄傲,作品开篇写道,“我们看见了阿肯色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两岸一溜细腻的沙滩,岸上生长着茂密的柳树和木棉。朝河对岸望去,只见一片平坦的原野,鲜花遍地,远处地势稍稍高起,错落间有大小树丛合抱,还有排排树木屏风,尽管这里是未经人工开发的荒野,整个风景却像是一幅精绘细描的观赏杰作”[9]。欧文对阿肯色河及其两岸景色的描写,展示了自然万物相依相生,生生不息的景观。与旧大陆相比,新大陆这片广袤的处女地和无边无际的荒野是美国的“根”,无垠的旷野成为作家﹑诗人和画家不断歌颂的主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和人文环境。
19 世纪上半叶,人和荒野的密切关系才开始逐渐形演变成一种模式,在这片新大陆上成长的荒野作家“深入荒野,意欲把荒野变成自己的语言,但却被荒野的魅力征服,成为了大自然的代言人”[10]。就人类和荒野的关系而言,人类不是荒野的创造者,相反的是,荒野成为人类文明的摇篮,是人类的根基。“这一片美丽的地域完全再现了应许之地的景象:一片流着奶与蜜之地,丰美的草原上供养着如海岸沙石般数不清的野牛,而点缀草原的无数鲜花对寻找琼浆的野蜂而言不啻为一片天堂”[11]。所以“荒野就生命的根源而论,其本身是有内在价值的。当荒野使参观者获得现实体验时,荒野携带着价值,而且它已经把历史和生态学方面的价值传递给了参观者”[12]。荒野让人类意识到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因此人的道德伦理也适用于自然和一切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
荒野表面上是一个名词词性,但事实上它却有形容词的功能。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它会在人的心中产生一种特别的感情和心境。欧文面对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时这样描述此刻的心情,“对尚未习惯这种境况的人来说,大草原会让人体验到一种无可名状的孤独……大地一望无垠,了无人迹,给人的感觉是我们已经远远离开了人类生息之地,感觉似乎走在了大沙漠的中心”[13]。这种“孤独”是荒野给人的特殊意义,“荒野代表着从堕落的文明社会的隐退,因为人类在荒野中可以与最高的真理和精神的美德进行最亲密的接触”[14]。
荒野中的壮美和未经驯服的野性虽让人惊叹,但人最终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西部的扩张与19世纪20 年代美国社会发生的重组之间的矛盾,即荒野与文明之间的矛盾也体现在欧文的这部作品中。欧文一方面称“危险和充满敌意的荒野”[15],另一方面认为“在西部茂密的森林里,自有一番壮观和庄严,唤醒了我内心里与在宽敞庄严的建筑里所感受到的完全相同的情感;听见风声穿越树丛,我不时想起管风琴的和声”[16]。总之,虽然敬畏着难以征服的荒野,作者对自然的热爱成为一种自省的心里历程,因为崇高壮美的荒野提供的自由和健康让人向往,所以他提倡一种田园式的生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主要责任是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和完美性。唯有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可持续发展下去,生生不息。
利奥波德延伸了道德客体的范围即把道德客体的范畴延伸到整体部落。人类必须认识到“地球是一个完整的存在物……我们认识到了地球——它的土壤﹑山脉﹑河流﹑森林﹑气候﹑植物和动物的不可分割性,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尊重,不是作为有用的仆人,而是作为有生命力的存在物……”[17]。罗尔斯顿继承并拓深了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 年)的“大地伦理学”(也称土地伦理学),他认为,“一个物种是在它生长的环境中成其所是的。环境伦理学必须发展成大地伦理学,必须对与所有成员密切相关的生物共同体予以适当的尊重。我们必须关心作为这种基本生存单位的生态系统”[18]。
此外,罗尔斯顿将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中关于荒原的部分进行深层次的解读和论证,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即“荒原伦理学”,提倡人们尊重生态规律,人类和荒野的关系不应该是资源关系,而是享有同样的生命权利和价值,其核心生态观念是“整体性”。因此,罗尔斯顿(H.Rolsdon)成为美国环境伦理的奠基人之一,他主要的著作之一《哲学走向荒野》成为生态主义者的一部圣典,让他成为“生态哲学的集大成者”[19]。他给予荒野最大的价值化,认为荒野和人一样具有价值,哲学的思考也应走向荒原,最终建立一种“荒野伦理学”。
欧文的《大草原之旅》中体现了罗尔斯顿的这种“荒野伦理学”,他写道:“越过密西西比河数百英里之外的远西部……那里是一片广袤的草原,散布者树林﹑树丛﹑树群;滋润浇灌着它的,是阿肯色河﹑大加拿大河﹑红河,还有它们的支流。在这片肥沃葱绿的荒野上,麋鹿﹑野牛和野马自由自在地游荡”[20]。欧文笔下的荒野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土地,他也深刻意识到生态整体的重要性,认识到所有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相互依存的,“我们的行为和实践——包括那些第二天性和潜意识——也传递着关于自然世界和我们之间关系的信息”[21],任何一部分的缺失都会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紊乱。
总之,“与其他旧大陆国家相比,美国感到了自己的与众不同:那就是旧大陆无法与之匹敌的荒野”[22],新大陆广袤的荒野给了美国人自信﹑骄傲和无限憧憬,丰美的土地﹑壮丽的山川河流﹑自由的飞禽走兽成为文化和文明的摇篮。对于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个体人类来说,生态成员的善恶取决于是否对维护生态群落整体的完整﹑稳固和和谐有利。“狩猎是否是对环境友好的活动”,“从某一方面而言,狩猎可以在野生动物管理中发挥作用,这似乎有助于健康的生态系统”[23]。
欧文对荒野的描写表达了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生态意识始终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在《大草原之旅》出现频繁的一词就是“荒野”,如“西部荒野之地”“广袤的荒野”“荒野林间”“未经开发的荒野”等等,对荒野的赞美是想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告知人们荒野的价值和意义,以及人类该如何处置好人与自然荒野的关系,即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二 尊重生命:动物伦理与生态意识
动物和人一样都是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意识同样体现在对动物的尊重和价值判断上,动物也应属于道德客体的范畴。澳大利亚哲学家皮特·辛格(Peter Singer)作为当代世界动物保护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在20 世纪70 年代就指出把动物排除在道德伦理客体之外,就如当初把黑人和妇女作为“他者”一样是极其错误的。辛格在其理论著作《动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2009)中指出只要是能感知到痛苦的生物都应该享有道德价值的判断,“对痛苦和快乐的感知能力是一个生命享有自己利益的充要条件,它最底线的利益是不愿遭受痛苦的折磨:比如你把一只老鼠用脚踢到了马路边上,这就触犯了它的利益,因为他感知到了痛苦。”[24]荒野上的马是真正的生命体验个体,“由着骄傲自由的天性在它自己的这片荒野上奔驰。相比之下,我们城里的马多么的不同!”[25]他们要受制于人,充当人类的仆役。人类应该给予动物同样的道德考量,人与动物是平等的,都有感知痛苦和快乐的能力。动物亦有喜怒哀乐,所以如果人类把动物排除在道德之外,没有赋予动物该有的地位,不顾及动物的苦难和痛苦,那就是类似于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物种歧视”。
《大草原之旅》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他(托尼施)抓到了一匹美丽的奶白色马驹,大约七个月大,因为小马没有足够的体力和马群一起狂奔。……马驹不停地踢蹬,拼命想要挣脱,而托尼施就抱住它的脖子和它摔跤,还跳到它背上做出各种滑稽动作,活像一只猴子跳在了小猫的背上”[26]。欧文对这种捕捉场景的描写深刻而细致的,毫无疑问,当托尼施沉浸在捕捉战利品的喜悦时,他把马驹的痛苦置之不顾,即没有把这匹马驹纳入自己的道德审判中去。这种对动物痛苦挣扎和无助的细致描写以及人类的代表托尼施的狂喜感,都表现了欧文的生态意识觉醒,渴求人能认识到动物的痛苦以及人类对动物所造成的苦难。以至于当欧文来不及制止自己的同伴比特猎杀一匹野马时,由于子弹偏斜,野马“毫发无损地”地冲进树林中,而感到很“十分满足”[27]。人类有义务从根本上来改变对待动物的方式,从行为上减少对动物的伤害,这样动物就可以减轻痛苦。动物因为感知力而拥有“利益”,所以就应该得到道德关怀。虽然从某一程度上来讲,辛格也承认人和动物就感知力而言有程度上的不同,理应享受的权利相对动物要多,但是就道德层面而言,人类不能因为感知力的不同而不顾及动物痛苦,人类的道德义务要求把痛苦减到最小。当欧文和其同伴不停地朝野牛开枪时,虽然对其山一般的肉体而言子弹总不致命,“但是有一颗更为致命的子弹射了过去,它全身一颤,转身试图涉水到对岸,但踉跄几步后便侧身慢慢倒下去,死了”[28]。欧文评价这是“英雄之死”而且“感到羞愧”,反映出作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想征服自然,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残忍无情,文明社会的价值观和荒野自由之间的冲突揭示了作者早期的生态意识。
动物权利论者里根(Tom Regan)从捍卫动物的权利出发,为动物解放运动提供了另外一种道德依据。里根认为动物和人一样都拥有“固有价值”(inherent value),即这种价值是独立存在的,不因他人的目的﹑需要为转移,是与生俱来的独特的价值。固有价值保证生物群体拥有不受伤害的道德权力,因此,动物和人都是生命的体验主体,就固定价值而言没有优劣之分,动物和人都是平等的,人类不应该把动物当作资源来看待。“有生命的个体不是仅仅意味着活着或者是有意识……它们有观察力﹑记忆力和未来意识;他们有因为愉快和痛苦的感觉引起的情感生活;它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它们也可以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目标采取行动……这些所有上述的内容都与他们是否对别人有用无关”[29]。一切有生命的个体都具有固定价值,所以我们要对任何的生命个体,包括动物,都予以充分的尊重,而不能认为他们的存在仅是对他人才是有用有价值的。
欧文在《大草原之旅》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一想到这只受伤的鹿在孤独中死去,那些尚把这样的追踪当娱乐的人心中不免感到怜悯,但这样的怜悯转瞬即逝。人生来就是食肉动物,无论怎样被文明改造,依然随时都会重拾杀戮的天性”[30]。欧文认识到人类把自己的狩猎活动建立在动物的痛苦之上,就其本人而言是极其反对和反感的。欧文对此种“追踪”表达了“怜悯”和悲愤,谴责人类的“杀戮天性”,具有早期的“反猎思想”,体现了平等对待动物的生态意识。
此外,当欧文在山坡顶上偶遇一匹漂亮的野生黑母马时,“我凝视着它,一直到它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心中暗暗祈祷,愿如此美好的动物永不受鞭勒束缚之羞辱,永远是大草原上自由奔跑的精灵”[31]。作者的“祈祷”一方面体现出对自由大自然精灵的羡慕,另一方面也为其未来的被杀戮命运感到深深担忧,从侧面反映了作者对人类猎杀动物行为的反对,体现了作者早期的生态意识,以致作者在猎杀一只母鹿时,心里隐隐作痛“把枪举了又放,放了又举,就是狠不下心去开枪”[32]。人类把猎杀其他动物当做一种“娱乐”,不把动物当作有感情和血肉的生命个体,没有把动物列入到道德客体的范畴,这样动物就不拥有生命权,人类就可以不受任何道德良心和法律的束缚随意猎杀动物。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谴责人类“他是大地上的疾病,忽而用双脚走路,忽而像服了麻药一样呼呼大睡。他杀戮着﹑吃喝着﹑成长着……他心里充塞了许多互相矛盾的欲望……无可救药地只能靠残害其他生命来维生”[33]。但是,人类存在于自然之中,如果不是人类创造了自然,那么则是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就必须服从自然的规律而不是自己的利益。就生态的整体性而言,人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所有的生物都是理性的,他们和人类有着同样的感情”[34]。人类作为文明的化身,文明要求人类“与其他动物﹑植物﹑土壤之间达到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和谐状态”[35]。
三 赋予自然主体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和自然的和谐应该是建立在和谐﹑尊重的基础之上的,形成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与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主体性哲学不同,“主体间性哲学则消除了主客二元对立,把存在确认为自我主体与世界主体的交往和融合……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处才能获得自由”[36]。人的主体性要体现在与其他存在物主体的对话中,在生态系统中,每一个物种都有主体性,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交流对话方式,人类主体要在与其他自然主体的对话中完成自身的存在,赋予自然主体性成为完整的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是主体和客体﹑主人和仆人﹑统治者和臣民的关系,也不能是人把自然当作神灵一样来崇拜和敬畏,两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彼此相等﹑互相尊重,为了更好地维护彼此间的利益而对话。生态批评家通过自然导向的文学和批评的方式赋予自然以发言权的方式,不如通过研究事物关系(人和其他万物一样,都是物)中的特殊关系。承认他者的主体性,要求人类主体能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与他们一起共悲伤,平等地对待他们,这样才能形成人类主体和非人主体之间的交流和对话,充分理解非人主体的权利和困境。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40 年)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人类理解论》中认为,人类有权利拿走“自然资源”,占为其私有财产。从这个思维模式来说,荒野也是资源,如果人类不利用开发,则是存在被浪费的可能。但是20 世纪以来各种生态问题层出不穷,土地沙漠化﹑全球变暖﹑淡水匮乏﹑物种灭绝等,种种事实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荒谬性。就荒野的价值而言,人类要首先承认荒野的主体性,人和荒野中的万物都是具有主体性的,不是传统上的主客二元论,而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唯如此,人类才能真正实现与荒野的交融,进一步实现人和自然的交互主体性关系。荒野中的万物作为具有主体性的生命个体,具有自己的生活和情感,人类不能把非人类自然物作为没有思想和情感,让其丧失了主体性,成为满足人类需要的资源。总之,人类的自由是建立在与自然万物的相互依存之中,人类要把自己真正作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其他生态组成部分平等对话和交流,真正达到和谐共处的关系。
在欧文的笔下,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主体间性交流关系至关重要,自然物和人一样同样显示出其主体性。人和自然的交互主体性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是人类要转换视角,设身处地地从自然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且认可自然万物的主体性地位和利益。欧文对动物表现出来的同情和关爱表明他把动物看作生命主体,在描述一只被人射伤的麋鹿时采用了拟人化的手法,“这可怜的麋鹿,显然是发现自己的生命渐渐流逝时,离开了同伴,找到了这个僻静之处孤独死去”[37]。“可怜”和“孤独”本是人类独有的情感体验,欧文用在了一只垂垂将死的麋鹿身上,感受到了麋鹿的存在,赋予麋鹿一个独立完整的主体性,表达了作者的生态思想。麋鹿和人一样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万物之一,其享有的主体权利,如果人类把自己看作唯一的价值载体时,生态系统的和谐将会被打破。
此外,欧文对生活在这片蛮荒土地之上的印第安人赞美有加,他在文中吐露“奥萨基人是我在西部所见过最为俊美的印第安人,此时,他们尚未完全臣服于文明。”[38]这里特别强调了他们尚未被文明改造和侵染,与文明社会的人进行比较,欧文对前者给予十分的赞扬和肯定,批判了人类自己创造的文明对其自由天性的束缚,“这就是野蛮状态中高贵的遗世独立之人……掌握着个人自由的极大秘诀。我等社会中人,其实都是奴隶,并非为他人之奴,实在是给自己做奴隶。那些虚妄的追求如锁链般捆绑着我们,每时每刻都限制着我们身体的行动,阻断着我们灵魂的冲动”[39]。虽然印第安人和白人同样身处同一片美洲的土地上,但是其理念却与西方传统迥异,他们“视个人与群体﹑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平衡为悠久的精神财富”[40]。欧文对印第安人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待自然万物和对待人类自己一样,相信“万物有灵论”,他非常羡慕印第安人跟自然这种亲密的关系。他们尊重自然,充分认识到自然和人类的交互主体性,他们“他们以符合其环境条件和知识遗产的方式行事”[41]。欧文对印第安人在这荒蛮无人迹所表现出来的勇敢和无所畏惧这样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许与他们所尊崇的一个信条有关。这些人相信,有一个守护神一直在关照着他们,他以雄鹰形象出现,高高翱翔在天空中那些常人目力不及之处。有时候高兴了,大神便飞到下界……每当此时,四季协调,玉米茂盛,猎物丰富。可如果有时候大神生了气,便将愤怒通过雷电打下来”[42]。在这段描述中,欧文把印第安人早期的生态观表达的具体而形象,从侧面也说明了自己的生态意识。虽然科学与信仰在这里撞击,但是作者还是更推崇信仰,印第安人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以使用﹑理解和适应周围的自然环境为中心”[43]。印第安人把自己和自然放在同等的地位来看待,自然也有喜怒哀乐,当然也会庇护大地上的人类,比如“鹰的羽毛具有神秘和至高无上的力量”,在人类有任何为难之际,自然的使者“雄鹰”会给人力量。这是人和自然达到和谐共处的关系时,才会拥有欧文笔下印第安人的生活状态。“西部的印第安人……他们是大平原上的游荡者,他们的生活更明亮﹑更阳光,他们几乎永远都在马背上,永远行走在鲜花盛开的大草原上,头顶万里无云”[44]。印第安人承认自然的主体性,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因为在尊敬自然的同时他们也会从自然获得自己的生存所需,在与自然主体性的交往中,没有一味的忘我而“魅化”自然。也就是说,印第安人的所谓迷信是一种最原始的生态意识和思想,他们对动物的猎杀只是满足自己最基础的生存条件,在主体间性的关系上是和谐的。人类主体和自然主体没有主次和优劣之分,也不能单向度地同化或入侵,而是要在和谐关系中维护人与自然的主体性。在人与自然相处这一方面,欧文认为印第安人是一个典范,而他笔下的印第安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反映了欧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
欧文在《大草原之旅》中对美国早期这片“荒野”的认识,以及早期的生态意识,对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欧文将自己对大自然的内心精神体验与辉煌壮美的西部自然景物描写融为一体,把自己的精神寄托于荒野之上,立足这片新大陆,强调荒野的价值,表现了美国的崇高之美。欧文“躺在开阔天穹之下,吸进的是未经污染的纯洁空气,精神为之大振,心头狂喜”[45],对他来讲能获得自然的审美体验前提是对自然的爱和尊重。这部作品虽然讲述的是作者跟随的一队人参加是狩猎之旅,但是在与自然的接触和体验中,更多表现的是其生态意识。正是由于人类缺乏生态意识,才会肆无忌惮地从大自然掠夺,造成生态失衡,拓荒成为美国生态史上的大事件。欧文借赫里克(Robert Herrick,1591-1674 年,英国诗人)之口表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烈呼吁“但愿没有豺狼狂信嚎,没有猫头鹰厉声尖叫/在你墓地的长空振翅翔翱!/但愿没有狂风暴雨/来蹂躏涤荡/你松软芳香的土地!/只有春天般的/爱使它永远昌盛繁茂”[46]。此外,欧文在《大草原之旅》中强调了生态整体观,即人不是站在自然的对立面,把自然看作仅仅是人类的资源,而是要努力维护自然整体的利益,建立一种和谐﹑稳定﹑完美的关系,把生态整体的利益当作人类最高价值追求。在对待人和动物的关系上,欧文对其遭遇“感同身受”,也体现了生态整体观。动物和人类一样有痛苦和欢悦的“感知力”也具有自己的“固定价值”,也应纳入到道德客体的范畴,人类作为和动物平等的生命个体,无权随意掠夺和剥削动物的生命权和生命价值。总之,欧文在对西部大自然的欣赏和书写过程中,以生态的视角来思考问题,希望能永远保持这片土地的美丽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