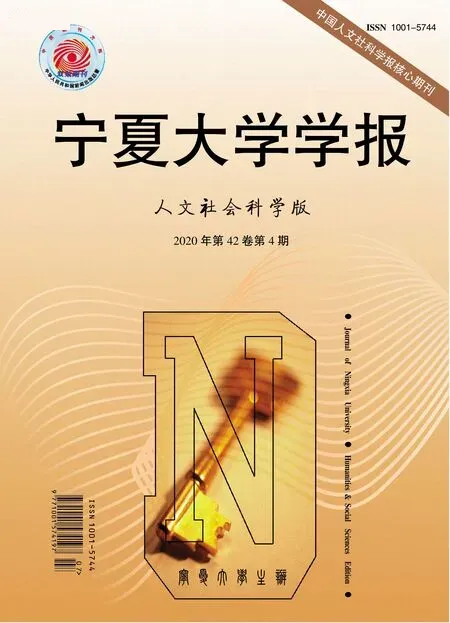论伯夷叔齐《采薇歌》在陇中文学的地位及影响
李政荣
(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 人文教学部,甘肃 定西 743000)
伯夷叔齐《采薇歌》出自《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1]伯夷叔齐的绝命诗《采薇歌》,从真正文人创作的意义上讲,它不仅开启了陇中文学的滥觞,也为中国文学凝成千古不绝的“采薇”情结,更以高洁出世的隐逸情怀成为隐逸诗人的鼻祖。
一 首阳山位置考辨
诗中的“西山”就是陇中的首阳山(今甘肃渭源县境内)。因为伯夷叔齐名闻天下,于是宇中有了五首阳的纷争。伯夷叔齐继周太王古公亶父二子泰伯﹑虞仲之后尘,互让君位,去国离乡,不以富贵为念,已经让人感佩至深。扣马谏君,虽然迂腐,但身上体现出的不畏强权﹑仗义敢言的勇气也让人肃然起敬,就连周武王的军师姜太公也认为他们是“义人”而“扶而去之”。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孔子的评价更让伯夷叔齐声名鹊起。后世文献如《吕氏春秋》《庄子》《孟子》《管子》《列子》中都有二人的影子。太史公将其事迹写入“列传”,更抬高了伯夷叔齐的身价。于是,伯夷叔齐的“粉丝”们都希望两位高贤埋骨己乡,便附会出诸多的首阳山来,为之起冢建祠,祭祀不绝。后人不辨真伪,人云亦云,造成了伯夷叔齐隐居以及埋骨之地的悬案。
《三家注史记·伯夷列传》“首阳”注汇集了五种有关首阳山所在地的主张:
(一)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引用汉代何晏《论语集解》中马融的观点:“首阳山在河东蒲阪县,华山之北,河曲之中。”[2]位于今山西永济市,相传是舜帝的都城。
(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用曹大家(班昭)注《幽通赋》的观点:“夷齐饿于首阳山,在陇西首”[3]。今位于甘肃省渭源县境内。
(三)戴延之《西征记》的观点:“洛阳东北首阳山有夷齐祠。”位于今河南偃师县西北。
(四)《史记正义》引用孟子和许慎的观点,认为首阳山在辽西。孟子云:“夷﹑齐避纣居北海之滨。”《说文》云:“首阳山在辽西。”位于今河北秦皇岛境内。
(五)张守节根据《庄子·让王》对夷齐结局的述评,认为首阳山在岐阳西北的清源县。“又下诗‘登彼西山’,是今清源县首阳山,在岐阳西北,明即夷﹑齐饿死处也”[4]。
对于首阳山确切位置,明代户部主事杨恩作《首阳山辨》,力辟蒲阪之说,而倡陇西之论。论据充分,令人信服。其理由有五:其一,蒲阪南部所谓首阳,经传中只有“雷首”“首山”,而不见“首阳”。《诗经·采苓》有之,但杨恩转引《毛诗通考》则曰:“《采苓》乃《秦风》之首,误收《唐风》之末,篇次相连而错简耳。”[5]而陇西“首阳”出自《尚书·禹贡》,与鸟鼠山东西相望。其二,伯夷叔齐隐居首阳的目的是避周,本当“远引,其心始安”。而蒲阪距离周都丰镐不足四百里,在王畿之内避周,不合情理。而陇西在周孝王封非子于秦时期才隶属周朝版图,是夷齐理想的乐土。其三,《采薇歌》明言“登彼西山兮”,而蒲阪之首阳相对于蒲阪应该是南山,相对于周都丰镐应该是东山,“西山”之说无从说起。而陇西在天地之西,左宗棠引颜师古语亦云:“歌登西山,当以陇西为是”[6]。其四,从“首阳”得名看,应该是居群山之首,最先受阳光照射。北方山脉系出昆仑,陇上诸山居首,终南﹑太白﹑太行﹑中条值胸腹。蒲阪首阳名不副实,陇西首阳才是真正的首阳。其五,夷齐采薇而食。蒲阪首阳不产薇,“每致祭,则取于别所,后来好事者或移植之,亦复不多,地气然耳”。而陇西首阳蕨薇遍满山谷,土人以之代食。以上五条足以证明首阳不在蒲阪,而在陇西。
光绪三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在《陇西首阳山新建圣清庙碑》(按:该文实为左宗棠幕僚施补华代笔。见施补华《泽雅堂文集》卷四)一文中,对杨恩《首阳山辨》给予高度评价:“《巩昌府志·艺文》载明人杨恩《首阳辨》,辨蒲阪﹑陇西首阳是非甚悉。”[7]并指出杨恩文中之不足:“不辨辽西﹑偃师之附会者,又误解《庄子索解》,谓岐山之西别有首阳。”左宗棠在该文中对杨恩文中不足之处做了进一步考辨。此文认为,辽西首阳是人们对《说文解字》“赐”字注解(“赐山在辽西,一曰隅夷”)的附会,且辽西“首阳”距离孤竹国几十里,伯夷叔齐不愿就国君之位而逃避,也应该远离孤竹,中子得国才能踏实。退一步讲,即使不愿远离孤竹,中子岂有眼看着哥哥弟弟被饿死之理。许慎只说“赐山”,并未说“首阳”。可见,辽西首阳明显是附会而来。左文引用孟子“夷齐避纣居北海之滨”之语,否定了偃师首阳之说。偃师离商都朝歌不远,若隐居偃师,那就不是避纣,而是就纣。最终的结论就是:“蒲阪既无首阳,辽西﹑偃师又附会不足据,则首阳实在陇西县。”笔者按:首阳明代属渭源县,清代属陇西县,今又归渭源县。夷齐二子从孤竹出发迤逦向西,投奔文王,文王既逝,阻谏武王不得,东不可归,周不可留,只有继续西遁,远离周疆。所以,夷齐隐居之地只能是今甘肃渭源之首阳。
笔者赞同杨恩﹑左宗棠二人的主张。至于《庄子·让王》中所说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以及《史记正义》作者张守节认为“首阳山在岐阳西北,今清源县”之说,杨﹑左二公尚未考辨。庄子所谓“北”亦即张守节所谓“岐阳西北”,岐阳指岐山之南,周代丰镐二京所在地。清源县就是今天的清徐县,隋开皇十六年建县,属太原市管辖,不在丰镐西北,而在丰镐东北。笔者认为,“清源县”应该为“渭源县”之误。渭源县原名首阳县,因伯夷叔齐采薇首阳山而得名,始建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 年)。西魏文帝大统十七年(551 年)改首阳县为渭源县,渭源县正好位于“岐阳西北”。
其实,不论从首阳山名称演变来看,还是伯夷叔齐隐居的目的和路线来看,首阳山本来面目还是很清楚的。辽西首阳山原名“阳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七“卢龙县”:“阳山,府东南十五里。峰峦高耸,下多溪谷,一作崵山。《说文》以为首阳山也。”[8]蒲阪首阳山,原名“雷首”“首山”。汉代以后的文献中才有了“首阳”之称谓。《汉书·地理志》云:“蒲反,有尧山﹑首山祠。”《汉书·郊祀志》云:“黄帝采首山铜”[9]。杜预《左传注》云:“首山,在河东蒲阪县东南,一名首阳山。”[10]宋代乐史《太平寰宇记》云:“雷首在河东界。此山有九名,谓历山﹑首山……”[11]其注引《嘉庆重修一统志》云:“雷首﹑首阳,本为一山,或称雷首,或称首山,或称首阳。初无一定,大抵山南为阳,以首阳为首山之阳者近是。”[12]河南偃师首阳山本名“首戴”。《水经注·河水注》:“河水南对首阳山。春秋所谓首戴也。”[13]所以,辽西﹑蒲阪﹑偃师三处首阳山本来不叫首阳山,汉代以后才有首阳之称,明显是附会而来的。而陇中渭源县首阳山其名亘古未变,建于汉高祖二年的渭源县原名首阳县,显然因“首阳山”而得名。因此,首阳山只能是陇中的首阳山。伯夷叔齐隐居的动机最初是为“让国”而去国,应当不在本土(辽西)隐居。后来打算投奔周文王而一路向西来到了西岐,正如《吕氏春秋·诚廉》篇所说:“二子西行如周,至于岐阳,则文王已殁矣。”[14]可是到了岐阳,却令二人大失所望。武王正在做取代商纣王的准备工作。让周公召公分别与胶鬲﹑微子结盟,许以高官厚禄。且“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15]宣扬吉梦以蛊惑民众,依仗杀伐来攫取利益,用这种办法取代殷商,不过是以悖乱取代暴虐。于是希望破灭之际,作出“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的判断,“如周”变成了“避周”。如果说首阳山在蒲阪或偃师,那就不是“避周”,而是随周就纣,因为蒲阪﹑偃师在岐阳之东,偃师离殷商朝歌不远,并且去蒲阪或偃师路线与武王伐纣路线相同。因此,首阳山不可能是偃师或蒲阪,伯夷叔齐不可能走回头路,首阳山也只能是陇中的首阳山。
二 “薇”真实身份考辨
《采薇歌》中的“薇”究为何物?这也是历来争议颇多的问题。历考古代文献资料,薇实为五物:除木本的紫薇﹑蔷薇主要用于观赏之外,另有垂水﹑野豌豆﹑蕨菜三种植物可作食材,都称“薇”。《尔雅》云:“薇,垂水,生于水边。”[16]《本草纲目》亦认同这一说法:“薇生水旁,叶似萍,蒸食利人。”[17]段注《说文》持否定意见:“不当以生于水边释之。”[18]而以“野豌豆”释之。《说文》:“薇,菜也。见毛传。似藿。”段注:“谓似豆叶也,陆机《诗疏》曰:‘薇,山菜也,茎叶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园种之以供宗庙祭祀。’项安世曰:‘薇,今之野豌豆也。蜀人谓之大巢菜。按:今四川人掐豆媆尖食之,谓之豌豆颠颠。古之采于山者,野生者也。释草云:垂水。薇之俗名耳。不当以生于水边释之’”。
笔者以为,伯夷叔齐所食既非“垂水”,亦非“野豌豆”,而是蕨菜。《史记正义》:“薇,蕨也。”《滇南本草》:“贯众,即蕨薇菜根。”[19]可见,蕨﹑薇同类。《国语辞典》:“薇:植物名。紫萁科紫萁属,多年生草本。叶由地下根茎丛生,叶上生孢子囊,幼嫩时可供食用,多生于山野向阳草地。”《韵会》:“萁,又菜,似蕨。”[20]可见,“薇”就是蕨中的一种。借用《说文》释词的术语,“蕨”是浑言,“薇”“萁”是析言,都是出产于阴湿山区的一种野菜。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有详细的描绘:“蕨处处山中有之。二三月胜芽,蜷瞌如小儿拳。长则展开如凤尾,高三四尺。其茎嫩时采取,以灰汤煮去涎滑,晒干作蔬,味干滑,亦可醋食。其根紫色,皮内有白粉,取粉柜牧,荡皮作线食,亦色淡紫,而其滑美也。”[21]笔者专程前往首阳山进行实地考察,渭源首阳山夷齐墓前砖坊联语中,题作“白薇”:
满山白薇味压珍馐鱼肉;两堆黄土光高日月星辰。
所谓“白薇”,其实就是白蕨菜。该处蕨菜实有别于他山之蕨,茎部及头部(若小儿握拳状)布满细密的白色茸毛,焯水后呈浅绿色。这种“白薇”在其他地方不多见,他处蕨菜头部多金黄色茸毛,茎部色泽呈现深绿色﹑浅紫色﹑紫色﹑红色不等,而茸毛很少。野豌豆山里到处都有,俗称“野扁豆”,但从未见有人拿它作为食材,倒是常见农民割来喂牲口。蕨菜身价比野扁豆高多了,俗语云:“大豆发芽,蕨菜钩打。”是说大豆发芽的时候,蕨菜也顶着弯弯的头颈长出地面可以采摘了。雨后或早晨,农人纷纷进山采集。采来的蕨菜焯水后或凉拌着吃,或炒肉吃,或晾晒成干菜,随时泡发食用。更有商家大量收购,腌制后发往全国各地出售。首阳山蕨菜早已驰名天下,杨恩《首阳山辨》就有记载:“陇西蕨薇遍满山谷,土人以之代食,且储以御饥。贾人转贩江南京都者,皆陇西产”[22]。
《采薇歌》中的“薇”就是首阳山上的白蕨菜,这首佚诗一旦被司马迁采入《史记》,“蕨薇”“白薇”便成了隐者独善其身的高洁人格的化身,“采薇”便成了隐士不屈于世俗的孤傲的象征,“食薇”也成了文人雅士难得的精神享受。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 《采薇歌》的深远影响
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姓可考的诗人是屈原,伯夷叔齐有名姓可考,生卒年虽不详,但商末周初之人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从西周立国算起,比屈原要早七百多年。伯夷叔齐比中国隐逸诗人之宗公陶渊明要早一千四百多年,比“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早五百多年。单从时间意义上来说,伯夷叔齐应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名姓可考的诗人,更是第一位有名姓可考的隐逸诗人。
《采薇歌》一经产生,便对陇中文学乃至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陇中士人在这里为之立祠修墓,祭祀不绝。宦游来陇的外籍诗人们来首阳山凭吊他们的遗迹,歌咏他们高洁的人格。今天留存的渭源首阳山自金元至明清时期的石碑达十几块,各类文字达十多万字。《莲峰山风土录》(徐化民编著)收录的关于此山的诗﹑文(含碑文)等达66 首(篇)。另外还收录了未收入志书的诗文83 首(篇)目录,两项相加150 首(篇)。金元以前志书无存,不知有多少诗文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现存的诗文创作或考辨首阳山的真伪,或记录首阳山各处建筑的更迭,或凭吊伯夷叔齐千古高风,或记录游览首阳山的旅途见闻感想,它们成为陇中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采薇歌》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赋予“薇”多重的文化意蕴,“薇”成了诗词中常用的意象。这一意象已超越了地域的限制,甚至超越了“薇”的植物学意义,因为它只是任由诗人驱遣的表达自己思想的多种象征的合成体。正如唐代诗人于濆《感怀》所言:“采薇易为山,何必登首阳。濯缨易为水,何必泛沧浪。”[23]“采薇”“濯缨”是灵魂,“首阳”与“沧浪”大可不必介怀。下文将对“薇”的多重文化意蕴一一进行考辨。
(一)政治漩涡中对自由与高洁的向往
佛教传说中有不少王子舍弃王位﹑献身佛法的故事。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其中之一。中国也不乏这种人,不过不是求法,而是舍王位而追求绝对的自由与远离尘俗污染的高洁人格,这种人多为道家中人,以尧舜时期的许由和商初的务光为代表,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秕糠,成了不贪权势者的典范。魏晋时期,政权更替频繁,白色恐怖笼罩朝野,士人生命朝不保夕,于是,避祸全身,向往自由高洁的呼声异常强烈。好多诗人自然喜欢“蕨薇”,向往“采薇”“食薇”。这时“薇”的文化意蕴便是自由与高洁的象征。且看阮籍《咏怀诗十三首》其十一“夷叔采薇,清高远震。齐景千驷,为此埃尘”[24]。拥有千辆战车的齐景公之王业化为尘埃,而伯夷叔齐采薇而食却清高之名千古流传。明末陇西诗人关永杰的《夷齐祠》结句:“词人莫用愁孤竹,镐雒周京久式微”。清代陇西贡生乔大贵的七律《夷齐祠》结句“纷纷戈马同蘼芜,惟有高风不计年”与前面阮籍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竹林七贤”领袖嵇康在《幽愤诗》中倾吐了“有志不就”的内疚,于是也有了采薇之念:“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25]陶渊明《读史九章·夷齐》:“采薇高歌,慨想黄虞。贞风凌俗,爰感懦夫。”前二句概括引述《采薇歌》,后二句高度评价采薇的意义:高风亮节超凡脱俗,对懦夫有着警示和启发意义。陶渊明《拟古诗》:“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26]反映他年轻时期“抚剑独行”的壮游生活中曾以伯夷叔齐的高洁和荆轲刺秦时表现出的豪侠精神自励。
在严酷的政治漩涡中,士人们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于是借助“采薇”“食薇”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高洁人格的追求。
(二)仕途失意者的归旌与执守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非常时期,士人为了远祸全身,特别向往自由高洁而引伯夷叔齐为同调。此后漫长的历史中,士人仕途失意后心灰意冷,也向往采薇,以清贫自守,这应该是魏晋士风的余绪。集南北朝大成的诗人庾信《拟咏怀诗二十七首》第二十一所反映的正是这种仕途失意后的失落与不屈的心境:“倏忽市朝变,苍茫人事非。避谗应采葛,忘情遂食薇。怀愁正摇落,中心怆有违。独怜生意尽,空惊槐树衰。”[27]采葛避谗,食薇忘情,便是生活的缩影。初唐诗人王绩《野望》尾联“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反映的是无人赏识自己,理解自己,那只好“怀采薇”了。晚唐诗人邵谒的《下第有感》形象地反映了科举落第之后的无奈和辛酸,这也是下第举子共同的心声:
古人有遗言,天地如掌阔。我行三十载,青云路未达。尝闻读书者,所贵免征伐。谁知失意时,痛于刃伤骨。身如石上草,根蒂浅难活。人人皆爱春,我独愁花发。如何归故山,相携采薇蕨[28]。
在仕途失意者的眼中心中,“采薇”“食薇”便是归途,是解脱,是执守。
(三)穷愁潦倒﹑生不逢时者的写照
伯夷叔齐采薇而食,最终饿死首阳山,因此“采薇”“食薇”又带上了穷愁潦倒﹑生不逢时的悲愤色彩。陶渊明《悲士不遇赋》:“夷投老以长饥……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对夷齐有才德而无法施展抱负﹑困饿而终的遭遇表现出无限同情。曹植《赠徐干诗》中的“薇”也是穷困的化身:“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薇藿弗充虚,皮褐犹不全。”[29]谢灵运《苦寒行》同样用“薇”这一意象表现穷愁:“樵苏无夙饮,凿冰煮朝餐。悲矣采薇唱,苦哉有余酸。”[30]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漂泊无依,在雪中与猴子争食栗子(《同谷七歌》),也曾在深山采薇:“飘荡兵甲际,几时怀抱宽。汉阳颇宁静,岘首试考槃。当念著皂帽,采薇青云端。”[31]唐代耿《赠韦山人》表现“心事与时违”后“孤云伴采薇”的清贫的隐居生活:“失意成逋客,终年独掩扉。无机狎鸥惯,多病见人稀。流水知行药,孤云伴采薇。空斋莫闲笑,心事与时违。”[32]唐代诗人孟郊潦倒终身,他诗中的“薇”自然带上了苦寒的特征。《感遇》其六:“举才天道亲,首阳谁采薇,去去荒泽远,落日当西归。羲和驻其轮,四海借余晖。极目何萧索,惊风正离披。鸱鸮鸣高树,众鸟相因依。东方有一士,岁莫常苦饥。主人数相问,脉脉今何为。贫贱亦有乐,且愿掩柴扉。”[33]秋风残照,极目萧瑟,鸱鸮悲鸣,众鸟相依。贫贱的“采薇人”紧掩柴门,乐其所乐。在这里,“采薇”“食薇”便是穷愁潦倒,便是生不逢时的写照。
(四)仁孝节义的化身,志士仁人的鞭策
儒家推崇忠孝节义的美德,而这种美德的实现有时候却是以牺牲自我荣华富贵甚至是君王之位为前提的。泰伯虞仲开其端,伯夷叔齐继其踵,他们的实际行动“求仁而得仁”。伯夷不就君位而出走是遵循其父的意志,这是“孝”。叔齐不就君位而出走是遵循了宗法制度中由嫡长子继承君位的传统,这是“悌”。后来他们扣马谏君,指责武王不忠不孝,这又是“忠”。最终采薇而食饿死首阳,这又是“节义”。正如唐代诗人李颀《登首阳山谒夷齐庙》所咏:“寂寞首阳山,白云空复多。苍苔归地骨,皓首采薇歌。毕命无怨色,成仁其若何。”[34]歌颂伯夷叔齐以“仁”立意。明代户部主事陇西人杨恩《夷齐祠》:“千载清风说首阳,首阳原不是周疆。莫疑野史流传误,始信忠名处处芳。”即以“忠”立意歌颂伯夷叔齐的。
明代山阴人何嘉瑶《登首阳山拜二贤祠》抒发了士人只有大节不亏,采薇而食,死亦安心的情怀:“秋不舍我去,乃复在西陲。悠悠千古心,触发渺无涯。适登首阳山,不必辨是非。昔日夷齐者,心安则以为。父子兄弟间,可逃则逃之。君臣不可逃,黄农宁若斯。茫茫宇宙广,一身将安归?作诗意高远,遑问知者谁。死亦安其心,偶然而采薇。旦望莫同语,各成其所宜。若无济世具,则是为夷齐。我来拜其象,出门望寒辉。人生百年内,大节讵可亏?”在这里,“采薇”“食薇”便是仁的体现,更是忠孝节义的象征。
(五)英雄末路时的悲歌
伯夷叔齐“如周”后,发现武王的一系列行为与他们的理想相去甚远,是“以乱易暴”,于是毅然决然“避周”,到不是周彊的首阳山采薇而食,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其行为本身是悲壮苍凉的。这又给穷途末路的英雄以直接的启迪。南宋末年,抗元英雄文天祥从伯夷叔齐身上找到了灵感,宁死也要与元朝抗争到底。于是有了《和夷齐西山歌》二首﹑《为刘定伯索油蕨》《南安军》《答元将》等“采薇”篇什,表现出自己视死如归的信念。“山河千古在,城郭一时非。饿死真吾志,梦中行采薇。”(《南安军》)早已做好了饿死的准备,梦中都在采薇!《答元将》小序已然让人感动不已,其序云:“张元帅谓予:‘国已亡矣,杀身以忠,谁复书之?’予谓:‘商非不亡,夷齐自不食周粟。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张为改容,因成一诗。”元将张弘范劝文天祥投降,认为大宋已亡,即使杀身尽忠也没人将其人其事录入史书。诗人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为例,说明“人臣自尽其心,岂论书与不书”的主张,并写下这首诗。其诗更让人感奋:
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智灭犹吞炭,商亡正采薇。岂因徼后福,其肯蹈危机?万古春秋义,悠悠双泪挥[35]。
诗的大意是说高人的名分好像有亏污,烈士对待死亡如同回家。智伯被害后,刺客豫让为报知遇之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改变声音形貌,矢志复仇;商朝灭亡后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首阳。赴汤蹈火,岂是因为追求一己之名利?回想起《春秋》中维护正义贬斥乱臣贼子的思想,不禁使人肃然起敬。
文天祥的几首“采薇”诗中,“薇”这一意象带上了悲壮苍凉的色彩,“采薇”成了英雄末路的慷慨悲歌。
(六)高蹈世外者的乐园
有些诗人生活比较优裕,或者受到佛老思想的影响,向往出世,于是把目光投向了“蕨薇”,向往“采薇”“食薇”,描绘出一幅幅人间仙境,俨然是高蹈世外者的乐园。在这里,“薇”便是隐士的招牌。且看李白《金门答苏秀才》:“缘溪见绿筱,隔岫窥红蕖。采薇行笑歌,眷我情何已。月出石镜间,松鸣风琴里。得心自虚妙,外物空颓靡。身世如两忘,从君老烟水。”[36]白天,沿着清溪可以看到碧绿的箭竹,隔着岩岫能够窥见鲜红的荷花。主人公苏秀才一边采薇,一边或歌或笑,眷念着他,不可以已。夜间,月出石如镜,风入松若琴。心里明白了虚无的妙理,外物的牵累便显得很无力。在这首诗中,诗人把采薇歌笑的主人公苏秀才置身于如同仙境一般的背景下,表现出对道家生活理想的认同和追求,洞彻虚无,身世两忘,抛却物累,让身心作逍遥之游。再如白居易《出山吟》也表现出与李白相近的情调:“朝咏游仙诗,暮歌采薇曲。卧云坐白石,山中十五宿。行随出洞水,回别缘岩竹。早晚重来游,心期瑶草绿。”[37]山中十五日,朝朝暮暮或咏游仙诗,或歌采薇曲。或卧白云里,或坐白石上。去时随着出洞之水,回归时依依不舍地与岩边绿竹作别。早晚还想着重游此地,心里牵挂着仙花仙草的长势。这里,“薇”成了诗人闲适心境的点缀。
伯夷叔齐千古一饿,千古惊艳。“顽懦于今齐仰止,清风百代受陶甄”。此后,《采薇歌》中的“薇”成了古诗词中常见的兼备众多文化意蕴的意象,融入了以《诗经·小雅·采薇》为代表的反映战争苦难和以《诗经·召南·草虫》为代表的表现爱情的意象群,极大地丰富了“薇”的文化意蕴,为陇中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注入了取之不尽的文化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