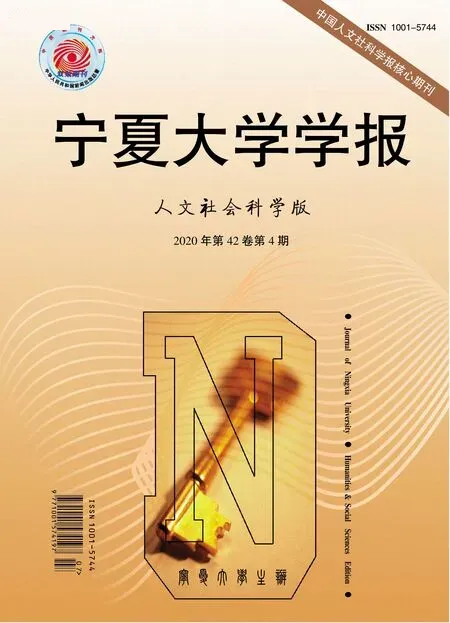情本体与向“空”而“有”:《红楼梦》价值建构方式探析
杨 帆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以“情”为本体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基本特征。“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1]。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这句话典型地揭示了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亦即“情理结构”)特点。社会规则的建立要从情感出发,但此处的“情”是指感官欲求与理性理智融凝而成的复合性情感:向原初动物性欲望中积淀起符合人类总体意识的“理”,对“理”进行内在体认,最终化“理”为“情”,理性被感性充分地接纳和吸收,不断生成人性心理中的高层次情感。这一高层次情感由于受到了理性的融入和提升,所以“近义”。情本体与中国文化“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方式密切相关,而这一建立价值的方式又典型地体现在了集传统文化之大成的清代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中。
西汉武帝时期正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本体化”的时代[2]。另外,关于“政治本体”与“文化本体”,笔者在此处略作说明。“政治本体”即以政治为本体,是一种以现实政治作为人生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作为行事准则与精神归宿的生存状态。而现实政治能够给人强大的信心,使人以政治功业为人生基点﹑行为目标和价值归宿的历史时期就是“政治本体化”时代。西汉前期,大一统政权建立之后,武帝刘彻第一次通过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将具有一定开放性﹑灵活性的儒家思想与稳固的现实政治秩序相结合,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政治本体化”时代。而到了大一统政权衰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乱离无状,礼义道德沦丧,儒家思想已经异化为徒具等级名分的腐朽意识形态,故朝命日短,篡弑频仍,现实政治秩序已无法为士人提供实现价值的机会和条件,“政治本体”由此被解构。直至初盛唐时期,强盛的国力﹑统一的政权﹑合理的现实秩序重新实现,尤其是唐代统治者对思想文化采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使得文人士子重新对现实政治充满了信心,相信功业可以实现一切价值,因此中国社会重新进入了“政治本体化”时代,“政治本体”的合理性也得到了最充分的释放。而从中唐开始,传统社会的时代精神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安史之乱”后,士人不再自觉地将自身的全部生命都纳入政治功业的范畴中,而是开始质疑政治功业与天道的关系,对“政治本体”的态度由拜服转向怀疑,从而开始在以“天道”为最高范畴的传统文化整体的层面上重新探求自身的价值归属。这种探求在后世最重要的表现可分为“主情”与“主理”两端。“主情”的一端主要体现在缘情之词以及曲尽人情的戏曲﹑小说的兴盛,向世俗感性生活中寻找归属;“主理”的一端则大体表现为宋明理学的诞生与发展,希望在道德理性中安身立命。由此,文人士大夫的关注点实现了由“天”向“人”的转变,中国传统社会开始进入后期,进入了“文化本体”的时代(所谓“文化本体”,其本质就是不断地进行心灵的追询,以追询本身为本体。不再将人生的全部意义寄托于现实政治,而是试图在心灵的追询中建立起全新的价值归宿与精神依托)。人作为“类”的理性已经觉醒,现实政治成为士人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精神归宿,汉大赋就是这种理性精神的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朝政的腐败﹑政治伦理道德的沦丧导致儒家意识形态失去了维系人心的作用,人作为“类”的感性的一面得到了觉醒[3],在共同的社会理性之外还要求有自身一定程度的﹑审美化的感性生活。志怪小说﹑志人小说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摆脱政治功业层面﹑满足自身无关功利的审美需求的结果。初﹑盛唐时代则是传统社会“政治本体”化的高峰期,思想﹑文化﹑政治秩序均呈现相对开放﹑融通而富有活力的状态,“粗陈梗概”的笔记发展为“始有意为小说”的传奇,情节结构更加完备,人物更为丰满生动,并且反映出一些社会现象。中唐以降,急剧衰落的国运使“政治本体”再也不能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据,人们重新思索感性生活与生命本身,逐渐开始探求“以文化为本体”的生存方式。唐传奇也于这一时期走向繁荣。宋元时期,话本小说的兴盛满足了市民阶层日常娱乐的需要,小说和戏曲作为民间文化的代表迎合了平民的欣赏趣味,反映了民众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憧憬。但无论是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唐代传奇还是宋元话本,都只是世俗感性生活的直观表现,民间文学虽然丰富鲜活,具有很大开放性,但却缺少理性精神的积淀,无法成为士人生命价值的依托。若不在小说中注入理性沉思,将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困惑﹑对伦理规范﹑价值观念的思索与叩问化入其中,小说必定只能流于稗官小道﹑街头巷语,没有自己独立的灵魂,无法与正统诗文相比。直到元末明初由文人加工而成﹑具有深厚悲剧意蕴的两部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出现,小说才得以像诗文一样,承担起探询“文化本体”的使命,在天道与人事之间展开心灵的追索。《三国演义》在仁政理想的幻灭中展现着历史与道德的背离,《水浒传》则通过表现“替天行道”的大忠大义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小忠小义之间的错位与迷误,凸显出真正的社会理想与现实封建政治伦理之间的鸿沟[4]。
到了明嘉靖﹑万历时期,以李贽﹑汤显祖等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在陆王心学尤其是心学激进派追求独立自主的人格的影响下,掀起了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极力彰显人的主体意识,强调冲破社会共同理性的个体感性,重视个人“绝假纯真”的自由情感与独特“性灵”的抒发。小说在明初已经融入了文人的理性精神,又恰逢个体感性觉醒的时代之潮,再加上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商业的发达,觉醒的人欲极易顺应本能的感官享受,沉溺于金钱与物质的满足。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诞生,作家以高度的理性审视着这场人欲横流的丑剧,对人性已经得到启蒙﹑却缺乏相应价值信仰的社会中的众生实相予以冷静的解剖,融合了民间关于色空﹑果报﹑神佛﹑迷信等种种观念,在写尽了“色”的丑恶之后归结于“空”的渊没。
历史发展至清代,传统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文化信仰中的合理性因素都已经充分释放,士人对“文化本体”的探询也显示出融会贯通﹑回顾总结的倾向。已经具有了强烈主体意识﹑感性和理性都已高度成熟的士人,便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对封建社会中各种不合理的制度﹑观念甚至文化本身进行质疑。《聊斋志异》以贯通三界的永恒之情对封建纲常进行否弃,《儒林外史》则在对士人整体生存意义的追问中向科举制度及其造成的人性异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但从小说在明代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起,任何一部小说对封建文化的质疑都不过是各执一隅,仅仅局限于生活的某一个层面,且常常达不到文化的高度,甚至根本达不到封建意识形态的高度,只是对传统社会的某些现实秩序﹑制度﹑实施方法予以质疑,甚至只是要求改良。而“超越了历史﹑道德的层面”,能够从“深刻的文化高度”[5]上对封建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价值评判体系进行彻底反思的,只有随即出现的《红楼梦》。
但《红楼梦》的价值还远不止于此。“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6](第二十二回),除了对各种僵化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予以蔑视和舍弃,进而对传统社会整体的价值评判系统进行怀疑以外,更能够试图站在“方外”来静观“人间”,感应着生命本体处的价值空没,进而探询人世的根本。在这方面,《金瓶梅》似乎已露端倪,但《金瓶梅》仍是拘囿于社会与人性的视角,而未能超越道德的范畴,达至哲学与“存在”的层面。况且《金瓶梅》仅归于冰冷的“色极为空”意识与庸简的因果循环,缺少生命的质感与应有的温度;《红楼梦》却实现了“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以“情”作为超越有限,超越经验与虚无的永恒本体。
一 《红楼梦》对异化价值评判标准的质疑与对生命本体的探询
第十九回,宝玉在袭人家见到袭人的一个“两姨妹子”,回到怡红院谈及此人便赞叹起来。己卯本对此有一段夹评:
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凡),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7]。
脂评此言正契合了原书第二回提出的“正邪两赋”说。“正邪两赋”说认为,天地间“清明灵秀”之正气与“残忍乖僻”[8]之邪气偶遇搏击之后自成一种气,秉此气而生者,既非大仁亦非大恶,生于权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生于诗书寒族则为逸士高人,生于薄祚寒门必为奇优名倡。纵观后文作者所列之属于此类之人,大多具有以下特征:不但不能以大仁大恶观念简单论之,更游离于封建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基本不受封建伦理的匡束。且大多以生命之情为本,王戎的“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9](《世说新语·伤逝》)仿佛正可为此类人作一注脚。而宝玉则既属于作者所列“正邪两赋”这一类的人物,又对这些人物有所超越。超越之处一方面在于宝玉的“情”是以生命本体之情为底色,同时融入了强烈主体意识的爱情;另一方面,则在于不仅不受封建伦理的规束,更彻底质疑封建意识形态和僵固的价值权威。
不少研究者都已经指出宝玉对传统社会“文死谏,武死战”的僵化思想的厌恶实脱胎于李贽《焚书》卷一《答耿司寇》:“夫君犹龙也,下有逆鳞,犯者必死,然而以死谏者相踵也。何也?死而博死谏之名,则志士亦愿为之,况未必死而遂有巨福耶?避害之心不足以胜其名利之心,以故犯害而不顾,况无其害而且有大利乎!”[10]“死谏”“死战”的官员未必都是为博名利,但确定无疑的是《红楼梦》自觉接受了明中叶以来以个体感性心灵的自由对抗传统的社会理性的启蒙思潮,对已趋向禁锢﹑不符合大多数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传统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反叛。宝玉厌弃八股,不通举业,但却空灵隽逸,诗思敏捷。种种“行为偏僻性乖张”[11](第三回)的表现本质上都是对压制自由性灵的不合理观念的否弃,同时蕴含着对新的价值观念的追求。但《红楼梦》更深层的意蕴在于,不仅对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和伦理纲常予以怀疑,更对世俗价值评判体系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力图破解人生的价值困惑。第一回甄士隐对《好了歌》注解道: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12]
人一生下来便被毫无选择地抛在空荡荡的世界上,无所凭依。面向永恒的宇宙,人生却如白驹过隙,短暂而不可把握,生命的荒诞与虚空因此而显现。为了填补虚空﹑消解荒诞,芸芸众生纷纷选择在功名利禄中满足自我,在纵情声色中悦己行乐。功业成就﹑家族地位﹑娇妻美妾,始终是世俗社会衡量人们的价值标准。但作者对此种僵化标准的质疑却如冷水浇背,令人陡然一惊:“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一语惊破众生迷梦,现实世界里富贵名利的获得要依靠外在的社会秩序和各种偶然条件,往往充满不确定性,既然终究有待于外界,那么只要得到便可能失去,人生也因此变得无常。况且,还有那永恒的终结作为一种无定的必然,时刻提示着“存在”的有限。所以,功勋爵禄﹑玉脂娇娃不过是暂时附着于人生的外相,并非生命的本真。《好了歌注》正是要警示人们勿认他乡为故乡,不应拘执于种种非本真的荣名利欲,而应该去追询真正的价值,探求和建构真正内在于人的“精神家园”。戚序本第五回回前评曰:“万种豪华原是幻,何尝造孽,何是风流。曲终人散有谁留,为甚营求,只爱蝇头……”[13]王希廉《红楼梦回评》中对第十七回宝玉初见大观园省亲牌坊之事论曰:“玉石牌坊宝玉心中忽若见过,直射第五回梦中所见太虚幻境牌坊。省亲不过是一时热闹,与幻境何殊?”[14]都可谓了悟作者意旨。第一回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15],世人以假为真,而此书正是要警醒世人勿向“假”中求“真”,立意是与世俗价值体系相背离的,不一定能为庸常之辈所理解,故云“荒唐言”“辛酸泪”。
作者以幻梦之心对世间万象进行置换,对庸俗而异化的价值标准进行了否弃,拨开价值的迷雾,以一双慧眼洞彻幽微,穿透纷繁迷离的现象界,看到了背后的本体之“空”。第十二回跛足道人带来的风月宝鉴“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16],己卯本夹评曰:“言此书原系空虚幻设”[17]。而当贾瑞将风月宝鉴向反面一照时,原来的凤姐立即变为一个骷髅:“所谓‘好知青冢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是也”[18](己卯夹),“美人即骷髅,骷髅即美人。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19](王希廉《红楼梦回评》)。在超越有限﹑窥破因果﹑直指本体的探询面前,再沉重的历史与人事也变得虚空而荒诞,饱经沧桑浮沉的生命历程终究化为幻梦,只得以苍凉的沉默感应着终极的“存在”。全书开篇即云“曾历过一番梦幻”,“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20]。《红楼梦》的确是基于“梦”“幻”“虚”“空”来立意的,戚蓼生《石头记序》即曰:“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21],但其内在本旨却绝非简单停留在宣扬“色空”“盛衰循环”“缘起缘灭”的层面,而是对传统的“真幻”说﹑“色空”说进行超越,对“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进行彻底追问,对世相人生进行本体性的探询。
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一节,宝玉与宝钗互看对方的配饰,写到通灵宝玉与金锁各自的外形时,书中对通灵宝玉的大小作了一番解释:“今亦按图画于后。但其真体最小……等语之谤。”[22]甲戌本眉评云:
又忽作此数语,以幻弄成真,以真弄成幻,真真假假,恣意游戏于笔墨之中……[23]
脂评此处所言之“以幻弄成真,以真弄成幻”并不仅仅指通灵宝玉的真幻,更是在询问“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孰真孰幻。戚序本本回回后评曰:“一是先天衔来之玉,一是后天造就之金”[24]。先天衔来之玉其实是一块本真的顽石,而后天造就之金却是为了非本真的机心﹑荣耀,经人为刻镂而成。“木石前盟”以本真的情感为基础,这种情感源于前世的回忆,正如骆冬青先生指出的那样,带有某种先验的色彩:“把爱说成是一个先天就具有的”“一个终极的﹑永恒的﹑谁都想靠近﹑却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点”[25],几乎本真到了超越此在这一经验世界的程度;“金玉良缘”则完完全全是尘俗中人出于利益欲望的驱使而编造的精美谎言。但世人却以虚幻的“金玉良缘”为真,力促宝玉﹑宝钗结缡;而偏以本真的“木石姻缘”为幻,致使宝﹑黛爱情最终夭亡。
“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亲就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彩,堪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26](第八回)本真的顽石自从坠入尘网,幻化为光鲜的“宝玉”,便失去了真正的幽灵境界,最终运败时乖,繁华破灭,金玉之缘终成一曲挽歌。作者以“白骨如山忘姓氏”有力地撕开了赤裸裸的生存真相:如今只见白骨累累,姓甚名谁早已被时间湮没,也毫无意义,无非就是曾经富贵的金娃玉郎罢了。
因此,曹雪芹在阅尽世间诸色﹑历尽风雨阴晴之后,以一支如椽诗笔,在亦梦亦醒之际,深度叩问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幻中寻真,无中生有,在非本真的红尘中找寻本真本己,在茫茫众生相中追询着深入本体的价值。
二 向“空”而“有”——以本体之情为归宿的价值建构方式
第十三回秦可卿将死时向凤姐托梦,谓贾府眼前的繁盛“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27]。对此,蒙府本有一段侧评:
“瞬息繁华,一时欢乐”二语,可共天下有志事业功名者同来一哭。但天生人非无所为,遇机会成事业,留名于后世者,亦必有奇传奇遇,方能成不世之功。此亦皆苍天暗中扶助,虽有波澜,而无甚害,反觉其铮铮有声。其不成也,亦由天命。其奸人倾险之计,亦非天命不能行。其繁华欢乐,亦自天命。人于其间,知天命而存好生之心,尽己力以周旋其间,不计其功之成〈于〉[与]否,所谓心安而理尽,又何患乎一时瞬息。随缘遇缘,乌乎不可?[28]
生命有限,天地永恒,即使再辉煌的功业﹑再伟大的人物也终将淹没在宇宙的洪流中。跟永恒的自然相比,世间的一切都不过是“瞬息繁华,一时欢乐”,最终都会归于虚无,这就是无情的人生实相,是关乎生命与价值的最彻底的悲剧意识。然而,“天生人非无所为”,人并不会因最终的空没与虚无就自甘毁灭,而是为了人类整体能够更好地存在与发展,面向本体性的虚空凸显人自身的深情,卓然挺立起自身的价值。此之谓“向‘空’而‘有’”,向人生本体的空没处建立起人之为人的价值与意义,向悲剧性的现实赋予无限的深情与乐感。至于“遇机会成事业,留名于后世者,亦必有奇传奇遇,方能成不世之功”,这是说外在价值的建立除了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具体作为外,还依赖于现实的社会秩序和一定的偶然性。“此亦皆苍天暗中扶助,虽有波澜,而无甚害,反觉其铮铮有声”,若功业有成,则是人类总体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实中的“人道”与形而上的“天道”冥然合一的体现;“其不成也,亦由天命”,若功业无成,也是社会的现实状态,说明人类总体的必然在某些有限的历史阶段﹑在每一个体命运中不一定都能有所体现。同时,功业的无成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导致人体味悲剧意识的现实动因,正是触发悲剧意识的契机。而“知天命而存好生之心,尽己力以周旋其间,不计其功之成〈于〉[与]否,所谓心安而理尽,又何患乎一时瞬息”,若是真正去体认天道的必然,并将这种必然完全内化为了生命之情,便可以摆脱外在的依待而以心理为本体,将价值的归宿由外在功业转入自己的内心,以心灵的自足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此之谓“心安而理尽”,由对功利的追求转向审美的人生境界,自可无待于功成与否,不拘系于是非穷达,从而完成了对“瞬息繁华,一时欢乐”的悲剧真相的审美超越!
因此,尽管《红楼梦》写尽了贵族家庭的没落与凄凉,对众生实相进行了本体性的探求,对始于荒唐﹑归于虚幻的人生历程进行了无情的提撕,但却绝不指向价值的覆灭与生命的荒芜,而是以向“空”而“有”的方式,面对空没的深渊“悲极而乐”地积淀起本真的情感,呼唤着美好的青春与人性。第五回“太虚幻境”中有一副对联:“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29]。对于“幽微灵秀地”,甲戌本有一条侧评:“女儿之心,女儿之境”[30]。在《红楼梦》中,女儿是美好的人情﹑人性的象征,是本真情感的象征,脂评确为深得作者文心。但另一关键在于,“幽微灵秀地”只是幻境,“无可奈何天”才是现实。对于整副对联亦有一评:
两句尽矣。撰通部大书不难,最难是此等处,可知皆从无可奈何而有[31]。
这更是明确点出了全书“向‘空’而‘有’”的价值指向。尘世之天无可奈何,人间尽是伤怀日,生命到头终归寂寥,但作者偏要从“无可奈何”之“空”中写出这一“通部大书”来,写出许多纯美的女儿之情来,写出那即世间而超世间﹑具有形上价值的“幽微灵秀地”来。开篇所言“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32],又说“使闺阁昭传”[33],亦表明了“闺阁”所象征的应然﹑本真的情感才是最终的价值所在。甲戌本凡例有一首诗: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34]。
为蜗角虚名奔波的人生是那样的浮华不实,汲汲于荣华富贵并非人生的应然状态,诗人通过对庸俗﹑虚浮的不合理生存状态的否弃来追问生存的终极意义。更值得深思的是,诗人在此并非仅仅否定声色名利等非本真之物,而是认为“古今”都如“一梦”中,历史都是虚无的,尽显荒唐而已。这就将对生命价值的追问推到了极致,并以此观照历史,撕开了历史与人生的悲剧真相。真相虽然是悲剧性的,但诗人却偏偏面向这悲剧人生“抱恨”“说痴”。情极生“恨”,情极为“痴”,“痴”正是对涵容了历史合理性因素的应然情感的坚持。作者向“空”生“情”,以本真情感替代了非本真的利禄勋誉,作为心灵最后的归宿。而此“情”也并非拘囿于尘俗之欲的狭小情感。第一回绛珠草与神瑛侍者的神话,甲戌本亦有一条眉评:
以顽石草木为偶,实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始结此木石因果,以泄胸中悒郁[35]。
所谓的“风月波澜”“情缘滋味”乃世俗风月﹑世俗情缘也,比如为了家族利益而打造的“金玉良缘”,为了感官享受而产生的动物性情欲等等。作者对此种沉沦于名利欲求的“情缘”进行了本体性的质疑与反思,看清了其最终带来的“无可如何”的价值空没,故而才以本真而超越的“木石情缘”为价值归宿。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妙玉将宝钗﹑黛玉二人拉进房中吃体己茶,用“瓟斝”与“点犀”各斟了一杯分别奉与宝钗和黛玉。宝钗的“”上有一行小字“宋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36],实是作者有意设计的虚幻之笔,表明“”本身就非实存之物。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宝钗的金玉良缘恰如其“”,虽经人力结成但终归一梦,虽真犹假;黛玉的木石姻缘亦如其“点犀乔”,虽未能落实但终与宝玉“心有灵犀一点通”,虽假犹真。
[红楼梦引子]云:“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37](第五回)“风月情浓”只是个体日常范围内狭小的儿女私情,甚至流于声色情欲;而“谁为情种”的“情”,指的却是生命意义上的一种本体性的深情。因此,作者以为价值归宿的“情”是一种本体之情,来源于现象却又超越了现象界的时空﹑生死和一切因果,来源于有限却又能够通向无限与永恒。“借幻说法,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笔,而情里偏成痴幻。试问君家识得否,色空空色两无干。”[38](戚序本第一回回后评)书中有不少情节涉及“色空”,但《红楼梦》的意义却绝不在于色空,而在于以“幻”传“情”,在空色相杂﹑有无相生的世界,对本体之“情”进行着永恒的追寻与向往。
三 从《红楼梦》诗词看宝玉与黛玉的价值归宿——以本体之情为基础的个体爱情
二知道人《红楼梦说梦》云:“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曹雪芹之孤愤,假儿女以发之;同是一把酸辛泪也。”[39]认为《聊斋志异》《水浒传》与《红楼梦》都是各自的作者为了抒发各自的“孤愤”而作的。这种看法实源自屈原的“发愤以抒情”:“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40](《九章·惜诵》)后代学者如司马迁﹑王逸﹑朱熹等大多将此句理解为屈原为了使心中郁结的愤恨得到宣泄,故而作此辞赋:“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懑以抒其情”[41]。但实际上这并非屈原作品的真正精神。屈原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当理想与现实不能统一时所产生的强烈的悲剧感,将文学与人的生命统一起来”,“将文学看成是对现实的审美超越,看成是文化理想的显现”[42]。《红楼梦》的创作亦同此理,境遍佛声在《读红楼札记》中言:“长沙吊屈,吾读《红楼》,为古今人才痛哭而不能已。”[43]尤其作者假林黛玉之笔而作的许多诗词,并非仅为抒发黛玉的一己之痛,更是作者在毕生经历中积淀而成的本真的﹑应然的﹑理想的因素的体现。《葬花吟》就是黛玉的“天问”。在黛玉这里,诗与生命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诗不是茶饭之余用以消遣时光﹑点缀风雅的装饰性文字,也并非用来宣扬教化﹑劝惩垂诫的益补人心之语,而是人本真生命的外化形式,诗心与人心已经达至冥然相契的状态。黛玉以诗的形式表现了对历史合理性因素与情感原则的坚持,对心灵寓所﹑价值归宿的追询过程。
《葬花吟》《桃花行》直接继承唐代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在“天人同构”意识的观照下,赋予“闺中女儿”青春的生命以天然的合法性:“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晨妆懒。帘外桃花帘内人,人与桃花隔不远”,“桃花帘外开仍旧,帘中人比桃花瘦。花解怜人花也愁,隔帘消息风吹透”[44],花与人异质而同构,人事活动完全合德于自然,因此具有永恒的意味。“胭脂鲜艳何相类,花之颜色人之泪;若将人泪比桃花,泪自长流花自媚”[45],眼泪是情感的象征,诗作由生命的本真过渡到情感的本真,由人事活动的天然合法过渡到情感的天然合法。最后以泪水的干涸象征着生命的消逝,本体性的悲剧意识进而凸显:“泪眼观花泪易干,泪干春尽花憔悴。憔悴花遮憔悴人,花飞人倦易黄昏。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46]花朵与春天终将化作一场虚无,何处才是人真正的立足之境﹑真正的精神家园?“天尽头,何处有香丘?”[47]“香丘”既是花的归宿,又代表着人最终的价值归宿。作者以追问“香丘何处”的方式,通过抒写黛玉对心灵栖息地与安身之处的不断追寻,表现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对人生此在终极归宿的询问。宝玉与黛玉同属“无故寻愁觅恨”[48](第三回)的一类人物,因此才有了听见《葬花吟》之后“心碎肠断”的一段大悲伤:
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49]。(第二十八回)
“这段悲伤”本质上就是对“存在”真相的悲伤,就是生命无意义﹑价值无所归的悲伤。宝玉搬进大观园后虽然快乐满足,但也时常“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50](第二十三回),其实就是追询价值而无果的外在表现;黛玉“好端端的不知为了什么,常常的便自泪道不干的”[51](第二十七回),与宝玉也是一样,都是心灵彷徨无依﹑价值没有着落的缘故。第二十八回宝玉唱的《红豆曲》中“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展不开的眉头,捱不明的更漏”[52],以及其“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的性格特征,也都是求索价值而未得的人生状态,是无法解决生命有限﹑价值无解的永恒之愁的心理状态。而面对这种理性思考已经无法解决的本体困境,作者应对的方式是情感超越:“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53](第三十八回)。对于全书大局来说,这种“情”是本体意义上的生命情感,如前所讲;对于宝﹑黛二人来说,“情”则是以生命本体之情为基础的﹑具有强烈主体意识的爱情。“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54],“相思血泪”与“春柳春花”同列并举,彰显了宝黛爱情的天然合法性;而“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绿水悠悠”[55]则将这种个体爱情提升到了与自然等同的高度,将一己之愁深化至永恒宇宙的本体性层面。而这种“情”由于经过了生命悲剧意识与价值悲剧意识的理性追索,因此具有了合理性和积极的精神指向,理性精神便逐渐积淀于情感之中,情中含理,又化理为情,最后归于超理性﹑超道德的高层情感,超越原初的物欲﹑情欲与功利,归于情理相融的审美境界。
因此,宝﹑黛爱情便具有了“立心”“立命”的性质,便是“人活着”的依据,从而与书中其他动物性成分较重的风月之情﹑寄生或依附于封建伦理纲常而存在的感情,或是遵循现实利益原则的感情区别开来。第七十八回贾母对宝玉“和丫头们好”并非“人大心大,知道男女的事了”感到十分“难懂”[56]。因为宝玉“和丫头们好”并非出于本能的情欲,而是将女儿看作本真情感的象征来守护。此“情”作为根本性的价值归属,自可安身立命。因此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辞试忙玉”一节宝玉所发的疯,实际上是失去价值归宿的本体之悲。宝玉将自己与黛玉的爱情当作人生的价值归宿,他是要在这种爱情中寻找终极关怀的。
综上所述,《红楼梦》站在哲学的高度,突破僵化价值标准的桎梏,面向寥落的生命本体怀有沉郁的情感,以“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方式对来自文化深处的悲剧意识予以弥合,在超功利的审美人生境界中构建心灵的归宿与精神的家园,深度契合了我们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三生石上旧精魂”(甲戌本第一回侧评),通部大书“全用幻”,然则“情之至,莫如此”(甲戌本第一回眉评)[57]。事虽幻,情却真。《红楼梦》超越了内容的真实直指艺术的真实,超越了历史的真实直指文化的真实﹑情感的真实。虽然“万境都如梦境看”[58],但却有一颗炽热的灵魂永远面向梦境而跳动,驰骋于茫茫大地之上。她在造化的游戏中,坚持着人类感性生命的应然,并以此启示世人寻找价值的真谛,实现传统文化的自新,不断推进着民族的文化传承与精神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