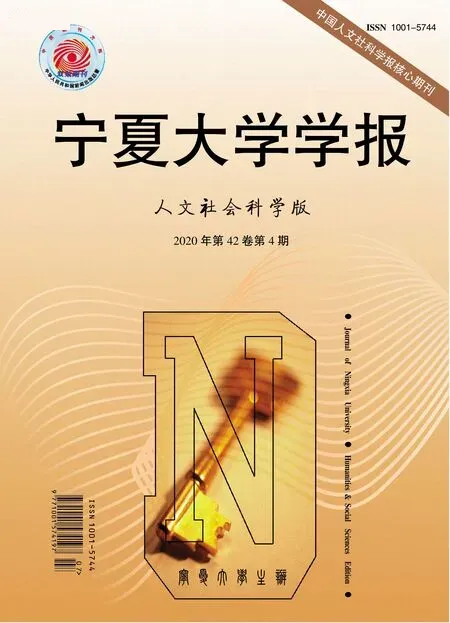唐宋八大家论说文中的句法修辞研究
胡 静
(西安理工大学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西安 710054)
论说文章出现以后,论说文章修辞相伴而生,并大放异彩。从先秦诸子百家政治色彩浓厚的论辩文章,到秦汉时期以政论为主的论说杂文,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议论横生的政论文,直到唐宋时期论说文章又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论政﹑论兵﹑讲学﹑明道等,成为文章的重要内容,不仅为文议论﹑诗也议论﹑词也议论﹑赋也议论。唐宋时期涌现了大批古文家,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论说文章。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论说文”,是在形式上依古代论说文分类原则为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文体形式:“论”体(包括“策”体文);“说”体;“议”体;“原”体;“辩”(“辨”)体;“问”“对”“答”等杂体。唐宋八大家的论说文数量较多﹑体式纷杂,但他们在各个题材中创作出传世名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散文构思精巧﹑手法多变。唐宋八大家在论说文中遣词造句﹑凝练自然,发扬了古人讲究“辞令”﹑重视“修辞”的传统。他们在论说文章中讲究修辞,通过运用各种修辞手法,使语言形象生动,有文采,从而使文章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产生更大地宣传效果。
句法修辞在言语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陶明濬在《诗说杂记》中指出:“句法犹为诗篇之要素”。唐宋八大家很重视文句的修辞锤炼,他们“从切情﹑切境﹑切题出发,对诗文语句反复锤炼﹑推敲﹑修改,以达到音律和谐,句式优美,简洁精练,获得最佳表达效果”[1]。唐宋八大家论说散文中句法修辞主要表现在句式的选择和锤炼上,他们为求文章深刻表情达意,常常运用辩证的艺术技巧,进行各类句式的精心选择与反复锤炼,使论说散文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语言面貌。以下从句式选择修辞和句法变异修辞两个方面,考察唐宋八大家的语言表达活动。
一 句式选择修辞
所谓句式,就是句子的结构形式。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句式来表达,使用不同的句式,其表达效果是不太相同的。汉语中有着众多的同义句式,有长句和短句﹑整句和散句﹑肯定句和否定句﹑主动句和被动句﹑陈述句和疑问句﹑设问句和反问句,等等。这些丰富多彩的句式,为我们选择﹑运用各种句式,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唐宋八大家很注意句式的选择和运用,读他们的论说文章,可以发现,这些文章都非常注意句式的选择和变化,各种句式交错使用,灵活搭配,从而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一)长句与短句的选择和锤炼
所谓长句是指词语较多﹑结构比较复杂﹑容量比较大﹑形体较长的句子。长句的特点是结构繁复﹑内涵丰富,表意容量大,表达精确﹑细致﹑周密,语意贯通﹑气势畅达﹑风格稳重[2]。所谓短句是指词语少,形体较短,结构比较简单,句容量比较简洁明快的句子。短句的特点是“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结构简明,节奏紧凑,能够有效地表达强烈﹑激昂的感情”[3]。如明代学者王世贞所说:“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4]长句短句各有其表情达意的特殊修辞功能。长句在句法结构上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容纳的句式内容更为丰富,可表现的情感更为细腻严密;短句在句法结构上比较简单,可容纳的句式内容较为简洁,可表现的情感更为快速高昂。“句子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基本单位,句子的长短取决于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当然也和作者的个性﹑气质相关。一般地说,长句不仅能够传达更多的信息,也宜于表达丰富强烈的感情,同时又可以形成一种富于动感和冲击力的气势。”[5]
唐宋八大家擅长使用长句,他们可以说是驱遣长句议论﹑抒情﹑写意的高手。他们经常运用一些长句,来表达其强烈的感情。我们的古人也早已注意到这种语言现象,宋代学者李涂分析指出:“韩退之三五十句作一句下。苏子瞻亦然。初不难学,但长句中转得意去便是好文字,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说得一句事则冗矣。”[6]韩文长句的使用大大加强了语势,增强了表现力和感染力,是韩愈表达强烈感情时常用的手法之一。他在《原道》开篇写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已乎,无待于外之谓德。”[7]作者在此构造一长复句,对作为孔孟学说核心“仁”“义”“道”“德”的思想内涵一一进行阐扬,从正面树立起圣人之道。这四处短句构成的长复句一气贯之,形成了文章强烈的感染力和旺盛的气势,也鲜明地表现了韩文雄奇奔放﹑“浑浩流转”的艺术风格。苏轼虽以写长句见长,但他也写了很多以短句为主的散文。比如,《梁贾说》描写梁贾回到家乡时的各种表现,“馈之浆,则愤不饮。举案而饲之,则愤不食。与之语,则向墙而欷歔。披巾栉而视之,则唾而不顾。”[8]这几句话把一个背信弃义之人刻画得活灵活现,令人生厌。这里语句短小﹑结构简单,起到了明快活泼﹑简捷有力的修辞效果。又如,欧阳修在《本末论》中关于“本末”的讨论:
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彼,或系于此,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9]。
欧阳修为了更好地宣传自己读《诗》解经的正确方法,提出本末论,为加强语言的论辩力量,他用简短精悍的短句进行论说。可见,长句和短句各有千秋,拥有不同的表达作用和风格功能,只要运用得恰到好处,都会产生不错的修辞效果。最为常见的是,在唐宋八大家的论说散文中,长句短句常常交互搭配﹑有机配合,形成作品的跌宕起伏和语言﹑情感的波澜。如柳宗元《封建论》中论及: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10]。
这段话,或短句领长句﹑或长句领短语,通过这种错落句式的有机搭配,充分发挥了长短句各自叙事﹑写意﹑抒情的功能,形成了或疾或徐﹑或刚或柔的语言节奏。唐宋八大家几乎每一篇论说文都存在着这种长短句配合使用的现象,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作者的有意为之,这样创作的目的就是使论说文章不凝滞呆板﹑古奥枯涩。总之,“长句和短句配合使用,当长则长,当短则短,能够使文章既简洁明快﹑生动活泼,又严密周详﹑细腻委婉。”[11]
(二)整句与散句的选择和锤炼
所谓“整句”,又叫“偶句”,是指结构匀称﹑对应整齐的句式。所谓“散句”,又叫“奇句”,是指结构灵活﹑长短不一的句式。整句和散句有不同的表达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八大家似乎意识中已经注意到整句和散句在文章中起到不一样的作用,所以在他们的创作中,并没有完全抛弃形式上的这种骈文俪句,虽然改革文章形式为中唐古文运动的关键之一,但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文章改革并不是“简单对骈文的否定,而是吸取了骈文的精华,摈弃骈文的糟粕,建立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12]。一般来讲,“整句的修辞效果是,形式整齐,声音和谐,气势贯通,意义和内容随形式的整齐而表达得集中﹑鲜明。”[13]“散句的修辞效果是,各种结构形式交叉并用,灵活多变,曲折尽意,能够避免单调呆板。”[14]我国古代散文自发端伊始,不少散文家进行理论阐述时力求句式整饬﹑排比成文。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倡导下,唐宋八大家在散文创作中以奇句散行的先秦两汉古文为体式,并吸取魏晋以来骈文中的偶句模式,形成颇具特色的文章形式。骈偶句连类引发﹑优美整齐﹑顿挫有力。苏洵就长于此道,充分发挥骈句概括力和感染力,如《权书·心术》就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15],“尺棰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16]等十几处骈偶句。
元动作单元作为数控机床的基本组成单元,其故障模式多种多样,而且不同的故障模式对整机功能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将故障影响、经济损失、检测难度和维修难度作为分级标准,本文将元动作单元的故障模式分成3个等级:关键故障、主要故障和次要故障。
一般来说,对偶句﹑排比句﹑反复句﹑层递句是偶句句式,这样的句式更适合表现舒缓的语势,奔放的感情,如:
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17]。(韩愈《原性》)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18]。(王安石《材论》)
这两段话都使用了结构相同或相似的整句句式,大大加强了文章的气势,给人一种势不可挡的感觉。那么散句,则出于具有结构灵活的特点,更适于用来表现起伏变化的情景,如: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归之。自荀文若盛名,犹为之经营谋虑,一旦小异,便为谋杀。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数也。孔文举奇逸博闻,志大而才疏,每所论建,辄中操意,况肯为用,然终亦不免[19]。(苏轼《管幼安贤于荀孔》)
这段话刻画了曹操生性多疑﹑阴险狡诈的性格,由于使用了大量参差错落的散句,文风顿然形象生动起来。可见,整句和散句用得恰到好处,可以使文章呈现不同的句式美。如果文章中将整句和散句合理搭配,使文章既不失整齐﹑韵味美,又显示了参差﹑灵动美。
行文中若能有意造成奇偶相参﹑整散相错,句式如能既具有整齐和谐之美,又具有参差错落之美,那么文章显得洒脱灵活﹑跌宕起伏。清代文章家包世臣曾在《艺舟双楫·文谱》中说:“讨论体势。奇偶为先。凝重多出于偶。流美多出于奇。体虽骈必有奇以振其气势。虽散必有偶以植其骨。仪厥错综。致为微妙。”[20]综观唐宋八大家论说散文中的句法修辞现象,他们灵活吸取了整句和散句各自表情达意的长处,文章中常常将整句和散句灵活搭配使用,形成奇中行偶,偶中有奇的语篇形式。如:
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渎,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贤于一乡者,一乡之望也;贤于一国者,一国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于后世者,万世之望也。孝慈友悌达于一乡,古所谓乡先生者,一乡之望也。春秋之贤大夫,若隋之季良,郑之子产者,一国之望也;位于中而奸臣贼子不敢窃发于外,如汉之大将军;出入将相,朝廷以为轻重,天下系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没,其事已久,闻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龙﹑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万世,其道可以师百王,虽有贤圣,莫敢过之者,周﹑孔是也。此万世之望,而皆所以为民之表也[21]。(欧阳修《章望之字序》)
除了长句短句﹑整句散句的配合使用,唐宋八大家还使用了其它错综变换的句式,他们在论说散文中会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杂用各种句式。在错综变化的句式安排下,语言的表达效果得到了加强,同时,使文章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例如,韩愈在《原道》中一句:
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23]。
通过作者的句式锤炼,这句话仅仅三十六个字,就用了感叹句﹑肯定句﹑否定句﹑双重否定句四种句式。其中肯定句“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与双重否定句“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这两句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但形成鲜明的对比,增加了语言的表达效果。所以说,恰当地选择﹑变换句式,能够有效地增添文章的风采,使文章波澜起伏,富于变化,避免凝滞呆板。
二 句法变异修辞
句法变异修辞,是通过临时改变短语或句子的常规形式而形成的一种变异修辞。它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错综语序,这是一种通过颠倒词语的顺序,而故意将整齐的句子写得参差不齐﹑错落有致的修辞方法。南宋陈骙在《文则》中指出一种“交错之体”,郑子瑜先生指出:“所谓交错之体,就是错综的修辞法”[24]。我国古代散文,较少受语法上的严格限制,因此在组词成句时,便有颠倒错综等种种伸缩变化的弹性。唐宋八大家在论说文的创作中,为了造成句子的拗折与新奇,往往会选择错综语序的句法修辞手法。有一种错综语序的表现是,在同一句话中颠倒词语顺序,即词语倒装,这种情况在文言文中比较常见,比如王安石《原教》一文就出现了数次倒装,如:
不善教者之为教,不此之务,而暴为之制,烦为之防,劬劬于法令诰戒之间,藏于府,宪于市,属民于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无失其为兄弟也,夫妇者无失其为夫妇也,率是也有赏,不然则罪。”乡闾之师,族酇之长,疏者时读,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顾有不服教而附于刑者,于是嘉石以惭之,圜土以苦之,甚者弃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谓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诚化上之意也[25]。
“不善教者之为教”“藏于府,宪于市”“于是嘉石以惭之,圜土以若之,甚者以苦之,甚者弃之于市朝,放之于裔末”,这几处为倒装句,主要是定语和状语后置,增强语气,突出所表达的内容。另外一种错综语序的表现是,唐宋八大家还常在上下句﹑前后句间错综语序,造成文句错综跌宕,音节波浪起伏,节奏疾徐变换,凸显语言艺术性。如:
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26](韩愈《原道》)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意思是指不堵塞佛老之道,儒道就不得流传;不禁止佛老之道,儒道就不能推行。韩愈在这两句中没有写出主语,这样和下句“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在句式上错综成文,节奏感很强。又: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27]。(韩愈《师说》)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了解句读,疑惑没有弄明白,有的(指“句读之不知”)向老师求解,有的(“惑之不解”)却不向老师求解。这里“惑之不解”和“或师焉”位置颠倒,本应是“句读之不知,或师焉,惑之不解,或不焉”。根据前后文意思,句式在这里颠倒顺序,交错成文。韩愈刻意改变语序,使语句前后对应工整,文章读起来铿锵起伏。
还有一种错综语序的形式是,为了避免同一顺序的反复出现,改变原有的逻辑顺序。如,曾巩《太学》:
天子立太学,立官以掌之,立师以教之,所以兴教化也,所以出礼乐,所以萃贤材也,所以养俊髦也。俊髦不能养,贤材不能萃,礼乐不能出,教化不能兴,则官师之过也[28]。
前面提到的顺序是教化﹑礼乐﹑贤材﹑俊髦,到了最后就变成了俊髦﹑贤材﹑礼乐﹑教化,这是语序上的倒装,这样起到活泼句式的作用,避免句式的重复。曾巩论说散文中有很多这样的错综句式,他的《议钱上》同样用到:
……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也,布者取其散也,泉者取其流也。流则天下之用足,散则天下之财阜,利则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后廉取兴,财阜而后礼义浃,用足然后德化被[29]。
第二句是按照第一句的逻辑顺序而来,第三句顺序是“用足”“财阜”“民和”,接下来改变论说顺序,先谈“民和”,最后谈“用足”。这种错综语序的形式,使句子波澜起伏,避免平板﹑单调,体现了语言运用的灵活性,表现了作者高超的修辞技巧。
修辞是一种思维形式,是使用者有意而为之,宗廷虎先生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修辞的研究”[30],语言使用者在进行表达和沟通的过程中,受整体直觉思维方式﹑取象比类思维方式﹑辩证思维方式等的影响,逐渐萌发出修辞意识,就如,先民敬畏祖宗﹑神祗,直呼其名是冒犯,于是言语上就产生和形成了避讳﹑委婉﹑敬谦的要求。这正是一定的修辞意识的体现和实践。也可以说,唐宋八大家论说文体现了他们自觉的修辞意识,他们根据文义需要,适时变换句式﹑交错语序,以此加强语言的表现力,完成论说散文实用性和审美性的高度统一,显示了他们精湛的语言应用艺术。唐宋八大家论说文中句法修辞艺术,深深打上他们的气质﹑性格的烙印,“不同的炼句法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古代诗文家不同的思想情感﹑生活际遇,不同的艺术修养﹑审美趣味,表现了作品不同的情﹑事﹑理,不同的题旨﹑内容。”[31]总之,唐宋八大家作为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们是杰出的语言工匠,通过巧妙安排﹑灵活运用文学语言,他们的论说文章融思想性﹑知识性和技巧性为一体,从而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