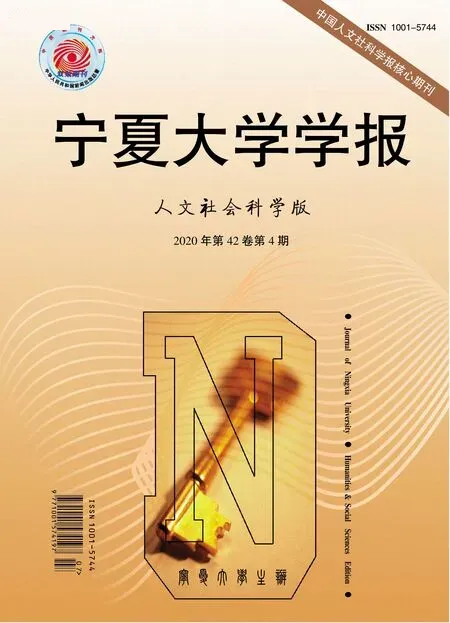古代陇中文学发展概述
连振波
(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甘肃 定西 743000)
陇中扼关陇巴蜀之咽喉,为丝绸之路之要冲。在陇山以西,黄河以南,洮河以东,横跨定西﹑天水﹑白银﹑平凉四市,包括安定﹑通渭﹑陇西﹑临洮﹑会宁﹑秦安﹑甘谷﹑静宁等十四县区的广袤黄土高原中部,是关陇文化的一大核心区域。陇中先民以此为基地,经过艰辛创造和开拓,发展起了陇右灿烂的史前文明,陇中文学亦渐次萌芽。殷商末年,伯夷叔齐的《采薇歌》揭开了中国文学的大幕,也开启了陇中文学的先河。《诗经·秦风》中的许多篇章,如《小戎》《蒹葭》《无衣》《渭阳》等诗篇多与陇中相关。东汉初,隗嚣割据陇右,由于他“素谦爱士卒,倾身引接为布衣交”[1],又兼“素有名,好经书”,所以“三辅老士大夫”如班彪者纷纷投奔,陇中文学呈一时之盛,这也为后汉陇中文人五言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土壤。隋唐时期,传奇小说的创作是陇中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此后,虽然经过了宋元时期的低谷,但随着明清关陇理学的传播发展,陇中诗文伴随着陇中文化的发展走向繁荣。
一 陇中古代文学发展流变的三个阶段
在华夏文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陇中文化既伴随着少数民族的汉化和汉文化的扩散吸引而趋同,又因人口流动﹑民族迁移﹑国家统一与分裂的战乱波动而趋异,这种趋同和趋异的变化中,形成了陇中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陇中是中原与西域(包括西戎﹑狄羌﹑吐蕃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伸缩进退﹑相互消长的中间地带,是从三秦文化到西域文化的中间环节,它联系着两方又自成体系,是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域内文明与域外文明双向交流扩散﹑荟萃传播的桥梁。从历史上看,陇中地区因为人口和民族的更迭,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特别明显,期间大致形成了三次大的文学发展高潮。
(一)先秦古诗与汉代文人五言诗创作
1.陇中的先秦古诗
远在尧舜时期,由于舜﹑禹征伐四夷“迁三苗至三危”,戎狄部落占据陇中。据《史记》记载:“郑玄引《河图》及《地说》云:‘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岐山相连’”[2]。鸟鼠山西南即今渭源县露骨山附近。后来秦霸西戎,西筑长城,陇中始归秦帝国统辖。应当说,在此之前应有多种文学现象已经在陇中大地发生,其中不乏民歌,如《击壤歌》也许是中国诗歌之祖。清人沈德潜《古诗源》说:“帝尧以前,近于荒渺。虽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伪撰,其事近诬。故以《击壤歌》为始。”[3]有人认为击壤是古时的游戏,《击壤歌》为古人游戏时唱的歌。但是,陇中作为先民最早的栖息地,他们在马家窑文化时期就有了自己的村落﹑居室和房屋。因此,那时的人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凿井(取水)﹑耕田(取食)和建窑洞(居处)。击壤其实是一种版筑的劳动,他们筑黄土为室,在完成自己的居室后,属于自我陶醉自得其乐的一种民歌。另一首古诗源头是《采薇歌》,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采薇首阳山,经过数千年的风雨沧桑,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采薇歌》是一首坦露心迹﹑毫不矫饰的抒情诗,也是一首爱憎分明﹑忧时忧民的政治讽喻诗。《秦风》中的《小戎》《蒹葭》《无衣》等,多与陇中有关,系秦人西霸诸戎时的战歌和情歌。秦人对战争普遍地怀有一种激情,最集中的体现就是《无衣》。古代西戎之地,如古平襄(通渭县)为襄戎之地,古伏羌(今甘谷县)为冀戎之地,陇西为獂戎之地,是秦国这次远征将陇中大地从戎狄手中夺过来,拉入到秦国版图。“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以一种无比激昂的斗志和集体乐观主义精神,表现了不问缘由﹑不计后果﹑不分贫富﹑同仇敌忾的战争热情,这是陇中尚武斗勇精神的真实写照。
2.汉代文人五言诗
汉代陇中的文人五言诗创作主要有李陵赠答诗﹑秦嘉徐淑夫妻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的创作。李陵为陇西成纪人(今甘肃静宁),为飞将军李广之后。他与苏武互相赠答的作品,作为汉诗中的经典,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尽管其真实性也是历来饱受争议,但“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的悲摧苍凉,让人赞叹不已。秦嘉徐淑是东汉桓帝时的“夫妻诗人”,现存秦嘉的五言诗《赠妇诗》是中国古代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也是现存最早的有名姓可考的五言爱情赠答诗。钟嵘《诗品》曰:“士会夫妻事既可伤,文亦凄怨。二汉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4]秦嘉徐淑以对生命的深沉忧虑意识,拓新了文人五言诗写作的题材,创新了诗歌的抒情方式,语言朴实,情真意厚,“歌诗婉约,妙语新声”,是文人五言诗和抒情散文的开拓者,对后世诗人及其创作有深远影响。除了秦嘉的五言诗,徐淑的诗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5]。她的爱情生活,细腻﹑忠贞﹑炙热﹑永恒,成就了“夫妻诗人”的爱情佳话;其人格精神,素雅贞静﹑行谊高卓﹑刚毅自立。《隋书·经籍志》称“梁又有妇人后汉黄门郎秦嘉妻《徐淑集》一卷。”[6]但到魏徵﹑长孙无忌撰写《隋书·经籍志》时已经佚亡。后通过《俄藏敦煌文献》(敦煌号第12213 号)《后汉秦嘉徐淑夫妇报答书》等文献看,秦嘉徐淑夫妇有大量的诗文互相赠答,并且与同时代的《古诗十九首》又有太多相契合的地方,故有学者推断:“在现存的东汉无名氏文人五言赠答诗中,定有秦嘉﹑徐淑二人的作品。”[7]笔者根据秦嘉徐淑生存的年代和《古诗十九首》出现的时间相合,生活情景与《古诗十九首》的情境吻合,创作风格﹑语言特色和用典手法上的相似,认为《古诗十九首》中的大多数篇目,当是秦嘉徐淑夫妻赠答诗[8]。也因此判断,这是陇中文学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期,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意义深远,影响巨大。
(二)唐传奇小说的创作
魏晋时东晋政权偏安江南,氐羌民族复兴,苻坚﹑姚苌﹑吕光等建立少数民族政权于关陇地区。苻坚,字永固,氐族,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县东南)人,他崇尚汉文化,汉文化修养很高,曾“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9]他在位时提倡文学,命群臣赋诗,自己也唱和。其弟苻融﹑侄苻朗在文学上均有建树。与苻坚关系密切,被尊为国师的王嘉,是陇中小说很重要的一位作家。王嘉,字子年,陇西首阳人,著有《拾遗记》。王嘉是楼观派的大师,是北朝道教改革中演变而成的新道派之一,“能言未然之事,辞如谶记”,其玄怪谶纬思想直接影响到了唐传奇小说的发展。
隋唐建立,陇中文学随着社会发展,传奇小说成了与诗歌并重的文学主流。一些著名的文人学士﹑朝廷官员都曾参与小说创作,尤其“陇西三李”(李朝威﹑李公佐﹑李复言)成就最高。李朝威代表作《柳毅传》﹑李公佐《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牛僧孺传奇集《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李朝威,陇西人,生平事迹无考,唐代中期著名传奇作家,他的作品仅存《柳毅传》和《柳参军传》两篇。《柳毅传》是唐传奇的代表作之一,该传对后来演绎故事影响甚大。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唐人传奇留遗不少。而后来煌赫如是者,唯《莺莺传》及李朝威《柳毅传》而已。”[10]柳毅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并赋予他正直善良﹑见义勇为﹑光明磊落﹑威武不屈的高尚品质;他的忠肝义胆,为龙女传书,不图私利,无居功自傲之色施恩图报之意,表现出柳毅是一个坦荡荡的君子。柳毅对于与龙女的爱情的态度也是严肃慎重的,认为“杀其婿而纳其妻”,从道义上﹑良心上都不能接受。这从根本上讲,也是陇中传统文化中尚勇重义的体现。龙女渴望自由幸福的生活并且大胆地追求,她有明确的生活目标,不甘凌辱,渴望生活的自由和婚姻的自主,百折不挠地为实现这一既定目标而斗争。这种精神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非常深远。李公佐,字颛蒙,陇西人。主要作品有《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庐江冯媪传》等。《南柯太守传》托笔梦幻,实写人生,揭示了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的主题。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的社会政治生活,揭开了我国小说浪漫主义创作的先河。《谢小娥传》首次以贫民女子为主人公,刻画了一个鲜活﹑大胆而执着的普通女子的爱恨情仇,超越了传统女性贞节烈妇的历史形象的束缚,具有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作品为唐传奇增添了不少亮色。洪迈《容斋笔记》:“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不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11]汪辟疆《唐人小说·序》:“唐代文学,诗歌小说,并推奇作”[12]。二人均把小说与传统的诗歌创作相提并论。
(三)明清诗歌散文的繁荣发展
1.明清关陇理学对陇中散文创作的促进与发展
唐代李翱师从韩愈学习古文,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所著《复性书》,糅合儒﹑佛两家思想,发挥《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思想,南怀瑾认为:“李翱《复性说》阐发性情之说,为北宋理学滥觞。”[13]北宋时期,关学大师张载的弟子吕大均﹑游师雄﹑种师道等追随韩琦戍边陇中。游师雄的诗歌《贺岷州(今甘肃岷县)守种谊破鬼章》:“围合洮州敌未知,烟云初散见旌旗。忽惊汉将从天下,始恨羌酋送死迟”[14],颇有陇右彪悍文风。随着关陇地区为金所有,“蓝田学派遂至无征”[15]。直到明洪武三年,徐达“自潼关出西道,捣定西,取扩廓。”元朝彻底灭亡,明清关陇理学渐次复兴,陇中诗歌散文“以理质,以气盛”,名家云集,实现了第三次繁荣。
明代陇中文学的代表人物是胡缵宗﹑杨庆和金銮,尤其以胡缵宗成就巨大。胡缵宗,字孝思,号可泉,别号鸟鼠山人,秦安县人。明武宗正德三年进士,历任安庆﹑苏州知府,山东﹑河南巡抚。师承湛若水,又以王阳明﹑吕枏﹑王九思﹑康海﹑马理﹑李梦阳等著名学者﹑诗人为友,游历苏杭,遍结名士,俨然是陇人之秀。他的主要文学与学术成就见于《鸟鼠山人集》。在经学﹑哲学﹑古文﹑诗歌﹑方志﹑书法等诸多方面均是名家,是全方位的文化巨人。他的诗歌因人抒情,见事立论,尤其长于拟古乐府,题材十分广泛。他以淡泊的心境﹑丰厚的阅历以及智慧敏锐的洞察力为支柱,在精神世界畅游,形成激昂悲壮﹑关注民生﹑悲悯人生的创作风格。清代前期主要有张晋﹑吴镇﹑许珌﹑王了望﹑胡釴﹑杨于果﹑王羌特和秦子忱,晚期以巩建丰﹑李南晖﹑牛树梅﹑安维峻﹑王作枢﹑李景豫﹑李桂玉的文学创作成就最高。吴镇是临洮诗人,得到著名诗人﹑文学批评家袁枚的赞赏,作品被采入《随园诗话》。袁枚又为吴镇诗文集《松花庵全集》作序:“先生之诗,深奥奇博,妙万物而为言,于唐宋诸家,不名一体,可谓集大成矣。”[16]杨芳灿说他“裁云缝月,妙合自然;刻楮镂冰,意惟独造。有稼轩之豪迈,兼白石之清疏……叶脱而孤花明,云净而峭峰出。”[17]随着关学在关中的衰落,陇中巩建丰﹑李南晖﹑牛树梅﹑安维峻等理学大师的散文却渐入佳境。巩建丰,字介亭,伏羌县(今甘谷)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国史馆攥修﹑云南学政﹑侍读学士,以讲学著书为乐,人称“关西师表”。巩建丰著述甚丰,总编为《朱圉山人集》十二卷。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四评价说:“诗文简易,无擅胜之处,亦无驳杂之处。”李南晖,字仲晦,号青峰,甘肃通渭人,师承巩建丰,人称“陇右真儒”。其著作《慎思录》思致奥广,实乃毕生心得,《清史稿·艺文志》存目。《读易观象惺惺录》(四十卷)﹑《羲皇易象新补》﹑《易象图说续论》(十卷)独劈易学研究的新途径,对现当代易学研究意义重大。牛树梅继承李南晖理学的衣钵,在心性学和格物致用方面超越前人。牛树梅,字雪樵,号省斋。《省斋全集》(十二卷)秉关陇之气,得河洛之蕴,“绩绍文翁,学宗关洛,循吏名儒,声闻海宇”[18]。早年受其父亲牛作麟《牛氏家言》的影响巨大,曾国藩说:“牛雪樵廉访树梅,述其父愚山先生作麟之言也,真挚坚忍,为近世讲家所不及。”[19]安维峻,字晓峰,任福建道监察御史,著《谏垣存稿》《望云山房诗集》等5 部。“主南安书院日,以为陇西儒宗云。”[20]甲午之战前夕,连续上疏六十五道,最著名的是《请诛李鸿章疏》:
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乃倭酋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彼既外强中干,我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唯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21]。
安维峻文风犀利,恣情任气,议论说理,入骨三分。虽为谏官奏议,但豪气袭人,排山倒海,陈情痛谏,声泪俱下,似武侯《出师表》堪为千古绝唱,为陇中文学平添华章。
2.明清陇中诗歌的空前繁荣
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建国,到明思宗朱由检于崇祯十七年(1644)自杀身亡,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诗文仍然居于明代文学的主流地位,产生了大量的文学群体,如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复社和几社等。在明代文学整体发展的影响之下,陇中文学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传统的诗文领域,出现了著名学者和诗文大家胡缵宗;在通俗文学领域,出现了影响明代曲坛的著名戏曲作家金銮。嘉靖十四年(1535),陕西巡按御史王书绅在陇西创办了崇羲书院,选巩昌府各州县学生200 余人就读。同年,渭源建立了渭川书院。在明代陇中书院的建设中,杨继盛是一个重要人物,嘉靖三十年(1551),兵部主事署员外郎杨继盛被贬为狄道典史,在临洮岳麓山超然台创办了超然书院,并亲自讲学,后来又在临洮设立了椒山书院,一时狄道读书之风兴起,附近州县学子纷纷负笈求学,陇中学风大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据统计,明代甘肃进士178 名,陇中地区50 多名,代表有秦安的胡缵宗,临洮的杨行恕﹑张万纪﹑潘光祖,陇西的杨恩﹑关永杰﹑郭充,安定区的黄谏﹑张嘉孚等,这些进士大多能诗善文,极大地繁荣了陇中地区的诗歌发展。
1644 年清军入关,清代文学走过了历史上最后一个辉煌的时代。从总体上看,清代文学走向全面繁盛,文学流派众多,作家作品数量庞大,各体文学也再次复兴,诗﹑词﹑文﹑小说﹑戏剧都产生了大量的作家,出现了一系列优秀作品,甚至汉代的赋和六朝的骈文等文体也都再现辉煌。清代陇中文学繁荣和书院教育相关。书院建设不仅推动了地方教育科举事业,还促进了地方学术和文学的发展。明末书院讲学结社﹑议论时政﹑从事反清斗争,清初曾一度禁止开设书院。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开始,康熙皇帝先后为20 余所书院赐书赐匾,陇中的一些书院也得以恢复和重建,如静宁陇干书院﹑临洮超然书院﹑巩昌府建南安书院﹑伏羌朱圉书院﹑秦安陇川书院等,这些书院的建设,不仅直接为陇中地区培养了大量科举士子,更是直接推动了陇中文学的发展。书院建设促进了人才的交流,这些人对陇中的贡献极其重大。如牛运震在甘肃做官十余年,对甘肃文学发展贡献极大。牛运震主治经学,但好诗,他任秦安知县时,创办陇川书院,奖掖文学,由是陇中士风振起,文学兴盛,培养了诗人胡釴﹑路植亭﹑张辉谱﹑张梦熊等人。
清陇中文学的繁荣与诗社的发展有直接关系。陇中最著名的诗社有洮阳诗社。顺治年间的天才诗人张晋才华横溢;乾隆年间吴镇横空出世,领袖关陇。其后吴承禧﹑李华春﹑李苞等人继续联社,唱和不断。嘉庆年间,李苞等人汇编洮阳诗社清代诗人作品为《洮阳诗集》,为地域文学甚至清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除此之外,巩昌以南安书院为中心,形成了另外一个作家群。其诗社情况,据牛树梅为陈时夏《集唐诗序》载:“庚辰辛巳之间,余以托钵计至郡砚耕。得与陈常于及包子裁﹑何郑圃﹑张省三诸君﹑李圣基订金兰交,为诗文社。冯敷五先生实倡之,诸人皆名下士。笔墨音源,意气笃焉!佳节令辰,古剎山馆之中,相与欢呼唱和以为乐者,不知凡几。”[22]以诗社为载体,诗人群体活动是清代文学特别是地域文学发展的重要形式,对于推动文学发展功劳巨大。
二 陇中古代文学的特色
(一)雄浑劲健与悲壮苍凉的风格特点
陇中是多民族聚集的地方,陇山渭水孕育了陇人粗犷豪迈之气,又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和生存状态艰辛,陇中人民具有对生命的敬畏悲怆之情。因此,陇人的诗歌绝非小桥流水﹑莺飞草长,而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阳关古道。陇山﹑陇水﹑陇上﹑陇头在中国文学言语中,是有特定的感情色彩,地域蕴含着悲壮之感。“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23]这些或许就是最早的陇中民歌,悲壮苍凉,荡气回肠。《三秦记》:“其坂九回,不知高几许,欲上者七日乃越。高处可容百余家,清水四注下。”郭仲产《秦州记》曰:“陇山东西百八十里。登山岭,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山东人行役升此而顾瞻者,莫不悲思。故歌曰‘陇头流水,分离四下。念我行役,飘然旷野。登高远望,涕零双堕。’”[24]当然,陇中诗歌并不完全是这种悲壮基调,如牛树梅的《禅牧山歌》,更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陇中风情:
禅牧山,接混茫,石骨草皮郁苍苍。龙背横屈佛顶秃,六月飒飒凛霏霜。地势远自中州起,坡陁渐上三千里。到此行行未觉高,回头身在白云里。盘膝坐啸碧峰头,千里万里双眸收。西望昆仑东渤海,呵气迥与青冥浮。吾邑偏隅隔关陇,此山高矗西天耸。若以东向俯诸州,足使五岳皆朝拱。禅牧山,何壮哉!不有圭峰之峻峭,不有岩壑之幽回。唯有两间雄厚气,莽然直溯鸿蒙开。我今为歌语山灵:山灵山灵,厘尔福,弥尔灾。兴云降雨庇吾民,无忝千秋俎豆陪[25]。
禅牧山就是陇中最高峰牛营大山,她“石骨草皮”,却又郁郁苍苍,“地势远自中州起”,不仅气势雄伟﹑傲骨超群,而且“西望昆仑”,“隅隔关陇”,有一种能够让五岳朝拱的胆气,这正是初出茅庐﹑立志高远的青年牛树梅所应有的雄心壮志。尽管他在“龙背横屈佛顶秃”的禅牧山上,没有看到奇峰顿起﹑岩壑幽回的佳境,但是,“唯有两间雄厚气,莽然直溯鸿蒙开”的气象,不正是禅牧山给人一种荡气回肠精神领悟?然而,作者又笔锋一转,以老杜忧民之情,呼吁山灵“厘尔福,弥尔灾”,兴云降雨,庇佑人民,在雄浑劲健中,糅合了悲壮苍凉,让人深思,让人感动。这种风格的作品,在唐传奇小说﹑陇中戏曲﹑文人散文中,表现得也相当明显。
(二)尚义重情与真率直露的情感内涵
陇中文学始终以感情真挚﹑重礼尚义为主要表现内容。东汉末年,秦嘉徐淑不仅有《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焦仲卿的悲怆和不幸,徐淑同样被其兄弟逼嫁,甚至不惜“许我他人,逼我于上,乃命官人,讼之简书”[26]。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让徐淑移节,而是大义凛然,以为“智者不可惑于事,仁者不可胁以死。晏婴不以白刃临颈,改正直之词;梁寡不以毁形之痛,忘执节之义。”[27]最终不为胁迫利诱所动,保持了自己为爱情献身的高贵品质。这种为爱情献身的专一精神,在陇中的诗文中随处可见。如著名的唐传奇小说《柳毅传》,虽九死一生而真情不改,他们绝没有郑卫之声靡靡之音;没有始乱终弃私订终身,而是在重情重义的道义框架内,有情人终成眷属。明清时期,夫妻感情甚笃者,直抒胸臆之佳作甚众。如牛树梅《遥祭王氏文》:“汝尝言我不在家,风声月影,犬吠鸡鸣,辄生无聊之思。悠然远想,不知所云。今则荒山孤塚,冷露凄风,不知冥漠之乡,曾否有灵,其更何以为情耶?汝死非其地,我终不忍百年之后,弃汝于异境也。”[28]颇有韩愈《祭十二郎文》﹑袁枚《祭妹文》情思婵娟﹑荡气回肠,至情至性,如怨如诉。王氏是牛树梅最喜爱的妻子,是牛树梅感情最深沉的爱人。从这篇《遥祭王氏文》中,我们能够看到牛树梅对妻子深深的爱和妻子王氏对牛树梅的深深眷恋。牛树梅在《桮棬志痛》中,还记载了一段其父母的感情往事,更能代表陇中文学中大多数人的情感精神世界:
父就视曰:“即不讳,何所欲言?”
母曰:“所不甘者,君寂寞难过,二孙女未嫁,长儿未有子嗣,其兄弟读书之事未成也!”
父曰:“我与汝有哑谜话,‘蓝田’二字记之乎?”
母曰:“忘之矣。”
父曰:“我图章俱在,临时榻汝手也。”
母愁结而泣曰:“我记起矣,你不要昧心也!”
父曰:“汝去且与舅姑处,他年我来时,引你同往”[29]。
读至此,直让人情思喷涌,声泪俱下,毫不做作,堪比苏轼“十年生死两茫茫”之叹。
(三)拙野质朴与多元荟萃的审美取向
陇中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历史上曾经是西戎﹑匈奴﹑鲜卑﹑吐蕃和西夏﹑蒙古人的居住地,许多少数民族在这里建立政权,民族融合和民族冲突的印记十分明显。陇中属于周秦故地﹑关陇咽喉。丝绸之路贯穿全境;万里长城横亘中央;渭水洮河流经域内,形成了“两河一路”的文化格局。陇中的文学创作,总不能完全脱离本地特点,其强健剽悍的心态与尚武斗勇的气质,与粗犷豪迈的人情民风结合,自然形成了陇中文学拙野质朴的审美特质。这种审美中产生的雄浑之气﹑真率之情,表现在诗歌中,是天罡正气般的力量,如胡缵宗的诗歌《终南行赠陈汝忠佥宪兼怀王敬夫段德光康德涵吕仲木内翰马伯循冢卿李献吉宪使》:
比斗城南终南山,下有泾渭浐灞同潺湲!太华东来接紫气,太白西出高难攀。豸冠绣衣云端客,鬃马嘶向山水间。公余踏马系何处?山青水白堪留扳,知君颇重文字交。于嗟乎,山水之间,有客有客贞且闲。美陂离骚席欲暖,鸡田注书门常关,泾野高风重山斗,对山浩气充区寰,河滨豪吟樽不竭,崆峒壮游辙将还。有此美人天一方,使我万里空愁颜。为我致谢诸君莫长啸,只今四海多痍癏[30]。
胡缵宗得太白飘逸之风,诗歌行云流水,自然天成。写景与抒情合为一体,评论与怀念水乳交融,用白描之法,让每一个人活灵活现,跃然纸上。另如吴镇的《我忆临洮好》:“我忆临洮好,灵踪足胜游。石船藏水面,玉井泻峰头。多雨山皆润,长丰岁不愁。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31]体现出了陇中独特的文化底蕴,从“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可以看出陇中文学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多元混存的特点。这种多元荟萃性不但丰富了陇中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也是陇中文学自性发展的一种遗传基因,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政权如何更替,他总是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贯穿在陇中文学发展的始终。
(四)兼收融合与自主创新的创作活力
从地域和文化个性上看,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洮河为中心形成的“两河一路”文化圈,正是陇中文化的核心地带,是黄土高原最为典型的农耕与畜牧交替﹑战争与和平更迭﹑华夏文明与少数民族交替的地带,以此形成的文化圈,其文学特点也必然随着陇中历史文化的演进而变迁。陇中人民习惯于呈现自然的原生态色彩,敢爱敢恨直抒胸臆,在真率之中,形成自己的抒情深度和文学景象。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陇中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有非常优越的教育传统。太昊伏羲生于古成纪(今甘肃静宁),狩猎畜牧,画制八卦,为人类的文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后秦祖﹑石作蜀﹑壤驷赤等孔门贤人把儒学引入陇右。唐代李翱(今甘肃秦安人)师从韩愈学习古文,发挥孟子心性之学,为关陇文化和文学的发生发展贡献巨大。二是陇人“重义尚武”的性格。陇中文化博大精深,秦霸西戎之后,推广“明法”“壹教”“吏之为师”三项教育政策。秦人以此精神和勇力,“鞭笞天下,宰割诸侯”,促进了当地生产力和文学的发展。三是汉儒是陇中核心价值思想体系。陇中地区为西部重要屏障,当地民间教育以“诗书传家”闻名。东汉初年,隗嚣割据政权十分重视文教,任用王猛﹑班彪等名士,极大地促进了陇中文学﹑文化的发展。四是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文化的推崇。陇中氐人苻氏建立前秦政权,他们继承了汉魏以来由帝王主持的宴饮赋诗的传统,文化教育十分发达。出现了苻融﹑苻朗﹑王嘉﹑苏蕙等优秀作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建设者,虽生于氐﹑鲜卑﹑匈奴酋豪家庭,擅长弓马战阵,但长期生活在陇中的汉族文化圈内,钦慕华风,倾身儒雅,崇儒重教,推动了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对陇右的繁荣富庶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民族风情与独具一格的地域特色
在漫长的历史中,陇中地区相继建立了一系列邦国性质的地方政权或酋长性质的土司政权,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明显的特殊性,在创造自己历史的同时,形成了众多的民族。从地域和文化个性上看,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为中心,形成了以“两河一路”为中心的黄土高原文化圈,显示了黄土高原文化的悠远古朴,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形态与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观念﹑习俗﹑宗教﹑艺术以及悠久历史﹑生存环境紧密相连,是一种广义的文化集合体。陇中民族的审美心态较中原单纯,他们习惯于呈现自然的原生态色彩,无中原文学的奥僻,较少堆砌典故,辞色亦取其自然。或者说,陇右文学在真率之中,形成自己的抒情深度。在创作思路上,中原讲究“扦情宜隐”,陇右民族则因缺乏曲折深邃的比兴构思而显得直露。但是换一个角度,在中原“比兴寄托”已成套路的程式下,陇右文学少此构思,反而铸就了其抒情直露之特色。如陇中民间文学,它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流传,主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达它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在创作与流传方面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
陇中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洮岷花儿是羌戎民族的文学遗存。这些花儿情歌是广大劳动人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它主要抒发了青年男女由于相爱而激发出来的悲欢离合的思想感情。在各类民间歌谣中,情歌的数量最多,艺术性也比较高。它总是采用多样化的艺术手法,或含蓄﹑或直率地表达青年男女对幸福爱情与美满婚姻的强烈追求,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纯朴健康的恋爱观念与审美情操。有的情歌还表现了对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的蔑视与反叛。
从内容上看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表达爱慕之情。如《单单爱下你着哩》的一段:“园子角里牡丹红,折上一朵爱死人,怀里揣么口里噙,怀来揣去揣不下,口里噙去耽搁大。进去园里扩白菜,要摘园里李子哩,别的花儿我不爱,单单爱下你着哩,不为你着为谁来,把你陪到底着哩。”二是表达相思之苦。如陇中山歌唱道:“白麻纸糊下的窗亮儿,风吹着当啷啷响哩,想起了尕花儿的模样儿,清眼泪唰啦啦淌哩。”以物象入情境,神形毕至,语意兼美。另如“黄河沿上的水白菜,一天比一天嫩了;尕花儿害上了相思病,一天比一天重了”等。三是表达对爱情的坚贞不渝以及同封建礼教坚决斗争的决心。如《宁打官司人不丢》,写一位姑娘为了追求爱情,被人诬告,吃了官司挨了打,但对恋人的挚爱却始终坚如磐石。
陇中花儿的艺术特点主要是情景交融,感情真挚,广泛地采用托物起兴﹑反复咏叹﹑一语双关﹑夸张﹑比喻﹑拟人﹑重叠等多种修辞手法。千百年来,他们以勤劳的双手﹑顽强的意志﹑睿智的思维,与大自然长期进行着坚强不屈的挑战和抗争,创造了丰富辉煌的农耕文化,也孕育出多彩灿烂的民间文学,诸如神话﹑民间传说﹑故事﹑歌谣﹑寓言﹑笑话﹑小戏﹑讲唱等,成为中华文化宝藏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以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32]陇中文学具有独特的地域和文化个性,以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洮河为中心形成的“两河一路”文化圈,是黄土高原最为典型的农耕与畜牧交替﹑战争与和平更迭﹑华夏文明与少数民族交替的地带,以此形成的文化圈,其文学的特点也必然随着陇中历史文化演进的特色而变迁。陇中人民习惯于呈现自然的原生态色彩,敢爱敢恨直抒胸臆,在真率之中,形成自己的抒情深度和文学景象。陇中文学也因此呈现出上述五大特色,并有延续发生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