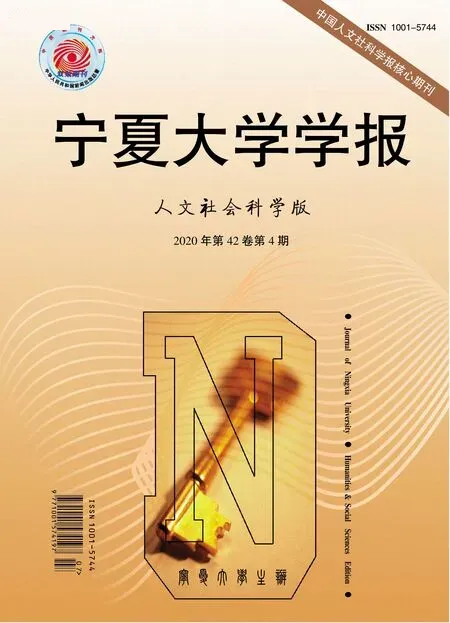元代《保母帖》观咏活动考论
马颖杰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关键字:元代;《保母帖》;文人活动;宗晋之风
晋兴宁三年(365),王献之保母李意如去世,献之“树双柏于墓上,立贞石而志之”[1],此中“石”乃献之为其乳母所书之砖石,“藏于墓……高尺余,阔尺七八,前有小砚影,书类兰亭,约二百许字”[2],亦即后世所言之保母碑(或称保母砖)。
八百年来世人一直未见保母碑真容,直至南宋嘉泰二年(1202)夏六月,山阴农人辟土,得砖于黄閍,是碑“色黝而润,后有‘晋献之’三字,旁有‘永和’二字。以志文观之,盖殉葬时物也”[3],与此碑同出的还有曲水小砚,正与碑文内容“殉以曲水小砚,交螭方壶”相合,时人断定此碑即是晋时王献之所题保母碑。
保母碑为周姓樵人发掘后,“归钱清王畿家”[4],是年(嘉泰二年)便有人从碑上拓得了墨本(即《保母帖》),姜夔跋中有记,嘉泰二年了洪“携墨本自钱清来示余”[5],后周必大跋中云,嘉泰三年沈曾智“出示越上新拓王献之保母墓碑”[6]。与此同时,保母砖在当时亦是可观赏之物,黄庭开禧三年(1207)“亲见保母砖刻于临安旅舍”,王畿曾“携砖砚入都”,让姜夔得以借观数日。可见不论是保母砖还是《保母帖》,在南宋皆曾用于文人间的交往。可惜后来保母砖损坏加重,难以长久,“砖既入土八百余年,已腐坏,恐不能久。近所摹本,比初出土时已觉昏钝,摹之不已,日就磨灭,得墨本者宜葆之哉”[7],并且随着保母砖的腐坏程度加深,从其上拓下的墨本清晰度逐渐降低,已得拓本便成了难得之珍品。至元代,存世之拓本(即《保母帖》)引来诸多文人观赏题咏,本文即是研究元代《保母帖》观咏活动。
一 元代《保母帖》的六种藏本
于元代出现的《保母帖》有诸多藏本,赵孟頫《题王大令保母碑》中记载:
《保母碑》虽近出,故是大令当时所刻,较之《兰亭》,真所谓因应不同。世人知爱《兰亭》,不知此也。丙戌冬,伯机得一本,继之,公余丈得此本,令诸人赋诗,然后朋识中知有此文。丁亥八月,仆自燕来还,亦得一本。又有一诗僧许仆一本,虽未得,然已可拟[8]。
据此,可知至元年间有四人得到《保母帖》:至元二十三年(丙戌),鲜于枢得一本﹑周密得一本;至元二十四年(丁亥),赵孟頫得一本;另外还有一诗僧手中有一本,共有四本。
在上述四种本子之外,苏伯衡所撰《跋保母帖卷后》中提及了另一本:“文清以谓尝见保母帖,虽墨本而笔意正如此,乃知古人字画妙固不可及,至于镌刻之妙,后世亦未易及焉。今此卷前后有桷字小方印,乃文清之名,岂其当时所见本耶?据周丞相跋,此盖拓本,然前后又有袁通甫印,通甫姑苏人,名易,尝为石洞书院山长,号称好古家,有静春堂,多藏法书名画,鲜于伯机﹑赵子昂极推敬之。而敬伯得此姑苏,其为通甫家藏旧物无疑矣。”[9]从此文中可知,苏伯衡所见《保母帖》为袁易旧藏,我们暂称此帖为袁易本。
最后,吴师道在《跋叶审言所藏晋唐石刻》中说到:“献之《保母帖》所谓黄门冈,在今会稽城外十余里禹穴﹑天柱之间,其文固有望于后人之无伤,而曲水小砚并出人间,岂字画实为之累耶?”意指叶审言藏有《保母帖》,不知是否为上述几种藏本之外的本子,暂称为叶审言本。
综上,我们可知的元代六种《保母帖》藏本分别为鲜于枢本﹑周密本﹑赵孟頫本﹑诗僧本﹑袁易本﹑叶审言本。
二 元代《保母帖》观咏活动及其流传线索
在上文说到的元代《保母帖》的六种藏本中,诗僧本与叶审言本资料记载较少,本文不予讨论,其他四人所藏之书帖在元代皆有围绕它们展开的观咏活动,其流传线索亦记录于史料中,下文分别论述之。
(一)鲜于枢本《保母帖》
鲜于枢,字伯几,号困学民,渔阳(今津蓟州区)人,元代著名的书法家。关于鲜于枢本《保母帖》的来历,元明之际刘楚《跋北山上人所藏晋献之保母帖》中有记载,说是鲜于枢“前元丙戌得之武林市肆”[10],后归北山上人,刘楚就是在北山上人处得见此贴。鲜于枢至元二十年得浙西宣慰司都事之命,赴杭州,其后虽调往他处,但时常往来于杭州,他与杭州的这种密切的联系,使得他在机缘巧合下,从市肆中得到《保母帖》。
目前可见材料中,至鲜于枢处观帖的记录有二:
一是刘楚《跋北山上人所藏晋献之保母帖》说此贴“后有赵文敏公书题,谓此碑最近出,大令手书当时所刻,世间无第二本”[11],知鲜于枢此本有赵孟頫题。又,鲜于枢是赵孟頫《题王大令保母碑》文中所言第一个得到《保母帖》的人,赵孟頫是时应未见其他本,据此推断,赵孟頫观帖并书题的时间是至元二十三年。
二是《四朝闻见录》附录《晋王大令保母帖》记载,仇远至元二十四年曾于弁阳山房见周密所藏《保母帖》,题曰:“丙戌冬,伯几出《保母帖》相示,命题诗。”[12]由此可知,仇远至元二十三年于鲜于枢处观赏其所藏《保母帖》并题诗。诗云:“我爱《保母帖》,人传中令书。不须疑断缺,幸是出耕锄。芸阁砖何在,《兰亭》字偶如。周姜题品重,瓦石亦璠玙。”[13]关于仇远其人,少为人知的是其除了文学家的身份外,亦是书法家,《书史会要》有其小传。戴表元《杨氏池堂燕集诗序》中记载参与周密至元二十三年组织的杨氏池堂宴集中的人中有仇远,可知仇远是年在杭州。如此,仇远至鲜于枢处观《保母帖》,应是他这年在杭州参与的文人活动之一。
综合上述两条记录,鲜于枢处《保母帖》的观咏情况为:赵孟頫与仇远至元二十三年观帖,赵孟頫书题,仇远题诗。
关于此藏本的流传过程,刘楚《跋北山上人所藏晋献之保母帖》中有云“往年见藁城倪中为钱塘沈彦中跋献之保母墓志拓本,引宋姜尧章记……倪中云彦中得此帖于监书博士柯敬仲家……今获观此帖于北山上人许。考其印识,皆鲜于伯机甫名,乃伯机甫以前元丙戌得之武林市肆”[14],据此推断其流传过程为:鲜于枢—柯九思—沈彦中—北山上人,中间或许还有他人,今不可考。
此帖在鲜于枢手中时,仅有赵孟頫与仇远两位观帖者记录,后传至他人,亦是只有零星记载。上文提到,倪中曾在沈彦中处观帖并作有跋文,刘楚《跋北山上人所藏晋献之保母帖》中谈及,还有一“不著名姓,乃云己丑正月四日见别本于教授曹彦礼家”[15]。己丑在元代有至元二十六年与至正九年,据后文中“此跋当是元至正间翰林诸老所题”[16]推断,上文所说己丑应是至正己丑。也就是说,当时有一位观帖者,于至正九年在曹彦礼家见到与鲜于枢本不同的《保母帖》,并将此事记于其在鲜于枢本《保母帖》所作的跋中。鲜于枢大德六年去世后,此帖传至柯九思与沈彦中,而柯九思至正三年已辞世,因此,文中所提翰林诸老可能是至正九年至沈彦中处观其所藏鲜于枢本《保母帖》。
因此,结合前文所述,鲜于枢本《保母帖》可考元代题跋者有:仇远﹑赵孟頫﹑倪中﹑刘楚,还有一不著名姓者。
(二)周密本《保母帖》
周密,字公谨,号草窗﹑苹州等,入元后定居杭州。不仅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元初杭州书画收藏界的核心人物,与赵孟頫﹑鲜于枢来往密切。家藏甚富,“多藏法书名画,以鉴赏游诸公”[17]。王献之《保母帖》便是其所藏书画之一。
周密本《保母帖》历代观咏活动的记录,为清人鲍廷博附在叶绍翁所撰《四朝闻见录》戊集后的《晋王大令保母帖》中。鲍廷博在刊刻知不足斋本《四朝闻见录》时,“以卷末有‘秘书曲水砚’一条,详及王大令保母墓砖”[18],为“校绍翁所记曲水砚事”[19],“取高江村家所藏周草窗拓本钜卷及宋﹑元名流题识,手录一卷,附刊卷末”[20],并谈到“当时模拓甚少,世罕流传。独弁阳翁周公谨所遗钜卷……予偶得寓目,亟手录之,尽二十余纸”,可见周密本《保母帖》在元代观咏活动的盛况。
为便于下文叙述,此处先交代周密本《保母帖》在元代的流传线索。据《晋王大令保母帖》中的记载,周密本《保母帖》在元代三易其手。延祐六年,汤炳龙在方天瑞白云书房观其所藏《保母帖》后言“予三十年前草窗家观此帖。当时欲题数语,匆匆未暇也。今解后白云山中人,又见之于是,弁阳翁已捐馆久矣……诸老品题咸在焉”[21],可知方天瑞所藏《保母帖》正是元初周密本。后至正十年尧岳跋张子英闲止斋所藏《保母帖》中谈及此帖之来历时说道“弁翁周公瑾之收藏,白云方氏之储蓄”[22],这不仅佐证了方氏家中所藏书帖来自周密,也说明其于闲止斋所见《保母帖》是张子英从方天瑞手中所得。如此,周密本《保母帖》的流传过程便清晰可见:周密—方天瑞—张子英。这三位《保母帖》的收藏者在元代皆发起了一定规模的《保母帖》观咏活动。
1.至元﹑大德年间周密处
《晋王大令保母帖》记载,至周密家观赏《保母帖》的人员共计26 人。其中,帖上题诗者有十位,分别为鲜于枢﹑仇远﹑白珽﹑邓文原﹑王易简﹑王沂孙﹑王英孙﹑龚开﹑盛彪和郭天锡,这些人所题之诗,算上周密本人所作,共计有十二首。除诗歌外,《晋王大令保母帖》还载有张坰﹑仇远﹑吕同老﹑鲜于枢﹑俞德邻﹑汤炳龙﹑郭景星﹑张谦﹑胡长孺﹑白珽﹑祝宜孙﹑龙仁夫﹑杜与可﹑龚开﹑赵由礽﹑汤垕﹑赵孟頫﹑钱国衡一行人(与上述所列题诗者有重合)所作的其他题跋内容,多数人所题仅记录此次观赏之行,此处不一一列举。
上述众人至周密处观其所藏《保母帖》共有三处地点,一是三秀堂,“秦川张垧谨观于弁阳翁三秀堂”。一是弁阳山房,仇远所题有云“重见此帖于弁阳山房”。还有一处是浩然斋,赵孟頫﹑赵由礽﹑钱国衡皆于此处有题。
《(民国)杭州府志》中关于“浩然斋”的记载如下:“周密晚年寓居钱塘癸辛街,作《癸辛杂志》《浩然斋视听钞》”[23]。赵孟頫寄周密钱塘寓居诗云:“三年漫仕尚书郎,梦寐无时不故乡。输与钱塘周老子,浩然斋里坐焚香。”[24]又,周密《弁阳老人自铭》中有言:“异时故巢倾覆,拮据诛茅,至是又为杭人矣。所居有志雅堂﹑浩然斋﹑弁阳山房。树桑艺竹,垒台疏池。间遇胜日好怀,幽人韵士,谈谐吟啸,觞咏流行。酒酣,摇膝浩歌,摆落羁絷,有蜕风埃﹑齐物我之意。客去,则焚香读书晏如也。”[25]可知弁阳山房﹑浩然斋皆在杭州,是周密生活和接待友人的处所。至于三秀堂,现存资料中未见明确记载,但亦应在杭州。
周密处《保母帖》观咏活动集中在至元﹑大德年间,恰好赶上了元初三十年杭州书法鉴赏的黄金时代,一批艺术家聚集杭州品评鉴赏书画[26],这也解释了为何周密处的《保母帖》观咏活动在元代最为丰盛和频繁。我们可从周密处观咏者的身份来看周密的交友网络,并借此管窥元代杭州文人的组成结构。
至周密家观帖二十六人之身份颇为不同,有文学家﹑书法家,有画家﹑鉴赏收藏家﹑刊刻家,有周密的词友,绝大多数人为南宋遗民。下文分类论之。
文学家兼书法家有六人:赵孟頫﹑鲜于枢﹑仇远﹑邓文原﹑龚开和白珽,皆收录于元典籍《书史会要》中。赵孟頫﹑鲜于枢与仇远的情况不再赘述,其他三人身份如下。
邓文原,字善之,至元二十七年行中书省辟为杭州路儒学正,他至周密处观帖应正是在他此次任职时。虞集《跋鲜于伯几与严处士翰墨》中云:“大德﹑延祐间,渔阳﹑吴兴﹑巴西翰墨擅一代”[27]。文中说的三人便是鲜于枢﹑赵孟頫与邓文原,可知邓文原在元初是与鲜于枢﹑赵孟頫齐名的书法大家。“正﹑行﹑草书,早法二王,后法李北海”[28],邓文原同赵孟頫一样,在书法上追求“唐法晋韵”。
龚开,字圣与,号翠岩,淮阴人。故宋遗民,入元不仕。袁世硕《解识龚开》一文从现存的文献资料对龚开的行迹作了考证:“他入元后交往的人物,大都是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人,即使不是浙江人也是曾经到过杭州的,说明他的活动主要在杭州。”[29]这也正好说清了他此时为何至周密杭州宅邸观帖。《书史会要》评其书法“作古隶,得汉魏笔意”[30]。
白珽,字廷玉,号湛渊,钱塘人。元初与仇远皆以诗名,与戴表元﹑赵孟頫﹑邓文原等人来往频繁,经常参与书画鉴赏题跋,是元初杭州文人圈的主要人物之一,德望清重,书学米元章。
元代画家﹑鉴赏收藏家有:
郭天锡,字佑之,号北山,山西大同人,至元二十三年任镇江路判官,二十九年得代。其私人所藏,收录于周密《云烟过眼录》《志雅堂杂钞》﹑鲜于枢《困学斋杂录》等书中,几种书内所列郭氏藏品中仅书帖就有几十种,可见其对古人字帖之兴趣。家中所藏甚富,也由于此,奠定了其在元初杭州书画鉴藏圈的重要地位。
张谦,字受益,号古斋,济南人。家蓄古物甚富,以博古称。至元间为江浙省掾,除检校,大德中累迁秘书监丞[31]。周密《云烟过眼录》记其所藏,应同郭天锡一样,为元代杭州鉴藏圈中重要成员。
王英孙,字才翁,号修竹,绍兴人,宋将作监簿,入元隐居不仕,作墨竹兰蕙,颇雅洁不凡[32]。周密《弁阳老人自铭》题下有“表弟前承议郎王英孙填讳”字,可知他除了画家的身份外,还是周密的表亲,并且同周密一样,“喜延致四方贤士,日以赋咏为乐”。
钱国衡,字德平,宋末元初人,入元不仕。以刊刻《兰亭十刻》闻于世,明代汪砢玉所撰《珊瑚网》中《墨花阁杂志》一节记载:“元大德间,钱塘钱国衡刻十种《兰亭》,笔法咸有异趣。南宋内府五十余种,与韩氏群玉堂﹑贾氏悦生堂本,尔时犹有存者,故国衡得选其萃耳。”[33]从上述资料中,知钱国衡《兰亭十刻》来自故宋内府与民间私人所藏,由其甄选刊刻。由此推测,是时钱国衡应是杭州书法鉴藏界的重要人物。
汤炳龙,字子文,山阳人,元代画家汤垕之父。明代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三《高尚书夜山图》众人题跋中汤炳龙题诗落款后有“淮人居杭授同知以文学名”一行字,可知他曾在杭州为官,因文学而知名于当时,戴表元为其作过《汤子文诗序》。与赵孟頫﹑仇远﹑邓文原等人经常参与同一书画观赏活动(未必同时),并留下题跋,如明代汪砢玉撰《珊瑚网》卷三十名画题跋六中的《江参百牛图》下,就有汤炳龙﹑邓文原﹑白珽等人题;又如明代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二《瓮牖图》下同题者有汤炳龙﹑赵孟頫﹑倪瓒等人。如此看来,汤炳龙应是元代书画鉴赏圈的一员。
周密之词友则有王易简﹑王沂孙﹑吕同老诸人,皆是宋遗民,与周密唱和往来。三人生平如下:
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又号中仙,会稽人。有《碧山乐府》二卷,又名《花外集》[34]。戴表元《杨氏池堂燕集诗序》一文记载了元初众人聚集周密杭州处所的一次雅集活动,其中便有王沂孙:“丙戌之春……王沂孙圣与﹑鄞戴表元帅初……皆客于杭。”由此看来,其不仅是周密的词友,亦是戴表元的文友,活跃于元初杭州文人圈内。
王易简,字理得,号可竹,山阴人。登进士第,除瑞安主簿,不赴,隐居城南,有《山中观史吟》[35]。
吕同老,字和甫,号紫云。济南人,有词见《乐府补题》,宋遗民。
其他南宋遗民还有:
俞德邻,字宗大,号太玉山人,永嘉人,徙居京口。咸淳癸酉登进士,以文章负世重望[36]。入元不仕。有《佩韦文集》十六卷,《辑闻》四卷,紫阳方公回﹑建安熊先生禾为之序[37]。
汤垕,字君载,号采真子,汤炳龙之子。妙于考古,精于书画鉴赏,在京师时与鉴画博士柯九思论画,遂著《画鉴》一卷。
郭景星,字符德,自号义山,镇江人,画家郭畀父。
胡长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38]。《元史》卷一百九十有传。元代蒋易《皇元风雅》中辑其诗若干首,其中有《题开元三马图》《题风雨渔舟图》《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后》《题醉王母图》等书画题跋,可见其爱好文雅,颇通文艺。
祝宜孙,延平人,成宗元贞元年为余干州教授。
龙仁夫,字观复。号麟阁,江西永新人。博究经史,以道自任。仕元为湖广儒学提举,晚年侨居黄州。著《周易集传》十八卷,文尤奇逸流丽,学者称麟洲先生[39]。
杜与可,曾任休宁县检校官,后出任兵部郎中。
盛彪,字元仁,号虎林,临安人,官至镇江学正,南宋遗老,为人“清介可重”。至元三十一年曾与仇远同观《唐人书七宝转轮王经墨迹》于鲜于枢困学斋,又“尝教授官馆于伯机太常家”[40],可见其与鲜于枢﹑仇远皆颇有交情,亦是元初杭州文人圈的一员。
赵由礽,不可考。但同他一起观帖之罗伯寿(《晋王大令保母帖》记载:“至元辛卯中秋日弁阳翁出示此卷,命题数语。然才思蹇涩,未能即就,姑识岁月云。清江罗伯寿志仁同观。大梁赵由礽识。”)其人,则可考之一二。明代余之祯所撰《吉安府志》简略记载其生平:“罗伯寿,泰和人,习举业,工八韵有声。”罗伯寿曾题赵孟頫所画的《赵文敏水村图卷》,而赵孟頫有《酬罗伯寿》一诗,知二人有文学和艺术上的往来。
张坰,秦川人。其他未详。
综合上述观咏者身份信息,除鲜于枢外皆为由宋入元之人,可见周密当时的交友范围主要在宋遗民中,杭州本就是宋遗民聚集之处,地利与人和,不难成就这样大的观帖规模。同时,从书法家﹑画家﹑鉴赏收藏家﹑刊刻家﹑词人等观帖者的不同身份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元代杭州文人的结构组成,虽不能全面覆盖,但足见是时杭州文人身份的多元化。
2.延祐﹑泰定年间方天瑞处
上文已说到,周密本《保母帖》后传至方天瑞手中。关于方天瑞其人,汤炳龙曾于白云书房观《保母帖》后题:“天瑞,天目间气人物,元英先生后人也……自号义斋。”仇远有诗《锦城方天瑞玄英先生后人得白云山居图彷彿桐庐山中隐所钱舜举真迹别有一种风致漫系以诗》,诗末记“延祐四年九日,书于杭城北桥”。马臻亦有诗《为义斋方山长赋青山白云图》:“玄英先生钓鳌手,结庐正对桐江口。坡陀四面环青山,山上白云终日有。青衫博士居临安,万山绕屋心自闲。松竹林中读书处,白云往往来其间。玄英隐处昔曾见,出岫无心如有羡。为与先生芳谱联,臭味相同故相恋。老我营得屋数椽,钱塘湖上连秋烟。青山白云夙所爱,为君写入图中传。”[41]据上述信息可知,汤炳龙所说“元英”之“元”应是“玄”字之避讳,玄英先生为唐代诗人方干,方天瑞为其后人。延祐四年,方天瑞得《白云山居图》,方氏白云书房之名应由此而来。又据仇远与马臻之诗,知白云书房坐落于浙江杭州。
周密本《保母帖》如何传至方天瑞手中,目前未知。但从方天瑞同仇远﹑马臻﹑白珽等人的交往来看,他们在元代同属于一个文人交际圈。既然如此,方天瑞与周密亦应有交集,周密去世后,方天瑞通过某种方式得到周密本《保母帖》,由此开启了方氏白云书房的观帖活动。
延祐六年,汤炳龙于方氏白云书房观《保母帖》,后于保和读易斋(李齐贤《益斋集》中记载汤炳龙曾为李齐贤画像作题赞,赞后落款为:“延祐己未九月望日,北村老民汤炳龙书于钱塘保和读易斋,时年七十有九。”可知保和读易斋位于杭州)。作诗并书题。同年,天目山云溪某人(《晋王大令保母帖》:“天目山云溪□庆书。”后有:按元迹“溪”下似“公”字,又似“台”字,莫辨”)。第二次来到白云书房,“得观此帖,不暇题品,以俟重来餍玩以续之”[42]。同时期,冯海粟观于白云书房,“义斋邀过其藏书之舍,首出此卷相示”,冯海粟题诗并对世人怀疑王大令《保母帖》真伪一事作了辩驳。泰定二年夏,白珽重观于方氏白云书房。
汤炳龙所书题中首句云“予三十年前草窗家观此帖”,当是时,与他同至周密处观帖的人中就有白珽(《晋王大令保母帖》原文载:“永嘉俞德邻﹑山阳汤炳龙﹑京口郭景星﹑济南张谦﹑东阳胡长孺﹑钱唐白珽﹑延平祝宜孙同观。”延祐六年上推三十年,是至元二十七年)。巧合的是,三十年后,汤炳龙与白珽又先后至白云书房观同一帖。事实上,二人一直有来往,私交甚好,《湖州路西湖书院增置田记》的石刻便是汤炳龙撰,白珽书,加上廉希贡篆额,三人合作完成。
去白云书房观帖之冯子振,号海粟,攸州人,召为承事郎﹑集贤待制。当时亦以文名天下,是元代的散曲家﹑诗人﹑书法家。清代黄文玠曾评价道:“湘之人,能传数百载者,在宋为王公南强(王容),在元为冯公海粟……至海粟公以集贤院学士与赵王孙辈文采风流,掩映一时,清词丽制,层见叠出。”[43]黄之评价一是说他是元代湖南人中的文学翘楚,二也提及了其在集贤院与赵孟頫等人的文学交往。冯子振本身也是书法家,崇尚二王翰墨,其与赵孟頫除以文学相交外,还因书法颇为相投,扬州《汉寿亭侯祠碑记》便是由冯子振撰文﹑赵孟頫书写的。
至治元年,赵孟頫作《方外交疏》云“处西湖之上,居多志同道合之朋”,文末所列好友名单中有廉希贡﹑仇远﹑汤炳龙﹑邓文原﹑冯子振﹑马臻﹑张雨等人。据此,冯子振至治元年(1321)应在杭州,其至方氏白云书房观其所藏《保母帖》应在是年或前后,不会差距太远。
3.至正年间张子英处
周密本《保母帖》在元代的最后一站是张子英处。关于张子英其人,黄溍《闲止斋记》有曰:“钱塘张子英,生宦家,且居今盛时,而雅不乐仕进,日以篇翰自娱。尤嗜渊明诗,摘其语匾所居室,曰间止斋,而属予记其所以名之义。”[44]可知张子英为钱塘人,仕宦之后,好雅,隐居不仕,而闲止斋为张子英所居之处。贡师泰《密庵记》有言“子英谓予曰:‘闲止在西湖故宅之东’”[45],又可知,闲止斋的位置临近西湖。元代为张子英闲止斋作诗者有数人,如袁华作《过张子英闲止斋阅法书名画归湖上以纪》﹑黄玠作《张子英闲止斋》﹑刘基作《张子英闲止斋三首》,这些诗作不仅说明了闲止斋在当时是知名的私人文化会所,时常有文人往来,也可从中看到张子英的交友情况,可以说是元末文人圈的局部投影。
至正九年,钱塘俞和同杨炳﹑李嗣儁观于张氏闲止斋。至正十年,尧岳观于张子英处并作跋。在此跋中,尧岳交代了周密本《保母帖》的流传线索以及历来题跋者名单“赵子昂﹑鲜于伯机﹑郭佑之﹑龚翠岩﹑胡石塘﹑龙麟州﹑盛虎林﹑冯海粟﹑邓善之﹑汤北村﹑仇山村﹑白湛渊”,并评述了周密本《保母帖》与赵孟頫﹑鲜于枢藏本的不同,“今钱塘张君子英以簪缨之华裔,好古博雅,一旦得之,藏诸箧笥,复有先辈亲染翰墨如此之多,手泽具存,可敬可爱。宇宙之间,唯此一本。松雪﹑困学,虽亦有之,而无是连篇累牍之跋语,相去远甚”,不同之处即是周密本《保母帖》上诸公题跋之数量远胜于赵孟頫﹑鲜于枢二人的藏本,这也可作为后世区分《保母帖》藏本的依据。至正十四年,林彬祖观《保母帖》并题诗,从其所题诗中“闲窗止水阅万变,人琴寂寞悲浮云”一句,可知观赏地点亦是闲止斋。
此外,张雨至正九年曾于浴鹄湾阅帖并题诗。《晋王大令保母帖》将此则记录夹在俞和与尧岳观帖活动中间,其意图所指应是张雨所阅之帖为张子英所藏周密本《保母帖》。考张雨所言之浴鹄湾的地点,明代释大壑撰《南屏净慈寺志》卷一形胜“湾里”条载:“浴鹄湾在赤山港口,其水曲,为浴鹄湾,张伯雨尝构水轩栖。”可知浴鹄湾位于杭州,靠临西湖,而“闲止在西湖故宅之东”,如此看来,两者距离应不会太远。又,张雨在黄溍《闲止斋记》一文完成后,另作《闲止斋诗有序》,与张子英从另一角度探讨“闲止”之意,文后附诗《闲止斋诗为张子英赋》,可见张雨与张子英交情颇深。尧岳至正十年在张子英闲止斋所见《保母帖》的诸老题品中,未见张雨之名,应是张雨于自家题诗,是时未与其他人之题跋攒聚一处,后人收录时,按书题之时间重新作了排序整理,故而有了我们今日所见之《晋王大令保母帖》中的安排。
至闲止斋观帖之俞和,字子中,号紫芝生,武林人。元代陶宗仪所撰《书史会要》中记载:“真﹑行﹑草书皆师赵魏公。其合作者,用公款识,殆不能辨真赝。”[46]解缙《书学传授》中亦提到了其师事赵子昂:“独吴兴赵文敏公孟頫始事张即之,得南宫之传,而天资英迈,积学功深,尽掩前人,超入魏晋,当时翕然师之……及门之徒唯桐江俞和子中以书鸣洪武初,后进犹及见之。”[47]综合上述两则材料知,俞和书法学赵孟頫,得其几分真传,待至明初颇有成就。
杨炳﹑李嗣儁,不可考。
尧岳,字子泰。杨基至正二十六年在考其祖父杨枢之交游者中云:“乡先生题其卷者凡八人……其六人,则响林陈先生者,先大父之忘年交。克明曹先生﹑天锡郭先生﹑君辅青阳先生﹑用中俞先生﹑子泰尧先生,皆大父之友,而尧又先人授业之师也。”[48]可知,尧岳与郭畀皆是杨枢之好友,又,元代郭畀所撰《云山日记》中多次出现尧子泰之名,二人亦应颇为相熟,相以文交。
林彬祖,字彦文,丽水人,至正乙酉进士,为永嘉丞,曾任江浙省都事,至正间任从侍郎,后进福建行中书省检校官,《(光绪)永嘉县志》存其资料,《全元文》有录。元末明初的刘基﹑王袆与其均有唱和,刘基作过《次韵和林彦文刘山驿作诗》,王袆作过《次韵奉答林彦文参谋》。而刘基与王袆都曾为张子英闲止斋作过诗文,如此看来,林彬祖与张子英应同属于一个文人圈,彼此往来,才有其至闲止斋观帖一事。
综上,周密本《保母帖》是元代观咏人数最多的藏本,时间跨度极大,均集中在杭州。实质上,三次观咏活动不仅是分别以周密﹑方天瑞﹑张子英三人为核心的文人圈人际往来,也是元代杭州文人活动在不同时段的三个组成部分。
(三)赵孟頫本《保母帖》
赵孟頫至元二十四年得到《保母帖》后,并未举办集中的观赏活动,至元二十六年时,他便将此帖送给了鉴藏家郭天锡,郭天锡在《保母帖跋》中言“至元己丑九月,获于赵兵部子昂”[49]。郭天锡得到《保母帖》后,曾将赵孟頫本《保母帖》与其他本作过比较,“及来杭,与别本较之,大不同,然未易与口舌争。深晓王氏书者,乃能知之。”其后题诗中亦有云:“兰亭贵重玉石刻,云是率更脱真迹。至今真赝乱纷纭,争似王书亲入石。”郭天锡意在说明其手中赵孟頫本《保母帖》与其在杭州所见其他本有出入,并且“大不同”,但具体如何不同,却未言明,也未谈及比较的对象。姜夔为《保母帖》所作的题中早已有言“有数人刻别本以乱真者”,结合郭天锡所见,现世的《保母帖》(不一定是本文论述的六种版本)的确真假掺杂,或许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有熟识王献之书法之人,才能辨别真伪。
至大二年,赵孟頫于范乔年处,重见当年自己送给郭天锡的《保母帖》,为其题:“吾旧藏此《保母帖》,郭右之从吾求,乃辍以与之,不意十五年后重见之也。《保母帖》虽晚出,然是大令无恙时所刻,与世所传临摹上石者万万也。至大二年七月廿日为范乔年题。”[50]后至正十七年,陈从龙观赵孟頫本《保母帖》并题:“今是帖,自子昂四传而至豫章龚本立……至正十七年六月廿日长沙陈从龙题《保母帖》后”[51]。
赵孟頫本《保母帖》的流传情况,上文已显现出清晰的线索:赵孟頫—郭天锡—范乔年—龚本立。赵孟頫本《保母帖》可考元代题跋者有郭天锡﹑赵孟頫﹑陈从龙三人。
(四)袁易本《保母帖》
袁易本《保母帖》记载较少,目前仅知其为袁易旧藏,上中有袁易﹑袁桷之方印,观帖者元代仅知袁桷一人,此帖后传至明人林敬伯手中。
以上就是元代《保母帖》观咏活动的具体情况。
三 元代《保母帖》观咏活动兴盛之原因
如上文所述,元代《保母帖》观咏人数众多,时间跨度大,不可不谓元代书法领域的大事。究其兴盛之原因,与元代书法的宗晋之风有关。元代提倡“复古”,书法领域亦是,如赵孟頫曾在《定武兰亭跋》中说:“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52]而书法上的“复古”之“古”,在赵孟頫的引领下,指的就是魏晋之法,更具体说就是宗“二王”,即王羲之与王献之。赵孟頫极为推崇“二王”,其有《论书》一诗:“右军潇洒更清真,落笔奔腾思入神。《裹鲊》若能长住世,子鸾未必可惊人。苍藤古木千年意,野草闲花几日春。书法不传今已久,楮君毛颖向谁陈。”[53]赞叹王羲之书法出神入化,艺术的生命力长盛不衰。赵孟頫作为元初文艺领域的领袖人物,其对“二王”之书的推崇,不仅代表了当时书坛的主流,也影响着元代书坛的发展走向。
而在《保母帖》的诸多题跋中,处处可见当时宗晋之风的影响。如周密题诗首句云“王郎擅风流,笔墨美无度”,邓文原兼论“二王”曰“右军天机精,笔端走风云。万世有能事,仰之道弥尊。后来独超诣,乃有中令君”,郭天锡高抬王献之之地位说“八百余年保母辞,献之笔法似羲之。断碑剥落百余字,高作欧颜千世师”,这些题跋的内容,已经超出了《保母帖》本身,皆是直指“二王”在书法领域的地位和功绩。可以说,《保母帖》观咏活动就是赵孟頫引领的元代书法领域宗晋之风的产物。并且,赵孟頫得到保母碑拓本时,曾对其作了极高评价:“世人若欲学书,不可无此。”宗晋之风的影响与这样高的基调在此,《保母帖》在元代如何不受重视。
到了中后期,脱离了元初鉴赏热潮,不论是《保母帖》的收藏者还是观帖者,除了因宗晋之风的影响对《保母帖》本身好奇和欣赏外,还因《保母帖》上有诸多名人题品为其增添了价值,而对这一份有额外文化意义的“神物”更为珍藏。如汤炳龙在白云书房观帖后题“诸老品题咸在焉……于是喜而为书此诗云”[54],汤炳龙三十年前在周密处观此帖,三十年后再见,风云变幻,此时已不是最初观帖时的惊艳,而是对那一段往事的追忆,过往如在眼前。又如尧岳在闲止斋观帖后有云:“今钱塘张君子英以簪缨之华裔,好古博雅,一旦得之,藏诸箧笥,复有先辈亲染翰墨如此之多,手泽具存,可敬可爱。宇宙之间,唯此一本……子英复有贤子秉中甫为之嗣续十袭而珍祕之,斯帖得所托矣。”[55]张子英手中的周密本《保母帖》上先辈题跋众多,这也是让他及后代对此帖视若珍宝的原因。
事实上,《保母帖》在元代流传最大的意义就是用于人际交往,查洪德先生在论述元代文坛的题画之风时曾谈到,元代文坛的题画活动是文人间的一种交谊方式,“为画题诗是一种机缘,通过这一机缘,将众多文人连接在一起”[56]。同题画一样,观帖,亦是一种高雅的交谊方式。元代《保母帖》观咏活动正是这一文人交往方式的体现,它不仅是元代文艺领域观帖之风的一个缩影,在书法史层面之上的,《保母帖》的流传和鉴赏,还是元代文人活动的见证。我们不仅可以借《保母帖》观咏活动来管窥元代文人的关系网络,还可从书帖的流传线索中目睹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