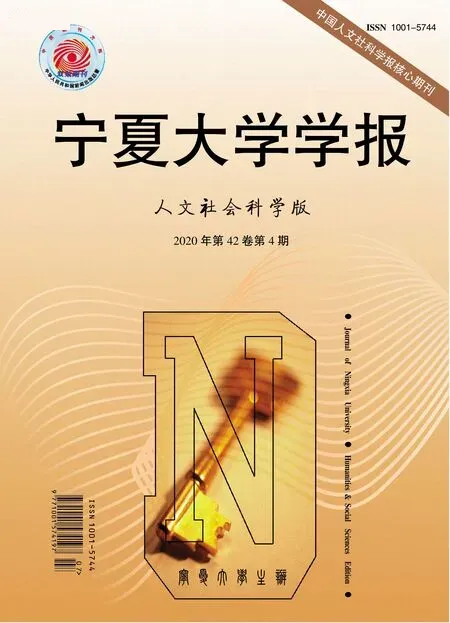是“列巴”还是“裂粑”
向德珍,马莉敏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 200444)
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先生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被誉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此书第四章“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中,将近代汉语里的外国借字分作四项:(甲)声音的替代(phonetic substitution);(乙)新谐声字(new phoneticcompound);(丙)借译词(loan-translation);(丁)描写词(descriptive form)。在(甲) 声音的替代(phonetic substitution)下又分四类:(1)纯译音的;(2)音兼义的;(3)音加义的;(4)译音误作译义的。在其中的“(2)音兼义的”部分罗常培所举例子当中,有一例这样写道:“哈尔滨管面包叫裂粑(хлеб)”[1]。罗常培认为这个来自俄语的外来词翻译方式是音兼义译的,即在书面翻译时所选用的汉字既与源词谐音,又兼顾了源词的意义,“裂粑”大约是有裂纹的像粑粑一样的块状面类食物之义。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不符合语言事实的错误,这种由俄罗斯传入的主要由面粉﹑荞麦﹑燕麦﹑酒花和盐等烤制而成的面包,在书面翻译时不应写作“裂粑”而应写作“列巴”(或其他形式,考虑到罗先生作书的时代是20 世纪40 年代,当时对外来词的书写形式还没有统一规范),此词的翻译方式并不是音兼义的,而是纯译音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此外来词的读音。此外来词既然是在哈尔滨地区首先使用,那么就应该考察哈尔滨人民对此词的读音。笔者调查了几位哈尔滨人(本科生崔东川等同学课上给我们提供了此词读音,并提出了一些见解,非常感谢)念此词为liěba(第二个音节念轻声)。既然第二个音节念轻声,那么就不应该写作“粑”;既然第一个音节念上声,那么就不含“裂开”之义。尹世超主编《东北方言概念词典》也标注此词的读音为liěba[2]。
根据学界的研究,这种俄式面包是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俄国传入哈尔滨的。关于其来源,学界历来主要有2 种说法:一说认为大约是在1945 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带来了俄式面包“列巴”(暂先记作“列巴”,下同)。二说认为1898 年俄国人在哈尔滨修建中东铁路,大量俄国人涌入哈尔滨。1900 年俄国人伊·雅·秋林在哈尔滨创立了“秋林洋行”分号,在此基础上开辟食品加工产业,于是哈尔滨有了俄式面包“列巴”的制作工艺,“列巴”首先在东北地区流行开来。时至今日,秋林公司生产的大列巴仍然声誉最佳[3]。刘定慧的文章《俄源词“列巴”在汉语中的发展演变研究》根据前人的相关研究,推测“列巴”更有可能是在1945 年以前就已传入哈尔滨,第二种看法更令人信服[4]。笔者通过提供直接的书面语言的事实证据也认为第二种看法更令人信服,第一种看法属不经之谈。例证如下。
民国才女作家萧红1936 年出版的散文集《商市街》[5]里已经出现了多处“列巴”(包括由“列巴”衍生出的词语“列巴圈”“大列巴”“小列巴”等)。例:
(1)“列巴,列巴! ”哈尔滨叫面包作“列巴”,卖面包的人打着我们的门在招呼。(萧红《商市街·提篮者》)
(2)厕所房的电灯仍开着,和夜间一般昏黄,好像黎明还没有到来,可是列巴圈已经挂上别人家的门了!有的牛奶瓶也规规矩矩的等在别人的房间外。(萧红《商市街·饿》)
(3)偷就偷,虽然是几个“列巴圈”我也偷,为着我“饿”,为着他“饿”。(萧红《商市街·饿》)
《商市街》描写了20 世纪30 年代萧红和萧军二人结合后从暂住哈尔滨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欧罗巴旅馆,到筑巢哈尔滨商市街25 号铁路局姓汪的庶务科长家耳房的一段饥寒交迫﹑穷困潦倒而又快乐的生活。《商市街》中还有篇散文题名就叫《黑列巴和白盐》,文中写道:“黑列巴和白盐许多日子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可见当时“列巴”在哈尔滨已是常见食物。再看1959 年出版的《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六十年》里也出现有“小列巴”。例:
(4)午睡后,还有歇晌饭,吃的是蜂蜜小列巴和葡萄干﹑沙糖﹑大米三合一做的饭,吃起来十分香甜。(哈尔滨车辆工厂厂史编辑组编《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六十年》,在富拉尔基别墅)[6]
此句例记述的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可见当时在哈尔滨已经有了列巴。
不仅如此,当时的上海也已经有了这种“列巴”,例证是当时居于上海的鲁迅先生1935 年7 月29 日写给萧军的信:
(5)我们近地开了一个白俄饭店,黑面包,列巴圈,全有了。[7]
据田飞﹑李果所著《寻城记·武汉》,在20 世纪30 年代的汉口也有了这种俄式面包,例:
(6)邦可西餐厅是当年武汉最正宗的一家俄式餐厅,由俄国人邦可和面包师扬格诺夫开设于1930 年,主要经营俄式西点和西餐,其精心烹制的罗宋汤﹑牛扒﹑鱼子酱以及俄式大列巴﹑馅饼﹑蛋糕等都是当时汉口市民最为喜爱的西式美味。(田飞﹑李果著《寻城记·武汉》,三教街公寓)[8]
由以上这些书面语言上的证据可以看出,显然早在1945 年之前这种俄式面包就已传入哈尔滨,并由哈尔滨流行到了中国其他地区,前述关于俄式面包“列巴”来源的第一种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第二,从最初此外来词的书面写法来看此词的翻译方式,仍然应该考察早期哈尔滨地区人民对此外来词的书写形式是怎样的。
前文提到,哈尔滨人萧红1936 年出版的散文中此外来词比较早期的写法是“列巴”,作家萧红并没有语言学专业知识,她当时在文中应该是采用了从俗从众的写法,如实反映了当时哈尔滨地区人民对此外来词的比较通行的书写形式——列巴。此写法透露出此外来词当时是以一个纯译音的方式进入汉语中的。
再看时间稍晚一些的例子,1947 年8 月25 日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鸣谢启事中也提到了“小列巴”。
(7)……洗头粉二十四盒,刷子二个,药布三匹一小卷,胰子二百六十二块,小列巴二个,牙粉四百八十六包,牙刷九十一把……(哈尔滨市档案馆编《哈尔滨市支援前线1946-1949》)[13]
此例与罗常培《语言与文化》成书的时间大致相同,也算比较早期的例子,写作“列巴”。
因此,从最初的传入地哈尔滨地区人民对此外来词的书面写法“列巴”来看,此词当初应该是以纯译音的方式传入的,而不是罗书所认为的音兼意译的方式。
第三,哈尔滨方言中根本就没有表示块状米面类食物之义的“粑”。朱建颂《方言与文化》[14]中说:“粑,今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山东﹑山西﹑广西的一些地方都用此字。”蒋宗福《四川方言词语续考 上》[15]列举了“粑”字的多个使用地域,也不见列哈尔滨。我们搜阅了包括方言词典等多部论著,均未发现“粑”字有用于哈尔滨方言的记录,这也和我们调查来自黑龙江的几位本科学生的结果相一致。因此,对首先流行于哈尔滨地区的俄式面包的翻译用字,根本不可能使用“粑”字。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对此外来词进行了考察,说明此外来词是纯译音词,书面翻译上不应该写作“裂粑”。
至于到底应该写作什么,我们应该坚持从俗和统一的原则。所谓从俗的原则,就是看此外来词通常被人们写作什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些文献作品中的写法。
早期提到此外来词的文献作品中,基本都将此词写作“列巴”,例如前文提及的萧红在1936 年出版的《商市街》和鲁迅先生在1935 年写给萧军的书信,都早于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作于1943-1949年),对此外来词一律写作“列巴”。前文提及的1959 年出版的《三十六棚——哈尔滨车辆工厂六十年》也写作“列巴”。
现今的文学作品和文献资料中也大都写作“列巴”。
(8)那天下午,我在阿合买提江街,一家俄罗斯人的面包房,买了两个嵌满各种干果的列巴,焦黄酥香。(亚楠《记忆追寻我》)[16]
又如张丽梅编著的《北国粮仓黑龙江》[17]中:
(9)哈尔滨的大面包叫“大列巴”,个大味美。
(10)“列巴”(音liěba)就是俄语里面的大面包,在哈尔滨,最著名的是秋林公司生产的,它是极富特色的欧式食品。列巴之大实属罕见,重达3~4 公斤。直径最大时可达33 厘米。其味道是甜中有酸,外焦里软。传统的加工方法是将发酵好的面团放在很大的立式烤炉里,采用东北森林里的硬杂木进行烘烤。
现今的语言学著作也写作“列巴”,如许志新著《东北方言解析》:
(11)【列巴】面包[18]
而且,现今的市面上不论是东北还是全国其他地区都在销售这种俄式面包,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两个地方才有了,商品的商标上也是一律写作“列巴”。
虽然也有少数作品和文献资料上写作“列粑”,但那很可能是误写或由误写引起的误传,如:
(12)听说秋林附近卖大列粑,一个好几斤重,买几个给马小子范丫蛋吃,小五小六也吃点。(田平《嫩江原 上》)[19]
(13)每到一站发给数量有限的酸列粑(面包)。(伊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伊春文史资料第8 辑》)[20]
我们看到有少数语言学论著也写作裂粑或列粑。如《汉语外来词词典》第138 页:
(14)黑列巴 面包。又作“列粑﹑裂粑”。源俄хлеб(hleb)。
又如唐作藩所著《汉语史学习与研究》第345页在音译兼意译的一类里列有“裂粑”[21]。詹伯慧和张振兴主编的《汉语方言学大词典 上》第269页,在黑龙江省“北三县”俄语来源方言词里举了“裂粑(面包)”例子[22]。
有的语言学书籍虽写作“列粑”,但是将之归为纯译音类,如唐朝阔和王群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第129 页[23]﹑徐枢著《语素》第45 页[24]。
还有的文献认为此外来词也可写作“咧巴”“裂巴”,如《哈尔滨市志34 宗教 方言》[25]。
我们认为以上不同的写法均应修正过来,规范统一写作“列巴”。虽然一个外来词特别是纯译音的外来词有几种不同的书写形式很常见,但是如果有的写法如“裂粑”会带来误解,就应该禁用这种写法,而且从规范化的角度考虑,最好一个外来词只使用一个翻译书写形式。
综上所述,此俄源外来词应该写作“列巴”,是纯译音外来词,而非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中所说的音兼义译的“裂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