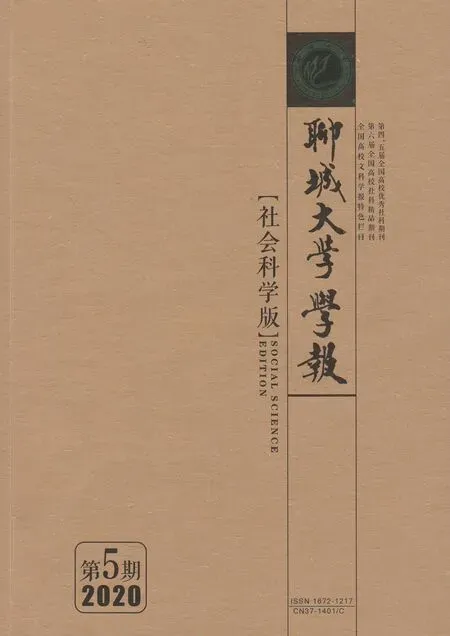论“怨谱”说的诗教内涵及其成因
王良成
(杭州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14)
晚明陈洪绶在评点时人孟称舜的传奇作品《娇红记》时说:“泪山血海,到此滴滴归源,昔人谓诗人善怨,此书真古今一部怨谱也”。①孟称舜:《新镌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古本戏曲丛刊》二集,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1955年,第23册,第93页。在这里,陈洪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怨谱”,“怨谱”说由此产生。关于“怨谱”说的真实含义以及对“怨”字的具体界定,一些学者在不否定“怨”字基本等同于孔子“兴观群怨”之“怨”的前提下,将“怨谱”在理论上界定为悲剧说。事实上,虽然《娇红记》《琵琶记》等剧作主要通过谱写怨艾之情来营造悲剧氛围,但从作品的具体内容及其评点者的真实用意来看,“怨谱”之“怨”显然没有超越孔子“兴观群怨”之“怨”的范畴。因此,正如不能将“兴观群怨”之“怨”界定为悲剧,同样也不能将“怨谱”说理解为悲剧说。另外,正如儒家通过“兴观群怨”等方式来达成诗教的目的一样,陈洪绶、徐渭等人既有通过“怨谱”来教化受众,又有藉儒家的传统诗教理论来提升戏曲地位等用意。
一
王国维先生是较早参照西方悲剧理论和中国古代戏曲发生、发展的实际状况,再结合具体作品的表现形态和审美效果,将中国古代戏曲从题材上区分为悲剧和喜剧的拓荒者之一。根据上述分类方法,王国维先生将《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剧作列为悲剧,并认为上述二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②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84页,第84页。与此同时,他又得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③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84页,第84页。的结论。对于前者,当今学界较普遍认同;对于后者,接受者却不多。除了王季思先生通过《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来证明王国维先生后一种观点的不成立之外,另有学者在对中、西古典戏剧理论和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比较之后,得出了“有剧本流传至今的古典悲剧,大约有以下15部,它们是:《窦娥冤》《赵氏孤儿》《灰阑记》《介子推》《汉宫秋》《梧桐雨》《潇湘夜雨》《琵琶记》《娇红记》《精忠旗》《清忠谱》《鸣凤记》《长生殿》《桃花扇》《雷峰塔》。真正有代表性,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比较高的,还是王季思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所收的十部剧作,它们是:《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琵琶记》《精忠旗》《娇红记》《清忠谱》《长生殿》《桃花扇》《雷峰塔》”①郑传寅:《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8-219页。的结论。
将《琵琶记》《娇红记》列入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悲剧范畴,应无疑问。那么,“中国的全部悲剧观还是以明代的‘怨谱’说作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怨谱说是浸透了中国气派的悲剧学说”②谢柏梁:《中国悲剧史纲》,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年,第180页。是否因此成立?从上述二剧所呈现的悲剧形态以及陈洪绶等人对这类剧作的评点内容来看,简单地将“怨谱”说等同于悲剧说,确实有不少合理因素。在陈洪绶的这条评语中,以“泪山血海”来概括《娇红记》的悲剧成分,可谓言简意赅。《娇红记》是一部反映申纯和王娇娘的爱情悲剧,它表达了当时青年男女“自求良偶”的心愿。“但得个同心子,死同穴,生共舍,便做连枝共冢、共冢我也心欢悦”就是这种心愿的最真实体现。不过,《娇红记》与《西厢记》《牡丹亭》等无媒自娶类的才子佳人剧不同:前者男主人公只要金榜题名,他们“自求良偶”的愿望最终都能顺利实现;后者却是男主人公即使进士及第,他们“自求良偶”的愿望在强大的现实面前依然无能为力,最终只能双双殉情而终。这种剧情架构,显然昭示了《娇红记》的悲剧性质。《琵琶记》的悲剧因素一点也不亚于《娇红记》,该剧反映了衷心遵循封建道德的蔡伯喈一家,当厄运来临时,封建道德既不能使他们免于悲剧性的命运,也不能为他们消除悲剧性的后果。和陈洪绶以“怨谱”概括《娇红记》的主旨相表里,明代著名文人、剧作家徐渭在对《琵琶记》评点时,也将该剧的主题言简意赅地归结为“怨”字。不仅如此,在《琵琶记》的评点过程中,徐渭对“怨”字的阐释比陈洪绶更明确具体。在徐渭看来,“《琵琶》一书,纯是写怨。蔡母怨蔡公,蔡公怨儿子,赵氏怨夫婿,牛氏怨严亲,伯喈怨试、怨婚、怨及第,殆极乎怨之致矣!‘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琵琶》有焉。”③毛声山:《绘风亭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前贤评语》,清映秀堂刻本。在类似上述的批语中,无论陈洪绶还是徐渭,都不约而同地将“怨”明确界定于儒家“兴观群怨”的诗教范畴内。如陈洪绶将“怨谱”之怨等同于“诗人之怨”,徐渭则将其“怨”字的外延和内涵直接与“兴观群怨”之“怨”划上了等号。
可以这么认为,不论是陈洪绶还是徐渭,他们在主观上都没有将“怨谱”说界定为悲剧说。毕竟,“我国古代剧作家没有明确地按照悲剧与喜剧的概念指导创作”。④郑传寅:《中国戏曲文化概论》(修订版),第170页。而且,在徐渭、陈洪绶生活的时代,戏剧界可能连明确的悲剧、喜剧概念都没有。“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琵琶记》第一出《副末开场》【水调歌头】),以高明代表的中国古代曲家在涉及悲、喜剧的审美效应时,往往视“乐人”之作为喜剧,“动人”之作为悲剧。如果“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的作品,是不能称之为悲剧的。既然如此,与其生硬地将“怨谱”说界定为悲剧说,还不如换一个角度对“怨谱”予以重新审视。无论陈洪绶的“怨谱”,还是徐渭所说的“怨”字,就其表层意义而言,都与孔子“兴观群怨”之“怨”的意思更接近。关于“兴观群怨”之“怨”字的具体含义,前贤详略兼该的发微已经久成定论。如晋代的何休将“怨”字解释为“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⑤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宣公第七》,四部丛刊景宋建安余氏刊本。汉代的孔安国释“怨”为“怨刺上政”;⑥皇侃:《论语义疏》卷九,清知不足斋丛书本。宋代大儒朱熹则注“怨”为“怨而不怒”。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卷第九》,宋刻本。因此,“怨谱”之“怨”的表层意义也应当作“怨恨”的意思理解。不仅如此,“兴观群怨”之“怨”并非一定要仅仅局限在“怨刺上政”的狭隘范围内,举凡家庭、朋友、男女之间,只要情感有所郁结,都可以通过“诗”予以抒发。正因为“怨”字可以如此界定,所以司马迁才将《诗经》的情感表达笼统归于“怨”。如果说何休、孔安国、朱熹等人距离孔子的生活时代甚远,他们的阐释或有臆测的成分,那么,亚圣孟子对“怨”意的解释应当更接近孔子的实指。孟子在《告子章•下》中回答公孙丑的论诗观时说:“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于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啼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在孟子看来,即使是关系最亲密的人,如果他们存在较大的过错,不仅可以怨恨,而且必须怨恨。当然,这是一种并没有忘记“亲亲”关系的“怨”,更是“仁”的表现。孟子的这种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对《诗经》全面解读的基础上。例如,《诗经》中符合“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怨恨之作比比皆是。姑且不论《伐檀》《硕鼠》《七月》等因社会地位不平等而产生的怨恨,就连婚姻爱情领域的诗歌也不乏充满怨恨的情感表达,如著名的《氓》《柏舟》《谷风》等就是如此。如果我们将《诗经》中的这类诗篇和《琵琶记》《娇红记》等作品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不难发现,不论在内容还是感情的抒发上,《琵琶记》接近于《氓》,《娇红记》则更接近于《柏舟》。《氓》诗的“怨”意是从一个结婚不久即为丈夫遗弃的少妇口中发出:“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对于自己的过去,不仅是悔,而且有着无比的恨”。①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42页。《柏舟》则是女主人公因为“自求良偶”受阻,无奈发出的怨恨之音:“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谅人只!”毫无疑问,《诗经》中类似《氓》《柏舟》《谷风》的诗篇,都可以按照上述的悲剧分类法被界定为悲剧题材,它们所描写的事件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典型的悲剧事件。但是,如果在界定《氓》《柏舟》《谷风》等是悲剧性作品的同时,进而将孔子“兴观群怨”之“怨”理解为悲剧说的话,这显然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命题。依此而论,即使承认《琵琶记》《娇红记》的题材是悲剧,似乎也不宜将“怨谱”说界定为悲剧说。因此,“怨谱”之“怨”其实就是儒家“兴观群怨”之“怨”在戏曲领域的时代性表达而已。或许,和孔子藉《诗经》来教化民众的诗教观一致,陈洪绶、徐渭等人同样希望通过戏曲来达到教化的目的。
二
其实,从“昔人谓诗人善怨,此书真古今一部怨谱也”可知,陈洪绶本人已经明确表达了并未将“怨谱”仅仅比附于悲剧说,而将“怨”字的外延和内涵仍然置于“诗人善怨”,也就是儒家“兴观群怨”说的诗教范畴予以发微。“‘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琵琶》有焉”,徐渭对“怨”字的界定与陈洪绶几无二致。更能说明问题的是,除了陈洪绶、徐渭,同时的李贽、祁彪佳等文坛巨匠或曲学名家也将“怨谱”置于儒家诗教的范畴内来发微。李贽认为:“孰谓传奇不可以兴,不可以观,不可以群,不可以怨?……今之乐犹古之乐,幸无差别视之其可!”②李贽:《焚书•杂述•红拂》,隗芾、吴毓华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111页。祁彪佳认为:“今天下之可兴、可观、可怨者,其孰过于曲者哉。……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诗三百篇莫能逾之”。③祁彪佳:《孟子塞五种曲序》,隗芾、吴毓华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242页。
那么,陈洪绶、徐渭、李贽以及祁彪佳等人为什么将“怨谱”之“怨”置于儒家的诗教范畴内予以发微呢?这是因为在元、明时期,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长期被视为不登大雅的小道,即使在“曲海词山,于今为烈”④王骥德:《曲律》,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512页。的晚明时期,在创作特别是在戏曲理论方面卓有建树的王骥德尚且被指责从事了“为道殊卑,如壮夫羞,小技可唾何”①王骥德:《曲律自序》,隗芾、吴毓华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第50页。的戏曲创作与研究。为了提高戏曲的文体地位,一些进步文人如李贽等,干脆直接从历史渊源上将戏曲与诗歌视为一体,并认为戏曲就是《诗经》与唐诗、宋词在当代的直接流变。如果将“怨谱”说与儒家传统的“兴观群怨”紧密关联,这就意味着戏曲已经具备了《诗经》等优秀诗篇才具有的诗教功能。用这种手段来提升戏曲的地位,迅捷且令人信服。因此,陈洪绶、徐渭等曲家有意识地通过“兴观群怨”之类的诗教观来阐释《娇红记》与《琵琶记》,可谓慧眼独具。尽管《娇红记》《琵琶记》在剧情上充满悲剧的因素,但陈洪绶、徐渭等评点者以及李贽、祁彪佳等著名文人却始终不愿意逾越孔子的诗教范畴,这或许才是上述文人每每将“怨谱”之“怨”与“兴观群怨”之“怨”相提并论的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怨谱”说显然不能被定义为悲剧说。
藉孔、孟的诗教观提高戏曲的本体价值并达到教化受众的目的,并非始于徐渭、陈洪绶、李贽等人,明初的周宪王朱有燉已经意识到这种方式的可行性。他认为:“南人歌南曲,北人唱北曲,和乐实友,与古之诗又何异焉。……(戏曲)体格虽以古之不同,其若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其言志之述,未尝不同也。……今曲亦诗也,但不流入于秾丽淫伤之义,又何损于诗曲之道哉?”②朱有燉:《散曲【白鹤子】咏秋景有引》,隗芾、吴毓华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第83页。徐渭在《曲序》甚至直接将戏曲视为《诗经》中的“小雅”:“怨诽则可以称《小雅》,好色则可以配《国风》。而其按之于指也,遇《小雅》则闻之者足以怨。遇《国风》则闻之者足以宣。……空同子称董子崔、张剧,当直继《离骚》,然则艳者固不妨于《骚》也。”③徐渭:《曲序》,徐渭著:《徐渭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31页。王骥德的观点比徐渭还明确:“《西厢》,风之遗也;《琵琶》,雅之遗也。《西厢》似李,《琵琶》似杜,二家无大轩轾”。④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原评》,明刘龙田刊本。这样看来,陈洪绶以“怨谱”说来概括《娇红记》,既从风格上注意到这些剧作的悲剧因素,也存在有意提升《娇红记》等作品地位的用意。如果不这样做,“为壮夫羞”的“可唾小技”,戏曲的本体审美价值与教化功能就很容易被漠视,更难入那些“壮夫”的法眼。如此看来,既然“怨谱”之“怨”被视为儒家的“兴观群怨”之“怨”在戏曲领域的创造性运用,那么这个“怨”字应该就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所体现的怨恨之意。因此,无怪乎陈洪绶、徐渭、李贽等人都以“怨”字为切入点,进而形成“怨谱”说这一完整的理论体系。另外,陈洪绶虽然没有象徐渭那样逐一总结《娇红记》的怨情,但这部作品却给人无时无地不在谱写怨情的感觉。从第四出《晚绣》开始,举凡有申纯、王娇娘出场的关目,似乎每个人物之间都充满怨艾的情绪,每个戏剧冲突都只能从怨艾的情绪中才得以展开。这些怨艾之情既有王娇娘的闺怨、飞红的自怨与王娇娘之父王文瑞的自怨,还有王娇娘怨恨申纯、怨恨父亲、怨恨飞红、怨恨天公与申纯怨恨王娇娘及其父王文瑞,更有申纯的父母怨恨王文瑞、王文瑞怨恨飞红等。在上述怨艾之情中,有些怨恨是赤裸裸的。如申纯的父母怨恨王文瑞:“自家断送了香闺幼女,又把别人家的孩儿辜负”(第四十八出《双逝》【二贤宾】);以及王文瑞怨恨飞红:“我想小姐申生,两下身亡,皆汝所为”(第四十九出《合冢》)等。有些怨恨则未超越“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如娇娘怨申纯“他做不的会蓝桥水淹的尾生,我做了赴元宵留鞋的月英。想痴心女儿,想痴心女儿,错认文君,许奔长卿。薄幸无端,辜负初盟,挣脱了锦片前程。”(第十四出《私怅》【催拍】)等。
另外,虽然申、娇二人对娇娘之父王文瑞的怨恨仅以“锦片前程事,怨天公不作成”和“恨则恨银河风波恶,将俺业身躯阻隔在巫山庙”等委婉方式进行,但这种“怨”其实和徐渭所阐释的《琵琶记》之“怨”不仅并无二致,而且更接近牛氏对牛丞相所表达的怨艾。当然,无论《琵琶记》还是《娇红记》所谱写的怨艾之情,它们都与孟子阐释的“《小弁》之怨”的外延与内涵基本相同。按照孟子的观点,倘若蔡母、蔡公、赵五娘、申、娇等人在人生的大不幸关头而无所怨恨,无疑是“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在孟子看来,亲亲之怨可以怨而且必须怨,这种“怨”是为了可“矶”,即激起亲之反省自责。这样看来,《琵琶记》就是“矶”与蔡公、蔡伯喈状况相似的家庭或个人反省自责,《娇红记》更是为了“矶”当时社会上行事与王文瑞相似的家长反省自责。不独《琵琶记》《娇红记》等晚出的戏曲作品如此,中国古代的戏曲雏形如《踏摇娘》原本就是这样。据崔令钦的《教坊记》记载,《踏摇娘》讲述的是“北齐有人姓苏,䶌鼻,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归殴其妻。妻衔怨,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①崔令钦:《教坊记》,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11页。时人表演踏摇娘的故事,除了为了“笑乐”,一方面是借戏为女主人公抒发怨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矶”女主人公的丈夫及行事与其相类之人的反省自责。此外,“优孟衣冠”借孙叔敖之子的怨艾之情激起楚庄王的反省自责等,都与《琵琶记》《娇红记》的创作倾向非常相似。如此看来,《娇红记》的创作宗旨和《琵琶记》近似,这两部剧作通过对怨艾之情的形象化抒发,不知不觉地完成了《诗经》等经典诗篇才具有的诗教功能。
三
明代嘉靖以前,多数文人对北曲杂剧非常推崇,对南曲戏文则颇多鄙夷。如“有人酷信北曲,至以伎女南歌为犯禁”;②徐渭:《南词叙录》,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241页,第239页,第240页,第239页。就连生活在苏州这种南曲盛行之地的祝允明,竟也指责南曲为“殆禽噪耳”。③祝允明:《重刻中原音韵序》,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第1集,第227页。这些文人之所以鄙视南曲、酷好北曲,从剧本文学的角度来说,南曲的作者多为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不高的书会才人,他们“语多鄙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也”;④徐渭:《南词叙录》,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241页,第239页,第240页,第239页。在音乐方面,南曲又属于“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⑤徐渭:《南词叙录》,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241页,第239页,第240页,第239页。可见,曲词的文野以及是否合律依腔是当时文人推崇北曲,鄙视南曲的主要原因。但是,从正德年间以后,舞台上南曲越来越兴盛,北曲却江河日下。到了万历年间,北曲在舞台上已经基本被南曲取代。但是,对于主要继承早期南戏的剧本体制和舞台风貌的传奇,多数明代文人不仅没有丝毫的鄙视,相反,他们还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创作、评点以及校正、出版等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戏曲在广大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便需要大幅度提升,而从学理上将戏曲归结为《诗经》等优秀古代诗词在当代的流变,就是提升戏曲地位最佳与最可行的途径之一。以南戏《琵琶记》为例。《琵琶记》在明代之所以取得绝大多数作品难以企及的荣耀,剧作家“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⑥徐渭:《南词叙录》,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241页,第239页,第240页,第239页。才是主因。可见,“与古法部相参”和“唐、宋之遗”才是明代文人关注的重点。那么,哪些戏曲属于“与古法部相参”和“唐、宋之遗”类的作品呢? 朱有燉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国朝集雅颂正音,中以曲子【天净沙】数阙遍入名公诗列,可谓达理之见矣。体格虽以古之不同,其若可兴、可观、可群、可怨,其言志之述未尝不同也。……今曲亦诗也,但不流入于秾丽淫伤之义,又何损于诗曲之道哉?”⑦朱有燉:《散曲【白鹤子】咏秋景有引》,隗芾、吴毓华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第83页,第83页。由此可见,朱有燉认为戏曲的创作和鉴赏应遵循以下标准:(一)衡量曲词优劣的标准应当与诗词一样,能够列入“名公诗列”才是好的曲词;(二)戏曲的社会功能应该是古代诗词的社会功能的延续,优秀的戏曲同样应该具有“兴观群怨”的诗教功能。在这里,朱有燉还明确肯定了曲、诗一体,“曲亦诗也”的观点。可以说,以朱有燉为代表的明初文人,在阐释戏曲所表达的怨艾之情时,基本等同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在他们看来,戏曲不仅和诗一样可以兴、观、群、怨,而且这两种兴、观、群、怨的出发点与最终的归宿也几乎完全相同:“若其吟咏情性,宣畅湮郁,和乐实友,与古之诗又何异耶?”⑧朱有燉:《散曲【白鹤子】咏秋景有引》,隗芾、吴毓华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第83页,第83页。
另外,既然戏曲在当时被视为古代诗词在当代的流变,那么戏曲与古诗的界限就没必要泾渭分明。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元、明两代的戏曲理论自然可以被纳入诗论的范畴。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论的指导,明代的很多剧作家便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诗词的创作手法来创作戏曲的曲词,很多文人受众也把戏曲的曲词当作诗词来接受。不仅如此,以诗词的欣赏方式与评价方法来衡量其他文学作品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强大审美和思维定势,而且这种审美、思维定势往往积重难返。不要说和诗词关系密切的戏曲创作如此,就连小说这种纯粹的叙事文体,为了显示作者的才情,仍然被插入大量的、可有可无的诗词,就连攀上中国古典小说顶峰的《红楼梦》都不能免俗。在这个层面上看,明代之所以出现汤显祖、孟称舜、吴炳等文辞派剧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拥有大量的拥泵者便绝非偶然。而文辞派剧作家对曲词的精雕细琢,简直就是传统诗词创作方法的翻版。如“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近郑若庸《玉玦记》作,而益工修词,质几尽掩。”①王骥德:《曲律》,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第121-122页。在创作方法上向诗词靠拢,在创作和鉴赏的理论上以诗词为皈依,更成为明代文人雅化戏曲的最常用手段之一。因此,“词家之有传奇也,诗之流委也;而传奇之有《西厢》也,变风之滥觞也”②《新刻合并西厢序》,隗芾、吴毓华编:《古典戏曲美学资料集》,第114页。的论调在明清的曲论中比比皆是。明代中、后期,虽然“曲与诗原是两肠”③王骥德:《曲律》,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62页,第121页。等独立曲体观被很多曲家明确,但就连提出这种观点的文人受众,也同样没有完全摆脱曲、诗一体观念的束缚,他们每每将戏曲与散曲并论,甚至与诗词混为一谈。例如,王骥德的《曲律》是一部代表明代曲论最高水准的著作,它虽然在卷三中专列《剧戏》一章,但王骥德却非常重视戏曲曲词的诗韵,并认为曲词创作应该沿袭“《国风》《离骚》、古乐府及汉、魏、六朝三唐诸诗,下迨《花间》《草堂》诸词”④王骥德:《曲律》,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四),第162页,第121页。优良传统。《娇红记》的作者孟称舜虽然也在《古今名剧合选序》中,从理论上明确地辨析了戏曲与诗词之间的异同,但在具体的创作中,他却十分注重诗意的曲词风格,故而《娇红记》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一样,以文采见长。显然,孟称舜更愿意把戏曲的曲词当作诗词来创作。
绾结而言,既然明代曲家多将戏曲看作“诗之流委”并有意识地以传统儒家“兴观群怨”的诗教观来创作戏曲,加之中国古代本无所谓明确的“悲剧”观念,因此,如果将“怨谱”之“怨”界定于传统儒家“兴观群怨”之“怨”的范畴内,既在学理上顺理成章,又更接近陈洪绶和孟称舜等人的评点与创作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