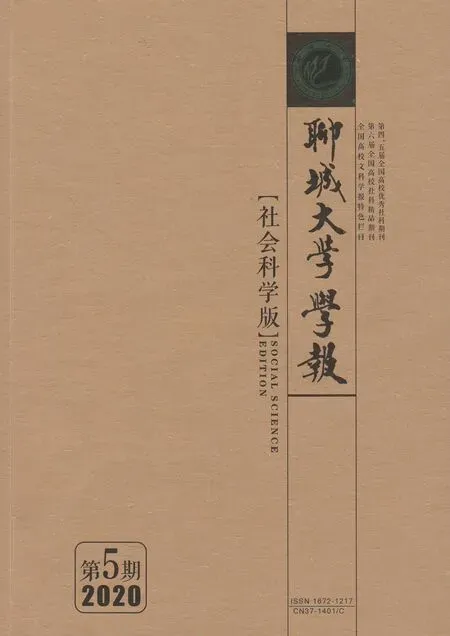大文学史视野下辽、西夏、金、南宋文学作品的选与注
苗 菁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59)
对公元916年到1227年这300多年时间的中国文学,社会上一般人们的认识往往会出现两个偏颇:一是认为这一阶段的文学就是“宋代文学”或“两宋文学”,而忽略了还有辽、西夏、金文学;二是就宋代文学而言,又偏重北宋文学,而或多或少地不重视南宋文学。导致认识产生这种偏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重视针对这一时期通史类或断代类文学作品的选与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下面就这一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与看法。
一、西夏、辽代文学作品的选与注
在同期存在的政权中,西夏最为弱小。也正因其弱小,和同样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金相比,西夏统治者强调自身文化独立性的意识就更强。所以,在创立西夏文之后,西夏文成为统治者强力推广的唯一文字。西夏国内的各种文书、印刷的书籍基本上都用西夏文写成。甚至西夏与吐蕃、回鹘、西域等政权往来的文书,也一律使用西夏文。只有与宋王朝往来的公文,仍在使用汉文,并专门设立了“汉学院”以掌管、撰写这方面的文书。由于这种极端重视西夏文的国策,所以今天发现的各种西夏出土文献中,用西夏文写成的占了大多数。同时,西夏虽然也有自己的教育、科举制度,但是立国189年,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汉文化素养比较高、重视诗文创作的文人群体,所以,就很少有西夏文人写诗作赋的文献记录,也没有某些西夏文人曾编篡过诗文集的记载。当蒙古人的铁蹄踏入西夏境内后,曾对西夏国进行过毁灭性破坏。不仅人民遭杀戮、城池被焚毁、陵墓被挖掘,就连西夏典籍也多被付之一炬。所以,西夏文献就丧失了能够传世的条件,这也就导致了今天存世的西夏文献相对较少。进一步,就使得在研究西夏文学时,会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先天不足。
目前,研究西夏文学所依据的文献,主要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如前所述,今天发现的西夏出土文献,大多数用西夏文写成,而且属于文学类的作品不多。所以,以这部分文献来研究西夏文学,成果既不会很多,成就也不会很大。今天西夏的传世文献中,那些西夏本国保存并流传下来的文献,由于蒙古人的毁坏也几乎荡然无存。而宋王朝保存下来的典籍中,还存有一定数量的西夏文献。这一类的西夏文献,几乎很少诗词歌赋,多数是在西夏、宋两国交往过程中,一些由西夏人撰写的、正式的官方来往文书;少量是由西夏传入宋王朝的、在西夏国内使用或流传的文书,如表、书之类。这类文书,无论是以何人的名义发表,都应是由西夏中那些汉族文人或精通汉语与汉文化的党项族文人所精心写成的,都有一定的文学性。这些文献应该是我们介绍、探讨西夏文学真实情况与水平的一个重要途径及窗口。
可惜的是,关于西夏文学,目前不仅没有总集类的文献,就是选西夏文学作品的选本也少得可怜,更不要说注释过的篇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和西夏相比,辽朝的情况就好得多。辽朝虽然也创立了契丹文,但由于辽朝统治者比较有自信,对汉文化普遍采取开放、学习、接受的姿态,他们其中的很多人既习契丹文,又习汉文,所以其文献往往是契丹文和汉文并行书写。这在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陆续出土的辽代墓志中就能很鲜明地看到这种情况。以墓志为代表的这些辽代出土文献的问世,无疑也大大增加了辽代文学文献的存世数量。
而在汉化的过程中,由于对汉语的深入学习,契丹上层人物也喜用汉语吟诗作赋,并用汉、契丹两种文字撰写文章,有些编辑成集,惜未留传下来。但他们中的某些人,如辽圣宗(耶律隆绪)、辽兴宗(耶律宗真)、辽道宗(耶律洪基)、耶律倍、耶律隆先、耶律琮及一些后妃、王公大臣等都有一些文学作品流行于当时。尤其是辽圣宗后,契丹贵族多学作汉诗。辽朝的汉人也能继续禀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韵脉,进行文学创作。一些汉族官僚常因文学水平高而得到辽皇帝的奖赏。辽代文学经历了自身的发展过程,虽从整体上看,始终难与中原王朝相比,但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如此,辽代文学作品存世的数量就相对较多。从今人编篡的《全辽金文》《全辽文》看,单是文的数量就达800余篇。这些存世的诗文为今天人们梳理、研究辽代文学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献基础。因此,人们对辽代文学的叙述、总结,就显得相对丰富。所以,与西夏文学相比,文学史上对辽代文学的介绍,列举的篇目就多得多。这些汉文写作的文章几可与中原王朝的此类文体相媲美。其文中体现出的“奄有大辽,权持正统”①《辽主耶律延禧降表》,[金]佚名编,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大金吊伐录校补》,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07页。的强烈的正统观,贞节、忠孝的伦理观,以及功业、地位、评价观等,都和中原王朝并无二致。其句式的讲究、辞藻的雅致、对仗的整齐、用典的贴切、风格的富丽宏赡,也决不次于中原王朝的一般庙堂文学。这说明在辽代,汉文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在广泛使用,实际上成为最为通行的官方书写语言。这也说明,在辽代有一个广大的,由汉人乃至于契丹人组成的汉文写作队伍。这是辽文达到相当成熟境地的重要标志,也是辽朝接受中华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目前,虽然研究辽代文学的论著有一定数量,而且文学史上对辽代文学的介绍也占有相当篇幅,但在选注上却存在着两个普遍的问题:
其一,谈到这段文学时,无论在论著中,还是在文学史中,大家列举的辽代作品篇目不少,但缺乏与之相对应的选注本。也就是说,文学史上或相关专著上被当做具有代表性篇目的作品,却根本看不到相应的选本,就更不用说对这些作品的注释了。比如,佚名的《造长明灯记》,很多中国文学的通史,或断代文学史都将之作为重要的辽文进行过介绍,但是却几乎看不到有人对其进行过详细的注释。再如,李万的《耿延毅墓志铭》,是人们谈到辽代文学或辽代散文时,被高频率举出的能代表辽代散文创作水平的作品,至今也无人对其进行过全文的注释。
其二,有的辽代文学的作品,虽然也被选了,并进行了注释,但都比较粗糙,并且错误还较多。如寺公大师的《醉义歌》,向来为人们所公认,是辽代诗歌的代表性作品。但在注释时,很多人往往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它原来曾是契丹文。到元代时,才由精通契丹文的耶律楚材将它翻译成汉文得以流传。今天看来,不可否认,这首诗歌作品确实是一首上乘之作。但能使诗歌作品呈现出现在这种精彩的,当不仅仅只有作者寺公大师创作的功劳,应还有耶律楚材由契丹文翻译成汉文的再创作的功劳。很多人在注释这首诗时,只把它当作契丹人用汉文写作的成功,却忽略了翻译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这应是人们没有认真地对该诗如何形成进行追根溯源的工作所导致。再如萧观音的《回心院》,人们也都公认,其成就较高,说其“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①[清]徐釚撰,唐圭璋校注:《词苑丛谈》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0页。但是萧观音为什么将作品题作《回心院》?在注释时,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注意。实际上,作品题作《回心院》是有来历的,它是在用唐高宗后王氏及萧良娣的典。作者萧观音通过对这个题目的命名,有十分明确的目的,就是她希企辽道宗耶律弘基能够回心转意,重新宠幸于她。而《回心院》诗作中还多处用典,也都用得十分贴切,这说明萧观音对中原典籍和诗文十分熟悉,如此才能顺手拈来,毫不费力。由此,也可见当时这些契丹贵族用汉文写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对于萧观音在《回心院》中所使用的典故,很多选注本在注释时,都没有进行过仔细的梳理,也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追根溯源。
二、金代文学作品的选与注
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金代保存的文学文献最多。这是因为,金代占据的传统汉族生活的地域最广,汉族人口最多,占其全国人口总数的80%。尤其今天的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之地,自古以来属于“中原地区”的范畴。所以,金代统治者在占据这个地区后,迅速汉化,在国家机器、典章礼乐、伦理道德、科举教育、文学艺术诸方面,都大量地吸收、融合了汉文化。金熙宗完颜亶时以接受汉文化为荣,更加速了吸收中华文化的进程。与此同时,金政权更以中原王朝自居,开始有强烈的“华夏”正统思想和“中国”意识。受这种意识所支配,甚至将南宋政权看作是“偏安政权”与“蛮夷之国”。因此,除了由异族统治,这些异族并享有某些特权外,整个金代社会和传统的汉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差别并不是很大。金朝统治者虽然也创立了女真文,但社会上的汉文普及度更高。汉文不但为金朝境内的汉人所用,而且契丹、女真、渤海上层人物一般也都通晓汉文。在使用范围和重要性上都在女真文之上。当各族语言不能沟通时,则更以汉文为共同语言。金人颇爱诗词,金朝皇帝从海陵王完颜亮,到章宗完颜璟、宣宗完颜询,皆工文章,善诗赋。而汉族士人写诗作文更是一种常态性的、不受任何干扰、甚至于以之为荣耀的事情。到金灭亡时,更有元好问以保存故国一代文献为宗旨编篡了保存金代诗歌的《中州集》。所以,因以上原因,和辽、西夏相比,金代保存的文学文献最多,这是必然的。
既然金代保存的文学文献多,所以人们介绍金代文学的选注本也就较多,甚至出版过《金代文学作品选》《辽金文学作品选》《宋金文学作品译注讲析》《全金元词评注》《金元词一百首》《辽金元诗选评》《辽金元诗三百首》等一系列的文学作品选。而通史型的历代文学作品选注本中,也往往把宋金或金元并列,将金代作为一个文学成就较高的时代凸现出来。但仔细分析这些选注本,就会发现,虽然选取的金代文学作品有相当数量,但其注释却往往比较简略,甚至粗疏。
由于硅片和托盘均要经过酸碱处理、清洗等必要工艺,因此对标签的耐腐蚀和防水性能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在宜科为客户量身定制的载码体解决方案中,根据托盘预留的安装空间来设计标签的外形尺寸,同时采用PVDF材质外壳封装,保证在PH值4~9、温度-40~150℃的范围内可以长期稳定地使用。
其一,对于影响到对金代文学作品全篇理解与把握的关键地方,因不愿做细致的工作,有时故意忽略而不去注释。如刘迎的《修城行》诗中有一句:“筑时但用鸡粪土”①[金]元好问编:《中州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页。,这其中的“鸡粪土”三字,所有注释金代文学作品的选注本中,都没有进行注释。人们在解读时也是对“鸡粪土”一笔带过。实际上“鸡粪土”三字是全诗的关键。所谓“鸡粪土”,是指一种土壤,这种土壤的土层中有少量石灰粉末形成的斑点,状如“鸡粪”,俗称“鸡粪土”。它粘合性极差,一遇风吹、雨打、日晒,就会整个松散,根本不适宜用作修筑城墙的材料。官吏们筑城时的草率与不负责任,在这一句中;修筑后城墙形同虚设,也在这一句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释“鸡粪土”,人们在阅读时就会望文生义,进行错误的理解。这首诗中还有一句,即“淮安城郭真虚设”。对这句中的“淮安城”,今天只有周惠泉、米治国的《辽金文学作品选》等极少数选注本注意到金时“淮安”并不是指今天一般人们所熟悉的“淮安”,而是另有所指,即指今河南唐河②周惠泉、米治国:《辽金文学作品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07页。。其他大多数选注本,甚至包括文学史、金代文学等研究论著中,在选或引这首诗时,都对“淮安城”不加任何注释或解释。而章荑荪的《辽金元诗选》,在选这首诗时,更直接将“淮安”注释为 “在今江苏”,这就把今天的江苏淮安当作了金统治区域的“淮安”,错误十分明显③章荑荪:《辽金元诗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51页。。
不仅对金代诗词的注释如此,就是对金文的注释也是如此。如赵秉文《磁州石桥记》的开篇一句“北趋南都”,很多选注本都作“大都”,这明显是错误的④[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十三,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9页。。称北京为“大都”,是蒙古入主中原后的用法。而在赵秉文生活的金代,根本没有这个称谓。所以这里应是“南都”。这是赵秉文在沿袭辽代的旧称。辽会同元年(938),将原幽州(即北京)升为幽都府,建号南京,作为辽的陪都。作者称北京为“南都”,仍是沿用辽时对北京的称谓。很多选注本对该句进行注释时,基本上都将这个问题避而不谈,这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再如,因元好问是金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所以选注本对他的文章选的篇目,比其他金代作家为多,注得也相对详细。但在注释时,仍还存在着当注而不注、甚至注释错误的问题。如元好问的《送秦中诸人引》一篇⑤[金]元好问著,姚奠中等校:《元好问全集》(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50页。,是人人皆选的文章。但在注释时,文中的一些关键点,或者一些有难度的词句,都没有注释出来。如文中的“长吁(xū)青云”一句,几乎无人注释。但这句是有来历的,语出《北史•献文六王传•成阳王禧传》:“(元树)每见嵩山云向南,未尝不引领歔欷。”⑥[唐]李延寿:《北史》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692页。再如“如举子结夏课时”句中的“结夏课”一词,人们在注释时,也只是简单地注释说:“学子的活动”。但其来历如何?根本没人指出来。所谓“结夏课”,本为佛家语,又称“结夏”“结制”。僧人在夏日安居修道,即称为“结夏”⑦[宋]吴自牧:《梦梁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9页。。后来举子们在夏日结合同辈读书习文,以备秋日应试,多借净坊庙院及闲宅居住,因此也就借用了这种佛家的用法,将这种活动称之为“结夏课”⑧[宋]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22页。。只有将文中一些关键词语的来历解释清楚,才能加深对这篇文章的理解。
其二,对很多金代诗词文虽然选了,也注释了,但是注释得十分简单,基本上是在疏通文字,按字面解释意思,不能很好地揭示作品的写作特点。比如,金代作家的文学功底十分深厚,和北宋作家一样,在诗文创作中使事用典是种常态。对于这一特点,几乎所有金代文学作品的选注本都没有很好地加以揭示。如元好问的《秋望赋》一文①[金]元好问著,姚奠中等校:《元好问全集》(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页,第218页。,一般注本在注释时,像“徙倚”“高明”“出处之有道”“南山石田”“云雷”“飞鸟”“剪桑梓”“鸷禽”等这些典故,往往都不加以注释。如此,对于《秋望赋》所抒发的恋故乡、忧公室沦丧之沉痛及愿为国立功建业的豪情等丰富而复杂的感情,就无法真切地理解。
再如元好问的《歧阳三首》诗作②[金]元好问著,姚奠中等校:《元好问全集》(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页,第218页。,因是元好问诗歌的代表作,所以注者蜂起,但其中也有很多该注而没有注的地方。比如,第一首中的“偃蹇鲸鲵人海涸”句,本从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鲸鲵人海涸,魑魅棘林幽”③[唐]司空图撰,祖保泉、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94页。中来,是在用典。“分明蛇犬铁山围”句中的“铁山围”,也是在用典。“铁山围”,即“铁围山”,又称“铁轮山”。佛教经典载:此山是围绕须弥山之咸海四围的山,传说此山由铁组成,故名。④[唐]道宣著,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页。此处用这个典故喻指凶猛如蛇犬的蒙古军如铁山般包围着凤翔。对这两句诗,没有一个选本的注释中指出或解释它们是在用典。
元好问《歧阳三首》的第二首是所有选元好问诗歌的选注本都要选的作品,但也同样存在着该注而没有注的问题。比如,该诗的第一句“百二关河草不横”,其中“草不横”是在用典;第三句“岐阳西望无来信”,其中“无来信”也是在用典。“草不横”,见《汉书•终军传》:“军无横草之功。”颜师古注云:“言行草中,使草偃卧。”⑤[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十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128-2129页。是指军队在草中行走,使草横倒。此处指金国到处为蒙古军队践踏。“无来信”,见杜甫《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⑥[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47页。。指与岐阳不通音讯,没有接到来信,实际说岐阳已经失陷了。虽然这首诗是人人都要选的作品,但仍然没有一个选注本的注释指出这两句诗是在用典。类似的情况,在金代文学选本的注释中比比皆是。
其三,很多文学史或专题性的古代文学发展的介绍中,在介绍金代文学及作家时所列举的代表性作品,很多选注本却没有选入。如王寂、赵秉文、李俊民、刘祁等人,都是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金代文学大家。他们代表性的诗篇,如王寂的《易足斋》、赵秉文《春游四首》、李俊民的《即事》,等等,都没有人注过。他们代表性的文章,如刘祁的《游林虑西山记》《游西山记》《归潜堂记》、李俊民的《睡鹤记》《刘济之忍斋记》,等等,也都没有人注过。在学习金代文学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刘祁的《归潜志》,是一部反映金代历史的重要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金代文学家的传记、言论资料。如此重要的著作,到现在既没有完整的一个注释整理本,其中一些比较精彩的篇章,在文学史或对金代文学介绍的论著中往往会被反复举例与引用,但却仍然缺乏与之相配套的选注本。就连元好问这样的大家,他的很多代表性诗文作品,如《箕山》《赵州学记》《送高雄飞序》等,迄今也很少能看到有选注本对其选入与注释。
三、南宋文学的选与注
如前所述,对公元916年到1227年这300多年时间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主要重视的是“两宋文学”。但就“两宋文学”而言,又重“北宋文学”,而轻“南宋文学”。反映在对南宋文学作品的选与注上,这种“轻”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一些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只在文学史中或介绍南宋文学的论著中提到,却很难看到有相应的选注本将其选入。如诗歌作品中,赵鼎的《泊白鹭洲,时辛道宗兵溃犯金陵境上,金陵守不得入》、张镃的《千叶黄梅歌呈王梦得、张以道》、姜夔的《除夜自石湖归苕溪》、戴复古的《诘燕》《江阴浮远堂》、方岳的《春暮》《月夜》《农谣》等;散文作品中,如刘子翚的《招剑文送刘致中》、王十朋的《读苏文》、陈亮的《中兴论》、朱熹的《送郭拱辰序》、陆九渊的《荆公祠堂记》、叶适的《烟霏亭记》、陆游的《跋李庄简公家书》、范成大的《馆娃宫赋》《三高祠记》、杨万里的《新喻知县刘公墓表》、文天祥的《衡州上元记》、谢枋得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等,都曾在文学史或介绍南宋文学的论著中被反复提到,但却很少看到有选注本将其入选并进行过注释。
其二,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南宋文学的大家们,他们的很多代表性作品,虽然在很多选注本中都被选入并加以注释了,但却存在着注释粗略,甚至不求甚解、错误百出的情况。如杨万里的《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是很多选注本都会选的诗歌作品①[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抄本。,题目中出现的“松源”“漆公店”这两个名称究竟指哪里?或者是在什么地方?《宋诗鉴赏辞典》②缪钺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1105页。《宋诗三百首鉴赏辞典》③朱德才、杨燕:《范成大杨万里诗词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第308页。《范成大杨万里诗词选译》④傅德岷、李元强、卢晋主编:《宋诗三百首鉴赏辞典》,武汉:长江出版社,2008年,第350页。《唐宋绝句五百首》⑤杨大中:《唐宋绝句五百首》,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71页。等,虽对其进行了注释,但却都将之注为“皖南山区”。这是影响最大的一个注释,影响所及,几乎一般性的或面向少儿的诗词读物中,也都将“松源”“漆公店”注释为“皖南山区”。一些选注者注意到将之注释为“皖南山区”有问题,也试图进行过订正。如傅璇琮主编的《中华古诗文名篇诵读•宋元明清》就将“松源”“漆公店”“大而化之”注释为“苏皖山区”⑥傅璇琮主编:《中华古诗文名篇诵读•宋元明清》,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55页。,更加谬之千里。在所有的对“松源”“漆公店”进行注释的选注本中,只有《杨万里诗歌赏析集》⑦章楚藩主编:《杨万里诗歌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第215页。中,将“松源”“漆公店”注释为“弋阳境内”,最接近事实。但它的注释,也仅仅到此为止。“松源”“漆公店”究竟在“弋阳境内”什么地方?属于什么样的地名呢?仍还需进一步明确。实际上,如果再进一步考证,就会知道,今天的弋阳,这两个地名仍还存在。松源,即今天弋阳境内的松源山;漆公店,即今天弋阳境内的漆工镇。只要将这两个地名找准了,整个诗歌作品中的其他地名,如“芙蓉渡”“溪源”就都能一一找寻到。如此,也才能进一步对诗歌作品中的“也知流向金陵去”“后山勒水向东驰,却被前山勒向西”这样的句子,获得符合其地理、地貌的解释。
杨万里类似的诗歌作品还有《宿新市徐公店》⑧[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三十四,四部丛刊初编影宋抄本。。诗共两首,其中,“篱落疏疏一径深”这首作品被人广泛选注,尤其是在那些针对少年儿童进行古诗词教育的选注本中更被高频率地选入。但诗题中的“新市徐公店”究竟在哪里?今天还有没有相应的地名?大多数选注本或者对此忽略不注;或者就简单地注为“地名”。就连影响最大的周汝昌的《杨万里诗选》也没有注释⑨周汝昌:《杨万里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225页。。一些注释过“新市徐公店”的选注本,往往也错误百出。周啸天《曲径通幽•宋诗名作欣赏》中竟将“新市徐公店”注为在“湖南攸县北”⑩周啸天:《曲径通幽•宋诗名作欣赏》,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第318页。,更显离奇。由此,也导致很多选注本跟着以讹传讹。比较接近真实地点的是《莫砺锋教你读古诗•初级版》中的注释。它对“新市徐公店”注释说:“在今浙江北部”11莫砺锋主编,赵超、沈章明编著:《莫砺锋教你读古诗•初级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3页。。这已将“新市徐公店”的地域范围缩小了,但还不明确、具体。实际上,“新市”即今浙江德清的“新市镇”;“徐公店”很可能即指徐姓主人所开的店。到今天,已有杨万里集的整理校注本,但在注释上仍还存在着如此多的问题,其他南宋作家作品的注释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南宋诗人喜欢写数首甚至几十首的组诗,但选注本往往只挑选选家认为最能体现作家特点与特色的一两首诗,很少注意到组诗本身的系统性、完整性与连贯性,这使得读者不容易看到组诗前后之间的关联性。如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共有两首①[宋]陆游:《剑南诗稿》卷第二十六,汲古阁刻本。,人们往往只选其中的第二首“僵卧孤村不自哀”,却舍弃了第一首。实际上,这两首诗是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舍弃了第一首对“僵卧孤村”及其环境的描写,第二首“夜阑卧听风吹雨”也就没有了让人如在眼前的动态的、形象的画面。
再如,范成大的爱国诗主要是他的七十二首使金诗。这些诗歌的最大特点是:作为纪录使金行程的诗歌作品,他对沿途所写到的景观都是有选择的。或者说,他选择的景观都是那些最能体现他爱国忠君、不辱使命精神的那些景观。为了突出这种特点,在选注时,就不能只选《州桥》一首,而应该相应地多选几首,如《双庙》《蔺相如墓》等作品都应该选入。
再如,文学史上对汪元量《醉歌》和《湖州歌》这两组组诗的评价都很高②[宋]汪元量撰,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页,第36页。,至有“诗史”的说法③[清]钱谦益:《跋汪水云诗》,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八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64页。。但对这两组诗,人们在选注时普遍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是普遍不重视对诗作中影响人们理解关键点的注释。如将这两组诗命名为“醉歌”与“湖州歌”,是采用了用旧题以写新意的拟乐府的创作方式。“醉歌”是仿唐人好写“醉歌”的习惯,以之抒写“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痛苦④[战国]屈原:《渔父》,[汉]刘向辑,王逸注:《楚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26页。;“湖州歌”则是依南宋时湖州一地流传的歌谣声腔与感情而创作,用以抒发“一声三四咽,掩抑含凄切”的沉痛⑤[宋]袁说友:《江舟牵夫有唱湖州歌者,殊动家山之想,赋吴歌行》,[宋]袁说友《东塘集》卷一,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作者对这两组诗命名的深意,很少有人加以注释,其次,是选得篇数太少。《醉歌》十首中往往只选“乱点连声杀六更”这一首;《湖州歌》九十八首中也往往只选“谢了天恩出内门”这一首。这两首诗,一首写了南宋政权投降时的情景;一首写了覆亡后南宋政权小皇帝被蒙古人由杭州强行押解北京的情景。两首诗作都有其典型性。但仅仅只选这两首,《醉歌》和《湖州歌》两组诗所反映的南宋灭亡时的丰富内容与作者的复杂情感却难以充分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