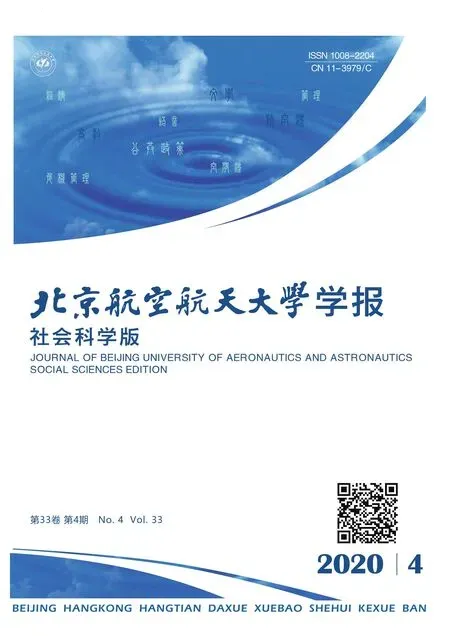浅析国际航空运输第五管辖权
宋 刚, 耿绍杰
(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5)
一、引言
国际航空运输中总会涉及航空公司与旅客之间的纠纷案件,这是无法避免的。现代国际航空运输的航班中总会搭载不同国籍的旅客,航班也会经停不同的地点,旅客也经常在不同的地点购票,事故的发生地点也会有所不同,这些因素会导致国际私法法律冲突问题,国际私法法律冲突既存在实体法冲突,也存在程序法冲突,而程序法冲突中最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管辖权冲突。若不能妥善处理国际管辖权冲突,则会产生诉讼进程缓慢、判决无法得到他国承认与执行等一系列后果。虽然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最著名的是统一实体法部分,但是也对包括管辖权在内的程序法部分作出了一些规定。因为如果只对航空承运人的民事责任作出统一规定,而不考虑管辖规则,就难以防止或避免当事人通过挑选法院来规避统一规则的使用,其结果将会严重妨碍和削减统一航空法使用的功效,无法避免法律冲突[1]。为此,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33条专门规定了国际航空运输案件的管辖法院,并且在第49条明确规定变更公约有关管辖权规则的协议或者条款均属无效。但是,该公约的管辖权条款却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其中以第33条第2款所规定的第五管辖权争议最大。
二、第五管辖权的由来及立法背景
与1929年《华沙公约》相比,作为新条文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33条第2款所规定的管辖权被民航业内人士普遍称之为第五管辖权,该条款被称之为第五管辖权的原因是因为该公约的前身1929年《华沙公约》规定了四种管辖权,而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中又完全吸纳了前者所规定的四种管辖权作为该公约第33条第1款,因新增加的管辖权条文位于前述四种管辖权条文的下方,故按顺序将新条文所规定的管辖权称之为第五管辖权。颇有特点的是,在第五管辖权处,国际民航组织改变了其一贯不给专业术语定义及解释的作法,较为详细地解释了何为第五管辖权①。
第五管辖权并非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所创,而是由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第12条所创,因美国的强硬立场,该议定书中规定了第五管辖权,但是该议定书因为批准加入的国家不满足生效条件,故该议定书并未生效。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所规定的第五管辖权与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中规定的第五管辖权差别较大,前者的条文冗长、复杂,而后者的条文仅表述为:对于因旅客死亡、身体损害、延误以及因行李毁灭、遗失、损坏或延误而产生的损失,责任诉讼可向本条第1款所列的法院之一提起,或者在旅客住所地或永久居所地的缔约国内,向在法院辖区内承运人设有营业机构的法院提起。相比较而言,前者仅适用于造成旅客死亡或者伤害产生的损失的情形,而后者适用于一切除货物外的相关责任诉讼。另外,前者对承运人商业存在的规定也更为细致。
其实早在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是否需要加入第五管辖权的规定时,美国就遭到了以法国为代表的几个国家的强烈反对,原本美国的提案是:或者在旅客住所地或永久居所地的缔约国内提起。原本的提案并没有要求承运人需要在旅客住所地的国家有商业存在时旅客才可以起诉。可以认为,该议定书中的第五管辖权加入商业存在的限制条件是美国对其他国家作出的一个小小的让步,其他国家担心其本国承运人仅仅因为旅客的国籍就被该第五管辖权条款拉入他国诉讼纠纷。例如,美国公民在非洲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埃航”)的航班前往中国,而埃航恰好不经营至美国的航班,其在美国也没有办事处等机构,那么如果根据美国原来的提案,一旦出现诉讼案件,埃航就要去美国参加诉讼。虽然增加了限制条件的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第五管辖权依旧遭到了反对与质疑,但是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该议定书的其他因素使得大多数国家没有兴趣加入这一议定书。
及至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起草草案之时,美国依旧表明了其强硬的立场与态度,如果不加入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第五管辖权的规定,那么美国是不会批准加入新公约的。因为当时美国民航实力极其强大,占据世界民航40%的运力,如果美国不加入公约,将会使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统一法目标落空。美国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要求加入第五管辖权的规定原因在于,美国认为20世纪中期以后,1929年《华沙公约》所规定的四种管辖权无法满足美国公民和其永久居民的实际需求,经常出现这两类人无法依据该公约的四种管辖权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的情况。例如,一位美国公民在德国购买汉莎航空公司飞往中国的机票,因汉莎航空公司的承运人住所地和主要营业地均在德国,订立合同的营业机构所在地也在德国,目的地为中国,故美国法院没有管辖权。美国对此种情况的多次出现非常不满,其认为美国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的利益无法在他国法院得到保护,因为经济水平差异等原因致使他国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远远低于美国法院对同类案件判决的赔偿金额。故美国意图大幅度提高其公民和永久居民在美国法院起诉的可能性以维护这两类人的利益。
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起草过程中,法国也表明了其一贯立场,依旧反对第五管辖权的加入。因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起草所造成的影响力较大,这次多数国家都对公约的起草颇为关注,其中很多国家也支持法国,表达了对第五管辖权的反对与质疑。反对与质疑主要集中于以下五个方面:①第五管辖权过于偏向保护旅客,而未考虑到承运人利益。②1929年《华沙公约》规定的四种管辖权已经足够满足大多数案件,设立第五管辖权是多余的。③中小国家的航空公司若依第五管辖权在美国遭到起诉并败诉,会承担高额赔偿从而有破产的风险。④基于原因③,为避免破产,航空公司会多支出保费以提高保额,这样会反作用于飞机票价格,让旅客承担更高额的飞机票。⑤第五管辖权主要保护的是美国公民,对于其他国家公民不能起到太大的保护作用[2]。经过多次协商、谈判,美国终于作出了让步,同意公约对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第五管辖权进行更多的条件限制,最终形成了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33条第2款。
三、对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五管辖权的评价
虽然有很多国家是反对在公约之中加入第五管辖权规定的,在公约生效后,实践之中第五管辖权的适用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但是笔者认为各方对第五管辖权的全面否定是欠妥的,虽然第五管辖权有弊端,但是并未像各方批评所说的那么严重。
首先,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前言部分明确表明要确保国际航空运输消费者的利益。但是公约规定的五种管辖权中的四种管辖权,即承运人住所地法院、承运人主要营业地法院、订立合同的营业地法院以及目的地法院,是明显偏向保护承运人的,因为承运人住所地和承运人主要营业地一般都是承运人的总部所在地,订立合同的营业地也往往存在着承运人的分公司。虽然单独分析第五管辖权可以明显看出是偏向保护旅客利益的,但是综合观察,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33条规定的五种管辖权整体来看,第五管辖权正是从保护旅客利益的角度出发在整体上平衡了旅客与承运人之间利益的,而非反对者所说的过于偏向旅客,不考虑承运人利益。
其次,虽然通常情况下国际航空运输中旅客的主要且永久居所地会跟承运人住所地、主要营业地、订立合同的营业地或者目的地之一重合,前四种管辖权即可起到与第五管辖权一样的功能[3]252。但是由于现代国际航空运输的快速发展,旅客的主要且永久居所地与上述四地点不重合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正如美国代表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起草时所主张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第五管辖权的规定,旅客就不得不前往别国提起诉讼。虽然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对诸如责任限额、突破责任限额的条件、免责事由等问题作出了统一规定,但是也将一些问题交给了缔约国法院,如事故的判定、诉讼程序、诉讼时效的计算方法等,旅客往往不通晓他国法律,且又需要承担较高跨国往返费用、申请签证等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不利于本来就相较于承运人而言处于弱势地位的旅客的权益保护。相反,若规定了第五管辖权,那么旅客便可以在其本国起诉,因旅客对其本国法律相对熟悉,且不用疲惫地往返于本国与他国法院之间,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大大降低。可见,在旅客的主要且永久居所地不与前四种管辖权地点重合时,第五管辖权有其存在的必要,并不是多余的。
再次,可以认为,中小国家的航空公司担心的不单是第五管辖权在美国的适用可能导致其破产,其担心的是第五管辖权在所有航空案件高赔偿标准国家的适用,如若其败诉,将承担较高的赔偿费用。该类航空公司这样的担心完全是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考虑,而没有考虑旅客的利益。假设一位美国旅客周游非洲后想日后可再来旅游,便在纳米比亚购买了纳米比亚航空公司从美国起飞前往纳米比亚的机票,日后飞行过程中产生事故,如果没有第五管辖权的规定,该名旅客无法在美国起诉,只能在纳米比亚国家的法院起诉,那么其所获得的赔偿额必定大幅度低于同类案件在美国所判决的赔偿额,因为法院一般会依据法院地的赔偿标准进行判决,而纳米比亚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差异较大。这就会导致该名旅客无法得到完全地赔偿,是极其不公平的。此外,中小国家的航空公司这种观点是较为肤浅、缺乏远见的,正是有了第五管辖权的存在,旅客才会更加广泛地将他国航空公司纳入出行选择范围,而中小国家的航空公司也可以凭借其较低的价格吸引一部分旅客,从而分得市场的一杯羹。同时,该类航空公司因惧怕高额的赔偿,也会刺激其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保障安全性,最终航空公司亦会因此受益而得到乘客的认可。且中小国家航空公司完全不用担心破产问题,因为保险保额基本可覆盖赔偿额度。另外,航空运输实践结果所体现的事实与公约起草时认为第五管辖权会显著增加保险费和票价的观点恰巧相反,事实是费用的增加微不足道[4]55。
此外,有观点认为,如果采用第五管辖权会产生同一案件造成多名不同国籍的旅客遭受损失,但是因不同国籍旅客的本国法院的不同而导致本国法院判处不同的赔偿金额,即同案不同判的情况。这就会涉及到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问题。还是使用上例但略作修改,一位美国旅客、一位韩国旅客以及一位莫桑比克旅客购买了纳米比亚航空公司机票前往纳米比亚,飞行过程中产生事故,如果没有第五管辖权则这三位旅客只能在纳米比亚国内的法院起诉,那么三位旅客很可能得到较为一致的赔偿金额,这是符合形式公平的,但是并不符合实质公平。因为这三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差异巨大,纳米比亚GDP全球排名第129名,莫桑比克排名130名,韩国排第17名,美国则排在全球第1名②。假设最后赔偿三位旅客每人5万美元,这5万美元可以完全弥补莫桑比克旅客的损失,但是不能完全弥补韩国旅客的损失,对于美国旅客所遭受的损失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只注重形式公平而忽略实质公平是违背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恢复性赔偿原则的基础上提供公平赔偿的主旨的。
最后,批评第五管辖权只保护美国公民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使美国旅客通过第五管辖权获得高额赔偿是美国提倡第五管辖权的最终目的。但是不得不说在本质上,第五管辖使各个国家的航空旅客可以在其本国起诉,方便旅客、节约成本、获得公平地赔偿。虽然公约所规定的航空公司商业存在的限制性条件较多,但是在当今航空全球化、航空联盟扩大化的背景之下,这些限制性条件在绝大部分国家均可得到满足。只要满足了公约所规定的航空公司商业存在的各项限制性条件,各国旅客均可在其本国起诉航空公司而非只有美国旅客。旅客本国的法院适用其本国法判决的赔偿金额是最符合旅客利益的、最适合保护旅客权益的。
第五管辖权也存在弊端,从前文所述第五管辖权适用条件之索赔情形限制可知,第五管辖权仅能在旅客死亡或者伤害而产生的损失中适用,不能适用于行李损失、货物损失和延误等索赔情形。单从条文规定来看,与未生效的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第五管辖权相比较,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所规定的第五管辖权是片面的。究其原因,是美国为了其他条款的通过而作出的略微让步。但是这将导致发生事故时,旅客若同时遭受了人身损害和行李损害,则旅客只能分而诉之,即在其主要且永久居所地国家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在其余四种管辖权法院提起行李损害赔偿。从这点来说,是不利于旅客权益保护的。
四、第五管辖权的适用
即使第五管辖权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反对,但是公约毕竟通过并生效了,所以缔约国法院都有义务去遵守并适用该规定,旅客也有权依第五管辖权的规定在其主要且永久居所国起诉。
(一)第五管辖权适用的条件
旅客若想依据第五管辖权规定在其主要且永久居所国起诉,需要满足相关条件:①索赔情形限制,仅能在旅客死亡或者伤害而产生的损失中适用,不能适用于行李损失、货物损失和延误等索赔情形;②时间及地点限制,当事故发生的时候,旅客在该缔约国境内存在主要且永久居所;③承运人旅客航空运输业务限制,承运人或者与其订立商务协议的合作伙伴的航空器需以经营旅客航空运输业务为目的到达该缔约国或者从该缔约国始发;④承运人处所限制,承运人或者与其订立商务协议的合作伙伴在该缔约国境内存在租用或者所有的处所从事旅客航空运输经营。适用条件处需要注意的是,在确定旅客主要且永久居所地时不能将该名旅客的国籍作为判断的决定性因素。另外,旅客航空运输业务是指将旅客从A地点移动至B地点的活动,而旅客航空运输经营是指运输业务、销售旅客飞机票、广告宣传等。可见旅客航空运输业务的范围要窄于旅客航空运输经营,后者包括但不限于旅客航空运输业务[4]52。
(二)第五管辖权适用上的争议
在实践中,管辖权适用引发的主要分歧在于公约规定的管辖权是“地指具体地”还是“地指国”。该争议由来已久,早在1929年《华沙公约》实行期间就存在广泛争议。所谓“地指具体地”是指,公约所称原告可以向承运人住所地、主要营业地……的法院提起,地是指具体的地点[5]。假设一名旅客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购买乘坐首都航空公司的航班,目的地是北京大兴机场。那么,依据“地指具体地”理论,原告可选择在首都航空公司住所地以及主要营业地北京市顺义区法院或者订立合同营业地纽约地区法院或目的地机场所在地北京大兴区法院起诉。所谓“地指国”是指,将“地”理解为国家。上例若按“地指国”理论,则结果将产生较大变化,首都航空公司的住所地、主要营业地以及目的地在中国,旅客若选择到中国起诉是可行的,至于具体法院,需要根据中国的民事诉讼规则确定。或者旅客可选择到订立合同营业地所在国,也就是美国起诉,同样,具体的受诉法院需要根据美国的民事诉讼规则确定。对比可见,两种理论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前者直接指向了某个国家国内具体的法院。而后者将原告引导至具体国家就截止了,具体的法院需要根据该国的民事诉讼规则确定。
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地指具体地”理论,其中以法国为代表,法国最高法院判决的Liberatorc C.Air France是该类案件采取“地指具体地”理论的经典案例③。英国采用的是“地指国”理论,英国最高法院判决的Rotterdamsche Bank V.British Overseas Airways是采取“地指国”理论的经典案例④。而美国从1963年飞虎公司案之后,开始广泛采用“地指国”理论,美国马歇尔法官所提出的国家是国际法的基本单位是其理论依据。美国权威航空法律师乔治·汤普金斯博士也是现代美国航空法学界坚决支持“地指国”理论的拥护者,他表示管辖权是一个大的概念,尽管一些早期法院判决将“地点”设定为国家内某个管辖区,但这些判决是错误的[6]。
在第五管辖权适用的过程中,依旧存在着上述争议。但是,与之前不同的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对第五管辖权进行“地指具体地”理论解释的时候会较为困难。其原因在于,第五管辖权是由美国提出的,而美国在提出第五管辖权的时候注意到了“地指具体地”与“地指国”之间的分歧,而美国又是“地指国”的拥护者,故为了更加明确适用“地指国”理论并维护其自己的利益,美国特意将条文设计成于传统管辖权不同的表述形式,即没有明确将有关诉讼可以“向旅客的主要且永久居所地法院提起”[3]247。正是由于此种设计,导致依照“地指具体地”理论确定第五管辖权法院会不明确。在实践中,存在不少国家的法院混合使用两种理论的情况,即在前四种管辖权的时候适用“地指具体地”理论,在第五管辖权时则适用“地指国”理论。在理论界,中国航空法学者郑派也提出了在适用前四种管辖权应当适用“地指具体地”理论而当适用第五管辖权条款确定具体管辖法院时应当采用“地指国”理论的二分法理论[3]256。笔者以为这种做法是值得探讨的,因为这有悖于法律解释方法之体系解释。体系解释最基本的考虑是要保证法律体系的融贯性,防止法律前后矛盾性的解释[7]。为符合体系解释的要求,应统一适用一种解释方法。
笔者认为在管辖权适用的过程中,若采用“地指国”理论是欠妥的。根据字面解释,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33条第1款规定的四种管辖权在英文文本中使用“place”一词,“place”在《牛津高阶词典》中的解释为“A particular position,point of area”意为具体一个地点[8]。在中文文本中使用“地”一字,“地”在《新华大字典》中的解释为:某一地区、地点[9]。两种文本均指向具体的地点,所以从字面解释的角度出发,应采用“地指具体地”理论。确立应以“地指具体地”理论作为前四种管辖权解释方法后,依据上文所述体系解释之基本考虑,第五管辖权也应当适用“地指具体地”理论确定管辖法院。同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也是适用“地指具体地”理论的重要缘由,该公约是规制国际条约解释领域的重要公约,参加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缔约国大部分也都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缔约国。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国际公约解释规则,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包括前言及附件。具体到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33条第2款所述第五管辖权的解释,则应按该款上文规定的四种管辖权所采用的“地指具体地”理论确定第五管辖权法院。且因《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要求解释条约需要参照前言、目的和宗旨进行解释,因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前言部分表明了其宗旨和目的,即增进国际航空运输规则的统一化并确保国际航空旅客的利益。若采用“地指国”理论确定第五管辖权法院,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旅客主要且永久居所地国的民事诉讼法以确定其具体的管辖法院,而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法院管辖规则是不同的,不利于国际航空运输规则的统一化,又由于“地指国”理论下法院的确定不如“地指具体地”理论明确,这有损旅客对管辖法院的预期利益。而“地指具体地”理论确立具体的第五管辖权法院则恰好相反,有利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宗旨和目的。同时,这是符合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确立的解释规则的。故从该角度观察,适用“地指具体地”理论确定第五管辖权也是比“地指国”理论合理的。
但是,适用“地指具体地”理论确定具体的第五管辖权法院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该条款确实未指向一具体法院。法国航空法学者本杰明·珀特里尔认为应该寻找一个最接近“地指具体地”理论的具体的第五管辖权法院⑤。笔者参考了该观点并将其认定第五管辖权法院的方法进行了改进。笔者改进之后的方法如下:公约第33条第2款共涉及三个地点,分别是旅客主要且永久居所地、承运人到达或始发地以及承运人处所地,认定具体的第五管辖权法院时应当寻找这三个地点交集处的管辖法院。例如,三个地点均在成都双流区,那么第五管辖权法院就是双流区法院。如果旅客主要且永久居所地在成都市、承运人到达地在乐山市、承运人处所地在绵阳市,三地点的交集在四川省,那么第五管辖权法院就是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最极端的情况是旅客主要且永久居所地在四川省、承运人到达地在北京市、承运人处所地在上海市,三地点的交集是中国,那么第五管辖权法院就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五、第五管辖权对中国立法的借鉴意义
中国《民用航空法》没有对航空案件管辖权进行规定。对于航空案件的管辖权由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7条和第29条调整。其中,该法第27条规定航空运输合同纠纷由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该法第29条规定航空运输侵权纠纷由事故发生地或者航空器最先降落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可见,中国相关法律并没有类似于第五管辖权的条款。
(一)借鉴第五管辖权的必要性
虽然中国法律规定,若中国参加的国际公约的规定与国内法律不一致的,优先适用国际公约。这样就使得第五管辖权在国际航空运输中可以使中国旅客受益。但是并不是所有跨国航空运输都能适用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如中国旅客乘坐高丽航空从北京起飞至开城的航班,在朝鲜境内飞行过程中因侵权事故遭受损失就因朝鲜不是该公约缔约国而无法适用公约规则,就使得中国旅客无法受到第五管辖权的保护,在此种情形下朝鲜的管辖权规则与中国《民事诉讼法》管辖权规则很可能产生冲突,即使最终管辖权规则指向中国法律,那么因为中国《民事诉讼法》第29条在此种情形下没有指向中国法院,则最终旅客只能去国外起诉。这是不符合世界范围内国际航空运输第五管辖权趋势的,也不利于中国旅客利益的。如前文所述,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第五管辖权并不是多余的,总体来说也是利大于弊的,也是符合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时代潮流的。故为了避免在上述情况下当管辖权规则指向中国法律,但中国旅客仍需去外国法院起诉的情况发生,也为了符合国际航空运输管辖权趋势。中国应考虑在《民用航空法》或者《民事诉讼法》中借鉴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五管辖权的规定,以切实保护中国旅客利益。同时,借鉴国际公约中的条款以完善中国《民用航空法》也是早有先例的,中国《民用航空法》私法部分的绝大多数条文都是借鉴1929年《华沙公约》、1955年《海牙议定书》、1961年《瓜达拉哈拉公约》以及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而来,故借鉴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五管辖权也是符合先例的。
(二)借鉴公约第五管辖权过程中的修改
1.索赔情形的修改
对于第五管辖权的借鉴不能一字不动地完全照搬,而是需要对其进行适当修改。首先,需要修改第五管辖权索赔情形的限制。公约中的第五管辖权仅限于旅客人身伤害的赔偿,但是一次航空事故很可能既涉及旅客人身伤亡,又涉及旅客托运行李或随身携带的行李的损坏。正如前文所述,按第五管辖权的规定,旅客只能分为诉之,在其主要且永久居所地国家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在其余四种管辖权法院提起行李损害赔偿。从经济角度出发,旅客行李的价值往往不是很高,而往返于本国与他国法院之间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是远远高于行李价值的。在此种情况下,旅客往往会与航空公司和解,但是由于航空公司处于强势地位,而旅客处于弱势地位,常常使得旅客的行李损失无法得到完全补偿。同理,延误所造成的损失和旅客行李所受损失的数额都不大,也会遭遇上述情况,故延误损失也应纳入新修改的管辖权条款的索赔情形之中。至于货物索赔,则与上述情况相反,航空运输所载货物一般价值较高,托运人往往也都是跨国贸易公司,拥有专门的法律人才,双方基本处于同一优劣地位,托运人一般不会在过分损失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与航空公司和解,故货物损失索赔可不必纳入新修改的管辖权条款的索赔情形。
2.旅客居所地的修改
需要明确公约英文译本中“Permanent Residence”和中文译本中主要且永久居所地的含义。著名航空法学者赵维田认为,将“Permanent Residence”汉译作永久居所是值得研究的,因为永久一词含有一辈子 不变的意思[10]。朱子勤认为,惯常居所和公约所采用的“主要且永久居所”的含义基本是一致的。习惯居所是指是一个人在某一段时间内生活的中心和居住的处所[11]。结合二者的观点,笔者认为在中国法律环境之下,应将域外法律语言转化为最贴切其本意国内法律用语。笔者认为,在中国法律语境下,应以《民诉法司法解释》第4条之规定所述经常居住地代替之⑥。
3.明确具体的管辖法院
正如前文所述,第五管辖权法院的确定存在分歧,故在借鉴过程中应解决这一问题。条文中应该明确指向某一具体法院,而非像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的条款一样规定模糊。虽然按照笔者在上文所述的方法可以确定一个具体的法院,但是这也是为了遵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方法并最大限度的符合公约管辖权规则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所以,如能在条文中直接了当、明确地指出管辖法院是最好的。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种方案:①向发生事故时旅客经常居住地法院提起;②向始发地或者到达地法院;③向承运人处所地法院。以上三种方案中第一种方案偏向于旅客。后两种方案因承运人在该地有商业存在,而旅客不一定居住在此地,可以认为后两种方案偏向于承运人。至于最后采取何种方法需要根据立法者的考量作出最终的决定。
如果以后立法机构认为需要借鉴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五管辖权的规定,可以参考笔者综合以上几处修改所提出的条文文本:对于国际航空运输中因旅客死亡或者伤害或者行李损坏或者因延误而产生的损失,如果满足下列条件,诉讼可以在中国提起,即在发生事故时旅客的经常居住地在中国境内,并且承运人使用自己的航空器或者根据商务协议使用另一承运人的航空器经营到达中国领土或者从中国领土始发的旅客航空运输业务,并且在中国境内该承运人通过其本人或者与其有商务协议的另一承运人租赁或者所有的处所从事其旅客运输经营。此类案件管辖法院为旅客经常居住地法院(如果立法者为了适当平衡旅客与承运人利益,可将案件管辖法院改为始发地法院或到达地法院或承运人处所地法院)。
六、结论
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五管辖权是由未生效的1971年《危地马拉城议定书》第五管辖权演化而来。虽然在公约起草过程中第五管辖权遭到了很多国家的反对,但是美国是该条款的坚定支持者,其目的是为保护其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利益。即使第五管辖权遭到了反对,但是最终还是被写入公约文本之中,在适用第五管辖权司法实践过程中应严格采用“地指具体地”理论确定具体的管辖权法院。各方对第五管辖权的批评较多,但是实际上这些批评都是没有根据的,并且在国际航空运输中第五管辖权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中国《民用航空法》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航空案件民事管辖权有所不足,所以有必要借鉴第五管辖权的规定,但是应该对其索赔情形、旅客主要且永久居住地的用词以及明确管辖法院进行必要的修改。
注释:
① 参见: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第33条第2款。所谓第五管辖权,是指对于因旅客死亡或者伤害而产生的损失,诉讼可以在这样一个当事国领土内提起,即在发生事故时旅客的主要且永久居所在该国领土内,并且承运人使用自己的航空器或者根据商务协议使用另一承运人的航空器经营到达该国领土或者从该国领土实发的旅客航空运输业务,并且在该国领土内该承运人通过其本人或者与其有商务协议的另一承运人租赁或者所有的处所从事其旅客运输经营。
② 数据参见:https://www.imf.org/en/Countries。
③ 参见:(1975)29 R. F. D. A. 75(T. G. I. Evry-Corbeil, 31 October 1974。
④ 参见:(1953)1 All E. R. 675(Q. B. 1953)。
⑤ 2014年4月30日,本杰明·珀特里尔在莱顿大学法学院举办的名为The Fifth Jurisdiction in the Montreal Convention: A pure rule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of jurisdiction; Justification and consequence的讲座中指出只有第五管辖权涉及的三个具体地点是相同的,此时才会产生符合第五管辖权的法院,否则就不存在符合公约条款规定的法院。
⑥ 所谓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离开住所地至起诉时已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公民住院就医的地方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