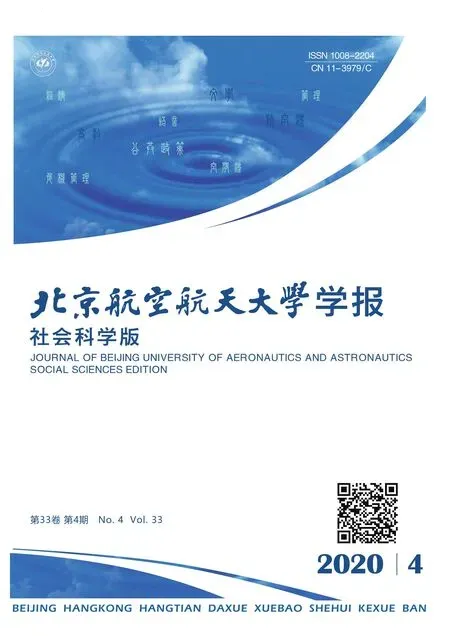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刑事诉讼的制度立场
初殿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3)
近来多起涉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受到学界和公众普遍关注,“王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成为系列事件的争议爆发点,引发了学界诸多讨论。然而,该案只是近年来频发的猥亵儿童案件的一个切口,让人们在感受到切肤之痛时作出了强烈反应。实际上,性侵未成年人一直是犯罪治理中的一块隐疾,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2020年6月1日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暴力化特点愈发突显,其中性犯罪尤为突出,近年来强奸罪一直排在首位,而猥亵罪则是大幅上升,在2019年攀升至第三位。亟待刑事司法制度回应的并非仅仅“王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而是以该案为契机,重新检视刑事司法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制度立场。
一、需要进一步思考的三组关系
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领域,笔者认为,就当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而言,有以下三组关系需要进一步思考,并通过具体领域的规则调整完善来明确制度立场。
第一,被告人权利保护与被害人权利保护。刑事诉讼许多基本理念和制度设计是基于控辨双方之间的不平衡地位,如无罪推定及其相关制度便是具体体现,这种不平衡相当程度上体现为取证能力。然而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控辨双方之间的这种实力对比发生了一定变化,不是因为公权机关不再拥有权力,而是因为证据上的困难使得公权机关失去了指控的利器。如果说证据是支撑刑事诉讼不断向前行走的血液,那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便属于典型的“贫血”案件,此类案件需要强化刑事诉讼有效实现国家刑罚权的功能。这样说并非否定无罪推定在刑事诉讼中的根基地位,而是建议思考是否需要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基于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对某些程序规则加以调整,进而真正实现这类案件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如有些已确立品格证据规则的国家在性侵犯(包括儿童性侵扰)案件中的松动便是一例。
第二,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关照与实体利益关照。刑事诉讼制度设计并非只影响诉讼权利,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着实体利益的实现。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关照来看,在上述两者之间,现有的规范目前主要还是侧重于前者,后者一定程度上缺位。在法律层面,中国《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中有一章叫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的是被追诉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是未成年人,所以该章主要是针对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是未成年人的被追诉人所做的特别规定①。基于教育挽救感化的总体方针,该章之下的制度既包括对未成年被追诉人的实体利益关照(如全面调查原则指引下的社会调查制度),也包括诉讼权利关照。与此相比,同样是未成年人,整部《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被害人的关照则显得颇为冷清,主要集中于诉讼权利关照领域,如询问时法定代理人到场的规定等;而且,诉讼权利关照的属性使得这些规定的适用前提是被害人位于相关程序之中时依然尚未成年,而实质利益关照则并不完全以此为限。2013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准确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了若干体现实体利益关照的内容,但严格说来,这仍是侧重实体法角度作出的规定,因为主要是对刑法条文的解读,而非从程序法、证据法角度强化实体利益关照。
第三,一次伤害与二次伤害。这一组关系与上一组存在一定关联。现在学界和实务界都很关注二次伤害问题,但对愿意站出来控告的被害人来讲,一次伤害问题最终得到司法怎样的回应与处理,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所以刑事诉讼作为一项有担当的制度,在关注二次伤害问题的同时,更应致力于解决如何正确认定和评价一次伤害的问题。而上述实体利益关照在相当程度上与一次伤害密切相关。如何通过程序与证据的制度设计调整,使得司法在面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时,不要显得过于无力和消极,是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二、刑事诉讼制度在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中的作用
以上三组关系汇聚的焦点,集中于刑事诉讼制度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追诉能力的提升,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刑事诉讼程序发现案件并启动侦查的能力;二是结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特殊性调整完善证据与证明制度。
呼吁制度上的这种改变,并非只具有公正解决个案的作用,而且将会从犯罪预防角度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治理产生效果。证据制度和诉讼程序并非仅仅具有在案件发生之后实现实体法规定的工具意义,亦非只是起到保障过程正当性的人权价值,而是能够反作用于尚未进入诉讼视野的、日常的行为选择,进而在诉讼之外也起到促进实体法和犯罪预防的作用。潜在犯罪人的犯罪成本预判与司法制度密切相关,而目前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证据制度的规定现状,一定程度上使得犯罪成本在某些潜在的犯罪人面前显得过于单薄,因其知道这类案件存在证明困难,定罪难度大,甚至有时难以立案。有研究者认为,证据和程序都能为实体法所规范的主要行为(Primary Behavior)而不仅是诉讼行为(Litigation Behavior)创造激励因素,经常被用作例证的是法律通过选择如何设置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来促进诉讼行为与主要行为的最佳关系,进而促进实体法所保护的各种社会利益。实际上,不仅仅是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包括证据规则、证据调查方式在内的程序法、证据法上的设定,同样会产生上述效果。
对于前述两方面问题,尽管立法层面尚未明确,但司法解释、司法实务、学界研究已经开始相关探索:
第一,关于强化刑事诉讼程序发现案件并启动侦查的能力,中国《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及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监察委员会、教育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都体现出这一方向上的要求。然而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结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特殊性对如何理解刑事立案标准作出具体指引,目前的相关规定仍然抽象。
第二,关于结合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特殊性调整完善证据与证明制度,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若干学者已经在性侵未成年人领域提出很多建言,在内容上包括了若干体现实体利益关照的程序法见解,如有学者提出在该领域确立特殊的证据规则,确立以“被害人陈述可信性”为核心的审查标准,转向多元“求真”证明模式,以及赋予法官积极调查的诉讼关照义务,等等。实务中,检察机关亦已在加强对此类案件证据的特殊规律研究,探索相应的证据标准。笔者认为,可以以在证据标准基础上,针对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证据较少、被告人多不认罪、被害人辨别表达能力偏弱的特点,进一步拓展探索此类特殊案件中证据规则、证据调查方式等证据与证明制度,在该领域形成综合考虑未成年被害人实体利益和诉讼权利的、体系化的特别程序。
注释:
①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14—2019)》中采用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表述,从而将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也纳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