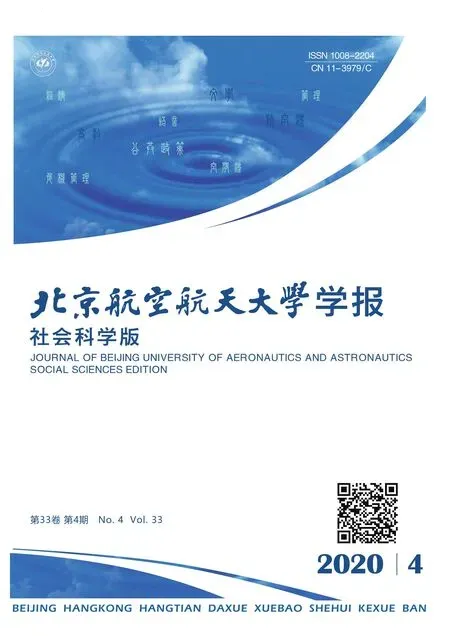从审判不公开看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
裴 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3)
2020年6月17日,“王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一审宣判,5年有期徒刑的刑罚引发了社会热议。与以往各种热点案件一样,网上涌现出大量关于该案件的细节披露和分析,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和被告人辩护律师也相继在媒体上发声,同时该案一审审判长也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采访。纵观当前舆论中关于该案的争议,视角多集中于定罪是否正确、刑罚是否适当、律师是否遵守职业伦理等问题。但由于该案是不公开审理,外界能够接触到的案件事实和证据极为有限,在此背景下对实体事项形成的认知难免有失偏颇;并且各方律师在庭外发表的言论本身不受庭审和证据规则的限制,因此也难以客观呈现案件全貌。相反地,该案的程序性问题虽受关注较少,但对于案件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具有重要影响。
在这些程序性事项中,最为直观的便是该案的不公开审判。该案一审审判长在接受采访时提到:“本案涉嫌性侵未成年人,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故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任何人员不得旁听。”以被害人为未成年人为由不公开审判,反映出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思路。但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法院以案件涉未成年人个人隐私为由而不开庭审理,该理由是否准确;二是不开庭审理是否切实达到了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效果。以下分别就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一、审判不公开中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的立法缺席
中国《宪法》第13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这一规定被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全文继承。审判公开之所以作为基本原则被确定下来,一方面,关涉到司法公信力,即使正义的实现“看得见”;另一方面,也涉及到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即便允许在特定情形下不公开审理,这些情形只能是例外情形,在现有刑事诉讼法律框架下主要包含两类:第一类是应当不公开的情形,包括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未成年被告人的案件;第二类是可以不公开,即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该案牵涉到上述例外情形中的两个要素:一是个人隐私;二是未成年人。
首先来看个人隐私。中国此类公开审判例外情形的表述由“阴私”(1979年中国《刑事诉讼法》)转化而来,多指向与性有关的个人事项。立法概念变动之后,性仍然是个人隐私的重要内容,并在司法实践中常构成审判不公开的依据。该案涉及的“猥亵儿童罪”属于性犯罪,因此基于个人隐私原因不公开审理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这里的个人隐私指向的不仅仅是被害人,还指向被告人;同时,就被害人而言,现有制度也并未区分成年被害人与未成年被害人。
事实上,考虑到隐私权保护与公开审判原则的内在冲突,如果单纯从保护被害人隐私的角度出发,并不必然推导出不公开审理规则。一方面,被害人并非庭审的必须参与者,被害人不到庭不影响庭审的进行,公开审判中必然要曝光的不是被害人而是被告人。另一方面,保护被害人隐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2013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18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确有必要出庭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有条件的,可以采取视频等方式播放未成年人的陈述、证言,播放视频亦应采取保护措施。”
观察域外立法与司法实践,可以看到多种不公开审理以外的保护方法,包括但不限于被害人出庭阶段要求旁听人员退庭、禁止法庭上表明被害人的特定身份事项、禁止庭外披露被害人身份信息等。例如,新加坡禁止披露性犯罪或虐待儿童犯罪的被害人的身份识别信息;违反该规定的行为将构成犯罪,可能被判处最高5 000元的罚金或最高3年有期徒刑;英国法中对公开审判的限制包括禁止对公开庭审进行报道、公开庭审中的部分信息不对外公开、不公开审理、通过电子通信方式庭审等;日本在涉及与儿童色情相关的犯罪中,授权法院作出在公开法庭上不得表明被害人特定事项的裁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2005年通过了《关于在涉及罪行的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事项上取得公理的准则》,之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示范法》,针对儿童被害人和证人的隐私提出了多项保护措施,如在公开记录中删除任何可以用于识别该儿童的信息、禁止辩护律师披露儿童身份识别信息、禁止披露任何可能暴露儿童身份的记录、庭审中隐藏儿童的生理等特征、涉及儿童的庭审阶段不公开等。通过这些措施,法庭可以最大限度平衡公正审判和隐私保护的双重要求。
其次来看未成年人。中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修订时增添“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并规定审判时被告人不满18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这里似乎与未成年人和不公开审理都相关,但其仅指未成年被告人,与未成年被害人没有关系。换言之,在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如果案件不公开审判,是因为被告人才不公开,而非因被害人之故。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中国现有《刑事诉讼法》规定中,关注点仅集中于未成年被指控人,对于未成年被害人和证人的关注明显不足。2013年《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提到,对于涉及未成年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未成年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及可能推断出其身份信息的资料和涉及性侵害的细节等内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律师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应当予以保密。但是,即便有上述保密义务的规定,中国《刑事诉讼法》本身并未作出相应规定,配套措施和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也并未跟上,这就降低了保密义务的实际效力。这一点在辩护律师和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向媒体披露信息方面尤为明显。
二、审判不公开中未成年被害人保护的实效减损
在该案一审判决作出之后,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和被告人辩护律师分别在媒体上发声,就案件陈述本方意见。被告人辩护律师在其发表的千字声明中提到:“北京的两家司法鉴定机构,7位国内权威的法医专家、妇科专家、DNA专家,对上海的门诊记录和司法鉴定意见进行了书证审查和专家论证,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支持上海鉴定当中所说的被害人新鲜伤痕、阴道撕裂伤、二级轻伤的结论。”被害人诉讼代理人披露的细节更多。这些庭外向媒体所作的被害人隐私和案情披露,不仅使得法院通过不公开审判保护被害人的效力大打折扣,事实上将法庭上的不公开审判转变为了法庭外的公开审判,被告人和被害人两方在媒体上展开辩论。
相比于公开审理,庭外公开辩论由于不遵守法庭审理的各项诉讼规则,其负面影响更大。首先,在公开庭审中,法庭尚可以制止涉及个人隐私的陈述,或者对相关证据进行庭外调查,但当双方律师将辩论搬到媒体时,法庭对于双方的言论无能为力。其次,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的关于被告人是否有恋童癖和性虐待倾向的品格证据,以及针对被害人阴道撕裂伤是新伤还是旧伤的说明,合议庭在庭审中可以专业且系统地评价其可采性和证明力,外界也可以观察到法庭与辩护律师事后认定不一致的事实和证据基础,但这些信息在庭外均看不到。最后,双方律师庭外信息披露带有强烈主观色彩,事实信息严重碎片化,证据支持明显不足,这些陈述不可避免地激化外界对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不满,并削弱公众对于刑事司法的信任。
此种情况下,审判不公开非但没有保护未成年被害人,还将其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有观点认为,辩护律师的行为已经构成中国《刑法》第308条之一的“泄露不应公开的案件信息罪”,是否构成该罪还需要刑法学者进一步论证。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如果辩护律师构成该罪,那么恐怕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也构成。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无论信息由哪方披露,都可能对未成年被害人造成伤害,这种伤害不会因为信息披露来自被害人一方而有所减损。
正如一审审判长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最后说的:“本案被害人已经受到了身心创伤,希望无论是网上还是网下,都不要以任何方式对她造成二次伤害,更不要打探未成年人的隐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中国《刑事诉讼法》看到这些未成年人,看到除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外,还会有更脆弱的被害人和证人。为保障公正审判和社会监督,未成年被害人的个人隐私保护不一定要通过审判不公开的方式进行;但如果通过不公开审判来保护,那么就应当让不公开成为真正的不公开。
三、结论
首先,刑事司法对于未成年人的完整保护,需要同时兼顾被指控人和其以外的诉讼参与人,其中又以被害人和证人为主。其次,刑事司法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应以成年人作为参照系进行细微调整,而是要在整体制度设计理念和架构上关照到未成年人的特殊需求。再次,审判公开原则应当尽可能的保障,在需要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中,不公开审判仅是手段之一,并且也应当作为最后手段;保护措施应当分层化,保密义务需要匹配相应的披露禁止程序和法律责任。最后,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义务应当适用于各类诉讼主体;就律师而言,既包括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也包括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未成年人被害人无力控制其诉讼代理人的言行,因此需要法律予以特殊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