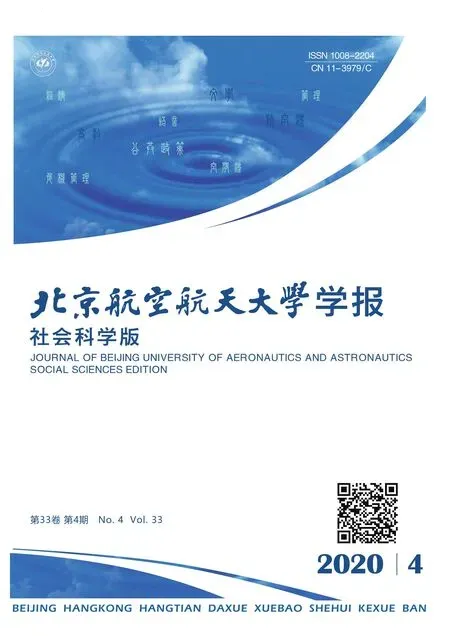论猥亵儿童案中强奸罪(未遂)的认定
王海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3)
在“王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中,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并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该判决宣告后,民意鼎沸,公众普遍质疑一审法院的量刑过轻,有轻纵被告人、弱化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之嫌。而学界关注的重点则是,一审法院在猥亵儿童罪的基本法定刑幅度(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内量刑,而没有在该罪的加重法定刑幅度(5年以上有期徒刑)量刑,是否妥当?因为该案固然不是在公众场所当众实施,但是鉴于被害人的年龄(9岁)、被害人伤害(轻伤),能否认定本案存在着猥亵儿童的“其他恶劣情节”,并适用加重的法定刑幅度,对被告人从重处罚,则成为了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该案关注的焦点应当放在定罪,而非放在量刑上,将该案定性为猥亵儿童罪,而非强奸罪本身存在着问题,正是因为定罪的不当导致了量刑的明显不当。
一、以猥亵儿童罪定性存在的问题
一审法院认为该案被告人构成猥亵儿童罪而非强奸罪,本身在定性上存在着问题。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构成猥亵儿童罪的理由在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性器官的相互接触,其行为不属于奸淫幼女行为,而属于猥亵儿童行为。但是,一审判决所主张的这种见解,是不妥当的。在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中,与被害人性器官的接触,只是行为人构成强奸罪既遂的要件,而非成立强奸罪的要件,如行为人出于奸淫幼女目的,对幼女实施暴力、胁迫行为,被第三人制止未能得逞的,即使被告人与被害人的性器官不存在相互的接触,也不妨碍强奸罪的成立,充其量妨碍的是强奸罪既遂的成立,行为人仅构成强奸罪的未遂。
二、强奸罪(未遂)与猥亵儿童罪的想象竞合犯
就“王某某涉嫌猥亵儿童案”,笔者认为,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犯了两项罪:一是强奸罪(未遂);二是猥亵儿童罪,属于——行为触犯数罪的想象竞合犯。
(一)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了强奸罪(未遂)
被告人的行为成立强奸罪(未遂),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被告人具有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故意。一是被告人具有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意图,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印证,即同案犯周某某称自己曾长期给王某某提供成年女性进行嫖宿,且从当前披露的情况来看,被告人王某某没有性虐待等畸形癖好,从日常的生活常理推断,被告人对于同案犯周某提供的该案被害人,怀有的意图应当是与其发生性关系,而非猥亵。二是被告人明知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对象是幼女,这一点有着较为充分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而就事实根据而言,认定被告人明知被害人是幼女,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印证:①据同案犯周某某的交代,称自己曾长期给王某某提供女性,不过以前都是成年女性,这次她以为是“王总的口味变了”。只有作为需求方的王某某明确提出不同以往的要求,要求周某某提供幼女,作为非法服务提供方的周某某才能明白该需求的转变,才会有针对性的诱骗该案中仅有9岁的被害人。②同案犯周某某是基于与王某某的约定,将被害人从江苏带到上海,若是被害人不符合王某某的要求,意味着周某某无法实现其不法的牟利动机。③被告人王某某走入房间后,对于9岁的被害人并没有表示拒绝,而是采取了猥亵行为,也能说明周某某提供的该种年龄的被害人,恰巧符合被告人提出的需求类型。而从法律依据上看,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法发[2013]12号)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第二,被告人已经着手实施奸淫幼女的行为。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与一般强奸罪相同,其实行行为包括了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手段行为具体包括行为人对幼女实施暴力、胁迫,或者采用其他使幼女不能反抗、不知反抗的措施等;目的行为则是与幼女发生性关系。因此,只要行为人着手上述手段行为,即使没有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就应当认定其着手了强奸罪的实行行为。而在非暴力、非强制性的奸淫幼女型强奸罪中,其手段行为多是对幼女采取引诱、欺骗行为,因此,行为人出于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意图,采取引诱、欺骗行为,并与幼女发生肢体接触时,就应当认定其对被害人身心健康法益造成了急迫的危险,着手了强奸罪的手段行为,不需要行为人与被害人的性器官存在着相互的接触。而在该案中,被告人王某某与同案犯周某某的约定行为、在酒店开房行为以及将被害人从江苏运送至上海的行为,都是为实施奸淫幼女制造条件的行为,属于预备行为,但是其自进入酒店内,通过哄骗、引诱等方式与被害人进行身体接触之时起,已经对被害人的身体法益产生了紧迫的危险,应当认定其开始着手了强奸罪实行行为中的“手段行为”,何况对被害人实施了进一步的猥亵行为,并造成了身体伤害,因此,认定被告人王某某已经着手强奸罪的实行行为,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被告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了奸淫幼女的行为。被告人虽然着手了强奸罪的实行行为,但是,其与被害人的性器官不存在相互的接触,因此,不能以强奸罪的既遂论处。而被告人实施的强奸行为之所以在达到既遂之前停止下来,在于被告人的性需求、动机因其猥亵行为而得到满足,没有必要实施进一步的性侵害,实现性器官的相互接触,其犯罪动机因其他方式得到满足而停止犯罪的,这种情形的停止,并没有显示出向法规范的回归,应当认定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止犯罪,如行为人在抢夺被害人手机的过程中,被害人将一叠现金扔给行为人,行为人因谋财动机得到满足,而放弃抢夺行为的,不能认定行为人自动中止了抢夺行为,应当认定该抢夺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止,行为人构成抢夺罪的未遂。因此,应当认定被告人实施的奸淫幼女犯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得逞,构成强奸罪的未遂。
(二)被告人的行为同时构成了猥亵儿童罪
在该案中,在客观上被告人王某某对不满14周岁的被害人确实实施了猥亵行为,并且造成了被害人的身体伤害。在主观上被告人表面上看起来只有奸淫幼女的故意,没有猥亵儿童的故意,但是奸淫幼女的故意与猥亵儿童的故意,两者之间不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等级序列关系。前者是一种罪过程度更重的故意,将前者降低评价为后者,对于被告人并无不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定被告人主观上也具有猥亵儿童的故意。因此,王某某的行为也同时构成了猥亵儿童罪。
三、结论
被告人王某某的一行为触犯数罪,属于刑法学理上的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就王某某触犯的强奸罪而言,根据中国《刑法》第236条的规定,应当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虽然其属于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但是,被告人王某某对不满12周岁的被害人实施侵害并造成被害人轻伤二级的严重后果,且被告人王某某到案后及庭审中拒不供认其猥亵的犯罪事实,应当依法或酌情从重处罚,因此,不宜对被告人进行从轻、减轻处罚。就王某某触犯的猥亵儿童罪而言,由于被告人不是聚众或在公众场所当众实施该罪,不存在依照中国《刑法》第237条第2款明文规定的加重处罚事由;此外,由于无法证明被告人多次实施猥亵儿童的行为、对多名儿童实施了猥亵行为,而且其猥亵行为只是造成了被害人的轻伤,认定该案存在着猥亵儿童的“其他恶劣情节”,不能不说面临着重大的障碍,因此,依据中国《刑法》第237条第1款、第3款的规定,适用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法定刑幅度,恐怕更为合理。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其触犯的猥亵儿童罪的刑罚明显低于其触犯的强奸罪的法定刑,因此应当认定王某某构成强奸罪(未遂),并在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法定刑幅度内判处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