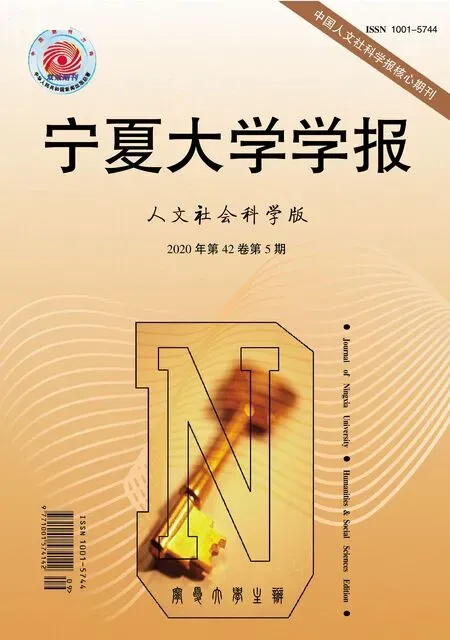论马洛戏剧中恶习人物的渊源、质变及经典化影响
周雪凝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恶习人物是戏剧艺术中一类典型而富有特色的人物类型,自古希腊时代就已有之。它在戏剧中的英文对应词是“The Vice Figure”或“The Vice”,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喜剧中的吹牛武士、机智的仆人、诡辩的密谋者或是具有怪癖的食客人物。作为马洛戏剧中极为关键且数量众多的恶习人物,其最直接的来源是英国中世纪的道德剧。在道德剧中,恶习人物作为地位次要的训诫式人物而存在,且性格特征固定与僵化。而马洛戏剧中的恶习人物顺应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主体意识不断上升的文化语境,产生了质变性转型:他们成为具有充沛生命力的主体性人物,不再承担刻板的说教功能,而是展现着主体自身的情感、欲望与个体潜能。国外关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恶习人物的研究较为充实:学者伯纳德·斯皮瓦克(Bernard Spivack)在《莎士比亚与恶的寓言(Shakespeare and the Allegory of Evil,1958)》、 道 格 拉 斯·科 尔(Douglas Cole)在《克里斯托弗·马洛戏剧中的苦难与邪恶(Suffering and Evil in the Plays of Christopher Marlowe,1962)》、 克 利 福 德·利 奇(Clifford Leech)在《克里斯托弗·马洛:舞台诗人(Christopher Marlowe:Poet for the Stage,1986)》中都专辟文章对恶习人物进行阐释。他们从历史溯源、宗教需求、世俗化过程、美学特征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在国内有关这一主题的探讨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首先试图追溯恶习人物在道德剧中的起源,并对其世俗化过程进行梳理;其后针对马洛戏剧中恶习人物所产生的质变及主体性特征进行概括;最后结合恶习人物的经典化特征,分析其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变革意义及美学影响。
一 恶习人物的溯源及世俗化过程
“邪恶因素”在英国中世纪的神秘循环剧中就已出现,主要表现在狂暴的希律王、吹嘘的法老、自大的彼拉多以及残忍的该隐等人物形象上,反映着道德混乱、秩序崩溃的严肃主题与宗教神学的思想观念,其后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快,逐渐演化成为道德剧中特有的恶习人物。道格拉斯·科尔在《克里斯托弗·马洛戏剧中的苦难与邪恶》一书中阐释了为何严肃的宗教戏剧中需要表现邪恶的因素,这主要存在两重原因:其一是中世纪的人们发现人类的灵魂非常容易变得膨胀,所以需要在戏剧中提醒人们自身的愚笨以及邪恶的品质;其二是中世纪的宇宙概念将自然宇宙整体与历史作为神圣目的之镜,当所有的事情被考虑在内之时,邪恶、喜剧、怪诞等因素都必须被包括[1]。正是基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观念和宇宙论思想,代表着邪恶因素的人物一直存在于英国中世纪的戏剧创作之中,并延续到对马洛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道德剧作品内。道德剧中的恶习人物可以被定性为表现恶劣品性的人格化概念,是一种僵硬的刻板角色,这种角色在本质上是缺乏人类基本感受力与责任感的,其功用就在于在道德剧模式化的场景中,化身为原始的邪恶动机阻碍人类的忏悔之路,并直截了当地揭示他所代表的罪恶的确切本质,起到说教性功用。
恶习人物从寓意性的道德剧渗透到世俗戏剧是一个缓慢过程,最初发生在16 世纪早期。在英国目前已知的剧本中,其首次出现是在约翰·海伍德(John Heywood)在 16 世纪 20 年代左右创作的两部世俗戏剧《天气的戏剧(The Play of the Weather)》和《爱的戏剧(The Play of Love)》中。在这两部戏剧中已经明确出现了带有世俗化特征的恶习人物和直接被命名为“恶习”的人物,标志着附属于宗教严肃主题的恶习人物被引入了更为世俗化的戏剧世界[2]。学者克利福德·利奇(Clifford Leech)认为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这类人物已经转变为“一类纯粹嗜爱恶作剧的有着无限活力的人物。他或许协助于魔鬼进行谋划诅咒的工作,但他如此这般行径是出于乐趣本身而不是因为他信奉般地献身于邪恶的目标”[3]。这一转变的重心在于朝向了人类自身的活力与乐趣。剧作家更为重视的是纯粹的世俗性欢乐和对人类主体自我的全新探知,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人物发展出的新的面向。这种趋向与近代早期人对自我的发现以及对传统神学思想的解构息息相关。但需要注意的是,恶习人物在16 世纪初期虽然已经渗透到各类世俗戏剧之中,但人物角色的主体特征还不明显,恶的美学风格还不鲜明。直到作为大学才子派之首的戏剧家马洛,他所创作的作品才塑造出具有经典化意义的恶习人物:他们保存了诸如统治欲、仇恨感、掠夺欲等人类的本能欲望,并将邪恶的本质展现到无限宏大与充沛的状态,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一度影响到同时代的莎士比亚、本·琼生(Ben Jonson)等戏剧作家以及19 世纪以来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者。
二 嬉戏的主体:马洛戏剧中恶习人物的质变
在恶习人物的世俗化转型中,“嬉戏”成为马洛恶习人物的主体性特征和精神面向。在《马耳他的犹太人》中,马基雅维利作为开场人在序幕中就谈到吉斯公爵将要来到此处视察,和朋友们嬉戏作乐,“嬉戏(Frolic)”一词奠定了该剧的总体基调。在《迦太基女王狄多》中,马洛以朱庇特与侍酒男童伽倪墨得斯的调情景象作为开端,并将朱庇特形容为“愉悦与所有嬉戏灵感的创始之父(《迦》,4.2.5)”[4](本文全部剧本引用来源于Christopher Marlowe:《The Complete Plays》,为简洁起见,其中引用的戏剧段落按照戏剧名称中译的首个汉字进行标注,如《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简称为《浮》,《爱德华二世》简称为《爱》,《马耳他的犹太人》简称为《马》,以此类推),为人物的精神状态烘托出统一的戏剧氛围。总观马洛戏剧文本,一方面,嬉戏成了多组重要人物之间的关系状态,如爱德华二世与其情人加弗斯顿,朱庇特与伽倪墨得斯,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狄多与埃涅阿斯等。另一方面,嬉戏的状态还形成了在剧场中特有的行进节奏、角色与观众互动的方式。
首先,马洛的恶习人物呈现出一种与对象化自我的嬉戏。关于“对象化自我”的概念,黑格尔曾指出:“在戏剧里,具体的心情总是发展成为动机或推动力,通过意志达到动作,达到内心理想的实现,这样,主体的心情就使自己成为外在的,就把自己对象化了”[5]。马洛戏剧中呈现的人物角色与内在性自我的嬉戏,标志着文艺复兴戏剧中人物内在自我的生成。学者克利福德·利奇将马洛塑造的帖木儿大帝等人物的行为概括为“一种人类意愿他自身沉醉的行为”[6]。这些戏剧人物经常沉浸在自我行动之中,其行为皆受其自身欲望的驱使。他们的行动不再束缚于道德剧中固有情节模式,不再需要外在魔鬼的诱惑,因为内在的欲望已然支配了他们的身体与行动。就像在《马耳他的犹太人》中巴拉巴斯的经典性的自我概括。
“至于我自己,我夜间四处闲逛,杀死在墙角下呻吟的病人;有时我到处走动,朝井里下毒……从那之后,我放高利贷,敲诈勒索、哄骗、造假,掌握了投机者的诀窍技法,一年之内我让破产者挤满牢房,让幼小的孤儿住进医院,每次月圆让这人或那人发疯,时不时就有人痛不欲生上吊自杀,他胸前挂着一张长长的申诉状,痛诉我饶有兴致地折磨他。你瞧我是如何让他们痛苦而得到福佑:我的财富足以买下这整个的城市。现在告诉我,你怎么打发时光?”(《马》,2.3.177-204)。
巴拉巴斯用这段经典对白表明他在戏剧开端扬言的复仇只是一个幌子,一个看似充分的理由。而实质上,杀人、投毒、引诱、勒索、哄骗、造假、折磨等邪恶手段才是让他获得愉悦与消遣的途径。因为他在复仇成功后并未收敛他邪恶的动机,依旧自由施展着自己的罪恶行径。罗伯特·洛根(Robert A.Logan)在分析巴拉巴斯犯罪原因时指出:“起初似乎是信仰状况和邪恶的政治阴谋强加在他身上的结果,后来则似乎成为他根深蒂固的心理特征”[7]。与其说这些残忍行径是巴拉巴斯的复仇,不如说他就是作为一个施虐与残忍的主体而存在的。这种内心状态不仅存在于巴拉巴斯,当浮士德说出:“你侍奉的神灵是自己的欲望”(《浮》,5.11)之时,也将自己的欲望当作行为的牵引力,其他恶习人物如爱德华二世与加弗斯顿,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情欲;帖木儿专注的是权力欲与征服欲,他们全被自身的欲望牵引着,陷入内在的孤独中,成为一种排他性的主体。
其次,这类恶习人物的嬉戏还表现为对剧中次要角色的戏弄中,既包括一种操控性的权力欲望,也包括一种暴虐的残害性欲望。例如在《马耳他的犹太人》中,巴拉巴斯将其他角色像木偶或兵卒一样的操控,他用伪造的决斗信、金钱的诱惑、淫荡的欲望、致命的毒药等伎俩,操控着剧中其他角色的悲惨命运,他的希望是“只要我活着,但愿全世界都灭亡”(《马》,5.5.10),他对于新买来的奴隶伊萨默尔(Ithamore)是这样教导的:“拒绝萌生这些感情:怜悯、爱、徒然的希望、莫名的恐惧。不要为任何事所感动;不要同情任何人,当基督徒们哀号时,你独自在狞笑”(《马》,2.3.172-175),巴拉巴斯沉浸在残害他人的愉悦中,甚至呈现出极端的美学风格。他摒弃了恶习人物惯常的闹剧感或轻松感,表现得更为阴暗与深沉,更多地承载了剧作家试图表达的恶的美学意旨。在《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一剧中,浮士德也同巴拉巴斯一样,他试图操控的是整个世界。浮士德利用梅菲斯特的黑魔法试图使万物运行顺从于自己的指挥。他说:
两极间一切运行着的万物
都得听我的操控。皇帝与国王们
只能在各自的领地发号施令,
但他们不能翻起风浪一手遮天;
唯魔法师的支配权可以超出这些,
直抵人类的理智意念的极限。
(《浮》,1.58-63)
这正像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洛斯比罗试图用魔法控制岛屿。浮士德的行为不仅是自我意识的体现,而且还是权力意志的追求,他妄图实现人类的极限权力,将人类自身视为凌驾于万物之上权力统治者。除此之外,这类恶习人物还具有损害他人的倾向:帖木儿残害、虐待众多国王并且血腥屠城;巴拉巴斯毒杀了修道院中全部的修女,也包括自己的女儿;梅菲斯特戏弄教皇和一众僧侣,嘲弄既成的规则与秩序。这些情节都表明人类的死亡灾难对于恶习人物来说仅是嬉戏的乐趣,人的身体成为他们施展欲望的支离破碎的客体。在马洛的戏剧中,恶习人物总是试图打破看似稳定的各类范畴,行为经常超出荒谬的边界,呈现游戏者的精神状态。
最后,恶习人物将观众作为他者进行游戏,与观众互动、共谋。观众作为戏剧演出中的活力元素,是剧作家们试图充分利用或实验的重要领域。马洛作为受到热烈追捧的剧作家,观众是其戏剧创作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曾评价说:“马洛所取得的突破是异常新奇的,他发明了一种戏剧化的控制观众的方法,能让他们随着帖木儿的吹嘘变成潜在的同盟者和受害者”[8]。马洛擅长利用恶习人物的旁白来造成一种与观众的互动游戏,观众时常被这些人物蛊惑的言辞、夸张的句式和引诱的动机牵引着,成为同谋犯,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他们的帮凶。《马尔他的犹太人》在第二幕第三场出现了29 次旁白,第四幕第三场总共89 行对话,就出现了10 次旁白,戏中巴拉巴斯几番询问在场观众对他行动的意见,对话和旁白非常紧凑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人物与观众互动的嬉戏状态。道格拉斯·科尔在研究马洛邪恶角色与观众的亲密关系时,进行了总结性的评价:“比起所必须的严格说教目的,演员与观众的亲密关系延展到更广的范围:邪恶角色会经常在他的表演中进行自我赞美,并且对于他的受害者或普通人类展露冷嘲热讽的蔑视,他乐于自豪地揭露自己即将展开的计谋与策略;当他的受害者出现之时,他就展开幽默的旁白,并且有时甚至一直持续进行喋喋不休的狡诈游戏,对人类的英雄传达自己真实的计划”[9]。
马洛恶习人物的主体性特征和行动的策略,非常具有侵略的诱惑性。他们迫使观众放下了压抑的传统式防御,变成任性的消费者,形成了以恶习人物的积极性为主导的游戏氛围。这种迫使观众形成的参与度与共谋感,其意义不止停留于娱乐和游戏的层面,而是倾向于以违反公认的道德判断、传统惯例、人性概念等实验性的手段,将观众赤裸裸地置于一个具有挑战性与颠覆性的剧场,对观众进行着观感与思想上的冲击,也展现了剧作家马洛所追求的恶的美学旨趣。
三 恶习人物的经典化特征及影响
马洛戏剧中的恶习人物在与自身、与他人、与观众三重嬉戏互动的维度中,完成了主体化的质变,形成了四种经典化特征:一是作为戏剧的主要行动者,他们具有充满无限活力的能量元素[10](马雷什(F.H.Mares)指出“与‘恶习’(vice)相关联的名字,是指代理人的涵义或者指涉一种面具或是伪装,这种说法可以解释此类人物在各种形式中的所具能量元素的意义”)。他们从道德剧中的次要角色上升为戏剧中的行动主角,对邪恶的施展呈现出宏大肆意的状态。二是人物呈现为孤立的异类存在,产生出了自负、矛盾与疏离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孤独的人物状态要比“他们通常被认为的更具有真实的本体论意义”[11]。三是他们作为嬉戏与反叛的主体,消解了现行的价值体系和制度运行规范,成就了马洛戏剧中的颠覆性风格。四是他们擅长职业性的吹嘘,呈现出一种雄辩式的夸张修辞,影响着在场观众的情绪,也影响了众多戏剧家的修辞风格。
马洛恶习人物的影响总体上可分为两个重要时期,这与其作品从16 世纪传播至今的状况密切关联。第一个时期是在他身处的时代,也即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直至英国王政复辟之前的阶段。第二个时期是19 世纪初期之后,随着浪漫主义对于文学偏好的转向,“恶”成为文学创作的关注对象,马洛的恶习人物被视为反叛人物的先驱。
在第一个影响时期,马洛对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影响是最为引人关注的。在伦敦剧场界,马洛作为大学才子派戏剧家群体中最负盛名的一位,他的戏剧演出受到热烈追捧,对莎士比亚的创作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学者罗伯特·洛根在分析《浮士德博士的悲剧》《麦克白》和《暴风雨》三部戏剧的关系时,指出“人们或许会认为马洛的影响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但是在莎士比亚的事业进程中,这种影响力似乎仅以一种更为深远、广泛和复杂的方式表现出来了。因为它的微妙,它会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但是却是不可以被忽视的”[12]。首先,马洛塑造的恶习人物巴拉巴斯对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的影响已经得到了研究学者的较多证实。例如,国外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在《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哈罗德·布鲁姆在《剧作家与剧作》、杰弗里·布洛(Geoffrey Bullough) 在《莎士比亚的叙事与戏剧来源(Narrative and Dramatic Sources of Shakespeare,Vol.I,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7)》中都谈论了马洛的人物巴拉巴斯对莎士比亚的人物夏洛克的影响。两位戏剧人物都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犹太人,都是与周围人物格格不入的异类,并且都展现出在金钱之爱和女儿之爱的矛盾中的困惑之感。在这一人物的塑造中,莎士比亚被学界普遍认为并未超过其前辈马洛所达到的艺术旨趣,巴拉巴斯作为独立行动的嬉戏主体“总那么逍遥开怀,因为他是个自由的人,或者说,是个自由的魔”[13],而相比之下,夏洛克更多被视为“一个反面角色而不是一个异类,是一个戏剧中爱情故事传统中的衬托性角色”[14],或一位“患有强迫症的病人”[15],是一个毫无新意的犹太人形象。其次,浮士德这一角色对于莎士比亚塑造麦克白与《暴风雨》中的普洛斯比罗都产生了较为直接而清晰的影响。浮士德与麦克白都表现为灵魂在诅咒中苦痛行进的精神状态,他们在对于时间飞逝的感受性、世界运行规则的无法掌控性、不具备忏悔能力的自我憎恨感、孤立堕落的绝望状态这些方面都具有强烈的相似性。而浮士德和普洛斯比罗二者的相似性则在于他们共同作为魔法的运用者,呈现出人类无尽的想象力和对于掌控秩序与规则的欲望。马洛虽然29 岁就意外身亡,但是其作品中蕴含的思想性、变革性与想象力,都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得到微妙的传接与重塑。学者罗伯特·洛根针对马洛对莎士比亚的影响作出了理性而客观的评价,他指出:没有固定的模式来描述马洛的影响如何典型地控制住了莎士比亚的想象力,也就是说莎士比亚接受或拒绝了哪些因素,以及在单篇作品中存在着哪几个种类的影响,同时也不能保证一旦一种影响形成了,它就会固定或者不会发展或变形。莎士比亚最终会将影响融合成自己的特征[16]。除了莎士比亚之外,马洛恶习人物所具有的无所不包的野心、超人的行径、夸张的话语也被同时代剧作家大量承袭,例如本·琼生创作的《美食家(Sir Epicure)》中的人物就内含这些经典化特色,而巴拉巴斯、帖木儿等人物在修辞上运用的节奏、语群、句式、古典风格等,也被同时期剧作家广泛模仿。但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繁荣阶段并未持续很久,自1642 年内战爆发,以清教徒为主的克伦威尔派执政后下令关闭所有剧场,标志着这一繁荣时期的终结,马洛的一切作品也随之销声匿迹,其传播和影响也因此中断。
第二个时期是自19 世纪初开始,“马洛的人生与全部作品都被浪漫主义者重新挖掘,对他们来说,马洛成为诗歌反叛的化身”[17]。马洛的恶习人物独具的颠覆特征形成了近代早期关于邪恶的经典化塑造,对拜伦(Byron)、玛丽·雪莱(MaryShelley)、王尔德(Wilde)、康拉德(Conrad)等作家产生了前驱性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已经很难确切追溯马洛对后世的清晰、直观的影响痕迹,就像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提到的后来诗人对前驱诗人的“修正及逆反”的观念[18]所揭示的,这种微妙的影响只能更多地从一种精神的、心理的、人格的、认知的维度去把握。拜伦的“东方叙事诗”塑造了一系列孤傲地反抗社会的拜伦式英雄人物,其修辞明显受到马洛作品《希罗与利安得》的影响,而玛丽·雪莱在《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中塑造的怪物具有浮士德式的野心——他希望找到一名妻子的意愿与破碎的没有母亲的家庭意象,都与马洛戏剧中彰显的特征相类似[19]。学者利萨·霍普金斯(Lisa Hopkins)指出了马洛对王尔德创作的潜在影响:浮士德的契约故事影响了《道林·格雷的画像》的创作主题。小说中道林·格雷愿为自身不会衰老而交出灵魂,鸦片馆中女人称他为“魔鬼的交易”以及他试图忏悔的徒劳等重要情节,都暗含着浮士德的精神历程[20]。另外,在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中,引入一名叫作马洛(Marlow)的叙述者,这名叙述者“对地图特别着迷。常常一连几个钟头盯着南美洲、非洲或是澳大利亚,让自己陶醉在探险家的荣耀里面”[21]。这与马洛塑造的帖木儿大帝、浮士德博士等具有征服欲望的人物相吻合,他们都充满着殖民式的地图性想象和获得权力与财富的欲望。可以说,马洛创作的恶习人物为恶的美学在近代早期的开端提供了经典化形象,而这种影响是微妙而深刻的,体现在人物的主体特征、生命感受或精神状况之上。
马洛的恶习人物抛弃了道德剧中说教的功用和僵化的性格,展现出主体的充沛生命力和个人的无限潜能,标志着英国文艺复兴戏剧中人物个体性自我的生成。一方面,他们开始注重个体欲望的展开,沉浸在自身构想的游戏性世界中,呈现出极端的个人主义或享乐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注重个体潜能的发挥,蔑视一切既定的规则和概念,试图消解永恒的意义和真实的灾难。马洛的恶习人物在恶之本能的爆发过程中,将观众赤裸裸地置于颠覆性的剧场,试图在人类的神圣与鄙俗之间探索出一条充满思辨与诗意的戏剧之路,其间涌动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朝向人类自我的革新性的戏剧精神与美学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