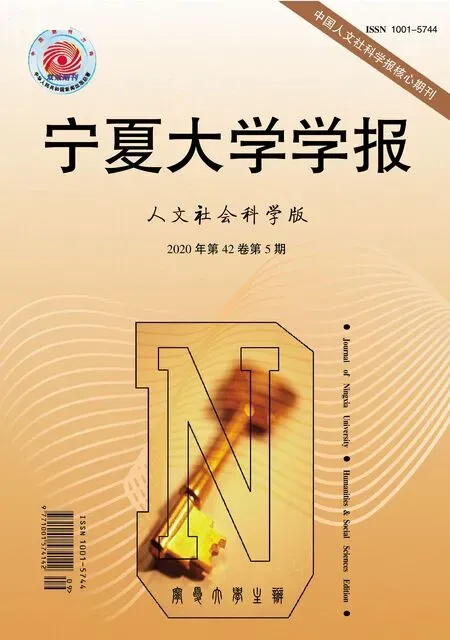论现代诗歌中的“象同意异”现象
——以卞之琳、艾青、导夫为例
马加骏,吕 颖
(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一直以来,中外理论家都有将意象视为“主客交融”的观念。早在南朝时期,刘勰便认识到,“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篇》)。文学形象的构成要素,既要包含“随物婉转”之物象,又要具备“与心徘徊”之心象,二者统一构成意象。法国哲学家伯格森认为,“整个世界就是意象的总和。意象有外在和内在之别,外在的构成物质,内在的构成精神,外在意象由主体构造,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外在的与内在的形象的区别只在于此时此刻它们未被主体所注意,即被知觉”[1]。直言之,“在文学文本解读学中,严格地说,研究的起点或者说逻辑的起点就是‘意象’”[2]。在浩瀚无垠的现代诗海中,将“化石”作为诗歌中心意象的诗作寥若晨星,加之对“化石”含义的固化认知,鲜有其多元意义的诗意解读。卞之琳、艾青、导夫都曾选取“化石”意象进行书文,其“化石”意象既包含一定的共性寓意,同时又指向三种异质哲思与时代倩影。三位诗人从共性寓意出发,通过诗意加工,使其发挥了不同的意指效果。因此,探寻诗歌中“象同意异”现象与其内在原理,有助于揭示处于异质时空的三位诗人之哲学思考与诗意启示。
一 “化石”之共性寓意
“化石”意象在诗歌中的创造性运用,突破了其符号能指链的固化束缚,使化石这一自然符码被赋予了审美意蕴。“化石”是古生物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其表层意义涵盖了“岁月沉积”“沧桑厚重”等固化特质,从其表层意义出发的历史、定格、岁月等衍生意义,成为“化石”恰如其分的共性寓意。在卞之琳《鱼化石》、艾青《鱼化石》、导夫《释放哲学的化石》等诗歌中,都涉及对“化石”意象共性寓意的表达,构成诗人理性世界与感性思维的二元统一。他们对现实时空与象征蕴含、具体概念与抽象情感的诗意描摹,是异质时空下诗人集体无意识的显性表征。对于诗歌意象的真正阐释,往往是对历史上、现实中或恒定不变的“人的存在”的多维阐释,因此,欲探究“化石”意象的共性寓意,还要到历史的大江大河中去回溯。
卞之琳的《鱼化石》创作于1936 年,那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正值五四时期之后,中西思潮多元碰撞交汇。诗人的创作环境处于“承前启后”的新时期,时代色彩在卞之琳“融古化欧,承上启下”的创作中得以彰显。加之,1936 年是诗人与其心爱之人张充和相识的第四个年头,面对“云树之思”的情愫,诗人在诗中又植入了“幽怨、缠绵”的爱情基调。时代背景与个人命运交织,为卞之琳书写“新”篇章提供了双向意指空间。艾青的《鱼化石》创作于新时期伊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文坛迎来了新的春天,一些作家带着对历史的伤痕与反思开始书写文学的新篇章。艾青便是其中之一,其诗作《鱼化石》的诞生也标志着新生命的复归,诗歌所焕发出的生机与朝气,丝毫未显示出此诗乃诗人耳顺之作。因而,《鱼化石》的诞生既是对以往的追思,也是“新”艾青的“出生证明”,开启了诗人创作的“新”阶段。导夫的《释放哲学的化石》创作于1984 年,这是一首有关“史”的诗篇。跨过两千余年的深沟巨壑来到新世纪的诗人,其诗作寄托了诗人对大国文明的回首与溯源,对大国沧桑峥嵘的深情凝视,让化石承载了从古至今的历史流动,厚重的思绪化作“哲学的化石”在诗歌中得以释放、迸发,诗人的哲思是对历史的祭奠。
回到当时的“现实存在”,三首诗作兼具“新语境”的共性特征,“化石”意象将过去的岁月封存于固态意象之中予以告别,诗人们怀揣着“爱情、生命、历史”迈入了人生新纪元。无论是考察意象的现实在场,还是回到历史潮流之中,不同的诗人之所以会选择同一意象创作不同的诗作,意象与表意之间必然具有相关联的共性寓意,这是诗人创作的心理机制之一。探究基于共性寓意之下所彰显的不同意义所指,更有助于我们解开每首诗背后的“时代符码”,汲取诗人的智慧结晶,探寻诗人的精神指向。
二 “象同意异”:禁锢、不息、恢宏
哲学家维科曾言:因为能凭想象来创造,他们就叫诗人。诗人在希腊文里就是创造者。诗人的思维纵横古今、超越时空。在意象的表达中,“象异意同”是诗人共通的诗意呈现。异质时空的诗人将趋同的情感用不同的事物(符号)代指,却能达到相同的情感抒发效果。意象的“象同意异”,同样是诗人的“诗性”宣发。当“月亮”不再是“思乡”、“长亭”不再是“送别”、“梧桐”不再是“悲戚”,便跳脱出某一意象的固化思维,超越某一原型的集体无意识,标志着某一特定意象符号的诗意转向。“情性”与“理性”共筑诗人的“诗性”。诗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创造者,是因为他们具有“诗性”。雅各布森谈及“诗性”时说道,“‘诗性首先存在于某种自觉的内在关系的语言之内’,语言的诗性功能‘提高符号的可感性’,吸引人注意符号的物质性,使人不仅仅把它作为交际的筹码来使用。在‘诗性’语言中,符号与它的语言对象脱了节:符号与所指者的正常关系被打乱了,这样就使符号作为自身有价值的对象而获得了某种独立性”[3]。雅氏意在告知我们,意象本身与所要表达的情感往往不需要有直接的关联性,它既要发挥语言的能指功能,指向符号的物质特性,同时也要跳脱对象的束缚,具有某种独立性。作为接受主体的人时常受到“格式塔”心理的影响,使存在于意识或潜意识之中的先在经验与接受符号相互交织,自觉发挥想象,本能地填补诗人诗作中的留白。若仅仅将符号作为一种交流的筹码,那“化石”便只是化石,名称只包含其“物质特性”,意象所指趋于统一。因此,除了辨明三位诗人对于“化石”意象的共性寓意外,还必须充分考察独立于固化内涵之外的符号异质意义。
(一)“化石”之禁锢
卞之琳在《鱼化石》中以一个女子的口吻诉说着他对于爱情的感悟与认知。“化石”一改“厚重”的能指,成为卞之琳爱的诗篇。“化石”本与“爱情”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卞之琳的笔下却十分融洽。二者虽互不关联,但诗人赋予其逻辑的勾连,使意象产生“陌生化”的诗意效果。
“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我往往溶于水的线条”[4],“我”只为悦己者容,溶于水后就可为你而肆意变形,为的是打动你、包容你。“我”可以不惜溶于水中,易去尊严,化作可以包裹你的线条。“我”要化作你的轮廓来迎合你的怀抱,这是一位男性诗人近乎放逐尊严的卑微,是他对爱情的真挚书写。“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5],镜子中的你与镜子外的我形影不离,相互映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其实一切都是镜像,是我的臆想。鱼本是鱼,石本是石,当你我都远了,没有了交集,鱼和石便成了鱼化石,失去了它们原来的模样。鱼和石虽在一起再不会分离,但只是被禁锢而从未有过交融。卞之琳的爱意似涓水细流、星火微光,从悦己者容到易去尊严,最终时光流逝冲刷了爱意,只留下了一块记忆。时空的距离成为化石的“禁锢”,“化石”虽让两人在物理时空中得以永存,精神上却依旧为“幻象”。当时间不断流逝,“你我都远了”,“你”亦非曾经的“你”,“我”亦非曾经的“我”,“你我”成了“鱼化石”,曾经热诚的爱意终究凝结为化石而成为回忆。诗人以爱情感悟再现老庄中“生生之谓易”的哲思:“爱”在历经卑微与冷漠之后不是永恒不变,即使我曾愿为你化为“线条”任意变形,也不曾使我走进你的视野。如今“你我都远了”,那份情谊早已改变,剩下的也不过是一块“化石”般的回忆。现实亦如此,没有亘古不变的事物,生生不息、革故鼎新才是万物发展的本源。如同“鱼化石”一般,不变的是被“禁锢”封存的记忆,而“其他”早已物是人非。
诗歌通过意象的陌生化,让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并知觉其余味之外,“程式”的陌生也赋予了诗歌丰富的外延意蕴。在《鱼化石后记》中,作者进一步诠释了这短短四行诗歌的智性表达。“我要有你的怀抱的形状,我往往溶于水的线条”,诗人巧妙地运用了中西经典——“女为悦己者容”以及法国诗人艾吕雅的诗句“她有我的手掌的形状,她有我的眸子的颜色”。“我”可以变成你想要的任意形状,“我”可以为了你扭曲我本来的线条,“我”要填满你的双眸,“我”要占据你整个世界。“你真像镜子一样的爱我呢”,作者在《鱼化石后记》中解释道:“我想起马拉美的‘镜子’,……是《冬天的颤抖》里的‘你那面威尼斯镜子’,那是‘深得像一泓冷冷的清泉,围着翼兽拱抱、金漆剥落的边岸;里头映着什么呢?啊,我相信,一定不止一个女人在这一片止水里洗过她美的罪孽了;也许我还可以看见一个赤裸裸的幻象呢,如果多看一会儿。’”[6],诗人在“镜子”原有“物质特性”之上又以“幻象”给予解释。“你我都远了乃有了鱼化石”正如前文所指,蕴含着“生生之谓易”的哲学思考,情与理的生存之道是“阴阳转易、生生不息”的不断超越、演化的过程。作者从情爱到万物生发的思考,使诗作在“诗性”的隽语注释下变得“智性”多元。
(二)化石之不息
在艾青的《鱼化石》中,蕴含的是生生不息、昂扬向上的生命精神。“动作多么活泼,精力多么旺盛,在浪花里跳跃,在大海里浮沉”[7],鱼儿是生命的幻化,无畏冰雪风浪,活泼灵动地穿梭于汪洋之中。这“跳跃、奔腾”的鱼儿亦可视作诗人“归来”后的喜悦与饱含活力的创作动机,他渴望奔腾、渴望自由,犹如新生——肆意地啼哭,欲让世界听到他“归来”的声音。
“不幸遇到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地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灰尘;过了多少亿年,地质勘探队员,在岩层里发现你,依然栩栩如生”[8],偶然的不幸,让那自由的鱼儿成了化石,却依然掩不住它那由内向外透露出的生命的不息与倔强。它的鳞和鳍是完整的,直到化为石头的那一刻,它还是对未来满怀憧憬,享受奋斗带给它的生命快感。一方面,鱼的遭遇恰好与诗人自身的经历相契合,彰显诗人假借“鱼化石”的诗意象征:祖国大地红日初升之际,“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艾青却被划为“右派”,本该迎着朝阳投入祖国建设的诗人却遭到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桎梏,如同鱼儿遇到了意外而失去自由。许久之后,浩劫不再,诗人虽饱受厄运洗礼,但光明的到来却让艾青仍旧如同当年一般朝气蓬勃、“栩栩如生”。另一方面,“鱼化石‘是沉默的,连叹息也没有,鳞鳍都完整,却不能动弹’,则暗示了受难者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窒息感。一片鱼化石凝聚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创伤”[9]。
“你绝对的静止,对外界毫无反应,看不见天和水,听不见浪花的声音。凝视着一片化石,傻瓜也得到教训: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净”[10]。你的肉体虽静止,但灵魂仍然在运动,形灭而神存。这不幸的偶然,让你丧失了生命,让你成了鱼化石。艾青给予诗作无限的智性观照: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当你的肉体静止了,意味着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但当死亡还没有到来,就意味着斗争还没有结束,你要继续遨游,你要继续发挥你的生命价值。偶然不可抗拒,但命运可以自我书写。如果你做到在最后一刻仍“栩栩如生”,那你的生命将永远不会静止。
艾青的《鱼化石》后来被收录于1980 年出版的《归来的歌》,诗集名称便可视为诗人对其新生的宣言,大多研究者都将其定义为艾青后期创作的代表作。诗人对“化石”意象的运用不仅限于个体自身的“高歌”“独白”,而且将其赋予“类”的言说。成为化石的“鱼儿”依旧“栩栩如生”,禁锢的最后一刻也在奔腾、斗争。这不只是诗人复出后的独白,更是在黑暗中不断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们的高歌。艾青的“化石”是对生与死的追问,运动与静止、生存与死亡、斗争与怯懦,共同建构了诗人“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精神旨归。诗人置身于历史中的书写,诗意地阐释“道法”与“辩证法”的内在联系:万物皆处于发展前进之中,唯有与黑暗斗争、与生命抗衡,才能自由地奔腾于波涛汹涌的历史浪潮之中。
(三)化石之恢宏
导夫在《释放哲学的化石》中作为历史的旁观者,介乎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视角之间,向我们道出了历史与不朽的究竟。历史厚重恢宏难以言表,诗人开篇便发出“该怎样/该怎样向你叙述呢”的疑问,它是“从黎明到黄昏又从黄昏到黎明”,昼夜交替、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自然哲思的呼之欲出。“它”经历过从黎明到黄昏时的光辉四溢,再从黄昏到黎明时的黑暗笼罩中砥砺前行。是“历史的残流从贝化石上悲惨地淌过/梦境/浑浊/星云/辉煌/多少飘零的季节,多少幻灭的奇迹”。“贝化石”见证岁月的风蚀,呼号疾苦与悲痛,有幻想、现实、浩瀚、辉煌,抵不过四季的飘零、时光的侵蚀。诗人的情感指向并非为一系列奇迹幻灭奏响挽歌,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崇敬、对反抗、不屈精神的讴歌,颇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的恢宏意境,却少了“独怆然而涕下”的苦闷消极之情。历史早已告别的“原始舞蹈、古生代的三叶虫、侏罗纪的鸟儿、白垩纪的河流”,你——化石,是“无数时代生命结构的基因”,是“闪灭不绝的烽火”,是“在沉积的意识层中打捞沉船”[11]。生命的不屈跃然纸上,导夫用“化石”观照历史,寻找历史的答案,在“化石”的引导下,让人们见证了作者时间与空间的意识流动,历史是在“化石”上放映的一场无声电影,无声却不静止,低调却不掩恢宏之气。
历史是不朽的,但“——什么/什么是不朽呢”,诗人二次发问。“残损的身躯覆盖着残损的黄土/躺在洪荒退却后野性的古陆/以/熟识过去的触觉/听人世永恒的律动”,历史虽然在岁月的侵蚀下残损,失去原始野性,却仍不褪色,聆听着世间万物的声音。不朽起自“长江黄河”,“长江黄河”孕育着神秘古老的东方文明,这是我们的历史,因此不朽源自历史。我且“只有我和我血色澎湃的同类长江黄河般地活着”,“我”不会也不愿被历史陨没,“我”有“我”的血色与激情,“我”就是不朽,“我”就是历史。“体觉/历史无情的凝聚/与最庄严的动响”[12],原来,“我”见证历史,“我”创造历史,“不朽”释放着哲学的化石,化石蕴藏着历史的“不朽”。诗人用全知的视角,体味“化石”所经历的一切,俯瞰芸芸众生,表达了诗人对“天下”的真切之忧,这是为恢宏历史谱曲,为历史与不朽做注。
纵观全诗,尽管意象与形式的陌生使得阅读有时存在“隔膜”,但诗中潜藏的逻辑暗线与时间的线性叙事纵横交错,勾勒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逻辑链条暗合于陌生意象之中,清晰与朦胧相撞,产生了似是而非的落差之美,彰显诗人宏大的历史观。尽管句子的承接、意象的铺排散发、跳跃,但“化石”这一中心意象,将散落在读者脑海中的零碎画面勾描成画。化石的“陌生化”效果正是借助接受主体强大的想象空间,让一首浩然悲壮的历史史诗在人们心中吟唱,比事无巨细陈述一切的艺术效果更为立体,加之接受主体不同的智力机能与期待视野,会让诗歌鉴赏有“远近高低各不同”之兴味。
被释放的化石,是诗人回到历史的哲学符号,是在探寻个体乃至历史时间的存在,正如诗中阐释历史是不朽的。欲寻求自身的存在,回到历史,在存在中寻求存在。历史不可忽视,如同加达默尔所认同的,“我们无法装作从一个历史之外的永恒立场出发拥有了‘终极’真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走在途中。我们的理解永远是历史地决定的,诠释的过程永无止境”[13]。谁都无法逃离历史存在之中,我们的诠释也势必要以历史为旨归,“由你释放哲学的化石/体觉/历史无情的凝聚/与最庄严的动响”。谁来体觉历史?是“你”,而“你”是存在于历史长河中的“我们”。诗人用哲学的化石“启智”:你我的存在,见证于历史的存在之中。
三 “象同意异”之“诗意”启示
如上文所述,同一意象符号,在不同的时代语境在场之下,产生“意异”之效,体现了人类语言艺术的多彩魅力。欲揭示“象同意异”的内在原理,要回到索绪尔的语言学,他将语言功能划分为“能指”与“所指”。索绪尔认为,某个特定事物的能指与所指不具有必然联系,而是约定俗成。人们将“化石”一词用语音符号加以注释,它的发音便是其能指所在。“化石”的自然属性和不同的“诗性”概念是人类赋予的概念所指。就语音而言,“化石”的语音表征在世界各地五花八门,人们通常对其自然属性“不言而喻”。诗人通过艺术加工,打破所指含义的固化意义,将其变成诗歌的符号为他/她所用,符合符号的“任意性原理”,这也是意象性陌生化效果的主要因由。
诗人对“陌生效果”的营造同样是艺术加工,“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奇异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14]。诗人善于察觉读者与具象之间的空白地带,通过陌生意象的晦涩表现来延长读者对作品的审美感知,将意象加工为一种“可观可见而非可认可知”之物,加深读者的心理体验,获得超越内容之外的形式延伸之美。此外,陌生化效果之所以可以被营造,是因为诗或可洞见人的“存在之地”,这一点在海德格尔那里已经得到论证:“在诗歌中,我们所说的东西较不重要。关键是对一种特别的情绪的传达,作为对通向存在的某种在的方式的揭示。”“诗人和诗性哲学家们是解释人的被遮蔽本质的先锋”“他(指海德格尔)试图诗意地传达根本的东西。他对现代性及其根源的批判,是经由诗艺而进行的。”诗中所表现的陌生与“似是而非”,正是人们缺失的“存在”,也是我们“根本的东西”。较之其他学科语言,诗语能更好地触碰现实世界中“暧昧不明”的地带。“化石”意象本未触及三位诗人指涉的哲思向度,但由于“化石”符号意义缺位,激发了新的所指意义在场,通过诗歌语言的传递便可直指诗人的思维高空。“根本的东西是靠我们很近,但我们却对之感到陌生”“它就是‘在者之在’,一种对于现代人来说依然是谜一样的东西。我们必须学会倾听语言,这样,根本的东西就会对我们言说。语言是一种敞开,特别是诗性语言,它对难以传达的东西特别敏感”[15]。
兼察三家之“化石”意象,卞之琳有“朦胧”“暧昧”之味,艾青含“硬朗”“朴实”之感,导夫则兼具“抽象与恢宏”。同为“化石”意象,三者表意都似“隔”有一层薄纱:艾青之“鱼化石”如同盖在蒸锅上的屉布,一揭盖,“面香”便透过屉布扑鼻而来,直击食客味蕾,硬朗的诗风让其尽显杜甫般“沉郁顿挫”。卞之琳之“鱼化石”犹如遮蔽正午骄阳的窗帘,将其拉上便可将万丈光辉隔于帘外,一旦打开,肆意的阳光便照亮屋内漆黑的世界,一切皆可洞明,其表现艺术与西方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艾略特等变形、抽象等富有哲思的象征诗歌同气共类。导夫之“哲学化石”兼收二家之长,犹如淘金时纱棉滤掉沙砾后留下的碎金,在意象与形式的陌生效果下,融合“汪洋恣肆的想象”与“气势磅礴的现实”,彰显历史的恢宏。三家“化石”各有所表、各有所思,尽显诗意魅力与“象同意异”之趣。通过考察三首诗作中同一意象的“异意”所指,三位诗人各具特色的价值取向与艺术形式跃然于纸,诗人艺术加工后“化腐朽为神奇”的独特魅力在名贸实易中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