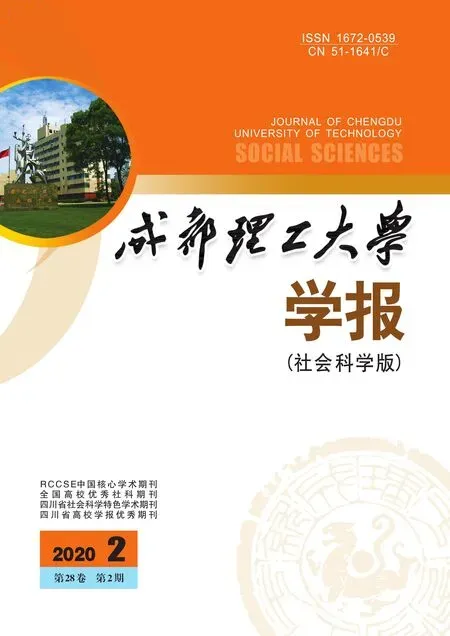近十年来国内马克思自然观研究综述
张雪敏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长春 130024)
步入21世纪,我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日渐凸显的生态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内学者开始重新研读马克思的自然观,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挖掘和现实分析,为解决严峻的生态问题寻找良策。系统而全面地梳理近十年来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并反思其中的不足,对于当下我国解决生态难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一、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与发展
对于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现有的著作和论文几乎都是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大致将马克思自然观的形成与发展归纳为萌芽、形成和完善三大时期,如解保军就从这三大阶段出发,指出马克思自然观萌芽时期的代表作《博士论文》,其中对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探讨表征着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初步认识;形成时期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能动作用、社会历史性等诸多方面解读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自然观形成的标志;完善时期的著作有《资本论》和《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予以深刻的生态批判,“完善了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史观视角”[1]。部分学者如董强将为后人所熟知的《哲学的贫困》和《哥达纲领批判》也列入完善阶段,认为马克思自然观的内涵在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新的拓展。
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在批判和超越西方传统自然观的基础上产生的新自然观,从根本上实现了对西方传统自然观的革命性变革。邓喜道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自然观所实现的对传统自然观的三大变革,一是以实践为切入点,它批判了本体论自然观严重忽视自然的社会属性,明确提出“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真正理解自然界的本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2],实现了从本体论自然观到实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变革;二是在批判近代机械自然观将自然孤立化和机械化的基础上,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及社会的辩证统一,实现了从机械自然观到辩证自然观的变革;三是批判了将自然看作上帝所造的创世说和由某种因素所构成的永恒不变的要素论,主张自然是运动的、变化的和生成的且与人紧密联系的人化自然,进而实现了从构成自然观到生成自然观的变革。
二、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论特质
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有其鲜明的理论特质。大致观点如下:
(一)实践性
刘希刚认为,“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最基本的特点”[3],正是劳动实践的“中介”促使自然资源成为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和基础,推动着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不断转换。杨勇兵认为,通过实践活动,人与自然才完成了本质上的统一,因而马克思的“‘人化的自然’在本质上是实践的”[4]。此外,陈墀成、蔡虎堂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外部的自然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立场”[5],实践表征着马克思自然观的全新属性。
(二)辩证性
邓喜道指出,辩证性是马克思自然观的又一主要特征。马克思在批判传统自然观的形而上学性的同时,也承继了旧自然观的辩证法思想,并将这种辩证法彻底贯穿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最终确立了“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6]。这种辩证性体现在三方面:自然人化的内容和形式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人类历史随着自然的发展而发展,应该以辩证的眼光来考察自然与历史的统一;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形式随着劳动的发展而发展。
(三)现实性
杨卫军认为,进入马克思视阈中的自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从来都不是脱离人的抽象自然。将人与自然割裂开来谈论,人与自然皆无现实性可言。贺来、冯珊认为,马克思所强调的自然不是“无人身的自在自然, 而是人类实践活动参与其中的‘人化自然’”[7]。邓喜道也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史与自然史、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多维度阐释了马克思自然观的现实性。
(四)批判性
方锡良认为,马克思是在批判西方传统自然观的过程中形成他的自然观,这种批判的研究方法自然使得他的自然观充满了批判性,通过批判以往自然观对人、自然及其关系作出的抽象解读,马克思的自然观立足于实践活动实现对人与自然的现实性统一关系的深刻理解。王雨辰认为,马克思自然观的批判性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乌倍河被严重污染和自然资源日益枯竭”[8],还造成大气污染和城市垃圾集聚,使工人的生活状况极度恶化。
(五)系统性
王丹认为,传统自然观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关系,马克思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人与自然及其社会视为有机统一体,这凸显出马克思自然观的系统性。张赛芳强调,“正是由于人的劳动和人所发展的工业使人、自然、社会成为一个整体”[9]。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不断提升认识、改造自然的能力,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益紧密,工业水平的提高使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变换正常持久地进行。由此,人、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以割裂,最终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六)社会历史性和过程性
杨卫军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体现了显著的社会历史性和过程性,这种“过程思想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实践)中”[10]。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阈中的自然是一种生成性存在,整个世界的发展表现为历史性过程,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周光迅、武群堂认为,马克思将人与自然及其关系看作人类历史的发展产物,人与自然在人类社会实践过程中彼此制约,内在统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表现形式随着社会历史形态的变迁而变迁。
(七)生态思维特征
王丹将马克思自然观的主要特征归结为生态思维特征,并指出这种思维是“从辩证思维的维度,对人与自身生存发展于其中的自然界,尤其是对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自觉审视和思考,并以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与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的思维方式”[11],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因诠释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而具有生态意蕴。自然在马克思那里摆脱了被工具化的宿命,真正被视为“人的无机身体”,作为大自然中一员的人类也自觉扛起了尊重和爱护自然的责任。
三、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
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存在如西方学者所言的生态思想的“空场”,马克思自然观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解决路径的深入剖析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态思想,主要内容如下。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理论主题。陶火生从唯物史观立场出发,强调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包括人的自然存在和自然的人的存在的有机统一,这种辩证统一的实现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人的生产性实践”[12]。也就是说,自然和人在实践活动中实现辩证统一。在生产实践中,自然不断被纳入人的活动范围内,人将自身的情感、才智、本质力量作用于自然,自在自然逐渐转变为人化自然;同时,人为了达到预期结果,以物的尺度规范自身的行为,将自然规律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实现了人的自然化。最终,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于实践活动中统一起来了。
(二)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
在陶火生、王丹看来,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二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是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它把自然的人化方向和人的自然化方向、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在生产力的层面上统一了起来,深化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构成社会的现实生产力,二者交互作用、彼此制约。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它为人类提供直接的生存资料,并创造出人类社会再生产的对象和资料。而社会生产力对自然生产力具有促进和引导作用,只有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自然界中蕴含的丰富的潜能才得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
现有研究都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深入剖析,将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生态危机爆发的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张进蒙认为,以实现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异化劳动。在这种异化劳动中,自然不再是人的“无机身体”,也不再是人确证和表现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只是供人类满足自己无止尽欲望的工具和手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沦为赤裸裸的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对自然的肆意掠夺使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被打破,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全球性生态危机随之爆发。
(四)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解决路径
王雨辰认为,马克思强调了生态问题的解决应通过对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变革,步入共产主义社会,方可真正化解人与人及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及其社会的和谐发展。陈雪峰认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是化解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13]除此之外,杜向民等还认为科学技术也是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要解决生态问题就必须合理的使用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促进科学技术的应用所产生出来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四、马克思自然观的当代价值
对于马克思自然观的价值,学术界主要从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两个层面进行探讨。
(一)理论价值
首先,马克思的自然观以实践为理论基石,这从根本上推动和实现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转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和创新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如张进蒙强调,以当代的实践为契机,从时代问题出发,在现实的历史语境中深入解读马克思的自然观,将其中“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转化为一种显性的理论体系,并将之转化为指导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科学图景,就成为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途径”[14]。
其次,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为当代生态哲学的建构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薛桂波、萧玲认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历史维度批判,以及由于现实研究的需要而创立的一般理论原则给建构当代生态哲学启示了理论原则的现实性要求”[15]。生态危机已然成为当今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之一,当代生态哲学的构建必须以现实的生态环境问题为理论关注点和立足点。
最后,马克思的自然观对于我们探讨当代西方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具有重要的启示。当代西方学界也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对人与自然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与论述,面对这些观点,我们既不可全盘接受亦不能完全否定,而应该坚持马克思自然观的基本理论视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实践价值
关于实践意义方面,已有成果大多将其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紧密关联起来。
1.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科学发展观
薛桂波、萧玲于认为,科学发展观以马克思的自然观为理论资源,“与马克思的自然观在价值论维度上实现了高度契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15]。二者的契合表现为四个方面:都是以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为价值始点、以人与自然及其社会的整体和谐为价值关系、以实践活动为价值中介,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
李勇强、肖玲、孙道进强调,科学发展观从其根本上来看,与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一脉相承的关系。科学发展观致力于推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可持续性发展,它所表现出的鲜明的价值追求与马克思自然观力求实现人与自然及其社会的和谐统一的内在旨趣高度一致,因而可以说,它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多维意蕴的创新和发展”[16]。
唐晓勇指出,现时代我们党所倡导和竭力践行的科学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17],丰富和拓宽了它的理论内涵和思想外延,日益实现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升华。马克思的思想对于我们破解当前的生态困境,缓和人与人以及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迈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大道具有重大价值。
2.马克思的自然观与和谐社会构建
黄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它有助于我们精准认识和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当代人对于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应当以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自觉遵循为底线。
高锐以马克思对自然特性和实践活动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相关论述为理论基点,较为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的自然观对于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导意义,最终指出构建和谐社会首先应在人与自然之间“确立主客一体化的人与自然新型关系”[18],将社会的发展与生态平衡的保护结合起来,同时还应在实践活动中不断追求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徐民华、刘希刚认为,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思想对于当代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对于生态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19]。这主要体现为:和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的统一性;“两大和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自然—社会关系和谐的理想状态;社会制度是人与自然及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人类是实现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主体力量。
3.马克思的自然观与生态文明建设
倪志安、王培培认为,马克思自然观的重要理论启示在于,其所揭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可协调性、人的生存方式等启发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竭力“改变现存中人的社会和人自身的、习以为常的生存发展方式”[20],以人的自身的和谐关系来引导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它的实践启迪在于有利于统筹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从而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
樊小贤明确指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在社会历史中相互依存的观点体现出一定的深刻性,“社会现实”是马克思自然观的巨大贡献,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指南。它启发我们“生态文明是一个持久的社会历史过程”[21],须切中当前的社会现实境况,从本国的真实国情出发采取相应的举措。
赵云营、牟海侠强调,我们应“领略马克思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22],应以马克思的自然观来引导我国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方向。它所深刻揭示的将自然当作人的身体来对待和解决自然异化状况的实践路径,启发我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应重视生态价值,维护生态环境的安全,积极开展各项环保工作。
周海生、刘秀荣、刘希刚一致将马克思的自然观归结为人化自然观,并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对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而言依然具有重要价值。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内涵,系统而深刻地阐发出人与自然之间最为真实的关系,因而成为“指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理论”[23],对解决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李刚认为,要实现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战略和新目标,“一定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导下直面那些深层次的、真正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哲学问题”[24]。他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对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启示主要有三点:建设生态文明应立足于我国的社会现实;生态文明建设应通过实践的变革来实现;保持限制资本与超越资本的内在的张力,在动态平衡中促进生态文明的发展。
总体而言,学者们从不同的维度分别展开对马克思自然观的重大意义的深入阐释和挖掘,强调了马克思的自然观在现时代的重要作用,它对于我国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乃至推进生态文明的全面建设,始终有着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
五、对于研究中不足的几点思考
通过全面、系统地梳理已有研究成果不难发现,随着近年来我国环境问题的凸显,马克思的自然观已然成为国内学术界研读的一大热点,且持续升温,研究内容逐步深入、研究视野愈益开阔,总体上成果丰硕。但与此同时,现有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明显缺乏整体性、系统性,存在着诸多不足。
首先,对于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论特质,现有成果大都只是从马克思所实现的对西方传统自然观的变革这一维度来凸显马克思自然观的实践性、辩证性、现实性、批判性等理论特质,而相对忽视了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支有影响力的队伍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学解读,分析其理论贡献及局限性,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维度的比较中彰显马克思自然观的当代性和科学性,这一相关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其次,这些成果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意蕴的探讨,大多仅侧重于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去阐释,而疏忽了自然、人和社会实质上构成有机体而从整体上予以考察,遮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关系的有机统一,对这点的相关论述仅仅局限于少见的几部著作和硕士论文当中,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亟需加强。
最后,在对马克思自然观的实践价值的阐发上,学者们虽然从诸多视角与维度进行了大量展开,但是整体研究还是缺乏一定的深度,对于建设生态文明的相关分析及对策,没能立足于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进行阐述。科学实践观是马克思自然观的基石,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中,必须始终以科学实践观来指导我们对自然的改造活动,最大限度地调节和引导实践活动的合理性、科学性,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进而推动和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