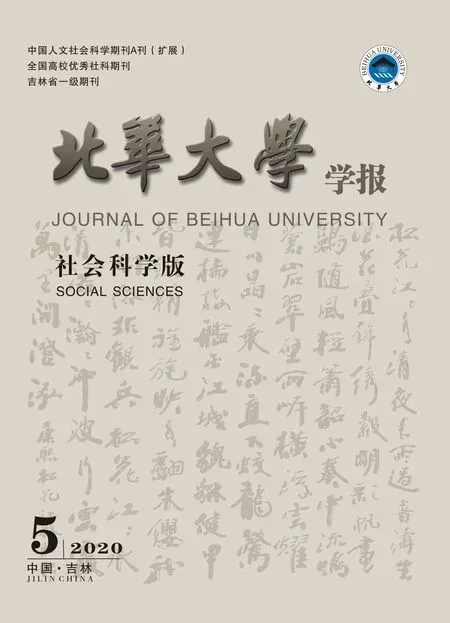创伤与记忆:日军侵华暴行公共记忆的重构
宫健泽
引 言
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两国在前30年间相互关系平稳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尽管其间出现过各种问题,但总体上中日友好不断深入人心,合作关系不断扩大,民间友好不断加深,双方关系密切前行。
在2000年前后,中日由于历史问题导致政治关系出现倒退,影响双方政治互信的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问题,诸如中日钓鱼岛问题,日本否定侵略的教科书事件,日本政要参拜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靖国神社事件,以及否定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历史等。现实中日关系中存在的其他分歧与问题,如安全保障存疑,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步提升,日本国内普遍产生一种恐惧心理,这一方面由其岛国天然危机感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其企图领导亚洲的传统军国主义观念作祟。
经济合作方面的东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难产。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是个呼吁多年的倡议,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实现,虽然中韩冲破层层阻碍建立双边的FTA,但是距离当初中日韩自贸区的设想相去甚远。要想实现东亚中日韩FTA任重而道远,其中中日关系的和平友好至关重要。
中日钓鱼岛争端后,在国民好感度民调方面的中日两国国民彼此好感度下降,由于受中日关系政治环境和国际日美同盟意识形态的影响,日本民众对中国好感度下降。因此,加强中日民间交流特别是青年人对彼此的了解非常必要。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也是横亘在中日之间的现实问题,日本的态度决定中日关系改善的程度。
一、不能遗忘的创伤:历史上的日军侵华暴行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随着国力逐渐增强,开始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由于地缘因素,日本周边国家朝鲜、中国成为日本向外扩张的首要目标。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积贫积弱的清政府以完败日本而结束战争,战后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赔偿日本白银两亿两,相当于当时每个中国人需要赔付一两白银。在随后的中日关系中,日本通过1904年的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占有俄国在中国的租界,将日本势力进一步渗透到中国的内陆。1926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提交奏折,指出:“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先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有名的“田中奏折”,也成为日本开始向外侵略的指导性文件。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沈阳,进而侵占整个东北。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迅速侵占整个华北,进攻上海,占领南京。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城后,实施了骇人听闻的屠杀中国士兵和平民的暴行。根据战后东京审判和南京审判结论,日本在南京实施为期6周的集中屠杀,加上后期陆续的零星屠杀,总共屠杀南京市内军民30万人以上,这是铁的事实,不容抵赖和否认。东京审判法庭判定:“20万人以上……不包括抛尸长江、挖坑掩埋和以其他方式处理的尸体在内”的数字,南京审判法庭认定“集体屠杀28案,19万人,零星屠杀858案,15万多人,死难人数达30多万”[1]的数字,日本南京大屠杀人数已有历史结论和法理定论。
南京大屠杀惨案只是近代以来日本侵华所制造的众多屠杀惨案之一,其他还有许多屠杀惨案,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有,旅顺大屠杀、平顶山惨案、上海屠杀等。其中旅顺大屠杀发生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自旅顺大屠杀发生后,尽管当时的日本政府曾一度试图掩盖事实,但国内外有良知的媒体记者、学者没有停止过对真相的探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美国《纽约世界报》的随军记者克里曼的长篇纪实报道,真实还原了当时旅顺被攻陷后日军的暴行;英国人詹姆斯·艾伦在其所著的《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一书中,以目击者的身份,细节呈现了日军在旅顺虐杀中国人的情景;民国学者孙宝田于1935年在日本殖民下的旅顺冒死查证,终得汇编《日寇旅顺屠杀两万人》一文;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也对日军在旅顺的屠杀做了详尽的记述。平顶山惨案也称为抚顺大屠杀,发生在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期间犯下的又一重大罪行。与旅顺大屠杀类似,日本侵略者在事后采取了一贯的毁尸灭迹的龌龊行径,企图完全销毁暴行罪证。平顶山惨案史料的支撑也主要是基于美国记者爱德华·威廉·怀特“抢救性”的实地调查与日本投降后战犯的供词及目击者的证言等。
中日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惨案实际状况的考证、惨案规模以及对幸存者进行的口述调查。如佟达的《平顶山惨案》、周学良的《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故事》以大量史料为依托,全面披露了平顶山惨案发生的全过程,成为研究该惨案的重要参考。日军在上海制造的屠杀惨案,主要表现在屠杀平民和战俘,屠杀平民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区和郊县,据统计,“自战争开始,至10月21日,在公共租界内为日方流弹击中死伤人数即高达5 000余人,其中死者计2 057人,伤者2 955人。至1937年底,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的界内华人死亡人数已高达35 171人。在上海郊县的屠杀就更加血腥和肆无忌惮,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极端残忍和残暴性。仅宝山、金山、奉贤、南汇、松江、崇明等上海郊县的部分暴行统计,侵华日军就屠杀无辜百姓15 488人。”[2]
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完整的户籍法,特别是兵员之中流浪者很多,如果将俘虏杀害,同释放到其他地方一样,在世界舆论上不会出现问题。”(1)此处引文参见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内部资料《对中国军战斗法之研究》(日本陆军步兵学校,1933年第32页)。为了实施恐怖威慑并消灭中国抵抗力量,日军在上海战场上,更是明目张胆地野蛮屠杀中国俘虏,据中方资料记载:“1937年9月16日,日本上海派遣军一部从上海罗店撤退时,将被抓来的十几名中国伤兵钉在墙壁上,用刺刀一个个开了膛,还割下伤员腿上的肉喂军犬。”[3]
以上三次大屠杀与南京大屠杀相比,无论在规模上还是人数上都无法相提并论,但是这些屠杀反映出日本侵略本质是具有同等效力的,正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所言:这些惨案,无论说3千人,3万人,还是30万人,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每一个惨案都是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的罪行。而我们开展此项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要更好地追思过去,关照当下,面向未来。
对于日本侵华期间所制造的屠杀惨案、屠杀平民和战俘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种战争犯罪行为超出正常人类所能想像的认知范畴。日军的行为与战后中国实施的遣返日本侨俘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在战争结束时,中国战区日本侨俘人数不少于300万人,国民党政府采取“以德报怨”的政策,与共产党合作,在美国的协助下,全力遣返日本侨俘,没有发生一起报复和屠杀行为,这在国际战争史上也属罕见。对于此举,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是感恩戴德。与此对比鲜明的是,处在苏联占领区域内的日本侨俘命运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被苏联拘留,进行劳动改造,许多人被疾病和虐待致死,终其一生没有返回日本。对此,日本一直耿耿于怀,曾经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为了表明日军也是受害者,多方搜集战时日军资料,并欲将这些资料申报为世界记忆遗产。于是日本欲将当时接收遣返日军侨俘的“舞鹤遣返纪念博物馆”资料整理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日本战败后,约有60万—80万军人和平民被拘留在苏联劳改营,“舞鹤遣返纪念博物馆”保存了1945—1956年有关拘留和遣返人员的详细记录。对日本此举,俄罗斯外交部批评了日本的这一做法。
对于日军屠杀中国的俘虏和平民,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也有指出:“被捕的中国人,其中许多人都被拷问、屠杀,编进劳动队中为日军做工,或者是被编入伪军中为傀儡政府服役。至于拒绝为这些伪军服务的俘虏,其中有些人就被送往日本,去缓解日本军需产业中劳动力的不足。在本州西北海岸的秋田收容所中,这样被送去的一群中国人,在981名中有418名就由于饥饿、拷打或忽视而死亡了。”(2)参见曹大臣《东京审判日本辩护证据研究——以南京大屠杀案为中心》(《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项目报告》第178页)。
对于日军所犯罪行,日本高层也有意地模糊掩盖,以“事变”为借口,否认对华“战争”,“按照日本军方的逻辑,日本没有向中国宣战,中日间的作战是‘事变’,不是‘战争’;因为不是‘战争’,作战抓捕的人员就不是‘战俘’,因此便进行了任意的杀戮、奴役、虐待。”[4]在中国战场上不设置俘虏收容所,不承认战俘的存在,被俘虏的中国士兵大多在战地就直接遭到了屠杀。
“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历史虽已远去,但其经验教训却历久弥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从旅顺到抚顺到上海再到南京,我们的先辈所遭遇过的,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苦难,更是人类文明史的黑暗与悲剧。然而战后以来,历届日本政府及其国内的右翼分子不仅不能积极承担战争罪责,反而一味积极策划“篡改”历史,不断给受害国人民的伤口上再添新伤。
二、缺失的共同记忆:战后日本对侵华暴行的忘却
近代中日关系,无论对中日两国关系,还是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关于近代历史的认识问题一直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二战后日本历史认识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一)教科书中的记忆缺失
关于日本教科书的历史认识与书写问题,内田树认为,“俄罗斯的教科书里也没有反省三国干涉还辽,美国的教科书里也没有关于朝鲜战争的内容。日本教科书里没有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也是正常的。”[5]41在2001 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 获得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对于日本国家军队对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无以计数的极端暴行极力加以淡化、否认或辩解。
对此,中国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卞修跃分析了2001 年4 月3 日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美化侵略战争、宣扬错误史观、掩饰日本国家侵略罪恶等反映战后日本国家错误历史认识的表述和企图,并从历史基础、思想基础、国际环境基础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对日本国家错误的历史认识的形成原因进行了研究。[6]184-207张宬对日本战后小学、初中、高中三阶段的历史教科书审定和修改前后的内容进行对比,从文本上分析政府意见对教科书修订带来的直接影响。[7]步平分析了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认为该书的历史观决定了日本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与掩盖。《新历史教科书》所反映的历史观即肯定战前日本的“国体论”,转移或淡化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和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这种历史观有可能把日本引向战争的道路。[8]
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记忆深处浮现突出的主题也随之变化。中国人民没有停止过对日本的批判。内田树认为:“一种做法是中国政府不刻意压制国民内心对日本的憎恨之情使之公然表现出来,另一种做法是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使中国民众不能表达对日本的憎恨之情。相比之下,中国人能够坦率地吐露对日本的真实感情是一种较妥善的处理方式。”[5]45-46教育实际上是由国家主导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系统地传授知识和技术规范的社会活动。从教育的实践中体现出其根本价值,包括普及先进的文化知识,宣传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推动经济增长,推动民族兴旺,促进人的发展,推动世界和平和人类发展。因此,“任何国家,不论其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国民教育都是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和任务,这一点在日本同样也不例外。教科书既是文化知识、思想观念的物质性载体,同时也是国家向其国民,尤其是下一代未来的国民传播知识、灌输思想观念、宣扬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根本媒介。”[6]200
安倍晋三出任首相之后,积极强化对教育领域的管控,主要表现在:“强化对教科书的管理,使之符合自己的历史观念。安倍政权认为,许多教科书还是建立在‘自虐史观’之上,存在着偏向的记述。为了清除这样的教科书,他着手大幅度修改教科书。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强化‘学习指导要领’的制定,提出了更加详细而具体的要求,而‘学习指导要领’是编写教科书的基本依据。如此一来,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学校教育之间就竖起了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9]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有外部与美国、中国等国的交往中的观念有关,认清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原因有利于形成对中日关系的正确认识及今后中日关系的走向的正确预测及应对。有学者指出:“不同于以往的美国纵容论、皇国史观论,从日本人的以退为进的罪己心理、既往不咎的放弃心理和唯强是从的实用主义心理,分析了日本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问题‘右倾化’的原因。”[10]“文化防卫论在完成其文化主张阐释的同时,担负起了为不同层面的历史认识做辩护的责任。蛰伏的日本文化论,构成日本历史认识史观的根部土壌。”[11]姜克实则从日本的基本政治立场、影响国民的无构造史观、战后的反省程度以及片面的被害意识等方面,分析日本人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12]
历史认识问题,并不是具体历史事实的问题,而是对历史深层认识问题,也就是某个历史事实在当下的外交关系中处于何种位置的问题。重要的不是过去的事实,而是现在对那段历史、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解释。日本把侵略中国正当化,以致现在日本的年轻人要么不知道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要么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要实现“东亚共荣”,帮中国实现“共存共荣”,甚至把“侵略”中国误认为是“进入”“进出”。
(二)日本和平纪念馆的记忆与忘却
战后出生的日本国民,现在成为日本社会的中坚,如何让他们形成二战中日本对周边国家造成的伤害的记忆,是当今中日双方史学家所面临的共同任务,如何构建公众共同的记忆,而不是忘却历史是我们面临的共同话题,也是双方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当今的日本,站在加害国民的立场投身反战和平运动的民间团体力量还比较薄弱,他们的声音还难以影响社会的主流。为此,全体国民的参与就显得十分重要。”[13]41内田树认为:“中国的近代史是列强侵略的历史,中国仅仅反抗日本的侵略是不公平的。最先敲开中国大门,对中国侵略的始作俑者是英国。19世纪末期,法国、德国、俄国、美国都随英国之后纷纷进入中国,对中国进行瓜分掠夺。日本是最后参加了‘瓜分战’,比起英国,日本的罪责要轻。”并狡辩到,“英国也没有对侵略中国进行道歉。在把香港占领100年之后归还中国时,英国首相、外相、女王也没有对中国道歉。”[5]39-40
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研究记忆主体,通常加害者容易忘记加害的事实,而被害者却保持被害的记忆。关于战争责任问题,受害国要求日本保持侵略战争造成人权侵害的记忆,而日本作为加害者却采取了忘却的态度。但是,日本对由“唯一原子弹爆炸国”的被害记忆而唤起的加害的事实却没有忘记。
正视历史,还原真相,是今后中日关系走向的重要影响因素。日本应承认真相,向国民展示、讲诉历史事实,并承担相应历史责任和进行赔偿,这才是日本今后应该走的路,也是中日国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
三、公共记忆的重构:中日关系的困境和希望
在历史事实中应该忘却什么,应该记忆什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将形成一个集体,并对集体价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国民国家,往往忘记在战争中杀害的敌人,而对于被杀害的本国军人却进行表彰、让人民永远铭记在心中。集体记忆的形成促进历史教育及国家性象征性纪念活动的进行。[14]163
“记忆共同体”的形成需要有共同的历史记忆,拥有共同的过去。不同时代的人形成的共同记忆也会有所差异。如年轻一代认为,“中日战争是我们出生之前的事情,我不清楚那些事”,年轻人选择了忘却。而上了年纪的人却说,“你们年轻人可能不懂,从前我们……”这些人只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记忆。“记忆共同体”形成之初,就有意识地忘却战争杀戮的场面、忘记阴暗部分,只记忆光荣事件、光明部分的历史。战争责任之所以被认识到,一方面是由于被暴力侵害国家的被害者提出诉求,还有一方面是国内战争被害者或其他有良知的文化人对“记忆共同体”形成挑战,也就是说“记忆共同体”受到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的相互作用。
(一)日本战争责任意识模糊化
对过去战争的责任,是否所有的日本人都应负此责任?未参加战争,未曾伤害或杀害中国人的日本人是否也应负战争责任?答案是肯定的。战时不反对战争,担当了战争责任的日本人都不能免除战争责任。
“(20世纪)90年代战争责任论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更加关注对于战争被害者如何进行补偿,对此法律专家、律师在理论上及实际赔偿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另外,赔偿组织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国际机构的关系,超越国界的NGO的联合都具有重要意义。”[14]197
从恢复性正义的视角来看,了解真相是达成和解,通向和平的必经之路。但单纯地了解真相并不够,还需要确定加害行为的具体责任,即加害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依据法律对其加害行为作出赔偿,这是恢复性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13]166
与战争本质论相比,人们更关心对因为战争而遭受严重灾难的人们的补偿问题,即开始从人权的角度对待具体的问题。并且,个人的补偿要求不是通过被害者所属的国家,而是直接向作为战争主体的日本政府要求补偿。因此,随着战后要求补偿的市民运动的发展,“战后补偿”一词也被广泛使用了起来。“战后补偿”不再是市民运动团体作为个人案件提出的法律问题,而是法院这一国家机构必须正式处理的问题,也就是对战争中的被害者个人如何进行补偿的问题。基于人权的考量,日本未经历战争的年轻一代也认为像“从军慰安妇”这样的暴力性奴役是严重的人权侵害,真是难以置信、法理不容。有许多年轻人参加了战后补偿运动。根据1993年《朝日新闻》的调查,有70%的20年代的年轻人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进行战后补偿。[14]200
(二)日本战争责任意识模糊化的缘由
日本右翼势力散布“战争不可避论”。一部分右翼势力宣扬日本资源缺乏,军事上进攻其他国家是为了生存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行为。“侵略”是“优胜劣汰”的必然选择。1995年岛村文相在就任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极力宣扬“战争不可避论”。声称战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战争是一种天灾,战时的一切灾难都是战争引起的不可避免的事情。日本声称,战争是悲剧。然而,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方是正义的,哪方是非正义的。它只是国与国之间差异摩擦的结果,当政治上解决不了时,作为最终手段只能发动战争。[15]甚至有日本人主张,只有战争,才能让散乱的国民意识得到统一,才能让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有压力得到自律,才能推动技术革新,也只有战争的威胁,能刺激一个国家避免死于安乐。这是极其严重的宣扬“战争正当论”的言论,对日本的历史认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日本在论及历史认识问题时的伎俩就是避重就轻,混淆历史事实,推托战争责任,认为战争时期和现代的年代没有关系,无需承担前辈们的战争责任。
(三)日本刻意强化被害意识
日本人在回顾1937—1945年的战争时,其回忆多是被害者意识。约有300万人参战,尤其是二战后期,日本本土66个城市遭受的美军大规模的轰炸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使日本人内心浓厚的被害意识到达顶点。几十年来,生存下来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深深刻下了受苦和破坏的记忆。著名的广岛、长崎和平纪念资料馆所展示的原子弹爆炸带来的恐怖后果,令人印象深刻。1999年在东京开馆的高层建筑昭和馆,主要展示了战时和战后使用的日用工艺品和生活状况。[16]
被害意识的加强使日本这种后发帝国主义国家忘记了曾经压迫、侵略别国的历史。广岛和长崎属于相同的民族共同体,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这加强了这两座城市的被害意识,这种被害意识也影响了参观过纪念馆、不了解这段历史的每一个日本人。[17]
中日两国国民对于过去的历史事实没有形成共同记忆,从“场”产生的记忆自然就会存在分歧。在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面前,中国对历史事实选择了记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日本则选择了刻意遗忘,遗忘掉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四)重构日本侵华暴行公共记忆的希望
日本侵华暴行问题是中日之间遗留的重大历史问题,如何认识这段历史,如何面向未来发展中日关系,始终是横亘在中日之间的一个悬而未决的基础性问题。时至今日,战后70多年过去了,日本政府没有正式承认侵华暴行,没有进行赔偿道歉,没有把史实真相正确地传达给本国民众。中日间如何重构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面向未来发展新型的国家关系,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双方的学者有义务为了建立公共记忆而建言献策。一味地指责和否认,只会加深彼此的不信任,只有建立在承认历史史实的正确历史观基础上,才能构筑“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中日两国才能和平走向未来。
如今的美日关系,看似没有隔阂,对于美日之间的战争,日本和美国都采取了共同忘记,好像一夜之间都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共同杀戮的经历不可能一夜之间全部忘记,虽然难以忘记,却使之忘记了。这是美日在国民间采取的骗术。对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历史问题,日美之间不是基于“共同记忆”而是“共同忘却”。不应该被忘记的过去的记忆,经常在某个时间某种情况下被想起。并且,往往是不应被想起的时候浮现出来。共同记忆与共同忘却看似相似,实则相异。日美对于互相杀戮的历史在双方的协议下共同忘却了。而中日对于残杀的历史却没能达成共同忘却的协议,中日共同记忆的历史虽然对双方来说是种深深的伤害,但却比日美共同忘却的历史更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历史应该在共同记忆的影响下书写,因此中国和日本应该形成更多的共同记忆,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基于历史事实形成更多的共同记忆,这是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结 语
战后70年来,由于战后处理不彻底等原因,日本长期在历史问题的困顿中纠结。日本国内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在解决战后和解问题上,日本期待的是一种外交上最低成本的边际效益,一种技术处理,并非追求自身精神层面的蜕变。[18]陈景彦从教科书问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问题等方面分析了日本首相及政府的历史观及日本政府右倾史观的原因,认为应该理智而冷静地对待历史认识问题。[19]
笔者认为:从作为加害者与受害者立场的记忆与忘却视角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应该从人权的观点来讨论、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补偿问题,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澄清历史问题,而且对中日关系及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发展之路都具有启发意义。
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日军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犯下了累累罪行,这种罪行已经成为了日军的伴生物和标志,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性、掠夺性、破坏性和它发动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给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无法估量的损失。
当我们回首这段历史,谴责当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无情践踏时,其出发点并非出于对本民族曾经苦难的无法释怀,更不是要激发记忆中的民族仇恨,而是要让人们对战争的本质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唤起人们的和平意识。只有深刻理解战争带来的苦难与破坏,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能更加珍爱和平,避免战争及类似悲剧的再度发生。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重新回忆历史的伤痛,不是一个种族对另一种族的反对,也不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偏见,它的目的是希望将这段历史的创伤固化为人类社会共同的记忆,从而避免重蹈历史覆辙。”[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