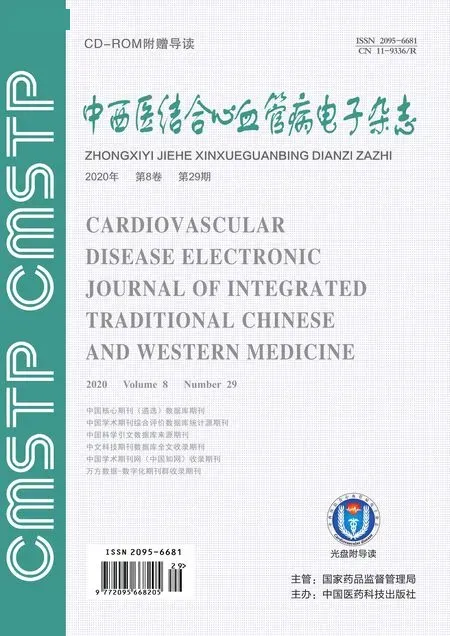不孕女性焦虑、抑郁的相关因素
苗瑛铭,万峰静,刘君儿,佟新阳,李 珑
(1.海南医学院,海南 海口 571199;2.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海南 海口 570311)
在世界范围内,不孕症影响着10 %的人口,且逐渐成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1]。在不孕症中,女性因素占据40%~55%,且女性各精神症状的发病率为男性的2倍[2],不明原因的不孕占据10%,这可能与心理因素有关,心理问题已经成为公认的不孕症因素之一[3]。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主要与人的焦虑、抑郁水平相关,国内外均有研究表明不孕女性的焦虑、抑郁状态普遍高于常模[4]。焦虑、抑郁与不孕症是互为因果的。焦虑、抑郁导致疾病的发生和治疗困难、生活和婚姻质量下降、性问题和家庭不和谐、影响社会稳定。为此,全球医疗机构在进行诊治女性不孕症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关怀和解决其焦虑、抑郁问题的迫切挑战。
1 不孕女性焦虑、抑郁的相关因素
1.1 ART治疗及结果
对于不孕女性来说,生育治疗对患者心理健康的影响最大[5]。随着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的发展,ART为不孕女性带来了巨大福音,但接受ART治疗的不孕女性背后却承载着无数的苦难与压力。不孕症治疗存在不确定性,这使得她们与未做过治疗的不孕女性及正常育龄女性相比有更高的焦虑、抑郁[6]。一项25年的系统评价指出[4],接受不孕症治疗的女性,其心理状态是不同于常人的,其中高昂的费用、躯体侵袭、重复周期、就诊次数、辅助生殖次数与焦虑、抑郁呈相关性[7]。目前ART治疗的成功率在50%~60%之间,且一次成功的概率不高,不同的治疗方案、检查项目及药物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接受腔镜治疗、输卵管造影后患者的焦虑、抑郁程度呈应激性增高[8]。
1.2 疾病自身
生育被看做是女性最基本的义务,我国的传统文化认为,传宗接代是生命的延续,是最基本的孝道,在此影响下我国不孕女性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从发病机制角度看,过度的焦虑、抑郁会通过交感神经系统—肾上腺髓质系统活动加强从而对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Hypothalamus-Pituitary-Ovary Axis HPO)产生抑制,导致肾上腺皮质激素增多,影响促排卵效果。在ART治疗中,激素水平的调整始终贯穿其中,自身激素水平的调整能力必须纳入到治疗中来,激素治疗越精确,其治疗的成功率越高[3];由心理应激导致的交感神经兴奋,加速儿茶酚胺的损耗使得子宫产生局部效应,干预配子体在输卵管中的输送,影响子宫血流,影响妊娠结局[9]。中医角度认为,强烈的生育愿望使女性心思郁结、气机不畅、肝失疏泄,从而导致焦虑或抑郁,这一现象又使气机瘀滞、疾血在胞内滞停,精子与卵子无法结合;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状态使患者情绪淡漠、失眠、体制变差,影响不利于ART治疗[10]。
1.3 人口学特征
与年龄有关:首先,女性的生育能力在26~35岁左右达到高峰,所以焦虑、抑郁在此年龄组更常见[11];其次,高龄使女性的生育能力呈指数型下降,焦虑、抑郁程度在此年龄组较高[12]:世界上女性延迟分娩的趋势越来越突出,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开放后晚婚、再婚人数的增加,高龄女性寻求ART治疗的比例明显攀升,因此,高龄也成为此政策下一项严重的心理社会压力。
1.4 性问题和家庭关怀度
以往的研究表明,来自于对未来关系的担忧,不孕女性对于配偶的依赖性极强,会过分关注配偶的态度和行为[13];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对于不孕症导致的配偶间性自尊和性乐趣的丧失,以及性交的压力比与其配偶公开讨论不孕症问题本身更令人不安[14]。因此,与配偶的关系,特别是配偶间的性问题,是与不孕相关的心理问题严重程度的核心表现。调查显示家庭关怀至关重要[15],82.9%的女性在接受ART治疗前已经取得家庭的支持,90.7%的女性认为与配偶关系良好。
1.5 认知与社会支持
不孕症在社会上存在不良认知,导致患者被歧视和贬低,在社会交往中不安和恐慌增加,焦虑、抑郁随之诞生[16]。Steuber[17]认为,缺少社会支持会增加患者的心理压力,降低治疗依从性。Jong-Yi Wang[18]认为,社会支持不是导致压力的直接因素,认知压力和自尊是压力源和精神症状之间关系的两个主要介质,通过增加社会支持和自尊能使不孕女性的焦虑、抑郁减轻。
2 总 结
不孕女性焦虑、抑郁越发严重,已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医疗健康组织的广泛关注,它是发自疾病自身的、不可避免的一种情感状态,主要与 ART治疗及结果、疾病自身、人口学特征、性问题和家庭关怀度、认知和社会支持,我们要根据个体独特的相关因素给与相对应的干预措施,未来的研究结果还需要更多多中心、大样本的实验数据来证实,对于未进行不孕症治疗的不孕女性也要给予关注其心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