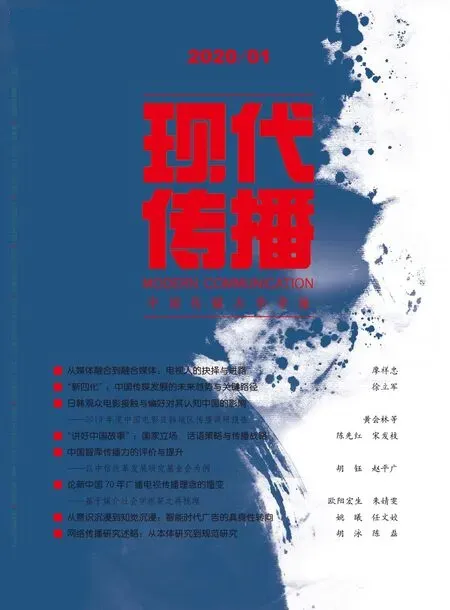建设性新闻:概念溯源、学理反思与中西对话
■ 郭 毅
一、问题的提出
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概念正成为全球新闻学热点。在业界,主流媒体纷纷呼吁践行“建设性”的新闻报道,欧洲的媒体管理者和一线记者还发起了一些旨在引领建设性报道理念、培育建设性新闻记者的实体机构和国际倡议。在中美洲、非洲和东欧,即便许多记者从未听说“建设性新闻”,其日常报道也不自觉地体现了建设性新闻理念。①在学界,2017年起一系列国际研讨围绕建设性新闻开展,其成果以专题论文形式刊登在新闻学领域的重要期刊。一些欧美国家还将建设性新闻课程纳入本科教学,其热度不言而喻。
近两年,有学者及时地将建设性新闻概念译介到国内,引起了回响,建设性新闻甚至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但仔细研读中文文本可以发现,一些关于建设性新闻的论述存在简单化和想当然化:简单地认为建设性新闻是一个革命性的全新概念,并想当然地以乐观的态度呼吁国内业界应用。这或许与近代以来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的中国思想界面对西方理论的惯性思维有关。这种思维表现为对西方概念异常兴奋,对其的译介和挪用被等同于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途径。
我国当代新闻学领域中,不乏看似新鲜时髦的理念和名词引进不到几年就热度递减、无人问津。要想避免这样的窘境,对“建设性新闻”的理解就必须准确而深入。而要将西方的“建设性新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则必须将此概念在理论谱系和学术脉络中进行比较、对话和反思。建设性新闻究竟是不是一个新的革命性概念?其在整体的新闻实践话语中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其概念自身是否存在问题?西方建设性新闻与我国本土学术话语有何异同?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当代建设性新闻的两条理论路径
近年来欧洲新闻界呼吁重新定义新闻功能和价值,提出建设性新闻理念,呼吁记者摒弃旁观者立场,主动介入公共生活,报道事件积极的一面,提供化解社会问题的方案。③当代学者沿两条路径对建设性新闻进行理论化:一是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切入;二是从佛学角度论述。忽略任何一条理论路径,对概念的译介都谈不上完整。然而我国目前只译介了第一条理论路径。
1.积极心理学与建设性新闻
当代学者一般认为,建设性新闻最初由丹麦记者Ulrik Haagerup提出,后经Cathrine Gyldensted的英文著作进入英美新闻学界。挪威学者Karen McIntyre在Gyldensted的基础上对建设性新闻进一步理论化,明确将建设性新闻定义为一种新的新闻类型:“其在保留新闻核心功能的同时,应用积极心理学技巧进行报道,更具创造力和吸引力。”④
积极心理学是一种手段,更是一个隐喻。19世纪的心理学重在诊治精神错乱,形成以探索心理和精神领域黑暗面为主的“疾病模式”研究取向。积极心理学则主张在精神疾病之外,研究积极的心理情绪,在修正错误的同时,引导正确方向。它关注个体的愉悦情绪,也关注群体的健康发展,既鼓励研究积极情感(如愉悦感觉)的获得,也探索积极品质(如诚实)的培养。⑤
建设性新闻与积极心理学构成类比关系。积极心理学是对心理学“疾病模式”反思的结果,建设性新闻则源于对新闻业“黄金时代”的反思。新闻史上的黄金时代以20世纪70年代末新闻媒体对“水门事件”的持续跟踪调查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为标志,它强调新闻的看门狗角色,记者以报道负面新闻为能事。但过剩的负面报道并没有消弭暴力冲突,而是相反的片面扭曲了整个世界。正如积极心理学反对过分关注消极情绪和疾病、提倡以积极因素建导个体最佳机能,建设性新闻反对过度关注灾难和丑闻,提倡以积极的方式报道负面事件、促进个人和社会健康发展。⑥
所谓“积极的方式”,一是在传递信息过程中激发读者的积极情感,二是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案。具体可细化为:(1)以解决方案为导向,提供成功化解问题的典型经验;(2)以未来为导向,采访时要多问一句“接下来呢”;(3)折中化,尽量避免分化公众;(4)建设性采访,多鼓励受访者针对社会问题做反思性陈述,并直截了当询问其在面临相关问题时将会如何解决;(5)使用数据证明被报道事件或社会现象进步的一面或进步的潜在可能性;(6)为公众赋权,媒体与读者合作生产新闻内容;(7)以公众为导向,报道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从公众感兴趣的角度报道新闻,与公众交换观点;(8)以行动为导向,记者不仅是社会问题的批判性力量,更应动员公众行动起来改善社会环境、追求美好生活。⑦
2.佛学与建设性新闻
建设性新闻在台湾地区也被译成“建构式新闻”。2016年和2017年台湾地区公共电视和世新大学分别召开了建设性新闻研讨会。TVBS电视台还专门成立了基金会,大力推广建设性新闻理念,并联合高校每年评选“全球华文永续报道奖”,激励华语地区的建设性新闻报道。
台湾学界认为,何日生在2005年早于西方学界提出建设性新闻概念。何日生是受美国新闻教育的资深新闻人,后加入证严法师创办的慈济大学。何日生回忆,证严法师所倡导的“媒体要竖立典范”、“大爱,扩大善”和“报真导正”促其反思以英美新闻业为主导的西方新闻报道范式,并提出建构式新闻。
何日生提出:“建构式新闻的主旨,就是以同理心报道事件,在发掘问题之际,同时寻求解决之道;记者的职责不是批判,而是为建构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而努力。”他认为,负面报道和过度批评应有所节制,但又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建构式新闻不是不报道负面,而是在每一项负面事件中,都提出让公众能依循的正面典范。”⑧
近年来,学术界还提出另一种受佛学启发的“正念新闻学(mindful journalism)”概念,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媒体实践中应用。这一概念最早由澳大利亚学者Mark Pearson提出,他还与斯里兰卡裔美国学者Shelton Gunaratne合作,出版了相关理论专著。这套理论也体现出“去西方化”的学术立场,它既是将佛学观念引入新闻学研究的直接产物,亦与挪威社会学家Johan Galtung提倡的“和平新闻”一脉相承。和平新闻对西方经典战争冲突报道提出批评,认为媒体对战争和冲突的渲染反而导致暴力冲突升级。因此,它强调新闻报道应关心战争中的人性而非流血事件,尽量呈现多方声音,寻找冲突的解决途径。⑨
同和平新闻与建构式新闻一样,正念新闻学提倡对西方主导的新闻价值加以必要修正,反对将新闻视为消费品,推崇其为一种社会性的善。受佛学观念启发,正念新闻学认为记者应通过新闻报道帮助他人脱离苦海。学者们由此提出正念新闻的10个原则。(1)理解悲伤和苦恼源于贪念和执念,区分短暂的肉体欢愉和持久的精神幸福。报道要引导读者净化心灵,追寻长久的精神幸福。(2)以“无我”为最高境界,报道应避免过度的个人主义。(3)世事无常,记者要成为社会变革的建构性力量,避免做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4)以“因果法”为分析社会问题的诠释框架。(5)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遵守道法自然的原则。(6)炫耀性消费增加人们的贪念,新闻报道应对之进行批判。(7)遵循中庸之道,避免极端。(8)记者应受道德约束,报道应不偏不倚、不诽谤他人。(9)佛家重视修养心性,因此记者要提高内在修为,成为一个“理智、进取、思想自由、观念开放、有耐心、有知识、有教养的报道者”。(10)报道事实清楚、完整、全面,从而促进公民社会康乐。⑩
三、建设性新闻不是新概念
当代建设性新闻的提出和理论化,本质上是对新闻功能和伦理的再省思。尽管学者试图从积极心理学和佛学角度对建设性新闻进行论述,但若将这些理论和实践话语置于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新闻实践史中来看,无论是其基本特征,还是新闻界的这种对新闻功能和伦理的省思精神,都谈不上是“全新的”和“革命性的”。
在西方新闻界,建设性新闻并非新名词。1886年便有英国报纸将《每日新闻报》视为“建设性新闻的典范”。距今一百多年前,建设性新闻还明确成为一些美国媒体的宗旨。1924年美联社芝加哥记者站负责人曾在演讲中指出,“建设性新闻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事物”。而整个20世纪,美国新闻界几乎从未停止呼吁建设性新闻。可惜的是,19世纪以来新闻史书写的辉格史观突出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历史叙述,遮蔽了新闻史的细枝末节,以致在各种新闻通史中都难以找到关于建设性新闻的论述。我们不得不在史料中重新耙梳,以勾勒当代建设性新闻的历史根系。
美国新闻界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围绕新闻的本质、功能、伦理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并对便士报时期煽情主义和报道不实造成的社会道德问题进行反思。报道真实性在20世纪初美国各州及联邦政府新闻伦理规范文件中得以落实,但煽情主义却在普利策所引领的新新闻主义和赫斯特引领的黄色新闻中一次次复兴。
19世纪末西方报界已经深刻认识到过度渲染负面新闻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许多报人公开批评读者追求感官刺激的阅读口味,纷纷指责盛行的煽情主义迎合公众的“变态审美”、败坏社会道德。人们意识到减少负面新闻和重塑公众阅读品味的迫切性,一场呼吁“干净新闻”和“正当新闻”的运动逐渐兴起。
1.从干净新闻到建设性新闻
美国西部是推崇干净新闻和正当新闻的重镇。这两个概念最初由《旧金山新闻报》在1895年提出。“‘正当新闻’适当地报道事件,‘非正当新闻’则专门刻画堕落和犯罪活动。前者还原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后者恶意丑化了整个世界。前者是公正的,后者是夸大的。前者是有道德的,后者是病态的。前者启人心智,后者激发败坏道德的好奇心。”干净新闻即是正当新闻,“它以冷静的、透明的、不加渲染的方式报道事件。不干净的新闻总是渲染罪恶。前者报道事实,后者呈现虚伪。前者令读者保持纯净心灵,后者以污秽腐蚀人心”。
在这场新闻运动中,“建设性新闻”是干净新闻和正当新闻的同义词,并逐渐取而代之。1916年,时任威斯康辛大学新闻系主任Willard Bleyer在威斯康辛编辑协会的半年会上对建设性新闻的概念做了明确表述,又经美联社报道,被当时报刊广泛征引。他指出“建设性新闻试图以对读者有益的方式呈现重大事件”,它“从个人和社群健康发展的角度提供重大信息,同时制造阅读兴趣。”报纸必须考虑新闻对读者的影响,故“建设性新闻应当更有益处、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报道负面新闻时,须标明“原因、责任、发生频率等,以使受众意识到其重要性,并在日后采取应对和预防性措施”。
这些表述与当下所谓的“建设性新闻”几乎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强调新闻记者不应是外在的旁观者,而应该在客观和准确的基础上,以更加积极的和引人入胜的方式,报道对个人和社会意义重大、振奋人心的新闻。建设性新闻不是回避负面新闻,而是全面报道、厘清因果、树立典范,帮助人们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2.20世纪的读者反映
建设性新闻早已为西方读者所熟知。整个20世纪中,这一概念不时地被读者用来臧否报刊,这可从美国报刊的读者来信中得以印证。
一方面,读者常因报纸未做到建设性而写信抱怨。如1919年旧金山居民写信批评报上的“评论大多措辞粗鄙”,缺乏建设性。他呼吁报纸“努力呈现广受读者欢迎的视角,做好建设性新闻”。1938年纽约居民在信中抱怨负面新闻过剩,“建设性报道的价值应获得社会更多关注”。1976年德克萨斯州读者批评当地报纸“未能提供建设性新闻”,要求报纸“少关心煽情琐事”。
另一方面,建设性报道常得到读者表扬。如1934年宾夕法尼亚州读者表扬报纸“赞助专家对社会问题进行调研的做法证明建设性新闻方兴未艾”。1954年肯塔基州一家报纸因“以建设性新闻扮演了真正的社会服务角色”而得到读者肯定。1971年亚利桑那州读者表扬一篇直面大峡谷环境污染的报道“证明报社正在做有良心有责任的建设性新闻”。1981年明尼苏达州读者高度评价一桩罪案报道作为“建设性新闻充斥着友爱、同情和谅解的积极情绪”。
可见整个20世纪北美读者所理解的建设性新闻与当下所说的建设性新闻在语词上毫无差别,在宗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由于当下所说的建设性新闻兴起并流行于欧洲(特别是北欧)新闻业界,其提倡者未必熟悉新闻史(特别是北美新闻理论史),才会有许多人误以为建设性新闻是一个“全新的革命性”概念。
四、建设性新闻并非毫无问题
概念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概念丛中、学术网络中的。研究建设性新闻,宜从学术史整体着手,在相关概念和学术系谱中进行反思。19世纪以来,学界对新闻功能和价值的讨论与反思从未间断。除干净新闻,还诞生了和平新闻、公共新闻、解困新闻、积极新闻、服务新闻的概念。有学者指出,这些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当下建设性新闻的提倡者,但他们并未说明,围绕这些概念的争议和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建设性新闻上,成为其鼓噪者尚无法解决的难题。
1.公共新闻与建设性新闻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起,新闻界意识到媒体过分依赖官方信源,以致沦为政客和专家的传声筒;记者恪守局外人角色,也加深了其与公众的疏离。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概念应运而生。它视受众为公共生活的参与者而非信息的被动接受者,鼓励公众借助媒体表达观点、参与公共事务。记者不是旁观者,而要联系群众,营造讨论氛围,帮助解决其所关心的问题,促使公众生活向好的方向发展。具体实践中,媒体通过数据调研公众兴趣、选择报道议题,或与公众对话、合作生产新闻内容。
建设性新闻和公共新闻都体现出公众导向,假定公众讨论可以促进公民福祉,也都认为记者是动员公众介入讨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力量。但这是过于理想化的。已有许多西方学者指出以公众为导向的新闻并不能激发出一种积极的参与式文化。通过数据调查选择的报道议题看似迎合读者兴趣,但受限于样本数量,这些议题不能准确反映社会各阶层的诉求;合作生产新闻看似吸纳部分公众进入制作流程,但他们无法代表整个社群。此外,这种公众自由讨论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社会变迁,也取决于其所依托的政治文化语境。在特定文化语境中,新闻激发的公众讨论发挥影响的空间有限,其结果往往是增强了公众的犬儒主义思想和对新闻业的失望。尽管公共新闻运动在1994年至2002年间一度达到顶峰,但许多西方媒体推出的公共新闻报道计划仍相继停止,公共新闻运动最终没能达到其标榜的“引领公共生活”的目标。因此以公众为导向的新闻报道所面临的上述难题仍需要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直面。
2.解困新闻、服务新闻与建设性新闻的问题
新闻界早已在批判负面新闻过剩的同时呼吁干净新闻和建设性新闻,传播学研究亦证明以冲突为导向的新闻激发了受众的负面情绪和同情疲劳,导致媒体信度降低、受众锐减。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解困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理念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它报道成功化解问题的典型个案,鼓励读者效仿。与解困新闻相似的是诞生于二战后的服务新闻(service journalism),它要求记者通过提供日常生活资讯来指导人们化解生活烦恼。与解困新闻关注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不同,服务新闻在内容上侧重消费领域。
建设性新闻与解困新闻和服务新闻一样,假定读者在信息杂陈的时代亟需媒体的建议和引导,但这种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也存在着问题。其一,这种导向是站在媒体的立场预设公众对媒体的需求。但在后真相时代,受众未必愿意对新闻媒体言听计从,更未必相信媒体树立的所谓典范。其二,它假设提供解决方案可以帮助化解社会难题。然而是否真的存在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各种解决方案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冲突,致使公众更加迷惑?其三,近两年的实证研究也对这种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新闻提出质疑。研究证明,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和以消极负面信息为导向的新闻都不会增加读者对受害者的同情,也都不会增进读者对特定社会问题的理解,解困报道更无法对读者的实际行为造成影响。鉴于得出这一结论的研究者正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理念的支持者,建设性新闻所标榜的社会功能和实际效果尤其值得怀疑。
五、建设性新闻的中国问题
建设性新闻不难令人联想到我国新闻实践的几个理念:建设性舆论监督(建设性批评)、“正面宣传为主”和“暖新闻”。当下有些论述,将建设性新闻与它们划了等号。要思考将西方建设性新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的可能性,必须将这些本土话语与西方概念进行比较和对话,而不是以“中国化”的名义简单地把它们混为一谈。
1.建设性新闻不等于“建设性舆论监督”
在西方建设性新闻传入之前,我国早就在谈新闻的“建设性”,并明确提出了“建设性批评”或“建设性舆论监督”。尽管它们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和改善现状,但这里的“建设性”和西方所说的建设性仍有不同。西方语境下的建设性新闻的落脚点是公民和社会,我国所说的“建设性”,强调的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新闻舆论监督。“建设性”在我国除了指新闻要对公民和社会有利,还要保证不损害党和政府的利益。这是西方语境中的建设性新闻不具有的内涵。
这种区别反映了中西两种“建设性”话语所依赖的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必须承认,中国的新闻业态与欧美等西方国家是不同的。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并不存在政府或党派对新闻伦理问题自上而下的领导,对于新闻价值和功能也并无一种官方的主导性定义。西方所谓建设性新闻,是新闻界在实践中不断反思的结果,这种对报道范式的改造建立在百余年来新闻实践和理念创新的反复摸索之上。中国新闻界所说的“建设性”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是与生俱来的品格。因此要将西方建设性新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必须深刻认识到中国的特殊语境,不能简单移植。
2.建设性新闻不等于“正面宣传为主”
当下我国提倡“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理念,它不仅要求记者宣传国家建设新成就,也要求媒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宣传国家建设成就符合我国业界对新闻建设性的普遍理解。我国媒体从业人员所理解的“建设性”除了“通过提出合理的建议帮助政府解决具体问题;协助政府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包括“建构一个积极的地方形象,提高美誉度”。这种理念与西方所谓建设新闻(development journalism)类似。建设新闻概念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认为新闻应着力报道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成就。这种报道范式是冷战时期的产物,但因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至今仍在新加坡、文莱、斐济、马来西亚、尼日利亚等亚洲和非洲国家盛行。在这些国家的实践中,新闻被视为国族建构的重要工具,新闻记者需要配合政治和经济精英建设国家。不过,建设性新闻的提倡者却明确将二者划清了界限:建设性新闻不是建设新闻。
此外,虽然西方建设性新闻与我国的“正面宣传为主”都批评负面新闻过剩,但中西对“负面新闻”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西方语境中,负面新闻过剩对个人和社会产生消极影响,造成受众对媒体的疏离。在我国,负面新闻过剩还被认为有另外一层影响,即破坏党和政府公信力。因此,“正面宣传为主”要求新闻报道不仅要有利于公民和社会福祉,还要对党和政府有利。
3.建设性新闻不是“暖新闻”
在“正面宣传为主”基础上,从2015年开始,我国不少媒体推出所谓“暖新闻”,并将之等同于西方的建设性新闻。暖新闻聚焦日常生活中的“暖心小事”、好人好事,试图树立引领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典型,本质上仍是一种典型人物报道。西方的建设性新闻关注的是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重大议题,而不是“小事”。建设性新闻虽然也谈“典型”,但这种典型是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成功经验,而不是践行某种价值观的典型。
“暖新闻”不仅不是西方所说的建设性新闻,甚至走入其对立面。建设性新闻坚决捍卫新闻的核心功能,即媒体对政府的监督功能、提供有用信息的功能、提示公众潜在风险的功能。“建设性”只是一种形塑新闻的基本框架,其关涉的是“如何报道”而非“报道什么”。从这种意义上讲,建设性新闻不是“好事新闻(good news)/积极新闻(positive journalism)”,更不是报喜不报忧。在实践上,积极新闻也曾一度在西方流行,但渐渐陷入困境。20世纪70年代英国BBC广播一度推出“积极新闻”栏目,但不到几年就宣告失败。而目前经常被建设性新闻提倡者用来举例的积极新闻网站,也并没有数量可观和固定的读者人群,影响力不可高估。
4.民生新闻与建设性新闻
民生新闻曾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民生新闻站在百姓视角,播报群众关心的事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它不仅涉及舆论监督报道,也提供生活服务类信息,它还鼓励受众参与新闻生产,因此拉近了媒体与受众的距离。从这些特征来看,民生新闻虽然在西方似乎找不到对应的概念,但却兼具前文提到的服务新闻、公民新闻、解困新闻之特征。从这个角度看,民生新闻尽管热度已大不如前,却更接近西方“建设性新闻”,或许可以成为将建设性新闻纳入中国特色主义新闻学理论的切入口。
不过,民生新闻在实践上与西方建设性新闻也有不同。首先是民生新闻对负面信息处理不当造成的伦理问题。一些借助暗访的调查报道,常常容易从通俗滑至低俗。而伦理问题一直是西方建设性新闻关切的核心之一,耸动的、煽情的报道方式是其坚定批判的对象。其次,西方建设性新闻关切的是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关涉全民福祉和社会进步,本质上是硬新闻。民生新闻容易出现报道内容的软新闻化,过剩的生活服务类信息挤占版面,对更重大的社会问题反而敬而远之。这种趋势近几年变得尤为显著,在许多城市的民生类电视节目和都市报中,天气变化、菜价涨落、家长里短等竟成为报道主体,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关切悄然不见了。
六、结语
尽管当代学者试图从积极心理学和佛学角度对建设性新闻进行理论化,但其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一个早在19世纪末就被明确提出并被报刊读者接受的概念。“建设性新闻”也不是一个革命性概念,而是在学理上与20世纪西方新闻学领域的其他概念相联系的概念,是概念丛中的概念。正因如此,建设性新闻“以公众为导向”和“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主张并非毫无问题。在对概念进行溯源和学理反思后,笔者不禁要对建设性新闻的过分乐观态度产生怀疑,建设性新闻真的“能够激发受众参与对话,以此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推动媒体价值的实现”吗?
新闻的建设性并非我国新闻实践话语中的新主张。但长期以来我们所说的新闻“建设性”与西方所说的“建设性新闻”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这些区别体现了新闻“建设性”的相关话语所依赖的两种不同的合法性基础,而这也是思考西方建设性新闻能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关键。
注释:
① S.Rotmeijer.WordsthatWork.Journalism.2019.20(4):600-616.
③ J.Mast.R.Coesemans & M.Temmerman.ConstructiveJournalism. Journalism.2019.20(4):492-503.
④ K.McIntyre.ConstructiveJournalism.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2015,p.8.
⑤ K.Hefferon.PositivePsychology.Open University Press.2011.pp.1-21.
⑥ K.McIntyre & C.Gyldensted,PositivePsychologyasaTheoreticalFoundationforConstructiveJournalism. 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662-678.
⑦ L.Hermans & N.Drok.PlacingConstructiveJournalisminContext. 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679-694.
⑧ 何日生:《建构式新闻》,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3页。
⑨ J.Lynch.PeaceJournalism.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2015.11(3):193-199.
⑩ S.Gunaratne.M.Pearson & S.Senarath.MindfulJournalismandNewsEthicsintheDigitalEra.Routledge.2015.pp.1-18,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