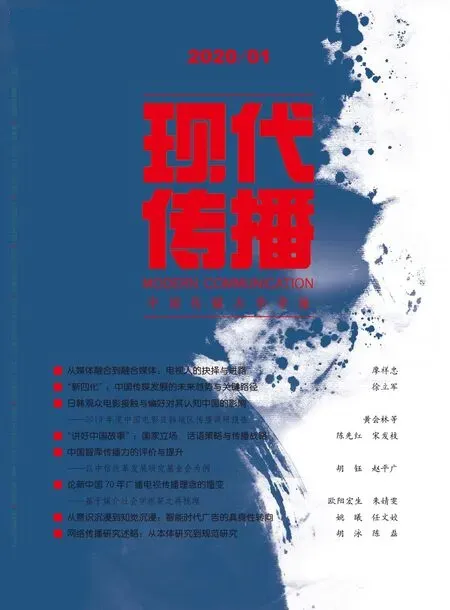新中国70年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演进轨迹
■ 覃 榕 覃信刚
一、问题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播电视众志成城、筚路蓝缕、创业创新,取得非凡业绩:人民广播事业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能继续播音的39座电台发展到如今的2825座,播出节目801.76万小时,全国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8.94%;电视台从无到有,如今共有3493座,播出节目357.74万小时,全国综合人口覆盖率99.25%。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资金短缺、百废待兴,中央挤出220万供发展人民广播事业之用。2018年,全国广播电视实际收入5639.61亿元,广播广告收入最高年份为155.56亿元。新中国成立当天,于1949年6月5日成立的中央广播事业处改组为广播事业局,当时全国广播事业只有1800名干部员工,多数只有高中和初中文化。截至2018年底,全国有广播电视从业人员97.90万人,81.38%为大专以上文化。①原有的广播事业局到如今已演变为广播电视总局、广播电视总台。而广播电视局、广播电视台则遍布全国省市县,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广播电视大国,正向广播电视强国迈进。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升温,如理论、节目、广告、文艺、媒介融合的回顾、总结与展望等。相比之下,对70年来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研究则较少。其实,新中国广播电视的繁荣昌盛,离不开管理体制的科学性、先进性和普遍性。“政贵有恒”,新中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从何而来,怎样演进,有何特色,本质是什么?在新时代,特别是广播电视体制还在深化改革的当下,文章以问题导向、前瞻眼光,梳理这70年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发展脉络,并提炼其特色与本质,“为政知所先后”,对我国广播电视强国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②考察广播电视体制70年的演进,离不开宏观视角、宏观叙事。但长期以来,新中国广播电视体制为宣传与管理一体,事业建设与广电传播一体,又需顾及广播电视媒介组织。这样,宏观、中观、微观都会涉及,管理体制与节目播出会并用,但总体上主要还是宏观叙事、阶段考察、特色分析、本质理论。
二、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演进轨迹
管理,从一般意义上讲,“‘管’如锁孔,通过一定管道即可对人、事、物进行管辖、约束,‘理’如治玉,是指通过整治、处理,使事物具有条理和秩序,亦即主其事者为管,治其事者为理”③。体制,则是指国家机关、事业、企业单位等机构的组织制度。“广播电视体制是广播电视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广播电视制度是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广播电视所有权、基本性质、基本目标等方面所构成的规范体系。广播电视体制就是这一规范体系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④
在世界上,现代管理理论起源于1911年美国商人弗德里克·温斯络·泰勒(Frederick W.Taylor)出版的《科学管理之原则》,终而演变为科学管理思想。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了行政组织体系理论。韦伯认为,组织者能依照某些原则来建构,即可成为产生效率的工具。他提出了科层组织概念,科层组织是指以理性的建构原则,在最有效率的方式下建构组织。这些原则包括:层级结构、规范、理性分工、专业技术资格、岗位、管理和所有权的分离等。⑤尽管韦伯的科层制观念广受诟病,但他的管理思想还是被不断采用,对广播电视管理观念、行为产生了不少影响。新中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无疑也涉及层级、规范、岗位、分工等,经历了从宣传与管理合一、“领导”与“管理”分开、“条条”“块块”结合,再到以管为主、适度放权、管办分离的演进历程。如果简要划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初创调整期与改革创新期。
(一)初创调整期:层级、结构、职责的形成
这一时期主要指的是1949—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可谓一穷二白,国家极度贫困,人民广播电台虽然已接近40座,但覆盖范围有限。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广播电视工作,广播发展较快,电视也于1958年诞生。但由于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以及“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影响,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也得随机而变,以适应现实的环境。从1949年至1978年,广播管理体制进行了四次调整,层级、结构、职责逐步形成。
1.宣传与管理一体,广播组织架构形成
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原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并领导全国人民广播事业。⑥通知明确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和新华总社为平行组织,同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从此,广播事业与新华社分设,成为独立的宣传系统。不同的是,新华社为单一的宣传机关,而广播事业处既有宣传,又包括了事业建设。之后媒介组织推行的“事业、宣传”双重职责,源至于此。
1949年7月27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北京新华广播电台。7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新中国的临时大宪章)中的第49条规定“发展人民广播事业”⑦,这就为发展广播事业提供了法律保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改组为中央广播事业局,直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新闻总署领导。⑧此次调整,名称只一字之别,但重要性不言而喻:广播事业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重要的组成部分,广播事业局是重要的组成部门。1949年12月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管理体制不变:局台合一,副局长兼总编辑。宣传与管理一体,广播组织架构初步形成。
2.“领导”与“管理”分开,广播媒介系统结构显现
194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政府成立后党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中央政府成立之前,党的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实际上暂时代替中央政府的文教机关,管理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现在中央政府已成立,全国文化教育行政工作,均应由中央政府文教部门来管理,目的是使党的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宣传部能够摆脱行政事务,集中注意力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领导和党的文化宣传政策的制定。⑨
1952年2月,实质由中央宣传部领导、管理的新闻总署撤销,广播事业局的隶属关系改变:由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接管理,之后再次调整,成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宣传业务则仍由中央宣传部领导。⑩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广播系统管理结构的一次大的调整。
中央广播系统领导管理结构确立后,1955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地方人民广播电台管理办法的规定》,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辖市人民广播电台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省辖市人民委员会的直属机构,受各该级人民委员会及广播事业局的领导。”此规定明确了省级广播媒介的层级领导关系。国民经济恢复以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期间,国家的行政区划曾做过多次调整,大区级、省级和省级以下广播电台也随之调整。截至1956年底,全国共有地方广播电台56座。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中国共有省级广播电台27座,其余为地级市广播电台,基本上建成了以中央电台为中心的全国性广播宣传网。“领导”与“管理”分开,广播媒介系统结构显现。
3.“条条”“块块”结合,双重层级领导
1959年,广播事业局的组织机构进行了第三次调整:事业局党组与中央电台编委会合一,形成一体化领导机构,全局部门细分,广播媒介设置有对内广播部、对外广播部、电视广播部等。而对内、对外、电视广播部,奠定了后来中央三大台的格局。1963年,广播事业局的领导体制进行了第四次调整:局党委统一领导,分设宣传、技术、政治、行政四种工作机构。这次领导机构调整,还建立了处理日常事务的部务会议。中央广播事业局和中央电台的调整,为全国地方广播管理机构和广播媒体树立了标杆。1964年,全国省级广播事业局全部建立,之后,地、县级也设置了广播事业局,管理体制采取“条条”“块块”结合、双重层级领导的模式。“条条”是指从中央到省再到省以下广播电视机构之间直接的纵向对口领导;“块块”则是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对同级所属的广播电视机构的直接领导。“条条”“块块”结合,双重层级领导,“是指既有‘条条’领导,也有‘块块’领导”。
(二)改革创新期: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优化与理性分工
这一时期主要指的是1978—2019年。十年浩劫,新中国广播电视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假大空”和个人崇拜的文章充斥电视和广播,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踏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征程,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中国广播电视体制共进行了五轮改革。
1.以管为主,广播电视媒介竞争形成
1982年5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根据该决议,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组建新的广播电视部。从广播事业局到广播电视部,一是局变部,广播电视管理部门进入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二是扩大了范围,增加了“电视”,强化了国家对广播电视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管理。1986年1月20日,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将广播电视部改为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决定。原文化部电影局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省市级广播电视管理机构也依照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做法,进行了机构划转和职能划转。此轮改革,最主要的也是加强了对广播电影电视的集中领导和管理。两轮改革,管办合一,以管为主,管理得到了强化,但办好广播电视媒体,抓好各项宣传工作仍然被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确定为主要职责。
广播电视部成立以后,于1983年3月31日至4月10日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将省、自治区一级机构统称广播电视厅,中央直辖市以及省辖市(地、州、盟)和县(旗)均称广播电视局。到1984年底,全国建立了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广播电视厅(局)29个,地区、直辖市级广播电视局(处)350个,县级广播电视局1700个,广播事业规模不断扩大。”
这些广播电视厅(局、处)置身于改革大潮,都积极探索自身的改革,以管理和宣传为主。其中较为突出的是上海市广电局,打破一个电视台一个电台的垄断局面,于1982年成立了东方电视台与东方广播电台,与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都是独立的法人,开展业内竞争,此举向专业化方向迈出了关键一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2.适度放权,广播电视媒介改革迭起
1997年9月1日,新中国首部《广播电视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条例》以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集广播电视宣传工作、事业建设和行政管理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1998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我国广播电影电视开始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改革:广播电影电视部改组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属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不再作为广播电视宣传机关和电台、电视台经办主体,主管全国广播电影电视事业,适度放权,“办”的职能被淡化,而“管”的职能被强化。国家机构改革后,全国省级广播电影电视管理机构也进行了相应改革 。
这一阶段,由于适度放权管理带来的效应,媒体改革盛况空前。自1999年6月广播电视集团化改革开始,到2004年全国共有21家广播电视集团成立。广播电视媒介组织还进行了频率频道改革、三项制度改革及经营性单位转企改制。从2002年起,中央电台启动了以“频率专业化、管理频率化”为核心的媒介改革,推出了《中国之声》《音乐之声》《民族之声》等8个专业化频率,全面启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实行全员聘用制,竞争上岗、按劳分配、按岗取酬。中央电视台从1993年开始,推行制片人制,先后创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现在播报》等节目,影响力扩大。从2000年开始,先后在英语频道、经济频道、西部频道和戏曲频道进行频道制管理改革试点,并实施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全面推行全员聘用制。2005年前后,又对体育频道、少儿频道进行频道制改革。而从2006年开始,所属经营性单位转企改制。全国广播电视媒介也先后进行了上述三项制度的改革。
1996年,国家广电总局首次明确提出电视节目除新闻节目外实行制作和播出分离的指导意见。但业内有不同认识和争论,制播分离改革停滞不前。2009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正式出台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制播分离积极稳妥地推进。
3.管办分离,广播电视媒介回归本体
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我国的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2013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合并,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加挂国家版权局的牌子。与此相适应,全国除少数几个省市外,也都组建了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局。
2018年3月,21世纪新一轮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改革开始,《国务院深化机构改革方案》强调,为加强新闻舆论工作,加强对重要宣传阵地的管理,充分发挥广播电视媒体的作用,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新组建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管理职能的基础上进行了“瘦身”,不再领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将原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电影和新闻出版的管理职能划转出去。此轮改革,管办分离,广播电视媒介回归本体,行业管理成效明显。省市区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广播电视台的改革已于2019年上半年全部完成。
三、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演进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前广播体制的四次调整,改革开放后广播电视体制的五轮改革,有如下特色。
(一)“中枢神经系统”与国家“脉动”的同步
广播电视是社会的中枢神经系统,是一种敏感的时间媒介,讲究时间的快捷,需要高效运行的媒介组织,这种媒介组织的高效又集中在管理层级的高效运营上。新中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演进,不断踩准国家的“脉动”,适应了时代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这表明广播即刻与国家经济建设紧密相连。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广播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宣传的中心。”从新中国成立第一天起,广播与国家密切结合,这是一种高度“适应”,也是广播人的重大历史使命。当天中央电台进行的盛大直播,则塑造了新中国“站起来”的国家形象,并开广播媒介政治传播、领袖传播、大型直播之先河,同时确立了大国广播播音风格。1957年,国务院开始了以扩大地方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央广播事业局具体落实,推动了广播事业的快速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广播管理体制的四次调整,改革开放后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五轮改革,都与国家的总体调整、改革相向而行,从而改革较为顺利。
(二)先“头部”后“身部”的全国范围全覆盖
欧美国家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大致分为两大类:国家垂直独立性政府管理机构;地区/社会联合自治性管理机构。苏联广播电视体制分为三级:中央级、加盟共和国级和地方级,实行国营广播电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虽然可以借鉴世界广播的文明成果,但国情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无法照搬其体制及运行机制。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当天,“头部”层级由副局长兼任中央电台总编辑、第一第二副总编辑,局台合一,局台下辖编辑部(组),这在行政管理体制、广播媒介管理体制上为“身部”——全国省市县广播管理机构和广播媒介引了路。之后,全国省市广播媒介也都设置了总编辑,负责电台宣传等事务,下辖编辑部和组。这样,广播管理机构和媒介组织形成了三级负责制,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不断进化。
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先“头部”后“身部”的做法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尽管它存在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因为它要保持稳定性、系统性及普遍性,这不同于广播电视媒介组织某一方面业务的调整。
(三)“条条”“块块”结合的内生管理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在不断演化中,摸索出了“条条”“块块”结合的组织架构。这种组织架构符合新中国广播电视行政管理规律,是一种内生的管理体制。1949年11月广播事业局组织条例规定,广播事业局的职责是:领导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直接领导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国内和对国外广播;普及人民广播事业。1983年3月,第11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各级广播电视机构之间实行上级广播电视部门和同级党委、政府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英国,而是给地方分权,既充分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也减轻了国家财力的负担。
(四)按广播电视规律办广播电视
新中国70年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演进,带来了广播电视新闻思想、新闻规律的自觉。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电台在开国大典的播音叙事中,创造性地确立了庄重、朴素、亲切、自然的播音风格。而播音,本身包含着“二度创作”,因而,“声音传播”与“文字传播”甚至后来的“声画传播”有本质区别。1950年4月,中央电台进行节目调整,设置七档新闻节目,两档《记录新闻》,还设置了一档评论与《首都报纸摘要》。七档新闻与两档《记录新闻》有自采新闻与“报纸摘要”,但《首都报纸摘要》则全是首都报纸的新闻加评论,广播媒介作了大量删削,融入口语,变成声音新闻,这种口语化的声音新闻播音风格已经转向,再不是战争年代每一次播音都是一次战斗,强调气势、激情、调子、音量,而是转向新中国广大听众适应的语态:庄重、朴素、亲切、自然。虽然报纸新闻的身影仍然存在,但用当代叙事话语来说,这已经是一种“融合新闻”,即声媒与纸媒的融合。尽管那时还没有媒介融合的理念,但在笔者看来,这是新中国媒体融合最初形态,也是新闻思想自觉与新闻规律自觉。但十年浩劫,“四人帮”控制舆论,广播媒介只能播纸媒的文章,而且必须全文播出,不得删减。这个时期,广播媒介整体沦为了报纸的有声版,也无法做到新闻思想自觉、新闻规律自觉。
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诞生,标志着电视在中国的起步。口播新闻始于1958年11月2日,初期称“简明新闻”,每次5分钟,文本由中央电台供给,这也是初始的广播与电视的融合。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省市电视台相继成立,大多采取图片报道、口播新闻的方式,采用新华社稿件及广播媒体供稿。但就在这样一种媒介环境下,电视台还参与了全国两会以及重大事件如原子弹氢弹爆炸、人造卫星的发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以及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先进典型的宣传。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彩色电视技术日趋成熟,电视夺走大部分广播听众,广播媒介直面挑战,不畏艰难。1955年,随着音乐排行榜节目《最佳40首》的兴起,音乐类型电台出现,将音乐的概念与广播的概念融合在一起,继而又产生细分市场、细分受众、音乐编排、时钟编排等概念。1965年4月19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全新闻电台。“全新闻电台这种形式就是全天24小时都滚动播出新闻节目,不设谈话类和音乐类节目,打开收音机就是新闻。”新闻的概念与广播概念结合在了一起。从此按广播规律办广播形成高潮。
与新中国早期的电视一样,美国早期的电视节目多是图片,观众由此给电视取了个绰号:带图片的烤箱。这个烤箱烤出来的“食物”总是不能引起观众的“食欲”。1980年,有“南方的喉舌”之称的泰德·特纳(Ted Turner)创办了有线电视新闻网CNN。CNN头条新闻24小时不间断地播报新闻,它的视野是全球化——从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向全球播报新闻,而且新闻报道现场化。这种非凡的活力和反应速度凸显了电视媒介新闻产品的别具一格,带图片的烤箱变成了“视频滚动的烤箱”。CNN的诞生,使一些关键概念扎堆产生并在世界流行:24小时滚动新闻、头条新闻、直播、纯新闻电视频道、图像记者等。这些观念影响了世界,也影响了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广播电视。
1983年3月31日,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与前10次会议有所不同,加了“电视”二字,标志着“电视”纳入治理范畴。会议提出“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和“扬独家之优势,汇天下之精华”方针,是广播电视新闻思想、新闻规律的再度自觉,极大调动了广播电视人的积极性,释放了广播电视人的潜能。1986年12月15日,改变广播传统语态、形态、媒介组织结构的广东珠江经济广播电台诞生,之后又出现专业化电台、类型化电台,广播媒介走上了按广播规律办广播的路径。中国电视改革也应该视1983年为元年:《春节联欢晚会》创办于该年,至今已有37年;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电视新闻杂志节目《九州方圆》也诞生于该年。而10年后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东方时空》等节目,改变了电视的叙事方式,亲切自然、平等交流的“说话方式”被越来越多的观众接受。1978年元旦定名为《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后简称《新闻联播》)的新闻节目将新闻概念与电视概念结合在一起,使“电视新闻”在新中国安营扎寨,电视人由此也树立了新闻职业意识,这种职业意识包含电视专业化、电视类型化。有研究者对《新闻联播》1999年11月8日至14日,2000年11月13日至19日的样本进行分析和研究,“将新闻的时效分为五类:今天、昨天、最近、无时间、将来。‘今天新闻’是在新闻中明确使用了‘今天’这个时间状语,其数量最多,共有141条,占新闻总数的45.5%”。这说明,《新闻联播》的时效性大大加强。同时,同期声的运用也有了很大进步,新中国电视走上了按电视规律办电视的媒介路径。
(五)职能进化伴随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历史进程
职能属性是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广播电视媒介组织的根本属性。时代不断向前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广播电视行政管理机构、广播电视媒介组织职能具有变动性,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及职能配置使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广播电视媒介组织权责一致,不断进化,是广播电视发展的应有之义。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媒介组织作为制度的载体,不但要回应现实关切,满足现实需求,更要关注未来,面向未来,管根本、管长远。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中央广播事业局一直承担宣传和管理双重职能,这与计划经济吻合,由此形成了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局面。1982年,国家机关实施改革开放后的首次机构改革,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广播电视部,除了克服组织臃肿的问题,还解决了人员老化、平庸的问题。这期间提拔使用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1984年10月,为适应新闻改革的需要,中央电台组建了新闻中心。1986年的机构改革,增强了宏观管理职能,淡化了微观管理职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逐步进化。1998年的改革,仅保留了原广播电影电视部的事业管理机构职能,不再沿袭新闻宣传机关的职能。与此相适应,广播电视媒介组织加强了总编辑制,实施干部聘任制,进一步推动广播电视媒介干部的年轻化。2013年的行政管理机构改革,深化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201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新组建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不再领导新组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此轮改革中与国家广电总局、人民日报社平级,广播电视回归了本体地位。这是70年来我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最大的一次进化,使我国广播电视事业行业管理和事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六)技术驱动广播电视体制持续变革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体,有专家一次又一次预言:广播将消亡。而互联网出现后,有研究者也认为电视将消亡。但是,广播抗风击浪,一再浴火重生,电视也求新求变、屹立不倒。这是为什么呢?因素很多,技术驱动是其中之一。广播科学技术从调幅、调频到立体声调频,从地面数字、卫星数字再到网络数字,电视科学技术从数字电视、网络电视、IP电视、移动电视、手机电视、高清电视到超高清电视,每次升级都在推动广播电视体制观念、运行的变迁。
1950年4月,政务院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把抄收中央和地方电台广播的记录新闻、向群众介绍预告广播节目、组织群众收听重要节目作为三项重要任务。中央广播事业局、全国各地电台迅速行动,在技术上创新,支持、辅导和帮助收音站,“据1952年底统计,各地共建广播收音站23700多个,收音小组数以万计,专职或兼职的收音员两万多名”。从1952年开始,人民广播事业大力发展农村广播网,到1956年6月底,全国已有783个县市农村有线广播站。由于这个时期全国电台技术人员增加,1956年2月2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村广播网管理机构和领导关系的通知》。《通知》除规定广播事业局设一相应机构负责全国农村广播网建设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可设立广播管理局或处,负责全省(包括城市效区)农村广播网的建设,并管省属市的人民广播电台。技术的扩展、升级,带来体制机制的变迁。随着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广播事业局变为广播电视部。与此相适应,广播电视科技司、科技委员会相继成立,并设置总工程师及技术办公室。媒介融合时代,媒介融合机构增设。受技术驱动,广播电视体制处于持续变革中。
四、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演进的本质
新中国70年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变迁有其内在规律,其本质如下。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新中国广播电视实践相结合
美国和意大利政治科学家丹尼尔·C·哈林(Daniel C.Hallin)、保罗·曼奇尼(Paolo Mancini)合作推出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与政治的三种模式》(2004),是在三个美国学者西伯特(Sie bert)、彼得森(Peterson)和施拉姆(Schramm)的《传媒的四种理论》(1956)闻名遐迩之后出版的,该研究探究政治与大众媒介结构的关联性,提炼出媒介体制的三种模式:“自由主义模式,盛行于英国、爱尔兰和北美;民主法团主义模式,盛行于欧洲大陆北部;而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盛行于欧洲南部地中海国家。”另有研究者认为,美国广播电视体制变迁,是从“公共委托模式”到“市场模式”。新中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与上述几种模式都不同,原因是新中国广播电视体制具有内生性与原发性,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我国广播电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与其他国家的跟进与模仿有本质区别。1954年7月到9月,中央广播事业局曾组织由18人参加的中国广播代表团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广播工作经验。同年10月编印《苏联广播工作经验》书籍并发行,11月在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学习苏联广播“集中统一”经验,实质性内容是要求各地方台用比较多的时间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用比较少的时间播送自办的地方性节目。这次“媒介朝觐”学来的经验,导致地方台节目纷纷下马,严重削弱了地方广播媒介的传播作用。两年后,第四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应该加以否定”。实践说明,新中国广播电视要借鉴世界广播电视的文明成果,但绝不能照搬照套。新中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演进,是长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广播电视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层级、结构、职责、经办权、所有权不断进化,特别是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台由广播电视管理部门实施行业管理、各级宣传部直接领导,作为国务院和地方政府的直属机构。这些演进举措,都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广播电视实践的有机结合。
(二)始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播电视管理机构、媒介组织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也是广播电视体制改革、调整的最终目的。中央电台前身——延安电台在纪念恢复本台广播一周年之际,在播出的《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一文中重申:“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一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强调了电台的人民性。调整、改革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办好节目,抓好覆盖,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收听收看好广播电视。新中国成立之初,刚刚“站起来”的人民群众还无能力购买昂贵的接收设备,我国电子工业初创,也生产不出大量的收听工具,全国新闻工作会议认为为广大人民服务,应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1950年4月,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到1952年底,全国已建收音站2.05万个,农民群众敲锣打鼓,集体收听广播,一部收音机就有几百人收听,不得不排队进行。之后又发展农村广播网,再经过一系列覆盖工程,至2018年底,全国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进入世界先进广播电视行业行列。这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最真实的写照。
(三)始终以广播电视的发展为要
从新中国成立70年的历史进程看,广播电视管理体制的演进做的都是发展的工作。这种发展实践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从“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到“发展电视”再到“发展人民广播电视事业、建设完善的广播电视体系”理念的提出,从建设“广播收音网”到“建设农村广播网”,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体制进行的五轮改革,以及秉承科学发展、新发展理念,改革广播电视管理体制、媒介组织结构,强化协调、分工、行业管理和所有权的分离,大规模改进节目形态、语态,推进一系列建设工程及媒介融合的实践,使新中国建立了完善的广播电视体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节目。广播电视走进了“千家万户”,无处不在,这些都是发展的结果。
注释:
① 数据参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18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http://www.nrta.gov.cn/art/2019/4/23/art-2555-43207.html,2019年8月6日。
② [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③ 邵培仁、刘强:《媒介经营管理学》,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④ 谢雅玲:《媒体发展新格局下县级广播发展探究》,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34页。
⑤ 陈万达:《媒介管理》,杨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36—38页。
⑥ 左漠野:《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⑦ 李勋岳:《建国前后职业报人的困境及出路》,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0页。
⑧ 卢德武:《西康人民广播电台研究(1951~1955)》,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0页。
⑨ 涂昌波:《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发展政策演进初探》,《现代电视技术》,2009年第10期,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