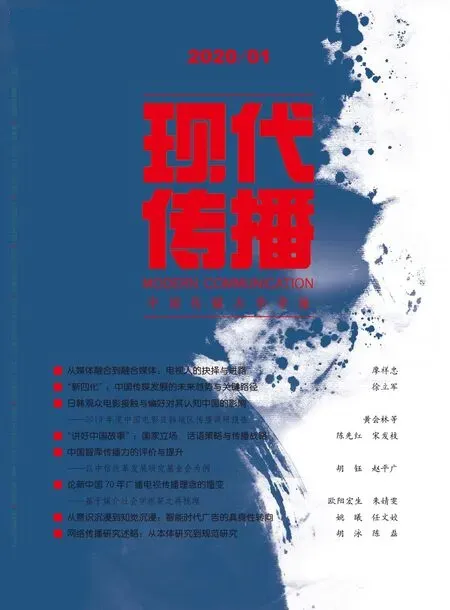“电影眼”的新启示:吉尔·德勒兹之“纯粹感知电影”的创造逻辑
■ 徐 辉
一、问题的提出
在电影界,无论是从事一线创作的人,还是致力于理论思考的人,对于吉嘉·维尔托夫所提倡的“电影眼”都不陌生。尤其是人们在谈论经典纪录片时,难免会想到“电影眼”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目前人们基本还停留在“客观地看”这个层次上。换句话说,理论研究者在谈对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的理解时,强调的基本都是:排除人的主观因素而客观地记录。
但是,当人们想到摄影机总是由摄影师所操作时,想到所拍摄的影像必定属于主创人员之所选择时,这一理解就会受到质疑,因为只要有人参与其中,就不可能做到“客观地看”。具体地说,人们不可能毫无选择地拍摄纪录片,制作中一定会有选择。那么,谁来选择呢?当然是主创人员,很大程度上是摄影师。既然如此的选择必不可少,那就意味着主创人员的主观意志必然已经参与其中。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可能做到客观地看呢?怎么可能排除人的主观因素而客观地记录呢?与此同时,在纪录片创作领域,目前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纪录片创作能不能“摆拍”?如果说能,那显然不够“客观”;如果说不能,则又和实际的创作相悖,因为很多优秀的纪录片中都有摆拍。退一步讲,很多优秀的纪录片都融入了主创人员的主观意志,或者说,任何影片都是主创人员主观努力的结果,维尔托夫自己的影片也不例外。这样看来,人们从来就没有按照“客观地看”的要求去工作。另一方面说,人们又无法否认这样工作做出来的纪录片是优秀纪录片。这样的话,就又出现了“电影眼”理论是否已经过时,在纪录片创作中究竟该不该按照“客观地看”来做等一系列问题。
以上问题,不但是困扰创作领域的问题,而且也是困扰理论研究者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重新将“电影眼”视为一个问题再加以审视、研究。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需要重视一个全面系统地思考电影的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相关观点。在他的电影学著作中,他对维尔托夫的这一著名观点进行了独到的阐释,从而使得这一观点重新焕发了生机,呈现出对于纪录片创作乃至对整个电影创作的崭新启示。本文试图在阐明德勒兹对“电影眼”之新阐释的基础上,结合他有关“气态感知—影像”的思想,谈谈“纯粹感知”之本然运行逻辑对电影创作的启示。
二、“电影眼”与“纯粹感知”
我们知道,“电影眼”是维尔托夫的著名概念,也是一个著名的电影创作理念。按照这个理念,维尔托夫留下了自己的经典影片《持摄影机的人》。吉尔·德勒兹在研究电影的时候,对这一电影创作理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精彩的阐释,形成了“纯粹感知”的概念。这一概念,同样意味着一个电影创作理念,并且和维尔托夫的理念有着内在的相同之处。具体地说,在德勒兹看来,维尔托夫的“电影眼”,指的是“物质眼”,也就是说物质本身拥有的、只属于物质的“眼睛”。①
1.“物质”会“看”
对于日常的我们来说,说物质拥有自己的眼睛,这显然是有问题的。物质怎么会有眼睛呢?这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常识,甚至有些痴人说梦的味道。然而,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很深刻的说法。阐明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德勒兹关于“物质”的思想谈起。
在德勒兹看来,物质不是死的、无生命的东西,相反它是活的,拥有自己的生命。用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说就是,凡是有点物理学常识的人,都会承认物质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此的相互作用等于承认物质微粒能够“接收”到来自其他物质微粒的“作用”,并能对之发出“反作用”。这便可以说明,物质微粒既有“感知”其他物质微粒的能力,也有对其他物质微粒施加影响的机能。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能根据日常的习惯而说物质是死的、没有生命的吗?显然不能!反倒是我们应该承认,物质拥有自己的生命,它总是“有生命的物质”②。既然如此,那么就必须承认,物质也会“感知”,从视觉维度说,就是物质也会“看”。因此,物质拥有自己的“眼睛”。
受柏格森等人的影响,德勒兹对生命问题极为关注。在谈到感知这一生命机能的时候,他主张我们当从两个不同的层面看,即日常层面和纯粹层面。就日常层面而言,感知即我们平常所谓的人类的感知;就纯粹层面看,感知则是物质的感知,即上面所说的物质微粒的感知。具体到视觉这个维度上,“看”也必定有两个不同的层面,即人类眼睛的看和物质眼睛的看。前者可以称之为日常性的人类的看,后者则是物质微粒的看。应该说,这属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但有趣的是,阐明这一点时,他结合的恰恰是电影。
2.“物化的摄影师”
我们清楚,电影呈现给我们的影像,总会有固定镜头、移动镜头和蒙太奇组成的片断(整个影片)。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摄影机拍摄出来的,也就是摄影机“看(感知)”到的。摄影机没有“看(感知)”到的事物而出现于电影中,这是不可想象的。据此,他主张所有的电影影像在最为基础的层面上都是“感知—影像”③。进而,摄影机的“看(感知)”,显然就是物质的“看(感知)”,因为摄影机是一个机器,当属于物质。就是在此,我们遇到了一开始就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按照我们的日常思维,摄影机的看,最终取决于摄影师。摄影机的观看,其实是摄影师的观看,摄影机不过是摄影师的一个工具,是摄影师通过摄影机在观看。摄影师才是真正的看者,即感知者。如果是这样,怎么能说摄影机的看,就是物质的看呢?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的确,对此我们说,操纵摄影机的永远是摄影师,是人。但作为摄影师的人,他有一个按照什么事物的观看逻辑让摄影机看的问题,或者说作为摄影师的人,有一个按照什么事物的观看逻辑通过摄影机看的问题。例如,摄影师是按照人的观看逻辑让摄影机看,还是按照物质的观看逻辑让摄影机看?是按照人的观看逻辑通过摄影机看,还是按照物质的观看逻辑通过摄影机看?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是前者,那么摄影机是人化的摄影机,但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就必须看到,此时操纵摄影机的摄影师则是物化的人。换句话说,此时的摄影师是站在物质的立场上,或者说是将自己化为物质来操纵摄影机、通过摄影机在观看。维尔托夫的创建正在于此。他主张排除主观而强调彻底的客观,毫无疑问走着一条将作为摄影师的自己物化的道路。在他那里,作为“人”的维尔托夫,其实是和摄影机同化的人(摄影师),他其实是在作为“物质—人”而存在、感知。换句话说,他和摄影机在物质层面上合二为一,都在按照上述物质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逻辑进行观看,进行感知。简言之,此时的维尔托夫作为摄影师,是一个“物化的摄影师”。此时此刻的“感知”,就是德勒兹所说的“纯粹感知”。
就此而言,用“客观地看”来理解维尔托夫的“电影眼”就显得不够准确。准确的理解是:“电影眼”即“物质眼”,它有一种不同于人类眼睛的观看(感知)方式。“电影眼”理论要求我们按照这样一种有别于人类眼睛的“观看(感知)”方式来拍摄影片,即按照“纯粹感知”的方式来拍摄影片。
在此,我们顺便可以回答一开始提出的影片拍摄中必然存在主观意志而不可能做到纯粹客观的问题。实际上,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理论,从来就没有否定在拍摄影片上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从来就不主张在这个过程中排除主观意志。甚至可以说,他还应该主张这样做。只是做的维度,或者说努力的方向不同于日常人们的理解:我们需要竭尽全力做到让自己“物化”、物化为摄影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按照物质微粒的观看方式,即按照“纯粹感知”的方式,来制作我们的影片。
3.纯粹感知的特点
那么,纯粹感知和日常感知有什么差别呢?最为核心的差别在于有无“中心”。在德勒兹看来,日常感知是有中心的,典型的就是人类的正常感知。人类的感知,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围绕一个中心在运作。从观看的角度说,这个中心就是我们平时观看的目标。例如,我们到一个人群纷乱的场合去找我们的一个熟人,这个时候我们的观看注意的只是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在这个中心的作用下,我们会将其他人予以忽视。如果我们回想这个找人过程,那么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我们承认自己看到了很多人,但在自己的脑海中却根本没有印象,其中甚至包括同样是自己熟悉的人。这就充分说明了,我们日常的观看,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的,仅仅选择了我们感兴趣的事物,而忽视了那些非中心的、我们不感兴趣的事物。应该说,这就是我们人类感知或者说日常感知的真相:在我们实际感知到的多种事物中,只将我们所关心的事物保留在自己的意识当中;我们关心的事物即我们感知的中心。严格说来,这并非观看或者说感知的原初真相。从原初的角度说,真正的感知,反而是物质的感知——它毫无选择地和任何的他物进行着交互作用,片刻不会停息。它的感知是全面的,不会忽视任何东西。根本地讲,物质的感知是无中心的,是绝不会漏掉任何事物的“全面感知”,即“纯粹感知”。
简单地说,所谓“纯粹感知”,即“有生命的物质”的感知是一种“无中心”的、时刻不会停息的“全面感知”④。
三、纯粹感知的呈现
阐明了何谓纯粹感知,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怎样将之影像化而呈现出来。如果说逻辑地将之说明是哲学的问题,那么将之影像化而呈现出来则是电影创造的问题。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德勒兹有关“感知—影像”的观点说起。
按照德勒兹的逻辑,电影是一个有生命的影像,我们所知晓的各种生命机能它都拥有⑤——其中就包括感知、情感、冲动、行动、思想、回忆等。当电影这个有生命的影像突出地呈现它的感知之际,它就会化身为感知—影像⑥。就感知而言,此时此刻电影这个影像所呈现给我们的,主要是“它”看到的事物。站在观众的立场上,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影像呈现给我们的它自身感知到的事物。例如,很多电影的开头是交待环境的空镜头,它呈现给我们的仅仅是一些自然或者城市风光。此刻,我们从这些风光影像中还看不出会发生什么故事,也就是电影的故事还没有展开。电影影像在此刻就是感知—影像,它在呈现着自身感知到的事物,并且仅仅是在呈现自身感知到的事物。从生命呈现来说,此刻的电影作为一个影像,便是在呈现自身的生命机能之一,这就是感知。在这里,“感知”便获得了影像化。
不过重要的是,感知获得影像化,或者说将感知影像化的具体方式。对此,德勒兹区分了三种情况,并将不同情况下的影像分别称之为“固态感知—影像”、“液态感知—影像”和“气态感知—影像”。
1.固态与液态:日常感知的呈现
“固态感知—影像”和“液态感知—影像”分别对应的是固定镜头和移动镜头的感知—影像。例如,电影在交待故事展开的环境之际,呈现出来的可能是一组属于固定镜头的空镜头——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就经常如此。对于这一组风景空镜头,它们都是在呈现影像的感知,呈现影像感知到的事物,因此皆为感知—影像。但由于这些镜头是固定的,因此每一个镜头都意味着一个固态感知—影像。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影像的感知方式看,它等于是在用一个固定的视角看它呈现给我们的事物。简单地说,电影影像在盯着这些事物“看”。如此仅从感知来说,那么我们就应该能够理解,此时此刻影像凸显出来的是电影这个有生命的影像的固定不变的感知,或者说它的感知方式是固态的。正是据此,德勒兹将此时的感知—影像称为“固态感知—影像”。
相应地,交待环境的镜头有很多是移动镜头,那么它作为感知—影像的感知方式就属于另一种情况——此刻的影像相当于在移动着观看,不断地变换着自身感知——也就是观看的视角。很显然,这个时候影像的感知就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相反它一定是变动的、流动的。简单地说,它是在变动地看,并呈现着自身感知的流动状态。据此,德勒兹将之称为“液态感知—影像”。
应该说,这两种影像方式完美地呈现着“固态感知”和“液态感知”。如果从影像创造的角度说,这意味着两种创造感知—影像的方式,即按照固态感知自身的运作逻辑,我们可以创造出固态感知—影像,按照液态感知自身的运作逻辑,我们可以创造出液态感知—影像。这就是发挥观看作用的固定镜头和移动镜头。严格说来,这两种情况都和人日常的感知方式是吻合的。当我们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盯着某种事物观看的时候,我们的感知就是固态的,在我们脑海中呈现出来的画面就是一幅固定镜头式的画面;而当我们走着,或者开着车观看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浏览,此刻的感知就是流动的、液态的,在我们脑海中呈现出来的画面就是一个移动镜头式的画面。因此,要呈现人类日常的感知,这两种方式足以胜任。
然而,正是因为和我们人类日常的感知方式相类似,在德勒兹看来,这两类影像所呈现的感知都还不是他所谓的“纯粹感知”。之所以不是“纯粹感知”,原因就在于这两种感知方式,都是有中心、有选择的,都不是“全面感知”。盯着看的情况自不必说,浏览同样是有中心、有选择的,不可能是全面的。当然,这里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识地、主动地浏览,另一种是无意识地、不得不进行地浏览。前者如我们搭乘观光列车看沿途的风景,后者如我们坐着高铁无意识地,有的时候是不得不观看车窗外的风景。就前者而言,这样的观看、浏览,因为是主动的行为,当然是有中心的、有选择的——其中心就是观看的目的。而从后者看,我们似乎没有了这样一个主动的、有意识的目的,然而必须清楚,这样的被动浏览不可能逃开列车车窗对我们的限制——例如,我们不可能看到列车正上方的风景——这样的限制,就意味着如此的观看必定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的,这个中心就是我们无意识中选择的、车窗规定的范围。因此,不论是哪种情况,感知都不是全面性的“纯粹感知”,都不可能像一个物质微粒那样,全面地和宇宙间的所有物质微粒进行互动,感知到宇宙间所有的事物。那么,是否还有按照纯粹感知的运作逻辑,将之影像化的途径呢?当然有!这就是德勒兹所谓“气态感知—影像”的方式。
2.“纯粹感知电影”
所谓“气态感知—影像”,已经不能仅仅从镜头看,而需要将整部影片视为一个、仅仅一个影像。或者准确地说,将影片中镜头间的衔接,视为它作为唯一影像的视角转换。这部影片我们称之为“纯粹感知电影”。我们关心的纯粹感知的呈现,就在这里成为可能。
在此,我们需要提到一种影片,最典型的便是罗恩·弗里克(Ron Fricke)的《轮回》(Samsara)和《天地玄黄》(Baraka)。可以说,这两部电影从头到尾都是由一些美轮美奂的风光影像组成的,其中根本没有故事片意义上的故事。应该是因为没有故事,所以人们习惯于将之归入纪录片的范围。这当然不错。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作为纪录片,这两部电影和其他的例如弗拉哈提的纪录片是不同的。例如《北方的那努克》还是有一个爱斯基摩人生存的故事在其中的,但罗恩·弗里克这两部电影却完全不照顾故事性需要,丝毫没有故事可言。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罗恩·弗里克这两部电影究竟是在干什么?站在纪录片的角度,人们当然可以说它的目的就是纯粹记录。这没错,但深入地看,我们则应该说,如此的纯粹记录所记录的,一定是感知——单纯的观看。整部影片作为一个影像,只是对如此观看(感知)的呈现。按照德勒兹“感知—影像”的观点,我们首先可以将这两部电影称为“感知—影像”。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问,这里涉及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知方式?无疑,如果从镜头的角度说,人们仍然可以说这两部影片中存在着两种感知方式,即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固态感知方式和液态感知方式,因为其中的镜头不是固定镜头就是移动镜头。然而,如德勒兹所提示我们的那样,电影制作除了镜头之外,千万不要忘了还有蒙太奇(剪辑)。如果我们从蒙太奇的角度,尤其是从整部影片的诸多蒙太奇的角度看,那么我们立即就会看到,其中包含着多次的“切”。如果我们能够将整部影片理解为一个唯一的有生命的影像在观看,那么这每次“切”就必定被理解为“视角转换”。如此一来,我们应该还能发现:如此的视角转换奇快无比。人在作为日常的人之际,其视角转换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达到如此之快,或者说人绝不可能如此快速地转换视角。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必须承认,如此之快的转换的视角所涉及到的观看,已经不属于人类。从感知来说,这里有一种非人的感知在运作。进一步说,此时此刻,电影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影像所呈现出来的自己的感知已经不是人类的感知;它所呈现出来的观看,已经不是人类的观看;它用来观看(感知)的眼睛,已经不是人类的眼睛。用维尔托夫的术语来说,此刻的电影只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在看,它的眼睛就叫做“电影眼”。
回到视角的快速转换,我们应该追问:宇宙之间什么东西会如此快地转换视角?答案:物质微粒!应该说,这个答案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物质微粒同时感知着宇宙间所有的事物,它用着一只可以同时观看所有事物的眼睛在看、在感知,根本没有视角转换问题。然而,如果从“呈现”的角度说,那就需要有一个顺序问题。或者说从将物质微粒的感知影像化呈现的角度分析,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这里必须有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我们需要将电影做成一个先呈现什么、再呈现什么、后呈现什么的线性影片。那么这样的顺序怎么排呢?答案是:极限性地接近物质微粒的感知方式,即尽可能地接近对所有事物的同时性感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上述的“切”。同时,这也是呈现“纯粹感知”的唯一途径。如此一来,被构成的电影因为以影像的方式呈现着纯粹感知的本然运作状况,所以我们将之称为“纯粹感知电影”。
四、“纯粹感知电影”的创造
实际上,在上面讨论将纯粹感知影像化之际,我们已经涉及到了纯粹感知电影的创造问题。只是,上述“极限性地接近物质微粒的感知方式”只是一个总的原则,具体的创作方式还需要在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解释。如果说为下面谈到的创作方式起一个总的名称的话,那么就应该叫作“电影眼的启示”。
“电影眼”即“物质眼”,全面性地感知一切是它本然的感知方式。在明确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结合取镜、分镜、蒙太奇这三个彼此交叠的电影制作环节来谈纯粹感知电影的创制方式。
1.去故事性与去人类性
所谓去故事性,指的是决不让日常意义上的故事形成。无论是《持摄影机的人》,还是《天地玄黄》《轮回》,都丝毫没有什么故事性。也就是说,从那里,我们根本看不出一个日常意义上的有情节的故事。应该说,这是纯粹感知电影有别于一般的故事片,也有别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的一个突出特色。之所以如此,理由其实很简单:一旦我们能够从其中看到一个日常性的故事,那么电影影像就一定在讲述着人类学层面的事情,而未到物质性层面。或者准确地说,物质性层面已经潜隐,日常意义上的故事已经突出。
当然,我们需要说明:故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一个是从日常角度,一个是从宇宙论角度。如果从前者,那么故事的内涵便是人类生活层面上的事情。例如当今的故事片,几乎都是在讲述关于人类生活的事情,上述《北方的那努克》之类的纪录片也是如此,它讲述的是一个人类生存的故事。但如果从后者来说,那么则意味着故事是宇宙论层面上的事情,也就是说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就是一场无始无终的故事。不过,这个意义上的故事,讲述的显然已经不再是人类生活层面上的事情,而是宇宙本身的事情。简言之,如果人们愿意从宇宙本身出发认为故事就是这个意义上的故事的话,那么纯粹感知电影里也有故事。只是人们一般不会这样理解,相反人们理解的故事一般指的是日常意义上的故事。我们在此强调纯粹感知电影的去故事性,是从日常故事方面来说的。
不过,这里还需要提示一点:诸如《动物世界》这样的,也可以归于纪录片的影片,并不是纯粹感知电影,因为它已经用一个日常性的故事整合了影片,只不过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动物,或者说是人化的动物——动物的行为已经被人化了。
与此不同,纯粹感知电影那里遵循的是相反的道路,即影片的人被物化了。我们在《持摄影机的人》《轮回》那里,无疑能够看到人类,但那里的人类已经被等同于一个物质性人,用德勒兹的话说就是“分子儿童”“分子女性”等⑦。当人观看这样的电影的时候,很容易就能发现,这样的电影中是没有台词的,或者说里面的人是不说话的。按照我的理解,这并不是人不说话,而是他(她)作为物质性的人、与物质等同的人,根本就不能说话、不会说话。这就是所谓去人类性,即将人类还原成物质微粒,只作为物质微粒出现在影片中。
2.断裂性和异质性
与前面的去故事性、去人类性相应,所谓断裂性指的是为了不让日常意义上的故事形成,而及时打断电影的连续性。习惯于将一切都理解为人类世界之现象的观影者,总是能够从一幅画面中构想出一个日常意义的故事。例如,当我们看到《轮回》中那场熟悉的佛教舞蹈画面时,立即就会联想到与之相关的故事。但很快,电影就将这场舞蹈给截断了,而不是让它长时间地,或者说完整地呈现。它仅仅是截取了这场舞蹈的一个片段。这种做法,便是在坚持断裂性原则:决不能让日常意义上的故事形成,绝不给观众从某个影像那里构想出一个日常故事的机会。当然,这个片段对于没有完整地观赏过这个舞蹈的人来说,或许不会像观赏过它的人那样很快就联想到相关的故事,但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同样能够构想出一个日常性的故事。纯粹感知电影的制作,恰恰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不遗余力地剥夺人们构想日常故事的机会。深入地看,这里的所谓“剥夺”,其实是一种启迪:让人们脱离人类日常的层面,而深入到更深的纯粹层面。为此,它的制作必须坚持断裂性原则。
与之相关的,是异质性原则。所谓异质性,指的是影片摄取的影像,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例如在《轮回》中,前一个镜头是有关佛教的画面,紧接着而来的一个镜头便是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画面。或者说前一个镜头是宗教性的,接下来的一个镜头则是自然风景。从镜头之文化内涵上看,这里出现的是将很多在文化内涵上根本没有关系的影像并置在一起。这就是所谓异质性。坚持这个原则的目的就在于不让人们将注意力过多地置于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上。我们知道,目前已经很难找到纯粹自然的东西,几乎一切都已经文化化了。然而,面对《轮回》之类的纯粹感知电影,观影者要想从文化内涵上来理解画面的话,那么他能够看到的只能是很多的异质文化被并置到了一起,或者说他只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文化的片段。这样的片段不可能给予观众完整理解相应文化的充分时间,因为它只是片段,当人们刚刚要展开对相应文化的理解时,这个片段就过去了。可以说,这里没有给予人充分理解画面关涉到的文化内涵的机会。应该说,这和上面决不给予人们构想故事的机会是同样的逻辑:将一切都还原到物质层面上。上述的宗教性镜头,在这样的电影中,也仅仅相当于一个纯粹物质性的自然风光镜头。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坚持异质性这个原则,否则的话,观众将会从文化角度来理解画面,而不是从物质微粒角度来理解画面。若此,就意味着纯粹感知电影的失败。
当然,对于断裂性和异质性,我们还需要说明,这仅仅是站在人类日常层面上讲的。上面所谈到的断裂是日常故事连续性的断裂,异质是日常文化内涵的异质。但如果我们转换一下立场,站在物质微粒的角度来审视,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既没有什么断裂,也没有什么异质。这里没有日常故事的连续性,但物质微粒之间持续的交互作用却始终是连续的,从未断裂,也不可能断裂。进而,物质微粒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永远是同质的,不可能出现异质性。⑧深入地看,纯粹感知电影正是要通过上述断裂和异质,让日常故事、人类文化意义上连续性退场,让物质微粒在交互作用层面上连续性出场。说到底,上述已经阐明的纯粹感知,从来就没有间断、断裂过。
总而言之,站在人类日常的角度,我们说纯粹感知电影中,需要实现空间上跨度非常大的画面并置。例如在《持摄影机的人》那里,是野外铁道旁摄影师的镜头与市内某房间里某女子醒来的镜头之间的并置;在《轮回》或者《天地玄黄》里,则是亚洲某地的镜头与欧洲或者美洲某镜头的并置。通过这样的处理,断裂性和异质性得到了很好的表达。这就是所谓“在任何时序上把宇宙任何一点与另一点链接”的“无界限和无距离地看”⑨。
然而,人们或许会说,如此一来,纯粹感知电影的制作岂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吗?这只需要组织一次跨国、跨区旅行,途中随随便便地拍摄一些杂七杂八的影像,然后打乱顺序,随机抽样性地将它们剪辑到一起即可。
严格说来,从逻辑上看,还真是这样。因为如果我们将一切都还原到物质微粒的层面,并且按照纯粹感知的运行逻辑的话,上述做法完全可以构成一部纯粹感知电影。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我们将卢米埃尔兄弟的那些短片随机性地组合到一起,便可以构成一部纯粹感知电影。然而,立足于当下的现实,事情绝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电影作为艺术,毕竟还有一个吸引观众的问题,即电影本身的魅力的问题。因此,在坚持上述诸原则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关注影片的审美性和哲理性。
3.审美性和哲理性
制作一部影片,实际上就是摄取宇宙间的一些影像,并将它们组装起来。然而,宇宙间的影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拍摄影片时是否要有所选择?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选择。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部电影的制作,决不能让多余的东西出现在画面中,否则就会出现所谓的穿帮现象。这意味着一部电影中不允许存在多余的事物影像。那么怎样判断哪些是多余的事物影像呢?对此,我们可以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说。例如,在电影拍摄中,用于录音的话筒,显然不能出现在画面中。这个话筒尽管对于电影制作来说是必需的,但对于电影画面来说,则是多余的。再例如,拍摄一部中国古代题材的电影,画面上不起眼的地方出现了一部手机,那么,这部手机就是纯粹多余的。由是而观之,所谓多余的事物影像,就是干扰电影效果的东西。就故事片而言,判定多余事物的准则可以界定为是否干扰故事。所谓故事片,从观赏的角度说,就是让观影者将精力集中于所讲述的故事。如果画面中一个东西,不利于或者扰乱这一点,那么它就是多余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纯粹感知电影不是故事片,相反是在尽其所能地消解故事。如上所述,无论是《持摄影机的人》,还是《天地玄黄》《轮回》等,都丝毫没有故事性可言。尤其是从纯粹感知即同时感知到宇宙间所有的事物这一点上说,那岂不是所有的事物影像都有资格进入纯粹感知的电影中?是不是就意味着对于这样的电影来说,已经不可能存在多余的事物?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上面人们所说的,制作这样的电影相当容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制作这样的电影依然需要相当严肃的态度和非常严格的选择。
在这样的选择中,有两个准则是不能违背的。第一个是遵循纯粹感知的逻辑,即将一切还原到物质微粒的层面,将同时感知到一切事物这一点予以影像化。前面已经讲过的去故事性、去人类性以及断裂性和异质性在根本上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二个则是审美化,即让进入电影的影像发散出一股非常强悍的吸引人的力量,形成一个强大的氛围,将观影者笼罩,使之忘我地、忘情地进入对影片的欣赏。这后一个原则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它是电影成为艺术的根本之所在。为此,我们需要在宇宙万象中选择那些能够体现这些的事物,尤其是用造成强烈的电影审美氛围的事物来制作我们的影像。应该说这是所有电影的一个共同原则,制作纯粹感知电影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和《持摄影机的人》比较起来,《轮回》这部影片,排除因时代所致的技术差异外,人们能够看到,后者的画面极其讲究,完全可以称之为“美轮美奂”,即使是它在呈现一些废墟之际也是如此。
当然,这倒不是说《持摄影机的人》这部影片没有审美性,相反我们也承认它审美性也非常强;只是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显得弱一些。这完全是时代差异造成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如我们今天观看《火车进站》,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震撼感,但这部影片首映时,历史事实却是它能够让观影者在惊恐中做出逃离现场的举动。历史地看,它的审美性是很强的。同样的道理,《持摄影机的人》也是如此。
只是,对审美性还不能完全如此表层地理解,而应该从影片魅力的强度和持续性上来理解。简单地说,影片的魅力,不仅需要时时刻刻拥有自身的强度,还需要持续地散发出撼人的力量。这里就包含着力量的变调问题,即一部影片不能让同一种调性的力量自始至终一成不变。一方面可以调整力量的节奏,另一方面可以转调,以保证影片魅力的奇异性不断丛生。应该说,这才是坚持审美性的根本所在。其实,从《轮回》这部影片看,它每进行一次视角转换,画面的风格都会发生明显的调性变化。例如,从刚开始的儿童舞蹈到火山爆发,就是明显的转调。整部影片的魅力本身总在变动中,不断地呈现出奇异性。
因此,制作纯粹感知电影,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审美性原则。只是需要说明,尽管故事片也坚持审美性原则,但那已经是让审美性为故事服务了。在纯粹电影中,审美性相对而言显得更为独立自足。
接下来,我们来说哲理性原则。严格说来,制作纯粹感知电影,未必要将一个什么哲理置于影片中,但纯粹感知电影中一定会有一个哲理存在。这一方面是电影事实,另一方面是逻辑必然。
从电影事实而言,《持摄影机的人》里面毫无疑问地有一个维尔托夫所主张的哲理:物质世界中的共产主义。⑩换句话说,这部电影之所以被前苏联的电影审查机构认同,原因就在于这一点:在单纯的看(感知)中,物质层面的共产主义蓝图被看到。同样,《轮回》中也存在着一个哲理:一切都在周而复始地“轮回”。应该说,这便和影片导演的目的相关。我们知道,一个导演,在制作影片的时候,总会追求让影片传播自己独特的想法。关于导演的想法,我们需要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封闭性的想法,一类是开放性的想法。前者是一种确定的想法,例如日常性伦理规范,它不会让观众进一步思考,只会让观众在接受的同时遵循之;后者严格说来是一个问题,它会激发观众的进一步思考,在思考的基础上更新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如果是前者,德勒兹是反对的。他指责好莱坞将电影院变成了集中营,说那有一种从希特勒到好莱坞,又从好莱坞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但如果是后者,那么德勒兹是主张的。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德勒兹的观点是可取的。因此,我们主张即使是拍摄纯粹感知的电影,也可以有意识地传播一个开放性的哲理,从而启发人们突破以往,走入新境。
其实,从逻辑必然而言,即使我们将诸如此类的哲理从电影中全部去除,最后也必然留下一个更具根本性质的哲理。在纯粹感知电影中,这个哲理就是纯粹感知的真相:全面地、毫无遗漏地感知着宇宙间的一切。应该说,这不但是一个有关感知方面的哲理,也是一个制作纯粹感知电影的创造性原则。如果要对制作纯粹感知电影必须坚持的哲理性原则予以表述的话,那么我们强调:它应该坚持的就是让纯粹感知的本然运作,通过影像而获得呈现,让观众在观影中经验性地领略纯粹感知的本然韵律。同时,这也是纯粹感知电影的社会、文化意义。
让我们就此回到一开始提到的纪录片能否“摆拍”的问题。如果说真的按照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理论来拍摄纪录片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拍摄纪录片不拒绝摆拍,只要是能够保证按照“纯粹感知”的本然运作逻辑来组织我们的影像即可。但也必须说明,如果人们不是按照“电影眼”的要求来拍摄纪录片,即不是要制作“纯粹感知电影”,那自然另当别论。
注释:
①④⑦⑨⑩ [法]吉尔·德勒兹:《电影1:运动—影像》,谢强等译,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32、93、94、103、63、130、131—132、63页。
② [法]亨利·柏格森:《材料与记忆》,肖聿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德勒兹论证物质拥有自己的生命,主要依据即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观点。
③ 不过,我们需要说明:在此将所有影像都视为感知—影像,仅仅是从最为基础的层面上来说的。如果不是从这个层面来说,那么影像有可能呈现为其他生命机能的影像,如情态—影像、行动—影像等。如果从德勒兹精确的感知—影像的界定来说,则必须说只有感知这种机能相对于其他机能突出呈现时,它才是感知—影像。
⑤⑥ 徐辉:《有生命的影像——吉尔·德勒兹电影影像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5、17页。
⑧ 这里的说法仅限于一般意义上。若从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的思想来说,这里无疑也包含着异质性,或准确地说是“奇异性”。限于篇幅,无法详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