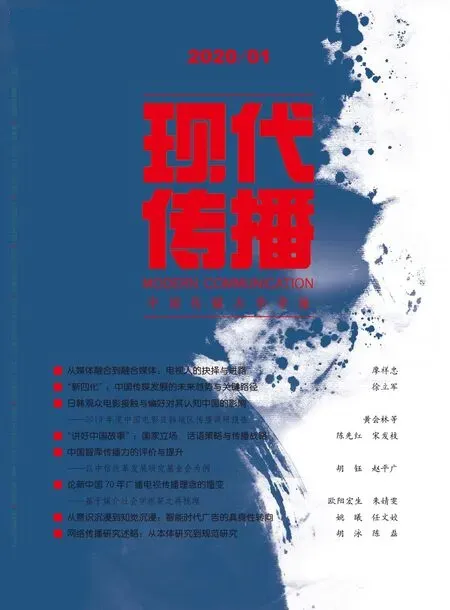揭示、间离、反思:细论反身模式纪录片的观念和手法
■ 唐 俊
一、历史的沿革与问题的提出
在对纪录片模式的研究中,“反身”一词还有反省、反思、自我反射、自我反映等多种提法,但对应的英文词汇均为reflexive或self-reflexive,在牛津英汉词典中reflexive被解释为:showing that the agent’s action is upon himself,简而言之即行为诉诸自身。从词义上理解,对创作者而言反身模式纪录片不但用影像语言反映客观现实,而且也将视点对准拍摄主体自身,从而形成一种双重视角。对观众来说,不但可以看到纪录片所关注的人和事物,而且还可从中了解到创作者摄制的方式与过程,同时影片的真实性、可信度及创作手法要经受双方的审视和协商。
这一类型的纪录片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导演吉加·维尔托夫在经典作品《持摄影机的人》中,就创造性地插入了摄影师和剪辑师工作的片段,被视为后世反身性手法的滥觞。而在二战后,现实主义影视创作迅速发展,随着轻型设备、同步录音在纪录片领域的出现,“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崛起,反对摄制者抛头露面,强调旁观、不介入,反身性探索只能长期作为一种实验性的存在。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现实主义创作亦受到质疑和批判,影像中所谓的现实被认为是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摆布的产物,而观众却深陷其中。电影理论家们希望透过教育和自我反射的电影,“借此不断提醒人们注意电影作为一种折射观念的中介和特性,而非社会现实的透明反映”①。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上述思潮的涤荡,西方新纪录电影(New Documentary)兴起,传统模式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纪录片的创作实践更趋多元化,技术的发展也使纪实影像原本毋庸置疑的可信度受到挑战,这一切使得欧美的反身模式纪录片从先锋、实验逐步走向中心、主流,跻身纪录片主要类型,出现了《细细的蓝线》《罗杰和我》等经典作品。在理论研究领域,美国学者比尔·尼科尔斯、珍·艾伦等对这一模式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纪录片基本被政论片、文献片所统治,类型上属于全知视角的说明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纪录运动”兴起,纪录片创作模式趋向丰富,在《望长城》《毛毛告状》等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对创作者摄制过程的反映。但总体上,追求客观纪实、秉持中立视角、创作者隐身于后的观察模式更受推崇,与之相悖的反身模式作品比较少见且处于边缘地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产纪录片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从业者的创作观念日益解放,彰显个人视角、摆脱中立立场的反身性策略和手法的使用也在作品中逐渐增多。创作者不再中立、旁观,而是坦然成为事件的参与者与作品社会意义的积极创立者。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一些反身模式作品与反传统、去中心化、不拘常规、张扬个性的后现代网络语境相融,其创作观念因而在网络亚文化主导的生态情境中得以显化,进而获得超越传统平台的传播效应。例如,有强烈反身特征、曾为不少电视媒体所排斥的《寻找手艺》在弹幕网站B站却受到追捧而成为爆款,《房东蒋先生》《龙哥》等反身纪录片也具有很高的网络传播度。因此,进入网络社会后此类纪录片更富活力,研究价值亦渐凸显。
但总体而言,由于观察模式在纪实形态作品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我国业界对反身模式还比较陌生,相关理论研究亦亟需深化。目前,国内对此类纪录片的学术研究多以个案分析为主,系统深入的论述较少。一些论述或语焉不详、简单化,如将反身纪录片局限于“引起人们对纪录片模式的探讨,试图推进纪录片本身面貌的改变”②;或有似是而非、过于泛化的问题,如将新闻调查类栏目、情感救助类节目中记者的介入也归于自我反射式的运用③。因此,对于反身模式纪录片的观念和手法有必要进行更为细致的梳理、分析,提供更为丰富的本土化研究成果。
二、揭示:通过个性化“自我表述”,展现建构现实的方式
1.反身模式纪录片对传统模式的反拨
社会建构主义是知识社会学的一种路径,与倾向客体主义的功能主义不同,强调人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意义,并通过互动,构成整个世界及其生活。在媒介领域,塔奇曼等西方社会学者的研究表明,新闻是现实的建构。而戈夫曼也注意到从纪录片生产的程序看,纪录片实际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意义的转化。④与新闻一样有真实性要求的纪录片,并不是像镜子般地复原物质现实,而是一种带有创作者自身视野、欲求、价值观念及文化背景等主体因素的对现实生活的影像建构。因此,“纪录片之父”格里尔逊将纪录片定义为“对事实的创造性处理”。英国当代著名纪录片理论家布莱恩·温斯顿认为,纪录片是“将观察到的各方面加以记录,再对其进行结构化(或叙事化)处理”⑤。这都凸显了纪录片对社会现实进行建构的本质。然而,大多数纪录片为了呈现原生态般的真实感,并没有向观众揭示这一本质并传递有关如何操控的必要信息,所以反身模式承担起了这一使命。
在其他几种纪录片主流类型中,说明模式纪录片(特别是政论类)以不容置疑的“上帝之声”及高度契合主题的采访来实现宣教目的;观察模式纪录片(直接电影)则力图隐藏创作者的工作痕迹,如“墙上的苍蝇”,给人以不介入、无干预的错觉。前者为全知视角,后者推崇客观记录,但它们均未反诸自身,创作者在片中通常成了隐形人,观众对纪录片摄制本身的情况无从知晓,因此也往往难以对作品有更全面、深入的认知。参与模式纪录片(真实电影)中有创作者身影的出现,包括与被采访者的接触、交谈,与反身模式比较接近,但绝大多数作品并未像真实电影起源之作《夏日纪事》那样对影片的建构意图作出说明,观众对于拍摄背后的状况仍然知之甚少。
反身模式纪录片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力图突破上述经典模式。美国学者詹·鲁比认为:“自我反射不仅自我意识清醒,而且还要充分意识到,自我的哪些方面有揭示的必要以使观众既能够理解制作的过程也能够理解合成的作品,要懂得揭示本身是有目的、有意图的,而不是单纯的自恋,不是偶然性的揭示。”⑥的确,反身模式纪录片有意图地揭示而非隐藏创作者建构现实的观念和手法,反映其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干预和操控,这是反身模式的基本构成条件。可见,反身模式绝不仅限于通过对模式、手法的探讨以推进纪录片面貌的改变,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诉求。其对于观众的意义或功能,美国学者珍·艾伦清晰地表述为:“使观众意识到这些制作过程是对影片的中立立场和客观纪实能力的一种限制,使观众注意到为了传达某种含义而选择和重组事件的过程。因此,自我反映是对强调真实性的传统纪录片模式的一种逆反或反拨。”⑦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出现了创作者身影和摄制过程的作品就都可归入反身模式,那是一种不严谨的泛化。
2.“客观描述性”和“主观干预性”
通过细致分析可以发现,在很多作品中,对摄制过程的呈现是偶然的、不自觉的,或者表象的、流程化的。有的虽然详细,但也大多属于“客观描述性”的,难以实现反身模式的诉求和功能。例如系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2》的最后一集《花絮》将镜头聚焦摄制组自身,集中讲述拍摄过程中摄制组如何克服各种困难,但并未揭示创作者个性化的建构过程(选择和重组);又如在一些电视专题报道中,虽然体现了记者的介入推动着事件的进展,但记者代表的是公众利益,强调的是中立立场而非个人视角,追求报道的客观、公正、权威,试图让观众认同结论而非自主判断,因此严格来说这些作品并不属于反身模式的范畴。此外,对情景再现手法的运用也需进行分析,大多数情景再现的运用是为了弥补画面不足或增强视觉表现力,暗示观众实际场景近似如此,而《细细的蓝线》则用这种手法建构了一起杀人案件的各种可能性场景,帮助观众进行判断,所以只有后者属于反身性手法。
在反身模式作品中,最关键的并非创作者身影是否出现,而是对创作者建构现实的观念及手法的揭示和对个性化主观意识的高度强调。“自我表述”是反身模式最为普遍的一种揭示手法,创作者在关注被拍摄对象的过程中,会不时将镜头、视点反转对准自身,通过画面、解说或字幕等元素将自我行为和感受融入在叙事之中。例如在纪录片《房东蒋先生》(梁子/干超,2004)中,摄影师梁子用第一人称表述,在片中大量穿插了她在上海工作期间与房东蒋先生的接触经历及内心感受。片中一些精彩的片段,例如梁子的第一次偷拍被蒋先生发现,两人间关于“小资生活方式”的辩论,在搬离老宅前鼓动蒋先生踢东西发泄,买蛋糕为蒋先生过生日,蒋先生拿起摄像机反过来拍摄梁子,说这才是“fair play”(公平游戏)等,都体现出鲜明的反身性手法。与前述的“客观描述性”呈现不同,该片有大量的“主观干预性”揭示,梁子既是该片的拍摄者,也是名副其实的“女主角”,如果没有她的介入、激发甚至挑衅,就不可能有该片的成立。区分“客观描述性”与“主观干预性”的一个比较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看作品中人称的运用,前者通常是第三人称,而后者更青睐第一人称。当创作者希望做个性化“自我表述”时,第一人称自然就成了最佳的选择,后文中将提到的几部作品恰恰也使用了第一人称,这绝非巧合。
《房东蒋先生》无疑包含了参与型纪录片的诸多要素,但创作者介入更深,在拍摄主客体高度相融的场景时,已不再顾及“中立立场和客观纪实”。如导演干超所说:“一般来说,拍摄者和被拍摄者要处于一种‘隔离’状态,这样才能够客观地讲述整个事情。但是这部片子里,我们把拍摄者和被拍摄者放在了同一个空间里,因为这个拍摄手法,使得这部纪录片至今还颇受争议。”⑧而观众则从中看到了此片的建构过程——大大咧咧、热情直爽的北京女摄影师,以其个性和言行激活了孑然一身、沉湎于自我生活方式的上海“老克勒”(指受西洋文化和生活方式影响,讲究品味的中老年男性),双方产生种种耐人寻味的互动,从而引起观众在地域文化及人性层面的深入回思。在这一过程中观众可以意识到,创作者建构了在自然状态下难以发生的故事片段,并进行了极具个性化的选择和重组。
当然,《房东蒋先生》是一个强干预度的案例。事实上,反身模式中“主观干预性”揭示的成立,并非建立在导演必须成为故事参与者的前提上,而是建立在对导演介入导致客体变化的展现程度的基础上,且这样的展现会使人们对纪录片长期标榜的客观纪实产生疑问。例如《寻找手艺》(张景,2017)中罕见地展现了多位手工匠人如何调整常态、配合拍摄的情况。做伞的老人“平时他都是三五把伞一起做,今天他表示愿意单独做一把配合拍摄”;做秤的匠人说“所以我先在这儿做了,方便你们拍这个过程”;“今天没有人预定面花,雷英华只能做个示范,然后把做好的重新压成面,避免浪费”。这也是一种“主观干预性”的揭示,以上这些状况虽在纪录片摄制中屡见不鲜,但通常在成片中都是被省略、被过滤掉的内容。与蒋先生在梁子介入后发生的故事相比,《寻找手艺》中展现的人物变化虽然是轻度的、细微琐碎的,但同样反映了纪录片建构现实的本质及其“客观纪实能力”的局限。然而,B站上《寻找手艺》的5万多条弹幕评论中,出现最多的却是诸如“真实”“真诚”“感动”的字眼。在我国,纪录片长期带有浓重的主流话语特征,而网络亚文化也一直在争取“草根”的评价权力,像《寻找手艺》这样的反身模式作品承认“客观纪实”的局限,与主流纪录片的权威话语与全知视角形成鲜明反差,却被网友们认为更贴近生活的真实,因而成为“草根”群体彰显评价力和影响力的理想之选。此外,同样具有反身性建构特征的“实验纪录片”《历史那些事》在B站亦有很高的热度,体现出反身性手法与网络纪录片的亲密接触。
三、间离:以多种“陌生化”手法,形成独特审美
1.对共鸣与沉浸的警惕与抑制
在传统的影视节目包括纪录片的生产中,创作者往往希望通过消除生产符号特征、强化真实感等手段,使观众能够沉浸于作品之中,把内容完全当成事实来接受,从而实现审美的愉悦和共鸣。然而,这也导致了观众的自主性和判断力弱化等弊端。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陌生化”(Making Strange)戏剧理论主张演员和角色、观众和剧情之间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使人们既认识对象,同时又产生陌生之感。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要求,演员必须放弃足以促使“观众与其人物形象产生共鸣”的一切,目的在于“使观众保持着进行评价的间隔,从而有可能理解所表演的东西的真正含义。从不充分的理解,经过不理解的震惊,达到真正的理解”⑨。这种传播效果被称为“间离效果”或“疏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s)。将此理论引入影视节目制作中,体现为有意识地使叙事间断、视点转换,以及运用一些非常规的艺术手法,使观众摆脱沉浸状态,抑制共鸣心理,得以保持自身的理性判断和思考,进而形成独特的审美体验。进入网络时代,随着观众自主意识的强化,“陌生化”手法也被越来越多地采用,使原本封闭、单向的影视文本呈现出开放、互动的特征,更加尊重观众的主体性和感觉丰富性。例如奈飞投资的热门美剧《纸牌屋》会不时让叙事有个小小的中断,男主人公弗兰克·安德伍德打破“第四面墙”,突然正对镜头向观众说话,坦露内心的秘密;在BBC与亚马逊联合出品的新版《李尔王》中,阴险的爱德蒙亦有直面观众的内心独白,这些均属以“陌生化”手法实现“间离效果”的影视实践。
2.反身模式纪录片中“间离效果”的实现
对于反身模式纪录片的研究,通常会涉及到“间离”审美效应。因为这类作品既关注被拍摄对象,又注重揭示主体自身,这种有意识的视点转换即为一种“陌生化”手段,易产生“间离效果”。如研究者指出:“间离效果决定我们不能按照固有的欣赏模式与欣赏对象自然而然地达成理解和共鸣……这种引领对于观众来说,是在培养日常生活中明确感知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⑩例如《房东蒋先生》的解说词是以梁子和蒋先生两人的第一人称自述交错展开的,这种对位转换就会产生“间离”或“疏离”作用,促使观众感觉到故事叙述的主观性,并进行调整和思考;在反映吸毒者悲惨生活的《龙哥》(周浩,2007)中,虽然导演的身影只是偶尔出现,但片中的字幕说明、逐渐增多的对话同期声以及对龙哥的干预和接济,却使观众不时意识到导演自身在故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不至于沉浸在龙哥极富表演性的讲述之中;《寻找手艺》经常在匠人的工作场景中穿插自身的生产符号,包括不时露出制作者持摄像机、话筒等传统意义上的“穿帮”镜头,也能起到“间离效果”,如同《持摄影机的人》中摄制人员工作画面的插入一样,不断向观众揭示影像的建构本质。
在求新求变的网络时代,个性化“自我表述”及其带来的“间离效果”能够使观众产生新奇感,增强作品的吸引力,这也是国产纪录片创作中反身性手法的运用逐渐增多的原因之一。《寻找手艺》将自身拍摄的种种状况不加掩饰地告诉观众:创作者作为纪录片爱好者卖了房子去拍片,录音是出发前一个星期才学的,机器是二手“残次品”,摄影师临时退出只好由司机顶替……这些带有自我讥讽意味的坦白反倒予人真诚、质朴的感受,使网友们对这部“草根作品”产生了兴趣。如果创作者屏蔽这些拍摄状况,像其他作品一样试图让观众沉浸于工匠技艺的展现,那么这个片子在诸多同类题材中就缺失了特性,观众很可能会觉得粗糙、不够专业而不予关注,这就是反身模式纪录片的魅力,即令观众在意外后理解,理解后认同。
3.艺术性“陌生化”手法的运用
近年来,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纪录片不断从影视剧、娱乐节目、动画片等类型作品中汲取养料,除了创作者通过“自我表述”形成客体与主体之间的视点转换,以及建构特征鲜明的情景再现外,一些反身模式纪录片运用更先锋、更具艺术性的“陌生化”手法实现“间离”审美,包括通过穿插美学风格迥异的影像,形成各种基于现实的发散性建构。例如我国香港地区的纪录片《坏孩子》(游静,2010)是一部讲述少年感化院中孩子生活的作品,影片的素材大多由这些孩子自己拍摄。编导运用丰富的剪辑技巧,插入很多相关影视剧和MV的片段,与孩子们拍摄的影像相呼应,打乱常规叙事,使观众的观影体验被一再间离,构成镜像和戏仿的反身性效果。事实上,这也可被视为一种另类或前卫的“自我表述”,虽然编导并未现身,但其建构意图却更为凸显张扬。这类手法不仅反映在上述的混剪方面,还体现于虚拟性的拍摄之中,现实故事被故意变形处理,迫使观众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接受。如在电视与网络端均很热门的纪录片《人间世2》(集体,2019)第一集《烟花》中,在骨癌患儿安仔弥留之际,正常叙事突然被打断,插入了一组出人意料的“陌生”画面:原本病殃殃的安仔似乎精神振奋起来,他装扮成了一个可爱的卡通形象,戴着红发,披着斗篷,拿着武器,在《逆战》的音乐中活力四射、纵情挥洒,似乎也在突破“第四面墙”与观众交流。其实,这个片段是先前孩子身体尚可时在医院附近的老厂房拍摄的,很明显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建构行为。该片总制片人说:“这些花季少年的青春被关在医院这个像牢笼一样的地方,但是他们内心是童真的,他们希望能够获得一次快乐的释放……他们希望能够扮演自己所认可的卡通人物,我们则希望帮他们圆梦。”这个段落没有解说词和采访,观众在惊讶、错愕之余,或许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创作者的用意。当然,观众也可能有其他的理解甚至排斥这种手法,那是他们的选择自由。总之,“间隔效果”的形成能够使观众与剧情保持一定的距离,有助于培养、增进观众的自主性和批判意识,这也为其进入反思层面打下基础。
四、反思:挑战传统规则,消解复原神话
绝大多数观众会将纪录片的内容完全当成客观事实来接受,这是长期以来纪录片对社会公众的真实性承诺造成的神话。“所有纪录片的习惯手法——表达形式上的一些惯例或套路——都出于一个需要,即让观众相信他们看到的一切是真实的。”一旦得知纪录片与客观事实有所不符(即使是个别关键细节),观众就很可能会感到受骗或被误导,从而使作品陷入到一场伦理危机之中。一个著名的例子是BBC的《人类星球2》被曝造假,片中描述的印度尼西亚雨林中部落土著建造、入住的树屋,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家,而是摄制组为了拍摄效果,委托当地人建造的,这对BBC纪录片的声誉无疑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反身模式纪录片对传统的现实主义规则和惯例发起了挑战,它的核心价值诉求在于:促使制作者和观众对所谓的“真实影像”进行反思,而不是迷信客观复原的神话。
1.摆脱形而上学真实性观念的束缚
如珍·艾伦所说:“向传统的纪录片模式挑战有许多种方式,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反对把真实性的要求看成是中立的立场。”比尔·尼科尔斯对纪录片的模式分类进行了详述,他认为,“在最好的情况下,反身型纪录片会促使观众对自己与纪录片及其所表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有更高水平的认识”。这里所讲的“更高水平的认识”,即指反思、自省的层面。欧美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反身模式纪录片是通过演员扮演的手法来激发这种反思的,这种扮演超越了一般情景再现的界限,甚至连采访也由演员完成,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建构特征。例如在著名的《姓越名南》(崔明菡,1989)、《远离波兰》(吉尔·戈德米洛,1984)中,观众起初以为看到的是对当事人的采访、在现场的实地拍摄,但后来却通过影片的进展或提示惊讶地发现(强烈的“间离效果”出现了),受采访者是请演员扮演的,拍摄地既不是越南也不是波兰,而是美国本土。但是,这类影片也逐渐能够被很多观众理解和接受,因为制作者当时因条件限制无法赴实地拍摄,扮演的内容也有真实的采访和资料作为依据。同时,这些放弃中立观察视角而大胆建构的影片,促使人们进而反思造就纪录片“真实感”的一些制作传统,如面对面访谈、证据式剪辑等的可靠性,也使观众意识到,有依据的再现、扮演未必就没有真实性。如此一来,客观复原的神话被消解了,一部纪录片是否具有真实性,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孤立的评价标准,而是要置于摄制者与社会现实、作品与观众的互动关系中来考量。布莱恩·温斯顿认为:“纪录片的未来要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解之上,即它对真实的主张并非不证自明,它的成立与否只能由观众自己来决定。”这些反思对传统纪录片观念特别是真实性观念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但也正因为如此,纪录片多少得以摆脱形而上学真实性观念的束缚,开拓出更为宽广的天地。纪录片当然要反映真人真事,但创作观念和手法却应当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不拘一格,甚至可以逆反传统,这是网络社会价值相对性和多元性的要求,也是纪录片在创新中前行的需要。
2.通过坦诚的文本与观众进行协商
坦诚的文本是反思、自省的前提,也是与观众进行协商的基础。但如前文所述,在大多数纪录片中,文本并非以坦诚的面目出现,人们虽看到了作品,但并未感知到制作者和制作过程,也就是说这三者的呈现是分离的、不连贯的。而“自我反射是以观众假定制作者、制作过程和作品以连贯的方式制作一个产品,不仅使观众意识到这些联系,而且使他们认识到熟悉这方面知识的必要性”。对制作者来说,这无疑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在中国纪录片中,目前像《姓越名南》这类在现实题材中运用演员访谈的作品罕见,能达到反思层面的尚少,但也有一些作品通过超出常规的坦诚文本体现出反思、自省的诉求。例如在《龙哥》结尾处,通过龙哥女朋友阿俊的讲述,导演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龙哥先前所谓“吞刀片”的说法所欺骗,从而使观众意识到片中其他一些记录的可信度也要打个问号。导演原本可以略去这段内容,然而“这样安排这个纪录片的文本肌理恰恰使我们看到作者对纪录片媒体、对自己摄像机权力和能力的质疑,这种坦诚的不自信和自我怀疑体现了对纪录片伦理的肯定”。这种质疑无疑具有较深刻的反思性。《人间世2》之《烟花》中,一段由患儿配音的解说词亦有明显的自省意味:“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这部影片播放到现在,哭的镜头我数了一下,有二十个,其实纪录片和真实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我们病房里笑声还是挺多的。”这既是一种描述,也是一种反思,它实际上告诉观众:你所看到的并非我们完整的生活,而事实上这也是纪录片生产的常态。尽管如此,由于逆反传统,特征鲜明的反身纪录片虽然让观众耳目一新,但却常常遭遇专业领域的非议,从《细细的蓝线》到《房东蒋先生》均是如此,前者甚至曾被奥斯卡奖评选拒之门外。随着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繁荣,更多富有创意、手法大胆的反身模式作品的出现亦是必然,人们也需准备好投入到相关的争议和讨论之中,在此过程中深化对纪录片的思考。
与力图提供证据式影像使观众感到毋庸置疑的传统纪录片诉求不同的是,反身模式纪录片敢于向观众揭示建构现实的过程,希望观众能够反思他们眼前的影像,这本身就是协商沟通的过程。回到前述《人类星球2》的案例,树屋无疑是一个精心建构的场景和情节(这在纪录片的实际摄制中并不少见),但由于观众未被告知,把它当成原生态的事实来接受并沉浸其中,得知真相后自然引起巨大争议。假设该片运用反身性策略,比如在片中提示观众,为了更具挑战性,摄制组与当地人达成一致,委托后者在大树高处建造树屋并尝试入住,那么观众就会清楚地认识到创作者介入了这一场景的建构,即使对这种做法可能仍然存在争议,也不致于产生强烈的被欺骗感及信任危机。如美国学者帕特里夏·奥夫德海德所说:“没有人能通过回避形式选择来解决与真实有关的道德问题,也没有哪种表现形式本身就是错误的。制作人与观众之间相互坦诚才是最本质的。”反身模式纪录片将制作者、制作过程、作品及三者的关联更清晰、连贯地揭示给观众,以期获得观众更多的信任,同时也引发观众更深入的思考。
五、结语
上述几个层面分别从构成条件、传播效果和价值诉求上对反身模式纪录片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反身模式向传统模式提出了有力的质疑和挑战,试图提供更为坦诚、多义、风格化的叙事文本,形成开放、自主、有助反思的传播结构,这与当今网络场域的文化语境互通,因而也获得滋长的助力。尽管存在各种争议和批评,反身模式仍以其独特的属性成为相对独立的类型,拓展了纪录片的思维空间与表现领域。伴随着中国纪录片生产的多元化、影像创作的平民化以及网络成为传播的主渠道之一,反身模式未来有着较大的发展潜力,创作者运用反身性策略和手法的创新意识也在增强,这是应当被宽容甚至鼓励的。
当然,和其他类型一样,反身模式也有着自己的边界和尺度,如果创作者操控过度、喧宾夺主、滥用技法,那么作品很可能会成为一场扭曲现实生活的晦涩游戏;若非实拍受限、持有事实依据、观众能够感知,那么运用情景再现和演员扮演的手段则与伪纪录片无异。此外,对于一些极为风格化的新奇手法,观众也易陷入审美疲劳。尼科尔斯说:“现在我们既要关注影片表现了什么,又要关注如何表现。以往我们是透过纪录片看世界,而反身模式纪录片要求我们看透它:究竟是一种构成,还是一种再现。”这无疑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使命,创作者需要在和观众的不断协商过程中继续寻找前行的路径。
注释:
① 赵艳明、李文聪:《论纪录片的自反性理念及其中国影响》,《理论界》,2011年第2期,第179页。
② 邱雨:《伪装起来的真实——以〈细蓝线〉为例探讨埃罗尔·莫里斯反身性纪录片的个性形态》,《戏剧之家》,2016年第17期,第103页。
③ 谭孝红:《纪录片创作中的自我反射式手法》,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1—23页。
④ [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7、173—184页。
⑧ 霍燕妮:《〈房东蒋先生〉获奖后饱受争议》,中国日报网站,http://www.chinadaily.com.cn/hqylss/2006-04/18/content_570455.htm,2006年4月18日。
⑨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布莱希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09—211页。
⑩ 董健:《论“间离效果”在电视节目中的存在意义及运用技巧》,《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8期,第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