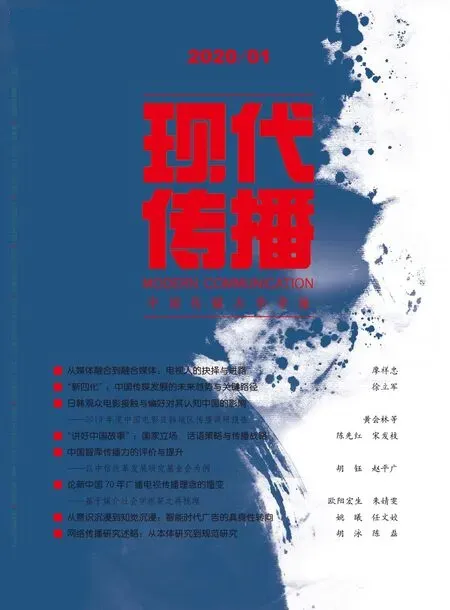制度遗产与农村广场舞兴衰
——基于江苏省R县的田野观察
■ 沙 垚
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年来,广场舞深度蔓延到了中国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广场舞进入公共话语领域,并成为媒介热点,2013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性年份。此前,媒体上的广场舞及其舞者大多被建构为负面形象,但2013年之后,广场舞逐渐与体育健身、群众文化联系起来,学者们开始将广场舞视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展开严肃的讨论。
2009年以来,每年夏季与冬季,笔者都会在自己的家乡江苏省R县三大队观察一支广场舞队,对舞者进行多次访谈。吊诡的是,恰恰是在2013年,该村的广场舞队解散了。2013年起,笔者跟随其中一位核心队员——莲女士加入农场社区的夕阳红舞蹈队,进行进一步的观察与访谈。
为什么一支跳了4年的农村广场舞队在城镇广场舞队蓬勃发展的2013年解散了?为什么农场社区的广场舞队却可以坚守并持续壮大?农场社区和普通农村社区有什么关联和区别?学者较多关注广场舞何以赢得那么多追随者,但却很少有人关注广场舞队为什么解散。而解散之原因涉及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及其与历史遗产之勾连等一系列重要命题,比如城乡关系急剧变迁对农村文化实践的影响等。本文便是通过讲述一支农村广场舞队兴衰的故事,及舞者的选择过程,来讨论历史与当下的断裂与传承,以及历史资源如何作用于当下。
二、从现状调查到社会历史深处
梳理广场舞研究的学术史,经历过如下三种研究路径。
其一,回答是什么原因,让这么多的人参与到跳广场舞的活动中来?这需要一手的数据,因此,以量化方法进行数据收集是广场舞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涉及各个省份地区,大致描绘出广场舞现状和生态面貌。如,王红涛的《芜湖市广场舞的开展现状与推广研究》①、李蕊的《豫南地区广场舞开展现状调查研究》②、马裕文的《常熟市区广场舞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③等。这些研究大致反映了当下广场舞的主要年龄群体、性别学历、阶层状况、跳舞频率、舞队组织情况等等。其中不少文章还提出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加强广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介入规范化管理,完善政策减少扰民,同时多派专业指导,增加骨干培训,引进比赛机制,等等。这一类量化研究同质化程度非常高,但不能说它们便没有意义,其价值主要在于通过大量的调查,完成了全国的大起底,摸清楚了广场舞的发展现状。
其二,广场舞研究与政策应用结合起来。比如王芳的《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金园园的《探讨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张海英的《论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④等,他们认为,广场舞有助于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能促进和谐群众文化的建构,是检验群众文化成效的重要手段⑤;增强了民众的文化素养及生活品味,能够推动社区文化建设,为群众的文化提供平台载体,帮助民众增强身体素质⑥。
虽然这些实践者或学者的文章,在机械的建立了广场舞与国家政策的关联,但客观上提升了广场舞的意义,并为之贴上了“政治正确”的“标签”,为下一步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学术支持。2016年,全国14个重点城市共有50085人同时跳舞,成功创造了新的最大规模排舞(多场地)吉尼斯世界纪录。⑦不得不说,广场舞之所以能风靡全国,与政府的大力倡导密切相关。
其三,相对概念化的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出现。比如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研究广场舞,认为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老年人也越来越注重娱乐休闲,广场舞应运而生⑧;比如用科塞冲突理论来分析广场舞带来的社区冲突,认为这种冲突对社会系统稳定发展亦有一定程度的益处⑨;再比如利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展开研究,认为“广场舞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空间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空间实践。主体的社会行动是连接空间的意义和物质形态的桥梁”⑩,等等。虽然这些文章缺乏学术层面的理论深度,但他们将广场舞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这与彼时大众媒介上广场舞低俗、愚昧的媒介形象有着很大的不同,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为广场舞正名,去污名化、去妖魔化的过程。
这些讨论将广场舞研究从现象层面引向了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层面。比如王婕用“同期群效应”的概念研究广场舞,分析出其中的集体主义特质,并认为“当代的广场舞现象是一种(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借助广场舞这一形式框架重构其集体主义理念的过程。”。再比如李园从自我建构和社会互动的角度切入,认为“广场舞作为传统思维与现代行为方式的缓冲地带,使得广场舞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社会结构系统进行调适”。沿着该路径,较有影响的研究有:王芊霓认为在社会多重断裂的背景下,广场舞可以作为一种消弭社会结构性危机的可能性;黄勇军和米莉认为广场舞“有效地填补了社会与心灵的双重真空地带”,是“断裂时代的自我弥合”,等等。
沿着历史的维度深入,学者们发现广场舞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史、文化史的勾连,主要集中在“主体”“空间”和“文化”三个方面。比如赵月枝聚焦主体,认为“农村广场舞可以看成是获得社会主义现代主体性的一代女性带动年轻一代的日常文化生活实践。……第一批跳广场舞的妇女应该是50后和60后这一代人,70后甚至80后是在她们的带动下开始的,因此,农村广场舞可以看成是获得社会主义现代主体性的一代女性带动年轻一代的日常文化生活实践”。至于空间层面,当广场的所指已经由原来公共空间、政治空间、群众文化活动中心转向消费主义,成为购物中心的代名词,如购物广场、美食广场等;罗小茗、王芊霓、张慧瑜等将这一“空间争夺”的观点应用到广场舞研究中,认为广场舞是大妈与“小资”两群体“争夺广场”的运动,是群众性文化诉求和城市中产“清静权”的正面碰撞。谷李在此基础上将主体与空间相结合,认为正是“在日益压缩的公共空间、难以发声的庶民文化与逐渐失语的群众文化相交的三岔路口”,广场舞的实践获得了意义。以周怡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切入,认为在广场舞的亚文化实践中,可以发现不同的“世代意识”和“主文化”的拼贴,在亚文化的拼贴和重构中,历史与当下、传统与现代得以勾连。
纵观这些研究,在历史层面,虽然学者们提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概念,但对于社会制度的变迁,尤其是当代农村文化现象与社会主义历史制度遗产之间的关系却甚少关注,而这或许可以成为勾连历史与社会的关键。本研究基于9年的田野观察写作而成,其特点有二:其一,不是对某次事件或活动的生动呈现与剖析,而更多在于对一段时间内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观察与思考;其二,从行文上,笔者没有遵循从个案到总体的归纳逻辑,以及从概念到案例的论证逻辑,而是遵循叙事逻辑和人类学体例,“在个案中进行概括”,从而有一些中观层面的发现。
三、三大队农村广场舞队的兴衰
三大队位于县城东侧5公里处,该村因地处县城近郊,以农业、手工业和进城务工为主要生存方式。村里开始有人跳广场舞是在2009年,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成员相对固定,约11人。至2011年,由于该团队核心成员的退出,村民们改跳健身操,参与者忽而数十人,忽而三五人。2013年之后,没有人再在本村跳广场舞。
三大队广场舞的发起人是朱女士。她一直是三大队的村干部,1990年代当了村主任,退休后便搬到县城与儿子住。“我原来在人民公园跳舞,儿子在县开发区有房子,离得近,但是那个房子没有车库,不好停车,不方便,刚好村里盖庄园,我就回来弄了一块地,盖了房子,就发动大家跳舞,还把人民公园的老师请回来教舞。”由于她在村里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威望,很快就拉起了一支广场舞队伍。另一位发起人是珍女士,她的情况与朱女士很相似,“我在浅水湾跳舞,带孙子,后来孙子考上大学了,我就搬回乡下住了,正好朱来找我,说弄个舞蹈队吧。”
2009年秋开始的第一批舞蹈是《烟花三月下扬州》《欢乐中国年》《卓玛》等,以民歌和主旋律歌曲为主;到2010年底开始跳《最炫民族风》《小苹果》等所谓的“流行歌曲”。据观察,每天来跳舞的人员,多则十五六个,少则五六个,相对固定的跳舞人员有11个。
通过广场舞团队成立的过程,可以看出广场舞并非是从农村文化中自我生长出来的,相反,它是从城市流向农村,反映出农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复制。
2011年正月初五是三大队舞蹈队唯一一次参加县里举办的广场舞比赛。参加县里的比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农村团队的舞蹈水平明显低于县城社区的舞蹈团队,因此只有在县文化馆熟人帮忙,或是县城团队不够的情况下,农村舞蹈队才可以参加。为了参加这次比赛,村里几个舞蹈队员还在朱女士家里开了一次会,会上决定,由袁女士提供布料,因为她家开织布厂;由莲女士做衣服,即红T恤和白裤子,因为她是个老裁缝,这也是这个团队唯一一套统一的演出服;由萍女士购买道具,包括扇子、黄绸带、碟片、U盘等,因为她较为富裕。
2011年7月,朱女士邀请大家在她家院子里跳舞,现场去了11个人,这11个人穿着统一的服装,红T恤,白裤子,手上拿着黄绸子,这是在县里参赛的服装,并录制了DVD。晚上,朱女士请大家吃饭,吃晚饭的时候,她说,她儿子又在县城买了新房,她年底要搬过去了,因此对她来说,这张碟片是她在三大队和大家跳舞的一个句号。
2012年起,村里的舞蹈队由莲女士和梅女士负责,跳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没人了。到2012年秋,村里分裂成两个队伍,其一是,一位老板在自己家院子旁边,搭了个棚子,买了两套大音响,组织大家跳健身操。“我不怎么想去了。因为老板家太远了(大概800米),去的路上,好多狗,我怕。”另一个队伍是,莲女士、萍女士和斌先生等几个人在莲女士家的院子,莲女士的儿子还买了一个1300元的音响。但是跳舞的人请假现象严重,据观察,每天跳舞的人少则三四个,多则五六个,有时候只有两个人跳。至2012年底,两个队伍都解散了。分析原因,第一个队伍缺乏文艺骨干,第二个队伍人太少,因此都支撑不下去。另外,2012年底朱女士突然因病去世,给舞蹈队其他成员也带来不小的精神冲击。
三大队舞蹈队11个成员的社会背景是什么,舞蹈队解散之后,他们各自去做什么了,从这里或许可以找到舞蹈队解散的真正原因。
朱女士,1948年出生,当了一辈子大队干部,退休之后随儿子住到县城。2009年回到农村,组织舞蹈队,到2011年随儿子搬离农村,在县城继续跳舞,2012年去世。
莲女士,1947年出生,农民,也是舞蹈队年纪最大的队员,曾经当过很多年缝纫工,现在没有收入,但由于先生过世,儿子均已成家,她也没有经济负担,主要由儿子赡养,儿子属于工薪阶层。
萍女士,1958年出生,长期经营一个家具店,2009年把家具店给了儿子之后,搬回农村居住,是舞蹈队最富有的队员。但在家闲不住,2011年她返回县城,在一家保健品公司当了销售经理,又挣钱去了。偶尔参加县城广场舞队的活动。
红女士,1968年出生,开着一个家庭作坊式的服装厂,有10个左右工人,她是老板娘。但她也要工作,比如给工人做饭,帮助剪裁、熨烫等,2013年之后不再跳舞。
袁女士,1972年出生,开着一个家庭作坊式的织布厂,2010年以后工厂亏损严重,不得不关门,袁女士自己也不得不到县城的大型服装厂当起了流水线女工,偶尔参加县城广场舞队的活动。
梅女士,1965年出生,一开始是卖保险的销售员,2012年以后,转行到县城一家超市做了导购,需要每天上班,偶尔参加县城广场舞队的活动。
凤女士,1951年出生,家里闲置房屋比较多,开办了村棋牌室,每天有人来打牌,交一定的场地费,凤女士负责准备午饭和晚饭,同时供应茶水和香烟。2013年之后不再跳舞。
葛女士,1966年出生,一直都是县城一家烟酒超市的导购,推销酒。2013年之后不再跳舞。
珍女士,1953年出生,是舞蹈队的另一位发起人,是村医的妻子,年轻时在县城服装厂当工人,后来就一直在县城照顾孙子。2009年,孙子考上大学,她也搬回到农村。赋闲在家,跳了几年舞。2012年以后,她去给厨师帮忙摘菜、洗碗,每天挣120元,外加一包20元的香烟,不再跳舞。
霞女士(1947年出生)和芬女士(1959年出生)两人都是村里开小卖部的,2010年之后,小卖部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就和珍女士一起去给厨师帮忙了,也不再跳舞。
分析这11个人的职业与去向,可以看出,一位退休大队干部作为组织者,两位较富有的老板,三位打工者,五位农民。而且多数情况下,老板、打工者和农民的身份是模糊的,甚至是可以转化的。同时,当三大队舞蹈队解散后,住到县城去的人,不管是什么身份,都继续跳舞;留在农村的人,基本不再跳舞。因此,从广场舞解散之后人员去向来看,广场舞也不是完完全全从底层发起的草根艺术,广场舞的繁荣呈现出从城镇流向农村的态势。
分析三大队广场舞队伍解散的原因:首先,朱女士的离开使村里没有了召集人,当召集人应当具有两个条件,热爱跳舞且跳得好,以及有社会资源和威信;其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在2010年之后影响到中国农村,家庭作坊式的加工厂订单萎缩,遭遇生存困境,村里的产业被破坏后,很多人为了谋生不得不放弃跳舞;最后,农村的社会结构也正急剧转型,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外出务工,导致小卖部因生意惨淡而关门,同时,一个新的工种出现了。
原先村里的红白喜事,请一个厨师过来,他只是负责烧菜,由主家找人去买菜,他的邻居会主动来帮忙摘菜、洗碗、打下手。但2011年之后,由于人口外流严重,农村的红白喜事开始实行厨师承包制,低则600元一桌,高则1000元一桌,所以厨师每次出去接单,都会带2—3个帮手,由此在农村生出来一个新的“工种”,该现象在2009年三大队开始跳舞时还没有出现。到2012年,11个人里面便有三个去给厨师洗碗了。当代农村社会正在急剧变迁,而农村广场舞队是很脆弱的存在,很容易受到冲击。
2009至2012年间,笔者观察到农村妇女频繁地在城乡之间流动,只要有空,她们就会搬到农村居住,一起跳舞,但她们并不能自由决定自己的时间和活动的空间,对一部分人来说,进城给儿女带孩子是主要牵绊;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在城里谋一份工作是生存之道,农村仅是一个睡觉的居所。关注农村广场舞舞者的生存状况,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不平等的城乡关系,农村依然是城市的附属。
四、农场广场舞队的故事
从2013年开始,莲女士跟着兰女士的队伍继续跳舞,兰女士是她初中同学,她在农场成立了一支舞蹈队名为夕阳红舞蹈队。笔者便经常跟着莲女士去农场,继续观察广场舞。莲女士说:“兰(女士)很有社交能力,一天到晚打电话联系演出,虽然我们嘲笑她没事忙,但她是个热心肠,人很好,我们还是很尊重她的。她很有名,经常有老板请她吃饭。现在她还在银行帮忙,经常说,要去开会,还挂个胸牌,蛮像那么回事的。”
农场,位于县城的西北侧约3公里处,距三大队约6公里。农场于1969年成立,由某师21团和地方上的农民一起开发,农民由此具有了农场职工的身份。至20世纪90年代初,农场改制,划归地方,农场重新成为一个村庄,它与其他周边的农村看上去是一样的,农民主要工作是种地或到县城工厂做工,生活方式也一样,唯一的区别在于退休金。农场改制时,普通职工女性50周岁退休,男性55周岁退休,可以直接享受退休金;如果年龄未到,则按照“视同”政策,多少年的工龄视同于交了多少年社保。所以,截至当前,几乎每一个农场的农民都可以享受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
农场的广场舞团队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见的形式,每晚约30人左右在社区广场上跳舞,人员不固定,相对随意;另一种是舞台表演,即从广场舞者中选拔出来一些舞跳得较好的妇女,12个人组成一支舞队,人员相对固定。夕阳红舞蹈队即是由此而来。这些舞蹈队的成员平时每日都在广场上跳舞,但一旦有“活动”,她们会整体亮相。
所谓的“活动”,又分为三种。一种是企业或商场的联欢、周年庆典、开业大典等,这些舞蹈队成员去商业演出,活跃气氛。第二种是公益演出,诸如参加慰问养老院、普法教育宣传、环境整治宣传等。第三种是广场舞比赛。夕阳红舞蹈队2018年共参加20场活动,其中商业演出10场,公益演出7场,比赛演出3场。“演出都不收费,商业演出有时会有个红包,五六百块钱,一个人分不到50块钱。慰问演出没有钱,会管一顿饭,还得个小礼物,比如洗衣液、沐浴露、洗发水、鸡蛋之类的。”创作是很辛苦的。2018年底,为了参加文化馆一场“周周演”活动,兰女士闭门在家好几天创作了快板《歌唱新区换新貌》,就农场如何从芦苇荡发展成现在的“新貌”进行说唱创作,然后组织队伍排练了20天。
那么,夕阳红舞蹈队为什么而演?笔者发现负责人兰女士非常忙,她每天都要与各类商家、文化部门和公益组织联系,换言之,其实商家不需要演出,是她“送上门”去的演出。“我手上有5个队伍,每个队伍12个人,我压力很大,我要经常联系到演出机会,不然队伍就散了。”言下之意是,创造演出机会是队长维系舞蹈队的一种方式。同时,对于一般舞蹈队员来说,有机会展示自己优美的舞姿,出点小名,也是人生的一种动力和享受。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或公益演出,在今天全球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日常生活的时代显得十分珍贵。
莲女士并没有坚持太久。因为她不会开电动车,从三大队骑自行车到农场太远了。兰女士说:“我们为了照顾莲(女士),(2016年)我在城东找了个寄养院,跟院长谈好我们每天晚上去那里跳舞,是个大食堂,里面灯、电风扇都有,但很脏,好久没人用了,狗屎什么的到处都是,我们就自己打扫。在这里跳了一年,很多城西的人不愿意了,他们觉得太远。后来,农场给了我一个大会议室做排练厅,我们就搬去西边了。”2017年,莲女士的跳舞生涯结束,这一年她刚好70岁。
总结不跳舞的原因,除了交通不便和年纪大了,莲女士还提到“退休工资”的问题。“那些人都是退休的,有会计、教师、工人、校长……就我一个人不拿钱,慢慢的,我也就不和他们一起玩了。”她提到在互换礼物和登台演出的时候,她都很尴尬,因为别人会买漂亮的衣服,涂口红,抹胭脂,化妆起来很漂亮,但她没有钱做这些。
正如上文提到,农场一对夫妇退休金加起来有5000多元,足够支持他们跳舞,也因此相当于一个村的农场社区,就成立了12个舞蹈队,约150人将跳舞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退休金解决了基本生活所需之后,农场的广场舞者开始寻求进一步的意义,她们不满足于在广场上进行日常性的锻炼和身体放松,她们成立了有组织的舞蹈队,一方面,开展一年两次的社区舞蹈汇演,全体队员集资购买奖品,请县文化馆的老师担任评委和颁奖嘉宾;另一方面,积极介入公益活动,结合县里的政策,自主创作,进行农村宣传。体现了文化和政治的自觉。这与农场的遗产密不可分,或者说,这些舞蹈队本身就是作为农场制度的一种遗产的表征而存在的。
三大队的珍女士和霞女士、芬女士不同,她并不缺钱,她丈夫有退休金,现在又被返聘着,她自己还有养老保险,珍女士夫妻加起来一个月有8000元,在农村属于高收入群体,远远高于农场社区,而且她两个儿子均已成家立业。可是,她为什么还是放弃跳舞,选择去跟着厨师洗碗?她说:“有钱为什么不挣呢?而且跳舞的人越来越少,没意思,就厌恶了,不如去挣钱,有空了打打牌。”观察发现,长期的打工经历使农村人缺乏安全感,村民普遍认为有钱不挣是一种很傻的行为。但对于农场退休的农民来说,他们固定的退休工资使他们获得稳定感。
这种心态上的安全感和文化的延续性得益于制度的保障。中国艺术研究院在2014年组织了一场主题为“新世纪的群众文艺与公共空间”的论坛,会上提到了广场舞与“社会主义记忆”的关系,但仅限于文化形式、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等方面。事实上,从农场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尤其是集体制度的历史正在以某种方式更为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能够支撑广场舞并持续发挥功能的是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的制度性遗产。换言之,当我们以“底层”“草根”等文化符号来欣赏广场舞时,可能会遮蔽其中社会主义的制度属性及其对当代城乡文化的贡献。
五、重新发现被遮蔽的制度遗产
2013年以来,广场舞逐渐告别负面的媒体形象,常常被以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的范式进行解读。从研究文献来看,不乏大量摸底性质的调查,也不乏具有理论深度的探讨,但在中观层面,对广场舞的长时段观察,尚不多见。笔者通过自己在家乡多年的观察,以及与跳舞大妈们的交流,发现身处社会转型和复杂政治经济结构中的她们,也在进行艰难的选择。
从三大队广场舞队兴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层面的城乡关系在文艺实践中的复制,路阳在对沙坡村广场舞传播研究的时候同样提出了“舞蹈下乡”,认为广场舞经历了从城市到乡村的流传过程。忽视农村的社会语境、农民的收入方式和生活方式,即便有来自城市的舞蹈老师、流动舞者积极推动,即便农民觉得一时新鲜,组建舞队,但舞队很难持久。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讨论广场舞对基层组织重建的可能性,如何抵御社会风险,意义不大。因为其一,研究者在讨论底层概念时,常常混淆了工与农,城与乡的差别,“工”的背后有老工厂制度的支撑,即便生活在农村,他们也有稳定的退休金;而“城”的中老年妇女有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他们也无需为生计发愁。因而,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公共和文化事务。第二,这种重建的可能性即便在理论层面是存在的,但在实践层面至少是脆弱的,一个舞者极可能因为一个带头人的去世,一个新的挣钱“工种”的出现就放弃跳舞,换言之,缺少集体主义的经济基础或制度保障,单靠文艺爱好者的主体性和文艺形态所内蕴的组织性很难改变农村的文化生态和政治经济处境。
但是,跟随莲女士的选择,笔者接触到了一支农场的广场舞队,发现能支撑农村广场舞走得更远更久的,正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中叶的制度遗产,比如国营农场制度,由于制度的保障,广场舞者获得了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稳定感,她们更能没有后顾之忧地投身广场舞活动,不仅享受文化带来的快乐,而且积极地寻求社会和政治层面的意义,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实现感。
在中国,“创办国有农场是新中国追求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战略举措之一,国家领导层希望由国有农场作样板,引领和推动全国农业的集体化和现代化。”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大批农场得到新建或扩建,开垦了大片的荒地、荒滩。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中小型农场纷纷改制,大多划归到了地方。“国营农场的现行体制既不同于集体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因为农场是农业领域中的国有企业,也不同于一般的国有工商企业,因农场地处农村,以农为主,在运营和管理上与农村人民公社多有相似之处。”农场职工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介于工与农之间。
在集体农场的时代,他们是工人身份,享受工人的福利待遇;农场改制后,他们大多成为农民,住在农村,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与普通农民无异,仅有的区别在于有无退休金。但是,追随广场舞的队伍,走向文化的深处,就会发现这一制度遗产与历史记忆的“合奏”,两者共同影响了今天农场广场舞的实践,但前者却是常常被遗漏的。一方面,制度遗产提供了退休金保障和心态上的安全感;另一方面,曾经集体主义时代农场组织过舞蹈队、合唱队,在一代人心中留下过歌舞记忆,农业生产与歌舞娱乐是一种统一的生活方式。在此后种地和打工的岁月中,农场农民对舞蹈的兴趣或许被遮蔽,但没有消逝,如今借助广场舞的契机,这一切都得以复活,舞蹈重新介入生活、介入政治、介入公益,体现出比一般农村广场舞团队更高的意义追求。
如果说,赵月枝、张慧瑜、周怡等人的发现在于以“主体”“空间”和“文化”的方式将以广场舞为代表的当代农村文艺和社会主义历史建立勾连,那么本文的贡献在于,从倾斜的城乡关系入手,重新发现了20世纪中叶社会主义初期的制度遗产在今天农村文艺中的积极作用。
事实上,不只是农场制度之于乡村广场舞,20世纪中期的制度遗产在当代农村文艺实践中依然留有广泛的影响。比如农村俱乐部,缙云县“15人以上的农村业余文艺团队686个,只要有节会文化活动,就有大批的志愿者来帮忙,一起做群众文化服务。2018年春节期间,全县举办乡村春晚163场,主要都是在志愿者支持下做起来的”。这样一支庞大、且有组织性的农村文艺队伍得以活跃至今,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农村俱乐部——在农村精耕细作三十余年的基层文艺组织——有着重要的传承关系,当代农村文艺活动重新繁荣,良好的群众文化土壤至关重要,但这个土壤不会凭空而来。诚如张炼红所说,当年的“人民性”在今天的意识形态中,正是以某种“民间性”来呈现的。
如刘岩所说,他之所以要再现和讨论“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的各种文本与文化现象”,是希望可以“最终抵达对蕴含社会主义经验的文化生产的未来可能的尝试性探究”。或者如王洪喆重新发掘社会主义生态和城乡建设的思想史之后,认为这有助于“将对当下城乡问题的理解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战略认识当中”。同理,我们今天将农村广场舞与国营农场的制度遗产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也是企图肯定并强调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并从中找寻面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可能,以打开新的想象。
注释:
① 王红涛:《芜湖市广场舞的开展现状与推广研究》,《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23页。
② 李蕊:《豫南地区广场舞开展现状调查研究》,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页。
③ 马裕文:《常熟市区广场舞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研究》,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1页。
④ 张海英:《论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赤子》,2014年第16期,第176页。
⑤ 王芳:《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科技创新导报》,2012年第29期,第241页。
⑥ 金园园:《探讨广场舞在群众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大众文艺》,2014年第12期,第19页。
⑦ 材料来源:http://sh.people.com.cn/n2/2016/1107/c134768-29268944.html。
⑧ 陈杨贵、陈宇家:《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视角下分析广场舞的作用》,《体育世界(学术版)》,2016年第1期,第22页。
⑨ 刘甫晟、谭达顺:《科塞冲突理论视域下广场舞的社会学分析》,2015年第十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杭州,2015年11月5日。
⑩ 王玉:《空间视角下的广场舞研究——以上海市W镇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