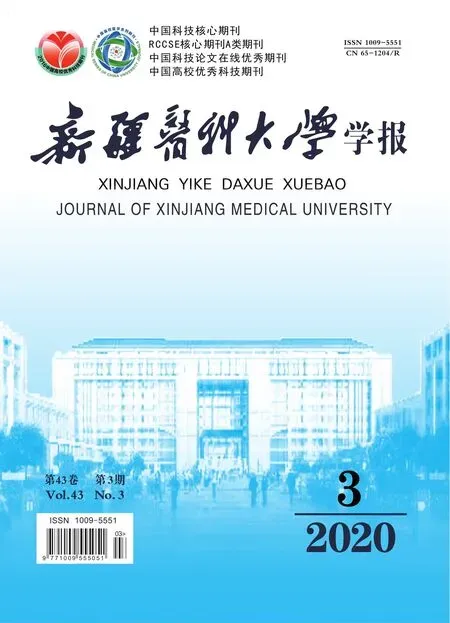基于中医经典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辨证论治初探
杜丹丹, 戴文敏, 崔媛媛, 宋维维, 彭 涛, 房 珂, 祖力米拉·吐尔逊买买提, 舒占钧
(1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乌鲁木齐 830011; 2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临床研究基地, 乌鲁木齐 830000;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感染二科, 乌鲁木齐 830000)
2019年12月初在我国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中心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以极强的传染性,在我国乃至世界迅速蔓延。患者以发热、乏力、干咳为主要临床表现,少数患者伴有鼻塞、流涕、腹痛和腹泻等症状[1],严重者快速进展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能障碍等[2]。目前尚无针对COVID-19的特效抗病毒药物,然而数千年来,祖国传统医学在“疫疠”、“瘟疫”等传染性疾病的认识和防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COVID-19属于中医学“瘟疫”范畴,病因为感受“疫气”,病位主要在肺脾胃。由于疫邪暴戾特性,新型冠状病毒从口、鼻、皮毛侵入人体后,迅速充斥表里、内外,弥漫上、中、下三焦,易造成多脏腑、组织的损害。鉴于中医在“疫疠”、“瘟疫”等传染性疾病方面治疗的优势,“辨证论治”、“有是证则用是方”等,早期、全程参与COVID-19的治疗,发挥中医药在COVID-19防治中的个体化优势,以期改善患者的症状及预后。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医理论对COVID-19进行探讨。
1 中医对COVID-19的认识
COVID-19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流行性、季节性和区域性,以急骤起病,传变迅速,病情凶险为特点,在病因病机和临床症候方面与瘟疫相似,所以COVID-19属于“瘟疫”范畴。历代医家对瘟疫的病因认识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素问·刺法论》提出了“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吴又可在《瘟疫论》中明确提到:“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认为温疫只有热证阳证,绝无寒证阴证,即使见到瘟疫厥逆之证,亦只是阳厥而非阴厥,强调 “客邪贵乎早逐”的治疗原则。《瘟疫论》云:“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说明了本病的发病取决于人体的正气的强弱和邪气的盛衰。《疫疹一得》云:“以其胃本不虚,偶染疫邪,不能入胃”,说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灵枢·经脉篇》云:“肺手太阴之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叶天士《温热论》云:“温邪上受,首先犯肺”。《温病条辨》亦云:“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肺”。COVID-19的传播途径以呼吸道飞沫传播为主,病毒首先由口、鼻、皮毛而入,首先侵袭手太阴肺经,肺为娇脏,且在上焦,最易受邪。肺与大肠相表里,肺部发病多会波及大肠。脾五行属土,肺五行属金,土生金,脾为肺之母,子病犯母,肺病及脾。此外,温疫为病,往往常兼夹秽浊之气,因此COVID-19患者多伴有腹泻、乏力、恶心呕吐、脘痞胀满、腹泻或便秘等表现。
人群普遍易感新型冠状病毒[2],疾病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人体的正气强弱和邪气盛衰两方面。人体正气强盛则病邪不易伤人,不能引起发病,即使发病,病情也相对较轻,倘若疫疠病邪太盛,超过人体的防御功能,即使人体正气尚无明显不足,也难以抵御疫疠病邪的侵袭。随着病邪可向里传变,表现为表病,里病,表里同病等不同类型,其表病为邪热郁于肌表或里热浮溢于表,里病又有上中下之分,有湿热内馈胸膈,阳明实热,劫烁阴液等病理变化。
已有研究认为COVID-19的中医病因病机为寒、湿,其中以湿邪为主要的病理特点贯穿疾病的始终[3-5],认为可以用“寒湿疫”作为新冠肺炎的中医命名[4-6]。通过对COVID-19患者进行尸检结果显示患者肺部渗出性反应严重,在肺部较深部有黏稠分泌物[7],提示COVID-19患者疾病过程中存在痰饮疾患,此处的痰饮为患者感受疫毒以后,机体的病理产物。《金匮要略》云“血不利则为水”,提示血滞可生痰,严用和《济生方》亦云“人之气道贵乎顺,顺则津液流通,决无痰饮之患。调摄失宜,气道闭塞,水饮停于胸膈”,《仁斋直指方》中认为清稀为饮而稠浊为痰。故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建议应该兼顾对痰饮的治疗和调护。
2 COVID-19的疾病分期与传变
COVID-19早期(潜伏期)、中期(进展期)、极期(危重期)、后期(恢复期),其中早期大概1~10天、进展10~20天、极期(危重期)20天以上、恢复期1周左右。
早期患者是指早期确诊和疑似的病例,也包括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处于潜伏期的患者。肺为娇脏,乃清虚之地,肺主皮毛,故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脾主运化水湿,同气相求,湿性疫疠之气,常可直取中焦,易伤脾胃。脾土生肺金,母子相生,共同受邪。治法可参照邪在上焦卫分,宜辛香透达,多用芳香清宣药物如藿香正气、三仁汤等。吴鞠通讲:“治上焦如羽, 非轻不举”,叶天士云:“在卫汗之可也”,薛生白认为:邪在表分用药取藿香、香薷、苍术皮、薄荷、牛蒡子等味。总之,早期治疗宜谨慎,细化各种体质,证候类型,对早期治愈,防范传播,控制疫情十分重要。
中期是指确诊病例早期失于治疗的阶段。叶天士在《温热经纬》云“在阳旺之躯,胃湿恒多,在阴盛之体,脾湿亦不少,然其化热则一”。湿性浊毒留恋日久,郁闭肺气,或因感染患者体质阴阳状态的不同, 或因治疗不当,湿性浊毒转归从化,变证随起,出现肺炎的重症阶段,治疗上参照邪在中焦气分,当分清湿热孰轻孰重,湿重者宜苦温燥湿为主,清热为辅如藿朴夏苓汤等;热重者宜苦寒清热为主,化湿为辅,如王氏连朴饮、黄芩滑石汤等;湿热病重者宜清热化湿并举,如甘露消毒丹,苍术白虎汤等;若湿浊化热,阳明热盛,则用白虎汤,若阳明腑实则宜凉隔散通腑泻热,灵活加减运用,及时采用“病证结合,中西并重”的诊疗措施,提高综合救治效果。
极期是指确诊病例或失于治疗,湿浊毒邪,进一步化燥伤阴,内闭心包;由于真阴耗竭,失血过多,气无依附,真气外脱,呈现一派“内闭外脱”的凶险证候。病情恶化出现或可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感染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多脏器功能衰竭,肺部CT检查有大量的渗出的重症危象阶段。此时当“病证结合,中西并重” ,及时采用吸氧合呼吸机支持等,提高患者的生存效果。
后期是指各种确诊、疑似病例和医学观察期的患者,经过治疗表现为余邪留恋,邪去正虚;肺脾气虚,气阴两虚阶段,此时治疗以扶正为主。
关于本病的传变,薛生白在《湿热病篇》中提出:本病存在顺传的正局和逆传的变局。湿性黏滞,病程缠绵,留恋在肺,在一经不移。大部分患者在疾病早期经治疗后好转,是为顺证。若病情在10~14 天逐渐出现高热、神昏、喘憋、咯血、便血,此为湿浊疫毒从化,从寒则困阻中焦、清阳不升,邪伏膜原、蒙蔽清窍;从热从燥,则湿浊化热化燥,热壅肺胃,耗伤真阴,灼伤脉络,甚或内闭心包,出现阴阳离绝的危象,是为逆证。
3 COVID-19的中医辨证论治
根据中药药物防病治病的基本作用,不外是驱邪去因,扶正固本,协调脏腑经络机能,从而纠正阴阳偏盛偏衰,使机体恢复到阴平阳秘的正常状态,即以药物的偏性,纠正疾病所表现的阴阳偏盛或偏衰。清代医家钱潢曾说:“受本难知,发则可辨”,根据在疾病中机体发生的反应,利用方证对应的原理,选取对证的方药进行干预,整体调控调和阴阳,疾病自愈。因此,针对COVID-19的中医治疗,临床医生应该望闻问切四诊合参,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舌象脉象,并结合西医疾病原理,把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结合起来,从而准确把握疾病的病位病性病机,辨证施治。李筱等[8]通过对COVID-19中医证候学的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发现,50%的患者以发热、纳差、乏力、咳嗽为主证,多数患者舌质淡红、红,腻苔、白苔;脉象表现以沉脉、滑脉、数脉、濡脉为主,这为COVID-19证型的准确辨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COVID-19初期以祛邪为主,恢复期以扶正为主。李东垣在《脾胃论》序中提到“百病皆由上中下三者,乃论形气两虚,即不及天地之邪,乃知脾胃不足,为百病之始”,故临床医生在治疗中要顾护患者脾胃,脾胃运化正常,人体正气得以充养,则不易染病。COVID-19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有发热咳嗽气喘,胸胁部不舒,或者合并胃肠的症状,如恶心呕吐腹胀泄泻等。临床症状中存在复合证,因此需要合方应用,即有是证则用是方。伤寒论六经病在传变出现合病与并病,使用麻黄桂枝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柴胡桂枝汤等就是合方应用。辨证论治的本质是一种信息处理的过程,而遣方用药就是向患者体内输入信息的过程,只要方证对应就可能起疗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全国推荐的清肺排毒汤,就是根据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观点,归纳出各种方证,把这些相关的方证综合在一起产生的是由五苓散、小柴胡汤、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四首经方加减而成,此方偏于温散,适合气温偏寒地区。广东气候偏温,肺炎一号方是以山慈菇连翘为君药,清解疫毒,化痰散结,柴胡青蒿蝉蜕前胡透热于外,金银花黄芩清上焦肺卫之热。经临床治疗后,患者症状改善明显。COVID-19的第七版指南中疾病证型为轻型(寒湿郁肺、湿热蕴肺)、普通型(湿毒郁肺、寒湿阻肺)、重型(疫毒闭肺、气营两燔)、危重型(内闭外脱)和恢复期(肺脾气虚、气阴两虚)。而清肺排毒汤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而且在危重型患者的救治过程中可以结合患者病情的实际情况合理应用。学术无疆界,治病在疗效。在COVID-19的中医治疗上,伤寒论是基础,温病各书是发挥,还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更要结合疫病具有传染的特点。
4 结论
中医的证可以对应西医多种类病,而西医概念上的病又往往体现传统中医上证的复合。在辨证论治上要抓住疾病的本质,针对性的遣方用药,便可药到病除,不可见一症用一药,也不可千人一方。临床在诊治COVID-19时要结合具体 情况,三因制宜,这也体现了中医的个体化辨证论治思想,及同病异治思想。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中医对于“疫疠”、“瘟疫”等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有目共睹。总之,中西医结合治病才能发挥更大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