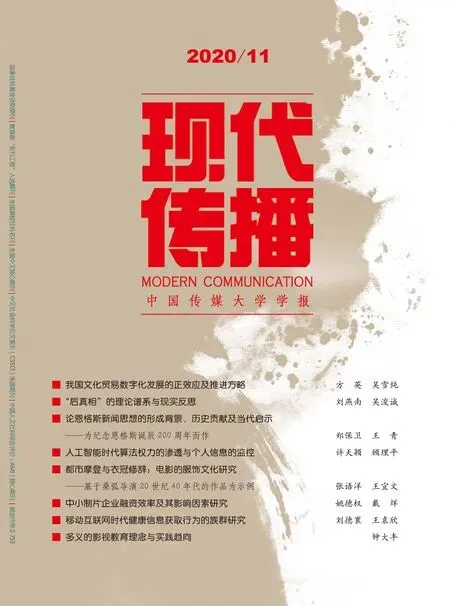“人工智能”思想溯源与教育精神的返回
■ 周廷勇
人工智能已经被提升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战略规划层面,进入到人类生产劳作的广泛领域。世界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对人工智能的反响也非常热烈。人工智能在现实中既有一种完成状态,也有一种发展着的状态,当然它也有可能会如广播和电视那样因为技术迭代成为稀松平常之物。无论是将目光聚集在“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的问题,还是着眼于研究人工智能的技术性特征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亦或是着力于人工智能在教育实践中的布局并推动教育变革,不可回避的首要的、根本的问题是“教育如何回应人工智能对人类命运带来的挑战”?因此,最为急迫的事情是,深思人工智能如何以其隐蔽的丰富本质凸显于人类生活之中。如此或许能有所领悟地观看到人工智能即将供奉出何种人类命运的未来,并由此略现当下和未来教育的微弱光亮。
一、人工智能的历史坐标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相生相随,迄今为止经历了80年的发展历程。尽管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纪40年代埃达·洛夫莱斯(Ada Lovelace)伯爵夫人对人工智能的预言,但是由于她没有提出实现人工智能的方法,因此,直到1936年,才由艾伦·图灵(Alan Turing)提出“通用图灵机”真正地解开了实现人工智能的谜团。①1950年,图灵在《计算机和智力》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他指出,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如果有超过30%的测试者在与计算机进行交互时,不能确定自己是在与计算机还是在与人类交互,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具有和人类一样的思考能力。②图灵的这篇文章第一次讨论了“机器能否思维”的问题和“人工智能”的概念问题。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马文·李·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克劳德·埃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纳撒尼尔·罗彻斯特(Nathaniel Rochester)四位学者发起“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提出人工智能的研究目标是制造模拟人类的机器,“让机器使用语言、进行抽象思考和形成概念,解决只能由人类解决的问题,并不断提高自身”③。自此以后,人工智能产生了符号模型和联结模型两种理论假设及其技术形态。④
符号模型人工智能实际是使计算机模拟人的形式推理或机械化推理过程,它源于约翰·麦卡锡提出的一个假设:学习或者任何其它的智能特征原则上都可以被精确地描述。这个假设把人脑和计算机都视为物理符号系统,并认为物理符号系统是智能的充分必要条件,认知的过程是符号运算过程。1976年,纽厄尔(A·Newell)和西蒙(H·A·Simon)提出了一种知识驱动或规则驱动的符号模型,知识库和推理机是这种模型的关键机制。⑤符号模型人工智能目前发展比较成熟的是由专家经验整理出来的普遍化知识组成的专家系统,其经典作品主要有IBM公司研发的深蓝(Deep Blue)系统和沃森(Watson)系统。1997年5月,IBM深蓝系统打败了当时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尔·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2011年,IBM沃森系统在综艺节目《危险边缘》中打败了最高奖金得主布拉德·鲁特尔(Brad Rutter)和连胜纪录保持者肯·詹宁斯(Ken Jennings)。
联结模型人工智能基于统计学原理和数据驱动,它并不用事先设定好的规律—规则去处理特定的问题,而是通过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算法,识别出事物的模态并让此模态更具可度量、可验证的特性,从而以此为基础识别不确定的事物,完成相应的任务。这个模型吸取了神经科学的许多理论成果,从脑科学的“神经元”概念中获得灵感,因此它有一个吸人眼球的别称——神经网络模型。它的经典作品是“阿尔法狗”(AlphaGo)。2016年3月9日—15日,韩国的九段围棋手李世石与“阿尔法狗”之间进行了一场世纪人机大战,李世石以1比4的总成绩负于“阿尔法狗”。“阿尔法狗”在此次人机大战中的致胜意味着人类在类神经网络系统、深度学习和价值评估策略等方面的假设在技术上实现了突破式进展。⑥
由于人类大量的行为、知识与推理机制充满许多不确定性,也难以计量化,机器语言难以对人类的行为、知识和推理机制进行精确描述,因此,符号模型和联结模型的人工智能目前都只能解决特定领域的、静态的、确定性的问题,而不具有推理能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更谈不上能和人一样具有自主意识,尤其是现有的人工智能做不到像人一样根据情境随机应变、由表及里、举一反三。人工智能的未来还充满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当然,也正是因为现实人工智能的“不能”,刺激人们在“不能”中寻找“可能”。据一项在调查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意见基础上的预测,2040年将出现强人工智能,2060年将出现超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是有知觉的、自我意识的智能机器,它能够感知周围环境,通过推理解决问题,最大程度地实现预定目标。超人工智能能够在信息不完善、甚至缺乏信息、数据和知识的情况下,比人类最聪明、最有天赋的人在完成多领域、非确定性的、动态性的任务方面还要完成得好。⑦这些信念并非完全幻想,而是有其现实基础。实际上,在解决符号模型和联结模型的“不能”过程之中,人工智能技术于20世纪末已进入第三代。⑧第三代人工智能是基于行为的人工智能,它聚焦于复杂环境下机器的行为控制,着力于智能机器与环境的互动,其标志性口号是“用世界本身代替世界的模型”,其经典作品是正处于研发之中的自动驾驶。⑨第三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意味着开启了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迈进的道路。
二、“人工智能”思想溯源
人工智能是现代以来技术的本质开始显露并达到统治地位的结果。人工智能看似横空出世,但实际上它的每一个零部件都扎根于历史深处,有其自然机缘,是自然在人类与天地万物的交互之中早已为之预备好的。这种预备是从人在生存、繁衍以及与万物共存的历史进程中发明、制造和使用工具开始的。人类文明史的核心构成部分即是工具的发明、制造和使用的历史,也即是技术发展史。走入世界任何一家博物馆,能够看到最多的东西就是人类用石器、青铜器、铁器、机器等各种器具在天地万物中留下的印迹。作为自然之子,人在其开端之处,就是“自然存在”和“技术存在”的集合体。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已洞见到人的这种双重属性,认为人的“技术存在”高于其“自然存在”,将“技术存在”拔高为人的本质。他指出:“惟有人才凭技术和推理生活”,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理性的创制品质”。⑩作为一种创作物,人工智能蕴含着什么样的理性品质?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曾对此做了深入剖析。他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上假设大脑和计算机都是按照形式规则加工信息的装置,在认识论上假设知识可被形式化、能通过逻辑关系表达出来并被理解,在本体论上假设世界可以被分解成与情境无关的数据或原子事实。我们试图在此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静观人工智能隐蔽的丰富本质何以凸显于人类生活之中。
首先,计算主义为人工智能的实现架起方法论桥梁。柏拉图最先开启西方哲学的计算理性思想。柏拉图认为,数学是一门有牵引力的学问,是“一切技术的、思想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要用到的”,面对可见世界的可变和信息杂多,正是“计算能力和理性”使灵魂脱离可见世界的可变和杂多,从而把握真正哲学的实在,“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在笛卡尔、莱布尼茨、霍布斯和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等人的努力中,人们探索到运用代数计算对事物特征进行数量特征表示的密码,并将其原理在机器上加以实现。弗雷格、罗素、怀特海和早期维特根斯坦都对符号模型人工智能产生重要影响,他们的思想的共同之处是,认为思维是用符号表示的逻辑过程,世界可以通过符号逻辑得以还原和形式化。在这些思想影响之下,形成了计算主义的核心信念,认为物理世界、生命过程和认知活动都是可计算的,“甚至整个宇宙也是由算法控制的”。认知可计算的设想正是人工智能从潜能到实现的关键,当前三种人工智能模型的差异或分歧之一便是算法不同。
其次,人的理性被降格为智能,为人工智能的实现备好认知基础。这在西方哲学的突破期就已开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运用“线段隐喻”讨论了人的灵魂的两次转向,第一次是灵魂由可见的和可变的世界转到可知的和永恒的世界,也即从想象和信念转向理智和理性。第二次是灵魂在可知世界里由理智转向理性,再由理性回转到理智。柏拉图描绘的灵魂的这个运动过程,实际上是理性降格为智能的过程。亚里士多德承继这个思想脉络,他在思想人的“技术存在”时,否定了人的灵魂中的无理性部分,确立了“推算”在理性灵魂中的地位。他认为,虽然人通过经验得到了技术和科学,但是,由于有技术的人“有理性、懂原理、认知原因”,因而,“有技术的人比有经验的人更加智慧”。智慧的获得,不能靠感觉,而是要由“有欲望的理智”和“有理智的欲望”在行动中达成。将人的欲望提升到智能程度与把人的智慧降格为智能,可谓殊途而同归,都证成了技术存在和技术理性,技术成为获得确定性真理的一种方式。智能从理性中分离出来,使人类能够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分解智能,从符号再现与运算能力、经验学习能力、人与环境互动的能力等方面定义智能,从而为符号模型、联结模型和行为模型的人工智能的出现奠定认识基础。
再次,创制科学理论为人工智能的产生铺陈实践论基石。创制科学理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创造。在承续柏拉图可变世界与不变世界的划分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划分出思辨科学(研究不变世界)、实践科学(研究与人类事务有关的可变世界)、创制科学(研究与自然事物有关的可变世界)。创制科学奠基人的技术存在。创制科学的产生源于创制活动,创制活动的本质是人的潜能的实现,潜能是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礼物,表现在人类的现实活动之中。人在“审视某种可能生成的东西怎样生成”的基础上,改变事物自身的运动状态,从而完成了潜能到实现这一运动过程。创制科学理论蕴含着真理观念的变化。在古希腊人那里,真理起初是动词意义上的“观审”。观审的生活是最纯粹的思想形态,是最高的行为。在《形而上学》开篇,亚里士多德将“求知”与“观看”联系起来。然而,虽然亚里士多德保留了思辨科学作为科学的科学之最高贵的位置,但他因将实践科学与创制科学视为与人的事务最相关的科学,从而为实践科学与创制科学预留了最重要的位置。这表明希腊人的真理观念已经悄然变化为:能够改变灵魂的哲学,是行动的而非言谈的,是实践的而非静观的。人类由此被求行动的意志所攫取,这种意志中蕴藏着强烈的制作欲望和成效欲望。人工智能正是人类这种求行动意志中的制作欲望和成效欲望的涌现带来的。
最后,对人之本质和存在者之本质的双重叩问为人工智能扎下存在论根基。海德格尔指出,人之本质与存在者之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共属一体的,在说出“人之本质”时,就已经道出了与存在的关联。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存在者之存在,它所道出的人之本质乃是:“人是理性动物”。在这种人的本质规定之中,人被构造为理性和动物性的独特结合。动物性是感性。感性关涉肉身和形体。在西方思想运演历程中,主流的观念认为,只有人从感性、肉身和形体的存在过渡和穿越到非感性、非肉身和非形体乃至超感性、超肉身和超形体的存在之时,生物的、动物的人才生成为“真正的人”。笛卡尔明确地开启肉身和理性的二元划分。在笛卡尔那里,肉身似钟表,是一个机械的、自动的装置,灵魂能够出窍,思维可以脱离肉身,肉身成了自动的、机械的空壳,只有“我思”才能真正确定“我在”。尤其是在加入“一般主体”这个概念之后,在向超感性、超肉身、超形体过渡之中,世界存在越来越被对象化,这个能够“灵魂出窍”的人甚而至于脱离世界存在这个基底,人的本质显现为“无根基性、永恒性、不依赖于时间性、自身肯定”的特性。肉身虽然会消逝、可以被消灭,但是心灵和精神不会消散、而是永恒的。人类存在的历史甚至可以被视为理性对动物性的驯服、灵魂对肉身的规训的历史。尤其在计算理性加快步伐攫取人的心灵和精神过程之中,人的心灵和精神被化简化约为智能,智能接管了人的身体,而智能被数理逻辑和现代科学接管,被化约为符号的再现过程。在这样的智能观念下,人类行为在智能的管制中受到形式化的、技术性的改造和加工,“无身体的智能”应运而生,智能被视为运行在一个称为大脑的计算机硬件上的“软件程序”,开启了人工智能的制作和运行,更进一步强化人对自身身体的智能化改造和加工。
催生人工智能的这些深层思想观念是由存在论贯通的。会说话、会思想的人类将人设立为自然之生物、动物,并以理性作为人与自然中其它生物的界限,确立“人是理性动物”的人之本质观念。这种观念设定人的理性对动物性的驾驭和超越。理性超越动物性,实际就是压低、限制人的自然本性。理性被化约为智能、被理解为人的心灵对存在者的觉知中呈现的推理能力。在创制科学观念之下,通过计算主义的运作,抽离了作为“自然之生物和动物”的人之“生动”,人被视为从某种技术上可制造的“自然之物”。
三、人类命运的岔路口
人工智能近在眼前,触手可及,但它的思想道路如此迢远而隐蔽。可以预见它也将远远而去。在为它的远远而去做准备的现代科学图景之中,从各个方向而来的研究正对人形成一种合围:神经科学研究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的生理机制;生物学研究人的基因甚而进展至人造肉身并试图揭示生命的密码;心理学研究感觉、知觉、注意、表象和记忆等关于人的意识的心理机制;语言学研究人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的语言运用和加工机制;逻辑学研究人的概念、判断、推理、证明、决策和问题解决的思维机制;文化学研究自我、他人、社会、文化、自然、进化等关于人的文化机制,计算机科学研究上述领域的现实操作机制和完结状态。所有这些科学活动,似乎都在为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的最后一跃聚集力量,很有可能由此制作出一个超越生物性存在的“大脑”甚至超越生物性存在的“人”。
但是,人工智能本质上不是任何人性的东西,它仍然只是一种人类的制作物,它建立在一种已经完成的、确定的人之本质和存在者之本质基础之上,“人工”两字意味着“人工”并不等于“人”。因而,人工智能以及为着它的远远而去做准备的各种研究人的学科,似乎是为了给人在世界秩序之中寻找一个突出的、特别的位置,但实际上,如果它们只是试图一劳永逸地定义人并为人绘出一个恒久不变的画像,那么它们就都还没有准备真正地去倾听人、思考人。人在本质上是生长着的、未完成的、是开放的,一旦将人的本质固定下来,那么这个固定的人之本质就将把人锁得牢牢的,这样人就会不停地消失。建立在这样一种锁定的人之本质基础上的技术和科学将会和其它技术一样支配着人的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类有时候太过于自信地以为,能够通过审视技术的经济、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而建立人类在技术面前的优越性和自主性,从而驯服技术。实际上,技术性地谈论人工智能的缺陷,或是谈论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性问题,都还不能让我们触及事情的关键。人们还不可能知道,人工智能时代的现代人,有朝一日成为智能工人意义上的人之时,他还能够从事何种人工;更不可能知晓,当今天的人类处于与人工智能的某种关联之中时,人类到底逗留在何处。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的本质虽然只是初露端倪而还未完全展开,但是在其还未完全展开的本质中所蕴含的思想观念已经开始将人类命运带入日益鲜明的分岔道路之前。
首先是人的本质之脆弱根基中显现的身体和心灵之关节点上的分岔。这条分岔由柏拉图开启。在《斐多篇》中,柏拉图指出灵魂优于身体、主宰着身体,而身体会阻碍人认识世界,甚至会把灵魂引入歧途。笛卡尔更明确有力地在身体和心灵之间划出一道鸿沟,把思想解释为一种与肉身相分离的活动,将意识和心灵视为存在的基础。自此之后,身体与情感、欲望和非理性相关联,心灵则力图超越并驾驭身体,并与理性为伍,理性被化约为智能,智能被定义为形式化和程序化的规则规律,规则规律被逻辑关系锁定,逻辑关系被数字编码,心灵在这样的出走道路之中被机器接管,由机器接管的心灵展现的理性看似来势汹汹、威力无比,实际上却让理性之路越来越狭窄。将心灵从身体之中抽取出来,并将心灵化约为可计算的智能,抽离的是人之自然,造就的是一副人的牢笼。无身的智能在根本上排斥和全面驱逐人的记忆,不能向存在之物和世界敞开自己,很难超越自身而观看。心灵出离身体之人,有如一棵大树被抽干了水分,它的躯干是僵化的、没有活力的,水分却四处飘荡、吹散乃至蒸发,人漂浮于其存在的根基。在理性如水分游荡并漂浮于天花板之际,理性只想回到它一直竭力超越的、鄙弃的身体及其所象征着的非理性那里,可是它们分离太久无法相认,人因此生活在摇摆和分裂状态之中。
其次是人的存在之脆弱根基中显现的人的存在和自然存在的分岔路。创制科学观念将静观的、观审的科学观念转变为视科学为由潜能转换为现实的创制活动,刺激了人追求成效的意志,从而开启人将自然作为对象、将自然设为对立面的道路。随着人的主体性意识的突显、世界进入图像化时代,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成为“对现实的极其干预性的加工”的科学。人类自我意志的强力贯彻越来越提升到对天地万物的加速改变、强力改造乃至疯狂加工,甚至人自身也被作为物而被改变、改造和加工。这种在人和自然存在之本质基础上进行的加工改变着人和自然存在之本质。在人从“自然之生物、动物”到“理性动物”再到“自然基本粒子聚合体”的本质之转换过程中,人的肉身、感性、情绪、情感、欲望、本能被剔除,人性被抽离得如此干巴巴,没有一丝血色与活性,人首先脱离了自身的自然,从而脱离自然之存在。这种脱离自身自然之人在对自然的疯狂褫夺之中将自然弄成一个满目疮痍、难于处理的客体,人的存在脱离自然,开启了人的星球流浪命运。今天人类的处境就像从生态优美的河流通向干燥的沙滩的鱼儿那样,只有竭力挣扎蹦跳于沙滩之上。人工智能便是在人类寻求让自己能够成为技术上可以被制作的道路之际突现于人类生活之中,是人类在沙滩蹦跳之际为了让自己活命的下意识之举。但是,海德格尔指出,如果人在技术上成功地制造自己,那么,“人就把他自己炸毁了,亦即把他作为主体性的本质炸毁了……于是绝对无意义的东西就被当作唯一的‘意义’……”。
然而,人类思想中闪现着一些微弱光亮,它们在阴影处照射着这些分岔路,让我们看到何者为歧路,何者为正道。海德格尔指出,存在与思维共属一体,它们之间没有距离,人的本质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人在其存在中“有所领会地对这一存在有所作为”。现代科学体系之下的脑科学研究、神经科学研究,也已经看到智能不再是一种符号运算和再现的过程,它归属于身体,有其运行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在探索智能、心灵和大脑之间的关系的途中,现代科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智能观念:智能源于心灵,心灵植根于大脑,神经元是大脑的关键,思维的运行依赖于神经元的整体激活。大脑并非如“缸中之脑”的假设那样能够独立产生智能,大脑与身体的双向互动才可能产生智能,即是说,智能来自于人身体之整体。因此,要理解大脑如何思维,“就有必要考虑到其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这样的认识轮回,似乎正探寻一条道路,以让身体和心灵、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对立返回到其共属一体的整体之中。
四、教育精神的返回
催生人工智能的思想观念将人类带上了什么样的教育道路?首先是教育的灵魂转向,教育的根本任务被认为是促进人的心灵发展。人的身体的发展被认为有其自然顺序而不需要特别干预,因而教育并不特别着眼于人的身体发展,或者说,身体的发展只是依附于心灵的发展。其次,转向灵魂之教育助力人之理性超越人之动物性,通过人的主体性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生长,划分出自然和人性的界限,从而在世界秩序之中为人找到一个特权的位置,使人不再受制于劳动、生命和语言,人因此得以在其有限之中追寻无限。再次,人的心灵被视为一种信息处理系统、一种计算装置,通过教育所生长的理性精神被降格为智能,智能被视为一种固定的联想和习惯的形成,固定的联想和习惯的形成之实质是接受它们自身蕴含的可以形式化和程序化的规则。最后,在如何塑造人的心灵问题上,教育逗留于计算主义的思想道路。在语言和数学因素的结合之中,通过对人类联想和习惯形成的规则进行编码,使之被分门别类地存储在人的记忆之中,能够随用而提取和重述,进而试图在分析人类行动的大量原始“素材”基础之上,区分出那些能够被计算的东西,并通过这些被计算的东西去寻找更多可以被计算的东西,从而将复杂的事物转换为简化的、确定的规则,并运用它们去调适未知的复杂世界。计算主义教育道路的最重要的结果是催生“通过机器教育人”的意识和行为。广播、电视、计算机都曾是对人类行为和世间万物的规则进行形式化和程序化的信息集成系统。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可能是实现“通过机器教育人”的理想中介。通过算法,问题、情境和解决办法被写入到计算机程序,世界被分解而又被整合入“内存”中,计算机犹如“字典”,遇到未知情境时,可以在简化重述未知情境的特征基础上按图索骥,在“查阅”行为中作出拟人的回应。
在对人工智能的思想假设所蕴藏的教育道路的追述之中,我们看到人类教育遵循“自然—人性—人工”的演化路径。人类受之于自然的教育褪去之后,是受之于人性的教育,而受之于人性的教育似乎正在匆忙地奔向受之于人工的教育。这种人工的教育是物化教育的极点,把教育带到技术化的高峰。世间之物无外乎自然存在物和人类制作物,自然存在物带来的教育越来越少,人类制作物带来的教育充满各处。技术化不单是指教育领域被技术所充溢或通过更多的技术来实施教育,更是指教育自身转变为一种生产和加工人的技术。在“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的论断中,“培养”两字蕴含的“栽培”“养护”的意思尚保留了对自然之人的敬畏,但“加工”两字整个儿地将人看作是物并对之进行技术化的改造。在一般的认识之中,这种技术化的教育似乎是为了人的,因而实质仍是受之于人性的教育,仍在人类的掌控范围之中。但实际上所谓的掌控都还只是一种假定。人类现在恰恰不能真切地掌控自己的教育,在教育的各种功能和价值面前,人们自知不应如此却欲罢不能的现象随处可见。人工智能带来的教育看似由人控制,实际它的出现,是人在它的召唤之下奔波忙碌的结果,人被它安排、摆置,甚至被它控制。
因此,在人工智能世界里讨论受之于人工智能的教育,真正的使命是思考并应合人工智能如何以其隐蔽的丰富本质突现于人类的生活,以及在回应它的这种丰富本质过程之中找到教育的立身之处,如此方能让作为技术的人工智能真切地融于教育行动之中并使之实实在在地成为上手的用具,让人有机会和决心改变人类命运的未来,而非只是让人在把玩用具当中技术理性地活着。实现这样的使命,首要的仍然是思想观念上的转变。最重要的观念转变即是从原有的“自然—人性—人工”的教育道路返回,让人工返回到人性,让人性回归自然,从而让“人工”“人性”“自然”各是其是而又共属一体。希企返回这样一种教育之精神,当然既不是期望人类返回茹毛饮血的时代,也不是期望人类回到田园牧歌般的状态,而只是期望在这样的返回道路之思中重新审视人性与自然之关系。自然并非自然科学眼中的“自然界”。自然并非与人性隔绝而老死不相往来,自然与人性的关系是相互交织、相互沟通的关系。自然的意思毋宁是海德格尔考证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和本质时的解释性说明:自然“作为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者之存在”是“从其自身而来的运动事物的运动状态的起始占有”,它是原因,招致某物,让存在者成其所是。与自然对立的乃是“人工产物”。人工产物的运动状态的起始占有不在其自身之中,而是在它的制作者之中,它怎样生成,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何以沿着“人工—人性—自然”的教育道路返回呢?一是让自然有机会是其所是。人类对自然作一种观察的、人类意志彻底贯彻的、极其干预性的加工态势所经历的时间可谓久长,正是这样的加工态势使得人类制作物愈丰富,则人类自身的根基愈脆弱。“人只是一个标志、一个显现者”。自然不是站立在人的对立面。人只是在自然之中领受自然的赠予。让自然有机会是其所是,人才能有机会向自然之树那样将自己的根深深地向大地延伸,将自己的枝叶自由地向天空伸展,与大地无缝连接,与天空和谐共处。二是让人有机会站立在他所站立之处。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者,人是生物、动物,这意味着人是生长与运动着的生命体。身体是人作为生长着与运动着的生命体的根本,是自然的造化,它们是一个整体。眼睛、耳朵、嘴巴、鼻子、手、脚等脱离了身体,也都不再是它自身,不再属人,人也不再是完整的活生生的人。只有智能、心灵、理性返回身体,和身体一起生命着、劳动着、对话着、思考着,于追求无限永恒之中承认有限、返回有限,人的存在才是可确定的。三是让教育有机会站立在它站立之处。从教育的视角看待教育固然是个理想的期待,但实情是教育立身于自然与人共在的世界。长久以来,正是由于人类设计而划出群体和阶层的界限阻断了自由交流,以及将人的思维视为是独立自主的、是与身体和物相分离的观念之影响,从而带来了学校与生活、活动与课程、经验与思维、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儿童与成人的对立,教育因此难以站立在它站立之处。在教育的立身之处,教育应似阳光和空气之于植物一样既在又不在,它只是在自然之中小心看护着人不被杂草和害虫的干扰,用自己的阳光和空气于无声之中引出并聚集人自身的力量和精神,让人和自然相互成就,人在自然之中繁衍生息成长,自然在人的成长壮大之中得以通向壮大之自然,由此而筑牢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根基。
五、结语
人工智能对于现代人和现代教育的影响并不完全是从它的技术特性及其运作层面而来的,根本上是从它以其隐蔽的丰富本质突现于人类生活之中的迢远思想道路而来。这条思想道路促动人类从技术上制造自己的狂想,人之自然本性被抽离,自然被加工,人的存在根基越来越脆弱。正是此一危险在光线微弱之处照亮着教育的未来之路:教育的未来并非现在的延续,而是一种返回,由“自然—人性—人工”的教育之来路原路返回。人和自然是生长着、涌现着、运动着的,是远未完成的。教育精神的返回即是返回人之自然和人所归属的自然,让智能归于心灵、心灵返回身体,人类重回自然,从而让自然、教育和人有机会站立在它们的站立之处并相互成就。此一返回既非“停车”,也非“倒车”,只是在思想的密林之中再一次提醒人类中心论固有的骄傲是何等封闭。在返回的途中,思想并不寂寞。在《庄子》“齐物论”王倪提到“孰知正处”“孰知正味”“孰知天下之正色”,这正是破解人类中心论的绝妙辩论。从人工返回人性之路,有待于重温《理想国》和《论语》的教育之思;从人性返回自然之路,有待于慎审《爱弥儿》《道德经》和《庄子》之中的自然之思。
注释:
① [英]玛格丽特·博登:《人工智能的本质与未来》,孙诗惠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10页。
② Turing,A.M.ComputingMachineryandIntelligence.Mind,vol.59,1950.pp.433-460.
③ J.McCarthy,M.L.Minsky,N.Rochester,and C.E.Shannon.AProposalfortheDartmouthSummerResearchProjectonArtificialIntelligence,August 31,1955.AI Magazine,vol.27,no.4,2006.pp.12-14.
④ 张钹:《人工智能进入后深度学习时代》,《智能科学与技术学报》,2019年第1期,第4—5页。
⑤ A·Newell,H·A·Simon.ComputerScienceasEmpiricalInquiry:SymbolsandSearch.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vol.19,no.3,1976.pp.113-126.
⑥ 蔡曙山、薛小迪:《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从认知科学的五个层级看人机大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51页。
⑦ Tim Urban.TheAIRevolution:TheRoadtoSuperintelligence.January 22,2015.https://waitbutwhy.com/2015/01/artificial-intelligence-revolution-2.html,引用日期:2020年7月20日。参考了知乎@谢熊猫君的翻译,https://blog.csdn.net/acelit/article/details/80205543,引用日期:2020年7月20日。
⑧ 张钹、宋笛:《基于深度学习的AI技术已触及天花板》,《经济观察报》,2019年5月27日。
⑨ 肖峰:《人工智能与认识论的哲学互释:从认知分型到演进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