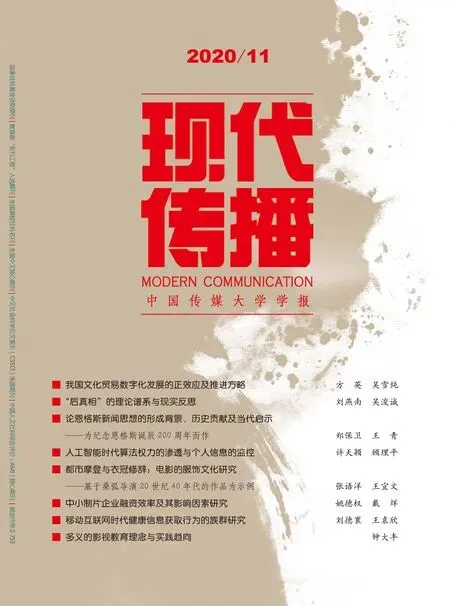“记忆作为方舟”:论文博类纪录片形塑集体记忆的媒介功能*
■ 曾丽红
一、问题的提出
聚焦历史沉浮与社会变迁的文博类纪录片大致经历了一个“展演结合”的发展历程:从最初的宏大叙事如《故宫》《国脉——中国国家博物馆100年》,到微观情境叙事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再到泛综艺娱乐化形态如《上新了·故宫》,近期则转型为更适合碎片化传播的微纪录片形态如《如果国宝会说话》。自文博类系列纪录片播出以来,《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多次发文报道与推荐,其在年轻受众聚集地B站、其他视频网站以及豆瓣网站也收获了超高人气与好评。对此,我们不禁追问:文博类纪录片缘何能够破圈层热播?其为何能够得到多元文化主体的一致接纳与认同?作为一种以影像为载体的传播媒介,文博类纪录片究竟以何种方式塑造了集体记忆的样貌与形态?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文化可以被理解为集体的不可遗传的记忆。”因为记忆不可遗传,所以需要扩散和传播,故而集体记忆天然具备一种与媒介的亲缘性。“集体记忆既不是一个和个人无关的产物,也不是像遗传一样,是生物机制上的结果。正因于此,媒介必须看作是记忆的个人和集体维度之间的交流和转换的工具。只有这样,个人的回忆才有可能通过媒介的再现和分配到达集体的层面。”①诚然,媒介及传播是推动记忆风化、变形、缩减或聚焦的首要动力。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传播通过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周遭环境”②。那么,如何理解媒介/记忆这组核心变量的历史发展逻辑?作为一个重要的传导因素,“传播”与其说是通过媒介信息的传递来影响记忆,倒不如说是通过媒介仪式的建构来形塑记忆。文化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不是指传达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传播的仪式观就是把传播看作创造、修改和改造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③固然,文化的感召与洗礼是理解当今媒介传播与社会变迁的最佳入口。藉此,本文以记忆为方舟,探析文博类纪录片的文化存储、场景联结和意识形态整饬的集体记忆媒介功能,力图以记忆的活性将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相串联。“通过将当下的影像、符号和地景与过去相连接,大众媒介使得社会的现在、过去乃至未来通过集体记忆的连续叙事得以整合”④,这种研究旨趣有益于绵延中华民族的记忆之魂和文化之根。
二、储存记忆:作为符号媒介的文博类纪录片的文化存储功能
记忆是实现时间延续的器官,其最本质的功能就是储存。文博类纪录片是一种以影像为内容载体的符号媒介,它通过影像符号将人类共享的经验封存起来,并以代际传承的方式突破记忆的时间之维。“如果我们可以回顾人类的过去的话,会发现它一直生活在充满记号的世界里。这些记号为人类开发‘世界’,使之象征化并换回它,而它的‘环境’也被置于其中。”⑤鉴于文博类纪录片是以历史文物的前世今生为创作内核,其信息制码必然包含了博物馆文物前尘往事的原始素材和证据资料,如照片、图像和文字等符号载体,这些是历史传统遗留下来的文化精髓和知识来源,也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的结晶与共享经验的见证。“传统从鲜活的载体和现时的演出转移到了抽象符号的中间地带,在那里创立了一种新的物化存在形式,即文本。”“而文本也可以‘溶化’成无形的、随时可以变革和重新塑造的大量数据。”⑥人类正是通过对数据文本的储存才得以将记忆保存下来,并将之改编、创造成为集体记忆的历史凭证与文化脚本,而这些恰好构成了文博类纪录片影像生产的硬核元素。“媒介通过将记忆物质化到数据载体上这一方式为鲜活的回忆在文化记忆里保留了一席之地。”照片、图像和文字被视为文博类纪录片最基础的历史来源,它们是知识传承和文化存储的影像基座与符号底色。于是,“文本这种形式代替了仪式。它们可以被积累、被改写、被批判,最重要的是可以被阐释。通过阐释,传统便具有历史性的发展能力”⑦。
文化是一张可以重复书写的羊皮纸,储存符号和提取信息构成了当下文博类纪录片内容生产的重要仪式。文化通过再生产超越了历史传统的断裂带,继而在人类记忆层面上建立了有意识的连续性。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文博类纪录片以影像数据等文本形态将文化储存起来,并通过符号的选调和征用建构起仪式化的意义传播空间。“每一个社会的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一整套特有的,可反复使用的文本、图像与仪式,对它们的‘培育’有助于表达和稳固该社会的自我形象。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一个群体正是在这种关于过去的集体知识的基础上,才形成了自身的统一性与特殊性的意识。”⑧吉登斯强调“构成传统的与众不同的特征是仪式和重复”⑨,通过仪式化的重复可以使其成为集体的标志。况且,“传统是认同的一种载体”⑩,通过集体对传统的认同,传统便以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进入到既存的生活秩序当中,记忆是一种与传统相聚的方式。媒介对记忆的建构通常采取遮蔽或凸显的方式,即通过外显的符号标识为集体记忆提供线索。作为存储文化的传播载体,文博类纪录片利用符号的存储、编码、组合以及再创造等功能,让传统的文化信仰再度得到印证,进而有机地培育了受众的记忆库存结构。
记忆既是记录、保存和延续的过程,也是被选择、被重组和被重构的结果,符号则是记录、延续和构建记忆的重要方式之一。凯瑞认为:“人类创造符号用来架构、传播思想与意图,用这样的符号来设计实践、事物与组织机构。换言之,他们利用符号以建构一个可以共同生活的文化。”在文博类纪录片的信息编码过程中,符号通常有三种被再现、凸显和征用的表意形态:其一是选择具有特定意涵的文物图案再现物质意象。通过文物图案的隐喻机制,“能指的制造、能指的再造、能指的借用构成了能指丰富性和多样化的机理”。如在《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中选择剑、虎符和太阳神鸟这些特定情境下约定俗成的图像符号来完成意义上的能指、所指和神话意涵。其二是选择热点时刻的影像和声音彰显文化意象。譬如《国脉——中国国家博物馆100年》对“国子监”的历史图片展示以及通过历史人物照片映射出与历史同构的文化时空。再如在《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曾侯乙编钟”中,节目直接以原始编钟发出的乐声来作为和声。其三是拓宽文字编织的“意义之网”。“凭借文化记忆,几千年的回忆空间得以展现,而正是文字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采取了节目文案的文字设计样式与文物质感相呼应的形态,如《红山玉龙:寻龙玦》和《贾湖骨笛》的标题字体设计分别对应着玉和骨笛的质感。由此可见,“作为‘术’的记忆正是以文字的这种固定能力以及存储经济的安全保障为模型;它把人的记忆以某种方式加以整理、训练和细化,使之一一成为存储话语、思想、图像和想象的大而可靠的仓库。”
三、激活记忆:作为技术媒介的文博类纪录片的场景联结功能
毋庸置疑,文博类纪录片也是一种以场景联结为形式载体的技术媒介,它通过技术媒介的链接功能将人类共享的记忆密码激活,进而突破了记忆的空间之维。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具有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特定文化社群对自己过去的记忆。“集体记忆具有连续性和可再识别性的特征。它的功能在于设计一个独特的轮廓并保证集体的独特性以及持久性。”在保证“集体的独特性以及持久性”的制度设计方面,影像媒介的技术功能凸显。“媒介和媒介化过程是个体与集体记忆之间的桥梁,这一方面促使个体经验‘外化’为文化记忆的元素,另一方面个体也只有通过交流和媒介接受才能‘内化’有关过去的共享知识。”显然,“照片、报告文学、回忆录、电影被保存在客观化的过去的庞大数据库里。而进入现实回忆的道路之门并未因此而自动打开,因为还需要所谓的第二媒介,即那些可以再度激活所存储的记忆的媒介”。如果说照片、图像和文字等符号是储存记忆的第一媒介,那么文博类纪录片是激活存储记忆的第二媒介(集体记忆媒介)。回忆的过程通常是通过暗示,即唤起回忆的暗示来启动的。“拥有共同回忆的群体认为,一些特别的地方或是风景是和特定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们在记忆文化中实现了这种召回记忆的功能。许多的记忆场所似乎主要成为了集体记忆的暗示媒介。”正如博物馆作为“记忆之所”,是保存民族记忆的重要场域,而文物作为承载历史文化的介质,则可以触发受众心灵深处的记忆开关。事实证明,任何个体的记忆都并非静态和孤立地存在,而是以动态和互联的方式共同参与了集体记忆的建构。一些特殊的物质符号和文化意象(譬如场景和空间),最终将通过纪念的溢出效应来奠基和启动个体的记忆程序。
社会秩序是由传播媒介“决定”的,或者笼统地说,是由技术决定的;而“技术这一最硬的‘物质人工制品’,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彻底是文化的产物”。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使得记忆的媒介化特征愈发显现,并使之成为构建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力量。哈布瓦赫精辟地指出,一个人的记忆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而发生的。“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体无疑是启动、制约、更新、改写人们的记忆的最重要的社会框架之一。”基于受众与文物的时空疏离感,二者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意义鸿沟。要让受众与文物展开对话,让受众走进文物的“内心世界”,则需要依靠技术的力量返回到原初的历史天空。尽管时空不可逆,但是技术却能够通过“穿越”和“再现”的方式,还原复活彼时彼刻的历史场景,进而在象征层面上激活受众的“记忆程序”。媒介技术的更新使得受众获取记忆的渠道和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与延拓。换言之,文博类纪录片利用实体和模拟场景的影像传导以及网络空间的延伸场景,激活并点化了受众对于国宝文物的“集体记忆”。在促活这些“临界记忆点”上,文博类纪录片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记忆的排练与操演。
(一)昨日重现:具象的电视节目场景仪式空间
1.作为“记忆之所”的博物馆实在场景
记忆始于“重新识别”(wiedererkenen)的欣喜,由于记忆积淀在场景、空间、形象和器物之中,故而“记忆之所”隐含的凝结的记忆元素能够唤起空间化的记忆结构。换言之,具有纪念意涵的空间场所能够成为激活受众集体记忆的动力装置与发生系统。克雷斯韦尔将场所理解为一种由物质性、意义与实践共同组成的“时空”集群,他认为场所的物质性与意义彼此依存,而“意义始终居于场所的地理分析之中心”。记忆依附于场所就像历史依附于事件,站在历史的同一片苍穹下,人类可以经历着延续的记忆。空间是记忆的承载地,而“存在空间”是沉淀在人类意识深处的具备认知功能的比较稳定的知觉图式体系。如作为“记忆之所”的故宫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空间”,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兴衰荣辱的历史。《上新了·故宫》首次开启了“博物馆+真人秀”的实景纪录模式,节目将叙事空间直接拉回到故宫,受众跟随着文创开发员和嘉宾的脚步在故宫里的各个场景空间游走,节目的叙事意境随之而摇曳生姿。譬如在第5期 “解密紫禁城里的最具传奇色彩的母亲”中,在顺治帝曾经居住的保和殿内,文创开发员和嘉宾讲述两度废后的历史故事及幕后原因。在董鄂妃曾经居住的承乾宫内,文创开发员和嘉宾共同讨论董鄂妃的生平及其与顺治帝的爱情故事,让受众直观地将解说与眼前的实景勾连起来,感受并想象着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件。通过重拾和提取被遗忘的历史场景,尘封的文物故事被打开,文化的延续脉络呼之欲出。
2.作为记忆链接的舞台模拟场景
“记忆场域的存在,是因为记忆的现场已不复存在。”记忆是一个永远经历在当下的关系,记忆的主体一直等待着被链接或被召唤。“集体记忆的召唤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表演性质’,而表演本身正是客体被询唤成主体的过程。”作为一种链接记忆的技术媒介,精妙的舞台场景设计是文博类纪录片召唤主体记忆的一个重要筹码,这些舞台场景承携着超越其物理层面的意义,通过暗含的象征层面的意义激发出记忆主体对于历史文物的记忆张力。具象的舞台模拟场景与受众的历史想象天空形成了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进而缔造出一种沉浸式的多元文化体验。在此过程中,受众的记忆可以被技术链接的记忆密码反复下载和重启。譬如《上新了·故宫》有一个舞台场景设计,文创开发员邓伦和周一围带队和嘉宾跟随专家进宫寻宝,在故宫专家的专业讲授下,受众可以深入了解故宫的历史文物瑰宝。通过假借专家的“复眼”探视功能和场景链接技术,受众全身心地投入到历史文物的记忆星云之中。而《如果国宝会说话》对历史情境的还原则采取了舞台场景的虚化技术,借用人物的背影或侧影来表现叙事意象。通过链接记忆的影像技术,文博类纪录片可以“复活”历史人物,还原历史场景,重现历史氛围和唤醒历史情境。这种基于现代技术的场景复原,是影像本体论的延展,它能够更好地架构起历史与现代的关系,同时也能有效弥补受众缺席历史的遗憾。尽管“记忆展演是在遵循脚本设定的前提下,展开富有创造性的‘有限’发挥”,但是通过“记忆展演”的仪式传播空间,节目将某些关键节点和文物意象的历史片段拉回到记忆漩涡的中心,从而将记忆客体召唤成记忆主体,记忆的活性由此而被打开。
(二)回忆空间——抽象的互联网延伸场景仪式空间
“互联网的存在使虚拟空间替代了物质空间,为记忆脱域提供了可能条件,使得现场不再意味着唯一与权威,记忆地点在概念上产生了颠覆,转变成为一个有着私人性与公开性的双重虚拟空间。”在记忆脱域时代,互联网提供了一种延伸场景,在此空间具备了优势,互联网使得记忆轨迹超越空间结构成为可能。在互联网场域中,“为了唤起回忆,仅仅依靠一点点地复原过去的情景是不够的。这种重构必须从既存在于我们意识中又存在于他人意识中的共同的环境和想象出发,因为它不间断地流转于这个意识和那个意识之间,这只有当所有的个体从过去到现在都同属于一个群体时才有可能。”互联网具备强大的“再域化”系统功能,它能够确保不同记忆主体的回忆空间相互连接并相互确认——互联网已然成为回忆空间的元场景。尽管电视媒体是集体记忆仪式化传播的主导场域,但在网络空间,每个受众都是接力传播与次生扩散的重要节点。“这时的集体记忆成为一个交流、协商甚至博弈的过程,而恰恰是个人记忆在网络和新媒体平台的分享、讨论、争论、过滤、协商中获得了集体经验和认同的沉淀,构建了一种新的集体记忆形式。”由于融合了电视文化与互联网技术基因,文博类纪录片能够将网络平台化约为集体记忆的意义镶嵌场所和意识流转空间。譬如当节目出现了某个有价值的讨论话题时,受众就会在社交媒体积极发言表态,弹幕的文化实践使得受众和节目之间产生了实质性的关联,进而固化了虚拟的共同在场感和神圣仪式感。此外,文博类纪录片还刻意打造了一个记忆话题空间,吸引大批受众围观入驻。如《如果国宝会说话》的动态海报就颇具话题度,它将历史钩沉的海报创意与现代生活场景勾连起来,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时空中展开了仪式对接与对话。藉此,不同代际的文化主体在虚拟延伸的互联网空间完成了记忆话题的讨论、转发、点赞等一系列文化传播实践,继而衍生出新一轮文物记忆的仪式化传播。
四、缝合记忆:作为话语媒介的文博类纪录片的意识形态整饬功能
文博类纪录片本质上是一种以叙事解说为内容载体的话语媒介,它通过媒介话语策略缝合了多元文化记忆并整饬着记忆的时空结构。鉴于不同年代的文化主体都有代际专属的共同记忆,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媒介,文博类纪录片通过整饬纷繁复杂的记忆纲领与意识情绪,来缝合不同代际的历史创伤与文化差异,进而将受众的记忆实践与主流的文化意识和政治诉求相勾连。齐泽克曾经借用拉康的“缝合”理论,提出在流动性和差异性越来越明显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可以“缝合”多元差异的社会话语。在后喻时代与后现代社会,尽管人们不再相信能够有“统领一切的意识形态”,也难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但“意识形态并非不存在,而是以一种‘隐含的、准自发的假定和看法难以捉摸的网络形成的非意识形态——实践的一种不能复归的瞬间再生产’”。惟其如此,在一个液态的多元文化结构里,各种纷繁复杂的话语才可能被“缝合”在一起。正如齐泽克所言:“众多‘漂浮的能指’,众多原型意识形态因素,被解构成一个统一的领域,就是通过扭结点——拉康所谓的‘缝合点’的干预完成的,它将它们‘缝合’在一起,阻止它们滑动,把它们的意义固定下来。”经过“有效缝合”,那些对立的甚至相互抵触的东西也有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论据”。意识形态往往是跟具体的媒介话语事件联系在一起而出场的,“结构选择的一个可供替代的东西是在话语事件中确定意识形态,强调作为一个过程的、转化的和流动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文博类纪录片通过在记忆层面上建立一个个话语联系的扭结点,从而将弥散失焦的集体记忆缝合起来,并整饬成为一个意识形态的“统一的领域”。在一个型塑“阐释共同体”的传播语境中,主流涵化的记忆话语对意识形态整饬具有强大的穿透功能。
(一)共同体话语缝合民族记忆
“‘传播’一词与共同体(community)、共同(common)、共享(communion)拥有同一个词根,这就赋予了传播新的生命,它倡导的是传统、延续与联结。”记忆是一个当下的创造性行为,它使得既往的文化实践和价值理念获得教化与规训。在经过对历史文物影像的储存、加工、创造、传播等一系列文化实践之后,文博类纪录片即刻升华成为民族认同的催化剂。多伊奇认为,民族力量重要的运用仰赖于“记忆、习俗与价值的相关性和稳定结构,而这些相关性和稳定结构又依赖于社会沟通中从过去到现在自始至终存在的交流技术”。通过影像历史的书写与转译,文博类纪录片打破既往宏大叙事的话语模式,转向“对话”和“交谈”等平行叙事的微观话语,有助于更好地激发、孕育和缝合民族的集体记忆。任何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都需要寻找到群体的归属感,“民族认同即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文化的人造物”,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故而作为世界政治单位的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继而指出,在民族认同的孕育形成以及民族记忆的连接共享过程中,大众媒介的传播居于核心地位。“正是大众媒介通过图像和语言的重复,生产了民族主义所必须的团结。在事先精心统筹好的时间与空间里,大众媒介,甚至在民族成形之前就生产了一个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当下的文博类纪录片承担了型塑和铸牢中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神话功能,其擅长使用“我们”等第一人称来强化虚拟在场的群体成员身份,同时征用“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华夏文明”等这类带有强烈归属意味的共同体话语来弥合民族记忆。“视域融合”下浸润在传统文化场域的受众瞬间被激活唤醒,话语联系的扭结点聚拢了他们的民族归属意识与原发情感。
(二)哲理思辨话语缝合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建立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之上,它通过运用一系列的符号系统和演示形式,最终实现意义的沟通与分享。在多元异质的传播语境中,不同代际的文化主体通过协商对话塑造形态各异的记忆政治,并构建媒介话语在文化场域中的游戏规则。“语言(即传播)是一种行为方式,或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互动。它不仅仅是再现或描述,事实上它是对世界的型塑与建构。”文博类纪录片充满了厚重的文化底蕴与时代基因,这种主流气质是通过哲理思辨的话语阐说来营造和赋予的。哲理性的解说能够召唤丰富的所指,进而提升节目的主旨意涵和受众的主体间性。譬如《故宫100》在阐述故宫“中轴线”时话语解说词为:“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宫殿群,令原本僵直的空间具有了音乐的节奏。它是北京城的脊梁、是穿行于大地的龙、是将天意融入人心的通道。”短短几分钟的哲理阐说娓娓道来文物的千年沉浮,记忆恰如电光石火,瞬间将受众锁定于主流文化的“阐释共同体”之中。再如《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在解读“陶鹰鼎”时解密生存之道与生活智慧:“陶,出于土,而炼就生活。它需要摔,需要捏,需要烧,制陶如塑人。”对文物蕴含的人性追问以及对生命真谛的恒远思考彰显出话语媒介的政治统合纲领与文化意识形态。“由传统文化绵延而来的庞大话语流,既是构成主体不可或缺的文化符码,又是把各种异质性因素裹挟其中不断延伸的‘他者话语’,还是历年历代各类群体进行交流和思考时共享的文化资源。”通过文博类纪录片对记忆话语的述行和操演,我们能够看到,回忆不仅位于国家文化政治策略的中心,而且“回忆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和实践的复杂的结构转变是在大范围的话语实践的框架内实现的”。
注释:
⑧ Jan Assmann & John Czaplicka.CollectiveMemoryandCulturalIdentity.New German Critique,no.65,2014.pp.125-133.
⑨ [英]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页。
⑩ [德]贝克、[英]吉登斯、[英]拉什:《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与美学》,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