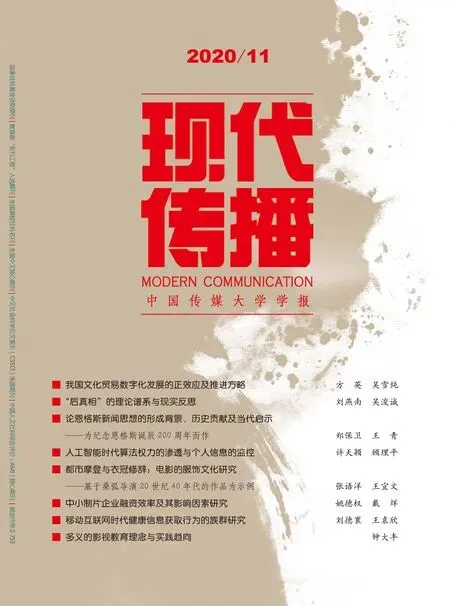“浸入”真实:影像内容新媒体化生存的路径转向*
■ 李 群
随着移动网络与虚拟技术的成熟,在计算机中介的作用下,人机深度交互,人类对于影像的观看模式转向为沉浸式、包裹式的体验,“场景”“沉浸”“交互”“体验”已成为用户视觉体验寻求“真实感”的主题词。技术的飞跃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传统的观看模式从视觉在场转向身体感知在场,对于真实的追求始终贯穿人类视觉文化的始终,虚拟现实(VR)技术作为一个关键节点,有力地驱动了影像内容新媒体化生存路径转向,即如何有效触及用户的精神和心理层面,让他们在影像所建构的内容中亲历现场,诱发情感的共鸣,浸入影像所建构的真实情境,在碎片化的新媒介语境中获得关注,与影像内容产生深刻的连接。
这意味着影像内容在艺术创作、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重新思考传媒艺术具有的鲜明的科技性、媒介性和大众参与性特征①,在“真实感”图景的重构上呈现出新的生发机制。新媒体时代对真实感的重构即充分利用媒介技术的优势,让用户真正浸入影像内容“真实”的感知体验中,这种真实感知的生发机制是建立在新媒体影像在创作、传播与接受过程三个维度的重塑,具体表现在:首先,在影像内容创作过程中,充分调动用户视觉、听觉、味觉、嗅觉等多重感官,实现对固有社会现实的多重解构,在创造性的混合空间中,使其浸入影像内容建构的“真实”空间②;其次,在影像内容传播过程中,利用虚拟数字技术与现实“融合”、以尽可能“延伸”用户感官③,以更加逼真现实的“在场”感知,与影像内容产生情感共鸣,进而产生“真实”的体验;再次,通过技术与情感的连接,重塑在场感,用户在审美接受上充分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在影像塑造的真实情境中打破了屏幕的区隔,全身心投入接受影像内容创造的真实意境过程中。用户的情感体验和社会互动在建构的媒介情境中共振越大,他们越可能完全浸入在新媒体影像所建构的真实情境中。
数字化浪潮中,影像内容 “真实”图景的路径转向在接受层面主要是围绕着用户的情感体验而形成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网站和其他虚拟实体对我们做出了实时的反应,它们对用户来说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④本文以真实感知的三个关键元素:在场、共情和具身参与,结合影像内容生发机制即生产—传播—接受三个维度,思考在新媒体时代,在影像内容重构上如何有效浸入真实,这种“浸入”必须实现媒介与心灵的弥合,必须触及用户的心理和精神。
一、浸入“真实”:理论溯源与内涵演变
关于真实命题的追溯,并非亘古不变的原则,而是在不断转换其形式、地位。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基于媒介技术制造的“灵韵”,其“本真性”是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感知。鲍德里亚所指出的“拟象三阶序列”第三序列的标志是“仿真”,是指在消费社会中媒介所创造的抽象符号与现实生活高度融合,并且区别于现实真实,是一种具有代偿性的“类像”。⑤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理论,正是看到了媒介与人之间边界的消弭,万物皆媒,媒介是人的感官的延伸。从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到保罗·莱文森的《人类历程回放:媒介进化理论》,强调的都是“媒介是人的延伸”,“电子媒介时代的人要用中枢神经系统和一切感官去拥抱世界”。⑥
数字技术的赋能,将不同时空的事件集合在一个虚拟创造的情境时空中,从而使得用户对另一时空的体验成为可能,这种“在场感”又指向用户如何在观看影像内容的过程中真正嵌入内容所重塑的情境中,获得一种与我们社会现实紧密关联的身临其境的体验,浸入真实,产生共情效应。
随着媒介的发展,传媒艺术所理解的真实,不再是由活生生的人在彼此面前的存在,或者是通过物理的时空关系来定义的。新媒体化影像 “真实”的体验,是复杂和特殊的,它所建构的真实是一种“多重假定的真实”,这种真实既包含了“艺术的”“假定”成分,又包含了“非艺术的”“假定”成分,这是由媒介的传播特性所决定的。⑦这意味着以动态影像为基础性艺术元素的传媒艺术,由于日常化、连续性、包裹式地用动态影像这种“真实的符号”代替“真实本身”,而表现出极度、极致地聚焦、呈现和张扬“现实”的美学风格,这成为传媒艺术和传统艺术在美学特征上的一个极为核心的区别。⑧
新媒体化的影像在内容生产上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呈现,构建了一种丰富的感觉,创造了一种具有即时性和强烈现实感的体验⑨,使得用户在他们现场展开的过程中目击或经历事件⑩。其创造的“真实”再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现实的图景,使用户获得一种“现场感”的满足。
因此,影像内容新媒体化的生存,在真实图景的重构上,将技术与艺术杂糅在一起,在内容生产、传播手段和审美接受上生发出新的生产机制。这一机制是建立在“浸入真实”内核转向上的三个核心要素:在场、共情和具身参与层面之上。影像内容浸入真实路径转向,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技术优势,将技术与情感有效结合,重塑在场感。其次,在虚拟与现实时空的融合中,充分调动用户的身体器官参与到媒介所建构的情境中,与影像内容产生深层次的情感连接,产生共情效应,忘记屏幕的存在。
二、在场感的重塑:技术与情感的连接
移动网络、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技术重新改写了 “在场”的基本含义,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对三维虚拟空间的营造,实现对于“浸入者”多重感官的刺激,进而制造出一个完全有别于此刻现实的“在场”,从而令用户对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真实事件的体验成为可能,这是科技通过改变时空观达成的。虚拟现实技术的核心是沉浸、互动和想象,以此实现对人类感知在场的器官的延伸,技术加持下,影像内容在生产上将从传统观看模式转向体验感知,通过建构的“感知现实主义”,与节目中的人物实现在场交流。
1.技术反哺下的情境重塑
技术反哺下的影像纪实,在媒介情境建构上不再仅是依托摄像技术或实时直播创造了一种“在场感”。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化影像在内容产业制作上依托技术赋能,在保障优质内容的基础上提升用户体验,技术重塑了内容产业。今年以来《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试图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与新闻节目的结合,尝试新媒体化影像在内容生产上的革新。在技术背景的支持下,通过对其直播技术在场感的全新探索,有效拓展了真实情境与虚拟社会情境的互动边界。虚拟技术的呈现,将在场、远程在场、虚拟远程在场加以融合,创造了多元混合的空间。
作为虚拟现实新闻报道先驱的《纽约时报》,其发布的反映难民状况的虚拟现实影片《无家可归的孩子》(The Displaced),视频讲述的是叙利亚战场让超过3000万儿童流离失所的故事。通过谷歌纸盒(Cardboard)的设备,观众置身其中,亲历难民被流放的苦难,虚拟现实技术将观众带到无法到达的现场,亲历事故灾难,让观众与新闻故事的接近性更强。在《纽约时报》虚拟现实新闻平台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一个每日更新的VR视频新闻产品每日360°(The Daily 360°),首次尝试日常360°沉浸式新闻报道。《纽约时报》通过运用技术优势,借助传统媒体在新闻内容生产上敏锐的视角和有效获取信息的方式,革新传统报道方式,探索和创造全新的影像语言纪实模式的可能手段。
技术打破了物理时空的局限,让在场感知的体验变得更加真实自然。然而,如何有效实现媒介所创造的抽象符号与现实生活高度融合?这种在场的感知不仅与技术有关,而且与用户心理因素密切关联。技术为场景的真实呈现提供了可能,同时更需要捕捉用户在观看影像后的生理和心理上产生的情绪感觉,才有可能实现图像内容所创造的媒介情境与社会现实场景的高度契合。
国外一些学者根据唤起的情感状态来追踪定义用户的这种融合程度,他们通过对在观看舞蹈表演视频的用户,使用皮肤电反应(GSR)传感器来测量个体的情感状态;他们使用了一种混合方法,将GSR数据和调查反馈相结合,以确定用户在影像播放期间他们的参与度。数字移动设备已经被用来收集用户的反馈,根据用户的喜好程度以及对问题的评论和回答的形式来获取他们的心理情感状态相关数据。例如科尔内斯(Corness)等学者通过采访来激发用户重新体验一场表演,获取他们对表演者的共情状态;蒂文(Teevan)等则使用图形来可视化观众的参与度,利用圆圈根据用户参与度改变颜色来捕获他们的认知。这些数据通过不同的衡量指标获取观众在某影像图景中的凝视时间和情感投入状态,为影像图景中真实感知建构的有效性提供了数据支持。
2.进入情境:浸入式体验
沉浸性是指用户感到自己身临其境,用户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如同身份扮演游戏,自己就是主角,全身心地沉浸于其中。“沉浸式体验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体验,以及彼此联系的方式,融合了虚拟和增强现实等技术的扩展现实技术,第一次弥合了与现实的距离,重置了人们在时空中的关系”。技术对于客观现实场景的多维呈现与用户在场景建构中所产生的“在场感”体验并非完全一致,超越观看的体验,只有嵌入亲历者内心认知的感受和提示才有可能真正产生一种真实的感觉。“感知现实”在技术加持下与其内容的建构密不可分,通过设置抽象的情节,增强内容的神秘性、悬念感,用户会浸入影像内容中与演员对话,建立一种更加深刻、私密的个人连接。
网络真人秀节目以“真实”为卖点,促使用户形成持续收看的动力。如何建立参与者和用户之间的私人连接形成对话,在于节目在内容生产上如何去建构在场感,以形成真实的感知。用户普遍不认可真人秀节目中那种以对日常生活琐碎与庸常记录的内容以标榜节目的真实性。用户认为真人秀节目虽然情境是人为制造的,是经过高度编辑过的,用户对于影像内容真实性判断,通常是在信任和怀疑之间“前后自然的运动”,并利用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和社会互动作用的方式来判断节目中参与者的谈话、表演、反应以及其他情况的真实性。
用户对于真实感的认知以接近他们亲身经历的体验“合理性”为评判依据。这一合理性的判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节目能否为他们提供“有人性”或是“真实可信”的明星形象;用户普遍认为明星真人秀节目的真实是一种“表演的真实”,因为明星先天具备表演能力,实际上削弱了对原生态真实的感受,但这种表演只要合情合理,与生活经历相吻合,同样能够通过建构的真实感实现与观众交流。他们在收看节目过程中依据个人经历判断到底是真实的个体形象,还是虚伪作秀,而对于那些不露痕迹而又令人信服的表演,同样能获得真实感。
第二,节目背景与故事内容的设计应符合逻辑,对逻辑认知的合理性来源于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社会行为的理解。节目情境设置的合理,能够激发出明星表现真性情的东西,以接近他们较为真实的个人形象,表演虽不可避免,但相比其他节目类型这种真实感更加强烈。例如用户认为真人秀节目通过情境化的设置,呈现出每位明星较为真实的一面,在严密的游戏规则设置下,明星身上表现出的个性特征特别真实,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某些深层的情感”,这种情感让人觉得温暖,积极向上,能够从中学到某些优秀的品质。
用户确认合理性的第二个要素在于节目所设置的背景与内容设计是否与 “现实”生活相契合。社会现实类真人秀节目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涵盖了当前社会的痛点而让观众产生真实的感受,其真实感的建构源于制作者对日常生活有细致入微的观察,用一种更为理性的方式去判断和选择内容以还原生活真实。《令人心动的Offer》以职场生活为题材,从初入职场的实习生的视角,全景呈现了律师职业的职场生态。节目从真实案件入手,展现了职场新人在强大的压力下逐步成长的过程,细节的真实让观众产生强大的带入感,通过情境设置,将观众与演员表演结合起来,创造物理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混杂空间,营造“在场”的感觉。
三、共情效应:情感联结与具身参与
突破时空的在场感的重塑,为用户观看影像内容产生共情的生发机制提创造了条件。所谓共情,即是让体验者去设身处地地体会别人的情感以产生情感共鸣;浸入真实,即意味着用户的情感体验和社会互动在建构的媒介情境中共振越大,这种共情的效果即越明显,他们可能完全浸入在影像内容所建构的真实情境中。技术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即成为我们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技术具身,意味着技术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身体经验中,它不能被理解为外在于身体的工具。当前的新传播技术的鲜明特点就是技术越来越透明化,越来越深地嵌入人类的身体,越来越全方位地融入我们的身体经验,传播的在场即意味着用户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然而然的连接,甚至忘记了屏幕的存在。
1.前置的后台场景
虚拟现实 (VR)与增强现实 (AR)技术,重构了真实逼真的场景,技术发展拓展了真实社会情境与虚拟情境边界的融合,梅罗维茨认为,情境的融合带来戈夫曼“拟剧论”中的前后台边界的消失。没有绝对的观众和表演者,更没有固定的脚本和场景,客体随时可能变成主体,后台随时可能暴露于前台,媒介建构的情境是动态的,场景分离所形成的“前台”“后台”行为是更为复杂的社会互动关系的表征,电子媒介开启的“混合情境”时代,不断突破前台的区隔,后台前置的方式将用户从虚拟情境带入真实情境。
网络真人秀节目打破了专业表演对前台空间的呈现,将摄影机放入表演者的后台,呈现参与者的工作空间、社交空间甚至生活空间等,多元化的前后台关系转化,实现信息的互补或者反差。《乘风破浪的姐姐》之所以能够引发高度热议,明星专业表演舞台的呈现所带来的视觉感知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节目打破了传统叙事的连贯性,穿插多个空间,镜头从舞台走向生活场景。将明星私人生活的后台空间转化为前台表演,这一方式让观众获得了窥视明星后台空间的特权,满足大众对明星专业性艺术享受后未被满足的偷窥的冲动。
不断前置的后台场景,摄像机成为观众的眼睛,大量中近景镜头的运用,观众在凝视的过程中,将明星代入到观众的社交距离,甚至产生亲密感。“真实的普通”正是这类节目的价值。节目用一种去光环化的叙事策略,后台前置让明星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缩小与观众的距离,以其特有的贴近性与亲近感赢得观众的亲睐,这正是对新媒体亲密感属性的真实呈现。
2.情感化互动:具身参与
后台的前置打破了前台的区隔,创造了一种日常化的“媒介情境”,依靠技术所创造的情境需要与用户的情感体验联系在一起,才能够产生一种“真实”的感知。
技术所建构的真实场景是作为一种特定的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出现的,是一种特定的参与方式。真实体验来自于我们有意识地抓住虚拟实体,作为对他们对我们的要求的回应。梅罗维茨“媒介情境论”的核心层次即是将情境与身体联结在一起,情境作为社会规范和社会中介,身体的感知、参与、共情才能够打破社会现实与虚拟现实的边界,实现有效的社会互动,浸入 “真实”。
影像内容在生产上以其直观生动的画面语言将现实真实与媒介真实连接在一起,新技术以其特有的传播逻辑使得内容的呈现由固化走向离散。数字化浪潮下,未来影像图景的重构将呈现出非线性的文化特征,给予用户更多的选择权和互动性。现实体验技术运用丰富多元的符号,充分调动用户感官系统获得更加立体、鲜活的内容体验场景,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如何让身体重返现场,激活人的身体,释放身体在交流中的能动性与生产性力量是内容制作上的一个重要命题。
新技术的即时性、强烈的互动性和交互性等核心技术嵌入传统媒体中延伸人类的感官,不再局限于传统媒介所呈现的视觉性,而是整个身体器官的卷入。这意味着用户对真实的体验并不局限于特定的观众和表演,而是一种情感互动——通过媒介持续与他人连接(熟悉或陌生的群体)创造了一种共同在场的体验。情感互动是媒介技术建构出来的形象逼真生活空间的逻辑支撑。
新媒体影像内容利用数字技术同步的即时感和代入感创造了一种真实在场的感觉,但却始终无法打破用户被区隔的现实,如何通过技术增强视觉文本的传达和反馈效果?场景的仪式感和即视感的创造可以在对他者的凝视中创造出超真实的感受。而对于虚构类节目而言,则可以通过运用戏剧元素,塑造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节等元素,用户被故事情节、人物吸引、处于兴奋的状态,获得对真实感知的体验。
影像内容的新媒体化发展在网络新闻节目上的尝试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新闻节目在内容生产上打破了传统的叙事逻辑,转向以第一人称视角,创造了一种与观众共同在场的体验,让观众体验新闻事件,重新改写传统内容叙事的模式。在嵌入的技术场景中,用户似乎是在与个人的对话中,紧紧与故事人物命运连接在一起,与之对话交流,实现节目内外的有效互动。
国内媒体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尝试一种全新的新闻内容生产,人民日报的《“9·3”阅兵VR全景视频》、新华网的《“两会”VR全景报道》、财新网的《“深圳垮塌事故”VR新闻报道》,节目以交互性叙事的方式,通过用户的“主观视点”与救援人员进入灾难现场寻找幸存人员,在影像观看过程中,用户被细节深深吸引,甚至产生一种与救援人员深入现场参与救援的感受,这种在场感的生动呈现,有效调动了用户的感官体验,将技术与情感巧妙粘合,嵌入节目内容生产。
此外,技术的发展为内容提供新的创作走向,如更强的互动性。以弹幕技术为例,弹幕技术使得用户通过实时互动的方式在视频内容上发表“即时评论字幕”,以满足其对信息、娱乐和互动的需求。将弹幕技术嵌入影像内容生产,影像不仅具备观看的功能,同时具有了较强的社交属性,是强化具身参与的一种有效形式。弹幕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示了用户对节目内容的感受,即时传播观影体验,潜在表达了自身的存在,实现与屏幕之外他人之间的连接,弥补了传统影像内容单向传播的短板。
近年来互动剧的出现,即是在技术搭建的平台上,充分研究用户的心理需求探索的新的剧集形式。互动剧通过用户的不同选择,决定人物关系和故事的走向,将在场与不在场的,虚拟与现实的空间连接,让用户见证彼此、参与彼此、形成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奈飞公司(Netflix)推出的《黑镜:潘达斯奈基》,将互动的方式嵌入剧情,用户在观看过程中会收到剧情关键节点发展的提示,将选择权交给了用户,用户在剧情选择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自己选择“分支”决定剧情的走向,作品通过六个不同的结局实现了用户自己订制剧情的需求,将镜头逻辑和现实逻辑高度重合,让用户在剧情中重新审视我们生活的现实。
四、结语
本文在数字技术背景下,结合虚拟现实技术探讨了影像内容新媒体化后“真实”图景重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何通过互动式与沉浸式的“深度开掘”与“主动参与”,延伸和强化用户的“直接体验”,以实现影像内容新媒体化生存,使用户完全浸入真实呢?研究发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影像的“清晰度”,强化了用户的认知、情感和行动意愿,但技术如何突破360度全景视频而真正实现沉浸式的虚拟现实还需要结合个人的感官体验,因此本文从在场、共情、与具身参与三个角度出发,指出技术的革新需结合优质的内容实现围绕着用户情感化的体验才有可能真正浸入“真实”。
技术不能仅仅只是一个虚幻的外衣,虚拟现实技术的视频产品还需要依靠头盔技术,那么如何提高虚拟现实头盔技术,同时创造出有优质的故事内容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此外,让影像内容充分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性”“交互性”的特点,真正创造出一个身临其境的环境,让用户在节目中倾听节目主角的感受,使内容充满冲击力、震撼力和价值表达,实现技术和内容的有效整合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二。
然而,在探索的过程中,在唤起用户情感体验建构真实的影像内容中,一方面研究者深耕内容制作,在遵守传统影像制作逻辑叙事中借鉴戏剧强烈的戏剧冲突感,增强节目内容的现实逻辑进而与用户产生强烈的粘性;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有可能造成内容生产方与技术建构者资本的联结,通过收集“凝视数据”,例如谷歌纸盒(Cardboard)或脸书(Oculus VR)作为官方指定“头显”,通过设备获取用户在观看影像过程中注意力曲线,从而精准布局情节、植入广告,强化了“人的注意力的商品化”进而实现对人的控制,陷入贩卖个人隐私数据的伦理困境。最后,将现场毫无保留地呈现给用户是否会影响观众的思考?如何细分用户市场,针对特定人群进行内容定制,并根据市场需求做出调整?这些都是未来在影像真实图景重构的探索中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 胡智锋、刘俊:《何谓传媒艺术》,《现代传播》,2014年第1期,第73页。
③ 段鹏:《智能媒体语境下的未来影像:概念、现状与前景》,《现代传播》,2018年第10期,第4页。
④ Philip Auslander.Liveness:PerformanceinaMediatizedCulture.Abingdon:Routledge.2008.pp.155-156.
⑤ 周勇、何天平:《“自主”的情境:直播与社会互动关系建构的当代再现——对梅罗维茨情境论的再审视》,《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12期,第16页。
⑥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何道宽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5页。
⑦ 胡智锋:《电视美学大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⑧ 刘俊:《极致的真实:传媒艺术的核心性美学特征与文化困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9期,第148页。
⑨ Ytreberg Espen.ExtendedLivenessandEventfulnessinMulti-PlatformRealityFormats.New Media and Society,vol.11,no.4,2009.pp.467-485.
⑩ Philip Auslander.LiveandTechnologicallyMediatedPerformance.Abingdon:Routledge.2008.p.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