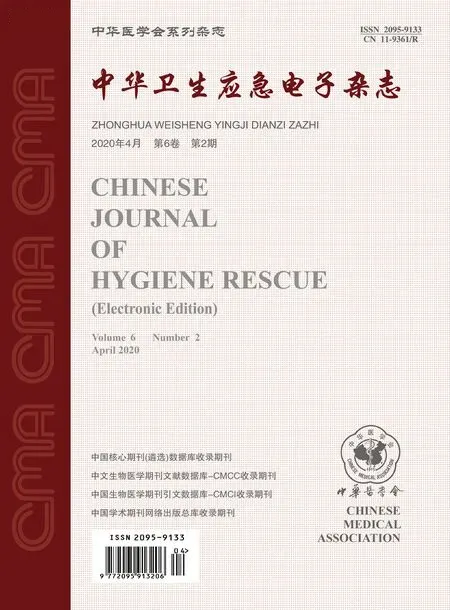重症患者的液体治疗:藏器待时而动
李文哲 肖雅文 于湘友
液体治疗是重症监护治疗中常用的措施之一。早在17世纪就有人尝试使用动物的羽毛和膀胱作为输液器将药物注入患者的静脉内,但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在当时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1]。直到19世纪欧洲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Thomas Latta医师尝试给霍乱患者输注盐水,结果发现可以显著降低霍乱患者的病死率[2]。此后,液体治疗在各类疾病的救治中迅速普及开来。截至目前,液体治疗已经是危重症患者复苏抢救中最常用的治疗措施之一[3-4]。除了少数如严重的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病例外,临床医师多已认定液体治疗是一种安全而且普遍适用的治疗方法。实际上,液体治疗在为患者带来有益的治疗效应的同时,其潜在的危害却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本文回顾目前重症监护中液体治疗的危害及患者容量反应性评估等方面的文献证据,为广大临床医师科学合理地实施液体治疗提供参考。
一、液体治疗是一把“双刃剑”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对于重症患者,即使以“生理”范围内的CVP值作为参照实施液体治疗,其疗效也可能是弊大于利[5]。临床医师应当谨记:液体也是一种药物!尤其是对于重症患者,过多或过少的液体都会对患者的预后产生重要影响。液体过负荷常见的并发症包括:(1)破坏血管内皮的糖萼屏障、增高血管内静水压导致水肿形成[6]。(2)液体的血液稀释效应及冷液体导致的体温降低可能诱发稀释性凝血病[7]。(3)液体的血液稀释效应还可能导致稀释性贫血,造成血液携氧能力下降[8]。(4)人工液体的成分及浓度与生理体液存在差异可能导致机体电解质和酸碱失衡,如常见的高氯性酸中毒等[9]。过度的液体治疗可能会因上述并发症而导致患者肺脏、肾脏、心脏、胃肠道以及大脑等出现功能障碍,甚至会严重影响患者预后[10-11]。最近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仅有50%的重症患者对液体治疗存在容量反应性[12]。因此,重症医师必须仔细地为患者进行个体化地滴定式液体治疗[13]。
二、容量负荷试验
容量负荷试验,又称快速补液试验或液体冲击试验,由Weil等[14]于1974年首次描述,是指对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重症患者快速静脉输液,评估患者循环系统对输液的反应性,以指导液体复苏治疗,避免输液所致液体过负荷的方法。该方法是临床常用评估重症患者容量反应性的方法之一,其主要原理是基于Frank-Starling心脏做功定律,在一定的前负荷范围内心肌初长度越长,心肌收缩力越强,心输出量越多。所有需要进行医疗紧急救治却存在液体复苏利弊困惑的临床情况均是其应用指征。实施时根据临床需求可选择晶体液、人工胶体、人血白蛋白或其它血制品,单次输液量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100~1 000 mL,首选经输液泵进行精确快速静脉输注,监测患者中心静脉压(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或肺动脉楔压(pulmonary artery wedge pressure, PAWP),分别遵循“2 - 5”“3 - 7”法则判定容量反应性,也可以动态监测心输出量(cardiac output, CO)或每搏量(stroke volume, SV),CO或SV升高大于10%~15%提示存在容量反应性,结合临床实际情况,可给予扩容治疗[15-16]。值得强调的是,容量负荷试验也具有其先天的局限性。
(一)CVP和PAWP预测容量反应性的价值
CVP是临床医师判断容量反应性的常用指标[17]。有诸多研究验证了CVP用于评估患者容量反应性的价值,但也有研究对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18-19]。CVP是反应右心室和左心室前负荷的指标,还反映了静脉回流的阻力及右心室的功能状态。因此,监测CVP可能有助于指导液体治疗。但CVP也容易受到胸腔压力、左心功能状态、心包以及腹腔压力等因素的影响,这会使得临床医师对其意义的解读变得复杂[20-21]。PAWP作为临床常用的监测指标之一,也存在与CVP相似的优势和劣势,容易受到如导致肺血管阻力改变的酸血症、缺氧等因素的影响[21-22]。因此,临床医师需要更清楚地了解CVP和PAWP的优势和局限性[23]。
(二)最佳的单次试验剂量
容量负荷试验中需要使用一定量的液体进行试验,该试验方法的局限性在于:进行试验的同时也等同于进行液体治疗。对于无容量反应性的患者,进行大剂量的快速补液可能会造成其不可逆的严重损害。再者,每日多次进行容量负荷试验,累积的液体输注量也可能造成患者液体过负荷,进而可能导致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影响患者的预后[24]。因此,有人提出使用50~100 mL小剂量液体进行容量负荷试验,相关研究也验证了其有效性[25-26]。但近来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使用4 mL/kg以上的液体进行试验才能观察到CO的显著变化[27]。因此,目前在容量负荷试验的单次输液量方面仍存在较大争议,小剂量液体进行容量负荷试验的有效性在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验证。此外,容量负荷试验输注液体的速度也会对CO的测量结果产生影响,输注用时过长可能会降低患者CO的变化幅度[28]。
(三)超声测量CO和SV的准确性
既往对于重症患者CO和SV的监测主要依靠脉波指示连续心排量监测(pulse indicates continuous cardiac output, PICCO)等有创监测方法,重症超声的推广普及使得在ICU床旁无创动态监测患者的CO和SV成为可能[29]。目前已有研究证实,无论经胸超声还是经食道超声监测,都能够准确地测量患者的CO和SV[30-31]。但最近另一项关于超声监测CO准确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窦性心律患者,经胸超声可以准确测量其左室流出道的流速时间积分(velocity-time integral,VTI)等指标,但对于房颤患者则需要增加测量次数。同一操作者执行两次测量的结果具有一致性,而两名操作者进行的测量则可能具有异质性。此外,经胸超声仅能准确测量出快速输注500 mL液体所引起的CO变化,而对被动抬腿试验(passive leg raising test, PLR)、小剂量(100 mL)容量负荷试验等引起的CO变化的测量可能会由于操作者两次测量之间存在的误差而产生偏倚,因此不足以用于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容量反应性[32]。笔者认为,重症超声监测的指标属于客观评估,但其有效性和准确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作者的实践水平,因此重症医师对于重症超声设备的使用和结果的解读均需要规范的培训以达到同质化的水准。此外,患者相关因素(如外科术后胸腔积气、先天性畸形等)对超声测量的影响也是重症医师需要统筹考虑的。
三、评估容量反应性的其他方法
(一)PLR
PLR是指通过改变患者体位使回心血量发生改变,监测前后CO或SV的变化幅度来判断其容量反应性[12]。其产生的效果和容量负荷试验相似,但不用输注液体,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容量负荷试验所致的如急性肺水肿、颅内压升高、组织水肿等相关并发症的发生。PLR评估患者容量反应性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诸多的研究证实,可以用于评估如存在自主呼吸、心律失常等特殊情况的患者[33]。需要指出的是,PLR也具有其潜在的局限性,包括体位变动受限、腹腔高压、下肢残疾的患者以及体位变动导致疼痛、咳嗽和觉醒等不适可能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影响CO的变化[34]。
(二)脉搏压力变异度(pulse pressure variation, PPV)
PPV是指评估脉搏压力差值和每搏输出量的变异性来评价患者的容量反应性,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常规监护仪直接准确获取,而不用测量CO[35]。但PPV的临床应用也具有其局限性,对于接受小潮气量机械通气或存在心律失常等并发症的患者,其预测价值的准确性会显著下降[36]。因此,对于接受小潮气量机械通气的患者,有学者提出“潮气量冲击试验”的策略,短时间内增加患者的潮气量以PPV的变化幅度来判断患者的容量反应性[37]。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进一步验证其有效性。相似的参数还包括每搏输出量变异度(stroke volume variation, SVV)。
(三)腔静脉直径的呼吸变异度
测量腔静脉直径的呼吸变异度多依赖于床旁超声,因其影响因素较多,所以用于判断患者容量反应性的价值仍存在较多争议。最近的一项Meta分析结果显示,腔静脉直径的呼吸变异度判断患者容量反应性的价值有限,尤其是存在自主呼吸的患者,而且腔静脉直径的呼吸变异度低于预测阈值时亦不能完全确定患者不存在容量反应性[38]。因此,临床医师在应用腔静脉直径的呼吸变异度协助评估患者是否存在容量反应性时,应综合考虑临床背景及患者自身的相关因素等。
(四)呼气末阻断试验(end-expiratory occlusion test, EEO)
EEO是指在机械通气过程中患者呼气末时阻断机械通气15 s并观察其CO的变化,若CO增加超过5%,则定义为EEO阳性,提示患者具有容量反应性[39]。EEO的主要原理:在呼气末阻断通气时,吸气对静脉回流的阻力消失,回心血量增加进而引起CO的变化。EEO的主要局限性在于其诊断阈值较低,临床应用过程中也可能会由于操作者测量的误差而产生偏倚。有学者提出了EEO联合吸气末阻断试验(end-inspiratory occlusion test, EIO),如此使得CO的变化幅度加大,利于临床实施过程中的测量[40]。未来也需要进一步验证其有效性及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五)肺复张
理论上,肺复张引起的胸内压增加会压迫右心房和腔静脉使血液回流阻力增加,从而降低了心脏前负荷,而这在低血容量患者中会更明显[41]。因此,通过测量前后CO的变化可以评价患者的容量反应性。但需要注意的是,肺复张引起右心前负荷降低的同时,亦会由于肺泡压力的增加压迫肺泡毛细血管导致肺血管阻力和右心后负荷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整体CO的变化[33]。所以该指标在临床中的应用也亟待进一步验证。
四、小结
在精准医疗和个体化医疗的时代,重症疾病的诊疗已经从“一刀切”的模式迈入根据患者的个体化需求制定方案并进行滴定式治疗的新模式。在重症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管理上,预测其容量反应性有助于使液体治疗更加精确合理。关于容量反应性,目前亟需的是对新方法的有效性进行验证,同时设法解决常用方法的局限性,扩大其适用范围。对于重症患者容量反应性的评估,目前尚没有完美的评估方法,因此,在必要时联用几种方法取长补短或许才是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