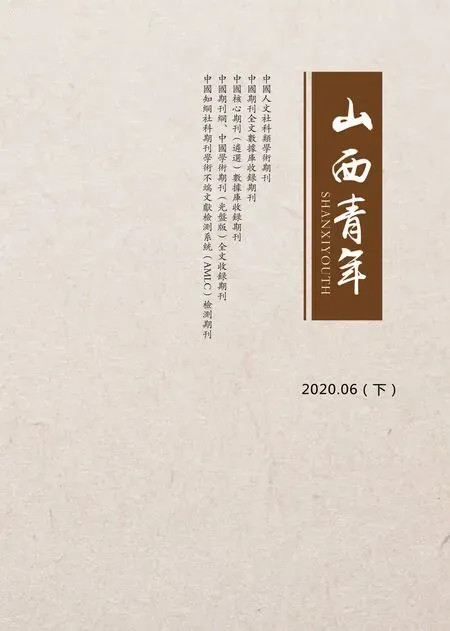新媒体语境下基层卫生部门危机传播策略分析
——以“五星酒店卫生门”事件为例
闫玉娇
北京市延庆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北京 102100
2018年11月14日,微博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的用户发布了一条题为《杯子的秘密》的短视频,曝光了14家酒店的卫生乱象,其中上海7家、北京4家、福州1家、贵阳1家、南昌1家。“五星酒店卫生门”迅速成为微博热搜话题。处于该舆情事件旋涡中心的不仅有被曝光的各家酒店,还有相关的监管部门。这是一次典型的发酵于新媒体语境中的公共卫生舆情事件。
胡百精基于对话范式提出了“事实-价值”模型,认为危机传播管理应该着眼于在“事实层面还原真相、补偿利益”①,在“价值层面重建信任、再造意义”②。危机传播中,对事实真相的还原和价值层面的重建同样重要。本文立足“事实-价值”模型,从事实之维对基层卫生部门的危机传播工作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可行性建议。
一、风险社会的全面到来和新媒体时代的焦虑
贝克在1984年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认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③,并且“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④。风险社会是一种系统性风险。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的信息传播速度和丰富程度实现了飞跃式提升,媒介不仅呈现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风险的助推器和发酵场。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风险和危机已经逐渐成为了我们社会生活常态的一部分,我们在新闻中看到事故和意外事件的报道,既震惊又习惯。
与风险社会相伴而生的是焦虑。罗洛·梅在《焦虑的意义》中提到,“焦虑体验就是一种存在感,是我在存在中体验到的不快乐、不安的情绪”⑤。这种不快乐、不安的情绪,会放大外在威胁的严重性,并进一步造成对外界风险评估的矫枉过正。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爆炸式增长的信息,海量的信息反而强化了作为个体的受众对于世界不确定性的感知。微博话题热搜榜每十分钟更新一次,被网络超链接重新结构化的社会中,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都有可能出现在热搜榜中,被围观、被评判,我们面对瞬息万变的外在世界,强烈地缺乏安全感。
2013年3月,人民论坛做了“当前中国人焦虑程度调查”,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自认焦虑程度较深,超八成公众认为焦虑情绪会“传染”,而“一次次大规模持续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都在强化着”公众的“公共卫生安全焦虑”。⑥
自媒体给处于焦虑中的人们提供了寻求情感共同体的便利,技术民主的赋权让公众的“公民意识进一步增强,从而使得人们获取信息更主动、互动欲望更强烈、质疑与批判意识更明显”⑦。
互联网的技术民主让话语权的争夺打破了传统的壁垒,而受众成为传播市场的稀缺资源。随着各种“大V”不断在互联网上振臂一呼甚至带领公众采取线下行动,“意见领袖”甚至占据了社交网络的节点位置。
二、改变以宣传的思路做危机传播的路径依赖
宣传在20世纪所发挥的作用,让宣传的洗脑和控制作用,成了当代人并不久远的集体记忆,并由此让公众生发出对宣传的警惕和不信任。“大众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传统的‘告知’和‘宣传’话语体系不再必然有效。”⑧
危机情境之中,陷入集体焦虑的人们过滤掉了职能部门的工作举措,并以寻找文中的漏洞作为新的兴趣点。面对这种情况,只有转变传播策略,“以人性化的方式表现出对事件的关心,然后是采取的行动和对事件的全局看法”⑨。
事件平息之初,公众对此类事件的关注仍然会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此时关注的焦点在于涉事主体会采取什么措施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出现,即事件会不会再次发生。“恢复管理既包括对危机所造成事实损害的补偿与修复,也包括对价值异化的弥合与救赎”⑩。
“舆论并不总是理性和正确,却始终强大而不可侵犯”⑪,传播素养,是新媒体语境对于组织和个人的时代要求。对于直面公众的基层工作人员,要避免因个人或者部门出现的不当言行引起误解、激化矛盾,一旦发生危机能够恰当、有效地开展危机传播活动,为处理问题、解决危机争取到理解和支持。公共卫生应急工作不仅是在专业技术层面解决公众的诉求,引导公众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最大程度回归理性,防止谣言散播和社会恐慌的出现,避免进一步演变为舆情事件,也是公共卫生应急处置中重要的内容。
三、做好事实之维的告知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最迫切想要知道的是真相。做好事实之维的告知,跑赢谣言和公众情绪发酵的速度,对后续处置工作的高效开展、挽救部门形象、降低损失至关重要。
关于事实之维的告知,胡百精提出了三个路径,即告知真相、充分告知、适度承诺。公共卫生应急事件直接和公众的健康相关,公众往往迫切需要知道事件的进展,以此来缓解因不知情带来的焦虑和恐惧。同时,职能部门需要给公众一个适度的承诺,这既是对在事件中受伤的公众情绪进行安抚,也为接下来工作的开展尽量争取更多的顺意公众。
危机修辞是涉事主体与公众进行沟通的媒介和工具,“危机修辞实质上就是危机情境下以人为本、合乎理性的公共表达”⑫,“在危机中,修辞替代不了应急救困、价值救赎和利害补偿,但可以提升它们的效率和质量”⑬。组织所发布的每一条信息都事关重大。必须在信息发布前对所有内容进行审核和评估,对可能出现误读的部分进行修改,避免多重解读的可能。公共卫生危机传播修辞应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要避免堆砌专业词汇。在突发事件中,生僻、太过专业的词汇会成为沟通的障碍,影响传播效果。“要保证信息内容通俗易懂,不适用晦涩的术语,既传达科学可知的风险信息,也要承认风险尚不可知的方面”⑭。
第二要避免对立性语言。在危机中,公众对于涉事主体的愤怒和指责是出于解决问题的迫切诉求。从根本上说,涉事主体和公众具有共同的目标,即解决问题、走出危机情境。涉事主体应努力缓和与公众之间的对立关系,促成与公众之间的和解以及“我们”共同体的形成。是“我们”要一起走出危机,而不是“你们”不要激动。
第三要重视非语言符号的运用。语气、手势、体态等非语言符号在播活动中可以传递出丰富的信息,在现场应急处置和新闻发布工作中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优秀的修辞不一定能够拯救危机,但糟糕的修辞一定会恶化危机,甚至自取灭亡”⑮。
四、构建话语联盟
媒体和意见领袖往往被看作是进行社会舆论监督的主要力量。广泛分布在新媒体世界的意见领袖,在传播活动中往往兼具专业性和道德优越性。他们既可以是危机的放大器,也可以成为危机的缓冲带,他们传递的不仅是信息,更是解读的方向。危机中当事主体的信息发布行为往往会被公众解读为自我辩解,但是作为第三方的意见领袖则可以因为其置身事外的超然立场而获得更多的信任,从而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站在专业角度的、有力的、第三方的发声就尤为重要。构建广泛的话语联盟,实现借力传播,对公众实现合理的疏导,对危机传播的效果有重大影响。
五、结论
互联网在“暴露危机、放大危机、制造危机”方面的巨大作用,让所有职能部门都面临着新的挑战,但是互联网同时蕴含着解决问题、促进社会进步的潜能,可以成为通向理解、构建和谐社会的通路。公共卫生机构和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搭建本专业和社会大众的桥梁,不断提升媒介素养和传播能力,建立以受众为中心的沟通和传播策略,合理运用传播媒介,促进对话和社会理解的形成。
注释:
①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82.
②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82.
③[德]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15.
④[德]乌尔里希·贝克.何博闻,译.风险社会.上海:译林出版社,2014.15.
⑤宁卫杰.城市公共安全焦虑,2015.12.
⑥宁卫杰.城市公共安全焦虑,2015.18.
⑦黄河,翁之颢.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形象构建的环境、路径及体系.国际新闻界,2016(08):74-91.
⑧黄河,翁之颢.移动互联网背景下政府形象构建的环境、路径及体系.国际新闻界,2016(06):80.
⑨匡文波.新媒体概论.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222.
⑩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80.
⑪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61.
⑫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46.
⑬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43.
⑭雷吉娜·E·朗格林,安德莉亚·H·麦克马金.风险沟通:环境、安全和健康风险沟通指南.第五版.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121.
⑮胡百精.危机传播管理.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