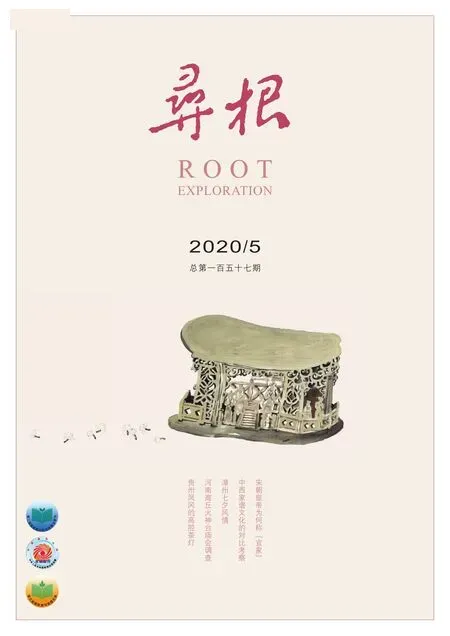清代考官的“名”与“利”
□陈德鹏
所谓“宦途最重是文衡”,自科举产生以来,能当上科举考试的考官,是历代官员的一大幸事,清代也不例外。究其原因,无外乎“名利”二字。
清代考官的“名”
清代考官的“名”大致可分为公、私两个方面。就公而言,是为朝廷选拔有用之才。乾隆皇帝曾对大臣们说:“为国求贤,乃人臣要务。”而求贤最重要的途径,莫过于当考官。选拔有用之才为国效力,谁录取的人才多,谁就会得到朝臣和舆论的肯定。据说,康熙二十年(1681年),归允肃为顺天乡试正考官,杜绝拉关系,一些落第者闹事,试图诬陷考官。刑部尚书魏象枢带着仆人、拿着垫子,到归允肃门前行四拜礼,说:“我为国家庆得人也。”朱彝尊是这一年江南乡试的副考官,回京后,魏又到其门前拜了两拜,对朱说:“非拜君也,庆朝使(考官)之得人也。”康熙六十年(1721年)会试,左副都御史李绂用唐朝通榜法,试卷不糊姓名,落第者到李氏门前闹事,李没奏报。康熙皇帝为了平息士子怒气,将李削职,发配永定河效力。《清史稿》评论说:“然是闱(这次科考)一时名宿,网罗殆尽,颇为时论所许。”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康熙皇帝去世后,李就被雍正皇帝特旨召复原职,并迅速成为最受雍正皇帝宠信的大臣之一。
就私而言,则是个人桃李满天下。按照科举惯例,考官与考取者之间构成师生关系,因此,“历主春秋两试者盈门桃李,众望之辄艳羡若仙焉”。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为母亲服丧期满的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进京,他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当会试副考官录取的进士大多已经当了高官,于是在家置办酒席招待这些门生。侍读学士史夔即席赋诗,其中有“郎君馆阁称前辈,弟子门墙半列卿”之句,盛赞李天馥门下人才之盛。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文华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尹继善,已年过七旬,才初次当考官,乾隆皇帝跟他开玩笑说:“汝可谓新妇生子矣。”当时,朝中称未当过考官的官员是“未字之女”(带有调侃意味),所以,尹继善曾写诗道:
杏苑悬弧典故新,
每因生子忆生身。
凌云老树枝分后,
可念当年手种人?
(尹自注:予之座师、房师俱已辞世)
宫花彩映绣衣新,
半老依然未字身。
自笑殷勤还学养,
宜男却是让他人。
杏苑,指新科进士游宴的地方;悬弧,古人生男孩会在门的左边挂一张弓,表示生了能打仗的男丁,这里指录取进士;宫花,是新科进士赴皇帝赐宴时戴的花。全诗的大致意思是:看到一科科新进士,就想起了当年自己考试的情景;现在那些当了高官的人,是否还记得以前录取自己的座师(主考官)、房师(荐卷同考官或房考官)?考中进士之后,自己虽然不断提升学养,可半辈子都没当过考官,就像“剩女”一样,只能看着别人生儿子。由此不难理解,乾隆皇帝以帝王之尊为何要用开玩笑的方式来祝贺尹继善当了考官。
正因为如此,程汝璞当浙江提学道后,文学家兼剧作家李渔送给他一副对联:
世间桃李尽出公门,何须腊尽始芳菲,满眼无非春色;
干磨试验和邦德功指数均采用标准邦德功球磨机(长×直径:305 mm×305 mm)。传统加热预处理采用电阻炉作为传统加热的设备(功率为12 kW)。
天下鱼龙都归学海,不待时来
方变化,启口即是雷声。
此联颂扬程氏录取的考生多,而录取的考生就是程的学生:所有的士子都是程氏的门生,不用等春天到来,程看到的全是鲜花盛开的桃李;众多学子都想鲤鱼跃龙门,却不用等待春汛,因为程开口说话就是带来春雨的雷声。程汝璞当提学道名声不佳,况且一个提学道怎能配得上“世间”“天下”?李渔送这样的对联,固然是出于奉承程氏,但也说明学差、试差在李渔这种连秀才都没考上的文人眼中,就如同春神、雷神一般。
正是由于这个“名”,在清代官场形成了一股爱才之风。
有人不惜家财以救济穷困书生。如龚鼎孳“怜才下士,嘉惠孤寒,海内文流,延致门下,每岁暮,各赠炭资,至称贷以结客”,没钱了借钱也要救济、结识有才之士。《清史稿·龚鼎孳传》说:“朱彝尊(学者)、陈维崧(阳羡词派创始人)游京师,贫甚,资给之。傅山(思想家、书法家)、阎尔梅(明末举人、文学家)陷狱,皆赖其力得免。临殁,以徐(文学家)嘱梁清标曰:‘负才如虹亭(徐,号虹亭),可使之不成名耶?’后以清标荐试鸿博,入史馆。”真是到死都没忘记爱惜人才。
有人为识拔人才而高兴。张廷璐任江苏学政时,录取秀才汪廷璇,感叹汪“他日名位不在吾下”,亲自为汪改名为廷。汪后来虽不如张(张是榜眼,官至礼部左侍郎),却也很厉害,是乾隆十三年(1748年)探花,官至工部右侍郎。乾隆十二年(1747年),阿克敦、刘统勋为顺天乡试主考官,录取朱,年仅十七岁。榜后,朱拜谒两位座师。阿克敦说:“子年少而魄力大,似先师安溪李文贞公(李光地)。”刘统勋也称赞朱:“子诗文已成家,留心经济,必成伟人。”足见二人对朱的钟爱。而朱也不负老师期望,次年联捷成进士,官至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太子太傅,是嘉庆皇帝的老师。乾隆三十年(1765年)钱大昕典试浙江,录取邵晋涵,高兴地说:“不负此行矣!”六年后,邵中进士,入“四库”馆,成为名噪一时的学者。
有人为了录取人才不惜与主考官相争。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兵部郎中陈为会试同考官,连续两次推荐本房首卷给主考都没录取,陈仍力争说:“此人后当为国家柱石。”主考才录取。此人就是阿克敦,后官至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编修卢文为会试同考官,得到一份佳卷,向主考推荐未果。前二十名确定后,各同考官退出,卢又再三力争不成,流泪而出。这位未录取者就是山东昌乐人阎循观,理学家、诗人。十年后,卢再次当会试同考官,揭榜,阎氏中第九名,侍郎刘荫榆惊道:“此即往年卢某所为抱卷而泣者也,今可为之一鼓掌矣!”
有人为了人才而不惜以身犯险。顺治十四年(1657年),礼部主事丁澎典试河南,见到一份奇特试卷,同考官已置于本房乙等,丁氏说:“此名士也!”决定录取,榜发才知道是李天馥。丁感叹道:“吾以世目衡文,几失此士。”此科,丁与正考官黄因涂改试卷被革职戍边,而李天馥官至武英殿大学士,没有辜负丁的一双慧眼。近代爱国诗人文廷式参加殿试,误将“闾阎”写成“闾面”被查出,翁同爱其才,说:“‘闾面’二字,确有来历。”有人说是笔误,翁又说:“曩吾尝以闾面对檐牙,讵误耶。”由于翁是光绪帝的老师,而文则是珍妃、瑾妃的老师,故无人敢再争,文中榜眼,翁与其他读卷官则因此被议处。
有人为不能录取人才而失望。道光六年(1826年),龚自珍、魏源参加会试,同考官刘逢禄阅龚卷,大喜,极力推荐;刘又在另一房看到魏卷,敦促该房考荐卷。榜发,龚、魏落榜,刘痛惜不已。俞正燮在嘉庆时已是名士,道光十三年(1833年)参加会试,试卷分在同考官王藻房,王阅卷大喜:“此非理初(俞正燮,字理初)不办。”极力推荐,却被主考曹振镛压下。榜后,俞来见,王握其手痛哭。咸丰五年(1855年),李鸿藻为山西乡试副考官,阅卷时,先是感叹没有中意者,在《日记》中不断说“无甚惬意者,殊闷人也”,“迄无甚佳者,闷甚”;后来二三场发现佳卷,可惜其第一场试卷却与人雷同,不能录取,李非常失望:“此卷文诗及二三场俱佳,必系能文之士,何以有雷同之弊,殊不可解,真令人闷闷也。”
正是出于爱才,清代官员才把当考官这个“名”看得比升官发财还重。湖南籍翰林陈源兖是曾国藩的挚友,陈身体不好,妻子又病逝,家道异常艰难。当陈氏外放知府时,本可以改善家境,但清朝有地方官不能当主考、学政的惯例,所以陈很不高兴。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人皆代渠(陈源兖)庆幸,而渠深以未得主考、学政为恨。”还是因为这个缘故,像李鸿章、袁世凯那样的晚清重臣,也会因为没当过考官而抱憾终生。李鸿章是翰林,有资格当考官。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户部尚书李鸿藻去世,余缺由礼部尚书孙家鼐改任,且孙与兵部尚书徐已当过这年顺天乡试的考官,刑部尚书薛允升被降三级调用。据说,李鸿章得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以为自己当次年会试考官的机会来了,他的幕僚于式枚甚至拟定了五道策论试题备用。可惜的是,次年朝廷又点了孙家鼐为会试正考官,李连个副考官都没捞着。后来,李在京城贤良寺与幕僚们闲谈,杨士燮炫耀自己考进士时写的文章。李不屑道:“中进士不得翰林,可羞哉!”杨中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甲六十二名进士,未入翰林,被戳中痛处,杨立即反唇相讥:“翰林一生不得衡文差(当考官),亦可羞哉!”气得李拿起拐杖就要打杨。而袁世凯连个秀才都没考上,自然没资格当考官,所以,“遇投帖称‘门生’者,大喜,必力援之”,算是过一过当考官的干瘾。
清代考官的“利”
按照冯桂芬的说法,清朝的“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清代京官大多比较穷,没法像地方官那样搜刮百姓,而且养廉银也比地方官少,所以就利用自己离皇帝近的优势,向地方官索取财物,而地方官也乐于以此巴结京官,就有了所谓的“别敬”(地方官赴任时送告别礼钱)、“炭敬”(送取暖费)、“冰敬”(送降温费)、“节敬”(送节日礼金)。因此,当京官,尤其是中下层京官,得想方设法捞钱。
士子考中进士、当了官虽是喜事,但经济负担也随之而来:先要给会试、殿试、朝考的老师(考官)送礼,然后每逢“年节必公宴老师,且送酒席于师母。三节皆往拜节,且有节敬。门生外放,岁有炭敬”。说白了,逢年过节都要给老师送礼、请老师吃饭。如果家境不好,这种“人情礼节”就是一项非常沉重的经济负担。“京中有讥贫乏打油诗云:‘先裁骡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二两银’者,惟座师乃克有之。朝殿老师,京钱八千而已。然三节两寿均不可少,总数为不轻矣。门生以此敬师,苟并此而吝之,是绝望于宦途也。”为了报答师恩,为了自己的前程,这钱无论如何都得花。可清代部曹、翰林的俸禄极其微薄,又无其他进项,有靠借债、赊账度日者,所以,“奴仆、债主,皆望其三年一差。倘不考差,则米盐无从赊取,而仆辈亦将望望然去之”。
在清代,有“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的说法。那么,当一次考官、一任学政究竟能收入多少钱?按照何刚德的说法,三年一次的“差”有三等:最好的是学政,三年届满,大省可得三四万两银子,小省可得万余两;其次是主考,好的省份一次可得数千两,不好的也可得九百余两;最差的是同考官,全靠本房录取的门生孝敬,一次大致在三百两左右,虽然不多,但相较于礼部尚书一年的各种津贴一千二百两、侍郎八百两而言,也不算太少。
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学政有养廉银。雍正元年(1723年),原大学士张英的儿子、户部尚书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璐出任河南学政,生活困难。雍正皇帝听说后向张廷玉了解情况,并令河南巡抚田文镜计算一下,最后确定河南学政的养廉银:每年用人夫、马匹银一千六百两,幕僚的束银一千两,赡养家庭一千两,各类杂用三千两,合计每年养廉银为六千六百余两,三年共需二万两。乾隆元年(1736年),又增加江苏、安徽学政的养廉银。直隶、江苏、安徽、陕甘、山东、山西、福建、云南的学政,每年四千两养廉银。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将河南、广东、浙江三省学政养廉银多于四千两的,均减至四千两,裁减的钱补给养廉银低的省份:江西由二千四百两增至三千五百两,广西两千两、四川三千两、贵州两千七百两、湖北三千两都增至三千二百两,奉天府府丞兼管学政的四百两增至五百六十余两,湖南的三千六百两照旧。
当主考官的有路费,但乾隆朝之前没有规定具体数目,各省督抚看情况给。乾隆三年(1738年)按距离远近作出规定: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各六百两,江南(包括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江西、陕西各五百两,河南、山西、山东各四百两,各省督抚不得任意增减。
当然,除上述官方规定的钱数外,各地科考还有一些陋规。如嘉庆四年(1799年)有人参奏,贵州学政向新考中的秀才收取红案银(红案是公布录取秀才的榜单),再加上书吏、保结廪生的索取,每人花费四五十两。贵州学政称,各省都有棚规(以童试考棚名义收的考务费),用以支付书役饭食、试卷、笔墨和考棚等费用,唯独贵州没有,只好向新考中的秀才每人收取一二两至五六两不等作为考务费。嘉庆帝无法,只好同意收取。次年,谕令将贵州学政的养廉银增加五百两,达到三千七百两,同时取消各省的棚规、红案银等所有陋规。可是,只增加贵州学政的养廉银,其他省的学政会有何感想?从清代官场的惯例看,陋规是不可能完全取消的,而陋规中的绝大部分都落入了官员的腰包。
考官除了路费,自然也有不少其他收入,因而是穷京官实现“经济翻身”的重要途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曾国藩当考官后的花费来看: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氏当四川乡试正考官,当年腊月给老家寄了一千两银子,次年四月又托人带回五百一十两,而且他自己在京城租赁“内城现住房共廿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三十串,极为宽敞”,又配了车马,“每年须费百金”;咸丰二年(1852年),曾又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因母亲去世未到任,江西省“送来奠银一千两”,曾氏用它还债和安葬母亲。至于像翁同那样的贵胄公子,更是地方官巴结的对象。同治元年(1862年),翁充山西乡试正考官回京前,“九房送程仪二百两”,又有“同城各官送程仪八百两”,再加上其他收入,除旅途用度外,寄回家一千二百两。
上述学政、考官的收入,在当时的官场算是比较正常的,至于不正常的能收入多少,就不好计算了。如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俞鸿图为江西考官,收受举人的牌坊银(官方给新举人竖旗、挂匾、建牌坊、立旗杆等的银子);十年(1732年),俞鸿图任河南学政,贪婪之心再起,与临颍县知县贾泽汉勾结,在许州以每个名额三四百两银子的价格卖了四十七个秀才,俞本人得银一万多两。雍正皇帝震怒,将俞处斩。据说,俞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被腰斩的人,临刑时因家产被抄没钱贿赂刽子手,被“斩”后仍然没有死,用手蘸自己的血在地上连续写了七个“惨”字。乾隆十二年(1747年),朱荃简放四川学政后,隐匿母亲去世的消息,不辞官、不守孝,收受银两、貂衣贿卖生童九人,并收新秀才贽礼银四五千两,又因为牵涉到文字狱,朱畏罪跳水自杀。乾隆三十年(1765年),梅立本任广西学政,到各属考试,比前任学政多用民夫七百名,每棚另收捐项银六十两为书役饭食钱;所到之处,勒索供应、凌辱地方官。陆川县知县杨是梅立本的会试同年,殿试梅是榜眼,而杨只中了三甲一百三十二名。据说,梅本来就有些看不起这位知县同年,因而对陆川县的供应百般挑剔,说该县准备考试用的书不齐,又嫌纸张不如广东产的优质纸等,几次责打杨派来办事的长随,杨只得亲自到梅下榻的公馆门前长跪赔罪,梅却拒不接见(一说是五月初一杨冒大雨送学政,久等梅不出署)。大雨中的杨实在不堪如此羞辱,当场自杀,而梅本人也被判死刑。嘉庆十五年(1810年),编修徐松充湖南学政,在长沙府学、长沙和善化两县学发《经文试帖新编》,每地发一百二十至一百四十本不等,每本收银三钱六分;考试优等秀才,每人收取数百文刊刻试卷费,等等。此类案件不胜枚举,而这些不正常的收入,即使在当事人的日记、家书中也很难找到详细记录,因而也算不出具体数目。
总之,在清代当考官是一件名利双收的大好事,大多数考官、学政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做得还不算太过分,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有用之才。但也正因为将“名利”二字看得太重,不少人早把自幼熟读的儒家忠君爱民思想忘得一干二净,搜刮地方,贪污腐败,沦为国家罪人。故晚清有人感叹:“当日翰林以考差为第二生命,真足以颠倒豪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