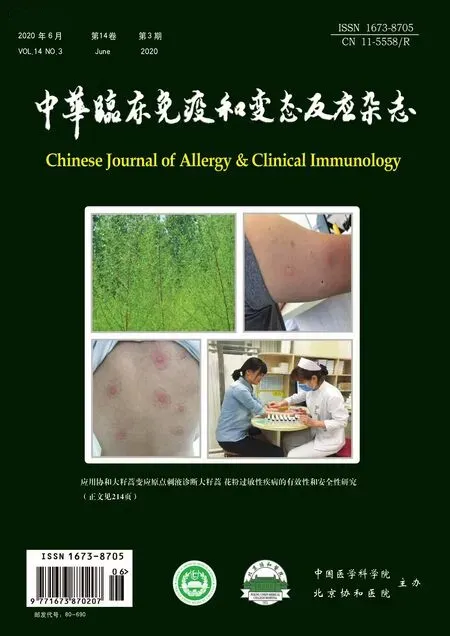高迁移率族蛋白B1在变应性鼻炎的作用机制
林小燕,李静,李勇,杨烨
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是由IgE介导的以发作性喷嚏、流涕及鼻塞、鼻痒为主要症状的鼻黏膜慢性炎症性疾病。AR影响着全球4亿患者的生活,其中20%~38%过敏性鼻炎伴发支气管哮喘[1-2]。2005至2011年,中国人AR发病率约为17.5%,并呈上升趋势[3],对人们的生活质量及工作效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医疗经济支出。AR的具体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虽然现有的药物可以有效的控制症状,但远期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探讨AR的发病机制以及新的治疗靶点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广泛重视。
高迁移率族蛋白于1973年首次在牛胸腺中被提取和鉴定,因其在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中迁移速度快而得名。高迁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box-1,HMGB1)是广泛存在真核生物细胞核中的一类高度保守的非组蛋白[4],其作为前炎症因子被证实在多种疾病中起重要作用,如败血症、肿瘤、动脉粥样硬化、组织缺血再灌注损伤、关节炎、哮喘、慢性肾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均与其促炎症作用相关[5-6]。在一定条件下HMGB1会释放到细胞外,与多种细胞因子及趋化因子相互作用,导致炎症反应的放大和持续[7],从而介导炎症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大量研究已经证明HMGB1与免疫炎症反应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变应性鼻炎的免疫调节失衡及上气道慢性炎症等机制已受到广泛认可。因此考虑HMGB1可能通过调节免疫细胞分化、细胞自噬以及上皮细胞损伤等几方面参与气道变应性炎症反应,本文综述HMGB1在AR发病中的作用。
1 HMGB1的结构、功能和常见受体
人类HMGB1基因定位于染色体13q12,HMGB1的初级氨基酸序列中含有219个氨基酸残基,相对分子量约为24 894 Da[8]。HMGB1蛋白由3个独特的DNA结构域构成(A-box、B-box和一个酸性C尾),HMGB1依靠DNA结合位点与单链、双链和扭曲的DNA无序列特异性相结合,能够稳定核小体结构和调节DNA的构象,促进某些转录因子包括类固醇激素受体等的结合[9]。其中A-box(9-85氨基)在N-末端,进化过程中高度保守;酸性C尾(C-tail)在羧基末端(186-215氨基酸),包含30个重复的天冬氨酸和谷氨酸残基,可参与调节核内HMGB1与DNA结合的亲和力,实现相关生物学功能[10];而HMG box B(89-162氨基)位于二者之间,具有细胞因子样活性,是引起炎性反应的功能结构域。研究证实,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及其他促炎细胞因子在HMGB1的作用区域定位于 HMG box B结合域的前20个氨基酸残基区(89-108氨基)[11],150-183氨基酸序列则可介导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RAGE)与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2/TLR4)的结合。从功能上分析,细胞外的box-B引起炎性反应,而box-A可拮抗box-B引起的炎症反应,且Box-A与C-tail 结合后能够增强其抗炎活性[10,12]。
早期对于HMGB1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其在核内所起到的转录和调控作用。正常生理条件下,HMGB1定位于细胞核内,参与了DNA修复、转录调控及维持基因组稳定性等多种DNA事件;直到1999年,Wang等[13]发现,脓毒血症等炎症性疾病可刺激巨噬细胞释放HMGB1至细胞外,作为一种重要的内源性促炎症因子和炎性介质,参与多种炎症性和免疫性疾病的病理过程。随着对HMGB1在胞外致炎作用的深入发掘,诸多研究表明,HMGB1可作为炎症介质,介导炎症细胞因子的释放,炎症介质进一步促进HMGB1的释放,形成一个正反馈放大炎症级联反应,影响着免疫炎症反应[14]。
2 HMGB1参与AR可能机制
2.1 AR与上皮细胞损伤机制
鼻黏膜上皮细胞作为呼吸道的第一道物理及免疫屏障,是机体接触及处理过敏原的始发环节[15]。正常鼻黏膜上皮细胞(nasal epithelial cells,NECs)结构及屏障功能的维持依赖于相邻细胞间紧密连接,Herbert等[16]的研究结果提示,尘螨变应原蛋白 Derp 1 可破坏黏膜上皮细胞紧密连接复合体,使黏膜上皮通透性增加,导致屏障受损及下游的免疫应答。在长期的慢性炎症刺激下,纤毛上皮损伤、脱落,杯状细胞增生以及细胞外基质沉积,导致鼻黏膜重塑[17]。研究发现,利用HMGB1刺激鼻黏膜上皮细胞可使上皮紧密连接蛋白occludin、ZO-1、claudin1表达减少,通透性增加,导致上皮屏障功能受损[18],屏障功能的损伤导致鼻黏膜更易受变应原及外源性有害物质的侵袭,是鼻黏膜慢性炎症迁延不愈的关键原因[19]。另一项研究显示,低氧诱导HMGB1从细胞核被释放到组织环境中,分泌的HMGB1通过参与IL-8上调介导鼻黏膜慢性炎症反应,考虑HMGB1可作为分子标记用于检测器官缺氧相关组织损伤[20],因此HMGB1有望成为降低鼻黏膜慢性炎症性损伤的干预靶点之一。
2.2 HMGB1与免疫调节细胞
AR是由多种免疫炎症细胞共同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目前辅助性T淋巴细胞(helper T lymphocyte,Th)失衡机制为主导的免疫学说已经得到公认[21-22]。正常情况下,Th1和Th2的增殖处于一种相对平衡状态,当进入黏膜的抗原物质为病毒、细菌时,则在机体发生Th1反应,Th1细胞分泌IL-2、IFN-γ,介导抗感染的细胞免疫。而当气道黏膜受到变应原刺激时,Th2 细胞过度极化引起Th2类效应因子(IL-4、IL-5、IL-13)优势表达,介导体液免疫,Th2细胞因子作用于B细胞,后者转化为浆细胞产生和分泌特异性IgE,进一步介导过敏反应的发生。体外实验研究表明,HMGB1 对T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具有双重影响,刺激Th1与Th2比率的降低,导致Th1/Th2平衡向Th2亚群优势分化[23]。外源性HMGB 1可通过诱导Th2型反应优势,促进中性粒细胞炎症,加剧急性过敏性哮喘气道炎症,而其中和性抗体(anti-HMGB1)可有效缓解这一现象[24],为HMGB1参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依据。另外,HMGB1还可能通过影响Th17细胞的增殖和活化而参与某些免疫性疾病,研究显示,重组高迁移率族蛋白(rHMGB 1)可加重哮喘小鼠气道炎症以及黏液生成,通过调节树突状细胞(DC)的功能诱导Th2、Th17极化,而anti-HMGB1则参与阻断Th2、Th17介导的炎症反应[25-26]。同时,嗜酸性细胞在Th2优势表达的免疫反应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当鼻腔黏膜受到病原刺激时,HMGB1大量释放至胞外导致嗜酸性粒细胞聚集,从而促进了TH2介导的免疫炎症反应,TH2反应发生后又反向刺激HMGB1的表达增多,进一步产生大量炎性细胞因子,加剧了嗜酸性粒细胞的聚集[27]。
因此,HMGB1可能通过影响免疫调节细胞成为免疫炎症性疾病的潜在治疗靶点之一。
2.3 HMGB1介导免疫炎症反应相关的信号传导通路
研究发现HMGB1 是重要的炎症调控因子。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和未成熟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受到外源性侵害时会主动或被动分泌HMGB1到细胞外,与相应气道上皮细胞表面模式识别受体(PRRs)结合,包括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受体(RAGE)、Toll样受体(TLR2/TLR4)家族部分成员、CXXL12、凝血酶敏感蛋白(thrombospondin,TM)等[28-29]。RAGE是第一个被证明的HMGB1结合受体,被认为是HMGB1参与机体炎症反应中最有效的受体之一[30]。Lee等[31]研究发现,炎症介导释放的HMGB1与细胞膜表面受体RAGE结合是触发相关炎症疾病的主要信号通路,可直接通过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 NF-κB)通路或间接通过MAPKS等通路使NF-κB易位,进而促进一系列的炎症因子比如TNF、IL-6和IFN-γ的释放[32],参与多种炎症及免疫性疾病的病理过程。但应用RAGE抗体或RAGE基因敲除方法,并不能完全抑制HMGB1引起的炎症反应,RAGE介导HMGB1的炎症机制目前未完全清楚。
近年来,Toll样受体在变应性鼻炎(AR)中的免疫调节作用逐渐被人们所重视。HMGB1通过与Toll样受体TLR4相互作用,激活NF-κB,引起该通路下游的炎症介质释放[33]。一项研究表明,在患有鼻息肉或过敏性鼻炎的慢性鼻-鼻窦炎患者的鼻分泌物中,HMGB1的含量明显升高,而HMGB 1可促进鼻腔上皮细胞产生和分泌炎性因子IL-6和IL-8,介导鼻黏膜上皮的炎性反应,但在使用TLR4抗体后,鼻黏膜上皮细胞分泌的IL-6和IL-8明显减少,提示HMGB 1在上呼吸道炎症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34]。与此同时,研究发现,进入上气道黏膜的变应原可刺激TLR激活抗原提呈细胞,诱导气道上皮TLR4表达升高,产生各种炎性介质和趋化因子,调节辅助性 Th1/Th2 的平衡[35]。
综上所述,HMGB1可以通过调节气道上皮细胞表面模式识别受体而参与上气道变态反应炎症的调控。
2.4 HMGB1与自噬
最新研究发现,在炎症应激(如感染、氧化应激和饥饿等)条件下,核内HMGB1转移至细胞质中,与自噬因子Beclin-1结合从而激活并促进细胞自噬[36-37]。HMGB1可通过主动分泌或者在细胞发生坏死时通过被动释放入细胞外间隙,在细胞外间隙的 HMGB1 调节细胞自噬的过程主要是通过与RAGE结合来实现激活下游 AKT-mTOR自噬相关信号通路,促进 PI3K Class III与Beclin1结合,直接导致细胞的自噬增强;而在核内的HMGB1在炎症状态下可以诱导微自噬而参与调控自噬过程[38]。自噬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的生理过程中,在进化上高度保守[39]。正常生理情况下,细胞内保持一个比较低的基础自噬水平,而当细胞处于应激(如感染、氧化应激和饥饿等)状态时,刺激细胞自噬水平迅速上调[40],对细胞自我更新和内环境稳态的维持起重要作用。Dickinson等[41](使用小鼠气道疾病模型)研究证明自噬参与了IL-13诱导的气道上皮细胞黏液的分泌和氧化应激损伤。变应性鼻炎和哮喘为上、下气道的变应性疾病,在流行病学、病因学和病理生理学上的相似性。Martin等[42]研究了自噬相关基因的多态性与哮喘的关联,发现哮喘急性发作期患者鼻黏膜上皮细胞中Atg5 mRNA的表达显著上升,说明自噬与变应性炎症反应具有相关性。因此,HMGB1可能通过调控自噬参与过敏性疾病的发病[43],但相关研究还比较少。
3 HMGB1与变应性鼻炎
AR是鼻黏膜接触特异性变应原后发生的由IgE介导的变态反应性疾病。通过上述总结,HMGB1可能通过调节T细胞分化、细胞自噬以及上皮细胞损伤等参与AR的发病,因此HMGB1可能成为治疗AR的一个新的且充满前景的方向。研究发现AR儿童患者鼻腔灌洗液中HMGB1的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与症状的严重程度强烈相关[38]。刘阳等[44]研究发现HMGB1在变应性鼻炎中鼻黏膜中表达増高,并与鼻甲黏膜中嗜酸性细胞数目呈负相关,提示HMGB1可能通过作用于嗜酸性粒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抑制变应性鼻炎的发展。丙酮酸乙酯(EP)已被证明是许多气道疾病的有效抗炎剂,可以抑制HMGB1的分泌,Chen等[45]在一项动物实验中发现EP的应用可有效降低过敏性鼻炎小鼠中HMGB1的表达及在鼻黏膜上皮层的释放,并且EP可以通过降低HMGB1表达来减弱AR的过敏反应,同时还减轻了AR小鼠鼻黏膜中杯状细胞増生等组织学改变。这些结果表明HMGB1可能参与了AR的发生发展,并有望成为新的治疗靶点。
AR和哮喘由于上、下呼吸道黏膜不仅在解剖上连续,且同属免疫系统相关淋巴组织,在发生、共存和相似性方面均有密切联系,一直存在有“同一气道,同一类疾病”(one airway, one disease)的假说[46-47],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综合征(CARAS)这一术语被引入来描述具有同一疾病的两种表现的患者[48-49]。早期有研究表明哮喘患者的痰液及血清HMGB-1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且与疾病的严重性成正相关[50]。随后HMGB1在哮喘中的作用越发受到重视。研究发现在卵蛋白(OVA)诱导的变应性鼻炎哮喘综合征(CARAS)小鼠模型中,屋尘螨(HDM)致敏可诱导气道上皮释放HMGB1,激活HMGB1-RAGE轴进而放大变态性炎症反应,使HMGB1成为治疗干预气道炎症性疾病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靶点[14]。同时,Tang等[51]发现TLR4拮抗剂可通过抑制HMGB1-TLR4 信号通路轴,下调炎性趋化因子的表达并减少单核细胞在鼻黏膜和肺组织中的浸润,从而减轻CARAS小鼠模型上、下气道症状。由此进一步证实,HMGB1可能在气道变应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4 总结
AR目前已成为影响全球健康问题,该病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临床上传统药物治疗及特异性免疫疗法均有一定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在AR致敏和效应阶段,HMGB1可能通过参与上皮细胞损伤、调节T细胞优势分化以及自噬等几个方面调节上气道免疫炎性反应。然而目前HMGB1在 AR中的直接作用机制研究较少,以 HMGB1为治疗新的干预靶点仍需要大量临床试验支持,本文通过阐述HMGB1在变应性鼻炎中的研究进展及作用机制,希望能为AR的防治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