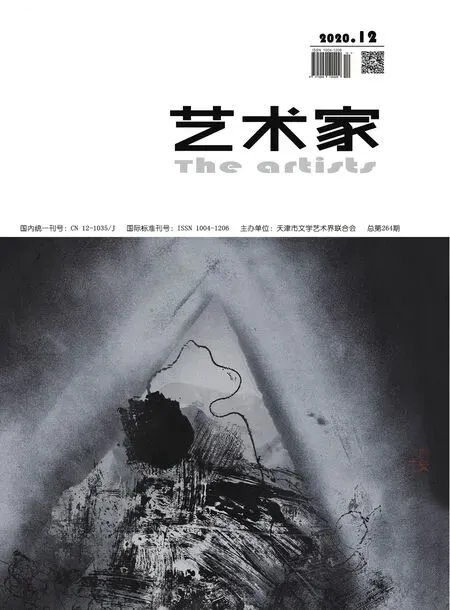书法与情感
□孙 越 山西师范大学
关于“情感”这一话题,汉代蔡邕有言:“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唐孙过庭亦有“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之说,这里的“达”和“形”正是表达之意,即表达书者的个性和情感。正如刘熙载《艺概》中提到的“笔墨性情,皆以人之性情为本”,这一系列的论述都表明书家情感与作品二者的紧密联系,以及书作中情感流露的重要性,即书法中的情感能够表露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读者的审美体验,表现书者的情绪、心境和意趣。
书法中的情感能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简言之,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人内心情感的表露。与其他艺术相比,“书”是更加持久、历久弥坚的,书法这种以笔画为媒介来表情达意的独特形式就如纸上的音乐和舞蹈。中国毛笔书法正是以汉字为基础,通过毛笔这种独特的工具来描绘书者的内心世界。
书法中的情感能表现读者的审美体验。内心世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最丰富的、最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因为它是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复杂的而非单一的,会有千变万化的可能性,也正是因为这样才更值得我们去琢磨和推敲。作为以“动”的姿态来表现人物思想感情的书法,其笔迹的美在根源上也不能脱离现实世界的“情”。千古绝唱《兰亭集序》是王羲之在时和气润的三月与文人墨客于会稽山下饮酒赋诗后将内心的愉悦和满足留驻笔端的产物;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充溢着对悲惨社会的控诉和鞭挞,那利剑般的线条是作者内心深处不可抑制的情感的宣泄;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更是通过笔墨线条,如“花泥”二字的牵丝连带、“苇”字下拉拖出的竖及几乎用笔肚抹出字形猛然放大、突兀的“哭涂穷”三字,将性情之中的旷达和对命运的哲思表现了出来,这种波澜后的平静让人折服。因此,情感的流露才是书法艺术透过墨迹要表达的实质。
书法中的情感能表现书者的情绪、心境和意趣。归结起来,“情感”的根源,绕不开情绪和心境。任何艺术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情绪和心境的影响,书法也不例外。不同的心境通过媒介——纸,传递给欣赏者的是独一无二的体验,所以古人作书个个不同。“要之皆一戏,不当问工拙,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这是米芾自己的审美取向,明确表明了书法创作的“尚意”观,其中“意”就是指书者内心的感受和联想。除此之外,执笔者还应把书法当作一种娱乐,书写时心情愉悦才是重点,而非结果的优劣。
上述内容在各个时期都有所体现,魏晋时期被视为文学艺术的自觉时代,此时的文人墨客强调对人物意趣的关注和个体复杂而细腻情感的表达,在语言文字难以尽意之时,书法便成了文人表露情感的一种重要载体,同时被以“二王”为代表的书家推至高峰;唐尚法之外,还有着张旭和怀素这样借助书写来抒发跌宕起伏情绪的典型;宋代打破唐法的拘束转而将“意”作为时代风气;在元代,不满异族统治的书家们书法上也以强烈的复古之风来表达心中的不满和无奈;明清的书风则更加注重姿态的变化。由此可见,无论在哪个时期,“情感”这一线索都始终贯穿其中。
相反,现代人作书多半是“为人”而不是“为己”,缺少了这种真实情感的流露。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人的内心轨迹,这种内心轨迹的起起落落才是线条背后隐藏的本质。“五乖五合”之“五合”早已不能同时具有,“神怡务闲”取而代之以“神短气浮”,“感惠徇知”取而代之以“急功近利”,心有所束怎能达到不拘谨呢?又怎能达其性情形其哀乐呢?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现代书家去思考和推敲的。首先,“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即是答案,因此在书法创作中应少一些拘谨和做作,多一些从容和惬意,从而达到最佳状态。其次,这里的“放笔”也不能理解为毫无法度的随意挥毫,而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对于多数人而言,当代的书法创作已成为一种有意识的艺术创作,情感吐露包括的随意性和真实性的融入也会随之大打折扣,这必定会使书法流于匠气。因此,情感应是第一位的。当然,情感的表达也要受理性的约束,否则仅有情感的宣泄,也不是艺术。在具体创造过程中感性和理性,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只是往往有所侧重。虽然当代书法的实用价值日渐消退,但它情感载体的艺术性、独特性、包容性,以及文化传承的功能性却有着无可代替的作用。
诚如托尔斯泰《艺术论》所言:“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情感。”情感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艺术的本质也正是“表意”“言志”,强调“书为心画”。中国的书法正是通过汉字的形来表情、言志、抒怀,从而多维展示书家的精神面貌并寄托人们的精神追求,这也正是书法的首要目的。因此,将丰富的情感体验融汇笔端,从而达到有情而发,才可能产生高水平、为后人赞叹的书法作品。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文化的滋养会使情感更加细腻饱满,因为书法不仅仅是艺术,更是文化及情感的依托。
——开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