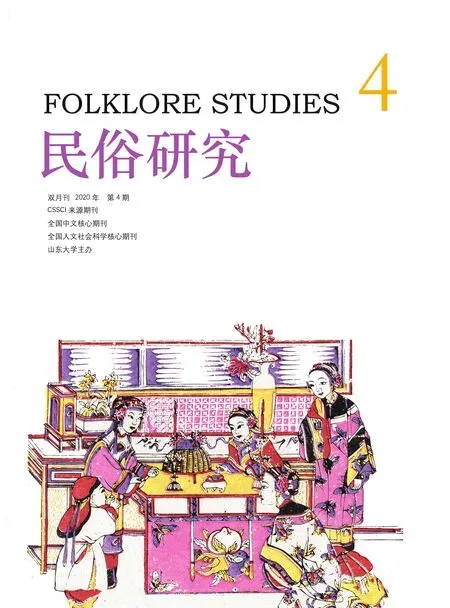眼光向下的性别回应: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中的歌谣与妇女
王均霞
1923年,刘经庵在其关于歌谣与妇女的研究中断言,“平民文学,妇女的贡献,要占一半”;“民俗学,妇女的问题,要占一半”。(1)刘经庵:《歌谣与妇女》,《歌谣》周刊1923年第30号。在中国民俗学史上,刘经庵大概是第一位明确将女性与民俗学并置的学者,也是第一位直白地强调妇女的文学与妇女的问题在民俗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学者。但刘经庵对该问题的关注绝不应该被看作孤立的个体行为。相反,在当时的研究语境里来看,这其实是研究者的一种潜在共识。例如,洪长泰敏锐地指出,有关妇女遭遇的歌谣帮助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者找到了揭露和批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新视角,成为揭示整个中国民众,尤其是妇女的真实生活状况的途径。(2)[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赵世瑜注意到黄石自1928年至抗战前这一时期,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习俗的学术论文,“代表了当时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一流成果”(3)赵世瑜:《黄石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李海燕强调五四民俗学运动是将民俗定位于底层话语或者女性话语(the discourse of the feminine)的。(4)Haiyan Lee, “Tears that Crumbled the Great Wall: The Archaeology of Feeling in the May Fourth Folklore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4, no.1(Feb., 2005),pp.35-65.另外,刘锡诚、王文参等学者也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对妇女及妇女问题的关注。(5)参见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王文参:《五四新文学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民族出版社,2006年。但整体而言,在中国民俗学学术史的研究中,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中的妇女问题研究尚没有被作为一个出发点得到系统归纳和总结,妇女问题研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也仍旧晦暗不明。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歌谣与妇女研究为中心来分析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妇女问题研究的整体取向及其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关系,以廓清妇女问题研究之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的意义所在。将歌谣与妇女作为研究的入口,是因为歌谣研究被视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起点,而且在之后的20年里一直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妇女作为歌谣的主要吟唱者,妇女的苦难生活作为歌谣的主要内容,吸引了当时许多研究者的目光,“妇女,伤痛与歌谣”成为民俗学运动中最持久的主题。(6)Haiyan Lee, “Tears that Crumbled the Great Wall: The Archaeology of Feeling in the May Fourth Folklore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4, no.1(Feb., 2005), pp.35-65.
一、妇女解放运动、眼光向下的革命与乡村妇女的发现
要理解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的歌谣与妇女研究,首先不能忽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金天翮就曾断言“十八、十九世纪之世界,为君权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之世界,为女权革命之时代”(7)参见金天翮:《女界钟》,李又宁:《华族女性史料丛编(1)》,纽约天外出版社,2003年,第79页。《女界钟》最早出版于1903年。。也确如其所言,二十世纪上半叶,妇女解放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解放事业纠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女性压迫被视作中国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8)[美]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9)Friedrich Engels, Anti-Duhring, 外语出版社,1976年,第334页。,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五四运动中最引人注目、最令人信服和最受人拥护的事业”(10)[美]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63页。。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分子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例如,在历史学领域,历史学家通过钩沉妇女生活史揭示“我们有史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底历史”(1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8-19页。。在文学领域,文学家通过小说的翻译与创作揭示传统父权制家庭对女性的束缚与压迫,鼓励女性勇敢地与父权制家庭决裂,追求个体的自由与解放。(12)参见杨联芬:《浪漫的中国:性别视角下激进主义思潮与文学(1890-1940)》,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美]李海燕:《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爱情的谱系》,修佳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中国现代民俗学正诞生于这样的时代,当时的民俗学事业的开拓者大都与妇女解放运动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例如,极力赞颂民间文学之真的胡适,与罗家伦合译了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提出“易卜生主义”,鼓吹“妇女冲破以男权为中心的家庭制度的束缚,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13)[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2页。。周作人写了许多与妇女问题相关的文章,提出了将女性视作人的妇女观。(14)舒芜:《女性的发现:知堂妇女论类抄》,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很少有人将顾颉刚与妇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但实际上,顾颉刚也是一位关注妇女解放问题的学者。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细致分析了旧家庭中的名分主义与习俗主义如何对妇女造成了压迫。(15)参见顾诚吾(顾颉刚):《对于旧家庭的感想》,《新潮》1919年第2期;顾诚吾(顾颉刚):《对于旧家庭的感想(续)》,《新潮》1920年第4期;顾诚吾(顾颉刚):《对于旧家庭的感想(再续)》,《新潮》1920年第5期。黄石在《妇女杂志》《东方杂志》《新女性》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与恋爱、婚姻、家庭、生育相关的文章,还翻译了顾素尔的《家族制度史》,提出“欲女子解放成功”,“非首先推翻家族制度不可”(16)黄石:“译后”,[美]顾素尔:《家族制度史》,黄石译,开明书店,1931年。!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妇女及妇女生活的关注与讨论遍布于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的研究中。以黄石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文献考据与文化描述的方法对相关妇女风俗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对北平郊区的妇女生活展开调查并撰写极为规范的民族志,以刘经庵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田野调查搜集与整理女性民俗资料,揭示妇女的生活状况。(17)王均霞:《从“事象”到“情境”: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目标生成》,《民俗研究》2014年第4期。其中,歌谣与妇女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
坦率地说,尽管大部分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者收集歌谣的初衷似乎并非是为了了解妇女的生活,但显然,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当这些歌谣被收集起来的时候,妇女及其生活便成为歌谣研究中无法绕过的一个主题。在关于歌谣搜集的田野介绍中,一些研究者坦陈他们的歌谣是从妇女那里搜集来的。例如,刘经庵说他所编辑的《河北歌谣第一集》总共有三百多首,“多半是妇女们给我说的”(18)刘经庵:《歌谣与妇女》,《歌谣》周刊1923年第30号。。刘达九在介绍自己的歌谣采集经验时,指出“欲求富于文学性的歌谣,须向妇女征求”。根据他的采集经验,女子对于唱歌特别有天赋,而且女子更“闲谈”些。“因此,欲求得直美的歌谣,是必向女子去求。成年男子所唱的歌谣,不是有意为之,便是记不完全。”(19)刘达九:《从采集歌谣得来的经验和佛偈子的介绍》,《歌谣》周刊1923年第30号。既然多数歌谣都出自妇女之口,那也难怪人们很快发现《歌谣》周刊上刊登的歌谣“有十之七八是妇女造成的”(20)许竹贞:《看歌谣后的一点感想》,《歌谣》周刊1924年第24号。了。刘经庵正是根据《歌谣》周刊上刊登的歌谣以及自己收集的歌谣,编辑了在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史上有着广泛影响的《歌谣与妇女》;董作宾也根据《歌谣》周刊上刊登的歌谣,编辑了《看见她》。还有一些研究者对自己收集的歌谣进行了性别化的分类与命名。例如,顾颉刚在《吴歌甲集》中就有“乡村妇女的歌”“闺阁妇女的歌”这样的分类;白寿彝的《开封歌谣集》中也有“妇女的歌”这一类别。
《歌谣》周刊也刊登了诸多讨论歌谣与妇女的文章,如《歌谣中的家庭问题》《闽南妇女在民歌中的地位》《歌谣与妇女》《看歌谣后的一点感想》《歌谣中的舅母与继母》《从歌谣看我国妇女的地位》《歌谣中的姑嫂》等。或许是受到歌谣运动的鼓舞,在这一时期的其他许多杂志,如《妇女杂志》《东方杂志》上也出现了不少讨论歌谣与妇女的文章。这些文章或直接从普遍意义上讨论歌谣与妇女问题,如《歌谣中的妇女贞操》《从歌谣上解剖旧式妇女心理》《从歌谣中剖视妇女》《歌谣与妇女问题》《歌谣中的家庭问题》等,或专门讨论特定地区的歌谣与妇女问题,如《河北南部歌谣中之妇女生活状况》《河南太康歌谣中的妇女的问题之一斑》《歌谣中的浙东妇女》《歌谣中的冀南妇女》《漳州的妇女歌谣》等。
与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虽将目标定位于全体妇女实则更关注城市资产阶级女性的主导潮流不同,民俗学研究发现了处在主流话语边缘的乡村妇女。整体而言,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目标(21)孙新、王涛:《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百年》,青岛出版社,2010年。,无论是争取男女社交公开,还是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抑或是争取女子经济独立,都与挣扎在生活最底层的乡村女性的最迫切需求相去甚远,即便是看起来最接近的反对封建婚姻制度,也无法对乡村妇女产生实际的意义,因为乡村妇女显然不能像城市里出走的“娜拉”一样与婚姻家庭决裂。在如火如荼的妇女解放运动中,乡村妇女却隐形于运动之外。当时许多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尽管女权问题早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题目,但乡村妇女并未享受到妇女解放运动带来的好处,仍然过着旧礼教遗留给她们的地狱般的生活。(22)参见王肇钧:《大名妇女歌谣研究》,《期刊(天津)》1934年第2期;亚葵:《从歌谣中去检讨农村妇女生活》,《绸缪月刊》1936年第2卷第5期。
而民俗学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关注到了这些被忽略的乡村妇女。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的肇始时期,民间就是民俗学研究的关键词,“到民间去”被与民俗学紧密地捆绑在一起。(23)[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正是在呼吁到民间去的声音中,民众进入到民俗学研究者的视野,其所指是与圣贤相对的“农夫、工匠、商贩、兵卒、妇女、游侠、优伶、娼妓、仆婢、堕民、罪犯、小孩……”(24)顾颉刚:《〈民俗〉发刊辞》,《民俗》周刊1928年第1期。等普通民众。顾颉刚批评说,圣贤文化并非不好,只是不适合于人性;与被圣道、王功、经典所束缚的圣贤相比,民众以自己的真诚创造了被压没在深潭暗室里的活文化。他呼吁知识分子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将民众文化与圣贤文化平等起来,平视民众文化。(25)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在岭南大学学术研究会演讲》,《民俗》周刊1928年第5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乡村妇女与其他处于边缘的民众一起进入民俗学者的视野。
顾颉刚在解释“乡村妇女的歌”和“闺阁妇女的歌”时,认为与更关注丈夫的功名以及夸耀自己持家能力的闺阁妇女的歌谣相比,乡村妇女没有受过礼教的熏陶,吟唱更多的是赤裸裸的爱情。(26)顾颉刚:《吴歌甲集自序》,《歌谣》周刊1925年第97号。胡适称赞顾所搜集的包括“乡村妇女的歌”在内的乡村“道地”民歌是真诗,可惜太少了。(27)胡适:《吴歌甲集序》,《国语周刊》1925年第17期。《歌谣与妇女》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乡村妇女,但在一篇介绍歌谣中的家庭问题的文章中,刘经庵说自己在采集歌谣时,那些妇孺们“谓我是读书人,不必学村妇小儿的俗歌”(28)经庵:《歌谣中的家庭问题》,《妇女杂志(上海)》1926年第1号。,可见其所辑录的歌谣大部分出自乡村妇女之口。而有一些研究直接关注的便是歌谣与乡村妇女生活,例如《从歌谣中去检讨农村女性的生活》《歌谣中的中国乡村妇女》《大名妇女歌谣研究》《歌谣中的冀南妇女》等。在这些研究中,歌谣成为揭示乡村妇女苦难生活的路径,因为乡村妇女“是民众中最痛苦最受压迫和受不平待遇的人”,歌谣能够真实地反映农村妇女的生活和地位。(29)彭寿延:《歌谣中的中国乡村妇女》,《女青年月刊》1935年第1期。
二、妇女的文学与妇女的问题
当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者在歌谣中发现了乡村妇女之后,其研究思路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个是从文学的视角出发,将歌谣视为妇女的文学,强调妇女在文学上的贡献;一个是从社会问题的视角出发,从歌谣中看出妇女的问题,强调妇女所遭受的压迫。刘经庵是最早注意到歌谣与妇女的研究中这两条路径的学者。在一篇文章中,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妇女的文学与妇女的问题”。他说,
歌谣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这话任谁亦不能否认的;但这样的材料,是谁造成的?据我自己的观察,一半是由妇女们造成的。——平民文学,妇女的贡献,要占一半。——歌谣是民俗学的主要的分子,这话任谁亦不能反对的;但所谓一般民俗,以关乎那一部分的为最多呢?据我调查所得,一半是讨论妇女问题的。——民俗学,妇女的问题,要占一半。(30)刘经庵:《歌谣与妇女》,《歌谣》周刊1923年第30号。
刘经庵的观点与周作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为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写的序中,周作人指出歌谣研究有不同的路径,而在当时“最为适当而且切要的”是“从歌谣这文艺品中看出社会的意义来,实益与趣味两面都能顾到”(31)周作人:“《歌谣与妇女》序”,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商务印书馆,1927年。,他称赞《歌谣与妇女》是这一研究路径上的代表著作。后来的研究者往往注意到周作人对歌谣中蕴藏的“社会的意义”的强调而忽视了他将“文艺品”与“社会意义”、“趣味”与“实益”并举的用心。(32)Haiyan Lee,“Tears that Crumbled the Great Wall: The Archaeology of Feeling in the May Fourth Folklore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64, no.1(Feb.,2005),pp.35-65.
(一)妇女的文学
《歌谣》周刊以及董作宾、顾颉刚等人的研究引发了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对歌谣的兴趣,开辟了歌谣研究的新道路,使其导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是推动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一是为现代中国带来了新的社会和思想影响”(33)[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1页。。就文学的维度而言,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者总结出民歌值得新诗学习的三个特征,即质朴、真性情和口语化(34)[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同时强调民歌所揭示的是“人生的艺术派”而不是“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35)仲密(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第5期。。作为歌谣之组成部分,乡村妇女的歌谣当然也具备这些特征,但同时研究者也发现了乡村妇女歌谣的独特之处。这些独特之处是在研究者所建立的多个比较的坐标系中得到呈现的。刘经庵的表述最具代表性,我们不妨将其完整地呈现于此:
妇女是自古多情者,她们不但富于爱情,——拜伦(Byron)谓“爱情是妇女的生命”——亦具有妒情的;且她们好以感情用事,她们易受外界的刺激,亦易有所反应,因之文学的作品,贡献的机会比较多些;所以歌谣的作家,多半是妇女们。我们知道天所赐于妇女的文学的天才,并不亚于男子,不过她们久为男子所征服,没有好好的发展罢了。但是她们富有情感,文学的天才,未曾淹没,遇有所触,可随时而发,把潜伏的天才,自然的流露出来。她们既久为男子所征服,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只有日居深闺,过那干燥的,寂寞的生活了。她们因为寂寞无聊,就信口吟哦些歌谣,来排解自己的忧闷。她们所歌唱出来的,虽有些是无甚意义,但有许多是关乎民情的,是表现她们的心理的。更是有些妇女们,受公婆的虐待,妯娌和姑嫂间的诽谤,以及婚姻的不满意,她们满腹的冤屈,向谁诉去?她们既不会像文人作什么离骚的词,断肠的诗,所以“就不平则鸣”,把自己的痛苦,放情而歌的唱出来了。若是我们拿艺术的眼光,来批评她们的作物,乃是人生的艺术观,不是唯美的艺术观。因为她们的歌谣是哭的叫的,不是歌的笑的,是在呼诉人生之苦,不是在颂赞自然之美,是为人生问题中某项目的而做的,不是为歌谣而做歌谣。当她们信口歌唱时,并不讲什么规律,亦不限什么字句,——她们讲亦不懂,所以不被限制——心里有什么,便唱什么,意思唱完,亦就停止,毫不讳避。这大概因为没有受过多大的腐儒们的礼教的熏冶,所以思想较为自由,不像曹大家等作什么《女诫》一类的书,来戕害她们自己的苦姊妹们。因为她们不会咬文嚼字,矫揉造作,只会用白描的手段,质朴的,逼真的去说,所以歌唱出来的,不但趣味浓厚,真切活泼,而且很自然,很能动听。至于文人学士,他们每日在文字中讨生活,什么文呵,赋呵,闹个不休,是不屑为此的。其余一般的人呢,因为生计所迫,终日劳碌,亦无暇顾此;所以歌谣的贡献,多半是妇女们。这样看来,我们若说妇女是歌谣的母亲,歌谣的大师,亦不算太过吧。(36)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2-4页。
刘经庵至少建立了四个比较的坐标来呈现乡村妇女的歌谣的文学特征,而这些特征又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研究者的支持。以下我们在刘经庵的总结的基础上,综合地讨论乡村妇女的歌谣的文学特征。
首先,在男性与女性情感表达的坐标里,人们认为女性较男性更多情且易于感情用事,因而“歌谣的作家们,多半是妇女们”。尽管歌谣整体上都具有真性情,但在这个整体之中再建立男性与女性情感表达的坐标,研究者发现妇女比男子更富于感情。如刘经庵所暗示的那样,人们相信,从生物属性上看,女性天生就比男性更多情,更易感情用事,再加上她们处于沉重的压榨之下,因而情感更容易不可遏制地爆发。(37)阿铁:《歌谣中的妇女》,《乡村改造旬刊》1933年第18期。在一篇讨论妇女与文学的文章中,丁英提醒读者注意民歌与妇女的生活之间密切的联系,认为作为人类之一员的女性有感情,有思想,更有不可抑制的愤懑,她们把自身的爱与恨、喜悦与愁苦都灌注到她们的文学作品里去了。作者强调,那些来自民间的充满了青春活力和热情的民间艺术,“在全部妇女文学中占着重要的一页,是应该与以强调和注意的”。(38)丁英:《妇女与文学》,丁英:《妇女与文学》,沪江书屋,1946年,第2页。引文中“与以”应为“予以”。
其次,在征服与被征服的坐标里,女性“久为男子所征服,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只有日居深闺,过那干燥的,寂寞的生活”,她们将一肚子的苦水倒向歌谣,因而她们的歌谣“是哭的叫的,不是歌的笑的,是在呼诉人生之苦,不是在颂赞自然之美,是为人生问题中某项目的而做的,不是为歌谣而歌谣”,所以她们的歌谣是“人生的艺术观”而非“唯美的艺术观”。这一点显然是乡村妇女的歌谣最独特的特征。在另一篇讨论歌谣与妇女的文章中,丁英指出“受着层层束缚的妇女,她们给歌谣写下了许多生活的故事。她们用爱和泪养育了它”(39)丁英:《她的一生——从民歌中看到中国妇女的生活》,丁英:《妇女与文学》,沪江书屋,1946年,第7页。。正是由于此特征,乡村妇女的歌谣成为呈现乡村妇女的问题的重要途径,并成就了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者参与社会变革的政治抱负。
再次,在上层女性与底层女性的坐标里,乡村妇女没有受过礼教的熏冶,她们歌唱时不受诗词规律与文字的限制,心里想什么,便唱什么,意思唱完,歌便也停止了。她们思想自由,因而敢把她们的中心思想(爱情)赤裸裸地叙述出来,这与闺阁妇女对于功名的吟唱形成鲜明的对照。(40)顾颉刚:《吴歌甲集自序》,《歌谣》周刊1925年第97期。
最后,在文人学士与村妇野老的坐标以及底层男性与底层女性的坐标里,乡村妇女不会咬文嚼字,因而她们的歌谣是白描的,是质朴的、逼真的,这使得她们的歌谣“不但趣味浓厚,真切活泼,而且很自然,很能动听”。也即是说,乡村妇女的歌谣富于文学性。研究者认为,与底层男性相比,乡村妇女更具有歌唱的天赋,而且比男性更“闲谈些”。那些成年男性,一方面他们终日劳碌,无暇顾此;另一方面,他们的歌谣,不是有意为之,便是记不全,而且以骂人的为最多。(41)刘达九:《从采集歌谣得来的经验和佛偈子的介绍》,《歌谣》周刊1923年第30号。
正是在以上诸多比较的坐标里,刘经庵总结说,妇女是歌谣的母亲、歌谣的大师。妇女的歌谣成为研究者所提炼和推崇的民歌之特征的主要代表,其对于新文学的贡献得到了某种承认。另外,将这些研究置于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中来看,与主流的强调妇女受压迫的时代风潮不同,这些研究还看到并高度赞美了最底层妇女的才情,并强调她们的歌谣之所以在形式上质朴自然,在内容上富于情感,与她们未受礼教的熏陶密切相关。
不过,从文学的视角讨论乡村妇女的歌谣,很快被淹没在从社会问题视角出发对妇女所遭受的压迫的揭露中,没有引起进一步的讨论。
(二)妇女的问题
与对乡村妇女的歌谣的文学特征的讨论相比,歌谣中所呈现的“妇女的问题”显然更受重视。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研究者相信,歌谣能够“纯真地摄影着现实的形象”(42)钟敬文:《江苏歌谣集序》,《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第1期,第3页。,蕴含着民众真实生活的丰富资料(43)林箫:《从歌谣中剖视妇女(一)》,《妇女青年》1936年第186期,第504页。。
研究者首先发现在当时的歌谣中关乎妇女问题的歌谣很多。根据谢晋青的研究,《诗经》中,在十五国风的一百六十篇诗歌中,关乎妇女问题的诗歌竟有八十五篇之多。(44)谢晋青:《诗经之女性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24年。“当《诗经》时代,人民没有受多大的礼教毒,思想颇为自由,尚且有那么多的妇女问题发生,何况秦汉以后,思想不能自由,人民大受礼教的束缚,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低下”(45)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4页。,关乎妇女问题的诗歌恐怕比《诗经》上还要多。那么,在妇女问题日益增多的情况下,这一问题为什么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呢?刘经庵将其归咎为民间采风传统的中断,政府不再关心民间的疾苦,妇女的声音也就没有被听到的机会。同时,在封建制度的荼毒之下,妇女自我内化了她们的痛苦,认为命该如此。(46)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商务印书馆,1927年。但妇女对于自身所遭受的压迫便完全无感了吗?显然也不是的。刘经庵指出,这些乡村妇女“虽不能像近今一般有学识的妇女,作什么女权运动和妇女参政等有规模的组织;可是她们的情感是未曾死的,还有一副脑筋,一张嘴巴,自己编几句韵语,唱几首歌谣,来申诉自家的痛苦”(47)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5页。。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些歌谣听到了妇女的心声,进而将歌谣视作呈现妇女问题的重要途径。
更进一步来讲,歌谣被作为呈现妇女问题的途径,原因至少有三:第一,在外在与内在的坐标系中,一些人认为,仅从外表去观察农村妇女的苦痛是不够的,“她们有着无限的凄楚和愿望,被礼教所吞噬却不能发泄出来。我们如果要根本去启发她们那含在内心里的疾苦与愿望——她们的生活,只有从她们所唯一能发泄怨望的歌谣中,才能够寻求出来”(48)亚葵:《从歌谣中去检讨农村妇女生活》,《绸缪月刊》1936年第5期。。第二,在书本知识与田野知识的坐标系中,一些人相信,要知道中国妇女的真切状况,仅靠书本上的记载是不够的。“最可靠,最可感人的材料,必须从民间流行的歌谣中去求,因为这些歌谣,足以代表妇女的真实呼声,不经文人的润色,而能够代代流传,普遍全国,自必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或‘感人密深’的魔力。”(49)腾公编述,焦毅搜集:《中国歌谣中的女性》,《妇女青年》1933年第58期。第三,在对西方的经验“拿到中国来,是否对症下药”的质疑中,一些人主张,“研究中国的家庭问题,还得由实行调查民间的家庭状况入手,我们研究歌谣的人,从歌谣中也略略看出一点民间的家庭问题”(50)常惠:《歌谣中的家庭问题》,《歌谣》周刊1923年第8号。。研究者对于通过歌谣来研究妇女问题充满了希望,周作人在为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写的序中,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歌谣选集,但也是一部妇女生活诗史,可以知道过去和现在的情形——与将来的妇女运动的方向。”(51)周作人:“序”,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商务印书馆,1927年。
通过歌谣来研究妇女问题,研究者将重点放在了呈现妇女在婚姻家庭中所遭受的苦难上,这种书写模式大概始自常惠。1923年,常惠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歌谣中的家庭问题》,通过歌谣勾勒妇女苦难的一生。这些妇女的苦难体现在她们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关系中,如姑嫂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婆媳关系。(52)常惠:《歌谣中的家庭问题》,《歌谣》周刊1923年第8号。此后,通过歌谣来研究妇女问题,研究者基本未超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框架。正是基于此框架,刘经庵完整地勾画出中国妇女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包括她的父母、她的媒妁、她的公婆、她的小姑、她的兄嫂、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她的舅母与继母、她的情人等十个类别。这些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多数,对女性造成的都是压迫而不是爱护。例如,女性在家里受父母的轻视,兄嫂的嫌弃,如果不幸母亲早亡父亲再娶,摊上继母,日子越发难过,如河南卫辉的歌谣:“纺花车,钻子莲,养活闺女不赚钱。一瓶醋,一壶酒,打发闺女上轿走。爹跺脚,娘拍手;谁再要闺女谁是狗。”又如广西象县的歌谣:“长江水,漫漫流,哥去广东不回头。大嫂打妹去烧火;二嫂打妹去看牛;三嫂要妹去挑水;四嫂要妹洗锅头。想起来,命不修!”仍是河南卫辉的歌谣:“小白菜,地里黄,七八岁时离亲娘。好好的跟着爹爹过,又怕爹爹娶后娘。娶了后娘三年整,养个弟弟比我强。他吃菜,我喝汤,哭哭涕涕想亲娘。”女性没有婚姻自主权,婚姻的成立全仰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不幸者多,妇女的歌谣中便多了对媒人的咒骂,如云南的歌谣:“歪茄子,病毛瓜,给我嫁在背时家。洗衣沟又深,找菜路又生,跺跺小脚骂媒人。”婚姻既成,小媳妇的苦难生活开始了,总是受公婆的打骂,如湖北黄冈的歌谣:“天上大星排不匀,地下小妇难做人,一升麦子磨三升,公公骂婆婆打,还说小妇给人家。剪下青发吊死咱,不要金装,无须银埋,留得美名千万载。”小姑也不是省油的灯,河南安阳的一首歌谣唱出了小姑如何挑拨离间:“小豇豆,崩破腰,我是娘哩小娇娇,我是爹哩白银子,我是哥哩一枝花,我是嫂哩搅地爬。今儿搅,明儿搅,我把嫂嫂搅死了;娘家来出气,就说哥哥打死了。”丈夫不是幼小,就是丑陋,最糟糕的是不成材,如山东德州的歌谣:“月亮奶奶明晃晃,开开庙门洗衣裳;洗的白,浆的白,摊了个女婿不成材。又喝酒又摸牌,早起去,黑了来,这个还不分打开;五个孩子一家俩,剩了个瘪肚跟着他奶奶。”儿子长大了也不孝顺,“娶了媳妇忘了娘”,生活中唯一的光亮来自于她的情人,只是这份光亮还不见容于礼教,如云南个旧的歌谣:“高山砍柴刺篷多,小妹头上管头多;心想留哥吃顿饭,谁知关门眼睛多。”(53)本段所有歌谣来自刘经庵:《歌谣与妇女》,商务印书馆,1927年,页码按顺序依次为第7页,第49-50页,第122页,第18页,第24页,第33-34页,第89页,第147页。
经由这些歌谣,刘经庵不仅详细呈现了妇女在家庭中所遭受的压迫,所经历的苦痛,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指明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对妇女造成的戕害:
中国的家庭,向来是主张大家族制的,因之妯娌与姑嫂间的倾轧,婆媳与夫妇间的不和,随处皆是,无家不有,中国家庭之腐败,真是糟到了极点了。要知道家庭的腐败,就是妇女们的不幸,因为妇女们总是幸福之牺牲者。中国歌谣关乎妇女问题之多,恐怕就是中国家庭不良之明证了。有人说,关乎中国妇女问题的歌谣,就是妇女们的《家庭鸣冤录》,《茹痛记》,我以为这话很有点道理。(54)刘经庵:《歌谣与妇女》,《歌谣》周刊1923年第30号。
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研究在当时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其后的许多相关研究都提及他的研究,并在研究思路和结论上借鉴这一延续自常惠的歌谣与妇女研究范式。
不过,跳出刘经庵等人的歌谣与妇女研究来看,此一时期发表的与妇女生活相关的歌谣,实际并不仅仅呈现妇女生活的苦难,也有许多歌谣反映了妇女生活的欢愉。即便是在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中,不少被归类为“其他”的歌谣中所呈现的那些“要老婆”“想女婿”“新婚与于归”的歌谣就充满了轻松愉悦的气息。另外,黄石在《从歌谣窥察定县家庭妇女的生活》将妇女的一生分为三个时期,一个是在家做闺女的时期,一个是在婆婆底下做媳妇的时期,一个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婆”的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最悲惨的是在婆婆底下做媳妇的时期,而在家做闺女的时期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婆”的时期被他称为定县妇女的“黄金时代”。在这些“黄金时代”的歌谣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妇女生活中自在逍遥的一面。(55)黄华节(黄石):《从歌谣窥察定县家庭妇女的生活》,《社会研究》1935年第59期。因而,很大程度上说,那些讨论歌谣与妇女的文章中所呈现的妇女生活的苦难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浪漫主义选择与建构,以把矛头指向封建家族制度。正如洪长泰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应该重点关心的其实不是民歌所描写的内容,而是20世纪初的中国民俗学者怎样解释这些民歌,以及支持这些解释的理由”(56)[美]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董晓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86页。。研究者对歌谣内容的选择性阐释,是与此一时期研究者通过歌谣来揭露儒家伦理纲常对妇女造成的深重压迫目标一脉相承的。
三、结 语
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关于歌谣与妇女的研究,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民俗学眼光向下的革命。在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思潮与民俗学眼光向下的革命中,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者从歌谣中发现了乡村妇女。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文学,认为由于未受礼教的熏陶,乡村妇女的文学在形式上质朴自然,不受咬文嚼字之累,在内容上更敢于表达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发现了妇女的问题,认为乡村妇女歌谣中所吟唱的是受传统家族制度压迫的悲惨生活,歌谣被建构成妇女的“家庭鸣冤录”“茹痛记”。无论是对妇女的文学的赞颂还是对妇女的问题的揭露与批判,研究者都将矛头指向了儒家文化所建立的一整套礼教制度。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的思潮是一脉相承的。妇女问题成为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者批判儒家伦理纲常、参与社会改造的浪漫主义路径。要充分理解中国现代早期民俗学研究,妇女问题研究显然是其中无法绕过的维度。
——学院派民俗学的世界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