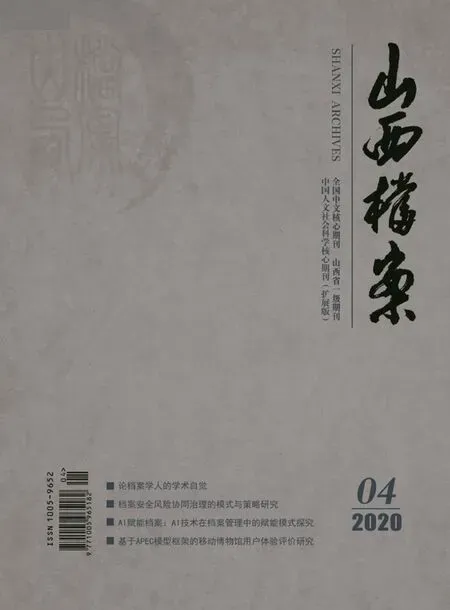数字人文视角下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路径*
(南昌大学历史系 南昌 330031)
0 引言
20世纪中期数字人文的相关研究步入人们视野[1]。2001年布莱克维尔出版社出版了《数字人文指南》,“数字人文”取代“人文计算”成为西方流传广泛的跨学科领域代名词[2]。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人文”逐渐成为备受瞩目的研究领域。数字人文研究不断深入,相关实践项目不断展开。各高校、研究机构纷纷成立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国内外相关数字人文学术会议和数字人文项目专题讲座方兴未艾[3]。数字人文是由“数字”与“人文”两个核心要素构成,是数字技术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数字人文是将数据分析技术、数据管理技术、可视化技术、机器学习、虚拟现实等数字人文技术和工具应用于人文研究。数字人文改变了传统人文社科项目的研究方式,人文学科借助数字人文呈现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目前档案界对数字人文的研究也愈发重视,“数字人文+档案”逐渐成为档案界研究的一种新思维,相关研究成果渐趋增多。但在我国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领域,鲜有数字人文应用的相关研究。鉴于此,关注和探索数字人文视角下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1 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的意义
地方特色档案资源是我国文化遗产资源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开展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重视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有利于社会记忆完整性构建。地方特色档案资源是该地区的鲜明标志,带有时代色彩和历史痕迹,能够再现地方历史,有利于构筑人类完整的社会记忆;其次,重视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有利于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地方特色档案往往带有民族特色、区域文化,开发地方特色档案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手段;再者,重视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地方特色档案作为独特的经济资源,带有当地的经济特色,将特色档案资源与当地旅游经济相结合是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的新价值取向;最后,重视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有利于推动地区人文精神建设。从地方特色档案资源中可窥探该地区的历史源流,了解一个城市的故事与智慧。重视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可以激活特色档案中的人文精神,真正实现一座城市一种情怀。
2 数字人文在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中的应用
2.1 以理念碰撞为契机,促进档案开发价值增值化
数字人文理念注重数字技术与人文思想的融合,有别于传统的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理念。数字人文理念与传统开发理念的碰撞能够促进传统档案资源开发价值观念的转变,进而促进档案资源开发价值的挖掘与增值。在数字人文理念积极影响下,档案馆在进行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中会逐渐注重档案资源中的人文价值,从而在开发中重视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人文需求,努力在特色档案开发过程中构建增值化资源库,进一步实现档案价值的增值化服务。如档案馆可在数字人文理念驱动下为特色档案馆藏资源可视化构建立体化三维环境:内部环境——语义化的馆藏资源;外部环境——兼有数字与人文素养的人才队伍;拓展环境——可视化研究的增值服务[4]。数字人文理念能够激发档案资源本身的“活性因子”,是实现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价值增值化的动力机。
2.2 以技术融入为依托,构建档案开发形式多样化
数字人文的技术体系主要包括数字化技术、数据管理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可视化技术、VR/AR技术、机器学习等技术[5]。数字人文技术在特色档案资源开发中的应用是在技术维度优化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形式。档案馆在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依托数字人文技术,并对其展开充分利用,能够形成多样化的特色资源开发模式。如国内“数字敦煌”项目中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使得人们能够更直观、多维的欣赏敦煌的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以全息视频形式再造往日城市繁华景象,展示历史群像,带给人们沉浸式观感体验[6]。可见,数字人文技术升华了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形式和表现模式,是构建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形式多样化的助推器。
3 现阶段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瓶颈
3.1 开发主体较为单一,导致开发聚力不足
目前国内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主体依然以档案馆为主,开发主体较为单一,易导致后续的资源开发聚力存在“熄火”现象。我国档案馆仍是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和主导者。但是,仅仅依靠档案馆单一开发主体不能够支撑起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大厦。因为档案馆在资源、资金、人才、技术等当面都存在一定的豁口,所以在后期的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难免会存在“力不从心”现象,以及更为严峻的“聚力”不足问题。较为单一的开发主体是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3.2 开发技术相对保守,造成开发创新走低
由于档案本身的特殊属性,相关档案部门在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难免会考虑是否存在档案泄露、档案损坏等问题。档案馆受限于档案材料本身,对于开发技术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会束手束脚。档案资源开发技术的相对保守,导致档案网站所展示的特色档案资源内容主要仍以纸质档案数字化为主,并未产生“质”变与“新”意。档案资源开发局限于内容展示、文字展示等,开发创新程度较低。数字环境下的档案资源开发工作不能只是档案网站挂着的一个个扫描文本。这并不是一种创新,这是在重复之前的开发老路。因此,开发技术的相对保守,仅依靠增量电子化、馆藏数字化是导致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创新一度走低的原因之一。
3.3 开发内容缺乏深度,导致开发产品乏善可陈
目前档案资源开发仍局限于史料编纂,编研开发的产品种类相对单一,档案产品内容和形式不够丰富[7]。档案资源的内容是特色档案的灵魂所在,一切档案开发活动的源头都是基于档案本身的特殊内容所展开。当然,对于档案资源的开发更是不能抛开档案内容空谈档案理想,这是不现实也是不切实际的。档案机构在进行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时对档案材料内容切入深度不够,开发拘泥表面,小“流量”产品社会认知度与感知度较低。只有深入挖掘档案内容,档案资源开发才能有深度,开发的产品才能有市场。
3.4 开发形式与用户需求脱节,造成用户参与度不高
现阶段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形式与“以用户需求为内核”的开发理念不太契合,开发形式落后于用户需求。同时,档案部门在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时调研度不够,未能对当下社会用户需求有着精准掌控,不能以受众需求为出发点。特色档案开发形式滞后于用户需求也难以开发出受到普遍大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档案产品。这也就造成目前我国特色档案资源开发面临的一个严峻而又现实的问题就是不能迎合数字时代档案用户多维度、深层次、高品质的档案追求和体验感,导致了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形式与当代社会用户需求相脱节的现状。反之,档案用户需求得不到满足,用户利用率低,那么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的用户积极性与用户参与度便随之降低。
4 数字人文视角下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路径
4.1 融入多元主体,实现跨界开发
数字人文的跨学科性和跨机构性决定着数字人文视角下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的跨界与融合。目前国内特色档案资源开发主体单薄,档案馆寻求多元化开发主体至关重要。对于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正如上文所述,仅仅依靠档案馆这单一主体单打独斗是难以做好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这一块大蛋糕的。因此,档案馆必须摒弃传统的观念壁垒,寻求跨界合作,要做到“跨界”、“破界”。总之,档案馆想要突破现阶段特色档案开发模式,要勇于跨越壁垒和边界,构建跨地域、跨主体、跨类型的“三跨”合作模式。如档案馆可同图书馆、博物馆合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和沟通机制,将两者的数字人文项目实践经验应用到档案馆特色档案资源数字人文项目开发中。并且进一步实现“三馆联动”的协同参与新机制,构建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合力,建立语义关联存储数据库、将馆藏资源进行集成开发并实现以检索可视化、呈现可视化以及统计可视化为支撑的资源库模式[8]。多主体融入式开发,将各自的馆藏资源进行跨界编译,能够为特色档案资源前期开发构建海量资源库。
4.2 开拓技术应用,实现创新开发
文本挖掘技术、GIS技术、VR技术、AR技术、可视化技术等数字人文技术应用使得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更具创新性。开发技术的选取需要以特色馆藏为基础,以开发目标为准则。在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坚持的初心是技术最终服务的依然是档案本身,重视特色档案在开发技术中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两者的统一,才能够依托数字人文技术实现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创新。如通过文本分析技术,可深入挖掘特色档案背后的内容;依托VR/AR虚拟现实技术,可实现特色档案的“历史重现”;采用可视化技术,可完成特色档案由数据到图形或者图像的转化等[9]。借助先进的数字人文技术,可将传统的特色档案资源进行加工、润色、再创作。如相关学者借助人工智能AI修复特色珍贵史卷,重现100年前清朝居民的生活画卷,实现静态档案到动态影像的转换,创新了传统档案资源展示形式与开发形式。如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在特色资源建设中研究的数字人文项目——“数字敦煌”,就是利用测绘遥感、3D打印等相关技术,将敦煌文物及莫高窟内外形态进行精确扫描、修复还原,并以数字形式保存[10]。因此,档案部门在进行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时,重视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将不同的数字人文技术与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相互融合,是实现特色档案资源创新开发的重要举措。总而言之,融合数字人文开发技术,从不同技术维度进行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要让特色档案资源通过数字人文技术“活化”起来。档案馆对特色档案资源的开发从“静态”到“动态”的转变,能够丰富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的内涵和外延,进而实现创新开发的目标。
4.3 深挖内容精髓,实现特色开发
档案机构对具有民族色彩和区域特色的档案资源内容进行深度挖掘,创建地方特色档案品牌文化项目,是实现档案资源特色开发的关键策略。针对特色档案资源的区域色彩,档案馆进行资源特色开发可以应用“水波效应”,将本馆开发的特色产品作为独家,作为波纹中心;其余可做衍生品,作为余波,要利用优势,打造优势,拓展特色档案资源开发内容深度与广度,增强档案资源特色开发的凝聚力与影响力。例如“隐秘的纽卡索”是英国泰恩-威尔郡档案馆开发的一款APP,它借助地理信息分析技术(GIS)实现“穿越时空”功能,当用户走在街道上,只要打开APP就可以看到街区的老照片、历史故事等[11]。那么,我国档案馆可借鉴上述实践经验,借助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等技术对特色档案资源内容进行特色定位分析,深入挖掘内容精髓,进行特色档案APP开发。档案馆需要重视深入挖掘特色档案资源库,透过特色档案现象看到特色档案本质、由果索因,解析特色开发的第三视角。除此,档案馆还可进行档案特色“IP”内容结合,实现单“IP”一枝独秀与双“IP”百花齐放繁荣开发局面,双管齐下深挖特色档案深层次的内涵,创造独家文化精品和地方特色品牌。
4.4 精准用户服务,实现参与开发
时代发展下人们更倾向于以新媒体技术为主导的网络环境下获取知识,因此档案馆在进行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时要定位用户群体,重视用户意见,精准用户服务,努力带动用户参与到特色档案开发中。针对用户画像技术,档案馆在进行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精准用户服务需要采集用户数据、进行用户数据清洗与转换、提取档案用户特征、构建档案用户画像,最终实现精准推荐服务的目标[12]。首先定位准确才能确保开发目标群体的正确性;其次,重视意见可提升用户参与积极性;最后,精准服务是前两者的落脚点,更是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一。因此,档案馆在进行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时,借助用户画像技术提供精准化推荐与个性化服务,满足档案用户的心理需求,才能更好的提升服务质量与用户参与度。除此,数字人文项目的发展为不同受众参与到特色档案资源开发项目中提供了新的思路。如美国“影谷项目 (The Valley of Shadow) ”是数字人文实践的典型案例,访问者在检索档案资源时可自主实现标签、笔记的创建[13]。总之,在数字人文视角下,档案馆在特色档案资源开发过程中,精准用户服务,积极搭建目标用户与特色档案资源开发两者之间的桥梁,才能更好实现特色档案资源的参与式开发。
5 结语
地方特色档案资源是随着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断沉淀下来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承载着独特的社会记忆和历史文化。在文化强国战略指引下,地方档案特色资源开发正逢其时。当数字人文逐渐成为改变知识创新与分享的游戏规则而被档案界所认识、接受并与之相结合,无疑为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视野、更加广域的空间。总之,观照数字人文理念,充分、合理、科学的利用数字人文技术,构建一个多元主体合作,跨界联合的开发网络,深入挖掘特色档案内涵精髓,精准用户服务等,将是未来地方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