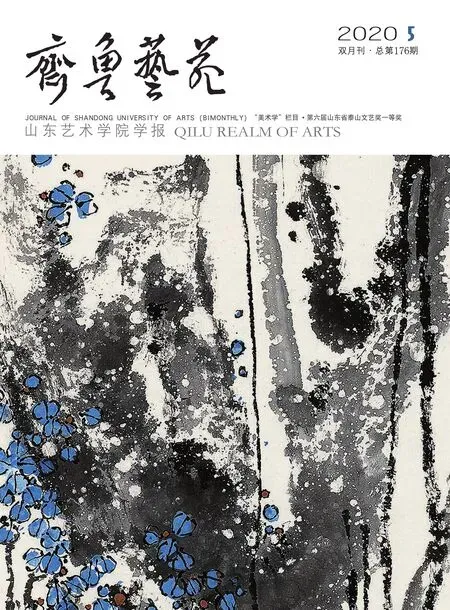摹象、喻象、意象:关于中西方“戏剧形象”问题的思考
杨慧芹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我们知道,艺术是要塑造出某种形象供人欣赏的。正如英文韦氏大词典侧重于“创作者—形象—欣赏者”三者关系,将“艺术”定义为:“艺术是有意识地运用技巧和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生产能为他人所共同欣赏的审美物品、环境或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作品”。《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解释“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如文学、雕塑、舞蹈、绘画等。”[1](P1550)黑格尔从哲学层面阐释“艺术形象”:“一切艺术的目的都在于把永恒的神性和绝对真理显现于现实世界的现象和形状,把它展现于我们的观照,展现于我们的情感和思想。”[2](P334)可见,不论艺术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其首要任务是塑造形象,然后才有可能言及其他。
东西方文学艺术家依据自身反映生活的方式的不同,在文学本质的体认过程中,对构成文学形象的“意”(主观情志)和“象”(客观物象)两方面之关系做出不同理解,提出运用摹象、喻象、意象三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和组合方法完成文学形象,产生的艺术效果自然迥异。戏剧艺术亦是如此,因其反映生活的方式不同,折射在戏剧本体上生发出不同的艺术方法和艺术手法,来实现创作者的主体情志和被描绘的客观物象的统一,最终在舞台上获得形象的体现,寻根究底,是由于中西方戏剧本体所蕴涵的美学原则截然不同,戏剧形象的创造规律自然也存在差异性和独特性。
一、“戏剧形象”的分类问题
既然“形象”对于一切艺术来说是如此重要,笔者就从“形象”问题出发来研究戏剧问题。 “形象”一词出自于《周易·系辞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3](P185)然而,“形”和“象”两个汉字合并使用,最早见于西汉时期孔安国的《尚书注疏》:“审所梦之人,刻其形象,四方旁求之于民间。”[4](P20)其中“形象”一词很显然是并列关系的同义复词,“形”即轮廓,“象”即造型,无“象”即无“形”,无“形”愈难成“象”,就词语来源来讲,“形象”一词显然是指直接与视觉有关的事物,奠定了形象论的基础。《辞海》对“形象”有两条解释:“①形状相貌。②指文学艺术区别于科学的一种反映现实的特殊手段。即根据现实生活各种现象加以选择、综合所创造出来的具有一定思想内容和审美意义的具体生动的图画。……由于各种文艺作品塑造形象的材料和手段不同,形象的构成和特点也不相同;文学用语言来塑造形象,音乐用声音来表现。它们的特点是具有间接性;戏剧除语言外,还借助动作来表演,绘画运用色彩、线条来表现,因此戏剧、绘画的形象具有直观性。”[5](P1982)
《辞海》中关于“形象”的第一条解释源于文字表面的意义,指生活中人和事物的形体面貌,具有视觉性和直观性。第二条解释是指在造型艺术(绘画、雕刻等)和叙事文学(小说、戏剧等)中,艺术家和作家所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等于生活中的形象,它的含义比生活中的形象更丰富、更复杂。与本文论述的“形象”更为贴近。同时强调不同的艺术门类,需使用不同的“材料和手段”,譬如:音乐塑造听觉形象,以特定音符的排列组合形成乐曲来表达情感、陶冶性情,是音乐对生活中的声音所做出的抽象处理;绘画塑造视觉形象,通过构图、线条、色彩等凝结成艺术作品来传达思想情感并使人产生审美愉悦。绘画和音乐两种艺术形式因此区别开来,其他艺术形式概莫能外。就戏剧形象的构形材料而言,并不像音乐、绘画、文学等艺术门类那样单一,其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诸多姊妹艺术的元素和特点,既有视觉形象、听觉形象,还有文学形象,它们综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我们称之为综合形象。
从地理位置看,我们会从人类多样化的戏剧形态体系中抽绎出三种古老的戏剧文化样式:一种是出现在西方的古希腊戏剧,两种是出现在东方的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这也为后世东西方戏剧形态的对垒拉开了历史的帷幕。随后,东西方戏剧艺术在原始宗教意识的驱动下跨越了历史的障碍,以其象征性和拟态性的表演形式不断变异与繁衍,最终在舞台形式、戏剧观念和审美形态上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并且这种差异日益突出和明显。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摹象戏剧雄踞西方舞台两千年余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近百年来迅速崛起的欧洲写实话剧;印度梵剧的演出传统已经中断,日本能乐却始终与中国戏曲之间绵延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如此,戏曲舞台的意象创造实至名归地成为东方戏剧的象征。喻象戏剧独树一帜,是近百年来产生的以“荒诞派为代表的”现代派戏剧,因其强调主体精神,力图摆脱物象的禁锢,而被视为摹象戏剧的衍生物、对立物和异化物。因此,意象戏曲和摹象戏剧成为东西方戏剧的主体。
以我国的意象与西方的摹象作比较,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的一段论述,对加深两者的认识有所助益:“诗的想象,作为诗的创作活动,不同于造型艺术的想象。造型艺术要按照事物的实在外表形状,把事物本身展现在我们面前;诗却只是诗人体会到事物内心的关照和观感,尽管它对实在的外表形状必须加以艺术处理。从诗创作这种一般方式来看,在诗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这种精神活动的主体性,即使在进行生动鲜明的描绘中也是如此,这是和造型艺术正相反的。”[6](P103)其中,“诗的想象”象征着“意象”艺术,而其他“造型艺术的想象”则指代“摹象”艺术,可以看出,即便在最终的艺术形象中都融入了创作者自己的主体情志,但意象艺术的表现和摹象艺术的再现是完全对立的两种美学观念,也是艺术家创作的两种不同方式,具体说来两者的区别有以下两点:一、两者达到统一的方式不同,是指创作者对客观物象进行艺术加工程度的不同,不言而喻,意象艺术中的“物象”完全是由艺术家的“意”来主宰,而摹象艺术中的客观物象是位于首位的,“意”不允许超越客观物象进行夸大变形。二、较之摹象艺术,意象艺术更具多义性。当然摹象艺术也要讲究内涵丰富,但是其“意”的指向性是相对固定的,在理解和把握的过程中不易产生歧义。但是意象艺术则不同,起主导作用的是创作者“精神活动的主体性”,由于每个艺术家拥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和轨迹,自然生发出对客观世界独有的感受和态度,其情绪心思可以是极其强烈的,甚至强烈到用错觉、幻觉来表达自己主观的“意”,势必造成物象的极大变形。如上所言,“意”甚至可能是主观幻觉或错觉,“象”是夸张变形幻化之“象”,多义性自然也在“意”和“象”之间若即若离的审美关系生成出来,正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一旦言传,语言就会将意凝固下来。
在形象塑造过程中,我国传统文论把艺术家(审美主体)的主观意念,称之为“情志”,简称为“我”或“心”。艺术家面对的生活客体(审美客体),称之为“物象”。西方美学中也早有相关论述,指出艺术创造原则中形成的主体与客体的结合是“第二自然”,区别于未经人类改造的“第一自然”中的事象和物象。既然如此,艺术形象最基本的构成有两个方面:一是艺术家面对的生活客体;二是艺术家的主体情志。并且,艺术家主体情志的一切方面都必须与客观物象相结合起来,方能创造出或是转化成艺术形象。中西方戏剧艺术同其他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者一样,对独立于主体意识之外的客观世界都有自己独有的审美判断和情感反应,对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的关系存在不同的理解,按照舞台实际需求采用不同的形象组合方式,塑造不同的戏剧舞台艺术形象。
二、剧的自觉:摹仿说与写实戏剧
(一)摹仿说
摹象戏剧主要是指欧洲写实性话剧,为何称之为摹象戏剧?我们还要从古希腊“摹仿说”谈起。摹仿说(Mimesis,希腊文,指一物对另一物的映照或代表)是西方诗学最根本的思想,对现有资料的梳理表明,该学说的缔造者是希腊哲人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 of Ephesus,约前540-约前480与470之间)。他提出了尊重自然、尊重现实的摹仿说:“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摹仿自然。”[7](P19),树立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文艺观。此后,该学说经历了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人酝酿与推动,久负盛名的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围绕着灵感说、摹仿说等焦点问题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体系,并使各种文艺理念得以阐释乃至争论,成为古希腊艺术理论的两座高峰。但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诗论家、美学家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首次构建了系统的诗学理论体系,并提出“艺术所摹仿的决不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是现实世界的外形(现象),而是现实世界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即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8](P60)成为“摹仿说”的集大成者与定型者。在亚氏看来,艺术的目的绝不仅在于忠实地临摹自然的对象,而在于创造艺术形象,正是摹仿的手段、对象和方式不同,产生并区分出不同种类的艺术。
以戏剧为例:“戏剧”的希腊文“Drama”一词,含有“动作”的词源意义,故戏剧的本义指动作摹仿。这种建立在亚氏“摹仿说”基础之上的戏剧本质论,给西方人埋下了“以戏剧为生活的再现”的戏剧观念,形成了文艺注重和强调真实的价值取向。众所周知,西方的文化艺术之源是古希腊,而戏剧艺术也出现在这个时代显然不是巧合,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进一步指出了希腊戏剧始于公元前6世纪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的祭祀活动,演出内容逐渐脱离宗教仪式的羁绊,过渡到穿插其他内容的悲剧或喜剧,具备了我们对戏剧理解的全部要素:1.角色装扮;2.行动模拟现实情境;3.诗化代言体表演形式,[9](P55-57)这三要素触及到戏剧的本质——动作、语言以及人物内心的摹仿。我们看到,延续了300余年的古希腊戏剧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戏剧文学剧本、完备的戏剧理论体系和雄伟的剧场建筑,其后古罗马承接了戏剧繁盛的接力棒,绵延600余年,于公元4世纪沉溺消亡,唯有一线余脉冲破黑暗的中世纪去迎接文艺复兴的曙光,此后的戏剧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形成了现代话剧、歌剧、舞剧三态分化。可见,西方戏剧从一开始就是以悲剧和喜剧的两种形态出现,并产生了相应的理论,此后任何时代、流派和样式的戏剧都毫无例外地派生在悲剧和喜剧的基础之上。
(二)摹仿戏剧
人类史翻过古希腊时代那一页,中世纪是宗教剧一统天下的时代,英国的神秘剧、法国的奇迹剧、意大利的圣剧以及德国作家的鬼神剧等对古典戏剧传统的叛逆,不仅没有使戏剧艺术健康发展,反而走上了歧途。16世纪文艺复兴和科学主义时代的到来使欧洲彻底脱离蒙昧而进入理性自觉,人文主义戏剧家们重新发现古希腊戏剧艺术的魅力,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戏剧观念也得到全面复辟。作为终结古典戏剧,并开创近代戏剧的巨人,莎士比亚以30余部戏剧把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艺术推向高峰,在历史剧、悲剧、喜剧三大类别的戏剧实践活动中对亚氏的“摹仿说”予以回应,让人们看到了“艺术是对人生摹仿”,这一完全区别于古代戏剧的全新模式,被后人盛赞为“生活的镜子”。同时我们也看到,理性主义的基因早已在古希腊文明中孕育,成为西方文明的底色,文艺复兴后期人们开始普遍接受和运用解析式的理性思维方式,极力推崇把现实世界用数学图式进行解构,戏剧同样被分解为纯粹的单项,各种艺术手段和因素彼此走向分离,音乐、舞蹈的元素逐渐划归为歌剧、舞剧的范畴,仅留下对话和接近生活的形体动作作为西方戏剧主要的表意符号和表现手段。
15世纪初,意大利人发现了透视画法的数学法则,并将此原理运用到绘画中获得了极大的景深感,同时这也深刻影响到了现实的戏剧舞台。具体说来,古希腊戏剧与莎士比亚的戏剧均缺少舞台布景,演员表演不受具体场景的限制,时空的自由转换依赖舞台语言和行动来完成。当写实性舞台布景出现在镜框式舞台上,这无疑对舞台样式和舞台表演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戏剧表演上体现在虚拟性、程式性、装饰性的表演被剔除乃至淘汰,在戏剧创作理论上则促成“三一律”戏剧原则的产生。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家依据时代标准,在亚氏对悲剧提出“情节整一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引申出“时间整一性”和“地点整一性” 。当然,新古典主义戏剧在恪守“三一律”这一创作规律的情况下,的确促进了戏剧创作愈加规整化,创造出一批优秀的剧作,如高乃依的《熙德》、拉辛的《费德尔》、莫里哀的《达尔杜弗》等。但是极端遵循某个理论或规律,就会将其变为谬论,时间与地点的不可移易性势必成为创作者的镣铐,对此,古典主义戏剧并非没有任何的质疑和抵抗,代表作家高乃依本人就不尽恪守这一准则,他在《论三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一文中立场鲜明地表示,某种程度上该准则束缚了剧作家的观念和手脚。18世纪浪漫主义思潮中涌现出众多的作家和理论家对“三一律”提出尖锐的批评,代表人物雨果指出“自然和艺术是两件事”,“戏剧是一面反映自然的镜子”,避免“平面镜”式的映照,采用“凸透镜”式的聚光手法去塑造熠熠生辉的艺术形象。但“三一律”的原则在批评与质疑声中,依然支配了时代和社会对戏剧创作的认识,甚至以一种“更近自然”的舞台方法,把浪漫主义引向充满矫揉造作和技巧主义的“佳构剧”。
也是在摹仿说的影响下,现实主义戏剧把浪漫主义戏剧的浪漫遐想拉回到实际生活之中,现实主义的艺术理论最早现于司达汤的《拉辛与莎士比亚》这篇美学宣言,就戏剧艺术而言,它要求抛弃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并把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并得到证实的一切都生动地呈现在舞台上来反映生活的真实,这实际就是艺术摹仿自然理念的翻版。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左拉所倡导的法国自然主义戏剧,主张戏剧创作“不必重视人物性格及其发展的描写,而只是着重从观察得到的某些事象的反映……环境的阐述越精确详尽越好;一切偶然发生的事变,违反科学的命运观念以及浪漫主义的个人感情和主观幻想必须摈弃,作品应该是社会生活片断的复本。”[10](P314)显然,自然主义戏剧是在艺术摹仿自然的创作原则基础之上,更加强调了戏剧艺术的真实性,对扭转贵族化和形式化的戏剧发展趋势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其更加细致入微的舞台写实手段难以表现人的内在真实。1887年法国启蒙运动戏剧家让·柔琏首先提出“第四堵墙”学说,将西方传统的戏剧求真观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三)喻象戏剧
20世纪初,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C.Stanislavski,1986-1938)在其演剧理论中提出“当众的孤独”“种子说”“体验理论”等观念,要求演员不再是演员本人,而是直接变成角色本身。这一代表性的论述,为演员化身角色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的同时,也导致了西方戏剧一步步走向了非假定性的极端。然而,求真的摹象戏剧观永远无法超越创作手段和工具的限制,在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之间画上等号。同时,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到20世纪前后,动荡不安的世界状态让人难以认识和把握,思想界也呈现出一派混乱的局面。现代人面对这纷繁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现象,感到失魂落魄与空虚绝望,一种普遍的精神危机积蓄孕育,最终酿成了现代主义的大潮涌起。于是,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体现在戏剧舞台上,就是要求对于人的意志、直觉、本能、潜意识进行体现,对于写实性戏剧手段和戏剧形式进行改革,提出用违背艺术本质属性的方法再现艺术,只会走向艺术的背离面。
摹仿戏剧自身在复制自然、摹仿现实的写实路子上已经走到极端,戏剧不仅不能给人提供审美愉悦和审美享受,而且舞台与生活的混同给人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厌倦感。19世纪80年代以象征主义戏剧为发端的喻象戏剧应运而生,包括其后相继出现了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荒诞主义等现代主义戏剧的思潮与流派,其最终目的都是对西方戏剧摹象理念与模式的抗衡和悖逆。从修辞学上来讲,直喻(Simile)也称明喻,指将某事某物与人们所熟悉的事物进行的一种比较,完成这样任务的手段不能是再现和摹仿,而只有表现和创造,要综合并运用所有艺术的表现手段,通过艺术想象创造客体,表现主体,创立“一种建立原形与神话、梦、超自然神秘成分上的一种戏剧”。[11](P238)荒诞派戏剧作为喻象戏剧的代表,被尤涅斯库称之为“反戏剧”或“纯粹戏剧”。它断然放弃了理性手段和推理思维,毫不理会任何传统意义上合乎逻辑的情节发展和形象塑造,所表现的正是人和世界自身的荒诞。总之,喻象戏剧的艺术家们通过直喻把握世界,达到一种抽象的荒诞效果。
现代派艺术家们把反理性原则的戏剧理念及实践活动带进了喻象戏剧,他们不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只承认“内心的现实”或“心理的现实”。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示出生活中神秘而又看不见的因素,揭示出它的伟大之处,它的痛苦”,努力寻找并揭示世界和人生表面和外观之下的真实。尤涅斯库说,他的方法是让舞台道具说话,把行动变成视觉形象。喻象戏剧在“物”与“我”的关系问题处理上,力图忽视、背离、摆脱客观物象对创作者主观情志的束缚,各种视像化的直喻成了表现主体的“我”最常见的舞台原则和创作方法。然而,就像荒诞派戏剧家所强调的那样,他们只是通过一些全新的手段和方式去表现“一种不可表达的真实”和“人在毫无意义的世界里没有幻想的真实”,无论是怎样的“虚无、悲观、荒诞,它们也毕竟表现的是一种真实”。[12](P239)因此,喻象戏剧其本质上具有写实戏剧的基因。
三、诗的精神:意象说与意象戏曲
东方文明中诞生的另一古老而成熟的戏剧样式——中国戏曲,在其孕育、生成、发展、成熟的过程之中汲取了众多审美文化因子,形成了蔚为大观又形态独具的艺术样式。它曾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村坊百姓情感的沉醉和生活的寄托之地。然而,这绝不是说戏曲无所不包就丧失了自身的本质属性和本体意识,施旭生提出,“特别是在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戏曲艺术本体曾被有意无意的遮蔽,或者至少缺乏一种本体的自觉,故而更需要戏曲获得一种本体的确认”,强调“戏曲并非是一种逻辑的抽象,或是思辨的产物。”[13](P15)怎样才能保证关于戏曲的本体追求不会陷入一种纯粹抽象的思辨,而是切近戏曲丰富的艺术实践呢?叶朗在谈到作为中国戏曲的典范样式的京剧时就曾指出“艺术本体是审美意象。京剧舞台显示给观众的是审美意象。换句话说,京剧舞台在观众面前呈现一个完整的、有意蕴的感性世界,一个情景交融美的世界。”[14](P186)可见,意象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和文化学范畴,具有中国艺术本体的意义,同时也是戏曲艺术审美体验中真切感悟和品位的对象。
“意象”一词最早出现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是以陶钧文思……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也。”[15](P413)概言之,即是诗人的物象,但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眼中,就会蒙上一层主观色彩,可谓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其中“玄解之宰”和“独照之匠”都是指写作诗文按照声律去下笔,观察着意象去写作的高手,“声律”和“意象”是驾驭文思最主要的手段(技术),是谋篇布局的开端。在诗歌创作中,声律和意象这两方面因素的重要性得到古今中外学者的一致认可,也可以说两者成为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根本要素。比如,美国的两个文艺理论家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和沃伦(Austin Warren,1899-1986)在合著的《文学理论》中就谈到:“像格律一样,意象是诗歌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6](P76)
与诗歌领域的声律研究相比,意象研究起步比较晚,起初很多学者认为意象(Image)这个概念是舶来品,源自于19世纪初英美诗歌意象派,是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一个重要支派,亦被认为是英美现代诗歌的一个发端,由于不满后期浪漫主义诗歌流派偏爱抽象的说理和直抒胸臆的抒情,而提出以“准确的意象”充当情感的“对等物”[17](P251-274),主张将诗人所有的感情、心绪和思想从始至终都隐匿于意象背后。主要领军人物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深受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影响提出“诗歌意象”理论,他明确地指出:“不把意象用于装饰,意象本身就是语言,意象是超越公式化了的语言的道”。[18](P234)他在剖析汉学家菲诺罗萨的汉诗笔记的基础上翻译和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并结集成《神州集》(1915年出版),唤起英美诗坛对东方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关注。此后数年掀起了翻译中国诗歌的热潮,比如,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 的《中国诗歌一百七十首》,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的《松花笺》等。可见,欧美意象派诗歌的兴起,与我国古典诗歌意象的表现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意象”这个概念不是舶来品,而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它是一个在中国文化演进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充实和更新的审美范畴,其原始思想来源可以一直上溯到《老子》和《易传》。《老子》二十一章中讲到了“象”:“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19](P96)老子心目中的“道”显然是一个超越人感性经验的精神之物,但并不意味着“道”是彻底的虚无,是指存在于冥冥之中能够决定世界万物发展规律的客观规律性,只有对“道”体悟至深的人方能感受到不以具体物象存在的恍惚之“象”。《韩非子》的《解老篇》对老子的上述阐述做出更为深刻的解释:“人希见得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20](P174)韩非子通过人们借助“象之骨”去主观臆想所得“大象”的形象,来解释比喻老子所说之“象”的不凝固性,想象是受人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所支配,而脱离具体事物的局限与拘束,一千个人头脑中会想象出一千个“大象”的形象,甚至同一个人也会因其自身想象的不稳定性映照出不同的“大象”之形。另一思想来源是《周易·系辞上》中:“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已尽其意。”[21](P199)其中“立象以尽意”是指圣人在观察世界万事万物之时体悟到了宇宙发展的根本规律和最高道理,却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局限性,而采用立“象(卦象)”的方式加以表达 ,所言卦象则是“意(圣人思想)”与“象(图案排列)”的一种结合,实际上是人们早期思维中的意象。
东汉时期的王充在《论衡·乱龙》中首次将“意”和“象”合为一个词,对于意象内涵的发展也做出了贡献, “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22](P16)熊头、麋头、虎头、豹头、鹿头、豕头这些依次递减的箭靶显然也不是暴虐无道的诸侯形象,已经超越了自己形象本来的意义,既指代权势地位不同诸侯,又象征征服者的身份、地位和权势的高低。《老子》中描述心中“道”之“象”始终未给人们一个可供把握的形态,《易传》中提供的“卦象”是一个抽象化的符号,而在《论衡》中的“意象”完全可以用现实之中的事物来取代,只是物象已不再是事物本身而已。就意象的概念内涵来讲,既有恍惚无状形而上的“道”,亦有实体具象形而下的“器”,其内涵演进的结果同时还在于,意象这个概念从哲学领域进入文学艺术的领域之中。
正是因为“夫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歌曲,则歌曲乃诗之流别”[23](P6)的发展趋势,让戏曲完成了由“诗(案头之曲)—剧(场上之曲)”这一质的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对戏曲舞台意象创造提出许多要求与限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从外部形态来看,戏曲表演的最高境界归结为“念唱和做工、舞蹈和音曲”的“融而为一”[24](P72)。诗、歌、舞同台是其本质特征和魅力所在,与之共生的各种单项艺术:音乐、舞蹈、说唱、杂技等因子纳入戏曲的磁场之中,逐步造就其舞台手段综合融通,舞台形式畅游通达的戏剧形态。二、从内在结构分析看,戏剧形象出自于戏剧表演对戏剧文本(诗、词、曲)的转换,在以“意”为主导,以“象”为基础的艺术创作规律的引导下,以演员表演为中心,更为准确的说是以演员的情感表达为需求,随意驱使多种综合融通性的舞台艺术手段,而不受现实生活情境的限制。这就要求创作者不仅要把握人物外形,更为主要的是去体验人物的心理特征,并将自己的情感融合在人物的内心世界之中,对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内在精神意态的把握上。三、从审美原则出发,正是戏曲舞台表现中的虚实相生原则,既讲“摹写达于极致,完全进入所扮演角色中去”的自由境地“不似位”,也强调舞台动作要注意形式美感,不等同于生活动作,所谓“演勇悍的风体”要“保持柔和之心”,“演优美的做工戏”要“保持强的心”[25](P85,86),才得以对客观对象进行随心所欲的夸张变形处理,化为人们所认同的意象表现的手段和方式(强烈装饰性的程式化动作),达到直趋其神的舞台效果。
翁偶虹先生在《梅兰芳的意象美学意识》中对影响了戏曲上千年的“意象说”有这样的论述:“他的造像之始,不只立象,还要立意。不只塑形,还要塑神;既立客观之象,又立主观之意;既不是对实象的摹仿,又不是主观的幻影;所谓立象尽意,意赖象存,象外环中,神形兼备。这样造象,是掌握了中华民族的美学意识——意象美学意识。”[26](P135)作为一种独特的戏剧形象塑造方法,戏曲意象创造离不开富有寓意的“物象”,更离不开蕴涵了艺术家主观意念的“心象”,最终则集中表现在“意象”的体验与感悟上。因此,独具异彩的意象戏曲,它既不同于西方戏剧写实主义的摹象,也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喻象,其特有的艺术手段、表达方式和创造规律,使得中国戏曲审美与文化带有鲜明而深刻的中国文化印记,是戏曲真正的生命价值之所在。
结语
综上所述,自亚里士多德提出以“戏剧为生活的再现”作为艺术追求之后的两千余年里,西方戏剧艺术经历了一次次历史的飞跃:从人文主义戏剧的大放异彩,古典主义戏剧对戏剧真实性强调到极致的同时也达到了艺术的高妙境界,到浪漫主义戏剧不再停留于如何把握现实世界的客观性,而指向人类丰富的自我内心情感世界,再到现实主义戏剧通过具体的舞台形象再现社会的生活和斗争,直至标新立异的现代派戏剧实验时代的到来。或许“摹仿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某种先天性不足,随着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日益尖锐,戏剧与真实人生的隔膜开始暴露。无论是摹象戏剧还是反摹象的喻象戏剧,其本质都是“物”与“我”关系的对峙,西方戏剧在理性主义道路的尽头遇到了难以跨越的鸿沟之后,古老的中国戏曲以其奇特的舞台方式发出神秘的召唤与启示,其在“物”与“我”契合交融的状态中创造出的艺术形象——意象及其美学追求,得到了世界剧坛的体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