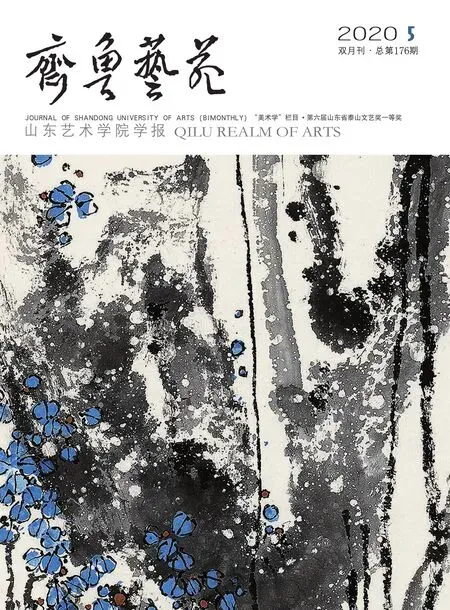“崇宋拥元”
——论《顾氏画谱》的收录原则
陈 煜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前言
顾炳,字黯然,号怀泉,浙江武林人(今杭州),是明代院体画家。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由顾炳摹绘的《顾氏画谱》在杭州双桂堂初刻刊行,同年又经顾三聘、顾三锡校稿后再次出版。十年后,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龚国珍又重新校稿,再版发行,可见该书在当时亦属于畅销书系列。《顾氏画谱》是以时间为序,收录了自晋朝至明朝万历年间活跃画坛的画家106人,人各一图,并请当时名公,于每幅插图的背面书写画家小传。
目前学界对《顾氏画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像的复制价值。简言之,《顾氏画谱》的编撰方式和图像作品,不仅成为了同代人乃至后世模仿的对象,也为一些财力许可而对艺术知识有追求的人,提供了了解绘画知识的渠道。[1]不过,就现有研究看,很少有研究者注意到《顾氏画谱》的收录原则,即画谱收录了哪些画家,收录标准是什么,收录目的又是什么。
《顾氏画谱》收录最多的是明朝画家,共42人,其中有吴门画派画家19人,院体和浙派画家18人,师承不明者5人。对于收录这些画家的目的,书中序言写道:“画家初学,益鲜窥古作者之真,而日堕恶道,于是焉有复古救时之虑者,为之象其模范而设其典刑,此吾友顾炳氏画谱所由辑也。”[2](P5)也就是说,《顾氏画谱》收录的这些画家,是在建议同时代的画家应当学习哪些正确的先辈典范。然而在16世纪末,《顾氏画谱》刊行前,继承宋画传统的院体和浙派画家已经到了人人质疑的地步,尽管尚有其它意见发挥的余地,但当时的人们更加推崇的是吴门画家和元画传统。《顾氏画谱》大量收录吴门画家,无疑是在迎合当时的受众群体,但又为何大量收录院体和浙派画家?
一、宋人遗风:浙派、院体的画学传承
据笔者统计,《顾氏画谱》收录院体画家16人,包括商喜、边景昭、李在、孙隆、林良、戴进、吕纪、钟钦礼、朱端、张珍、王延策、杜堇、王乾、周臣、唐寅、仇英。浙派画家6人,除蒋嵩、张路以外,戴进、吴伟、钟钦礼、朱端都曾入画院供奉。也就是说,画谱收录院体和浙派画家共计18人。本文之所以将院体画家与浙派画家一起论述,是因二者在画学传统上属同一源头。[3](P27)
院体画家通常是指在宫廷以画奉职的画院画家,不过民间亦有师法南宋院体者,由此形成了明朝院体之别派,如杜堇、王乾、周臣、唐寅、仇英、张珍等。明代画院盛于宣德至弘治年间,主要继承了两宋的院体传统。可以说,明代的宫廷绘画,无论是山水、人物、花鸟及其它画科,画法和风格意蕴或多或少都有两宋院体画风的痕迹。这种现象既与明初统治者政治诉求和审美趣味一致,也与明前期入画院供奉的画家多来闽、浙地区相关。由于南宋都城设在杭州,因此浙、闽两地,自南宋以来,便形成了以传承南宋院体画风为主,并吸收李郭派特色的区域画风。当这些画家进入画院后,元代被抑制的院体画风得到复苏,而他们所操持的南宋画风,也就成为了潮流。
明画院鼎盛时,浙派创始人戴进和弟子吴伟,都曾入院供奉,画风深受院体绘画影响。如戴进融南、北宋为一体的追求,以及吴伟工谨的白描技法,显然深受宫廷绘画的熏陶。[4](P108)他们后来在院外建立浙派,同样主宗南宋院体画风,这种师承关系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追随者。浙派一词最早出现在何时已无从可知,目前学界多认为是在明末,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云:“国朝名士仅仅戴文进为武林人(杭州),已有浙派之目。”言论一出,浙派之名由此确定,而戴进也被推为浙派之祖。由此观之,浙派概念虽然始于地域性,因戴进是浙江人,但它“同时又是一个画风概念,是由画法技巧与艺术风格师法南宋院体的画家群体。”[5](P48)
正德以后,宫廷院体和浙派绘画逐渐走向了衰落。促使院体和浙派绘画衰落的因素有很多,不过,来自文人的贬低是院体和浙派画家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嘉靖二十年(1541),在《中麓画品》中,李开先对宫廷院体花鸟画的评价,一改过去褒扬而代之以贬抑。书中批评“边景昭如粪土之墙杇以粉墨,麻查剥落无光营坚实之处”,“林良如樵背荆棘涧底枯木匠氏不顾”;他还提出了“画有四病”,即僵、枯、浊、弱,位列其中的多是院体画家,如边景昭、林良、吕纪。[6](P914)这与永乐年间,解缙赞边景昭“当代边鸾”,景泰至弘治年间,萧镃、卞荣、丘濬赞林良画的“天趣”、“善画天下无”形成了鲜明对比。[7](P207-219)隆庆三年(1569),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表达了对院体、浙派画家的轻视,他不仅将明代院体画家列入二流,还直言蒋嵩、张路的画“犹具辱吾之几榻”。[8](P193-195)
除此之外,由于浙派画家在继承南宋院体的基础上,着重发展了笔墨强劲的一面,因而作画风格简劲豪放,透露出一股阳刚之气,这有违于文人画家所推崇的蕴藉含蓄之美,也引发了“正统”文人和理论家的猛烈抨击。嘉兴文人项元汴在《蕉窗九录》中,就将浙派画家,如钟钦礼、蒋嵩、张路等,冠之以“狂态邪学”的污名。[9](P41)持类似观点的,也包括浙江地区重要的鉴赏家,如高濂、屠隆等,甚至在《顾氏画谱》中,都记载了吴人以“浙气”一词,嘲笑戴进等臻于古妙的画家,画谱写道:“吴中以诗字妆点画品,务以清丽媚人,而不臻古妙。至姗笑戴文进诸君为浙气。”[10](P136)
二、拥元抑宋:浙派、院体的画坛困境
需要指出的是,《顾氏画谱》提及的“吴中”,其实是苏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古称,亦称“吴门”,“吴门画派”的名称正是由此而来。吴门画派崛起于正德年间,嘉靖以后,逐渐取代了浙派和院派成为了画坛主流。据笔者统计,《顾氏画谱》收录吴门画家19人,包括王绂、夏昶、沈周、陶成、文徵明、谢时臣、王毂祥、陈淳、文伯仁、朱贞孚、陆治、鲁治、钱毂、文嘉、陈栝、周之冕、孙克弘、莫云卿、董其昌。有明一代,凡临摹自唐王维以降,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米芾、米友仁、赵孟頫、高克恭以及黄公望、王蒙、吴镇、倪赞者,多为吴派画家。顾炳将以上14位画家全部收入画谱,显然对吴门画派的画学师承也有清晰的认识。
吴门画派推崇元画,这股鉴赏风气,在明初院体画风流行时就已经开始酝酿发酵,经由明中期吴门画家的大力学习后,元画逐渐成为众人追捧的对象,再加上徽人在书画市场上的推波助澜,元画热的局面终于变得势不可挡。[11]嘉靖以后,又有董其昌、陈继儒等学者辈出,绍沈、文之绪,将先辈的拥元态度发扬下去,而且他们还用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元画的收藏和学习中。其实早在隆庆二年(1568),这股由吴派画家引导的元画热,就已经让偏爱宋画的王世贞感叹“几令宋人无处生活”。
16世纪末,当吴门画派成为画坛主流后,文人对沈周、文徵明以及元画的热爱与模仿,促使一些论画言说——画论和画评——在托举吴派画家的同时,对院体、浙派画家,以及南宋院体传统,抱之以贬斥的态度。隆庆三年(1569),松江文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就提出了画学“正脉”与“院体”之分,他认为,所谓画学“正脉”是指荆、关、董、巨、李、范及李唐,而南宋的马远、夏圭则被排除在“正脉”之外,何良俊批评他们“只是院体”,未能做到“笔力神韵兼备”。[12](P193-195)
万历二十二年(1594),詹景凤也提出,“文人学画,须以荆、关、董、巨为宗,如笔力不能到,即以元四家为宗,虽落第二义,不失为正派也。若南宋画院诸人及吾朝戴进辈,虽有生动,而气韵索然,非文人当师也。”[13](P161-162)到了董其昌时代,一套更加清晰的画学传承已被整理出来。董其昌认为王维之后的荆、关、董、巨、李、范为画学“嫡传”,李公麟、王诜、二米、元四家为董、巨“正传”,而李思训以下的赵幹、赵伯驹,以及南宋四家——李唐、马远、刘松年、夏圭,则是“非吾曹当学”。[14](P174)可以看到,由文人主导的论画言说,一直试图强化一个理念,即将南宋院体与画学“正脉”、“正派”或“嫡传”区分开来。
事实上,早在宋代,当稳定的宫廷画院制度催生出一种特有的院体风格后,以苏轼、米芾为首的文人们在提倡文人画的同时,就开始有意识地将文人绘画与隶于役事的职业画工的绘画区分开来。[15](P71)宋人邓椿在撰写《画继》时,已将士大夫画家与职业画工分开叙述。南宋灭亡后,文人画在赵孟頫的提倡与发扬下日趋兴盛,对院体绘画的鄙夷开始在元人所写的画史或画论中流露出来。夏文彦的《图绘宝鉴》就多次使用“无一笔院体”来表示他对某一位画家的赞赏。[16](P847-893)到了明朝末年,士大夫画与院体的对立,已演变为将南宋院体视为绘画传统之“不可学”的代表。
三、崇宋拥元:画学典范的树立
对于明代的画论或画评而言,宋画与元画孰优孰劣,一直是它们讨论的话题。而选择学习宋人画风或是元人画风,则是明代画家所必须面临课题之一。由于明代画坛提倡仿古,号为名家者,其画要皆有所师法,即画家需要借助临摹古人的方式学习绘画。当他们选定了临摹的对象,大体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学习内容。如此,明人在评价作画风格的好坏时,所依仗的便是画家学习了哪些先辈典范。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就曾批评沈仕、陈鹤、姚一贯“初无所师承,任意涂抹,然亦作大幅赠人,可笑可笑”,足见明人对学习先辈典范的重视。[17](P193-195)
不过,明代的画论家,在建议同时代的画家应当遵循哪些正确的先辈典范时,言论中往往掺杂着个人的好恶,如以沈周、文徵明为首的吴门画家,他们在临摹古人的同时,逐渐树立了一套始于文人画家学习的权威性典范,其中,元四家就是最为卓越的对象之一。以文徵明为例,他推崇学习元画,认为赵孟頫、高克恭、元四家以及老师沈周的绘画,都远出宋代大家之上。持相似看法的,还有文徵明的好友何良俊,主张“元人之画,远出南宋诸人之上”。在《四友斋丛说》中,何良俊评价文徵明能以一名业余画家的身份,兼顾业余画家与职业画家之所长,而戴进“则单是行(即行家,意指职业画家),终不能兼利(即利家,意指业余画家),此则限于人品”,字里行间明确流露出抬高吴派,贬低浙派的倾向。[18](P193-195)
与何良俊同时期的李开先却与之相反,他在《中麓画品》中对沈周评价甚低,认为沈周的山水画“笔无法度,不能转运,如僵仆然”。[19](P108)李开先是明代推崇宋画和浙派人士之一,他将继承南宋院体之法的戴进列为明代画家之首,并视为典范,言其“高过元人,不及宋人”。16世纪末,高濂也是推崇宋画人士之一,他在《遵生八筏》中评价戴进师法宋人,近学元人,如黄公望与王蒙,甚至还胜过二人。[20](P558)可以看到,当画家撷取的画学典范分属不同的脉系时,明代的画论家似乎很难撇清个人立场,他们多持褒贬之意,要分品第、定高低。
顾炳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于是他借邓椿来讽刺当时的画论家或画评家。书中序言写道:“前贤论画定品格者,有神、逸、能、雅之悬,拔气韵者,有轩冕岩穴之辩。……今顾炳也,何人敢与于此窃师邓公寿不主褒贬之意?”[21](P21)宋人邓椿,字公寿,所著《画继》主张不分品第,且不立褒贬之意,这种画史态度也是《顾氏画谱》的收录态度。[22](P272-279)顾炳并未因自己是一名院体画家或浙江人,而独尚院画,也未争辩宋画与元画孰优孰劣,他秉持的是一种“崇宋拥元”的收录原则。
总的来说,《顾氏画谱》收录明代画家42人,除师承不明者,吴派画家有19人,院体和浙派画家18人。画谱收录体现吴门画派的画学师承者14人,另有南宋画院画家14人,包括赵伯驹、马和之、李唐、杨士贤、李迪、萧照、苏汉臣、李嵩、刘松年、夏圭、马远、马麟、陈居中、鲁宗贵。尽管在十六世纪末,继承宋画传统画家已经到了人人质疑的地步,但难得可贵的是,顾炳在树立画学典范时,坚持将宋人画风与元人画风并重,或将院体、浙派画家与吴门画家并重的收录原则,这既是对当时由文人主导的画论或画评的一种反击,也是在为南宋院体画学传承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