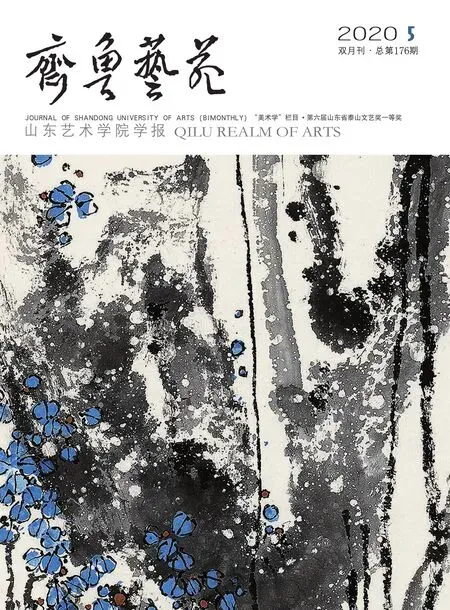《哪吒之魔童降世》:游戏化叙事、重构式人物与想象力美学
张明浩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回顾与梳理2019年上映的中国电影作品,可以发现,《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魔童降世》)可谓名利双收,成为了该年度的最大赢家。一方面,它是“电影工业美学”的现实佐证:“影片在美学层面进行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影像转化,呈现出典雅又不失‘灵气’的美学图景;‘接地气’的现实感和话题性及民间亚文化的开掘,又传达了喜闻乐见的世俗之美,共鸣了普泛性的世俗人伦之情……影片在工业层面努力进行‘工业化’、规范化、系统性、协作性的制作和运作,体现了电影工业观念……影片所呈现的‘工业化’特点与所表露的‘工业缺陷’,都为中国动画电影未来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镜鉴,悬拟了高远的未来指向”[1](P25-30)。
另一方面,基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进行文本重构与现代性改编的它,在剧作结构、叙事方式、人物塑造等方面均表现突出,为国产动画电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可借鉴蓝本:《魔童降世》基于受众以往对《封神演义》《哪吒闹海》等作品中故事建构、家庭组合的互文记忆,进行了大刀阔斧且颇具现实感、话题性的改编与文本重构。影片不同于以往类似作品中重点讲述哪吒与家庭的悲欢离合及其瞩目的生平事迹,而是把戏剧冲突集中为“反抗天命”与“自我救赎”等方面,讲述了因身份而被自幼歧视的哪吒,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突破自己、打破狭隘、回归社会、成为英雄的故事。毋庸讳言,这样的改编,无论在艺术方面,还是在商业方面,亦或是在未来中国动画电影的取材、制作等方面,都颇具借鉴意义与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析与研究。
一、剧作策略:互文叙事基础上的文本重构
德国学者卡尔-海因茨·施蒂尔勒(Karl-Heinz Stierle)曾言“任何文本都不始于零”[2](P70-80),“因此,所谓互文性是指,每个文本都处于已经存在的其他文本中,并且始终与这些文本有关系”[3](P258-273)。哪吒的故事可谓流传千古,当下受众所熟知的关于哪吒的故事内核、人物形象,多来源于明代小说《封神演义》。中国影视行业中有诸多作品对哪吒这一形象及其故事进行过书写,如《梅山收七怪》(1973)等;在动画界,则是1979年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最为经典,该片“手持火尖枪、脚踏风火轮”的哪吒“龙宫复仇”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因为关于“哪吒”的文本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才为《魔童降世》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记忆互文根基:影片取材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但在文本、人物、叙事、主题、美学等诸多方面,与受众以往的文化记忆体形成了强烈反差,进而打破了受众的定向期待视野,增加了话题性与新鲜感。
(一)“传承”与“重构”:标准剧作结构下的游戏化叙事
美国编剧布莱克·斯奈德在《救猫咪——电影编剧宝典》中,曾在剖析电影剧本后,划分出15个关键节拍[4](P57),用以指导类型电影剧作,即开场画面、呈现主题、铺垫/建构、推动/转折、争执/挣扎、第二幕衔接点、B故事、游戏时间、中间点、敌人逼近、一无所有、灵魂的黑暗、第三幕衔接点、结局、终场画面,这一电影剧作结构范本,可以在诸多好莱坞主流商业类型电影中得以印证。《魔童降世》虽非好莱坞电影,但在参照布莱克·斯奈德节拍表后,我们不难发现,该片在剧作结构上,对好莱坞商业类型电影的模式,进行了借鉴与创新。
以该片“开场画面”为例,其内容为太乙真人与申公豹两人在元始天尊的帮助下,收服混元珠,并介绍其来历,在此之中,隽永的画面呈现、高饱和的色彩,确定了影片古典美学的气韵风格,并起到了介绍故事前史的作用。再以“B故事”为例,在影片第30分钟时,影片开启了另一个故事,山河社稷图出现,哪吒进入山河社稷图,开始与师傅修身养性、学技艺,而这便是促使哪吒转折的节点,在这里哪吒不同于以往的“小魔头”,而是逐渐开始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又如“灵魂的黑暗”这一节点,在这里哪吒孩童的身份被唤醒后,因为愧疚、不甘而离开大家,前往森林,一人独处,这与节拍点作用不谋而合:即主人公处于深渊、找不到拯救自身及周围人的办法、看不到希望……《魔童降世》的剧作结构颇具好莱坞商业类型剧作特质,从“开场画面”到“终场画面”无不紧扣受众心弦,并一步一步促使其进入影片,与主人公共同经历“启、承、转、合”。与此同时,在叙事方面,影片有着经典三幕剧、英雄之旅式的叙事结构,也融合了西方“戏剧体”电影与东方“叙事体”电影的特征(1)“戏剧体”电影是指“一切进展都奔赴冲突的爆发”,而“叙事体”电影则是指“形成单元间均衡起伏的节奏”,《魔童降世》中在“生日宴”冲突爆发的设置,具有“戏剧体”电影的特征,而三幕中分别的起承转合,又形成了单元间的均衡节奏,具有“叙事体”电影特质。参见杨健. 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7:44.。无疑,正是影片对标准化剧作结构的借鉴、对经典化叙事模式的传承,才保证了受众的情感调度,加固了影片的地基、促进了影片的传播。
值得强调的是,影片在传承的同时,根据现代“网生代”受众群体的审美喜好(如游戏、梦幻等)进行了“游戏化叙事”[5](P31-34)的尝试,此叙事方式亦为“影游融合”“既电影、亦游戏”式跨媒介叙事(2)陈旭光教授曾提出“跨媒介叙事”的概念,此种叙事方式形成了“既电影、亦游戏”的叙事美学。参见陈旭光,李黎明. 从《头号玩家》看影游深度融合的电影实践及其审美趋势[J]. 中国文艺评论,2018,(7):101-109.的重要方式。此种“影游融合”叙事模式,表现为人物设计、场景设计的游戏奇观化[6](P31-34)与“游戏线性故事”[7](P155)设置,它不但可以满足受众视觉奇观性想象的需求,而且可以使受众体验到“过关斩将”的游戏快感。如《白蛇:缘起》便“具有游戏化的场景设置”[8](P116-120),而《魔童降世》更是在场景制作、故事讲述、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了“游戏化叙事”的尝试。
首先,从影片人物来看,人物(角色)作为影片叙事过程中的关键,具有连贯叙事、代入受众等方面的作用,而动画电影的人物天然与游戏中角色有着密切联系:同作为技术生成的三维虚拟体,并且在形态、动作等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影片在人物外在造型、人物动作、人物服装变化、人物技能等方面体现出了“影游融合”的特点,而这些小细节又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影片总体的游戏化基调,成为影片“游戏化叙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是影片中形色各异的人物造型,给受众一种玩家选择角色的快感。影片开头便是太乙真人与申公豹“打怪升级”的桥段,混元珠在此似如游戏中“终极大Boss”,而太乙真人、申公豹、元始天尊则如可以供受众选择进行此次战争的角色。同样,影片中的哪吒、敖丙、李靖、李夫人等人,亦表现出不同的外在形态与核心技能,供玩家(受众)选择,如果受众选择李夫人,那么要完成疏导孩子、抵御外来入侵的任务;如果选择李靖,则要完成保护哪吒、维护陈塘关的重任;如果选择敖丙,则要承担攻打陈塘关、帮龙族翻身的任务……无论受众代入(选择)哪个人物,都可以在该片(游戏)中体会到过关斩将、完成任务、赢取奖励的快感,这无疑拓展了受众感官体验的范围,使之体会到“选角”的游戏感。
二是影片中人物的动作呈现,具有游戏的实践体验感。哪吒从家庭到街上,从街上到海边的游走过程,极似游戏玩家在“游戏中的奔跑”“选择地图”“走出营地”“走向战地”的过程。哪吒大幅度的动作,也极似游戏人物“发技能、出大招”的指示。哪吒的打斗过程,更与游戏中的打斗升级场面极为相似,如哪吒、敖丙二人最后的比拼,二人各发技能,从内到外,从手、脚到法器、技能都与“拳皇”等拳击、格斗类游戏人物的动作不谋而合……从人物行走方式、打斗程式等诸多动作中,受众都似乎会不自觉产生记忆互文、游戏文本互文,想到以往自己所玩过、所见过的游戏,并在观影过程中再次体验到游戏的刺激感。
三是影片中人物技能随服饰变化的设置,具有游戏代入感。片中哪吒从儿童时期变身到青年时期的服饰、外形、技能等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敖丙在“初遇哪吒”“抵抗哪吒”“成为反派”的各个时期,外在服装也有明显不同。李夫人居家与上战场的服装也有较大差异……影片通过人物服装变化,来进一步代表人物性格、技能的变化,而此种逻辑与游戏中的“换皮肤”“换装备”等互动性设置极其相似。当敖丙穿上“装备”“万龙麟铠甲”时,便可以抵御强攻击;而哪吒在换上“混天绫”“乾坤圈”的装备后,便可以增加技能;太乙真人在乾坤圈“法宝”(武器)的帮助下,可以压制哪吒……诸如此类通过更换“皮肤”来更改技能,通过安装装备来提升技能的设置,都较为符合游戏玩家的互动性、体验性心理,极具游戏感。
其次,在场景制作与呈现方面,和传统线性叙事电影不同,游戏化叙事的电影故事空间,更表现为一种“游戏发生的空间”[9](P31-34),在这一空间内的工具、场景等,都为触发游戏环节打下基础。导演建构的山河社稷图、陈塘关、地下龙宫等空间,为玩家(主人公)提供了一种可游戏化空间,在山河社稷图中,哪吒可以通过“笔”来改变整体内容,空间随着玩家(哪吒)的意念而变化,极具游戏化与想象力;在陈塘关内,玩家要经过各种关卡(哪吒要面对不同村民的歧视等)才能获得重生。同样,导演也在李府中设置了诸多类似的游戏类关卡,如哪吒想要出门,便必须要骗过守门的两个仙童,他故意惊吓村民及出逃李府时所选择的面具、石头等工具,以及影片中的树林、瀑布、沙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玩家(哪吒)可以用何种资源闯过关卡、触发下一步剧情,赢得胜利。此种游戏化的空间设置、工具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叙事的前进与转折,而受众也于此代入到哪吒这一游戏玩家角色之中,跟随其一起探险、成长、闯关,而其也令受众产生如游戏操作的体验感与互动感。
最后,在故事讲述方面,影片呈现出一种游戏线性“英雄闯关式”的关卡样式。影片以“魔丸转世→外逃李府→报复村民→被关画作→大战水怪→被人误解→不出家门→大闹宴会→拯救苍生→承受天劫”为故事总线,讲述英雄自我成长、自我认同的过程,亦具有“闯关”色彩。一方面,哪吒从“被偏见”到“被认可”的故事线索,本身就带有一定程度上的突破性与闯关感。另一方面,影片中哪吒收服水怪、结交朋友等支线,也具有游戏质感。在收服水怪的过程中,哪吒从村头到村尾,不断用技能攻打水怪,而水怪则用毒泡泡回击哪吒,在这一支线叙事体系内,哪吒与水怪形成游戏中的二元对立关系,并最终以玩家(哪吒)胜利告终。在哪吒、敖丙相识过程中,二人在隔离人群的沙滩(对应游戏中特定的、与世隔绝的结拜场景)相知相识,并最终结交好友,与游戏中团队生成的方式相似。此外,山河社稷图中的叙事亦具游戏风格,哪吒在画作中修身养性提高技艺,并最终接受模拟战争考核的设置,与游戏中玩家“回家修炼”的程式相似,也与单机游戏中玩家通过“人机模式”提升自己技能的设置不谋而合。纵观《魔童降世》的故事构设,主人公(玩家)不断需求认同的闯关过程与最终攻打终极大Boss、对抗天劫的环节,本身便带有游戏风格。与之同时,影片中的支线叙事,又在一定意义扩展了影片游戏世界的维度,使其实现了“影游联动”的效果。
综上所述,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影片标准化的剧作结构与游戏化的叙事创新,为其打下了坚实基础,它在传承以往哪吒故事的同时,又进行了文本重构与剧作创新,不但吸取了西方剧作模式的经验,而且加入了现代青少年受众所喜闻乐见的游戏元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二)“解构”与“颠覆”:对经典神话人物谱系的现代化、立体式重塑
在全媒体时代,人物性格是否鲜明,人物造型是否新颖独到,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动画电影的传播与发展。[10](P58-64)毋庸讳言,《魔童降世》的成功,离不开其新颖独到的人物塑造。该片在保留以往《哪吒闹海》主要人物设置的同时,对其进行了“颠覆式”塑造,此种对受众互文记忆中人物的大胆解构与颠覆性重构,无疑在打破受众定向期待视野的同时,加强了影片的传播力度。与《哪吒闹海》的人物形象、人物行动动机相比,《魔童降世》的形象设计更具现代化特质,多为立体、生动的圆形人物(3)福斯特曾在《小说面面观》中,将人物类型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扁平人物”又称性格人物或漫画人物,即自始至终人物性质单一而纯粹、平面化,甚至可以用一个句子概括其特点。“圆形人物”则是立体的、复杂多面的——“一个圆形人物必能在令人信服的方式下给人以新奇之感……如果他无法给人新奇感,他就是扁平人物;如果他无法令人信服,他只是伪装的圆形人物……圆形人物绝不刻板枯燥,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活泼的生命”。参见(英)E·M·佛斯特. 小说面面观[M]. 苏炳文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63-64.,行动动机也都有现实溯源可寻,受众不仅可以对正面人物产生认同,而且能够了解反面人物背后的心酸苦辣。
与此同时,影片在塑造反面人物时,也做了游戏化、现代性的处理。如说话口吃、做事糊涂的申公豹,因为自己“妖怪”身份被元始天尊歧视,所以才想报复天尊、自己封神,但是他每次在设计计谋时都会“出糗”,令受众哭笑不得,而其在最后时期也未曾想伤害过陈塘关百姓,并且还为避免战争屡次提醒敖丙不要前去“多管闲事”(正是因为敖丙在哪吒成魔时拯救了百姓,才被百姓鄙视,最后酿成大错)。故此,我们不难看出,申公豹也有一颗爱民之心,他也只是一个被歧视而走向报复之路的“天涯沦落人”。又如影片中的黑暗大Boss——龙王,虽极其阴险、手段毒辣,但也曾经是帮仙家打下江山的重要成员,却因人们猜疑而被封锁数年。于此而言,孰好孰坏似乎并不是导演的设计一锤定音,而是想让受众于主人公现况中细品。再拿敖丙来说,导演给这一“反派”一幅惊世容颜与温柔之心,但也却因人民的鄙视、偏见而走向末路,但最后与哪吒同仇敌忾、共迎天雷的选择,又表现出他的大爱、善良之心。亦如李靖这一人物形象,虽然爱民、护民、爱子、爱妻,但也有着偏见、狭隘之心,当他看到拯救自己的是龙族后,立刻反击并让敖丙真实身份暴露于众,此时,他把敖丙从善良的英雄一下拉到了邪恶的罪人,这无疑是压垮敖丙的“最后一根稻草”,进而直接导致了敖丙的杀戮……如上,我们似乎可以发现,导演并没有给人物或好或坏的固定形态,而是以“事出有因”的出发点塑造人物,让受众在每个人物经历中去体会角色的内在,这种塑造方式与价值观念立场,无疑是对《哪吒闹海》的一次突破与颠覆。
此外,《魔童降世》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以哪吒这一角色的塑造为例,影片保留了《哪吒闹海》原有的身高比例与出生契机等引发受众产生记忆互文的关键点,但对哪吒的总体命运、外在造型等方面进行了大胆地现代性重塑。一方面,“寻求认同”代表“网生代”受众想要融入社会的内心所想。另一方面,“乖张造型”与“反叛性格”也一定程度上意在彰显当下青少年与众不同的个性。此外,“烟熏妆”“大眼睛”等外在造型也颇具现代玩偶造型、游戏角色造型风格。此外,《魔童降世》中的敖丙、太乙真人等人也都在性格、造型等方面一反以往、颠覆受众审美,此种基于受众互文记忆的大胆创新,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影片的话题性与吸引力、增强影片的传播力、保证作品的受众数量。
综上,通过文本对比、剧作解读等方法,对影片的剧作结构、叙事方式、人物塑造等方面进行分析梳理后,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魔童降世》是基于受众互文记忆的一次充满想象力的文本重构,一方面,影片的成功与精准的剧作结构密不可分,合理的剧作节拍拉动受众情愫,进而带动了影片口碑;另一方面,影片游戏化的叙事方式充满想象力,为影片锦上添花,同时也代表了其对“想象力消费”(4)参见陈旭光. 关于中国电影想象力缺失问题的思考[J].当代电影,2012,(11):98-101. 陈旭光,陆川,张颐武,尹鸿. 想象力的挑战与中国奇幻类电影的探索[J].创作与评论,2016,(4):123-128. 陈旭光. 类型拓展、“工业美学”分层与“想象力消费”的广阔空间——论《流浪地球》的“电影工业美学”兼与《疯狂外星人》比较[J].民族艺术研究,2019,(3):113-122. 陈旭光. 中国电影呼唤“想象力消费”时代[N].南方日报,2019-5-5(7). 陈旭光. 论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力消费”[J].当代电影,2020,(1):126-132. 陈旭光,李雨谏. 论“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学与“想象力消费”[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37-47.陈旭光,张明浩.论电影“想象力消费”的意义、功能及其实现[J].现代传播,2020,(5):93-98.的实践,颇具游戏感的人物塑造、空间设置与故事讲述,使受众产生带有游戏感觉的互动感与体验感;最后,影片对以往受众互文记忆中人物形象的大胆颠覆与现代化创新也极具想象力,增加了影片的话题感与现实性,进而保证了影片的传播效果。
二、想象力美学:视觉奇观的呈现、超现实情节的设置与温情世界的营造
历经5年、60多家制作团队、1600多位制作人员、20多家特效公司团队制作……种种特质下的《魔童降世》具有一定的工业化属性,但也表现出了小作坊式生产的弊端,如协作不完善、工业化制作流程不规范等问题[11](P25-30)。同时,作为魔幻类电影的《魔童降世》,也是“想象力消费”(5)在互联网时代,“所谓的想象力消费,就是指受众(包括读者、观众、用户、玩家)对于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的审美欣赏和文化消费的巨大需求。显然,这种消费不同于人们对现实主义作品的消费需求,我们也不能以类似于‘认识社会’这样的相当于‘电影是窗户’的功能认知来衡量此类作品。在互联网时代,狭义的想象力消费则主要指青少年受众对于超现实、后假定美学类、玄幻、科幻、魔幻类作品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互联网新媒介时代下,“想象力消费”类电影具有四种形态:其一是具有超现实、“后假定性”美学和寓言性特征的电影;其二是玄幻、魔幻类电影;其三是科幻类电影;其四是影游融合类电影。参见陈旭光. 论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力消费”[J].当代电影,2020,(1):126-132.类电影的力作,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窥见并再次论证魔幻类电影“想象力消费”的具体策略:一种是满足受众外在奇观化审美需求的想象力美学呈现与具有“超现实”“无中生有”等想象力特质的情节、形象设置;一种是满足受众内在心理化需求的“情感共鸣式”想象表达。(6)参见陈旭光,张明浩. 论电影“想象力消费”的意义、功能及其实现[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5):93-98.
(一)想象力加持下的奇观异境呈现: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影像转化
《魔童降世》在立足传统、发挥想象力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如意境美学、写意精神、乐舞精神等)进行了现代影像转化[12](P25-30),并通过营造一幅幅视觉奇观与幻想灵境图,彰显出了“想象力消费”的外在形式策略:满足受众外在奇观化审美需求的想象力美学呈现。
首先,影片为受众营造出了一幅幅飘逸灵动、鸢然而深、并且充满想象力的意境空间图,呈现出一种“天人合一、虚实相生、情景交融、时间空间化的意境美学精神”[13](P11-18)。影片“开场画面”便给受众一种“宁静致远”式“悠然见南山”之感,在大远景、高饱和度的视野下,在对称型、开放式的构图中,受众仿佛立足于仙界、脚踏祥云,前方是层峦迭起的山峰,后景是一望无际的云层与漫天灿烂的霞光,实可谓给其一种虚实相生、天人合一且颇具“霓为衣兮风为马”的体验,在营造典雅之境的同时,表达出了其精妙绝伦的独特想象力与创造力。
自“开场画面”勾勒出影片整体基调后,淡雅、幽深并且颇具“桃花源”质感的陈塘关便展现在受众面前,伴随着CG长镜头与摇镜头,位于山水之间、立于彩霞之处的地形图呈示于众。在此之中,村民生活井然有序、周边环境宁静悠然、建筑质朴大气,似“清明上河图”一般热闹非凡,却又似“山水图”一般宁静自在,静与动之间表露出一种“时间空间化”之感,呈现出天人合一、情景交融之势。另外,影片中的“山河社稷图”亦充满灵动之气,显现了导演丰盈的想象力与卓越的创作才能,在哪吒“入画”后,导演先以远景牵引出哪吒面前雄伟壮阔、高雅别致的宫殿,表现了哪吒与画作融合的意味,后用拉镜头,为受众呈现山水相间、淡雅别致的画作全貌……哪吒与画作于此融为一体,而其在此之中的修行、玩耍也别有一番天人合一、物我相融、虚实相生之感,而蕴含着意境美学或写意精神的传达。除此之外,影片中阴森黑暗的龙宫、余辉照耀的海滩等场景,都与主人公相辅相成,形构了动静结合的二元质感,为受众营造出一幅幅意境悠远的灵动之景,既满足了想象之需,也彰显了影片清新雅致的美学特质。
其次,影片总体基调呈现出独特、灵动、飘逸、悠扬,并且蕴涵着些许“流动性”“运动感”[14](P11-18)的乐舞气韵。一方面,影片的构图、景别与镜头呈现出别致的流动感,而其较多运用长镜头,摇镜头也较为缓慢,在镜头流动转化之间给受众呈现出如泉水细流一般的“运动感与流动性”;另一方面,影片中的山水、草木、房屋等呈现出“线之美”,以哪吒刚入画的宫殿为例,在给人以崇高质感享受的同时,其流畅的弧度、对称的构造与四周飘逸的云层,也带来了似乎独具东方韵味的舒缓感;再以“山河社稷图”的湖面为例,湖中的山水草木,静态暗流的泉水、仰天长啸的荷叶、立于叶上的层山、飘渺灵动的祥云,都在外部形态与内里构造之处,勾勒出了一幅“清泉石上流、莲动下渔舟”的风景。虚灵的空间、流动的镜头、雅致的景别……种种特质下的《魔童降世》,不仅对中国传统乐舞气韵进行了现代影像转化,而且为受众呈现出了一幅幅、一个个灵动飘逸的图景,极具想象力与创造力,满足了受众“视听震撼,奇观梦幻”式的审美需求。
(二)情节、叙事的想象力美学彰显:怪诞、夸张、超现实、出乎意料
如前文所述,《魔童降世》呈现出一种游戏化叙事与互文记忆基础上的文本重构设置,影片夸张怪诞的主人公造型、超现实的叙事场景呈现及出乎意料的情节设置……都体现出影片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都呈现着想象力美学、彰显着想象力消费的内在策略。
首先,影片基于受众互文记忆的文本重构,体现出其独到且卓越的想象力。影片对以往“哪吒闹海”故事的颠覆与现代性改编极具话题性与创造力,一方面它从“魔王降世、收服魔丸”为故事的出发点,不但重新想象了哪吒的前世,而且二度创造了他的今生,大胆重构了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如敖丙性格、敖与哪吒的关系等),给受众以出乎意料的审美体验;另一方面,影片叙事呈现出游戏化“闯关”特点,与以往“哪吒因过失而失去生命,复活后选择复仇”的故事设置相比,《魔童降世》采用“哪吒为赢得认同,而不断突破自己、突破社会、突破命运”式的闯关设计,以出乎意料的改编,打破了受众定向期待视野,极具创新价值。
其次,影片的诸多情节设置呈现出超现实、出乎意料的想象力美学风格。哪吒“入画修行”,作为实体进入到虚拟空间,在其中修炼、嬉闹的情节,超乎现实逻辑,亦表达出一种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哲学色彩。同时,“山河社稷图”中哪吒“以笔运景”的情节设置,亦具想象力与创造力:通过一只笔便可以改编世界、移花接木、扭转乾坤……这无疑是诸多受众闲暇之想。另外,影片中哪吒敖丙共抵天雷、地下龙宫共铸万麟甲、哪吒敖丙海边相遇、李靖殷夫人共抵龙族来袭、申公豹设计陷害、太乙真人吃酒误事等诸多情节,都一反受众定向思维,超乎现实、出乎意料。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除情节、叙事外,影片中夸张、怪诞、一反以往的人物造型也颇具想象力与创造力,给受众以出乎意料的审美体验。“黑眼圈、大龅牙”的丑哪吒、“鞋拔子脸”的申公豹、“油腻大叔”样式的太乙真人、英姿飒爽的殷夫人等作为叙事的行动者与接收者,在自身呈现想象力的同时,也表现出影片整体的想象构设。
(三)温情世界的呈现与人文诉求的表达
鲁迅先生把《封神传》列为明代神魔小说一类,评论其为“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15](P187),尽管此中表现出了鲁迅先生对此类作品“自写幻想”的批判,但时至今日,尤其对于魔幻类作品而言,“自写幻想”似乎已经演化为一种叙事方法与表达方式:基于原始神话故事进行现代性转化,并借古喻今,“把人性、爱情、人与自然事物的原始情感推向幻想世界进行‘询唤’,完成大众对魔幻和超验想象世界的消费”[16](P41-44),进而表达出影片独到的人文诉求,为受众呈现出一个温情世界。《魔童降世》便是如此。
首先,影片为受众勾勒出了一个充满亲情、爱情、师生情的温情世界。受“身份之因”而饱受偏见之苦的哪吒在父母、师友的帮助下走出阴霾、重获新生的故事,本身便带有温情之意味。相对于哪吒所面对的偏见与狭隘,因其之过失而不断受村民指责的李靖与李夫人,所承受的辱骂、责怪、谣言等与之不相上下。但尽管如此,李夫人依然在妖怪入侵陈塘关时,呈现出放弃骨肉至亲时而深入骨髓的创痛,李靖也不断放下身段为哪吒求情,二者对职业、对百姓的尊重,也在无时无刻温暖着受众之心灵;当哪吒屡次闯祸回家后,二者语重心长的教导,无不流露着至上之亲情;面对哪吒的误解与反抗,二者虽表明气愤,但却多次心疼而怜惜,表面严厉的李靖甚至以身为契,代替哪吒承受天雷之刑……无论是李靖、李夫人对陈塘关百姓的保护,还是对哪吒的宠爱,都在为受众呈现出类似现代父母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一边是在外应酬、挣钱养家、处处小心谨慎,一边是在内持家、保护孩子、照顾老人、时时不敢懈怠。此种借古喻今的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在使受众感受温情的同时,已让其产生认同与代入感,呈现出影片独到的人文关怀。此外,影片中敖丙、哪吒一同抵御天雷,哪吒说服敖丙,敖丙应邀参会等设置,也在想象重构而丰满情节架构的同时,为受众呈现出了二者亦敌亦友的纯粹情感,温馨无比;同时,影片中太乙真人对哪吒的不离不弃、认真负责、隐忍宽容、精心照料也充满温情,代表着当下含辛茹苦、不畏辛劳的教师精神,亦不难让受众产生认同、达到共鸣。
其次,影片对“偏见”进行了审视与反思,极具人文关怀与现实价值。纵观影片的主要冲突,我们不难发现,把主人公“逼向梁山”的往往是大众的成见。哪吒因“魔丸”身份而自小被鄙视、被孤立,就连小朋友都对其言语攻击。哪吒在救人后被误认为打家劫舍、抢走小女孩。哪吒在出门玩耍时,被定义为出来祸害村民……被鄙视、被孤立、被妖魔化的哪吒,也曾想通过拯救人们、入画修炼等方式融入社会,但村民对哪吒的成见,一步步地让哪吒走向了深渊。一句妖怪来了,不仅刺痛哪吒的心,更指向了受众的心。同样,出生“灵丸”的敖丙,也因其龙族身份而备受煎熬,善良大度的他,拯救了即将要被哪吒毁灭的陈塘关,但只因村民得知其为龙族异类后,便对之大开杀戒的选择,引发了敖丙的报复。与其说是哪吒、敖丙伤害陈塘关,不如说是陈塘关百姓因自我的成见而引火上身。哪吒、敖丙所经历的一切,也正指向了现代受众所经历的:当下人们为赢得别人认可,而不停改变自己,甚至违背内心,社会也经常以“出身”“家庭”“学历”“背景”“过往史”等标准来评价个体。哪吒、敖丙通过自己的反抗,进行自我救赎的设置,无疑颇为契合诸多受众意图对抗不公、做回自己的情感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大众在工作、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中的压力与苦闷,给其以片刻的精神复归与解放。诚然,哪吒、敖丙通过牺牲自己的形式,回归社会、成为英雄、得到认同的设置,具有浪漫色彩,但此种温情处理,也促使身份代入的受众获得快感:“身份边缘的我,也是可以作为英雄拯救那些当初看不起我的愚昧之人的”。此中,哪吒、敖丙由“被边缘”到“被英雄”的弧度性人物设置,无疑是一种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连接和转化,也颇为符合受众想要成为“平民英雄”的未来之想象。我们可以通过此种结局设计,感受导演“期待每个生命个体得到认同、渴望每个个体成为自己的英雄”的美好期盼与人文关怀。我们更可以从此种假定中,窥见影片想象力消费的内在策略:将原始情感推向奇观异景的幻想世界进行“询唤”。
结语
就一定意义而言,作为一个具有“合家欢”性质的电影片种,动画电影的发展是颇具前景的。它在好莱坞占据重要地位,以《狮子王》为代表的诸多票房与口碑双丰收的佳作,都在直接证明发展动画电影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纵观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我们的作品,在票房和口碑等许多方面,与好莱坞相比,都有着不小的差距。但自《西游记之大圣归来》(2015)取得斐然成就后,我们便可以看出趋势,即动画电影在中国是有光明的发展前景的、是符合受众审美需求的。2019年的优秀影片《白蛇:缘起》《罗小黑战记》,尤其是《魔童降世》的成功,更是直接佐证了动画电影未来势不可挡的发展劲头。
诚然,《魔童降世》的成功具有偶然性,与2019年暑期档其他影片状况、自身排片及精准宣发密不可分。同时,相较于好莱坞动画大片的强视效、大体量、泛共鸣而言,它在体量积累和视听呈现等方面均有所欠缺。但是,所谓瑕不掩瑜,我们应该看到,《魔童降世》对于国产动画电影发展的推进作用,它的成功不但给予了中国动画电影在未来创作上的广阔空间,也给予了“电影工业美学”在未来理论建构与实践道路上的极大自信。就此而言,我们应该大力呼吁、大量创作此类充满想象力、具有奇观化视听、饱含趣味性与游戏性、满足受众认同心理与“想象力消费”需求、传递普适价值观念且拥有票房号召力与话题性的动画大片。
无疑,中国动画电影应在包容、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大胆突破、精心制作,满足互联网受众日益增长的“想象力消费”之诉求,传达中国精神与中国梦的核心内涵,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增加文化自信与自觉。笔者相信,未来国产动画电影将在践行“电影工业美学”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好,将在扎根国内的基础上,走向世界!